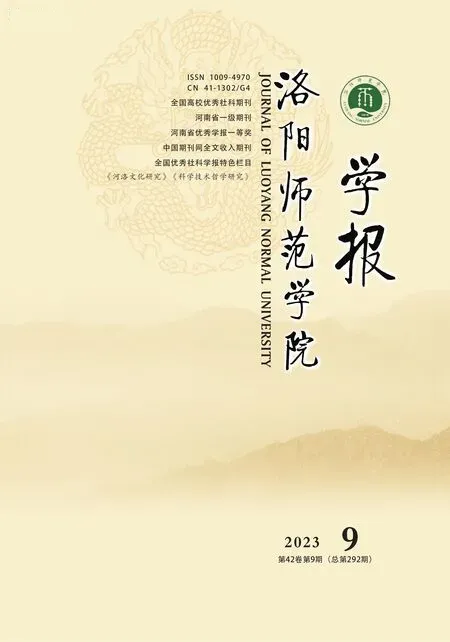乡土审美的变奏:21世纪中原剧作家现代戏创作的群体特征
陈晶晶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河南戏剧是中原文化的重要内容,21世纪以来河南剧作家群脱颖而出,先后创作出了《香魂女》《村官李天成》《风雨故园》《常香玉》《焦裕禄》《重渡沟》等优秀现代戏,屡次获得“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奖项,成为全国戏剧界成果最突出、影响最深远的创作群体之一,构成了中国戏曲现代戏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中原剧作家群”的视角,全面展开对河南现代戏的研究很有必要,既能填补河南戏剧研究中对“新世纪剧作家群”的研究空白,增强学界对河南剧作家群的认知,也能对未来中原经济区的文化建设提供重要学术支撑与实践价值。
一、观念转型下的人文内涵
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观念、文化习俗及审美方式不断变化,河南现代戏逐渐摆脱了以往农民戏剧中的固有模式,中原剧作家群接受着多元、现代文化艺术观念的冲击,表现出清晰又复杂的人文倾向。一方面,在文化气质上深受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熏染,创作观念携带传统文化浸润的人文情结,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与传统美德为己任,肩负起戏曲在新时代应有的文化担当,产生了《程婴救孤》《老子》《玄奘》《清吏郑板桥》等一批优秀的新编历史戏,流露出对传统道德、文化与政治精神的深切回顾与依恋。另一方面,在艺术观念上追求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更加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展示,力图开掘出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产生了如《香魂女》《风雨故园》《焦裕禄》《红旗渠》等洋溢着浓郁时代精神与现代文化气息的作品,在人性揭示与文化阐释上,显示出不俗的实力。
姚金成的《香魂女》作为21世纪以来河南首次获得国家“文华奖”的剧目,最成功之处便在于文化内涵上的提升,它摆脱了以往河南戏剧人物塑造简单化、类型化的倾向,力图多角度、多方面展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主人公香香是一位从传统女性角色迈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性人物,一方面她有着现代观念影响下的经商意识,抓住时代机遇,摆脱了贫苦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在思想深处仍遗留着传统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童养媳出身的她,终日饱受无赖丈夫的拳脚却不敢和心爱的人远走高飞。明知道自己的痴呆儿子无法过上正常的婚恋生活,但仍然在传统婚姻观念影响下买来一个儿媳妇,制造出另一个“自己”,造成了青年女性环环的悲剧轮回。剧作家写出了“她追求自由、幸福、美好人生的一面,也写出了她懦弱、卑微的忍受和人性被金钱奴化产生的占有欲的一面”[1]。更加耐人寻味的是,除了《香魂女》,姚金成早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归来的情哥》《闯世界的恋人》中就已塑造出新旧时代中遭遇困境的农村女性枣花、石榴,她们和香香、环环一起构成了新时期以来中原女性心灵的变迁史,更进一步探索了造成女性苦难命运的社会文化、习俗观念、伦理道德的深层文化动因,体现出剧作家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演绎着我们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心灵史”[2]。
除此之外,“乡土文化”在河南戏剧中历来是表达重点,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浓厚文化背景。如陈涌泉的《丹水情深》聚焦南水北调的搬迁移民,突破了传统乡愁的故园情结,指向了一种文化乡愁,充满着浓郁的人文意味与乐观情怀。这种乡愁所包含的美学内涵深嵌在地域文化之中,以富有本土人物、语言特色的戏剧形式体现出来。李丹霞和方小荷、夏小满、老贵爷、移民村的其他人物一样,“位卑而不失尊严,贫穷而不改气节,身小而不渺小,处下而不低下”,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发生冲突时,他们的挣扎让人伤感,他们的行为让人动容。《丹水情深》毫不避讳地具体描述了修建丹江水库大背景下人民所经受的艰难情状及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大段唱腔质朴通俗、饱含深情,浓缩了编剧多年来对农村生活的记忆与体验,在更广层面上凸显出现代人对无法回去的故乡难以泯灭的伤感情绪。“乡愁”成为一种丰富的美学符号,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当代戏剧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范式”[3]。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主题性创作倾向明显的“定向戏”中,文化内涵的深入开掘依然是21世纪中原剧作家群集体的创作取向。如《焦裕禄》的成功在于老题材出新意,在传统的焦裕禄故事中开掘出新时代的内涵,在突破传统“英模戏”高大上模式的同时,将焦裕禄悲剧性的一面并不讳言地揭示出来。焦裕禄表态“让老百姓吃不上饭,才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后,一系列措施无不显示出他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叛,在政治生涯与百姓利益之间,他选择了后者,注定要经历一系列巨大的挫折,在病重折磨中亦饱含着对家人难言的愧疚。现代戏《焦裕禄》的成功就在于他身上自始至终保存着真正的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坚定政治信念与为人民服务的情怀,尽管这种追求遭遇巨大阻力,但仍然不能使之屈服,从而使这个形象接近了西方古典悲剧人物的英雄气质与审美风格上的崇高感。这是近年来,主旋律戏曲达到的难能可贵的艺术高度,被有关专家誉为开辟了突破“禁区”的“新路径”[4],形成了新时代戏曲现代戏创作的高峰。
二、时代精神熔铸的现代品格
21世纪河南戏曲现代戏的编剧群体在创作精神上,紧扣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这集中表现在主旋律戏曲创作中,多以反腐倡廉戏、扶贫致富戏、人民公仆戏、好人好事戏为主。在弘扬时代性的同时不忘融入现代意识,洋溢着浓郁的主体精神,以精神的现代化来深入描写人的现代化。写人性,写真实、复杂、深刻的人物,成为河南剧作家群的集体追求。
河南戏曲从包公戏、张鼎戏、唐知县戏到今天的李天成、马海明、焦裕禄戏,一直以贴近群众、理察民情的政府官员为主要塑造对象。不过,包公戏到唐知县戏核心是为民做主和为官做主,当代焦裕禄戏的核心是带领百姓脱贫致富。随着权力视角的下移,《村官李天成》《重渡沟》等戏皆体现了现代底层官员体贴百姓,与老百姓儿女情长、家长里短相结合的倾向,诸如此类的平民化风格强烈的主旋律戏皆有着清晰的草根视角,注重刻画人民公仆人性的多面,不回避他们面临的真实困难,以及性格、行为上的弱点。如杨林的《红旗渠》通过杨贵和黄副县长关系的描写,鲜明刻画了主角独特、多面的性格,以及内心复杂真实的情感波澜。如杨贵祭拜拐头山的列祖列宗那场戏,立下庄重誓言:“今天借你一条路,明天还你一条渠。”他冒着断送仕途乃至生命的危险,动用国库储备粮救下几十万修渠大军的生命而被调查,此处的表演是杨贵用颤抖的手捡起吱吱留下的胭脂盒,继而发出嘶哑的咆哮,进而发疯似的丢茶杯、扯桌布,最终披着桌布瘫倒在地上无力地哭泣。通过人物两跪和两哭等动作细节,真实塑造出杨贵多角度的复杂性格和辗转内省的丰富情感,突破了传统英模的单一化形象,重塑了新时代英雄的现代人格。
此外,从地域角度看,戏曲的现代转换在河南戏剧中呈现出明显的从“草根性”向“都市化”转型的倾向。以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郑州为例,表现新郑州人的戏剧题材丰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现代戏剧目佳作迭出。郑州戏剧人的创作主体意识普遍增强,创作上更注重对现代人性、现代思潮、都市情感的深切关注,强调对深层社会哲理和人物复杂心灵世界的开掘。如王明山的《啼笑皆非》(2005)、马书道的《当代孝子》(2005)、李清芳的《跛子张的婚事》、王明山的《清风茶社》(2010)、王明山的《李祥和的婚事》(2013)、陈涌泉的《都市阳光》(2015)等一系列都市题材的作品反映了河南戏剧在题材城市化、戏曲情节现代化、戏曲人物人性化、戏曲意蕴诗意化等诸方面的创新与突破,丰富了郑州的戏曲现代戏剧目,增厚了郑州的戏曲文化底蕴[5]。
三、回归地域剧种特色的“戏曲化”路径
戏曲现代戏一直面临话剧加唱和程式化两个主要问题,即戏曲化和生活化。京剧演绎革命历史题材较好地解决了戏曲化问题,但在表现现实生活时远没有像豫剧等地方戏做得好[6]。1980年以来,戏曲舞台模式开始突破写实主义的主流框架,传统戏曲的写意方式重新复归,促使豫剧在舞台表现上将生活动作程式化,情感表现节奏化、韵律化,增强了表演的写意美、动态美和舞蹈性。在实践路径上,21世纪中原剧作家群现代戏的创作观念从20世纪90年代先锋性强烈,导致豫剧去戏曲化、去剧种化、去歌舞化的现象凸显,到2000年以来逐渐转向吸收传统河南梆子戏的特质,传统戏曲美学原则得以复归和突破,重新走进了戏曲化的实践路径。如导演李利宏用“固本求新”[7]的创作原则指导姚金成《香魂女》的舞台创作,在姚金成剧本所营造的诗意浪漫的氛围中,固守豫剧传统程式,创造了“窑变”“窑败”等戏曲歌舞,同时又设计了“喜船舞”“红灯舞”等舞蹈,通过意象化的舞台形象将剧本所塑造的环境氛围和人物心理情感具象化地传达出来。
21世纪以来,舞台的多元探索进一步影响到编剧者的剧情结构方法与审美风貌,出现了浪漫叙说、纪实戏剧、散文式结构等复杂结构。如韩枫、杨林执笔的《常香玉》用了散点透视的方式,用诗化的散文结构把镜头聚焦在常香玉人生道路的几个关键点上,大胆重组了戏剧叙事时空,实现了青年、中年两个常香玉同台表演的双线结构,极大提升了现代戏的叙事维度,整体呈现一种“剧诗”的诗意风格。同时,导演在戏剧结构走向和舞台样式的把握上,有意强化了剧本的散点式结构,形成了对戏剧舞台假定性的重新诠释和彻底运用,整体荡漾着一种诗性的气韵。
河南现代戏编剧艺术在时代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大背景下,经历了不断选择调整,不断创作革新的过程。新时期以来受到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及国外音乐剧的影响,从生活化到程式化,由写实到写实与写意并举,始终以生活为基础,以中原文化为根脉,从单一到多元,进入了理性自觉发展时期,实现了创作手法的多元融汇,舞台艺术整体性表现得以突出和强化,使河南戏曲的艺术审美迈向了新高度。《村官李天成》《红高粱》《风雨故园》《焦裕禄》等剧作在不失生活根基的前提下,以新的艺术形式,结合新的声光电技术,大胆运用戏曲假定性的时空自由和程式技术手段激活传统,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和质感。如《村官李天成》中的“拉车舞”“滑跪”“劈叉”“跪搓”“吊毛”等传统程式技巧的娴熟运用;《焦裕禄》中的“高抢背”,种泡桐的集体舞和抗洪抢险的高难度翻扑动作;《红高粱》中的担酒坛炸鬼子的身段动作;《风雨故园》中的白练缠身的挣扎姿态;《香魂女》中拟人化的钧瓷舞队等都是象征性的舞蹈语汇,蕴含着丰富的美学品格。这些都是剧作者根据人物行动的需要强化了戏剧情境,深入人物的内在精神层面,巧妙化程式为生活,既不失生活的真实,又得写意传神的内在美感,展现出河南戏曲现代戏舞台艺术的多元格局和风貌。
在戏曲音乐形式上,编剧有意强化主题性音乐段落,逐渐呈现角色化的唱腔音乐,多以“主题性音调”贯穿全剧。设计上大胆吸收西方歌剧、舞剧、交响乐的主题贯穿技法,有力促进豫剧音乐的个性化和现代化发展,这种变化影响了21世纪中原剧作家群对唱词的处理。如姚金成的《焦裕禄》,“焦裕禄”的主题音调共出现79次(含完整、变奏等形式),次生主题音调“光明行”及其变调共出现8次,通过多重暗示凝练并强化了焦裕禄的整体音乐形象。此外,拓展新的旋律材料,挖掘更多的旋律手法,也是豫剧音乐形态走向丰富多元的重要手段。如《铡刀下的红梅》利用山西民歌“交城山”主题音调作为“刘胡兰”的音乐形象[8],实现豫剧现代戏唱腔音乐材料的拓展,强化了角色个性与心理情绪。可以说,剧作家综合了时代审美的特点,“变古调为今调”,在传统唱腔基础上注入为当代观众乐于接受的内容。所选曲牌、曲调坚持“移步不换形”原则,保留传统音乐底色,用延伸、移位、转调等手法加以变化,既保持了传统曲牌的基本结构形态和旋律特征,又呈现出新的符合今人欣赏趣味的风貌。
21世纪以来,河南剧作家群的现代戏创作呈现两条鲜明线索:一是模范人物,主题性创作突出;二是贴百姓、接地气的民间情趣作品。综合以往成就,河南戏剧要探索在中国戏曲现代戏发展过程中的示范性和样本意义,那么它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多元的。比如改编外国优秀作品、加强都市题材创作、注重传统品格与程式化用,才能提炼出更加丰富的表现样式,促使河南戏剧在未来能够健康、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