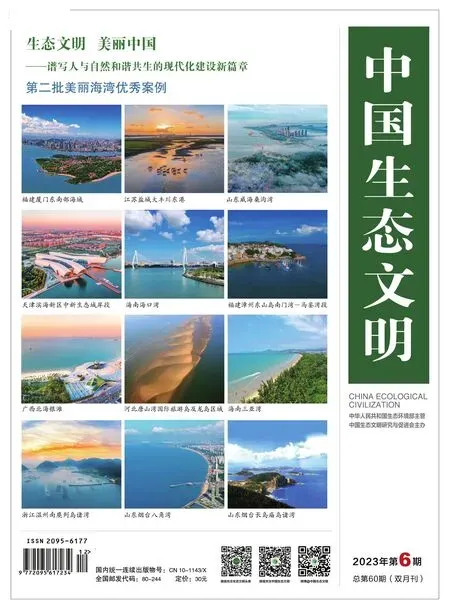生态文学时代的生态诗歌空间
——著名诗人梁志宏访谈录
□ 李景平

◇ 梁志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首届至三届理事。文学创作一级。曾任太原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城市文学》主编。出版诗集《冶炼太阳》《行走的向日葵》《俯首人间》、四卷史诗《华夏创世神歌》、长篇自传《太阳下的向日葵:一个正统文人的全息档案》等,并著有《梁志宏文集》和《梁志宏文集续编》。曾获《诗刊》年度优秀作品奖、首届赵树理文学诗歌奖、首届全国绿风诗歌奖、《山西文学》年度非虚构文学作品奖等。

◇ 李景平,中国环境报社驻山西记者站站长、高级编辑,山西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著有《绿歌》《20 世纪的绿色发言》《与黑色交锋》《报人论报》《山西之变》《走过时光》《风在心间流过》等。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环境文学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黄河》年度文学奖等。
◇无论是传统诗还是现代诗,都与自然、与生态、与环境葆有血肉一般、灵肉一般的内在联系;诗歌,无论从内在创作力还是外在感应力上,都与时代、现实、未来葆有青春一般、生命一般的天然关系。进入生态文明的时代、生态文学的时代,诗与自然生态的默契,诗与文明进程的默契,必然比任何时代愈加彰显。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塑造,为现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书写空间。
◇科技和诗歌都是想象力的产物,科技是想象力的实现,也是对诗歌想象力的触动和呼唤。现阶段,诗歌在生态危机之下显得微弱、尴尬,力量尚未发挥出来。
◇自然诗、环境诗、生态诗,不应该都是花花草草,应该有大视角、大视野、大意象、大气象、大胸怀、大胸襟。现代诗歌和现代生态诗的创作空间,也像它所面向的自然、生态、天地、宇宙一样,将会是无限的。这也许是神话和科幻给现代诗歌的新的启迪。
诗歌创作本身就像一条穿越时代变迁的河流,生态诗写作正是歌唱与批判的契合
李景平:您是较早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诗人。您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开始环境诗或生态诗写作的?
梁志宏:最早在20 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我还没有自觉的环保意识和创作内驱力,大多是日常生活或采风所见所闻引发感怀。之后,随着社会发展和舆论影响,逐渐生成了生态环境忧患意识,生态环境问题也逐步成为我诗歌创作的题材。
一是歌颂生态环境保护的诗。我最早感动于袁克良老人,他多年住在慕云山植树造林,变荒山为绿岭。我以他为原型写了百行叙事诗《老人与树》,还写了散文诗《森林组曲》。
二是揭示生态环境危机的诗。1988 年写了短诗《停水的日子》,揭示太原地下水位沉降的危机:“感觉脚下有一只巨型漏斗/会将城市漏成沙漠/直至某一天沉陷”;1989 年写了《难老泉咏叹调》,为晋祠难老泉断流而惋叹,也寄予了晋水复流的希望;及至世纪之交,我创作了《问天》《面对残桩》,是对山西省城空气严重污染和云顶山森林乱砍滥伐的反思之作。
三是重大生态环境题材的诗。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我三赴“引黄入晋”工地体验生活,创作出版了叙事长诗《河颂》,作为时代三部曲的压卷之作,是一部现代文明颂和人民颂,也是一曲解决山西省城严重水荒的生态壮歌。进入新世纪后,我开启了汾河生态诗的创作。
在生态环境诗歌创作中,我履行作为公民的生态环境责任并付诸行动。2000 年秋,我与山西作家孙涛一行,目睹娄烦县云顶山森林乱砍滥伐现象,当即以太原市人大代表和作家名义写了《莫让云顶变秃顶》一文,投书《太原日报》《山西商报》,同时配照发表。太原电视台记者赶赴云顶山跟进采访报道,引起了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及时进行了整治。
李景平:我一直关注汾河,曾提出“生态汾河”的概念。您写过数量可观的汾河题材诗歌。记得在太原汾河景区最初建成的时候,许多人赞美汾河,您却写了一首揭露汾河污染的诗,这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梁志宏:我出生并成长于太原这座城市,居所与汾河相距一箭之地。身为诗人,我自然会抒写汾河,抒发所感所思、所喜所忧,就有了热情歌赞与内心隐忧交织的诗篇。
您说的那首诗是《对一条河流诉说企盼》。其实诗里既歌颂了十里景区获得联合国人居环境“迪拜奖”,又揭示出汾河仍存在忧患。“可当我遥看,清流另一侧河道/依旧蒿草疯长污流蜿蜒/缕缕忧患与企盼,缠绕心窝”;“我企盼汾河从头到尾变清/春光千里,飞舟如梭/企盼元好问雁丘词里的雁队/剪裁秋色,年年从我头顶飞过”;“诉说企盼:不只企盼一条河流/不只停留于诉说”。这首诗只是注入了忧患意识,温和地揭示汾河景区靓丽背面真实存在的生态阴影,希望提醒并促进山水的全方位治理和保护。因为我相信,一个城市能够建成巨大的汾河景区,也一定能够治理好污染。要说有一点精神的话,这精神的实质是一种信心。
李景平:一片欢呼声中您居然写出了批评,这在您的诗歌创作和一贯的诗歌意象中,是很少见的。这个细节是否明确标志着,您的诗歌创作启动并进入一个不同的转变或反思的时代?
梁志宏:纵观我的诗歌创作历程,要说“启动并进入一个不同的转变或反思的时代”,还是应该以1982 年创作与发表《检察长的眼睛》来划线。这里称“时代”有点大,称“阶段”比较准确。创作转变和反思,主要表现在创作理念上从“应制诗人”向“说真话、抒真情”嬗变;创作主题上从一味歌颂粉饰向歌颂与批判结合转变;创作方法上从现实主义向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融递变。最为突出的表现是20 世纪80 年代后,太阳意象、向日葵意象的逐步嬗变,和诗歌创作中人性的复归及诗人主体意识的确立。
以汾河诗为例,在《对一条河流诉说企盼》之前,也曾注入过反思。1989 年的《挽汾河》中,面对“一道酱色沉重蠕动的/如茶色玻璃将白云染黑的”汾河,我并非哀挽,而是“挽起孱弱的母亲河/注入一个儿子的热血……”,表达治理汾河污染的强烈愿望。1996 年山西作家赴引黄工程采风,路上我与韩石山、贾真等驻足宁武看汾河源,写下《汾河源情思》,揭示源头一泓清泉流至省城“那衰竭的身躯,污秽的容颜”,在末节发出“汾河呵!醒来/我在源头呼唤”的声音。同样意蕴的还有《汾河与我的城市》,那是2000 年国庆节前汾河景区一期工程竣工,我坐在迎泽大桥上的庆典会场,当即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多节诗,诗中有一节展示汾河“沦为一条枯萎的污河”的现象,另一节抒写建设者“对一条河流和一座城市的双重拯救”。
我在诗歌创作中注入“转变和反思”是改革开放时代启蒙引发的,也是与时俱进一以贯之的。正如评论家孙钊在《歌唱与批判的契合——梁志宏诗歌漫评》中指出的:“漫长的创作道路,歌唱是他创作的主流方面,是他主要的表达方式,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他的另一面——沉思与批判性表达”;“赞美的同时有深深的感叹,感叹中带着忧患与批判,诗人热情的目光闪射出痛切的人文忧患与深度关怀”。对于我的诗歌创作,这个评价我是认同的。这个“歌唱与批判的契合”,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概括。正是这种辩证性,我的诗文创作体现了热情而理性的歌颂、温情而善意的批判的特点。也正是这种辩证性,改变了一些人认为我“只是歌赞者”的偏见。
李景平:汾河经过几期治理,已经成为一条延绵千里的风景带。您所批评的汾河问题也在解决。在您的诗歌里,又是怎么表现其美的?
梁志宏:近年,我写的关于汾河生态风光美和人文风情美的诗,总计不下50 首。前者如《雪映金银木》《汾河这条冰水线》《春日看汾河湿地》等,后者如《与金银木合影》《一个盲人来看莲花》《来访雁丘处》等,尤其抒写汾河岸上金银木意象的诗有十多首。我写金银木风景之美“这雪白与焰红/柔情与炽烈,相映相惜/构成了汾畔最美的雕像”(《雪映金银木》);写金银木人文之美“举着金银木红印的签证入冬/穿越朔风的凛冽、雪花的温情/抵达岁月:又一重境界无边的辽阔”(《举着金银木的签证入冬》)。我在《金银木意象:审美发现与精神寄托》诗论中表示,“我笔下的金银木意象,既是一个喻象,更是平凡人朴素内敛的品性和高洁坚韧的情操的象征”,是我“诗歌审美上的一种新变和追求”。
不仅是我,就现当代山西乃至中国诗人看,他们创作的诗,本身就像一条穿越时代变迁的河流。战争年代,马作楫写过“汾河水奔流似声声怒吼”,吴伯箫写过“汾河像鲜血流注的血脉”;和平时期,郭沫若写过“汾河两岸稻田丰”,乔羽写过“汾河流水哗啦啦”,文武斌写过“汾河的歌流进我的心窝”,等等。汾河的生态环境之变,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在山西诗人的创作里。贾真说汾河是“割不断的根系/是山西人血脉的源头”,赵国增诗写“是春风和逐梦的合力/推动着汾河景区激情向南延伸”,荫丽娟诗写“虹桥上缀满花香和希望/桥下汾河水长长/流过百万市民的心怀”,陋岩笔下的汾河“不是一条河/而是一脉酒”,想象尤为奇特。
作家总是清醒的,对汾河的书写始终保持着清醒。我曾读过杨新雨的散文《两条汾河》,他写汾河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污水蜿蜒。我呢,2018 年写了直面汾河生态的《看汾河》和《裸露的河床》。前一首以自愧的心态表示,看惯了河面碧波云影和岸上林木草色,“却常忽略另一半河道/荒草漫漫间,一线细水污浊”,进而深入到智性层面,智者乐水也当“识水”,并进入“洞穿尘世中人”识人的高度。后一首看到景区因更换橡皮坝放空蓄水裸露出干涸的河床,“扯动我心底几分忧思”,“这裸露的苍凉,铺开一张/生态试卷,何时千里碧波复流/抚平母亲河的呻吟和喘息。”
我以为,揭示问题是对山西全流域治理汾河战略部署的呼应,也是对人们在生态汾河建设上有所担当和应尽义务的提醒。诗人对于汾河的爱,不仅仅是赞美之爱,还是忧患之爱,关怀之爱,爱她,疼她,忧她,护她,爱憾忧痛,在诗人笔下总是一种纷繁交织的审美。唯此才是真正的公民之爱。
在生态文明新时代,诗与自然生态的默契、与文明进程的默契,必然比任何时代愈加彰显
李景平:我写过一篇散文《汾河雁过》,散文引用了四个诗人的诗篇,汉武帝刘彻的《秋风辞》,金代元好问的《雁丘词》,明代张颐的《汾河晚渡》,当代诗人您的《突然想起大雁》。文章将笔触凝聚于大雁,在大雁的变化里看汾河的变迁,在汾河的变迁里看大雁的命运。也许诗文与自然生态自古就有一种默契?
梁志宏:那首诗是我行走汾河岸上突发灵感而作,也是日常关注汾河生态林木花鸟的结晶。您那篇散文立意构思均好,有很强的历史纵深感。我同意您的观点,诗歌文学与自然生态古往今来都是维系一体的,自然生态包括大地、河流、空气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当然会成为诗人作家关注和表现的母题。老子“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的道家学术思想,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李白、苏东坡等寄情山水,写下多少热爱大自然的名篇;陶渊明、王维等回归田园,达到了人与诗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
生态文学在古代战乱或近现代工业化初期某个阶段会退而弱化,但当破损和恶化的生态环境急需保护与修复时,生态环境问题又会成为文学创作的热门选题。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许多生态报告文学力作横空出世,生态散文佳作纷纷问世,生态文学正在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
李景平:诗人总是敏感的,甚至是敏锐的,一种时代的敏感,一种时代的敏锐。您觉得诗歌界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有什么样的表现?
梁志宏:据我观察,诗歌界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并付诸创作,大约晚了10 年之久,且少有持续性创作的生态诗人,更少有锋芒犀利的力作佳构。
在20 世纪80 年代及以前,诗歌界对生态环境少有关注,即使有也是植树造林之类。我读过诗人公刘写的一首《运杨柳的骆驼》,表现绿化沙漠的。那时的生态诸如空气、土地、河流问题并不突出,即使北岛等先锋诗人的关注点和反思点也都集中在社会和意识形态上。
以诗歌起家的徐刚最早反思生态环境,也是以报告文学形式揭示森林乱砍滥伐现象,他应该写有保护生态的诗,但影响有限。山西作家哲夫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起,接续创作长篇小说《黑雪》和“猎”字号长篇系列小说,在全国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徐刚、哲夫可称为中国最早进行生态环境文学创作并持续发力的生态作家。
进入21 世纪之后,国内有几部生态环保诗集的出版,我未读过,但据了解,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诗刊》主编李少君一直倡导“自然诗学”,主张创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歌,意在提倡生态环境保护题材的诗歌创作,但到目前诗坛也未见多少力作叫响。生态诗歌创作尚有巨大的空间。
在生态文明新时代,生态文学蓬勃发展,生态诗歌的绿色声音也在上扬。我想,传统生态诗是有持久和深厚的影响力的,现代诗也具有广博和丰沛的创造力。无论是传统诗还是现代诗,都与自然、与生态、与环境葆有血肉一般、灵肉一般的内在联系;诗歌,无论从内在创作力还是外在感应力上,都与时代、现实、未来葆有青春一般、生命一般的天然关系。进入生态文明的时代、生态文学的时代,诗与自然生态的默契,诗与文明进程的默契,必然比任何时代愈加彰显。
想起一件诗歌文化关乎生态文明的事例。最近太原汾河岸上雁丘文化提升工程已经竣工,规模宏大的雁丘园在国庆节前盛大开园,成为省域又一个热门旅游打卡地。我想此举能够实施,与市民多年呼吁和文化舆论促进有关。2017 年3 月1 日新华社发表一篇通稿《探访山西太原汾河岸:雁丘今安在》,我时任太原诗词学会会长,作为主要采访对象,曾呼吁扩建雁丘园、打造汾河诗意走廊;之后我组织学会各诗社赴雁丘采风创作,在《太原晚报》推出了诗歌专版,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我想,生态诗歌对生态文明建设还是可以尽力的。
现代诗歌和现代生态诗的创作空间,也像它所面向的自然、生态、天地、宇宙一样,将会是无限的,这也许是神话和科幻给现代诗歌的新的启迪
李景平:曾经读过您的创作史诗《华夏创世神歌》,我们不妨探讨一下神话对人与自然的抒写。人类似乎就是从自然之中破壳而出的,人类原初对于自然的抗争乃至战胜,往往是以神话文学的形式实现、表达和传播的。就是说,人类在与自然抗争的时候,依靠想象创造神来战胜自然。您的神话诗里存在这样的意蕴吗?
梁志宏:人类所有文明古国都曾浸泡在神话的海洋里。人类原初的生存和进化,伴随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也伴随着同自然的抗争以及对自然有限的战胜,往往都是以原始的思维与想象,用奇幻变形的神话方式来表达。我于20 世纪90 年代初构思重铸神话,1995 年出版了万行史诗《华夏创世神歌》,分爱神女娲、龙神黄帝、神羿射日和大禹治水四卷,通过对远古巨神的神格定位及亦神亦史的创意设计,艺术地再现华夏民族与大自然抗争、开创文明新世的全景,兼具文献性和创意性。人类进化中都遭遇过洪水危难,有过与洪水抗争的神话传说。西方神话中人类乘“诺亚方舟”逃离险境,中国神话里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神羿射日,都表现的是人类与大自然洪水猛兽和炎炎酷日的抗争,并最终以神力战而胜之,当然带有想象和理想成分。
重铸神话并非照搬,贵在合理创意和审美再造。我举《大禹治水》为例。元神话有“禹出鯀腹”记载,我写鲧在腹中孕育神子禹时,“感到苍生一万声呼救一万支耒锸/涌动在自己胸膛、腹腔”,让苍生的一万支耒锸化为大禹的骨骼,让苍生的一万声呼救化为神子的血脉。在疏治黄河上,我让大禹抽出自己一根肋骨化作一根神锸,一路迸发雷电劈开黄河龙门、长江三峡,直至疏引洪流入海。这样的神锸,凝聚了民众的呼声和力量,显示了神性与民性的统一,赋予了英雄与苍生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评论家吴思敬在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概述改革开放40 年诗歌成就评论中说:“大解的《悲歌》、叶舟的《大敦煌》、梁志宏的《华夏创世神歌》等,均以恢宏的气势,雄浑的意象,把古老的东方文化与现代人的意识糅合在一起,致力于呈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李景平:人类在神话中想象的东西,也是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但科学发展和工业创造使故事的神话变成了现实的神话。科技源于神话般的想象和启迪,却又给世界带来了生态环境危机,使之成为人类最大生存危机。这些危机,已经解决的有之,正在解决的有之,尚未解决的有之,正在发生的危机有之,在现实危机面前,诗和神话似乎遭遇了尴尬。
梁志宏:现阶段,诗歌在生态危机之下显得微弱、尴尬,力量尚未发挥出来。科技和诗歌都是想象力的产物,科技是想象力的实现,也是对诗歌想象力的触动和呼唤。我相信,在现代文明进程里,诗歌无疑也是能够揭示危机、冲破危机的,诗歌是可以呼唤全社会关注和构建生态文明的。生态文学的再度崛起,希望众多诗人和作家提升生态文明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从而创作更多的黄钟大吕般的生态诗歌和文学力作。诗歌想必能够发挥神奇的想象力,能够发挥智慧的作用力。
李景平:在走过蒙昧时代之后,人类的神话想象力伴着人类的启蒙和文明消失了。如果不是从审美视角看,也许没有人会相信神话。那么,现代科幻是不是衔接了远古神话的表达方式?现代科幻小说和新的科幻故事,是不是也有这个意义上的探索?
梁志宏:元神话是人类幼年期也即蒙眛期,为求生存、繁衍与发展的梦幻式想象和奇幻式表达。进入文明时代的次神话如《天仙配》《西游记》等,承接了元神话的表达方式,只是故事的背景隐约换成了社会人间万象。当代科幻文学,我以为也是远程衔接了神话文学的表达方式,以纷纭现实社会和高科技发展为大背景引发种种神奇的想象。两者的区别在于,神话想象最为荒诞神奇,是蒙昧期的人类面对危机时的祈祷,敬神祈神,崇拜英雄,既敬畏自然又与自然灾害抗争;科幻文学是高级神话,想象多少有了科学成分和认知,并且直面现实的生存困境,是对人类危机的预警和走出危机的引导。
我想,无论是远古神话还是现代科幻,现代诗可以借鉴和汲取的东西很多。古代屈原的楚辞已经将诗歌的视角伸向了深广天空,当代刘慈欣的科幻又将文学的构想探进了浩瀚宇宙。神话和科幻,《天问》和《三体》,给现代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巨大的借鉴空间,也向现代诗歌创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应该说,自然诗、环境诗、生态诗,不应该都是花花草草,应该有大视角、大视野、大意象、大气象、大胸怀、大胸襟。说到这,我想到我的太阳意象、黄土意象、大河意象,这些自然意象,过去,我写了红色的变革的意蕴,现在看,也可以写绿色的生态的意蕴。所以说,现代诗歌和现代生态诗的创作空间,也像它所面向的自然、生态、天地、宇宙一样,将会是无限的。这也许是神话和科幻给现代诗歌的新的启迪。
李景平:您后来的诗歌创作,我明显地感觉到两条线索,一条是现代化建设的线,它成为你诗歌的主体意象;一条是绿色化文明的线,也在成为你诗歌的主体意象。这两种意象,可以说越来越进入一种现代融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您和更多诗人,正在成为抒写人与自然和谐融合的现代诗人,这种和谐融合,会成为现代诗的人文精神。
梁志宏:您印象中现代化建设的主线,与评论家杜学文指出的“大诗歌形态”不谋而合;您所说的绿色化文明的线,在我中后期的创作中时现时隐,但尚未成为“显像”。我曾对我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创作有过概括,一处表示“努力创作回应时代,叩响灵魂,讲究诗歌艺术品质的作品”;另一处认为“体现了我抒写时代主潮和日常生活与情感两个向度,同时在艺术上开拓新的广阔空间”。现在想来,这应该就涵盖了您所说的“一条绿色文明的线”,只是在这方面我做得还很不够。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塑造,为现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书写空间。我愿为此而付出微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