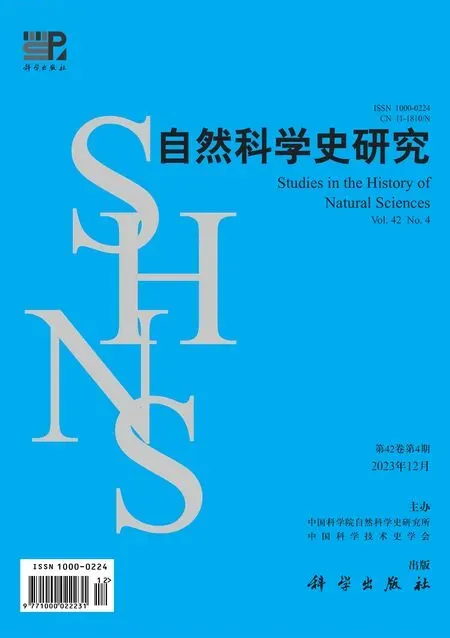“食鱼致病”医学观念与殖民海洋渔业:医学社会史视角下英属印度海洋鱼类腌渍产业发展历程研究(1867—1930)
刘 旭
(重庆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65)
英国殖民政府对印度海洋渔业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始于1867年。是年8月,殖民当局在马德拉斯管区开展了首次印度渔业资源普查,印度殖民海洋渔业就此发端。该产业发展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867年至1911年为渔业部门同殖民盐业部门合作的“鱼类腌渍产业时期”;自1911年坎努尔(Cannanore)建成第一家沙丁鱼鱼油工厂至1947年印度独立则为“沙丁鱼鱼油产业时期”。在印度炎热潮湿的气候条件下,捕获的鱼极易腐败并招致诸多疾病。这使得疾病卫生问题对于印度殖民渔业发展至关重要。正是这一现实需求为英帝国的医学家们提供了宣扬医学新说学术意义及现实价值的绝佳机会,“食鱼致病”这一与印度殖民渔业产业深度捆绑的医学学说就此诞生。该学说认为,食用不卫生鱼肉制品不仅不能为人体提供足够营养,反而会诱发痢疾、腹泻、霍乱及麻风病等多种疾病。因此,在冷藏技术难以普及的印度殖民地,发展鱼类腌渍产业并以食盐腌渍鱼货,可作为两全其美之策:一方面,鱼类制品必须符合国际卫生标准方可顺利售出获利;另一方面,以食盐这一“预防药物”腌渍鱼货,也可以彻底根治殖民地民众“盐地加工”致病恶习,从而减缓相关疾病扩散。基于此观念,英属印度殖民渔业迎来了首个发展阶段——鱼类腌渍产业发展时期。一段医学思想与产业发展深度纠缠的历史就此展开。
总体而言,学界对于英属印度渔业问题关注尚少,基于早期咸鱼腌渍产业与医学/公共卫生关系的研究则更为鲜见,存在较大探讨空间。虽有珍妮·威廉(Janine Wilhelm)、德贾尼·巴塔查里亚(Debjani Bhattacharyya)等从环境史角度出发,对英属印度海洋渔业有所论述,但其研究缺乏医学社会史视角,未能揭示该渔业产业与医学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至于简·白金汉(Jane Buckingham)等麻风病历史研究者,则多将研究精力置于麻风病患隔离及治疗方面,对于一度在印度殖民地颇具影响的“食鱼致病”学派缺乏关注。因此,本研究将基于医学社会史研究框架,首先从营养医学角度出发,尝试以医学思想变迁的新视角解读英属印度近代渔业兴起的原因。接着围绕“食鱼致病”医学学派与英属印度渔业之间的复杂关系展开论述,重点分析食鱼诱发麻风、霍乱等疾病的“食鱼致病”医学观念对于殖民咸鱼腌渍产业兴起之影响,兼论盐作为“预防药品”的过程及时人针对“盐地加工”的批判。最后,阐释医学/公共卫生思想指导下相关渔业生产活动的发展历程,分析该产业难以依“食鱼致病”学派规划实现繁荣发展,最终与“食鱼致病”医学学说同步衰落的深层次原因,从而为理解医学科学知识与经济产业、文化观念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提供鲜活例证。
1 鱼肉营养价值的“再发现”与印度殖民渔业的兴起
鱼肉制品虽然不是印度民众最主要的食物品类,但仍在其餐桌上占有一席之地。除耆那教信徒、婆罗门、首陀罗出身上层职业种姓、湿婆信众、金匠职业种姓之外,占印度人口多数的印度教下层民众并不抵触食用鱼肉。相反,简易腌渍的咸鱼配上黍粥是印度下层民众平日充饥饱腹的主要饮食。但这也致使以咸鱼为代表的鱼肉制品长期难登大雅之堂。正如鱼类学家弗朗西斯·戴(Francis Day,1829—1889)所说:“可以明确地说,鱼更适合作为印度帝国土著居民的日常食物。而不应令其食用村庄里的羊、猪和家禽。因为当能够获得鱼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去食用它。”[1]
鱼肉制品的卫生问题是制约渔业产业发展的首要因素。一方面,由于气候原因,鱼在被端上印度民众餐桌时很难确保新鲜卫生。腐烂变质的鱼因而被视作只适合下层民众的劣等食物,印度上层阶层及欧洲人对于食用鱼肉制品嗤之以鼻。另一方面,炎热气候也导致新鲜鱼货的加工和保存问题成为决定印度渔业产业兴衰的关键因素。尽管印度鱼类捕捞量巨大,但新鲜鱼获往往不及运至印度内陆就会因粗劣加工而迅速腐败,这严重制约了印度渔业发展。根据殖民当局19世纪70年代的统计数据,印度远离河海的内陆地区多存在水产品供应不足现象:旁遮普76个行政区(Tehsil)中仅有7个可以确保鱼类供应,48个全年供应不足;奥德有3/4的区供给不足;西北省38个区中只有13个可以确保日常供应;马德拉斯管区只有近海地区鱼类充足,内陆39个区中仅有4个可以确保供应;孟买管区则因交通不便(没有便捷的航运运输)导致全境供应不足。上述现象的直接结果是可食用鱼类制品市场售价水涨船高。在旁遮普等地,鱼肉价格甚至已经接近羊肉。这一鱼肉制品的巨大利好使得殖民渔业官员相信,由殖民政府经营的官营渔业必将成为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印度殖民渔业的兴起也与工业革命后营养观念的变迁密切相关。在英国,工业革命导致的食物短缺问题及食物观念的变化,使得鱼肉制品的营养价值终被“发现”。事实上,自中世纪以来,鱼肉制品并非欧洲上层居民可食用肉类食物的首选,牛、羊、鸡等才是欧洲上层民众餐桌上的主要食材[2]。与印度情况相似,保鲜及加工技术的落后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因而在欧洲,新鲜鱼类的最终归宿也多是被制成质次价廉的咸鱼并出售给下层民众。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下层阶级日渐贫困并脱离畜牧生产,工人阶级食用肉类的机会因此逐渐减少。而霍乱、伤寒、疟疾等疾病的流行,亦使得为工人阶级提供营养食物以令其具备疾病抵抗能力一事至关重要。因此,寻找替代昂贵牛、羊、鸡肉的营养肉制品以提高工人阶级体质,抵御各类疾病,从而为工业革命提供一支强有力的劳动力大军,成为欧美各国政府及医学界的共同任务。
在此背景下,各国开始关注鱼肉制品的营养价值:“有一些鱼,如鲱鱼(herring)、鲭鱼(mackerel)、西鲱(sprats)有着和牛肉、羊肉及猪肉一样的氮元素含量,正如化学所揭示的,吃它们和吃肉一样可以做好重体力劳动(hard-working)。”[3]而当鱼类(特别是海洋鱼类)逐渐由中产阶级垂钓消遣的猎物及下层民众的吃食,转变为维持工人阶级体力的廉价营养食物之时(1)海洋渔业及马铃薯种植业共同改变了英国民众自中世纪以来形成的饮食习惯,并使得鱼和炸土豆条成为可供英国工人阶级食用的新廉价食物。,渔业资源便成为支撑各国国家工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这无疑是导致鱼肉营养价值观念在全球迅速传播扩散的根本原因。鱼肉的营养价值观念很快影响到美国,在一本名为《海中牲畜》(TheCattleoftheSea)的书中,作者直白地指出:“它(鱼类)会为不断下降的肉类供应提供理想替代品,并以足够低的生产成本确保其最为低廉的价格……蛋和肉类都不能确保如此低的价格。”[4]鱼肉对于工业革命及各国经济的战略价值,甚至促进了食用鱼肉医疗功效神话的出现。这一现象在各国渔业兴起的早期阶段尤其明显。在食用鱼肉医疗功效神话影响下,长期食用鱼肉行为的文化形象发生了根本转变,它从贫困阶级的象征及可能的致病因素,迅速转变为可以确保身体健康强壮的良好饮食习惯:“没有什么群体能赶得上渔民,如我们所见能够有更大的家庭规模,更健美的女人,更有活力和激情的男人,并更容易免患各种疾病。”([3],383-384页)食用鱼肉甚至事关人种存续,“在世界许多地方,吃鱼的人都是强壮的典范。而吃鱼这一饮食习惯很难被认为会导致人种体格衰落”。([1],239页)
西方世界食用鱼肉的热潮很快传播到殖民地印度。殖民渔业官员普遍认为,鱼肉是远比牛羊肉类更加廉价的非蔬菜类食物,它具有重要的营养与经济价值。正如殖民渔业官员奥森纳(Othenan)所说:“鱼,特别是沙丁鱼是(印度)西海岸最贫困阶层的主要食物之一。因其口味甚佳且有着丰富营养,同时又比其他食物便宜。”[5]而印度民众吃不到卫生且廉价鱼肉的结果,“是通过减少其食物的方式渐渐消磨了人们的强健身体”。[6]鱼肉更是应对饥荒的极佳食物,“人一直处于饥饿状态,而其周围却有着完美的动物食物来源。这一来源实际上是取之不尽的,只需努力捕获即可”。[7]总而言之,印度殖民渔业官员对于鱼肉价值的“发现”使其相信,殖民官营渔业终将成为提高印度民众体质、解决饥荒问题,同时获得巨大利益的朝阳产业。
2 “食鱼致病”医学疾病观念及其对“盐地加工”生产技术的批判
借助医学疾病知识,宣传食用不卫生鱼肉制品致病性,推广标准化卫生加工鱼制品,无疑对于吹捧鱼肉“卫生健康”营养价值的殖民鱼类腌渍产业意义重大。如前所述,鱼肉易腐败特性是制约殖民渔业发展的首要瓶颈。它不仅不利于鱼肉制品的长途运输,也致使咸鱼加工成品口感不佳。而从疾病卫生角度而言,腐烂变质的鱼肉制品也容易成为各类传染疾病的传播媒介,从而成为公共卫生隐患。对此,马德拉斯渔业总监弗兰德里克·尼古拉斯(Frederick Nicholson)指出:“这个国家生产的腐败的鱼,不仅被引起腐败的众多细菌及其活动产生的有毒物质所渗透。它也很可能借助苍蝇为主要媒介诱发包括霍乱、伤寒等在内的特殊疾病。”[8]据印度殖民报告所示,痢疾、腹泻、食物中毒及肠胃疼痛都是食用不洁净鱼肉制品可能招致的后果。如在马拉巴尔,“在台风季节来临前几个月时,空气十分湿润。这些腌制过程中的鱼吸引了水汽。至少在马拉巴尔,它们直接或协助引发痢疾及腹泻的现象并不少见……在马拉巴尔海岸与锡兰,食用沙丁鱼,无论是亚洲沙丁(clupea neohowii)还是黑尾沙丁(clupea melanura)都会引发中毒状况”。([1],242-244页)不仅如此,受制于医学认识,在认清病因之前,缺乏维生素C导致的坏血病也被认为与食鱼习惯密切相关,“在欧洲一些地区,坏血病被认为为食鱼所致”。象皮病等皮肤病也是“食用处于腐败状态或者未很好加工的鱼所致”([1],245页)。甚至挪威人的痨病(phthisis)也被认为与其食用变质鱼肉及奶制品的不良习惯密切相关。
因其引发痢疾、疟疾等疾病,食用不卫生鱼肉更被时人视为麻风病的重要病因。当时一些殖民医师认为,疟疾(2)医学界对于疟疾这一疾病的认识形成较晚。在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包括疟疾在内的众多疾病都被笼统地冠以“热病”(fever)之名。、痢疾等疾病会间接引发麻风病。在他们看来,食用不卫生鱼肉会引发作为痢疾及疟疾共有症状的腹泻,这是诱发麻风病发病的重要病因之一。因此,食用腐败鱼肉的行为便与麻风病联系起来。以医师乔纳森·哈钦森(Johnathan Hutchinson/ Jonathan Hutchinson,1828—1913)为代表的“食鱼致病”学派医师(3)19世纪末20世纪初,医学界在麻风病致病问题上主要分为两大流派。以伊拉斯谟·威尔逊(William James Erasmus Wilson,1809—1884)为代表的“瘴气”学派认为,瘴气是导致罹患麻风病的主要原因。而乔纳森·哈钦森一派则坚持认为麻风病是由于不洁净饮食引发的,腐烂变质的鱼是引发该疾病的主要食物。认为,“这一疾病(麻风病)是由腐败的、干燥的和未完美腌渍的鱼所引发的”。[9]为收集证据并宣传其学说,哈钦森于1903年亲身前往印度。在其影响之下,印度鱼类学家弗朗西斯·戴也成为“食鱼致病”学说拥趸,在弗朗西斯·戴看来,“麻风病是一个(病因)清楚的疾病,它一直被认为与食用不卫生的鱼有关。麻风病在旁遮普、西北省和其他内陆省份并不少见。那里的人们完全拒绝食用任何腌鱼。在雨季购买小鱼是其食用腐败鱼肉的唯一途径。在烹饪之前,这些鱼多少已经处于腐败状态”([1],245页)。借助弗朗西斯·戴的支持,哈钦森的“食鱼致病”说得到印度殖民医学界乃至英帝国医学界的普遍承认,以致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一观点已经被所有的麻风病学权威所接受”。[10]1925年成立的不列颠帝国麻风病救济协会(British Empire Leprosy Relief Association)亦成为麻风病“食鱼致病”学说的重要推广机构。诚如1926年于乔乌德瓦尔(Chowdwar)设立麻风病专科医院(Gram Sangathana Kendra Leprosy Clinic)的拉克希米·纳拉亚娜·萨胡(Lakshmi Narayan Sahu,1890—1963)所言:
麻风病的感染病因很多。梅毒、慢性疾病、钩虫、过度工作、懒惰、丝虫病、麦地那龙线虫……然而土壤、饮食及土地法令(Land Laws)是三大主要致病因素。那些因为土地贫瘠而得不到足够蔬菜吃的人们,那些食物中包含鱼干和米饭的人们,那些肮脏的和不洁净的人们,那些没有土地并过着不稳定生活的人们最容易患病。[11]
随着腐败鱼肉被视作感染各类疾病的重要传染源,印度民众“不卫生”的咸鱼加工方式亦开始引发“食鱼致病”学派及殖民渔业官员的共同关注。其背后原因除消除公共卫生隐患外,提高印度海鱼腌渍制品国际声誉并为设立官营咸鱼加工工厂扫清障碍亦是重要因素。讽刺的是,造成这一咸鱼加工方式在下层民众中广为流行的原因恰是殖民政府的食盐垄断。英属印度殖民当局对食盐的垄断是造成印度食盐价格高昂及渔民使用食盐加工咸鱼活动逐渐减少的直接原因。正如弗朗西斯·戴在1873年《印度缅甸海鱼及渔业报告》(ReportontheSeaFishandFisheriesofIndiaandBurma)中所言,盐价上升是孟买管区拉特纳吉里(Ratnagiri)等地近15年内渔民使用食盐腌鱼活动持续减少的直接原因。孟买南部区(Southern Division)盐税助理专员(Assistant Commissioner of the Salt Revenue)也无奈承认:“外国渔业相较我们有着决定性优势。因其每莫恩德(maund,一种计量单位)咸鱼使用的盐一般需要花费2安。尽管这一价格也不低,但是多数不列颠课税盐是无法以低于2安每莫恩德的价格出售的。因此,外国渔业可以自由地使用食盐彻底加工鱼。相反,我们的渔民则忍受着相对高昂的盐价,不能承受(盐的)浪费。结果是,他们只能使用仅足以维持鱼短期内(不至腐败)数量的盐。这根本算不上是咸鱼加工。”([7],49页)
盐价高昂迫使多数印度下层民众只得按照“盐地加工”(Salt-Earth)方式对捕获的鱼类进行简易加工。所谓“盐地加工”,指的是使用海边盐场的盐水或盐土加工鱼类的腌渍方式。与大量使用盐涂抹鱼肉的腌制加工方式不同,在“盐地加工”过程中,渔民会先使用海水对鱼肉进行清洗并使之吸收盐分,之后将鱼肉埋入海边盐地以促使其进一步吸收盐分。除了将鱼肉埋进盐地之外,使用沼泽盐地堆放也是下层民众常用的“盐地加工”制作方法。一位殖民官员详细描述了当地居民使用这一方式制作咸鱼的主要流程:
它主要在沼泽地进行。在这种不洁净的状态下,盐分会借助摩擦进入鱼肉中。沼泽的主人则会在沼泽边将河道打开一个口子。以使得足够的盐水流进封闭的沼泽中。静置几日后渔民被允许以8派每篮子(约3莫恩德)的价格在其上堆积鱼肉。([7],78页)

然而无论是马德拉斯管区的“马都拉”、缅甸的“腌鱼”,还是孟买管区的“盐地加工”,“在欧洲人和印度上层人士看来,这些(工艺生产的产品)仅仅可以被用在粪肥坑中”([8],64页)。约翰·斯诺霍乱“水媒”传播理论的流行,更使得殖民渔业官员相信,霍乱这一主要借助被污染水源传播的传染疾病,很可能通过食用被污染的盐水加工咸鱼而大肆传播。不仅如此,鱼类喜食粪便的习惯也被认为足以引发霍乱传播,“(我们)正在考虑霍乱是否因食用未完全清洁或者烹调的鲶鱼(macrones)及海鲶(arius)所致,因这两种鱼类喜食粪便”([1],242页)。而霍乱弧菌的发现也证明了被污染食物的高危致病性:“这意味着(霍乱)传播的方式可能有多种,但是基本上都是借助被感染的物质进入肠胃得以传播。这多通过食物或者水实现,但或许食物更为普遍,一方面因为食物比水更容易由他人传递(而被污染),特别是在这一国家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在很多方面都提供了霍乱弧菌增殖的合适媒介。”[12]
那么如何才能根除下层民众“盐地加工”恶习以防控相关疾病?解铃还须系铃人,因食盐价昂导致的“恶行”需借助普及廉价食盐加以解决。正如孟买管区拉特纳吉里区税务官所言:“对于食盐征收的重税,毫无疑问是传染疾病和其他由于吃到没有完美加工的鱼罹患的严重疾病的根本原因。”([7],13页)食盐也因此在殖民地印度开始由一种单纯的烹饪调味料,上升为治疗霍乱、麻风病等传染疾病的预防药品,“免费使用盐被强烈建议作为一种预防性药物。毫无疑问,那些被剥夺了这一调味品的人们容易成为可怕疾病的受害者。盐要使用在一些食物中,而考虑到霍乱的肆虐它也应该免费”。[13]而随着碘元素功效的发现,新鲜卫生的鱼成为足以与直接摄入食盐达到同等功效的替代品。英帝国医学界的部分医师就此得出结论,虽然食用不卫生鱼肉可能罹患痨病,但食用富含碘盐的卫生海鱼却可以防治肺结核,新鲜海鱼摄入不足也因此被视作肺结核的重要病因:“肺结核不仅在整个联合王国的工人阶层中,也在其国内及海外服役的军队中盛行。这些人每日都会被配给肉类,但很少吃鱼。”[14]
借助“盐”这一重要资源,包括印度渔民在内印度下层民众的身体健康、道德层次与经济水平被紧密勾连,从而最终被用以证明殖民官营渔业的存在价值。高昂的盐价则被视作殖民地渔民群体贫困、衰弱与堕落的重要原因。正如欧内斯特·英格索尔(Ernest Ingersoll,1852—1946)于《科学》杂志刊发的《鱼与印度饥荒》(FishandFamineinIndia)一文所言:“早前的英国统治者对于进口的和本国生产的优质食盐课以重税,它甚至对于使用贫瘠盐场土地的行为也予以征税。”[15]而在鱼类学家弗朗西斯·戴看来,昂贵盐价不仅使得渔民贫困并无力食用卫生价廉的鱼肉制品,更是导致殖民地印度渔业产业起步艰难的根本原因。如在内洛尔(Nellore),这些在葡萄牙殖民者到来之时“一度十分富有”甚至有能力组织军队的渔民,如今却“因贫困而被发现其数量在逐渐减少,他们或因霍乱及其他疾病(死亡),或只能(转行)作为水手在海边船只上打杂”([6],21页)。因此,食盐价格高昂、鲜鱼市场狭小是造成渔民贫困的根本原因。高昂盐价使其难以负担制作咸鱼所必须的食盐数量。即使渔民捕捞再多的鱼,也只能任其腐败。而当勤劳出海变得再无意义,渔民的道德品行也因此变得放荡起来:“不应该在渔民身上倾注同情心,因为他们是独来独往、终日快活和烂醉如泥的一帮人。”([6],22页)基于上述论断,廉价食盐就此被赋予了拯救渔民身心、复兴印度渔业的崇高使命。
3 殖民鱼类腌渍产业发端及卫生加工目标的失败
印度殖民地渔业官员及公共卫生官员普遍认为,确保以洁净卫生方式产出可以长期保存的水产制品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振兴印度海洋渔业、解决渔民贫困、道德败坏问题及消除食用腐败鱼肉所致疾病的关键。而由殖民官方控制鱼类加工工场,并使用政府官盐加工咸鱼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途径。
受资金设备所限,殖民时期的印度无法效仿欧美诸国大范围推广冷藏设备及运输汽车。殖民渔业部下辖冰块仓库建立一事一拖再拖,亦使得保鲜车推广目标难以实现,甚至连最基本的保鲜箱(live chest)都难以普及。“配送问题毫无疑问是最为重要的,在孟加拉国,缺少冰或者其他形式的冷藏方式看起来是增加(鱼类产品)供应面临的主要困难”。[16]冷冻鱼肉配套设施的缺乏使得咸鱼一度成为印度殖民地除鱼罐头之外的主要水产制品类目。
由于食盐是咸鱼加工过程中的主要原料,殖民当局的鱼类加工场最初皆由殖民盐业部门(Salt Department)掌控。通过合作,殖民渔业部门及盐业部门起初似乎实现了“双赢”:殖民渔业部门可以放开手脚尽情捕捞“取之不尽”的海洋渔业资源,不必再担心过剩的鱼获最终因腐烂而浪费;盐业部门则可以顺利出售其高价食盐,从而解决食盐销售难题。咸鱼腌渍产业甚至解决了食盐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低品质瑕疵盐的销路问题。以往,食盐炼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无法结晶的盐屑(当时的盐主要是结晶盐),这些盐屑多因不便出售而被直接销毁。殖民鱼类加工工场的兴起改变了这一浪费局面:“在食盐生产过程中,低品质的盐不应该被销毁,而应该以成本价出售给加工厂。”([7],78页)鱼类加工工场因此一度成为了一桩有利可图的买卖。为了迅速实现产业扩张,殖民盐业部门甚至一度免除了印度渔民的“盐地加工”盐税,只需后者同意在官营咸鱼加工场工作即可。在殖民盐业部门及渔业部门的合作下,以加工咸鱼为主要业务的官营鱼类加工工场逐渐在印度主要鱼类产区推广开来。马达拉斯管区咸鱼加工工场蓬勃发展,截至1916年,管区内已设立118个鱼类加工工场。[17]
但产业的迅速扩张很快带来了负面效应。尽管有着如此数量和规模的加工工场,殖民官营加工工场的咸鱼加工效率仍然远远落后于殖民渔业的日常捕获量。这直接导致许多捕获的鱼类无法得到有效加工,只能任其在太阳下腐败变质,这无疑严重破坏了加工工场周边的环境卫生:“当(加工场)没有时间和空间时,沙丁鱼和鲭鱼……被散落在叶子垫子上置于阳光下晒干,既不清洁也不使用盐腌渍。”([8],67页)而鲨鱼、狗鲨(dog fish)、鳐鱼、灰鳐、海豚等难以出售的“没有人食用的”鱼类,则被殖民渔业加工产业彻底抛弃。这些鱼类除少量被免费移交给印度海军以作为军队口粮外,大都被直接丢弃在了近海区域。殖民渔业官员对此感叹道:“将鳐鱼丢出甲板,不仅浪费了好食材,对渔场也有着十分有害的影响,因其(腐烂的尸体)将其他鱼种驱赶出了渔场。”[18]上述做法无疑与“食鱼致病”所强调的腐败鱼肉足以致病,需密切关注鱼肉制品及其加工工场卫生状况的建议背道而驰。
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原本旨在生产卫生鱼类制品的殖民咸鱼加工工场,反而时常成为致病疾病爆发的源头。事实上,在殖民时期,因霍乱爆发导致相关加工工场关闭停业之事屡见不鲜,官营咸鱼加工工场甚至由此成为了霍乱防治的“前沿阵地”。加工工场的工人不得不在公共卫生方面身先士卒:“在马尔佩(Malpe),霍乱于(1927年)12月初爆发。马尔佩咸鱼加工工场的员工应该在为水井中加氯消毒及为房屋消毒方面尽其可能地协助健康监察官(health inspector)。而由于大众对于疫苗接种有着天然歧视,制鱼工场成员必须在接种疫苗过程中身先士卒。”[19]不仅如此,殖民当局在渔业加工产业从业人员卫生教育方面也煞费苦心。卫生与保健知识被纳入殖民当局为培养合格渔民开设的培训学校(training institute)课程内容之中。正如马德拉斯渔业报告所述:“他们(印度青年渔民)应该掌握专门的保健和卫生知识,应该教给他们节俭品德及基础社会科学。因为在所有群体中他们最为浪费和放纵。”([5],83页)渔民教育被殖民渔业视作消除“盐地加工”等不卫生鱼类加工方式、培养殖民渔业员工的重要手段。在孟买管区南部山区兼职渔业主管(Part-time Superintendent of Fisheries in Southern Range)T·J·沃克(T.J.Walke)的带领下,当地殖民渔业部积极向印度渔民传授制作卫生腌鱼、熏鱼及鱼肥技巧。马德拉斯管区亦将英国本土及美国的“干净、卫生、更合适的腌渍和风干”([5],52页)方式引进到了达努尔(Tanur)等地的加工工场中。
而在斯诺“水媒理论”影响下,殖民当局很快意识到,鱼类加工工场的不洁环境是导致印度海岸地区霍乱肆虐的重要因素。而殖民时期流行的湿法加工咸鱼制作工艺,则被认为应对加工场卫生环境问题负担主要责任。
湿法加工(moist curing)是殖民时期咸鱼腌渍产业采取的主要加工工艺,由于该工艺中大量采用海水,致使咸鱼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包含血肉的污水。这些污水在印度炎热的气候下极易腐败变质,从而散发恶臭气味并滋生苍蝇,进而成为传播疾病的病源。因此,设法改进湿法加工工艺便成为确保咸鱼加工场不至“致病”的当务之急。其做法包括:严格确保鲜鱼在运至加工工场前已使用海水充分清洁,确保“干净的储藏、干净的盐和干净的晾晒场所”([8],65页),迅速加工处理以防变质,定期清洁消毒加工场所和及时处理无用的鱼骨与鱼类内脏等。
为了解决湿法加工产生的污水污染问题,孟买管区政府在1937年专门颁布决议(Resolution General Department, No.1960/33, Dated October 21, 1937)。决议规定可以重开因公共卫生原因关闭的咸鱼加工场,但必须首先按照卫生方式改造加工场地;务必以更易清洁且不会使污水渗入的水泥地面代替泥土地面;除此之外,使用氯化钙消毒、在加工场内部设立排污设施等也是咸鱼加工场公共卫生改良措施的重要内容。客观上讲,上述措施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如在孟买管区,“更好的卫生状况被认为直接影响了卡纳达(Kanara)工场双棘原始黄姑鱼(goal)及鲶鱼(shengala)的加工流程,卡纳达与拉特纳吉里工场使用湿法处理鲭鱼的过程也受到影响。它直接导致了丽蝇(blowfly)的消失”。[20]
尽管宣称防治疾病,但英属印度殖民当局在其鱼类加工场推行公共卫生措施的直接目的仍是以盈利为先。这是由于作为咸鱼加工场主要产品的咸鱼在本质上是一种食品,而食品的产品质量多受其加工场所卫生条件影响。印度不利的气候条件及加工场所卫生环境的恶劣,导致生产的咸鱼极易因不洁环境而降低品质,进而影响销售。诚如弗兰德里克·尼古拉斯所说:“产品是第一位的。要施以不同改革以生产出更佳产品。这首先将会吸引更高阶层的消费者,并渐渐变得令其他人可以接受……至于鱼类,其质量远比数量更为重要……在所有日常食物中,鱼是最容易腐败的。其腐败后也是有毒的。而现有条件下增加捕获量无异于增加有毒食物。”([8],62页)事实上,根据殖民时期档案记录所述,不卫生的加工环境很容易影响水产加工成品品相,甚至出现霉菌感染。如咸鱼的“红眼”(pinkeye)现象、因储存条件不佳引发的“锈斑”(rusting)以及风干虾类的白赘等。这些霉菌病害不仅直接影响了加工场的产品品相,更使得相关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销量不畅,缺乏竞争力。对此,一位殖民渔业官员无奈指出:“总体而言,西方国家和日本加工的鱼要远比印度加工的更加干净、卫生。结果导致后者不为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甚至是埃及和巴勒斯坦(市场)所接受。”([5],138页)
公共卫生状况对于殖民渔业控制的牡蛎及珍珠养殖场同样十分重要。殖民渔业部官员普遍认为,印度牡蛎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可将其去壳冷藏以出售给印度的欧洲人及社会上层人士,亦可晒干或制作成罐头供应中国市场。尤其考虑到“虽然其数量可观,当地人却很少食用有壳水生动物。他们厌恶这类食物,除在马拉巴尔、蒂鲁内尔维利(Tinnevelly)和拉马纳塔普拉姆海岸(Ramnad Coasts)以外,牡蛎仅仅被下层人口、欧洲人及英裔印度人食用”([5],88页),因此必须效仿日本及西欧经验在印度建立牡蛎养殖产业。但同咸鱼腌渍产业相似,公共卫生状况不佳引发的牡蛎病害,亦是制约牡蛎产业发展的重要障碍。如马希姆湾(Mahim Creek)的牡蛎及蛤蛎就一度因水体污染无法食用。因此,“营地的健康,如水源供给、卫生状况、医疗条件和防治传染病措施等”同样成为牡蛎及珍珠产业成败的关键。([5],165页)
但殖民政府在渔业推行的公共卫生措施却遭到了印度民众的激烈抵制。在孟买管区,T.J.沃克所担任的兼职渔业主管一职在设立仅2年半后(1919年10月至1922年3月)就被废除。其成立渔民合作组织的建议也因当地水产中间商(local savkar)[21]的抵制而难以落地。数年间仅有2个协会注册,且在注册后也没有进行任何捕捞作业。与此同时,随着殖民咸鱼加工工场的推广,“逃避了严格的加工规则管制,同时逃避了特许(License)费用及行业税(profession tax)”[19]的“盐地加工”最终被勒令禁止。无法自行加工所获鱼肉的渔民被迫加入工场做工。殖民当局这一做法成为了许多印度渔民反感殖民加工工场卫生措施的重要诱因,“渔民将咸鱼加工工场引入的清洁措施视为对其个人权利的侵害”[22]。南卡纳达(South Kanara)的渔民甚至专门组织了针对殖民咸鱼加工工场卫生规则的抗议活动。显然,印度渔民清楚地意识到殖民渔业公共卫生规训背后蕴藏的权力利益关系,并深切地感受到这一殖民关系对其利益造成的损害。
实际上,“食鱼致病”学派设想下的渔业收益与公共卫生“双赢”局面并未持续很久。高昂的盐价使得盐业部门长期亏损。过度依赖食盐的咸鱼腌渍产业自然受到波及,“这一(马德拉斯)管区的盐价在1924年4月1日以前一直为10安每莫恩德,这导致盐业部门出现巨大亏损。在1922至1924年平均每年亏损超过175 000卢比。这些年的亏损迫使盐业部门将加工场转交给了渔业部……印度政府不愿为鱼类加工工场支付任何多余费用”([5],133页)。虽然加工工场的食盐是由殖民食盐部门提供的免税盐,但高昂的食盐运输费用却还是极大地增加了咸鱼加工成本。同样在马德拉斯管区,殖民渔业产业在1927至1928年年度所获收入总计为99 169卢比。但其中多数(85 920卢比)为牡蛎养殖产业所得,咸鱼腌渍产业收入仅为17 473卢比。而在刨去食盐运输成本及其他费用之后,该产业实际利润仅为3 894卢比。拖网汽船的引进及殖民沙丁鱼鱼油产业的兴起,给摇摇欲坠的殖民咸鱼加工产业带来了致命一击,早期以食盐为核心的、殖民盐业部门主导的殖民渔业的产业模式开始瓦解,殖民咸鱼腌渍产业逐渐为殖民鱼油、鱼肥加工产业替代。在马德拉斯管区,咸鱼加工工场的管理权于1924年4月被正式移交给殖民渔业部。孟买管区甚至出于未来产业不明朗的考虑,直接于1922年废除了殖民渔业部;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该管区殖民渔业部因鱼油产业兴起而重建,管区内咸鱼加工工场的管理权才最终从殖民盐业部门处转至殖民渔业部门手中。[23]总而言之,尽管“食鱼致病”学派为英属印度渔业找到了食盐腌制这一兼具公共卫生功效及产业前景的发展方案,但殖民当局长期维持的高盐价却使得这一前景难以实现:殖民渔业部门不仅无法真正解决咸鱼加工生产过程中面临的卫生致病问题,也难以在成本允许条件下产出符合国际市场卫生标准的咸鱼腌渍制品,最终致使殖民鱼类腌渍产业走向衰落。
4 结 论
在英属印度鱼类腌渍产业的发展历程中,以“食鱼致病”为代表的医学疾病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借助对印度土著“盐地加工”这一“致病”鱼类加工习惯的批判,英属印度官营咸鱼腌渍产业不仅获得了科学上的逻辑合理性,同时也借助取缔“盐地加工”吸纳了一大批从业渔民,从而为该产业发展初期的迅速拓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强调食盐的“预防药品”作用,“食鱼致病”学派也为相关渔业产业的成功指明了发展前景:确保咸鱼制品及其加工环境的卫生条件,从而挽回印度鱼类制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这一医学学说与渔业产业之间的互动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它不仅有助于理解不同学科科学知识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关系,特别是对于理解英帝国殖民知识网络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其参考价值,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科学知识与现实诉求之间复杂的共生互动关系。
然而,不能过高评价以“食鱼致病”为代表的医学疾病知识在殖民海鱼腌渍产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虽然这些科学知识在相关产业建立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导致殖民海鱼腌渍产业失败的根本原因仍是经济上的及殖民政治制度层面的。在殖民体系下,海鱼腌渍产业无法兼顾维持利润与提高产品卫生标准两大目标,这是其失败的直接原因。事实上,尽管殖民当局一度在殖民咸鱼加工工场推行公共卫生措施,改良咸鱼加工工场公共卫生条件,但追求产品利润却始终是其根本目标。打着消除“致病”鱼肉制品的幌子,借助咸鱼加工解决印度官营食盐价高难销难题并实现盈利,才是官营鱼类加工工场设立的初衷。南卡拉那税务官(Collector of Souh Canara)H·S·托马斯(H.S.Thomas)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期望,在那些鱼足够充足的地方,他们(渔民)会发现购买更多的盐用以加工咸鱼是值得的,而我们也会发现盐的消费会增加。”([7],76-77页)因此深究下去,就会发现许多公共卫生措施背后都有着实用主义的获利目标,如取缔“盐地加工”实则是为了拓宽咸鱼销路并为殖民加工工场提供渔业工人。而那些看似出于防疫疾病考虑的卫生措施,其关注点也仅为殖民咸鱼加工工场内部及周边地区,对于周边印度渔村及海岸地区却未有丝毫涉及。(5)虽然英属印度殖民当局在印度农村地区采取了一些疟疾防护手段,但它对于印度渔村的霍乱、麻风病等疾病却并未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显然,对于殖民渔业官员来说,借助公共卫生措施生产出洁净卫生、广受市场欢迎的咸鱼制品才是首要目标。因此殖民渔业官员只关注其经营的加工工场的卫生状况,对海岸及海洋地区的环境及公共卫生状况则漠不关心。那些在殖民当局眼中“没有”经济价值的其他鱼种,往往都会连同加工工场产生的鱼类内脏及污水一道,丢弃到海滩之上或海水之中。正如一位殖民渔业官员所说:“(鱼类加工工场)将1至2吨臭沙丁鱼埋在有孔隙的海边沙地中,几个月后再将余下的挖出来是管理上的失误。将鱼头扔进海里或者扔在沙滩上,或者将鲨鱼骨架和鳐鱼埋在土里并不再挖出完全是浪费。”([8],73页)
“食鱼致病”这一医学观念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观念对于英属印度殖民地创立海洋渔业产业迫切诉求的迎合。事实上,该学派代表人物乔纳森·哈钦森对印度殖民地极为重视,他不仅多次前往印度收集数据,更将“食鱼致病”学说与殖民渔业部门的合作视作该学说推广的关键途径。可以断言,“食鱼致病”这一医学学说实际上与殖民早期咸鱼腌渍产业形成了某种“共生关系”,其命运也宿命般地与后者联系起来。正因如此,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丁鱼鱼油产业的蓬勃发展,殖民咸鱼加工工场及其公共卫生措施很快遭遇了冷落,“产业的狂热导致私人企业在公共卫生方面缺乏关注”([5],64页)。对于此时的殖民渔业官员来说,如何尽可能多地捕获沙丁鱼并制成优质鱼油出售才是当务之急。当更盈利的产业模式出现时,成本高昂的“卫生”腌渍咸鱼制品产业最终被殖民政府抛弃。而与相关产业关联密切的“食鱼致病”这一医学学派,也因失去现实基础及产业支撑价值而在印度殖民地遭遇冷落。最终,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高光时刻后,“食鱼致病”学派在30年代与印度殖民咸鱼腌渍产业一道走向衰落。不仅“食鱼致病”学派所强调的食鱼导致麻风病之说为格哈德·亨利克·阿玛尔·汉生(Gerhard Henrik Armauer Hansen)提出的麻风杆菌致病说所取代,甚至连该学说本身也逐渐被后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