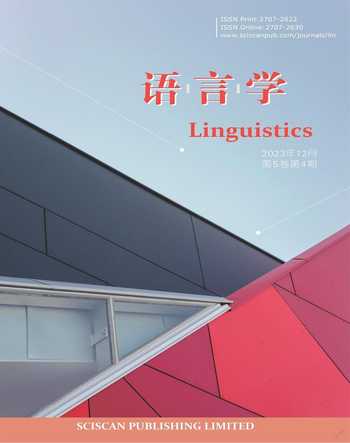儿童的精神表情及其诗意呈现
刘巍
摘 要|在《朝花夕拾》的所有篇目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堪称是最温馨的散文;它不仅清晰地构建了亦诗亦幻的百草园游乐和有涩有乐的书屋求学;也动态地描摹孩童的天真、快乐、渴慕、惊恐、矛盾、无奈等情绪流变;立体地熔铸了鲁迅的批判精神、教育理想和艺术创作观。本文拟从原创性角度回味成人的“真童话”;从审美性角度吟咏无韵的“长诗篇”;从现代性角度阐释民族的“新文学”;从历時性角度来构建永恒的“百草园”;借此解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内蕴的儿童精神表情与原创的诗意特质。
关键词|《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精神表情;原创诗意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人到中年的鲁迅,遭遇段祺瑞政府的通缉和学者们的排挤,不得已放弃写作杂文;转而用散文笔法开启返乡之旅。1926年9月18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以下简称为《百草园》)登上了摹写儿童生活的散文舞台,最纯真地演绎了儿童的精神表情,最原创地展示了诗意特质,成为近代散文的经典。
本文拟从“原创性、诗意性、审美性、历时性、现代性和民族性”[1]角度展开对《百草园》经典性的分析,以期更清楚地解读《百草园》的诗意美。
1 成人的“真童话”:从原创性角度看思想内容
关于百草园,作者在原稿开篇说已卖给他人,在清稿中加“早已”[2]来强调其仅为“记忆中的杂草”;文末交代绣像被卖给有钱的同窗,“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文章首尾各用一个“早已”,表明鲁迅回望童年时产生的时光远逝的感伤和物去人非的怅惘。正文中,作者首先描述了百草园里孩子们既能沉浸式地游玩,亦可仰望式地听“母亲”阿长[3]讲故事,还能体验式地随闰土父亲捕鸟;用艺术的温情呈现成人的“真童话”。
1.1 浸游在亦诗亦幻的百草乐园
“不必说”引出梯阶式的植物园:有颜色的绿菜红桑,有质感的石井栏,有高度的皂荚树;“也不必说”描摹动静相宜的生命圈:春有胖蜂吸蜜,夏有高处蝉吟,秋有云雀直入云天。一句“单是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拉开了精彩体验的序幕:首先是观赏动物们的吹拉弹唱:油蛉低唱,蟋蟀弹琴;其次是惊险地玩弄“毒虫类”:翻砖见蜈蚣;指按斑蝥,听“拍”声,见“烟雾”,悟快乐;最后是体验舌尖美味的快慰和幻境未实现的惆怅:勇避覆盆子的刺,去体验其“又酸又甜”的果实;试吃人形何首乌根欲变仙……
夏天的野草丛氤氲着魔幻与隐秘,令人神往。赤练蛇的传说和美女蛇的故事在长妈妈那里幻化为美女与野兽的交锋:文质彬彬的读书人、神出鬼没的美女、得道高深的和尚、枕边的小盒子、墙头的人首蛇身交织出现;“沙沙沙”妖怪来,“豁豁”蜈蚣飞,金光一道飞去飞回,蜈蚣吸取脑髓低调凯旋。
冬日的荒园有捕鸟的体验。“这些活动不但于小孩很有兴趣,也能增进他不少的知识”[4]。为学捕鸟,儿时的鲁迅学着把握天时“待积雪盖地两天”;掌握扫雪露地,支竹筛、撒秕谷,系长绳牵线,远处看鸟雀,伺时机拉绳罩鸟等一系列动作;识得“鸟性”:麻雀贪食,张飞鸟性躁;更体悟了孩童与大人的差距:闰土的父亲很少时间能捕到几十只鸟,而我“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还了解到自己“太性急”了……
1.2 求学于有涩有乐的三味书屋
离开百草园去三味书屋,求学生活既有涩有乐又五彩纷呈。
令人诧异的是开学礼无需拜孔子,只要“对着那匾和鹿行礼”;令人恭敬的是先生为“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让人反省的是询问“怪哉”会让老师“有怒色”;令人有收获的是读书、习字、对课进步;令人放松的是可去后园寻乐;令人体悟温和的是除了瞪眼和大声,老师并不常用戒尺和罚跪;令鲁迅有成就感的是收获两大本绣像。因此,在三味书屋的生活并不枯燥乏味,而是既有涩味也有快乐,还让人忍俊不禁。从某种程度上讲,正因为“正直、倔强、嫉恶如仇”[5]的寿镜吾老师指导,年少的鲁迅才得以从严酷的封建教育中获得宽松的求学和难得的快乐。
1.3 原创性与诗意美并蓄
作者用原创的手法构筑《百草园》的诗意美,具体如下:
第一,用童心童眼观世界。百草园动植物繁多,高低有致、色艳质美、动静相宜、音韵和谐且险境迭出。鲁迅不只“通过儿童的眼睛”[6]追忆后园的自然风物,还“渗透了他自己童年时代的爱憎情感”[7]。因此儿童扔砖、跳石井栏的舒爽、按斑蝥享视听盛宴的愉悦、食用人形何首乌的嗅觉的快慰和幻境未实现的惆怅、对长妈妈故事的追问和人生体验的失落、对捕鸟的急切渴望和无奈、对求学的从恐惧到害怕再到释然等一系列的精神流变,作者的诗意呈现正是“以儿童的天然的正常的兴趣和爱好作为对人和事的评价尺度”[8];因而读者不仅能畅享“生活的色相”[9],还能理解作者内心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用儿童的眼睛和心理”进行“自觉的儿童世界的复原”[10]的创作方法。
第二,以童言童语写真情。《百草园》语言富有情趣,是用童言童语叙写儿童的爱憎。因为儿童的爱憎没有功利的影响,因而善恶美丑都能客观地呈现。比如,描述孩童仰望式听故事中用短句“后来呢?”,接着模仿长妈妈的口吻回答:“后来,老和尚说......”这些语言描述了儿童感受事物的方式,清晰地镌刻儿童听故事的“精神表情”:无限的神往、极度的渴盼、莫名的恐惧、长久的追问、对真相的渴望。又如描述冬日捕鸟的感悟,作者直接引用了闰土父亲的口语:“你太性急,来不及等它走到中间去”,朴素的话语描摹出孩童急于求成的真实心理。再如,文本从百草园过渡到三味书屋时,作者帅气地连用两次使用德语“Ade”,这既诚恳表达儿童对百草园的不舍,也真实地呈现儿童习惯用特殊口语表达生活的习惯;更用真切的童言童语来探究自己被送进私塾的原因:也许因为拔何首乌、也许因为抛砖头、也许因为跳石井栏……这些发问和一连串思考,构成了幼稚孩童内心真实的惊恐与溯源的疑惑。
第三,画群像立体谈教育。从文题上看,《百草园》写的是乐园游玩和书屋求学;但从教育角度来看,它叙写了对自然教育、民间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综合认知。
儿童在自然间沉浸式赏玩,听听鸟语、闻闻花香、吃吃何首乌根变仙、按按斑蝥见烟雾、想想飞蜈蚣现高能,这是大自然赋予孩子的无形教育。赤练蛇和美女蛇的故事来自坊间传说,讲故事是间接地从语言上训诫儿童的“做人险恶”,这是民间教育在儿童想象力激发的效果;捕鸟是直接地从生活技能上指导儿童面对生活的耐心;闰土父亲指导下的儿童参与式的技能教育,与阿长夏夜讲故事的处世教育彼此呼应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父辈母辈参与的儿童家庭教育的完整版。三味书屋的求学是近代学校教育的地方代表,寿镜吾先生的“方正、质朴、博学”给学生以“身教”,读书习字对课对学生以“言教”,教师沉浸式的朗读给学生以“示范”,给学生去后园玩乐在课堂画画,实则为不愿泯灭的儿童好玩天性以“放风”。
这些教育的呈现不仅以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为教学场域,更是给教育者和受教育对象素描了群像:大自然、长妈妈、闰土父亲、寿镜吾老师为施教者;鲁迅及其同窗则是受教育者;各种教育立体行云流水般展露又悄无声息地诗意呈现。在“朴素的叙述中渗透作者真挚的感情,在简洁洗练的文笔中有深长的韵味;虽为个人回忆,但有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在为数众多的现代散文创作中,它的艺术成就是创造性的。”[11]王瑶的这段评价,是对《百草园》原创性和诗意美的集中评述。
2 无韵的“长诗篇”:从审美性角度看语言铺陈
依据“鲁迅语言的色彩感、音乐感和镜头感”,我们可以把三味书屋部分的“文字文本转化为电影、电视镜头”,转化为画面感极强、人物特写清晰、层次分明的多组镜头。
镜头一:书房里,寿先生答礼的特写。三味书屋中,一字排开的学童们拜了挂画,转而跪拜寿先生,寿先生“高而瘦”,须发花白,戴着大眼睛,和蔼地笑意吟吟地“答礼”;鲁迅毕恭毕敬回礼,心中满是疑问“不要拜孔子吗?”
镜头二:讲台旁,师生问答“怪哉”的慢镜头。满怀期待地,鲁迅问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回事?”先生直接怒怼:“不知道,你只要读书。”鲁迅心里凉了半截,心里十分纳闷,“难道学生不该问这事?寿老师是十分渊博的,这些应该是知道的啊?”
镜头三:书屋中,儿童学习的快镜头。早上“读书”;正午“习字”;夜晚,“对课马上要开始啦,我看到是对独角兽”,“樟寿,你说呢?”“四眼狗吧”。同学欢天喜地,马上用“九头鸟”“四眼狗”“三脚蟾”等答案炮轰寿老师;但寿老师却连连摇头,满怀期待地望着鲁迅。想起老师额外教给自己的《尔雅》中“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鲁迅脱口而出“比目鱼!”“你学得真不错”,鲁迅见到寿老师少有地点头。
镜头四:后园里,同窗玩乐的多镜头。“溜啰,后园去啰!”学童们一个牵着一个,轻手轻脚来到后园。于是在高高的花坛上,有人在折蜡梅花;桂花树旁,有人正蹲着寻蝉蜕;金苍蝇被找到后,孩子们有的玩苍蝇;有的玩“戏棍”,让苍蝇飞舞;有的玩“飞雪”,给苍蝇的腿上缠白纸条;有的玩“喂蚂蚁”,看一群弱小的蚂蚁拖着强大的苍蝇身体离去。
镜头五:书屋里,师生读书乐的双镜头。先闻教师的厉喝“人都到那里去了?!”;后园的孩童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教室;听到“读书”便“放开喉咙”:“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上九潜龙勿用”…… “你念错!”“嘻嘻,你也念错了!”高亢而嘹亮的声音响起“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寿老师正“微笑起来,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
镜头六:课桌上,群童忙“私活”的远镜头。“好啰,做戏啦!”将纸糊的盔甲套在指头上,几个学童做起戏来;鲁迅用荆川纸蒙在《荡寇志》上、蒙在《西游记》上继续描绣像,“可以装订两大本了!”小鲁迅窃喜一番,深吐一口气,把绣像本装入书包,微笑着满心欢喜地离开三味书屋。
上述《百草园》的画面旁,可以配上一行行没有韵脚的诗;因是回忆,所以文本内容可算是诗化的童年;因此《百草园》虽没有整齐的韵脚,却是画面感极强的诗歌,它承载着儿童的情绪流变和审美、诗意的特质,是无韵之诗的散文化。
3 民族的“新文学”:从现代性角度看继承创新
《百草园》不仅继承传统写作手法,更是在“现代思想意识和现代审美品格的确立上”获得了现代性的本质。
首先,《百草园》吸取传统散文的描述性。如儿时的鲁迅玩耍斑蝥的手法颇似沈复在《童趣》于帐中玩弄蚊的场景,“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之冲烟而飞鸣”,孩童因此全身心投入且快乐无比。其次,《百草园》运用“故事体”。如安排长妈妈讲述美女蛇的故事、闰土父亲指导我亲自捕鸟的生活体验,这些故事将梦幻色彩与现实感悟结合起来,反映儿童对世界的理解和抗争,营造了审美的叙述。《百草园》还呈现对传统散文写作的创新。如使用双视角的叙事替代传统散文全知全能的单一视角:主体部分用儿童的视角叙事,用童心童眼看世界呈现纯粹的童真童趣;在首末段、中间部分插入了创作时的成人视角,丰富人们对生活的认知与评判。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思考:《百草园》对春夏冬三季叙写详实,为何缺少对秋季的详叙呢?原来其弟弟周建人创作过《秋草园》,真切摹写周家后园秋季的荒凉和萧索,鲁迅曾为之誊写;由于散文的纪实性,鲁迅不摹写后园的秋季,使《百草园》与《秋草园》形成创作上的互注,也体现了审美性和原创性。
《百草园》艺术构思还源于鲁迅对异域文学样式的自觉接纳与学习,最典型的莫过于鲁迅对德文版《小约翰》和日文版《出了象牙塔之后》的翻译。《小约翰》用儿童的奇幻之旅表达人类在成长经历中的诸多冲突体验;因此我们便理解《百草园》的诸多“冲突”——人形的何首乌根寻而不得的怅惘;美女蛇故事启迪我“做人之险”,我因此时常警惕“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却无果;冬日我渴盼能多捕鸟,却因“太性急”而事与愿违;寿老师雖渊博却怒怼学生问怪哉的话题;最严厉的书塾竟然允许孩子长时间在园里玩乐;孩子们朗读时多处读错,寿老师没有纠错反而自顾自地朗读辞赋;大户周家的长孙上学未写成了书却收获两本绣像;名家早年手记极其尊贵,竟被富商卖去做门面支撑而无法寻觅。《百草园》以童眼回眸过往,用童语描述童年,然而揭示的却是人们在成长道路上的疑惑与矛盾。作者当时的人生处境与《小约翰》的结局相似:“上了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难的路”[12]。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可算是鲁迅“译过《小约翰》后的一种自我追忆。”
如果1927年翻譯德文版的《小约翰》是《百草园》内容的精神来源;那么1925年翻译日本人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塔之后》,则给了《百草园》极好的形式借鉴。对于“Eassy”的风格、写法与作者才思,在《出了象牙塔之后》一书中均有精准的论述。鲁迅正是既“富于诗才学殖,而对于人生的各样的现象,又有奇警的锐敏的透察力”,又“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谈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并“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因而使《百草园》成为“装着随便的涂鸦模样,其实却是用了雕心刻骨的苦心文章”。
对传统散文创作的继承,对兄弟文本的互构,对异域文学样式的学习,鲁迅在《百草园》的创作如黑洞般吸纳诸多的创作智慧,给各代读者无限的解读可能,因而也创建了中华民族文学的新样式。
4 永恒的“百草园”:从历时性角度看历史超越
文学反响效应常分为现实性影响、后时性影响和历时性影响,“经典性的文学作品更着重历时性影响”。
《百草园》用现代性手法描绘天真儿童的梦幻乐园和展示了懵懂少年的求学世界;文字之间流淌着的真实儿童世界的叙述和孩童们真诚无邪的诉说,因此《百草园》不再仅仅属于鲁迅个人的童年追忆,它被后世子孙反复朗读品鉴,并构建各自心中的永不磨灭的“百草园”;这些也成就了《百草园》作为经典的历时性。
鲁迅以《百草园》等“参与了现代叙事散文体式的建构,丰富了现代叙事类美文的形态”[13];也成就了《百草园》的经典性。
参考文献
[1]王泽龙.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典化[J].学术与探究,2002(5).
[2]朱正.跟鲁迅学改文章[M].长沙:岳麓书社,2004:65.
[3]张显凤.母亲的缺席与隐秘的伤痛:再读《朝花夕拾》[J].鲁迅研究月刊,2013(3).
[4]周作人.鲁迅的故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5]苗体君,窦春芳.鲁迅、三味书屋与寿镜吾先生[J].文史月刊,2010(11).
[6]王瑶.鲁迅作品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7]钱理群.让鲁迅回到儿童中间:刘发建《亲近鲁迅》序[J].鲁迅研究月刊,2008(12).
[8]钱理群.和中学老师谈鲁迅作品教学[J].鲁迅研究月刊,2012(1).
[9]鲁迅,朝花夕拾[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64.
[10]丁文.从“秋草园”到“百草园”:文本对话与经典生成[J].现代中文学刊,2017(3).
[11]鲁迅.鲁迅全集(第14卷)[M]//鲁迅,译.小约翰.广州:花城出版社,2021.
[12]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M]//鲁迅,译.出了象牙塔之后.广州:花城出版社,2021.
[13]丁晓原.精神的表情:近代散文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Childrens Spiritual Expressions and Their Poetic Presentation
—Interpretation of From the Hundred herbs Garden to the Bookstore of Three Flavors
Liu W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zhou Xinhua University, Guangzhou
Abstract: Among all the articles of Morning Flowers Picked up at Night, From the Hundred herbs Garden to the Bookstore of Three Flavors is the warmest memories; It not only clearly constructs the poetic and fantastical amusement of the Hundred herbs Garden and the astringent and joyful study of the House of Three Flavors, but also dynamically depicts childrens naive enjoy, longing, fear, contradiction and helplessness, and three-dimensionally casts Lu Xuns critical spirit, educational ideals, and artistic creation concepts. This paper intends to recall the “true fairy tales” of ad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iginality; to sing “long poems” without rhy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s; to explain the “new literature” of th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and to construct the eternal “new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hemer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the “New Literature” of the nation is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lessness, the eternal “Hundred herbs Garden” is constructed; and through this, the expression of childrens spirit and the original poetic qualities of “From the Hundred-Clover Garden to the Bookstore of Three Flavors” are interpreted.
Key words: From the Hundred herbs Garden to the Bookstore of Three Flavors; Spiritual expressions; Original poe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