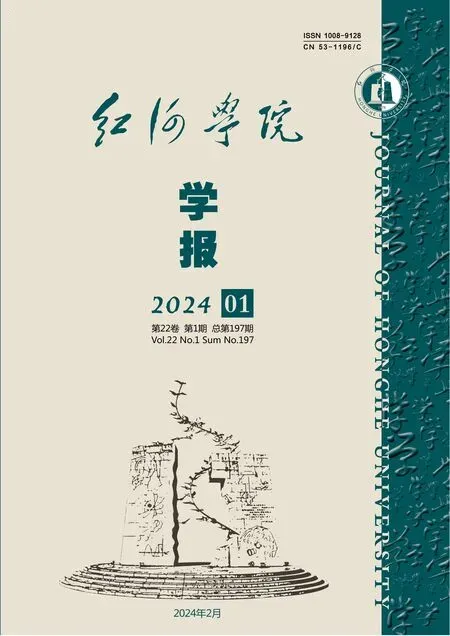基于古歌文本的哈尼族人居环境的演进过程研究
——以《哈尼阿培聪坡坡》为例
李方闰,杨宇亮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云南昆明 650500)
哈尼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境内人口160多万(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居住在云南省南部,除境内外,在缅甸、泰国、老挝、越南也有较多分布[1]。哈尼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他们的风俗礼仪、规章制度、历史传承等都用古歌的形式世代口述传唱。哈尼族古歌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文字系统的传承作用,是哈尼族先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理解人与自然物质能量交换的基本规律、把握筑居和生计生态环境选择、组织生活和生产大小周期律的地方性知识体系[2],蕴含着丰富的人居环境智慧,是研究哈尼族人居环境时空变迁的重要信息源。
人居环境是指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与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是人类在大自然中赖以生存的基地,是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3]。近年来,哈尼族人居环境受到建筑学、风景园林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关注。杨宇亮等[4]以元江南岸为例,分析得出梯田村寨集生产、生活、信仰三类空间为一体,最终形成了小规模、高密度、以哈尼族为主的多民族混居的空间特征。钱云[5]结合北京林业大学团队近年来持续对哈尼族人居环境开展的多项研究,以哈尼族乡土景观为例,从风景园林学的角度研究典型乡土景观,追溯其演变的过程。刘志林等[6]以哈尼梯田核心区为例,分析哈尼族聚居区人居环境分布的空间格局特征。
哈尼族古歌被哈尼族称为“哈尼哈吧”,是哈尼族文化口耳相传的基本方式与主要载体,涵盖了生产生活、风俗礼仪、规章制度、起房盖房、历史传承等极其丰富的内容,哈尼族古歌的主要内容整理如表1所示。

表1 哈尼古歌分类
近年来,哈尼族古歌的学术价值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王馨[7]以《窝果策尼果》《觉麻普德》等古歌为主,阐释了哈尼族古歌是记载哈尼族民族集体记忆的载体,是了解哈尼族历史传承、文明发展的切入点;钱叶春[8]从文化诗学的角度写出《求福歌》在古老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以及人与自然相互化生的神话意识中呈现出奇幻迷离的神秘美;王惠[9]以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得出在迁徙和发展过程中,哈尼族女性扮演了极为重要的社会角色,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王丹[10]以《哈尼阿培聪坡坡》中的生活秩序为核心,写出哈尼族的生活秩序在迁徙中不断舍弃与重建,这些礼俗秩序为哈尼族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制度性安排。以上研究较有代表性,然而,将哈尼族古歌与人居环境相结合的研究并不多。《哈尼阿培聪坡坡》是以研究哈尼族迁徙历史为主的古歌,系统地论述了哈尼族的诞生、发展、迁徙、定居以及各迁居地的生产生活、社会状况、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和各次重大征战等。本文主要以《哈尼阿培聪坡坡》中所记录的伴随着哈尼族迁徙地的变化其居住方式、生产生活、社会发展也随之变化的关系,来探讨哈尼族人居环境的变迁。
综上,对于哈尼族人居环境的研究多集中于聚落空间、建筑本体与地方景观。而对哈尼族人居环境变迁的历时性研究却受限于历史材料的缺失,还非常少见。为此,本文以哈尼族最重要的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11](以下简称《聪坡坡》)为信息源,尝试通过文本探寻与田野调查的结合发掘哈尼族的人居环境智慧,探讨哈尼族人居环境的演进过程。
一、以迁徙为线索的人居环境变迁史
哈尼族原属氐羌系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迁徙之后才定居于今天的哀牢山区,迁徙是哈尼族最重要的历史记忆,正是在迁徙这一紧密关涉所有族群成员的历史场景中,哈尼族先民以共有的历史与文化凝聚起共同记忆,逐渐形成对“哈尼族”身份的族群认同,人居环境也参与构建了此认同过程。正是在迁徙过程中,哈尼族的人居环境经历了从居无定所、到定居村落、再到人居环境的成熟与模式化的变迁过程。可以说,族群迁徙构成了哈尼族人居环境变迁的基本线索,而《聪坡坡》就是众多哈尼族古歌中最重要的迁徙史诗。通过对《聪坡坡》的梳理,结合地理因素考量,我们可以勾勒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迁徙路径,如表2所示。

表2 哈尼族迁徙的基本概况[11]3-271
据《聪坡坡》记载,哈尼族先民最初生活于虎尼虎那,居住了23代人,后来历经什虽湖边、嘎鲁嘎则、惹罗普楚、诺马阿美、色厄作娘、谷哈密查等地后,又在元江北岸石七等地,最后定居于元江南岸的哀牢山区。在漫长与复杂的迁徙过程中,对于迁徙地点与现地名的对应关系等关键信息,学界尚有不同意见,现代汉语地名一列是采用目前可信度较高的史军超[12]学者的研究。然而,作为典型的稻作民族,哈尼族异常重视水稻种植,《聪坡坡》中有大量针对生计方式变迁的清晰信息,而人居环境恰恰是对生计方式做出适时调适和与之匹配的结果。因此,以贯穿迁徙过程中的生计方式变迁为线索,可将哈尼族的人居环境变迁分为三个阶段:生活于“虎尼虎那”的“起源—自发”阶段、从“什虽湖”到“石七”的“发展—自觉”阶段,以及最终定居于元江南岸的“完善—自为”阶段。其中,起源、发展、完善是对过程的描述,自发、自觉和自为是对人居行为的性质概括。
二、“起源—自发”阶段:人为营建的开端
(一)高山环境中的群居生活
《聪坡坡》记载:“在那远古的年代,天边有个叫虎尼虎那的地方,奇怪的巨石成千上万,垒成了神奇巍峨的高山。哈尼先祖就出生在这个地方。虎尼虎那神奇又荒凉,五彩云霞在岩石上飘荡;找着吃食,他们吃撑肠肚,找不着东西,他们饿倒地上,看见猴子摘果,他们学着摘来吃,看见竹鼠刨笋,他们跟着刨来尝。”[11]3-12哈尼族先民最初生活的虎那虎那应为高山环境,天然资源丰富。后来,“炸雷把大树劈到在地上,森林里烧起了七天不熄的大火。火光把先祖的眼睛照亮,先祖把火种捧回山洞,把它小小心心保藏”[11]12。哈尼族先民学会了使用和保存火种,大大增强了适应自然与利用自然的能力。哈尼族先民还观察到,“小小的蚂蚁抬得起老鼠,比蚂蚁大的人抬得起大象,老老少少都跟我上山去,齐心合力把野物敲翻,惹斗领着大家去打猎,从这山爬到那山”[11]15。在初辟鸿蒙的虎尼虎那时期,哈尼族先民以采集狩猎的方式,过着集体劳动、居无定所的群居生活。
(二)从洞居到树居的原始聚居点
在虎尼虎那,哈尼族先民“撵跑豹子,他们就搬进岩洞,吓走大蟒,他们就住进洞房”[11]11,洞居成为主要居住方式。洞居以天然山洞作为栖息地,是大自然造就的原始空间,虽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却为房屋的构建提供很大参考价值,哈尼族先民正是借助于在洞居阶段得到的空间体验去营建房屋的[13]。对哈尼族而言,洞居有一种磁性引力的作用,这种磁性引力来源于它已被哈尼族意识到的安全保障功能,每当天黑或危险来临之际,哈尼族先民便进入山洞,以求得身体与心理的安适与平衡。“哈尼先祖生养下了大群儿孙,石洞不能再当容身的地方。看见喜鹊喳喳地笑着做窝,先祖也搭起圆圆的鸟窝房。”[11]13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居住需要也在持续增长。山洞作为居住场所把人限制在狭小范围内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洞居的价值逐渐衰落。为此,哈尼族先民开始学着喜鹊做窝,在树上搭建起属于自己的鸟窝房,其居住方式由洞居演进为树居。“鸟窝房搭上树杈,冷天暖和热天荫凉,圆圆的房子开着圆圆的门,堵起大门不怕虎狼。”[11]13鸟窝房是哈尼族先祖走出山洞后建造的第一代房屋,其基本形式是在大树杈上架以枝条,铺垫枝叶茅草作为栖息之所,树居可以防止野兽侵袭,起到保护族人的作用,哈尼族的人居环境从原始的自然庇护上升到人为庇护,从居无定所的生活中萌发出最初的定居意识。
“起源—自发”阶段是哈尼族萌生出人类意识与行为的初民社会时期,哈尼族先民在采集狩猎的生活中,会本能选择、利用天然物满足基本的庇护需求,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是一种“自发”性质的人居行为。
三、“发展—自觉”阶段:在模仿自然中调适
(一)农业的产生与发展
“从前人见野物就跑,现在野物逃到远方,先祖们找不着肉了,两座山峰戳上肩膀。”[11]17随着人口增加导致天然食物资源越来越少,哈尼族人们不得不迁离故土,寻找新的家园。“先祖离开住惯的山岗,艾地戈耶把先祖领到新的住处,这里有宽宽的水塘,先祖就在什虽湖边盖起住房。”[11]18-19这一次顺水而徙的行为,使哈尼族从海拔高的虎尼虎那走向了海拔低的什虽湖畔,并在半定居的生活中学会了饲养野物和种植草籽,“才下的小猪肉不香,不如将它喂养,再破它的肚肠,遮姒把小猪抱去,从此把野物饲养;黄生生的草籽结满草秆,先祖们吃着喷香的草籽,起名叫玉麦和高粱”[11]21-23,动物驯养与原始农业的发展使哈尼族先族摆脱了对天然资源的简单依赖,培养了最初的种植经验,走上通过劳作满足自身基本需求的生计方式道路。
当“哈尼来到南方的群山,来到嘎鲁嘎则地方”[11]27时,与南方古老的稻作民族——阿撮(傣族)相遇,“阿撮教哈尼破竹编箩,阿撮教哈尼织帽子”[11]28,由于之前哈尼族社会并未出现水稻这一作物,傣族是稻作民族,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哈尼族可能在嘎鲁嘎则向傣族学习了种植水稻。在低山环境的惹罗普楚,哈尼族先民第一次开发出大田、种植水稻,“新谷回家的时节,脚碉像啄木鸟把树敲响,清香的新米煮好了,头一碗给阿波阿匹先尝”[11]40-41,自此开启了哈尼族农业和历史的新篇章,开始向南方稻作民族的转变历程。水稻种植伴随着定居生活,导致了哈尼族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飞跃,开始从采集型简单社会向复杂型农业社会的转变,如社会分工细化,“寨里出了头人、贝玛、工匠,能人们把大事小事分掌”[11]43,以及规模化的商业活动。
在掌握了稻作种植技能后,哈尼族在后续迁徙中,始终优选位于坝区、适宜种植水稻的环境:如在诺马阿美生活了13代,稳定的稻作定居生活使水稻农业水平进一步提高;在谷哈密查期间,“哈尼学会烧石化水,也学会造犁铸剑”[11]162,掌握炼铁技术制造新的生产工具,带来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持续提升;在石七开出“纳罗普楚”[11]240的大寨,使“荒凉贫瘠的石七,一天变出七个样”[11]241,哈尼族先民在此时已熟练掌握稻作生产的相关技术,农业生产水平已发展到较高程度。这些在坝区环境中持续积累种植水稻的农耕智慧,为定居哀牢山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从半定居到定居型村落
伴随着稻作农业的产生与发展,哈尼族也从半定居过渡到定居阶段。在什虽湖边,“先祖去撵野物,烈火烧遍大山”[11]25,的经历表明,打猎、烧山游耕还很普遍,哈尼族在此阶段的居住方式应为半定居。直至惹罗普楚,哈尼族先民彻底结束了游耕的历史,定居化的人居行为开始固定下来,“哈尼忘不了惹罗,那头一回安寨定居的地方,那头一回开发大田的地方”[11]32,其人居环境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初步总结出“惹罗古规”这一哈尼族人居环境基本原则。
就聚落层面,“一寨最大的是神山,神山上块块石头都神圣,神山上棵棵大树都吉祥,大寨要安在那高高的凹塘,寨头要栽三排棕树,寨脚要栽三排金竹,吃水要吃欢笑的泉水,住房要住好瞧的蘑菇房”[11]247-248,惹罗古规中涉及如下人居环境要素:神山、神树、凹塘、寨头、寨脚、水源、蘑菇房。其中,凹塘是寨址所在,位于寨头和寨脚之间,“上头的山包做枕头,下头的山包做歇脚,两边的山包做护手,寨子就睡在中央。神山神树样样不缺,寨房秋房样样恰当”[11]270。
就民居层面,“惹罗的哈尼是建寨的哈尼,一切要改过老样。难瞧难住的鸟窝房不能要了,先祖们盖起座座新房。惹罗高山红红绿绿,大地蘑菇遍地生长。小小蘑菇不怕风雨,美丽的样子叫人难忘。比着样子盖起蘑菇房,直到今天它还遍布哈尼的家乡;哈尼姑娘和媳妇,盖房时候最忙,姑娘上山割来茅草,落在蘑菇盖上”[11]37-39,哈尼族先民模仿蘑菇的特点,盖起了蘑菇房,并成为哈尼族传统民居的基本样式。早期的蘑菇房应该是坡屋型的草顶,以适应惹罗普楚山地型的多雨环境。在诺马阿美,“先祖又把新的式样增添,两层的房子又多建一层,矮矮的耳房站在旁边。房顶修成平平的晒台,老人爱去烤太阳,小娃爱去摔大跤”[11]66,从惹罗普楚到诺马阿美的蘑菇房变化,是应对地理环境差异的有效措施:前者位于多雨的低山环境,后者位于海拔更低、干热型坝区,平屋顶的形式显然应对了干燥少雨的环境,晒台的为晾晒作物提供了较好的功能空间。主房与较矮的耳房围合成“一正一耳”的布局,应与后者较为平坦的坝区环境有关。蘑菇房在满足“惹罗古规”的前提下,表现出形态与功能的灵活调适。
在从“什虽湖”到“石七”的“发展—自觉”阶段,哈尼族先民在定居环境中萌发出自觉意识,进一步摆脱自然环境对人的约束,在宏观层面总结出组成人居环境中的若干要素,在微观层面则以对蘑菇的形态模仿,初步形成适应环境、功能合理的民居形式。这一切表明,哈尼族已经能够凭借以自身能力,“自觉”构建与自然环境、生计方式相适应的人居环境。
四、“完善—自为”阶段:新环境中的成熟与模式化
(一)山地环境对坝区稻作的调适
经过漫长艰辛的迁徙,哈尼族先民最后南渡红河,进入哀牢山区。“人定居在哪里,先要确定建寨的地点。从前哈尼爱找平坝,平坝给哈尼带来悲伤,哈尼再不找坝子了,要找厚厚的老林高高的山场,山高林密的凹塘,是哈尼亲亲的爹娘;走进旺旺的草丛,绕过高高的老崖,望见迷人的地方。”[11]262-264由于迁徙的苦难记忆,哈尼族在选择寨址时非常注重隐蔽性和防御性,“山高林密的凹塘”为等高线内凹、四周林木繁茂的微地貌,具备较好的隐蔽性、相对平缓的坡度、以及丰沛的水源,是哈尼族人居环境的理想场地。
开田与安寨是同步进行的,即将原始山地改造成能种植水稻的耕作用地。哀牢山是横断山余脉,山地特征发育显著,这对习惯于平坝稻作农耕的哈尼族祖先,无疑是严峻的挑战。“搬开黑亮的石头,把大田开到山上,引来清亮的泉水,栽出绿绿的稻秧,到秋风吹起的时候,山上山下一片金黄。”[11]241-242文学化的表述,不能掩盖坝区稻作智慧迁移中的复杂性。以稻种选择为例,根据哀牢山区垂直气候分异显著的特点,哈尼族先民培育了许多稻种,分别在不同海拔高度、不同气候中种植,大致而言,在海拔1600 至1900 米的气候温凉的上半山,使用小花谷、小白谷等耐寒稻谷品种;在海拔1200 至1600 米的气温温和的中半山,使用大老梗谷、细老梗谷等温性高棵稻谷品种;在海拔800至1200 米的气候温热的下半山,使用老皮谷、老糙谷等耐热稻谷品种;在800米以下的炎热河谷,使用麻糯等耐高热稻谷品种[14]。
分配、管理好水资源也是山地稻作中必须考虑的要素[15]。“崖缝里冒出大股清泉,像沸腾的水珠串串。”[11]64-65哈尼族先民创造了木刻分水法:即用质地坚硬的木材,根据每户梯田的面积,刻出宽度不同的槽口来约定每条水沟应该分得的用水量,带凹槽的横木就是分配水源的一把尺子。分水一般由“咪谷”牵头,经全村人协商、约定每条水沟应分得的用水量,由年长且有威望的老者在横木上凿出开口宽度、深浅不一的凹槽,将之安置在渠道的分水口处,水流沿着凹槽流入支渠灌溉梯田。
哈尼族先民正是基于坝区稻作技术的调适,根据哀牢山的环境条件,最终累积为适应地域环境中的生存智慧,创造出世所瞩目的哈尼梯田。
(二)人居环境的成熟与模式化
在哀牢山区,哈尼族遵循“惹罗古规”的基本原则,对人居环境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并在山地环境中成熟完善,形成相应模式。
1.模式一:“四素同构”的聚落整体格局
在聚落整体层面,哈尼族聚落形成以森林在上、村落居中、梯田在下、水系贯穿其中的人居环境格局。寨子上方有森林,下方有梯田,森林涵养水分并形成溪流,供日常生活使用并灌溉梯田,“森林、村寨、梯田、溪流”形成了“四素同构”的整体格局[16]。在这一自洽系统中,郁郁葱葱的树木在维持生态、提供水源的同时,也保护村寨免受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村寨居中方便森林管理和梯田耕作;层层梯田错落有致,为哈尼族提供最基础的食品保障;源源不断的水流自上而下贯穿村寨和梯田,解决了人畜饮水和灌溉梯田的问题,实现了各系统间物质与能量的交换。
2.模式二:“寨头、寨心、寨脚”的村落空间结构
在村落层面,哈尼族村寨形成以“寨头、寨心、寨脚”三要素构成的空间结构。“上头的山包像斜插的手,寨头靠着交叉的山岗。下面的山包像牛牴架,寨脚就建在这个地方。寨心安在哪里?就在凹塘中央。”[11]35“寨头”即“寨神林”,位于寨子的上方,是“寨神”居住的地方。在森林与村寨之间,哈尼族会挑选一片树林作为护佑村寨的寨神林,再挑选一棵粗壮、健康的树作为神树。寨神林是哈尼族一年一度祭祀寨神的场所,每年二月“昂玛突”节,哈尼族男子便带着祭祀物品进入寨神林祭祀寨神,祈祷村寨平安、家庭安康、六畜兴旺。“寨心”即“凹塘”,包括主体建筑蘑菇房,以及水井、长宴街、水碾房等公共空间。水井是寨中村民使用最频繁的日常空间;长宴街是哈尼族过十月年时举行长街宴的地方;水碾房主要用于加工粮食。“寨脚”以介于村寨与梯田之间的“磨秋场”为主体,是每年“矻扎扎节”祈愿秋收丰产的场所,附设祭祀房。“寨头、寨心、寨脚”三者缺一不可。
3.模式三:民居的基本样式——“蘑菇房”
在民居层面,蘑菇房构成了聚居主体。蘑菇房为木构土墙的民居,材料为木材、土坯、石头、茅草,木材即采用当地山林中的冬瓜树,屋顶用稻草覆盖。蘑菇房多为三层,首层低矮潮湿,主要用于饲养牲畜和堆放农具;二层作为村民日常生活的主要空间,以火塘为中心,紧凑的空间安排应与山地环境中的用地紧张有关,二层室外平台是室内起居空间的延伸,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空间的不足[16];三层主要用作储藏粮食的空间,也有一个晾晒作物的平台,其余以草顶覆盖。这一点有别于“谷哈密查”时期的平顶蘑菇房,其形式与功能的安排,显然更能适应潮湿多雨的稻作适宜气候,也能适应山地环境的稻作生计方式。
正是通过以上三种模式的完善,哈尼族的人居环境在聚落整体、村落结构、民居特征三个层面均已成熟,发展出定型化的人居模式,不仅足以自如应对哀牢山区对人居环境的约束,还承袭“惹罗古规”,成为哈尼族人身份认同的基本符号,具有“自为”特征。
五、结论
文章以哈尼族古歌作为信息源,通过文本探寻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对哈尼族人居环境开展历时研究,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贯穿民族历史的迁徙过程构成了哈尼族人居环境变迁的基本线索,习得水稻种植是哈尼族在迁徙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以此可将哈尼族的人居环境分为“起源—自发”“发展—自觉”“完善—自为”三个阶段。
第二,在“起源—自发”阶段,哈尼族先民居住于高山环境,在采集狩猎的生活中,会自发的选择、利用天然物满足基本的庇护需求;在“发展—自觉”阶段,哈尼族先民在迁徙中学会了水稻种植,在定居中“自觉”构建与自然环境、生计方式相适应的人居环境,并在宏观、微观层面初步形成“惹罗古规”的人居环境框架;在“完善—自为”阶段,哈尼族熟练掌握了山地精耕稻作的生计方式,人居环境在聚落整体、村落结构、民居特征三个层面均已成熟并定型化,并成为哈尼族人身份认同的基本符号。
第三,哈尼族古歌是哈尼族先民智慧的结晶,蕴含着大量的历史与族群记忆,是研究哈尼族人居环境时空变迁的重要信息源。很多少数民族都有类似的口述族群记忆,以此开展人居环境的相关研究,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普遍意义。
——以宁波市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