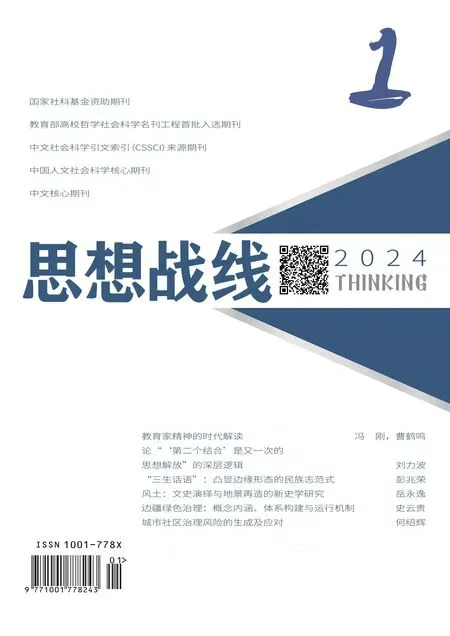主佃借贷与贫富相资
——对宋代契约租佃制下富民借贷的探讨
黎志刚
宋代是我国古代契约租佃关系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同时也是民间借贷关系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契约租佃关系和民间借贷关系的结合,主佃借贷成为这一时期日益普遍的一种借贷形式。关于这一时期租佃关系的变化,学术界已经有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1)关于唐宋以来租佃关系的新发展,梁庚尧、葛金芳、林文勋诸先生都有精彩论述,具体可参见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葛金芳:《中国近世农村经济制度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日本学者高桥芳郎对宋代以后主佃之间的法律关系变迁做过专门探讨([日]高桥芳郎:《宋至清代身分法研究》,李冰逆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此外,杨宇勋、王文书等分别论述了灾荒救济中贫富相资的借贷行为及借贷思想。本文试图选择主佃关系中的借贷关系为研究对象,对宋代经济关系的发展进行具体探讨,以进一步深化对宋代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
一、宋代民间借贷与契约租佃关系的发展
宋代,中国古代民间借贷关系获得空前发展。这一时期,民间借贷渗入小农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成为小农延续再生产的重要影响因素。北宋时,祖无择就提到当时的“田农之家,往往举息钱以市种与牛,乃克播种”。(2)祖无择:《谢雨祝文》,《全宋文》卷九三七《祖无择四》,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50页。到了南宋,真德秀称:“下等农民之家,赁耕牛,买谷种,一切出于举债。”(3)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六《对越甲稿·奏乞蠲阁夏税秋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94页。当时的一些农家,“夏田才种,则指为借贷之本以度冬;秋田甫插,则倚为举债之资以度夏”。(4)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六《对越甲稿·奏乞倚阁第四第五等人户夏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06页。可见,借贷关系已经深深影响到小农经济,成为农业再生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使得这一时期的小农经济发生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变化。所以南宋人王柏总结道:“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5)王柏:《鲁斋集》卷七《社仓利害书》,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这一时期,也是租佃契约关系大发展的时期。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和土地兼并的盛行,契约租佃关系进一步发展。北宋神宗时期,吕陶称:“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耕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6)吕陶:《论限名田责宰守疏》,《全宋文》卷一五九八《吕陶一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32页。到了南宋更是如此,陆九渊就指出:“所谓农民者,非佃客庄,则佃官庄,其为下户自有田者亦无几。”(7)陆九渊:《陆九渊集》卷八《与陈教授》,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8页。黄震甚至以“近世有田者不种,种田者无田”(8)黄震:《黄震全集·黄氏日抄》卷七八《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21页。来总结这一时期租佃关系的发展程度。正因为如此,苏辙就这样描述宋代社会的情形:“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无田者为之耕。无田者非有以属于天子也,而有田者拘之……故夫今之农者,举非天子之农,而富人之农也。”(9)苏辙著,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应诏集》卷十《进策五道·第二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87页。这充分反映了契约租佃关系已经在社会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随着契约租佃关系主导地位的确立,民间借贷关系与契约租佃关系的结合表现得越来越紧密,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经济关系。朱熹就说:“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讨田耕作,每至耕种耘田时节,又就田主生借谷米,及至终冬成熟,方始一并填还。”(10)朱熹:《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〇〇《劝农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624页。早在北宋,陈舜俞就称:“千夫之乡,耕人之田者九百夫,犁牛稼器无所不赁于人。”(11)陈舜俞:《都官集》卷二《厚生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而在四川地区,“民多大姓,每一姓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赖衣食贷借,仰以为生”。(12)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附录三·韩魏公家传》,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1851页。在许多地区,佃户在需要资金种食时,向地主进行借贷往往成为他们的首选,并成为一种习俗和被社会普遍认同的行为。如朱熹就称:“州县火客佃户,耕作主家田土,用力为多,全仰主家借贷应副。”(13)朱熹:《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九《约束粜米及劫掠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608页。这些地主“递年多是春间将米谷等先放下户,秋冬随例收息”。(14)朱熹:《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十《再谕上户借贷米谷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044页。因此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针对贫民缺稻种的情况,就指出“乡俗体例,并是田主之家给借”,并因此“欲依乡俗体例,各请田主每一石地借与租户种谷三升,应副及时布种,候收成日带还,不得因而收息。如有少欠,官司专与催理,不同寻常债负”。(15)朱熹:《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一《乞给借稻种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946页。可见,佃农向地主借贷谷米这种主佃借贷形式已经形成一种常年惯例,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一种普遍情形。
二、主佃借贷与宋代贫富关系的新变化
这一时期日益普遍的主佃借贷现象,实际上是契约租佃制度与民间借贷关系相结合的集中体现,其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也体现了均田制瓦解后地主和佃户关系的特点。这种借贷关系以主佃双方为主体而展开,主要原因是主佃双方经济依赖性加强,即地主和佃户在经济关系上的“贫富相资”。
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度的瓦解和土地自由流转的加剧,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富民阶层”崛起并日益成为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核心。(16)林文勋,谷更有:《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5-67页。而在农业生产领域,主要表现为富民取代国家,成为对小农生产、生活影响最大的社会群体。宋人王柏说:“田不井授,王政堙芜,官不养民而民养官矣。农夫资巨室之土,巨家资农夫之力,彼此自相资,有无自相恤而官不与也。故曰官不养民。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以之禄士,以之饷军,经费万端,其始尽出于农也,故曰民养官矣。”(17)王柏:《鲁斋集》卷七《赈济利害书》,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这种农夫和巨室间“彼此自相资,有无自相恤,而官不与也”情形的出现,正是主佃之间经济依赖性加强的鲜明体现。
关于契约租佃制度下这种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学界以前主要看到的是对立斗争的一面,而对其相互依存的一面看到的较少。对此,林文勋先生已经有过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宋代地主与佃户的关系类似于明清苏州纺织业中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都是商品经济下的一种劳资双方的经济依赖关系,地主和佃户在经济上互相依存,具有共同的利益。(18)参见林文勋:《唐宋历史观与唐宋史研究的开拓》,载中国史学会,云南大学编:《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74页。宋代,已经有许多人认识到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民间借贷关系与租佃关系,都是贫富相资、主佃相依的重要表现,也是双方共同利益存在的必然结果。正如宋神宗时御史中丞邓绾在上奏中说的:“富者所以奉公上而不匮,盖常资之于贫。贫者所以无产业而能生,盖皆资之于富。稼穑耕锄,以有易无,贸易其有余,补救其不足,朝求夕索,春贷秋偿,贫富相资,以养生送死,民之常也。”(1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神宗熙宁八年冬十月辛亥”,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605页。朱熹也说:“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借以养活家口,田主亦藉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立。”(20)朱熹:《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〇〇《劝农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624页。这生动地说明了主佃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没有地主,佃农无法获得土地和资金从事生产,而没有佃农,地主也无法获得财富的积累。而主佃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正是通过租佃关系和借贷关系来实现,并在这种经济关系的联结中而进一步加强。陆游就说:“贷粮助耕耘,客主更相依。”(21)陆游著,钱忠联校注:《陆游全集校注·剑南诗稿》卷四〇《九月七日子坦子聿俱出敛租谷鸡初鸣而行甲夜始归劳以此诗》,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60页。所以袁采说:“假贷钱谷,责令还息,正是贫富相资不可阙者。”(22)袁采:《袁氏世范》卷三《假贷取息贵得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64页。主佃借贷这种契约租佃制度下的民间借贷形式,既是契约租佃制度的重要补充,也是贫富相资的重要体现。
这种主佃间贫富相资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是一种双向而非单向的紧密联系,并导向双赢的结果。一方面,作为农业生产主要劳动力的小农,往往是“室庐之备、耕稼之资、刍粮之费,百无一有”,只有靠地主提供土地、房屋、耕种资金来延续再生产和生活。虽然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人身的依附关系,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主要是因为经济关系而暂时存在,小农在这种经济关系中绝不只是被兼并的对象,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辛勤耕作积累财富,摆脱这种依附关系,文献记载,宋代的小农“或丁口蕃多,衣食有余,稍能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主户而去”。(23)胡宏:《胡宏集·书·与刘信叔书五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7页。从实践来看,这更多的是一种经济合作关系而非人身依附关系。小农绝不只是被兼并和剥削的对象,他们通过这种租佃和借贷关系,不仅可以维持再生产,也可以实现积蓄,甚至有可能通过积蓄购买田产上升为富农地主,进而“再传而后,主佃易势”,(2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主佃争墓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25页。成为新的富民。而主佃之间的这种借贷关系,也因此某种程度上更加具有了互利的色彩,与其说是阶级阶层之间的借贷,不如说是社会群体之间的借贷,是社会群体间资金的有无调剂。这表现在不仅佃户对地主有强烈的依赖,地主也对佃农有强烈的依赖。南宋人袁采就说:“人家耕种出于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为重!遇其有生育、婚嫁、营造、死亡,当厚周之。耕耘之际,有所假贷,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亏,早为除减。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时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干人私有所扰;不可因其仇者告语增其岁入之租;不可强其称贷,使厚供息;不可见其自有田园,辄起贪图之意。视之爱之,不啻如骨肉,则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俯仰可以无愧怍矣。”(25)袁采:《袁氏世范》卷三《存恤佃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50页。可见富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其与佃农共同的经济利益,认为在耕耘之际,要有所借贷,并少收其利息。苏轼也说:“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课,非行仁义。然犹至水旱之岁,必须放免缺负、借贷租粮者,其心诚恐客散而田荒,后日之失,倍于今故也。”(26)苏轼:《苏轼文集》卷三一《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82页。
特别是在灾荒年间,如果富民不主动对佃农进行借贷救济,最终损害的是自己的利益。根据宋人的记载来看,随着契约租佃关系主导地位的确立,灾荒中富民成为流民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显著的现象。这就是因为佃户流移,导致富民也无法顺利实现土地的经营并获取财富。宋神宗便指出:“近河北镇、赵、邢、洺、磁、相等流民过京师者,甚有力及户,闻非因灾伤乏食就谷,止缘客户多已逃移,富者独不敢安处田里。”(2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六,“熙宁七年九月庚子”,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249页。南宋人郑侠同样目睹了这样的情形,他提到熙宁年间流民众多,“其间有稍富者,问其徙之因,曰:‘贫富大小之家,皆相依倚以成,贫者依富,小者依大,所以养其贫且小,富者亦依贫以成其富,而大者亦依小以成其大,富者、大者不过有财帛仓廪之属,小民无田宅,皆客于人,其负贩耕耘,无非出息以取本于富且大者,而后富者日以富,而以其田宅之客为力,今贫者小者既已流迁,田无人耕,宅无人居,财帛菽粟之在廪庾,众暴群至,负之而去,谁与守者?此所以不得不随而流迁者也’”。(28)郑侠:《西塘集》卷一《流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除了灾荒时期,在日常的农业生产中主佃借贷也成为维系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这不仅表现为地主依靠借贷佃户来维系契约租佃关系,也表现为佃户通过借贷地主来维系契约租佃关系。宋代社会中地主对佃户的借贷屡见不鲜,但也存在佃户对地主的借贷,《东轩笔录》中就提到了这样一件事,宋太祖时汜县的酒务专知官李诚,有庄田“方圆十里,河贯其中,尤为膏腴。有佃户百家,岁纳租课,亦皆奥族矣”,后来庄田因故为官府籍没。贾昌朝做宰相时,命汜县官吏措置出卖,当时的县尉侯叔献主张由李诚后人购买,但无奈李诚的孙子财力不足,最后李诚庄的佃户共同凑钱借贷给李诚的孙子,从而赎回庄田,并以此维系了这种租佃契约关系。
(侯)叔献乃召诚孙,俾买其田。诚孙曰:“实荷公惠,奈甚贫何!”叔献曰:“吾有策矣。”即召见佃田户,谕之曰:“汝辈本皆下户,因佃李庄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今李孙欲买田,而患无力,若使他人得之,必遣汝辈矣。汝辈必毁宅撤廪,离业而去,不免流离失职。何若醵钱借与诚孙,俾得此田,而汝辈常为佃户,不失居业,而两获所利耶?”皆拜曰:“愿如公言。”由是诚孙卒得此田矣。(29)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2-93页。
这一事例不是地主借贷给佃户,而是佃户借贷给地主。这些佃户之所以愿意凑钱借给李诚的孙子赎回庄田,不仅是因为他们“本皆下户,因佃李庄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更是为了今后能够“常为佃户,不失居业,而两获所利”。这不仅表明了借贷关系在维系租佃契约关系上的重要作用,也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租佃契约关系的发展是主佃双方共同利益的必然选择,是当时极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所以,单纯地把主佃借贷关系看做是主户对佃户的剥削是不对的,无论是地主向佃户借贷还是佃户向地主借贷,这种主佃借贷关系的形成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主佃双方之间存在的共同的利益。而正因为如此,主佃借贷关系也就成为贫富相资的主要内容,成为契约租佃关系的必要补充。
这种主佃相依关系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众所周知,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土地和资金。中国民间俗语常说:“有土斯有财。”宋人也强调:“农为四民之本,食居八政之先,丰歉无常,当有储蓄。”(30)陆游著,马亚中,涂小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卷二五《丁未严州劝农文》,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6页。资金和土地作为小农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不可缺少的作用。只有小农能够顺畅获取到土地、资金等重要生产要素,农业生产才能获得迅速发展。唐宋以前,这方面主要靠国家力量来保障。在井田制和均田制下,国家主要通过土地分配,保障了小农的土地占有,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而当小农缺乏种子、资金等生产要素时,也可以通过国家的赈贷等“补助之法”来获取。《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提到国家“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郑玄注曰:“散利,贷种食也。”唐人贾公彦疏云:“丰时敛之,凶时散之,其民无者,以公贷之。”(31)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一九《地官·大司徒》,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41-742页。可见国家的赈贷成为小农生产资金的重要来源,《管子》中就说:小农“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钟饷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32)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二二《国蓄第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由于国家在土地政策和赈贷制度上的作用,唐宋以前,通过国家力量使农业生产要素得到了有效结合。
而唐宋以后,随着富民阶层的崛起,这一状况发生了改变。富民作为财富力量的代表,占有了大量的资金,而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和不抑兼并政策的实施,他们又通过土地的买卖获取了大量的土地,从而一跃而成为土地和财富的主要拥有者。而丧失了自身土地的自耕小农则成为迫切希望获取土地和资金的劳动力。在这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组中,农业生产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须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三大生产要素的重新结合。由于富民与贫民一样,同属于“齐民”的一种,他就只能主要通过租佃契约和民间借贷这两种经济关系来实现小农与土地、资金的结合。贫民与富民之间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形成,正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贫富双方利益的必然要求。刘秋根教授认为,中国农业金融史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自战国、秦汉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中叶为第一阶段;自唐代中叶经宋元至明代中叶为第二阶段;自明代中叶至鸦片战争前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家主导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地主阶级主导的阶段;第三阶段则是商人阶级主导的阶段”。(33)刘秋根:《中国封建社会农业金融发展阶段初探》,《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刘秋根教授所指的地主阶级,在乡村中主要就是地主。而地主之所以成为这一时期农村金融的主导群体,正是由整个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化带来的。主佃借贷作为契约租佃制度与民间借贷关系的集中体现迅速发展起来,也是社会经济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必然结果。南宋时,叶适说:“县官不幸而失养民之权,转归于富人,其积非一世也。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技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34)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二《民事下》,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57页。这表明小农经济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而契约租佃下的小农经济模式因为能够使土地、资金和小农本身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已经成为当时更有效率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
三、主佃借贷的双重性与政府调适
主佃借贷这种契约租佃下的借贷行为带有双重性,正如北宋胡寅所说:“称贷所以惠民,亦以病之。”(3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六《国用考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66页。一方面,一些主佃之间的借贷与其他借贷形式一样,是为了获取高额的利息。欧阳修在《原弊》一文中就指出,富民对佃农的借贷加剧了贫富的分化和兼并。他说:
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顷者,养客数十家,其间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过十余户。其余皆出产租而侨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数十家者,素非富而蓄积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与公家之事,当其乏时,尝举责于主人,而后偿之,息不两倍则三倍。及其成也,出种与税而后分之,偿三倍之息,尽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场功朝毕而暮乏食,则又举之。故冬春举食则指麦于夏而偿,麦偿尽矣,夏秋则指禾于冬而偿也。似此数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户常尽取百顷之利也。(36)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六〇《原弊》,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871页。
虽然欧阳修指出的佃农向地主借贷“息不两倍则三倍”,等到收获时“偿三倍之息,尽其所得或不能足”的说法未必是普遍情形,但地主借贷佃农追求高利息的情况无疑是存在的。
但另一方面,由于共同利益的存在,与其他一些高利借贷相比较起来,这种借贷却更多地表现出温情的一面,利息相对较低,对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也更大。如宋人薛季宣描述当时看到的情形就指出:“安丰之境,主户常苦无客,今岁流移至者争欲得之,借贷种粮与夫室庐、牛具之属,其动费百千计,例不取息。”(37)薛季宣撰,张良权点校:《薛季宣集》卷一七《奉使淮西与虞丞相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09页。这尤其表现在一旦发生灾荒,一般的佃农因为有来自地主的借贷,反而比自耕农受到的打击更小,更易于维持生产和生活。而由于缺乏主佃间这种借贷关系的救济,有田的自耕农或中农甚至比佃农更为可怜。如南宋真德秀就说:“若五等下户,才有寸土,即不预粜,其为可怜更甚于无田之家。盖其名虽有田,实不足以自给,当农事方兴之际,称贷富民,出息数倍以为耕种之资,及至秋成不能尽偿,则又转息为本,其为困苦,已不胜言,一有艰歉,富民不肯出贷,则其束手无策,坐视田畴之荒芜,有流移转徙而已。”(38)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一〇《对越甲稿·申尚书省乞拨和籴米及回籴马谷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73页。他认为田地占有较少的自耕农,若缺少国家的救济,反而比无田的佃农更为可怜,只有借贷富民“出息数倍”才能维持生产,且一旦缺少这种借贷,小自耕农经济便无以为继,只有“坐视田畴之荒芜,有流移转徙而已”。其他臣僚在上奏中也说:“凶年饥岁,惟中户最可悯怜,盖中人之家,入仅偿出,粒米狼戾,尚鲜盖藏;不幸遇灾,自救不给。州县例行科抑,使之出粟,期会督迫,逾于常赋,鬻田贷室,转粜应输;富者乘时高价取赢,反遂其吞并之计;胥吏并缘推排,以饱溪壑之欲。”(39)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刑法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8369页。也提到灾荒之中中户受到富民高利借贷和沉重赋役的双重打击,难于维持再生产和生活。
由于主佃借贷关系存在双重性,总的来说,宋政府对民间借贷采取了既限制打压又重视保护的政策。但在应对民间借贷的过程中,宋政府逐渐发现这种借贷关系的不可缺少和重要性,开始着重维持借贷关系上这种主佃贫富相资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宋人就说:“农民之用不足,不免称利于富家者,事之常而无足议者也。”(40)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9页。因此,在青苗法的实施过程中,一些官员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韩琦针对王安石采取青苗法打压民间借贷的情况就说:“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一姓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自来衣食贷借,仰以为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苖钱与之,则客于主户处从来借贷既不可免,又须出此一重官中利息。”(41)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附录三·韩魏公家传》,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第1851页。司马光虽然也看到了“今农夫苦身劳力,恶衣粝食,以殖百谷,赋敛萃焉,徭役出焉。岁丰则贱粜以应公上之需,给债家之求。岁凶则流离异乡,转死沟壑”,(42)司马光:《上仁宗论劝农莫如重谷》,载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一〇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29页。但还是认为小农的这种借贷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主佃借贷,他说:“是以富者常假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43)司马光:《上神宗祈罢条例司常平使疏》,载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12页。针对政府官员打击富民借贷的举动,南宋人真德秀也说:“夫安富恤贫,王者之政也,而今郡县之官,往往有嫉视富民之意,多方破坏,不尽不止,独不思富之与贫,相须而济,今有余之家窘于科敛,摧于告讦,皆蒿然有不自存之态。于是赊贷之路穷,而贫民益困矣。古者君与民为生,故有省耕省敛之政。今毋望其能如古也,惟民自为生,官勿挠之足矣。”(44)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对越甲稿·直前奏札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3页。
在这种情况下,主佃借贷作为“民自为生”的重要途径,日益得到宋廷的高度重视。如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二十五日,有臣僚言:“临安府诸县及浙西州军,旧来冬春之间,民户阙食,多诣富家借贷,每借一斗,限至秋成交还,加数升或至一倍,自近年岁歉艰食,富有之家放米人立约:每米一斗,计钱五百。细民但救目前,不惜倍称之息,及至秋收,一斗不过百二三十,则率用米四斗,方粜得钱五百,以偿去年斗米之债。农民终岁勤动,止望有秋,旧逋宿欠,索者盈门,岂不重困?夫民之贫富有均,要是交相养之道。非贫民出力,则无以致富室之饶,非富民假贷,则无以济贫民之急,岂可借贷米斛却要责令还钱?”(45)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八》,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7354页。因此下令债负只能用本色偿还。程珌也劝谕贫富相资,称:“《周礼·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既曰恤贫,又曰安富,大抵富人资贫人以为财,贫人恃富人以为命,贫富有相资之理,不可偏废。”(46)程珌:《壬申富阳劝农文》,《全宋文》卷六七七七《程珌四》,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91页。因此,在宋代的劝农文中,往往将借贷关系和契约租佃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对富民进行劝谕,如南宋人熊克守有《劝农》诗:“凡农主客两相依,以富资贫政所宜。要彼力耕吾有望,借粮借种莫迟迟。”宋人许及之在其《劝农口号十首》中也将租佃关系和借贷关系看作当时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说:“三劝农家敬主人,种它田土耐辛勤。若图借贷相怜恤,礼数须教上下分。”“四劝农家劝主家,去年早稻失收多。未还旧欠无从出,随力周旋更借它。”(47)许及之:《涉斋集》卷一五《劝农口号十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见,借贷关系与契约租佃关系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常态,成为主佃相依、贫富相资的一个重要表现。
特别是在灾荒救济之时,这种借贷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迫切需要加以引导和鼓励。南宋人唐仲友就说:“劝谕借贷,最为救荒之急务。”(48)唐仲友:《悦斋文钞》卷一《台州入奏札子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5页。在发生灾荒时,官府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依靠主佃关系来进行赈济。如陈宓在家乡遇到罕见大旱时,除上书朝廷请僧牒市米外,也“分委寄居士人,劝中上户及时假贷佃大绝粮”,极力劝谕主佃借贷,他认为:
贫富有无相资为生,今富者取民之息,必欲罄竭而不恤其饥寒,不知农民一日尽偿,必至逃亡,则后日何所取利?农民耕种,必假贷于富室,收获在家,(49)原文为“必假贷于富,富室收获在家”,疑衍一“富”字,且句读有误。乃不明还其主,以致欠负,不知今年不还,明年将于何处举债?是自绝其衣食之源也。况又有词到官,官必为理。今官司既不妄追逮,民当畏法顺命。富者当恤贫,贫者当依富尔。父老其以令言更相劝谕,则家洽人足,孝弟姻睦,为礼义富庶之邦,岂不伟哉!(50)陈宓:《安溪县劝农文》,《全宋文》卷六九五四《陈宓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76页。
南宋官员胡太初也认为利用主佃借贷关系来进行赈济是最好的办法:“其有旱涝伤稼、民食用艰者,当劝谕上户,各自贷给其农佃,直至秋成,计贷过若干,官为给文墨,仰作三年偿,本主其逃遁逋负者,官为追督惩治,盖田主资贷佃户,此理当然,不为科扰,且亦免费官司。”(51)胡太初:《昼帘绪论·赈恤篇第十一》,《说郛》卷八九,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因此庆元元年(1195年)二月十一日,臣僚上书言及灾荒赈贷之法时也说:“赈贷,自来官司常患民间不能偿而失陷,每都各请忠信有物力材干上户二名,先令机察都内阙食主户,劝谕邻里有蓄积之家接济,秋熟,依乡例出息倍还。若不能遍,即令结甲具状赴官借贷,仍令所请管干上户保明,县照簿税量其产业多寡与之。若客户,则令主户与借,自行给散,至秋熟,则令甲头催纳所借。”(52)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8008页。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六月十一日,朝廷又下诏称:“浙西、江东路州军被水去处,令两路提举司多方劝谕有田之家,将本户佃客优加借贷,候秋成归还。若致欠负,官为理索;或其家无力,并有田阙少谷种,并许于常平钱内支借,以助补种,毋令荒闲田亩。”(53)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八》,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7365页。乾道年间,赵不息在永康针对发大水闹饥荒的情形,就制定了三种对策:“民业耕者,田主借贷之;游手末作,上户籴米赈之;老幼疾患,官为粥饭养之。”(54)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二六《故昭庆军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赠开府仪同三司崇国赵公行状》,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14页。最终度过饥荒。绍熙二年(1191年)正月九日,淮西旱灾,当地官员“遂劝谕税户,令招集流民以为佃客,假借种粮屋宇,使之安存”。(55)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8083页。

总之,宋代以后,主佃借贷关系日益成为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作为租佃关系和借贷关系的集中体现,主佃借贷的出现是贫富民之间共同利益发展的必然结果。主佃间的这种借贷关系虽然带有双重性,但又是不可缺少的。从主佃借贷的发展情形可以看出,契约租佃关系和民间借贷关系较好地实现了农业生产要素的结合,成为唐宋以后乡村经济的两驾马车,共同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