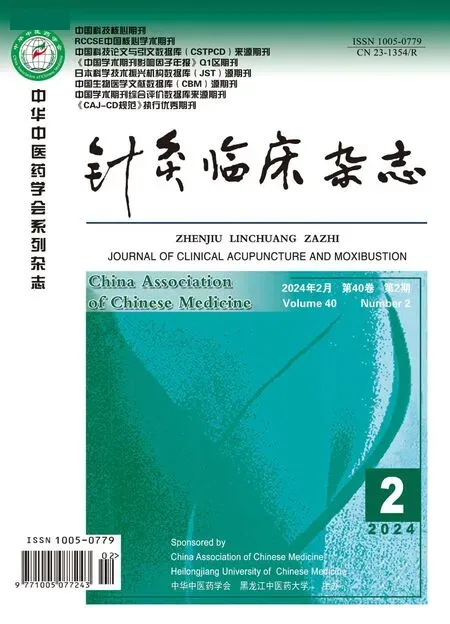注射针刀对椎间盘源性下腰痛患者疼痛程度及炎症反应的影响
刘建梁,王 苗,景福权,赵 平,周 钰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下腰痛临床发病率高且病程较长,在不同年龄段均可发生,据统计,全球约有5.4亿人受腰痛困扰,已成为一个医疗和社会经济的综合性挑战[1]。椎间盘源性下腰痛(Discogenic low back pain,DLBP)在临床中较为常见,多由椎间盘炎症、退变等因素刺激,使椎间盘疼痛感受器发生作用,进而诱发下腰痛行为学的发生,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诸多影响[2]。中医对DLBP具有深入认识,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将其归于“腰痛”“历节”“痹证”等范畴,可治以活血化瘀、通络止痛[3]。针刀疗法是中医特色的外治方法之一,与传统针刺相比具有得气感强、镇痛作用好的优势,能够通过松解病变组织局部粘连缓解疼痛,促进血运和局部微循环,对DLBP患者具有明显疗效[4]。注射针刀是在以小针刀松解粘连组织的同时,配以药液的消炎效果,使患者疼痛迅速缓解[5]。本研究结合临床经验,采用注射针刀干预DLBP患者,评价其对患者症状的改善情况,分析小针刀、药物封闭及注射针刀3种治疗对DLBP的临床疗效,为DLBP的中医治疗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21年10月—2022年9月就诊于本院全科医学普通内科、针灸推拿科病房及门诊,确诊为椎间盘源性下腰痛的患者90例为观察对象。根据患者就诊顺序编号为1~90,采用SPSS 20.0软件随机分配为注射针刀组、封闭组与针刀组各30例。其中注射针刀组男性16例,女性14例,年龄20~57岁,平均为(42.14±4.05)岁;病程6个月~5年,平均为(10.31±1.65)月。注射组男性17例,女性13例,年龄22~60岁,平均年龄为(43.07±4.51)岁;病程7个月~5年,平均病程为(9.39±1.02)月。针刀组男性15例,女性15例,年龄23~55岁,平均年龄为(42.14±3.82)岁;病程6个月~7年,平均病程为(10.20±1.45)月。3组患者入组前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经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批准号:K202107-19)。
1.2 病例选择
1.2.1 诊断标准 ①西医参照疼痛研究国际协会拟定的DLBP诊断标准[6]:慢性腰痛反复间歇发作>6个月,无神经根损伤和受压表现,MRI提示T2WI像出现信号降低,表现为“黑间盘”,纤维环后方见信号增高区域,硬膜囊无明显受压;②中医依据《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相关标准进行诊断[7]:腰部酸痛缠绵,痛有定处,下肢乏力,遇劳加重,俯仰旋转受限,舌淡苔薄,舌质暗紫,脉弦紧或沉细。
1.2.2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上述西医、中医诊断标准者;②年龄范围20~60岁;③志愿进行临床试验,入组前未接受手术治疗。
1.2.3 排除标准 ①X线、CT提示腰椎管狭窄、腰椎峡部裂和腰椎滑脱者;②有神经根损伤和受压体征者;③伴有腰椎结核、肿瘤及骨折等器质性病变者;④患有心脑血管、肝肾等严重内科原发病者;⑤有出血倾向者;⑥患有精神疾病者。
1.3 治疗方法
1.3.1 注射针刀组 患者取俯卧位,根据查体及影像学检查情况,在腰椎旁、腰骶部、髂骨外缘与臀外侧等病变部位选择3~5个阳性反应点,用针尾部按压痕迹标注,局部碘伏消毒并麻醉后,用4号注射针刀(北京华夏医疗器械厂)迅速于皮下进针5~8 mm,达到疼痛或痉挛点后,各注入配制药液3~5 mL:2%利多卡因(山东华鲁制药有限公司,批号2107261)10 mL+0.9% NS(山东威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号2109120)10 mL+曲安奈德注射液(仙居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号211203)25 mg混合药液,随后行纵向松解手法,解除高张力痉挛后出针,棉球按压针孔止血,1次/周,共治疗1个月。
1.3.2 注射组 痛点定位同注射针刀组,局部碘伏消毒后,注入配制药液3~5 mL(2%利多卡因10 mL+0.9% NS 10 mL+曲安奈德25 mg混合药液)行局部封闭治疗,1次/周,共治疗1个月。
1.3.3 针刀组 阳性反应点定位同注射针刀组,用针尾部按压痕迹标注,局部碘伏消毒并麻醉后,用4号无菌针刀(北京华夏医疗器械厂)迅速于皮下进针5~8 mm,达到疼痛或痉挛点后,行纵向松解手法,至针下松软后出针,棉球按压针孔,1次/周,共治疗1个月。
1.4 疗效标准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7]中相关疗效标准于疗程结束后对3组临床疗效进行评价。临床控制:经治疗后腰痛症状完全消失,疗效改善率>90%;显效:经治疗后腰痛症状明显好转,疗效改善率70%~89%;有效:经治疗后腰痛症状较前缓解,疗效改善率30%~69%;无效:经治疗后腰痛症状较前无明显改善或更重,疗效改善率0%~29%;其中临床控制、显效和有效为治疗有效,统计各组临床总有效率,临床总有效率(%)=(临床控制数+显效数+有效数)/总例数×100%。
1.5 观察指标
1.5.1 疼痛直观模拟评分(VAS) 分值范围为0~10分,评价标准:0分代表无痛,0~3分代表疼痛轻微,4~6分代表疼痛尚可忍受,影响睡眠,7~10分代表疼痛剧烈难忍,影响食欲和睡眠,无法耐受[8]。
1.5.2 日本骨科学会腰椎疗效评分(JOA) 满分为29分,分别对患者自觉症状、临床体征、日常生活和膀胱功能4方面进行评价,总分越高者表示功能障碍越轻[9]。
1.5.3 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DI)评价 包括疼痛程度、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提物、行走、坐、站立、睡眠、社会活动及旅行9个方面,每项分值为0~5分,按(实际得分/可能获得的最高分数)×100%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功能障碍越严重[10]。
1.5.4 抑郁自评量表(SDS) 包括20道题目,分4级进行评分,得分>53分表示已有抑郁症状,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重[11]。
1.5.5 血清炎症因子检测 于治疗前后取患者空腹外周血,离心去除杂质,采用ELISA试剂盒检测血清中六酮前列腺素F1α(PGF1α)、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β(IL-1β)与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的变化。
1.6 统计学处理

2 结果
2.1 3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结束后,针刀组临床总有效率为76.7%(23/30),注射组临床总有效率为80.0%(24/30),注射针刀组临床总有效率为90.0%(27/30);注射针刀组临床总有效率明显高于针刀组、注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针刀组、注射组临床总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3组临床疗效分析 [例(%)]
2.2 3组VAS、JOA评分比较
治疗开始前,针刀组、注射组与注射针刀组VAS、JOA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组疗程结束后,VAS评分较前均显著降低,JOA评分明显提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注射针刀组患者VAS、JOA评分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针刀组和注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注射组患者VAS、JOA评分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针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3组治疗前后VAS、JOA评分比较
2.3 3组ODI、SDS评分比较
治疗开始前,针刀组、注射组、注射针刀组ODI和SD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组疗程结束后,ODI、SDS评分较前均显著降低(P<0.05);注射针刀组患者ODI、SDS评分的下降程度较针刀组和注射组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注射组患者ODI、SDS评分的下降程度较针刀组更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3组治疗前后ODI、SDS评分比较
2.4 3组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治疗开始前,针刀组、注射组与注射针刀组血清PGF1α、TNF-α、IL-1β及IL-6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组疗程结束后,PGF1α、TNF-α、IL-1β及IL-6水平较前均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注射针刀组患者PGF1α、TNF-α、IL-1β及IL-6水平明显低于针刀组和注射组(P<0.05);注射组患者PGF1α、TNF-α、IL-1β及IL-6水平的下降程度较针刀组更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4 3组治疗前后炎症因子检测水平比较
3 讨论
以往认为,神经根机械性受压及损伤是导致下腰痛的最主要病因,而随着医学基础研究的开展及临床中CT、MRI等技术的成熟运用,发现约85%的腰痛患者不伴有神经根压迫,因椎间盘退变而引起的DLBP则占非神经根压迫性下腰痛的39%[12-13]。目前,DLBP的临床疗法众多,然而现有的侵入性治疗可造成椎体滑移和神经损伤且复发率较高,保守疗法效果不确切,远期效果欠佳,新兴的基因疗法仍存在较多争议[14]。近年来,针刺、推拿与小针刀松解等中医特色外治方法在DLBP治疗中的作用逐渐受到关注[15]。
DLBP属于中医学“腰痛”“历节”“痹证”等范畴,多因风寒湿邪气侵入周身筋脉,气血凝滞,日久而致局部经络痹阻,筋脉失养;或外力损伤腰部,阻滞气血,不通则痛[16]。针刀是将中医针刺与西医手术相结合的一种微创疗法,通过对局部穴位的刺激全面调节病变部位,达到刺治与割治的双重效果,用于慢性陈旧性损伤可收获良好疗效[17]。近年临床研究显示[18],小针刀松解术在缓解DLBP患者疼痛、促进微循环和改善血运等方面取得了满意疗效。注射针刀是将针刀微型外科和注射药物融合,针刀可通过松解粘连组织改善局部病灶血供障碍,加速能量的补充,并促进堆积代谢产物的清除,且针刀较常规针灸针刺激量大,患者得气感强,在小针刀松解粘连和挛缩的同时,再配用药物起到营养和消炎作用,使“针”“刀”“药”三者结合,可高效改善局部病灶,并减少感染风险,使患者症状进一步减轻,使术后疼痛更快缓解[19-20]。
曲安奈德是一种长效肾上腺皮质激素药物,而利多卡因是一种局麻药物,两者作为局部封闭用药联合应用,能够在短期内缓解无菌性疼痛,同时维持较长的药效,但并不能解除导致疼痛或炎症的病因,即周围神经的粘连病灶[21]。本研究着眼于应用注射针刀在松解DLBP患者粘连区软组织的同时使封闭药液直达病灶,以避免两次进针可能造成的位置不准及感染等问题。观察其疗效可见,经治疗1个月后,注射针刀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针刀组和注射组,在对患者症状、疼痛程度及功能状态的改善方面,注射针刀治疗后,患者VAS疼痛模拟评分及ODI指数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JOA腰椎疗效评分明显提升,改善作用均优于单纯针刀和封闭注射治疗。DLBP患者由于功能障碍和日常生活、工作能力的下降,就诊时往往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症状,影响疾病的恢复进度[22]。本研究中,患者经治疗后SDS评分均明显降低,其中注射针刀组较针刀组与注射组改善效果更为明显,表明注射针刀治疗可有效缓解DLBP患者抑郁、焦虑状态,改善疾病预后。
目前研究认为,椎间盘退变过程中促炎介质的大量释放可刺激椎间盘纤维环发生自身免疫应答,进而刺激脊神经,诱发疼痛症状,是导致DLBP病情发生的重要因素[23-24]。白细胞介素-1β(IL-1β)的水平与炎症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在DLBP病变过程中,IL-1β的过度释放可促进椎间盘中六酮前列腺素F1α(PGF1α)的分泌,引起椎间盘损伤和退变[25]。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是机体免疫反应的核心因子,可作为DLBP的早期血清标记物[26]。有研究报道,TNF-α、白细胞介素-6(IL-6)等可刺激细胞聚集,促进炎性递质的分泌,导致DLBP发生[27]。本研究结果显示,3组患者血清中PGF1α、TNF-α、IL-1β及IL-6的水平均明显低于治疗前,与针刀组、注射组比较,注射针刀组PGF1α、TNF-α、IL-1β及IL-6水平均明显降低,提示注射针刀在松解粘连的同时,可有效减轻炎症介质的堆积,在抑制炎症状态过程中可与药物发挥良好的协同增效作用。
综上所述,注射针刀疗法用于DLBP疗效确切,在减轻患者临床症状、缓解局部疼痛及抑制炎症反应方面较单纯针刀松解和药物封闭治疗更优越,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