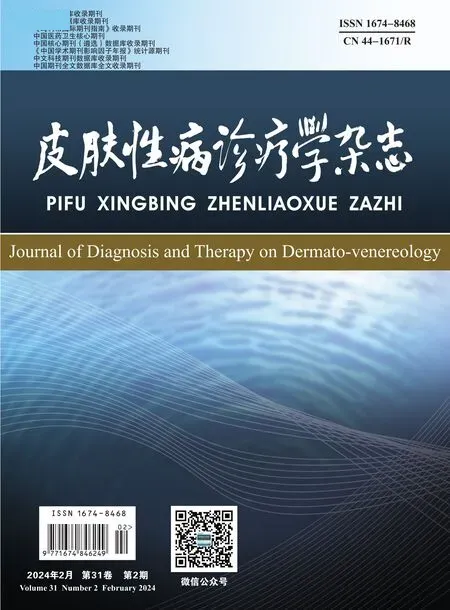成人临床表现不典型丛状血管瘤2例
杨娈, 于晓静, 孙青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 济南 250012
1 临床资料
患者1,男,41岁,因颈部红色斑块伴疼痛2年就诊。患者2年前无明显诱因颈部出现多个红色丘疹,渐增多、增厚呈斑块,伴刺痛,无发热,未诊治。患者既往体健,无类似疾病家族史。
体格检查:系统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皮肤科检查:颈部散在分布红色斑块,最大面积约7 cm×3.5 cm,上覆簇集性暗红色丘疹,质韧,触痛,部分呈假性水疱样损害(图1)。

图1 患者1临床表现: 颈部散在分布红色斑块,最大面积约7 cm×3.5 cm,其上集簇性分布暗红色丘疹,质韧,部分呈假性水疱样损害 图2 患者1皮损组织病理:真皮及皮下组织见结节性内皮细胞增生,呈丛状排列(HE, 2A:40×; 2B:100×)
初步诊断: Sweet病(局限型)。
辅助检查:血小板83×109/L(正常值:125~350×109/L);凝血功能示纤维蛋白原(FBI)1.98 g/L(正常值:2.0~4.0 g/L),凝血酶原时间(PT-S)14.6 s(正常值:8.8~13.8 s),凝血酶原标准化比率(PT-INR)1.25(正常值:0.8~1.2),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比率(APTT-R)1.42(正常值:0.8~1.2),凝血酶时间(TT-S)18.20 s(正常值:11.0~17.0)。皮损组织病理:真皮及皮下组织见致密的结节性内皮细胞增生,呈丛状排列,似炮弹样外观(图2A、2B)。免疫组化: CD31、CD34阳性,D2-40局灶阳性(图3A~3C)。

图3 患者1免疫组化(SP,200×)Figure 3 Immunohistochemistry of patient 1(SP,200×).
最终诊断:丛状血管瘤。建议口服普萘洛尔治疗,患者拒绝。随访4个月,患者曾间断外用糖皮质激素软膏,皮损无明显改善,未进一步治疗。
患者2,女,30岁。因左足背褐色结节伴痛痒2月余来诊。患者2月余前无诱因左足背出现一褐色结节,偶有瘙痒,触痛,未诊治。患者既往有干燥综合征病史,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羟氯喹及吗替麦考酚酯治疗。
体格检查:系统性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皮肤科检查:左足背分布一直径约0.8 cm的褐色结节,质硬,表面粗糙(图4)。皮肤镜:暗棕色背景下,中央白色瘢痕样条纹,周边红棕色无结构区,散在紫红色血管腔隙或紫癜样结构,边界模糊(图5)。

图4 患者2临床图片:左足背有一直径约0.8 cm的褐色结节,质硬,表面粗糙 图5 患者2左足背皮疹皮肤镜表现(20×):暗棕色背景下,中央白色瘢痕样条纹,周边红棕色无结构区,散在紫红色血管腔隙或紫癜样结构,边界模糊
辅助检查:血常规、肝肾功、凝血功能、尿常规正常;体液免疫系列示免疫球蛋白G(IgG)23.70 g/L(正常值:7.0~16.0),补体C3 0.888 g/L(正常值:0.9~1.8);抗核抗体定量(ANA)1 ∶640阳性。皮损组织病理:真皮见内皮细胞排列致密,呈丛状增生(图6A、6B)。免疫组化:CD31、CD34阳性,D2-40局灶阳性(图7A~7C)。

图6 患者2皮损组织病理:真皮见内皮细胞排列致密,见裂隙状血管,部分管腔内见红细胞(HE, 6A:200×; 6B:400×)

图7 患者2免疫组化(SP,200×)Figure 7 Immunohistochemistry of patient 2 (SP,200×).
诊断:丛状血管瘤。治疗:手术切除。术后随访一年,无复发。
2 讨论
丛状血管瘤(tufted angioma, TA)是一种罕见的良性血管增生性疾病,好发于婴幼儿期,多为先天性,60%~70%患者在5岁之前发生, 约20%在成人发生,仅10%可自行消退,消退时间约6到24个月[1]。TA一般无性别差异,部分报道成人患者中女性(68%)多见[2-3]。TA好发于躯干上部、颈部及四肢近端,也有眼睑、耳鼻、口腔粘膜及颅内受累的报道[4]。典型的临床表现为边界欠清的暗红色斑块及斑片,亦可表现为质硬的丘疹或结节,常伴疼痛、多毛、多汗等症状[2]。约10%的患者可伴Kasabach-Merritt现象(Kasabach-Merritt phenomenon, KMP),以血小板减少、微血管溶血性贫血、消耗性凝血功能障碍为特点[5]。
本报道的患者1血小板减少,凝血功能异常,但KMP通常血小板<50×109/L,纤维蛋白原<1 g/L,因此临床工作中需进一步追踪各项指标变化,警惕KMP的发生[5]。
TA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明确,部分学者认为TA是淋巴管和血管源性肿瘤,可通过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存在体细胞GNA14(p.Gln205Leu)及原癌基因NRAS(p.Q61H)突变,影响MAPK或RAS通路[6-7]。TA还存在抑癌基因TSC2和PTEN的缺失,异常激活mTOR通路,上调磷酸化的P70S6K和4EBP1,导致肿瘤增殖[8]。此外,TA发病还可能与妊娠、创伤、感染、疫苗、器官移植、免疫抑制等因素有关[9]。Kim等[10]报道1例与妊娠相关的TA在分娩后消退,其病因可能与雌激素促进血管增生有关。本文报道的患者2有干燥综合征病史,其病因可能与免疫功能紊乱,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有关。
成人丛状血管瘤的鉴别诊断主要包括:①卡波西样血管内皮瘤(Kaposiform hemangioendothelioma, KHE)在组织学上与TA极为相似,但KHE通常浸润更深,可累及肌肉、骨骼及内脏,组织病理可见密集的梭形内皮细胞,呈肾小球样结构,D2-40在丛状增生的毛细血管瘤样区域呈阳性,在周围扩张的血管中呈阴性[11]。②卡波西肉瘤组织病理表现为大量梭形细胞增生,呈条索状排列,可见核异型性、裂隙状血管、血管外红细胞外渗并大量含铁血黄素沉积,通常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1和人疱疹病毒(HHV)-8表达呈阳性[12]。③血管肉瘤组织病理可见真皮内不规则的血管腔,内皮细胞呈束条状侵袭性生长于胶原束之间,可见核分裂及细胞异型性[13]。本文2例患者均浸润表浅,病理示丛状增生的内皮细胞似炮弹样外观,未见大量梭形细胞,无核分裂及细胞异型性。免疫组化示CD31、CD34阳性,D2-40局灶阳性,具体表现为D2-40在周围扩张的血管中呈阳性,而在炮弹样增生区域呈阴性,诊断符合TA。此外,在临床上,TA因皮损可表现为红肿热痛,有时会误诊为局部感染或炎症[2]。患者1因皮损表现为疼痛性红斑,部分呈假性水疱样损害而初步拟诊为Sweet病(局限型),是一种由中性粒细胞广泛浸润引起的炎症性疾病,局限型患者有时可无发热表现,极易误诊。因此,及时完善组织病理有助于明确诊断。患者2临床上与皮肤纤维瘤表现极为相似,皮肤纤维瘤好发于中青年女性,表现为孤立性的褐色结节,组织病理为真皮内结节,无包膜,由成纤维细胞、胶原纤维组成,通过组织病理亦可鉴别。
皮肤影像学也有助于TA的诊断。Gong等[14]报道超声下TA多病变浅表(<1 cm)(71.4%),边界清晰(76.2%)。MRI下TA多表现为T2信号均匀增加,T1信号减弱,有时可见流空影[15]。此外,Oya 等[16]报道TA皮肤镜下可见真皮内大量微小的红色腔隙和细线状白色条纹。本文报道的患者2皮肤镜下也可见大量血管腔隙或紫癜样结构以及白色瘢痕样条纹,提示这可能是TA皮肤镜下的一种特征性表现。
对于TA的治疗,局限型TA可观察或应用β受体阻滞剂、局部注射激素、手术切除等方式治疗。大面积TA或伴KMP者常以系统性类固醇激素或长春新碱作为一线治疗[16],长春新碱在改善血小板减少及肿瘤质地方面优于激素[17]。近年mTOR抑制剂西罗莫司及其衍生物依维莫司已用于难治性TA并可改善KMP症状,疗效显著且安全性较高,但需警惕潜在感染的风险,可预防性应用抗生素,减少感染性并发症[18]。其他治疗方式,包括脉冲染料激光、冷冻、电子束放疗、泡沫硬化疗法以及外用他克莫司软膏、咪喹莫特乳膏等均适用于浅表性疼痛性TA。本文报道的2例患者均病灶局限,浅表侵犯。患者1因拒绝用药,随访观察;患者2行手术切除无复发。
综上,成人丛状血管瘤临床表现可能较不典型,及时完善组织病理及相关血液学指标检查,对疾病的诊断至关重要。此外,皮肤镜对诊断也具有一定提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