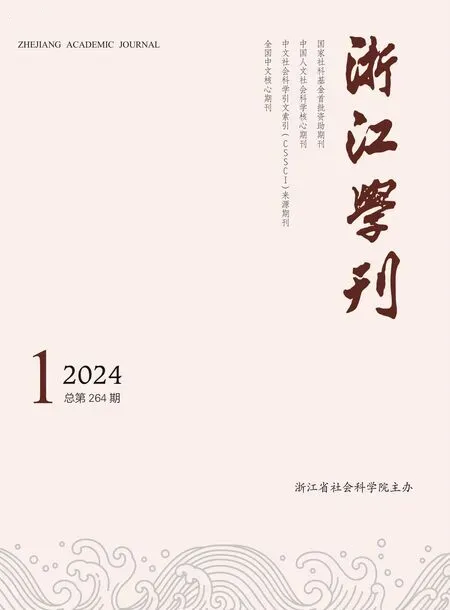“复现”的冲动:苏轼诗歌中的互文性写作*
罗 宇
提要: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件或同一类事进行书写,诗歌内容具有相承关系,形成一系列“复现文本组”,可称为互文性写作。苏轼诗歌中的复现文本组,具备了不断衍生的机制,可以从往日书写中自我再生,不必以诗人的当下在场与直书所见为前提。过去不是由物质世界,而是由文学书写构成。高度文本化的诗歌反过来改造现实世界,甚至重塑了诗人的行为。文本创造了文本,文本“创造”了现实,正是“复现”的奥义。苏轼诗中的复现呼应了中唐至北宋的“言尽意论”语言观转向,宋人对语言的乐观态度推进了互文性写作的发展。互文概念还关涉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情志说与修辞学,具有更为深远的诗学意义。
苏轼诗中有一种突出现象,即“用自己诗为故事”,在当下创作中化用、呼应自己的往日书写。此现象最早由北宋黄彻《溪诗话》提出,(1)魏庆之著,王仲闻点校:《诗人玉屑·卷之七》,中华书局,2007年,第207—208页。姚华提出“私典”概念进行研究,(2)参见姚华:《“私典”及其诗学转型意义:以苏轼诗歌为中心》,《文学遗产》2021年第5期。本文受到该研究的启发。强调了“私人化”的一面,未充分关注“互文性”的一面。近年来中外学界以互文性理论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成果颇丰,(3)例如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郑学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商伟:《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顾彬著,吴娇编:《顾彬唐诗九讲》,商务印书馆,2020年。诗人的自我引用现象受到关注。宇文所安指出:“作家们复现他们自己。他们在心里反复进行同样的运动,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同样的故事。”(4)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14页。
本文引入互文性概念研究苏轼诗歌中的自我引用现象。互文性写作可定义为: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件或同一类事进行书写,诗歌内容具有明显的相承关系,形成一系列“复现文本组”(5)姚华提出“异时文本组”概念,本文受此启发。。这些诗常以“复过”“又至”“再作”为标题,聚焦于当下对往日书写的观照。区别于“私典”,“复现”以文本书写为前提,仅取自诗人生活、未被书写过的事物不属于复现的范畴;区别于同时写作的同题组诗,复现特指诗人在不同时间的创作,尤其关注当下与过去的对照。复现文本组在苏轼诗中广泛存在,其涵盖主题之广、时间跨度之长、特征之鲜明,显示出不可估量的研究价值。
一、“复现”:日本《四河入海》中的实证
在黄彻的影响下,最早研究苏轼诗中复现的是日本五山禅僧。14至16世纪,苏轼诗文大量传入日本。笑云清三《四河入海》是日本五山时期苏诗“抄物”(注释书)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有苏轼诗中复现的大量实证。
《一》(9)即一韩智翃《一韩闻书》。云:“イツモ坡ガ我ガ作タ事ヲ故事トシテ、イツモ用ルリ。”(中译:东坡总是把自己所作之诗化为故事,并且经常这样用。)(『四』8:2:184)
五山禅僧强调“イツモ用ルリ”“多自用其诗句”,明确指出了复现在苏轼诗中的普遍性、规律性。复现在《溪诗话》中仅偶一提及,传入日本后发展得更广泛,成为了五山禅僧注解苏轼诗的高频概念。《四河入海》中明确指出复现的诗就有两百余首,主题极为丰富。借助异域之眼反观自身,往往能对苏诗含义发前人所未发,习焉不察的现象也会浮出水面。
那么,为何苏轼诗中的复现在日本更受关注?其一,宋诗“分类注”的注本类型为五山禅僧提供了发现的契机。诗歌题材分类在苏轼诗东传日本后发挥了独特作用,甚至超过了在中国的影响。(10)参见王友胜:《〈苏诗补注〉的文献诠释与历史价值》,《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何泽棠:《〈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4期。相比于编年注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在中国的风行,分类注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传入日本后反而更受重视,《四河入海》以之为底本,将苏轼诗按题材分为七十八类。(11)参见罗宇:《盆石卧游:日本五山禅僧对苏轼诗的接受》,《外国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其中,相同或相近主题的诗歌依类聚集,使得“复现”前所未有地彰显。例如苏轼过庐山数回,诗歌多收入《四河入海》“山岳”“溪潭”类中,(12)文本集中在《四河入海》“卷七之三”与“卷八之四”当中。引发了五山禅僧对“苏轼入庐山”的兴趣,《白》云:“凡先生入庐山,又过庐山之下数回。……此篇似庐山经过之时作也,故举数问经过之事。”(『四』8:4:248-249)苏轼过庐山的诗从元丰七年记录至建中靖国元年,时间跨度达十七年,在编年本中分散于卷二十三至四十五之间,实难统而视之。但其在《四河入海》中列于同一门类、同一卷次,页码紧密相连,能发现苏轼“过庐山之下数回”不足为怪。再例如苏轼过淮河数回,《过淮》《淮上早发》等诗多收入《四河入海》“纪行”类中,(13)文本集中在《四河入海》“卷一之一”至“卷一之四”当中。促使五山禅僧总结一系列诗歌的共性:“然则十往来纪实也。”(『四』1:2:72)以上例子充分证明了复现在苏诗中确实普遍存在,也显示出五山禅僧的重视。
其二,五山禅僧重视实录、释义详尽的特点有助于他们对复现进行全面梳理。《四河入海》是面向异国读者的注本,释义详尽是基本特征(14)董舒心:《〈四河入海〉研究》,南京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又因五山诗歌普遍具有日记化性质,(15)张哲俊:《诗歌的日记化与长诗题:记忆张本即信史张本?——以日本五山文学为中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重视实录的特点也鲜明地表现在五山注释中。中国古注也重视考证,尤以查慎行《苏诗补注》长于考证系年,(16)曾枣庄:《清注苏诗述略》,《中国韵文学刊》1999年第2期;王友胜《〈苏诗补注〉的文献诠释与历史价值》,《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但中日注家的侧重点不同。五山禅僧尤为关注复现文本组的时间跨度,瑞溪周凤《脞说》云:“虽无‘传柑’语显其诗中,推年数则十年也。”(『四』6:1:662)王注、施注、查注对“十年”未详细阐释,五山禅僧则不厌其烦地考证。相比于考证某首诗的系年,他们对追溯一系列诗歌文本的关系更感兴趣。另外,五山禅僧对考证年份、日期的准确性有严苛要求:
《白》云:“虽然尾欤首欤,除其一年而云五年也。凡量年数,有除首尾二年,又有加首一年而除尾,又有加尾一年而除首,又有加首尾二年,事不可守一隅也。”(『四』15:2:127)
他们不仅细究“三年”“五年”等概数,还总结了“量年数”的一套方法,足见用心之苦。五山禅僧颇以考证时间的准确性为傲,认为赵次公注解得不够详尽:“次公……似不细考也。”(『四』19:3:705)“次公……何夫误邪?”(『四』4:2:415)对时间的细究有助于全面梳理复现文本组,使以往不被注意的文本系列豁然显露。
复现在苏轼诗中确实普遍存在,《四河入海》不仅提供了大量实证,还启示着复现具有更深远的诗学意义。
二、自觉的营造:“复现”的创造功能
苏轼诗的复现文本组中最早被人关注的是“黄州梅花”系列,《溪诗话》云:
人们从未停止过对美食的追求,我也一样,看到好吃的东西总不免喜形于色,食指大动。美味能满足人的口腹之欲和给人带来愉悦感,古代思想家老子说:“五味令人口爽。”美味来源于食材的品种、新鲜程度和取决于烹饪技艺的高低。论食材之广泛,烹饪技艺之复杂与高超,色香味形之讲究,中华饮食无疑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用自己诗为故事……坡赴黄州,过春风岭有绝句,后诗云:“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至海外又云:“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17)魏庆之著,王仲闻点校:《诗人玉屑·卷之七》,中华书局,2007年,第207—208页。
这三组诗形成了一个复现系列,需探究的是:复现的诗歌文本是如何生成的?复现的诗歌与诗人当下所处的现实世界是何关系?复现究竟是偶然、还是诗人自觉的营造?其一,诗歌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是复现得以生成的前提。元丰三年苏轼被贬黄州,度关山时作《梅花二首》:“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18)苏轼撰,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二十),中华书局,1982年,第1026页。后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苏》”、卷数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元丰四年苏轼作《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苏》21:1078)岐亭梅花就在眼前,(19)正月二十二日,两日后苏轼再往岐亭,作诗《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苏》21:1078),证明当日岐亭确有梅花盛开。却空有其名,诗人眼中只有去年的细雨梅花。眼前事物全在变迁,唯有诗人记忆里的梅花依然带来“正”强烈的感慨,时间对它不起作用。仿佛它自从被创作出来后,便拥有了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生命。“细雨梅花正断魂”之所以成为绝唱,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此时此地的所见所闻,而是它与前作之间的互文关系。诚然此诗与诗人当下所处的现实世界有相关性,但不紧密,只能参照前作才能充分阐释。一首诗不是因它自身,而是因其前作而知名,这种怪象正是复现的迷人之处。
其二,地点的变换与重塑。苏轼在春风岭亲见梅花仅有一次,此后所写的黄州梅花都不是当下在场之作。诗人离开黄州后流离各地,书写黄州梅花的传统不仅没有中断,还越写越知名。绍圣元年苏轼在惠州松风亭又一次写道:“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苏》38:2075)诗人亲临春风岭时写的诗,反而不如回忆春风岭时写的诗知名,岂非怪事?但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却又见惯不惊,究竟为何?归根结底,因为诗人回忆和书写的是高度文本化的黄州梅花,而不是在春风岭上见到的梅花本身。换言之,一首诗完全可以从往日文本中自我衍生,不必以诗人的当下在场与直书所见为前提。例如元丰八年苏轼刚离开黄州,“黄州梅花”便从写作现场抽离:“南行度关山,沙水清练练。……殷勤小梅花,仿佛吴姬面。”(苏轼《王伯敭所藏赵昌花四首》其一《梅花》)(《苏》25:1334—1335)名为题画诗,诗人却不描绘画面内容,而是以黄州关山梅花占据全部篇幅。《白》云:“此篇专以往事为言也。”《脞》云:“盖言如上所谓谪黄州之时途中见梅花,今又见赵昌所画,忆着昔事,为之流涕也。”(『四』11:3:545)诗人需要以自己往日的诗歌为中介,跟近在眼前的梅花画建立联结,从而完成当下书写。回顾苏轼创作史,黄州梅花诗的地位正是这样建构起来,复现具有塑造经典主题的力量。
文本化的黄州梅花不依赖具体地点而存在,甚至连春风岭地名本身都是诗歌文本化的产物。春风岭位于何处尚无定论,据考是麻城县羚羊山西南方向的某分水岭,(20)凌礼潮:《苏轼诗文中“关山”“春风岭”考释——兼论苏轼入麻城路线》,《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从前并不知名,在苏轼题诗后才变为方志中的著名词条。最早收录该词条的是南宋《舆地纪胜》(21)其他提及“春风岭”的方志中较著名的还有《方舆胜览》,但成书晚于《舆地纪胜》,且《方舆胜览》里只有“黄州”一门,无“春风岭”词条。明弘治十四年《黄州府志》卷二“春风岭”词条引《方舆胜览》,但实际上“今本《胜览》卷五十黄州无此”。(李勇先:《试论〈方舆胜览〉》一书的流传及影响》,《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6期。):“春风岭:在麻城县。岭多梅花,东坡自新息渡淮由是岭,见于诗咏。”(22)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四十九》,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67页。检阅《麻城县志》(23)现存最早为康熙九年本,内容引用《大明一统志》。:“春风岭:在麻城县,岭多梅花。宋苏轼自新息渡淮由此岭,有诗。”(24)方志远等点校:《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一》,巴蜀书社,2017年,第2684页。作为物质的春风岭并不重要,没人记载它距离麻城县多少里、有何地形特征。对方志的读者而言春风岭必须真实存在,但这种真实性不在于地理特征相符,而取决于它与苏轼诗的文本联系。因此“见于诗咏”才是最关键的,“岭多梅花”才是必不可少的。似乎唯有符合苏轼诗的描绘,才能证明这是真的春风岭,是文学书写而非地理特征赋予了春风岭真实性与权威性。后世寻访春风岭之人众多,北宋张耒:“东归已过春风岭,度尽千山路渐平。”(25)张耒撰,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张耒集·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90年,第407页。南宋诗人往春风岭寻梅的热情更高涨,但标志性的梅花并未出现。为何方志记载的“岭多梅花”在现实中没有兑现?大约因为苏轼所写的春风岭本就只是泛指一处分水岭,诗人无意指明具体地点,后人依诗寻岭注定会失望。然而后人言之凿凿以“春风岭”为题作诗,即便未至春风岭、未见梅花,仍不妨碍吟咏“春风岭上梅”。即便看不见,也无妨用诗歌书写的方式将春风岭重新创造出来——如同当初苏轼也用诗歌“创造”出了它一样。既有苏轼诗歌为证,春风岭就应该在那里。它必须存在,哪怕只是为了成全诗的世界。(26)将经典诗歌书写过的事物视为“标准配置”,在其“缺席”的情况下仍坚持写作,文本世界替代了真实的物质世界,成为诗人模仿的依据、创作的动力。这种“缺席”书写的方式兴于中国,并盛行于日本。参见罗宇:《审美代偿:日本五山诗歌中的“缺席”书写》,《国外文学》2022年第3期。
其三,时间上的自觉营造。黄州梅花的文本化力量是如此强大,它不仅命名且重塑了现实中的地点,还支配并控制着诗人的实际行为。回到原点,元丰三年正月二十日(27)《白》云:“集中但题云《梅花两首》。而先生尝自写,则题云‘正月二十日过关山作’。”(『四』14:2:24),苏轼写下《梅花二首》。元丰四、五、六年,苏轼连续三年都选择在同一天往岐亭再看梅花。若说元丰四年苏轼再至岐亭是事出有因、日期巧合,那元丰五年就很特殊了: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苏轼《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苏》21:1105)
元丰五年苏轼依然选择同一天、约同一批人、再来同一地点,分明是有意复现去年的场景。(28)王水照、朱刚也认为元丰五年苏轼再来女王城,并非偶然,而是有意复制去年的行为:“分明是有意营造这种氛围。诗题里面所谓‘忽记’云云,乃是诗人笔下的狡狯。”参见王水照、朱刚:《苏轼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4-106页。从初作《梅花二首》开始,文学书写使黄州梅花文本化,文本化的黄州梅花也反过来改造现实世界。换言之,不是诗歌记录或复制人的行为,刚好相反,是诗歌“塑造”了人的行为。由此看来,诗歌中的复现不是一种偶然,而是诗人自觉的营造。
时间上的自觉营造,再度印证了书写的力量和文本的权威性,它召唤着诗人不断在正月二十日重返开端的场景。假如初作《梅花二首》不曾写下,那苏轼每年同日去看梅花的行为根本不会发生。文本化的黄州梅花得以形成,它跨越时空,不论现实世界如何变幻都不足以带来威胁。那么一切发生过的事都可重回,至少在诗歌的世界里可以让一切重回。“已约年年为此会”不仅是现实邀约,更是苏轼在宣告要一年年复现诗歌的世界。哪怕通过重塑自己的行为,也必须维持正月二十日的创作传统。于是诗歌创造行为、文字衍生地点的奇迹再次出现。复现的冲动就像文学书写的引擎,它不断将消逝的东西召唤回来,并从中创造新生命。
在引擎的推动下,苏轼诗中的复现文本组具备了不断衍生的机制,可以从往日书写中自我再生。苏轼许诺的“已约年年为此会”在现实世界里成真了,试看元丰六年:
乱山环合水侵门,身在淮南尽处村。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苏轼《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苏》22:1154-1155)
“复出”“仍用”表明此诗是有意复现往年的场景,整首诗都是对前几首的改编、重组:“五亩渐成终老计”是对“数亩荒园留我住”的续写,“长与东风约今日”是对“已约年年为此会”的改写,“暗香先返玉梅魂”是对“细雨梅花正断魂”的重复,全诗主旨也是前作的延续。眼前事物可随意替换,看到什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契机,让诗人将今天与往日相联结,从而复现前作的模式。
可以看出,文本传统代替现实世界,成为诗人写作的源泉、不竭的动力。过去不是由物质世界,而是由文学书写构成。过去之所以被记住,是因为诗人对它重复不断地书写。换言之,没有被书写的“过去”是不会存在的,留存在诗人记忆深处的只有文本化的过去,它擦不去抹不掉,像幽魂一样在诗歌中不断复现。牟复礼有类似结论:“过去是文字的过去,而不是石头的过去。”(29)牟复礼:《中国城市史一千年:苏州城的形态、时间和空间观念》,常建华主编:《中国城市社会史名篇精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135页。在复现的文本中,真理尤为明晰:文学书写是自我完成的,它创造了一个文本化的“现实”,替代了真实的物质世界,成为诗人记忆的渊薮、创作的动力。简而言之,文本是由文本自身,而非物质世界创造。文本创造了文本,正是“复现”的奥义。
三、未完成的约定:“复现”的预言力量
苏轼诗歌中复现次数最多、最知名的是“夜雨对床”诗歌系列,《王直方诗话》云:
(东坡)在郑州寄子由云:“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坡在御史狱有云:“他年夜雨独伤神。”在东府有云:“对床定悠悠,夜雨今萧瑟。”……又曰:“对床欲作连夜雨。”又云:“对床老兄弟,夜雨鸣竹屋。”(30)蔡正孙撰,常振国、降云点校:《诗林广记·后集·卷四》,中华书局,1982年,第274—275页。
每当苏轼与苏辙离别之际“夜雨对床”便频频出现。需探究的是:诗人不断复现同一主题的动力是什么?动力从何而来?
其一,“夜雨对床”的文本化。传统的睹物思人诗一般以睹物为前提,即景写作是基本属性。但苏轼背离了即景写作的前提,不必真正面对夜雨也能在诗中吟咏。有时苏轼确实置身雨中,但他大部分“夜雨对床”诗都不是在夜雨中写成,这些诗反而更知名。例如“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描绘的是想象中的夜雨。再例如著名的狱中绝笔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予以事系御史台狱》其一)唤起诗人思绪的不是眼前的夜雨,(31)从苏轼同一天写下的“风动琅珰月向低”(《予以事系御史台狱》其二)中可确认,当天晚上明月高照,并无夜雨。不是嘉祐五年寓居怀远驿时的夜雨,不是他人生中任何一场真实的夜雨,而是他笔下反复书写的文本化的夜雨。文本的力量如此强大,二苏兄弟当面相聚仍要吟咏夜雨对床:“今日情味虽差胜彭城,然不若同归林下,夜雨对床,乃为乐耳。”(32)苏轼撰,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八》,中华书局,1986年,第2142—2143页。元祐三年时二苏兄弟共同在朝、受到重用,在仕途、亲情都极圆满之际,苏轼却始终不忘夜雨对床之约。此时兄弟对床听雨并非难事,苏辙在同一年便有诗:“对床贪听连宵雨。”(33)苏辙撰,蒋宗许等笺注:《苏辙诗编年笺注·卷十五》,中华书局,2019年,第1316页。但共同听雨的眼前情景,并非夜雨对床的真正实现,文本化的夜雨对床与现实世界剥离开来。
其二,“未完成”的约定是诗人重复书写的动力。夜雨对床之约蕴含了两层心愿,一是兄弟相守,二是早日退隐,但最终都落空了。《王直方诗话》云:“相约退休,可谓无日忘之,然竟不能成其约。”(34)蔡正孙撰,常振国、降云点校:《诗林广记·后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275页。正因一直未能实现,诗人才会“无日忘之”,才会在一生的不同时期反复提及。一旦约定完成,这个诗歌系列就宣告结束了,因为诗人摆脱了“未完成”的焦虑。确乎如此,诗歌不断复现的往往是不完满的、未能实现的东西,诗人真正忘记的只有完满的、已实现的东西。苏轼一生与苏辙离别十余次,每次离别都会唤醒约定不能实现的痛苦。据统计:“先生与子由离别,大数一十一度……自此以后,终兄弟不得相逢。”(『四』20:3:63—64)在现实中一次次尝试却未能成功之事,变为诗人无法化解的心结。“未完成”所导致的内心冲突越尖锐,记忆的时间就越长久,复现的冲动就越强烈。
归根结底,现实世界总是动荡不安,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而文本世界却是稳定的,更重要的是诗人自己可以成为文本世界的“造物主”,用书写的方式改造现实。二苏兄弟夜雨对床的约定最终未实现,但现实世界的遗憾可通过文本来补偿。例如后人修建了听雨的建筑,从诗歌书写中衍生出物质实体:
听雨轩在中和堂后……取东坡“中和堂后石楠树,与君对床听夜雨”之句为扁。(《苏》18:953)
昔眉山苏氏兄弟,少时诵唐人诗语,而有风雨对床之约,其后各宦游四方,终身吟想其语,以相叹息。……而名楼以为之志,他年或敢忘诸,谓此楼何!(35)吴敏树著,张在兴校点:《柈湖文录·卷四》,岳麓书社,2012年,第354—355页。
后世的听雨轩、听雨楼都是苏轼诗的产物,文字衍生建筑的奇迹再次出现。奇特的是,尽管诗歌所写的夜雨对床并未成真,却不妨碍它对现实世界产生真实的、持续性的、强有力的控制和影响。甚至后人津津乐道的也正是约定的未完成:“抑苏氏能为此言也,非能践此言也。”(36)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八八》,中华书局,2011年,第3754页。至此,未完成的个人遗憾化为了后世的共同心结。文本书写所创造的夜雨对床,召唤着后世之人继续完成。于是,听雨建筑纷纷因此而立,复现的行为将永远循环。
可知“未完成”的约定不仅是诗人自己重复书写的动力,更是后人复原文本的动力,夜雨对床因此成为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母题。文本是否真的能改变未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假如人人都相信文本的力量,那么它就真的可能塑造人类的行为,从而反过来改造现实。这种心理与诗谶相通,中日注家都将复现称为诗谶,《一》云:“先生多自用其诗句以为故事,且谓之诗谶也。”(『四』10:4:452)《白》云:“次公云:‘先生于诗语中两言入海,皆成谶语。’……言物无心,后皆成谶,亦前定也。”(『四』12:3:647)诗谶意味着往日书写会对当下或未来的现实世界产生影响。苏轼很重视诗谶,元丰七年他梦见一句诗:“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37)苏轼撰,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卷一》,中华书局,1981,第15页。七年后诗句应验:“忽悟所梦诗,兆于七年之前。”(38)苏轼撰,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八》,中华书局,1986年,第2144页。九年后再次应验:“是见于梦九年。”(39)苏轼撰,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第567页。与其说诗谶真能预言未来,不如说诗谶被当作一种文本阐释的话术。人们普遍愿意相信,文本世界会对现实生活产生神秘的影响力量。换言之,未来在真的来临之前,早已被文字“书写”过了。
从这个意义而言,文本书写不仅创造了过去,还“创造”了未来。未来总是诞生于过去的基础之上,既然未被书写的过去是不存在的,那么不被文本书写所影响的未来也不存在。当然,这并不是高估文学的作用,而是从更高的互文层面重新评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刘勰对“文”的概念有系统论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40)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原道》,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页。人文与天文都出于“自然之道”,“文”就是世界的征象,而非对世界的描摹。诚如黄侃所注:“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41)黄侃著,黄延祖重辑:《文心雕龙札记·原道第一》,中华书局,2006年,第5页。互文关系编织的天罗地网,包含天地万物,没有什么能置身其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全都经过了“文”的洗礼;我们亲历的现实人生,无一处不曾被“书写”过。尤其中华文明以书写为中心,人们对文本书写的重视超过其他文明,这也正是互文性现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尤其丰富而悠久的原因。
四、“言尽意”的转向:宋代语言观与互文性写作
若从唐宋诗歌转型角度考察,“复现”还具有更深远的理论意义。《溪诗话》提出“用自己诗为故事”,多举白居易、苏轼为例证,正呼应中唐至北宋诗歌转型的倾向:“言尽意论”的语言观转向。李贵指出:“中唐—北宋的诗歌革新实质上是语言本体观的反转,是诗歌语言的革新,语言取代意象被视为诗歌的第一要素,诗歌的优劣不在意象的优劣,而在语言的表现力,在于表达的‘尽’否和‘造语’的‘工’否。”(42)李贵:《言尽意论:中唐—北宋的语言哲学与诗歌艺术》,《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宋人对诗歌语言具有强烈的自信心与进取心,这种语言乐观主义推进了互文性写作的发展。
其一,语言对题材的占有困境。一方面宋诗对唐诗题材的复现成了不可避免的问题,宋人的任何写作本质上都是一种“复写”(43)孔帕尼翁在《二手文本》中将互文手法当成所有文学写作的模式,认为“写作就是复写”。参见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页。。在此困境中,宋诗题材的扩展是应对之策。另一方面,与题材扩展并行的,是宋人对语言的开发。诗歌对不同题材的挖掘终有穷尽,语言对同一题材的写法却能变幻至无限。例如王安石、欧阳修、梅尧臣等人以王昭君为原型进行同题诗歌竞赛,对已定型的题材进行多角度翻案。再例如欧苏“禁体物语”的原理,也是对已定型的写法进行对抗。翻案法、禁体诗在宋代的风行,正显示着宋人在“意新”“语工”两方面做到“言尽意”的努力。正如周裕锴指出:“从宏观的角度看,整个宋诗就是一次对唐诗的大翻案。”(44)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年,第198页。宋人努力在书写领域与唐诗争夺占有权,语言或曰文字书写在宋代成为作诗的最高目标。宋人的语言乐观主义既表现在诗人与他人的竞争,也扩展至诗人与自己的竞争,于是自我复现的诗歌开始涌现。黄彻认为复现的原因是“作诗多者乃有之”,此解看似浅显,实则揭示真理:复现不是作诗数量多者,而是表达“尽”、语言“工”者乃有之。
其二,中国传统的互文性写作。20世纪60至80年代,互文性理论在巴赫金、克里斯蒂娃、巴特等人的提倡下,发展为影响深远的理论。(45)姚文放:《文本性/互文性:生产性文学批评的文本形态》,《文艺研究》2022年第5期。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复现,与西方的互文性理论有相通之处。正如杨景龙指出,中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用典、化用、拟作等手法,可对应西方的互文性写作概念。(46)杨景龙:《用典、拟作与互文性》,《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商伟也指出:“与欧美文学相比,中国语境中的典故出处等互文性现象更丰富,历史也更为悠久。”(47)商伟:《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52页。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互文性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互文性写作大量、真实地存在,具备比西方文学更丰富而悠久的传统;另一方面,互文性的修辞学倾向在中国古代文论中饱受争议。中国古典诗学以“情志说”为正宗,以《诗大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为正统,这是一种“去修辞学”的诗学。人心内在的情、志、意被视为诗歌的最高理想,而人工修饰的文、言、词被无视或贬低。在情志说的框架内,互文性写作难获主流认可。但是,诗学理论上的黯淡,并未遮掩住创作实践中的光芒,宋人的互文性写作在修辞学上有着重要贡献。进一步而言,宋人是迟到者,唐人何尝不是?文学史能绵延数千年,充分证明了任何题材都不可能被一次性穷尽;而中国古典文学的悠久历史,又何尝不是一部“复现”的历史?反向言之,或许正是因为互文性在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过于繁盛,才会引起警醒,令古人不得不呼吁力戒“矫情”。
综上所述,宋代诗学中的互文性概念既参与了语言观上的反思与实践,还关涉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情志说与修辞学,具有深远的诗学意义与理论价值。进一步而言,互文性所体现的文本传统与现实世界、文学形式与思想内容之间的矛盾,是文学史、思想史上的永恒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