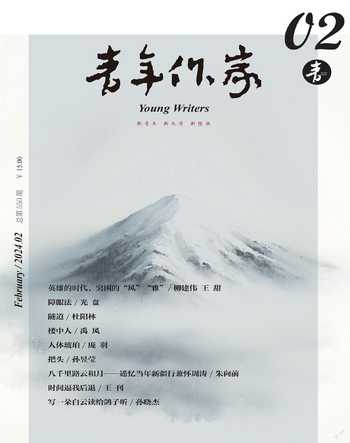火车快跑
一
地上的事要从天上说起,具体而言,要从那些云说起。
地陷东南,站在村庄高处眺望,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陡坡。南面开阔低沉,边缘显示着一条漂亮的弧线,弧线延伸到天际尽头,然后扎进大地深处。北面群山巍峨,山影重重,即便天气好的时候也难看清它们的样子。那些叠加的山影在远处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屏障,偶有几户人家点缀出来,提示大山的存在。无数个晴朗的日子,我一边放羊,一边望着天上的云出神,渴望自己可以像云一样,可以抽身而去,离开大山。北面山间的云,雪白、柔和,姿态万千,可很多年里,人们并不注意它们。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一辈子被土地束缚,无心,也无力欣赏头顶的风景。后来,我走出大山,去到很多著名旅游区,比方说湘西,比方说云南,当我接触那里的人,发现他们跟村里人一样,只关心粮食、收成以及儿女的成长,至于美以及审美,无关紧要,生存之外的一切都被忽略了。
相对而言,南面的云显得昏黃、浊重,仔细分辨,甚至有一点脏。然而,就是那样的天空,那样一块被脏云笼罩的地方,让村里人充满了向往。原因很简单,那是县城所在地,那些昏黄浊重之物,由汽车尾气和工厂排放的废气构成。从县城出发,一直往南,朝弧线的尽头走去,将抵达广州、深圳,那是打工挣钱的地方。
事情总是这样,越重的东西越须轻拿轻放,沉重之物往往要靠轻盈的东西托着,正如白云托起大山,灵魂托起肉体,而火车托起整座县城。那时的县城肮脏破败,道路狭窄,交通秩序也混乱不堪,红绿灯多是摆设,无人将它放在眼里,街角旮旯里人畜粪便随处可见,但它毕竟是我们勉强可以触及的叫做城市的地方。那里有政府大楼,有一栋挨一栋的小区房,还有储蓄所、电话亭、新华书店,更有远道而来的咆哮着的火车。
现在,我终于说到了火车。
像饶舌的老太婆,一番遮遮掩掩后才谈及正题。
关于火车,我首先想到的是从云层穿越而来的汽笛声,那声音坚硬如铁,带着不可回避的威严。只可惜,很多时候火车进站时并不鸣笛,我只能匍匐在地,通过大地的震颤,用耳朵和胸膛去感受它的来临。少年时代的我,脑海中有三个截然不同的火车形象,它们分别由三种截然不同的人所构建。
第一个形象来自孟林。他有两个家,一个在村里,另一个在火车上,除了逢年过节,其他时候多半在跑江湖。孟林长年住在火车上,火车走到哪,人就跟到哪。他很有钱,日子过得潇洒,不但在村里修了小洋房,在县城也买了一套,那是一个在火车上做生意的人。别人难得一上的火车,孟林不但每天可以坐,还能靠它发财致富,这让大家羡慕不已。
相对于孟林,在另一个故事中,火车向我展示的是它极为凶险的一面。那人不知姓名,身材魁梧,据说是李家寨的,是个热心肠。一次,他跟女儿一起坐火车,在车上遇到歹徒作恶,他站出来替人打抱不平,结果遭到暗算,横尸野外。那人确实有一些拳脚功夫,自恃本领高强,正因为这样,当所有人都选择视而不见时,只有他出手阻拦。教训完歹徒,他去上了一趟厕所,之后就不见人了。女孩久久不见父亲回来,就到厕所去找,她找遍了所有车厢,敲遍了所有厕所的门,都不见父亲身影,直到火车到站,她也没能等到父亲,只好一个人回去了。两天后,有人报案在铁轨边发现一具男尸,正是女孩的父亲。李家寨离我们村不远,那人却不知姓名,由此我怀疑故事的真实性,它很可能是杜撰的,以此告诉我们,出门在外,少管闲事,多出眼睛少出嘴。与孟林相比,这个故事显然更具现实意义,毕竟这种事谁都可能遇到,孟林的本事却不是人人可以练就的。
更多一种形象来自打工者的描述。他们众口一词,却刻画不出火车的准确模样。不知道是表达能力有限,还是所坐的火车各有不同。那些打工者,无论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个个对火车充满敬意,可描述起来却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在他们眼里,火车永远是拥挤的,难上的,不知何时抵达,也不知何时出发,充满了不确定性。它没你想的那么好,他们说,坐火车可不是闹着玩的,赶火车并不轻松愉快。白天坐火车和晚上坐火车不一样,晴天和下雨天也不一样,大雪纷纷的时候,又是另一番情景。他们谈论火车的时候,更多是在谈论火车上的人和事,火车本身反倒被遗忘了,像一群饿极了的人,只顾把肚子填饱,完全不记得吃下的是什么。
三种截然不同的描述让我陷入了巨大的迷茫之中。
二
我们县的火车站在城西,不在进城的必经之路上,没有特别的事,我们很少往那边走,即便去,也是匆匆一瞥,没有多少时间停留。少年时代,我去县城的次数少得可怜,车站又是小站,经过的车次有限,每次在街上听到动静,朝车站方向飞奔而去时,火车早已走远,只留下一个短小的尾巴,一甩就不见了。车站站台简陋,从人行天桥往下看,只是几排滴满油渍的铁轨,充满颓废、浓烈的工业气息,正是那种气息对我实施了致命的诱惑。铁路属湘桂线,建于抗战初期的1938年,迄今已有几十年,然而铁路线经过的地方,还是那么落后,乃至于闭塞,似乎铁路仅仅只是经过,火车轰隆隆地来,又轰隆隆地去,并未惊动沿线人们的生活,除了那些打工者,铁路的存在对大家没什么影响。
20世纪90年代前,村里坐过火车的人屈指可数,没有远亲,坐火车都是为了出门打工。1995年之后,我们跟火车的联系才多了起来。村里的孩子,不论男女,大多初中一毕业,办一张临时身份证,就到南方打工去了。我妈坚决反对我出门打工,在她看来,那些人没挣到几个钱,每年开春火急火燎地出去,年底又灰头土脸地回来,一年到头只不过多看了几个地方而已。他们不知道自己该去哪,能做什么,纯粹是为了出走而出走,盲目地把自己抛给了未知世界。安心读书,考上大学,堂堂正正地走出大山,母亲如此教导我。因为母亲的坚持,我与火车的会面被一再推迟,在此之前,哥哥先一步登上了火车,他是村里第一个本科生。
哥哥的大学在省城长沙,放在全国,也赫赫有名。每年春节过后,当打工者纷纷涌向南方,只有他反其道行之,独自北上,给人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似的悲壮。我问他坐火车的感受,他笑而不语,说,你很快会知道的。哥哥说这话时,已经在读大三了,连着坐了三年的火车,每学期至少两趟。哥哥对我很有信心,但很遗憾,他的描述比外人还要模糊。他在有意回避什么。
那年高考,我发挥失常。成绩出来时,学校和我都很失望,班主任想动员我复读,来年考个好学校,我自己也有这个意向。可两兄弟读书,家里早已山穷水尽,再也拿不出一分钱了。我只有一次机会,有学校就读,没有,那就接受命运的安排,老老实实出门打工。填完志愿,一连二十几天,度日如年,每天经受失眠的煎熬,家里看出我的苦楚,却束手无策,帮不了任何忙。我依然每天到山上放羊,依然站在山巅朝县城方向张望,脑袋却是木的,茫茫然一片空白。不知接我的火车来不来,从哪个方向来,我填了三所学校,从以往录取情况看,希望渺茫。
好在,它到底还是来了。
一辆不知名的火车,猛地急刹车停在了我身前。
我从来没注意,也不知道常德师院这个学校,更没听说改名后的湖南文理学院。像绝大多数考生一样,我有着不切实际的臆想,平日关注的都是名牌大学,诸如清华、北大这些,很少注意地方高校。小孩子年幼無知,谈论理想时都想当科学家、军事家,有谁想去当农民,或者出门打工?志愿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填的,并且接受调剂。那时没有电脑,更没有智能手机,无法通过网络查询学校的具体信息,哥哥也爱莫能助,旁敲侧击地在他常德籍同学里打听到一些零碎的信息。从通知书上的简约地图看,我要坐火车往西北方向走,经衡阳,过长沙,穿越整个湖南,由最南抵达最北。
要去一个完全没想过的学校读书,心里难免有些失落。但终归还是高兴的,无论如何,我以后不用放羊了。
三
东安是个小站,很多车是过路车,并不在此停靠,经过的时候,鸣一下喇叭,告知一声,便扬长而去。过东安到长沙去的车每天只有一趟,在凌晨一点。我没有选择,要么下午出发,在站里等半天,直到午夜时分。要么托关系,在县城找一个落脚之地,时间到了,再去赶火车。我们家的人脸皮薄,不愿为小事给人添麻烦,再熟悉,再有交情,即便人家主动开口,我也不敢上门叨扰。早早赶到车站等着。极度的疲惫和焦灼的等待,让午夜时分的我看起来像一个逃难者,过去对火车的想象早已不知所踪。
好在有哥哥作伴,坐了三年火车的他,经验丰富,此刻充当着向导和送行者的双重角色。火车进站时,一道黑影巨墙般遮住了进站口的灯光,在光线暗下来的瞬间,候车室的人如睡醒的猛兽,不由分说朝进站口涌去。哥哥拉了一下我的衣袖,喊了声,跑!行李箱不再拖在地上,而是扛在肩膀上,不是朝眼前的车厢跑,而是奔向更远处的车厢,这是哥哥提前告知了的。他说,县城这样的小站,上车的人太多,都奔向眼前的车门,你很有可能挤不去,成为火车的弃儿。事实证明,哥哥是对的,他这么多年没有白坐火车。
人实在太多了,除了我们县的,还有隔壁新宁县的,他们县没有火车,要出门,只能来我们县坐车。开学季正值客运高峰,很多时候乘务员连大门都不开,不是他们工作失职,不愿开门,而是人满为患,根本无法推开车门。有能耐的,从窗户爬进去,那就走,爬不进去的只能等明天的下一趟。好在当时的火车票有效期是三天,每个人有三次这样的机会。现在看来,三天有效期的设置,正是为我们县那种小站乘客所准备的。
为了不耽误行程,很多人坐火车都有朋友相送,先让乘客爬进去,之后他们再把行礼从窗户塞进去。有经验的乘客会随身带一根短小的木棒,万一里面的人嫌挤,故意关窗,他们会用木棒把车窗撬开。那些年,我见过各种各样的坐火车的招数,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每当火车开动,总有一部分人会赶不上车,被滞留在夜色之中。看着那些绝望无助的人,我不禁眼泪盈眶。那是我的兄弟,是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姓氏的我。
夜色中,闻到一股特殊的酸腐味,有机油的成分,也有方便面的成分,还有汗臭、铁锈等其他成分,那种气味除了火车站哪里都闻不到,我想,那就是火车的味道。
四
第一次出远门,忐忑又激动,不敢闭眼睡觉。事实上,也没有条件睡觉。在没有实名制的年代,票贩子一人可买上百张票,然后转手高价卖出,从中赚取差额,他们就住在车站附近,以此为生,几乎垄断了票源。那些人有小道消息,知道什么时候出票,什么时候排队是空等一场。票贩子买完一半以上的站票,工作人员又垄断了坐票,其他人自然无票可买,无论多远的距离,哪怕坐上两天两夜,都只能站着。出行的艰难,也让我明白,为何村里那么多人宁愿老死在山里,也不出门谋生。
那是一辆老式绿皮火车,很难说它到底是客车,还是货车,又或者运牲口的专用车。车里被塞进各种不明物件,蛇皮袋、塑料桶、拉杆箱、竹筐、油瓶,吃的、用的,甚至还有厚厚的棉被(未雨绸缪,夏天出门,也要带上冬天的物品)。凡家中所有,生活所需,都被他们搬上了火车。他们是带着村庄上路的,走到哪都没有安全感。越穷,带的东西越多,有钱人才两手空空,他们只要带上钱就行了。我曾在火车上见过活鸡活鸭,还有尖叫的猪崽。人们对于猪崽上火车似乎并不惊讶,也不嫌弃,给予了相当的照顾。至于它是如何上车的,更无人追问。人连脚都没地方站了,一个个脸贴着脸,肉贴着肉,居然还慷慨地给小猪留下一处可以横放的空间。他们生怕小猪会被挤死,或者热死,对于人,则没有这种担心。挪过去一点,再过去一点,插进来一个人,再插进来一个人,空间的挤压,就像对时间的利用,永远有压榨的可能……那头猪崽之所以受到礼遇,跟它的用途相关,它是被老头用来给儿子定亲的,女方要求按当地的规矩办事,必须从男方家里送一头猪崽过去。满车人挤得死去活来,喘息不定的时候,只有那头猪绅士般横卧在地,火车开动之后,摇晃几分钟,它就发出了畅快的鼾声。我羡慕那头猪崽,看起来它才是真正的乘客,而我更像是牲口。
原本一个人的位子,要坐两个人,每人各搭一半屁股。过道、厕所门口,全挤满了人。每次有人上厕所,需要全车人的配合,餐车经过时动静更大,工作人员老远就开始指挥,车厢像结实的罐头,被填充得满满当当,水泼不进。然而,就是这看似密不透风的人肉罐头,每到一站,火车一停,总能挤上三五个人来。于是,罐头变得更紧致了。即便如此,每当火车停下,车窗打开时,我们都忍不住伸手,拉他们一把。没在深夜赶过火车的人,肯定无法理解这种特殊的友谊。
那辆车在所有小站都停,虽然并不都开门纳客,却一定要停下来喘几口气,休息够了,再继续上路。有时只停几分钟,有时长达半小时。后来才得知,它不是在喘气,而是在给主干道上的车让路。东安、冷水滩、祁阳、祁东、衡阳、株洲、长沙,中间夹杂七八个小站,三百六十公里路,要坐六个小时车。我没有选择,那是从县城路过的,去往省城的唯一一趟车。
五
九月,天气依然炎热。车厢里蒸起了人肉包子,雪花膏、脚气的味道混合汗水、污泥以及打碎酸菜坛子的气味,我们是没洗干净的馅,被匆忙掺了进去。没有空调,顶部只有一排小风扇有气无力地摇动着,它们吹出的风完全可以忽略。有人开始脱衣服了,先是一两个,三五个,然后迅速蔓延,车厢很快赤条条一片白肉。女人们对此并不介意,没人因为不文明而提出抗议,她们选择了闭目养神,或者扭头望窗外的夜色。其实她们也想脱,只是碍于性别,不得不故作矜持。她们的衣服跟男人一样,早已湿透。
车走的时候感觉还好,一旦停下,如重物压身,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想挪个位置,哪怕换个姿势也行,然而不能。身边某位乘客说,别急,到衡阳就松了,衡阳是大站,会有很多人转车。但衡阳很危险,千万不要下车买东西,火车好坐,衡阳难过,他补充说道。我问,为什么衡阳难过?他说,衡阳乱,扒手小偷最多,他们在那里有窝。我有些惊讶,问哥哥,是这样么?哥哥说,是的,都这么说,不过我从没在衡阳下过车,不知道具体情况。旅途寂寞,又热得难挨,那人找到话题打发时间,滔滔不绝起来。知道么,北方来的大雁飞到衡阳就飞不过去了,因为雁过拔毛,它们怕。我听完笑了起来。要不是读过那首古诗,我可能真信了他的鬼话。
车到衡阳,状况并未改善。虽然有很多人在那里下车,可同时,又有更多的人涌上来。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命运,谁能抵挡?不过,那人的话,并非空穴来风。有一年寒假,因为没买到长沙的票,我被迫在衡阳转车。午夜时分,都市尘埃落定,天空繁星点缀,穿过车站广场时,我忍不住放慢脚步,独自在广场散起了步。可没走多远,我发现有一前一后两个黑影在向我靠近,他们手里好像拿着什么工具。意识到问题,我赶紧转身朝进站口方向走去。见我要走,那两个人也快步跟了上来。好在这时又有五六个背书包的学生出现,他们大概跟我一样,也是在衡阳转车,结伴来广场散步的。歹徒误以为我与那几个学生是同路,被迫停下脚步,躲在角落里徘徊不前。我朝那几个学生做了一个手势,他们扭头看了一眼,很快明白我的意思,一行人快步进了车站。短短的几分钟,给我留下了惊心动魄的印象。那时,火车站没有电子监控,不法分子有恃无恐。
六
后半夜的火车走走停停,车厢里人声渐息,慢慢归于平静。坐着的、趴着的,什么都不顾直接瘫倒在地的,能睡的人尽可能入睡了,有的甚至站着进入了梦乡。车灯很亮,窗外一片漆黑,不时有亮着灯火的屋子闪过,大约是经过山区或者某个小镇了。车轮哐当作响,制造出强烈的恍惚感,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也睡着了,睡梦中的我,坐着巨轮在黑暗的海面上漂浮,那些亮着灯的房子,是大海中的灯塔,让我暂时摆脱了对黑暗的恐惧。
不知到了哪,一心只想着天亮。
哥哥说过,天一亮车就正式进入长沙地界了。到了长沙,一切会变得不同。因为从长沙到常德的车况比这一段好,乘客要少很多。那段路是从大城市往小地方走,每到一站都会有人下车。
之前我对长沙有过很多猜想,可当黎明降临,自己真正站在它跟前时,却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坐了一整夜车,一直站着,脑袋是懵的,心神飘忽,感觉身体失去了重量,在额头上拍击两下,传来的是木质般的回响。天亮得很早,七点半世界已被太阳完全照亮。晨光下只见一片耀眼的楼盘和满城的喧嚣,车站对面的五一大道上车来车往,这是我对长沙仅有的印象。我站在车站广场,远远看了它一眼,便匆匆跟哥哥道别。
出了长沙,再没遇到过高山,最多是几个起伏的土丘。益阳之后,更是一片坦途,视野一段比一段开阔,世界进入了另一个次元。这就是洞庭湖平原了,平得让人踏实,让人心安。东安、衡阳段,感觉不是在坐火车,而是在无底深渊里爬行,不知身在何处,此时,我才真正体验坐火车的滋味。窗外那些景物,稻田、荷花、不断出现的河流和桥梁,偶有一块山坡进入视野,堆积出翠绿的浓荫,渔船和打鱼人在水面上漂着,遥远又亲切,如此景象跟那个被大山环绕的村庄完全不同。这里的云与故乡相比,薄而轻盈,有一种彻底的自由,世界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它的丰饶,我兴奋莫名。
依然是站票,不再摩肩接踵,身体有了足够的活动空间。依然是绿皮火车,但安装了冷气空调,凉风一吹,心情大好,即便一夜没睡,也不觉得累。尽可能捕捉眼前的景色,有白鹭在田野翻飞,过膝的禾苗在长风吹过时俯下身子,露出其间的涓涓水流,这一切让被黑夜遮蔽整晚的心瞬间变得明亮。跨出家门之后,我第一次产生“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因为我看到了所谓的别处的风景,看到了不同地方的农民的命运,他们在这么大块、这么平坦的农田里劳作,真是有福啊。相比而言,老家那些梯田实在太陡峭了,如果能在这里拥有一块土地,即便当一个农民,也可以过好一生吧。在泥土里长大的人,生平第一次对土地产生了占有欲,此前,我无比讨厌它们。
车过汉寿,上来一老一少两位僧人。他们买的也是站票,从脸色、容貌看,老者年岁不小,有人给他让座,他坚辞不受。见老者不坐,年轻的也陪他站着,大约是徒弟了。两人肩头各背一个黄布口袋,布袋一角有褪色的淡蓝色字样,我看清了,印的是“乾明寺”三个字。年轻僧人从布袋里摸出一个诺基亚手机,以为要给谁打电话,没想到只扫了一眼,又立马抬头,嘴里念念有词起来。他是在念经。据说僧人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窗外景色跟手里的那个手机,在他看来,大概只是记录经书的工具吧?大地的经书,我们或许能略知一二,他手里的经书,旁人无从了解,更无从分享。他念经的样子,很像学生在填补缺失的功课。老者不看我们,也不看徒弟,面露微笑,把目光投向窗外,眼里流露出大规模的笃定。两位僧人除了装扮,跟其他乘客没什么区别,但他们的存在,让整个车厢变得异常宁静和平稳。如果前一夜有他们在,也许就不会那么难熬吧。出家人两手空空,却给了我们最大的秉持,那種感觉难以形容。
因为心情好,感觉火车也快了起来,三个小时很快过去。
七
常德到了,广播在大声叫喊城市的名字,陌生又令人激动的名字。
我看了看手里的电子表,时间是下午一点。从县城出发,到常德,包括中途转车,花了整整十二个小时。十二个小时耗掉了我人生的头二十年,这是从大山到平原的距离,也是从一种命运到另一种命运的距离。尽管常德是座小城,但在当时的我看来,已经是广阔的世界了。我整了整衣裳,托着行李箱,大步走出了火车站。
学校早有专车等候,它会把新生从车站直接送到学校门口。
上车的人中有两张熟悉面孔。我敢断定,他们是我的同乡,跟我一样,是坐同一列火车从东安县城来到这里的,只是不知道是否来自同一所高中。我没跟他们打招呼,在我看来他们和别的同学没什么区别,彼此朝对方笑了一下,安然落座。
校车停下时,我看到一片恢宏的建筑。從栅栏望进去,里面过道宽敞,绿树成荫,花坛里种了各种没见过的花,最前方一栋高大的办公楼耸入云天。托着行李箱准备往里走,却被领路的告知,你搞错了,学校不在这边,而在马路对面。我有些不知所措,尴尬地顿了好几秒钟才回过神来,然后跟着队伍,过了斑马线。因为前面建筑的衬托,我看到的校门显得很矮小,围墙和栅栏也稀松平常,单从外观看,甚至不如刚刚毕业的高中。原来此前经过的那片区域不是学校,而是工厂办公区,扭头望去,只见对面墙上从左至右,赫然挂着五个烫金大字:“常德卷烟厂”,落款者是“启功”。那栋高大的建筑物也不是什么办公大楼,而是芙蓉大酒店,它顶上立着牌子,要走远一些,抬起头才看得到。我们学校的校门也有题款,是竖排的红色字体,落款者的名字是草书,我认不出来。
这种一街之隔的强烈对比,很容易给人造成心理落差。不过,对一名高考失利者而言,有书读就不错了。后来,校方似乎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我毕业的前夕,将大门改成了后门,后门当作了前门,捯饬整理一番,终于像是一所大学了。我觉得这个做法很英明,堂堂大学,怎么也不能连一个工厂都不如。
很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当时的感受。踏进大学校门那一刻,我感觉大地还在摇晃,火车还在奔驰,它的车轮并未停止,我的身体也还处在颠簸震颤当中。哐当哐当,世界来到了我脚下,火车继续开着,开往不知名的终点和无法预测的未来。
【作者简介】秦羽墨,本名陈文双,生于1985年,湖南永州人,中国作协会员,现供职于常德市文联。著有散文集两部,小说集一部,多篇作品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曾获《创作与评论》杂志年度作品奖、第二届三毛散文奖、湖南青年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