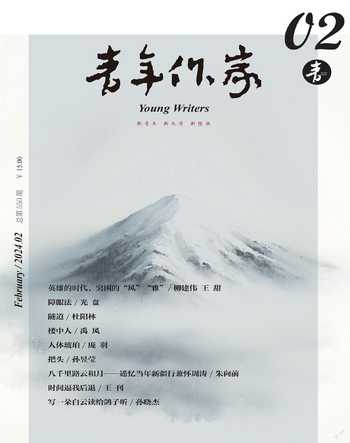同堂
赵黎英
爸妈在温暖的冬日下午抵达位于新泽西的霍博肯小城。他们一路风尘,先从北京飞上海,停留一晚后,再由浦东国际机场搭乘唯一的直飞航班赴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爸妈探孙子的计划推迟了数月。我的宝宝E出生于2021年5月。由于种种原因,我和先生决定不请月嫂“独立”照顾宝宝,令爸妈和亲友费解。在我产假结束上班前,我们照顾了宝宝三个月——他们至今不敢相信。爸妈给E装了满满一个行李箱的礼物,包括五套金饰、七双鞋子、八套衣服和两个木头玩具,还带来了奶奶去世前亲手缝制的三件肚兜。E只对一只小木碗感兴趣。
“哇,他好像个小乞丐哦。”我评论道。爸妈非常生气,从此我再没见过那只木碗。
他们到家的第一天,我爸洗脸堵住了洗手池。我和先生不得不拆开下水道。最后还是我灵机一动,用长长的香氛木枝把塞子顶了上去。当时我俩还觉得这个挑战颇为有趣。第二天,我爸做饭时炸掉了玻璃锅盖,接着是灯泡、尿布桶、他的老花镜……
爸妈不觉得我们租的两居室公寓是家。公寓里摆满了我们精心挑选的古董家具和时髦朋友们送的过于“艺术”的家居用品。
“你有没有正常的盘子?”我爸接管厨房后问我。他搞不懂木盘、瓷盘和甜点盘的区别,也不在乎什么酒杯、香槟杯、马克杯、玻璃杯。而我从前都没想过这会是个问题。
我爸忙着重建厨房的时候(指挥我买大菜刀、十种不同口味的辣椒酱、一个超大洗菜盆……),我妈正焦头烂额。E拒绝吃她喂的水奶。我妈坚持不懈,耐心满满,但身为她的女儿,我知道这个过程一定会让她心碎。至于我爸,他拿着奶瓶对镜头摆拍几次之后,就理所应当地放弃了。
“喂个婴儿罢了,能有多难?”
我们第一次吵架是因为他总是半真半假地问E要不要和他们回国住三年。
第二次吵架是因为我“好心”问他想不想去曼哈顿感受最后的圣诞节日氛围。
一个月后,我们最大的争吵爆发了。我爸多次批评我妈动作太慢之后,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说他应该“帮忙”照顾宝宝。一般情况下,我拒绝在和男性谈论家务勞动时使用“帮忙”这个词。但为了“屈就”,我还是说了。
他恼羞成怒。
“我每天干多少活儿?你没看到你妈喜欢照顾孩子吗?我做饭,倒垃圾,热奶!”
“你是说……把奶瓶放进加热器按一下?倒垃圾最多五分钟。做饭最多一小时。我妈每天工作几小时?”
我冰冷的计算彻底惹怒了他。“我跟我老婆说话,你插什么嘴?这不是你说话的时候。”
这又触到了我的死穴。我们都还记得我俩在纽约我的毕业典礼前的那次激烈争吵。他责怪我妈没有正确刷地铁卡。我替她帮腔的时候,他说,他想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那场战斗以他威胁飞回国结束,而我哭着大叫,“我今晚就给你买票。”
我爸 2020 年退休,作为大家长,他受到所有人——我家、亲戚家、亲戚的远方亲戚家、老家隔壁村的二叔三婶的尊敬。他是单位领导,有绝对权威。工作几十年来,他从没停过,在家待超过一天就浑身不舒服。
可现在他成了旅居美国的中国老人。他不懂这里的语言和文化,但拒绝承认。他不喜欢我教他,更不喜欢我是那个教他的人。小时候他一直是我的模范、我的英雄,可现在我长大了,成了老师的老师。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了。
我的父母和所有父母一样,望女成凤。我也没让他们操过心,读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商学院,在纽约工作,定居在哈德逊河对岸五万人口的中产小城霍博肯。
他们曾经都是记者。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我爸就教我“认识社会”。他是最拼命的记者,几乎走遍了全国。不管什么人,只要聊上三两句,他就能立马辨认出对方的口音、老家的区县、当地的风物,还能说上几句各地方言。无论在如何混乱的场景,他总能认清方向,免去繁琐。他常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小时候,他象征着全部的成人世界,我迫不及待地希望像他一样,在这个混乱而令人着迷的世界游刃有余。
世事难料,长大后,我并没有在他的世界生活。我偶尔也会用上几招,令我的先生惊叹(“这么聪明!”他会用会得不多的中文称赞我)。其中最好用的,就是通过各种细节迅速判断出对方的出处,只不过不再是区县,而是大陆、香港或者韩国——那些我曾经生活过、留下珍贵回忆的地方。
没想到,在这个白人社区,我爸又用上了他那一套。据我妈说,他们遛娃的时候,我爸会直视遇到的每个亚洲人的眼睛(又一个令我尴尬的行为),用中文发起对话。到目前为止,他屡屡成功,只失败一次。
他们就是这样认识郭阿姨的。郭阿姨打开了霍博肯“海漂”一族的大门。阿姨是我家楼上邻居毛毛家的保姆。她五十来岁,个高结实,是经中介引领,从河北农村来美国打工的。郭阿姨来这里是为了圆自己的“美国梦”。她在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落脚,先在中餐馆做洗碗工,后来餐馆生意不景气,又做起了育儿嫂。阿姨每周工作六天,休息那天常搭雇主的车去法拉盛见朋友、给家里汇钱,除了不能回国,她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这栋楼有八家中国人,”她非常肯定地告诉他们。“三楼三家,四楼两家。之前五楼有两家,一家搬出去了。六楼有两家,新来的是上海的。”
这种了解让我先生直冒冷汗。
郭阿姨的领路人角色到刘大爷出现后便告一段落。刘大爷和我爸妈背景更为相似,有一个在大学教书的儿媳和在谷歌工作的儿子。刘大爷摆地摊起家,但最终成了一名颇为成功的商人,并资助儿媳攻读博士学位。他和我爸很快成了朋友。从冷冻比萨的价格到对俄乌战争的看法,他们的讨论涉及方方面面。刘大爷自诩为“霍博肯通”。
刘大爷掌握更多的八卦传闻。傅大叔的儿子房子是八十万买到的,“很划算”。王叔叔的儿子在 Meta 工作,儿媳还在华盛顿读研究生,孙辈只能靠爷爷奶奶照顾。李爷爷家的房子是低价租的,现在房东把租金抬高了三分之一,全家决定搬到泽西城的一栋三层联排别墅。在刘大爷看来,那地方比这里差远了。
“他们住不起这儿。”刘大爷说,随后便历数泽西城的各项不是。
“那儿真的脏乱差,不适合养小孩吗?”爸妈问我。我说,泽西城很大,每个城市都各有利弊。他们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
李爷爷和邻居告别时,我爸妈仔细观察刘大爷的反应。
“那儿不安全。”刘大爷最后说。
“我会功夫。”李爷爷开玩笑道。
我问我爸对刘大爷的咄咄逼人有何感想。
“做人不能这样,不厚道。”
我以给E送水杯为借口,观察爷爷奶奶们的动向。他们聚集在公园一角,他们的谈话主要集中于对各家宝宝的动作描述。
“看,E在喝水!”“哇,嘟嘟也想喝水。”“他们都想喝水!”“毛毛走到小树林去啦。”他们似乎没什么话可说,也可能因为我的在场。
爸妈上下午各出门遛娃一次,带回来的故事,用先生的话说,“比我们住这里的三年还要精彩。”陈家老两口在公园迎上了我爸妈,原来他们错把我家的婴儿车认成了郭阿姨家的。而他们急着找郭阿姨的原因则是她介绍认识的“劲松奶奶”(没错,以北京街道命名)。奶奶的女婿是美国人,奶奶热心,替着急为女儿找对象的陈家老两口物色了一个合适的ABC,“各方面都挺不错的,就是有点矮,一米七。”开心过头的二老还没回到家,就不慎遗失了通过郭阿姨拿到的劲松奶奶给的联系电话,心急如焚,只能在公园守株待兔,殊不知等到的却是我爸妈。
我妈补充,陈家二老口音浓重,又似耳背,沟通不畅,但陈家姑娘在高校任职。
“怎么还需要爸妈找男友呢?我看你们都是瞎操心。”我说。
我先生十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在一段旧录像中,他身穿黄色羽绒服,看上去是个典型的亚洲小孩。那段录像总让我想起20世纪90年代电视上的亚洲移民,譬如《北京人在纽约》。录像中,坐在表哥的车里,十岁的先生似乎对小狗比对全新的美国更感兴趣。在另一张照片中,他站在一栋别墅前,手里拿着可乐。“在美国,你每天都能喝可口可乐。”
移民前,他和家人住在首尔江南区的公寓。我的公公毕业于高丽大学,在起亚汽车工作,然后转到一家建筑公司。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韩国人还没有能力自由旅行时,这家公司把他派到了南亚、中东和欧洲。到美国后,他尝试过各种工作:汽车推销员、补习班老师和洗衣店老板。
与大多数第一代移民不同,我公公他们从未要求我先生从事更易提升社会阶层的职业。创意写作硕士毕业后,他住在纽约东村几平方米大的房间写作,同时在非营利组织帮助工人维权。直到三十岁,他才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我们在同系相遇。
从子女教育来看,我父母和公婆的理念相近。我爸妈也从未要求我根据收入来选择职业。毕业后,我从事艺术管理工作,之后来到纽约攻读历史硕士学位。在他们生活的圈子里,没有人的子女会如此“特立独行”。除此之外,我的两组父母几乎没有共同点。
爸妈到达霍博肯后,公婆前来接风并在我家共同庆祝圣诞节。在“亲家峰会”上,他们愉快地交换了礼物。两位父亲互相询问彼此去过哪些国家并进行比较:法国、意大利、土耳其、朝鲜、俄罗斯……
在父亲们外交的过程中,母亲们笑着看向彼此,没有出声。
一个月后,我们邀请公婆共度农历新年。我从中国城买了墨水和红纸,设计了家宴菜单。所有菜品都结合诗句命名,我爸也得以展示他的书法水平。我先生让婆婆带来她的拿手菜。他负责了菜单上的韩文部分,以及清酒和甜酒的插画。公婆对爸妈的菜式赞不绝口,餐桌上,他们的话题只有食物。
第二天,我们在一家俯瞰哈德逊河的酒店餐厅吃早午餐。餐厅里挤满了派对装扮的年轻女孩,看上去像是从新泽西各个小城涌来的。这是那种我和先生曾经绝不会踏入一步的餐厅——吵闹、豪华但没有格调——但它很宽敞,并提供儿童座椅和尿布台。这对我们曾经热衷的那些浪漫温馨的小众餐厅来说都是奢侈。结账后我才意识到,近两小时的一餐里,我没有和任何人真正交谈。
但是有E在。因为他,两个家庭走到了一起,维持表面的和平。有时这就够了。
八十年代末,我也曾是那个一切的中心。奶奶从乡下来帮忙照顾我,从我出生到幼儿园,然后是小学和初中的几年。记忆中,我从来不喜欢和爷爷奶奶在一起。我不能完全明白他们的方言,无法和他们交流,更別说互相理解。他们对我来说太老了,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出生了,和我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呢?我也不记得爸妈和他们有过任何真正的对话,除了晚饭吃什么以及“不要囤塑料袋”。我还记得,午饭时我常常沉浸在言情小说里,尽管他们就坐在我身边。我当然知道这不礼貌也不应该,可在青春期以自我为中心的少女心中,我不在乎。我甚至一度没当他们是爷爷奶奶,而只是爸爸的爸妈。
爸妈可能批评过我,也可能尝试改变和上一辈的关系,但他们太忙了。虽然没有语言表达,我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对父母的爱。特别是老人去世时,少不经事的我看到了爸妈的爱和脆弱。妈妈伤心了好几个月。至于我爸,他强忍眼泪,用我从没听过的温柔语气对我说话,好像他很害怕。我想他真的很怕。
当我不再需要照顾时,奶奶离开了北京,再也没有回来。“最近我一直在想你奶奶,”我妈说。“我们跟她一样,甚至比她还惨。至少她还能听得懂。”在美国三个月后,爸妈得出结论,他们永远不会搬到这里。他们不想完全依赖女儿,在没有朋友和自由的情况下度过晚年。
我曾对我们的关系非常自豪。我和爸妈不像大多数传统家庭,把我们的谈话限制在是否吃过饭上。我们分享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我常怀念我们在北京夏夜晚风下沿着河边散步唱歌的美好。从小学起,我爸就会设定主题让一家三口在规定时间内写作文。他会评论每个人的作品,包括自己的。结论总是一样:“我女儿写得最好!”
岁月悠悠,改变在不经意中发生,以至于我都没有机会留心丢失了什么。离开北京上大学后,家成了一个遥远的概念。爸妈是如此遥远,起初是地理上的——两千英里之外——然后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当我在香港和纽约建立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后,那些美好的回忆逐渐褪色。
这是我离家后第一次和他们同住。在霍博肯我的家里,他们变成两个老人。周围的一切都太过陌生,我和先生谈论的所有事情,他们都难以理解。但他们一直在努力。他们甚至问起我当地的华人教会,他们一向对这些最没兴趣。“听说他们有免费英语课。”“他们好像有很多活动呢。”在这个年纪,很残忍地,他们也许体会到了第一代移民的感觉。
来之前,爸妈偶尔会跟我提及我的老同学们的消息。在机场,他们遇到了我的小学同学,他做地勤,给了爸妈一些方便。他们去派出所的时候,遇到了我的初中同学。她问我妈:“她真的要销户吗?”二十多岁的我从未质疑过我选择的生活。如今我三十几岁了,奔波于工作和家事,有时会想,一路越走越远,真的是件好事吗?如果我从没有离开过家,爸妈会不会更快乐?我知道我不会,我的高中和大学同学们也不会——他们都是“别人家的孩子”,离开就不会回头。
尽管我不愿承认,爸妈真的老了。有时我会隔着客厅观察对面的父亲,他走路的样子,他在沙发上打瞌睡,他下垂的嘴角。我们常常沟通不畅,因为我说话太快,或者他没在听,或者内容对他来说太陌生,需要太多解释。他不再是我记得的那个人。我记忆中的他潇洒不羁、诙谐幽默。虽然他的顽皮偶尔还会从笑声和表情里闪现——和E几乎一模一样,但他早已不似从前。
我爸一直以我为傲,把我“当男孩养”,告诉我要自信坚强。但在E身边,他变得异常温柔。在室外,他不断摸他的手,保证他不会太冷(尽管我说过多次正确的做法是摸脖子的温度)。E用小手敲打桌子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手垫在桌子上怕他疼。E终于开始学习站立时,我爸僵硬地陪在他身旁,看得出来,他用尽全身力气才能控制自己不把晃晃悠悠的E抱进怀里。
变老是不是意味着失去个性,直到变成一个连女儿都不再认识的陌生人?我问自己,等E长成一个美国小孩,他还能和我的爸爸妈妈沟通吗?他会怎么看待我和他们的关系?
“等我死的时候,”我爸在厨房撒着过多的盐和辣椒说,“你给我烧炷香就够了。”
“说什么呢!”我被自己突然的眼泪吓到,逃进了房间。
爸妈来霍博肯之前,我在一家可爱的童书店给E买了绘本《大洋彼岸的爷爷》。作者从一个亚裔美国小男孩的角度描绘了男孩和祖父之间温暖的爱的纽带。“爷爷总是打盹。他吃难吃的东西。他说我听不懂的话。”男孩说。但共度夏天后,他们变得親近了。“我们一起看着海浪来来去去,就像大海另一边的海浪一样。爷爷拥抱我,就像爷爷一样。”
我深深地被这个故事打动,迫不及待地想把它读给E听。但不知道为什么,爸妈来帮忙后,我却似乎开不了口给他们介绍这本书。
我爸三月份的回程航班取消了,当他急切地等待回国投入工作时,他曾经的下属带他进行了一次很美国的公路旅行。他很兴奋,和我们分享了无数照片,表达了各种我不屑于争论的观察。我也急切地等待他回国,以便我们重建日常生活的节奏——我妈、我先生、E 和我。
如果可以选择,我不会想再和爸妈同住。但我们三代相处的时间还有几次?还有多久?时不我予。
【作者简介】赵黎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学系硕士,以中文和英文写作。作品发表于端传媒、三联生活周刊、三明治等。英文作品The Bureaucrats Daughters获2018年手推车奖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