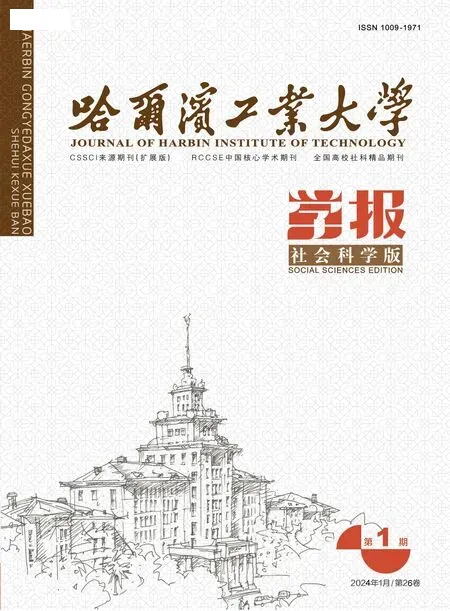“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与“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
刘冬颖 李思远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80)
在中国古代天下观中,“四海”与“九州”是有文献记载以来古人对天下与世界最早的认识,既反映了古人对地理空间的认识,也代表了他们对世界疆域的想象。 其中,“四海”一词最早见于《尚书》,《舜典》有“四海遏密八音”,《大禹谟》有“敷于四海”“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等等[1]282,意为尧、舜、禹的恩德惠及天下四方。 《禹贡》更是勾勒出了天下九州、“四海会同”的格局,蕴含了早期中华文明的“大一统”精神。 在十三经中,“四海”一词出现五十余次①“四海”一词在十三部经典文献中一共出现了51 次:《诗经》2 次,《尚书》16 次,《礼记》12 次,《周礼》2 次,《春秋谷梁传》2 次,《论语》2 次,《孟子》11 次,《孝经》3 次,《尔雅》1 次。,既指东、南、西、北四方疆域,也指夷、狄、蛮、戎等华夏族周边的各部族。 如《诗经·商颂·玄鸟》载:“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来假,来假祁祁。”[2]1344这是对商王武丁政绩的歌颂,不但有中原诸夏部族,还有氐、羌等部族的朝觐与朝贡。 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以“四海”为天下的观念也逐渐成为历代君主一统天下的政治理念与文人的国家政治文化理想,确立了“四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在二十四史中,“四海”出现千余次,不仅成为历代史书帝王本纪中君王实现天下“大一统”的象征,也展现了中央王朝与其他民族地区互相交融的历史。 作为中国古代天下观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四海”观念所指疆域范围与历史内涵的演变,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人对国家与世界边际的地理认知,也体现了对国家统一的“大一统”文化精神的认同。
一、“四海之内”:中华民族“大一统”精神的地理基础
夏、商、周时期伴随着中国各部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产生了以“中国”“天下”“九州”“四海”等融汇了天下观与疆域观的地理词汇。 “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3]445,是先秦时期人们认为的中国疆域范围。 作为中国早期地理观之一的“四海”,蕴含着“四方”疆域观、“四夷”民族观与“天下”世界观,不仅指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疆域,而且指中原地区周围四方民族的居住地,更是指代“天下”的世界观。
(一)“四海”之“四方”疆域观
“四海”所代表的“四方”疆域观,以“天圆地方”宇宙观为基础,一般认为“四海”是“九州”的边界。 “天圆地方”不仅是中国古代天下观的雏形,更是奠定了“大地四方”的空间秩序基础。 殷商甲骨卜辞中已存在“东西南北”的方位概念,如,“贞:燎东西南,卯黄牛”[4]2051,“庚戌卜,宁于四方,其五犬?”[4]4247可见,表示四周方位的“东西南北”及“四方”等地理疆域概念早已在商代出现。 先秦时期常用“四方”“四极”来指代“四海”之意,即中原地区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区域,有东海、南海、西海和北海之称,如《礼记·祭义》有言:“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5]3469《周礼·校人》载:“凡将事于四海山川。”郑玄注:“四海,犹四方也。”[6]1859但“四海”具体的疆域有不同理解。
首先,“四海”指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海域,古人认为中国四面都有海,以此作为世界的边际。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地理观念的影响下,东、南、西、北四海确指的海域范围也不尽相同,多指相关方位的海域。 因中国东南临海的地理位置,先秦时期的“海”一般多指“东海”与“南海”,二者又可互相指代。 如《诗经·江汉》“于疆于理,至于南海”[2]1236,王元林认为此“南海”指今东海海域[7]75。 又如《孟子·离娄上》“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8]5919,一般认为是黄海海域。 秦汉之后,“南海”多指今南海及东南亚海域。 又因中国西北多高山沙漠的地理特征,“西海”与“北海”多指湖泊或较远的海域,如《淮南子·人间训》言“子耕于东海,至于西海”[9]1293。 汉代设立“西海郡”,青海湖又称“西海”[7]77。 “北海”在先秦时期又指“渤海”,如《左传·僖公四年》有“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10]3890,《孟子·梁惠王上》有“挟太山以超北海”[8]5808,一般是指今渤海海域。 汉以后“北海”泛指北方偏远的地区或湖泊,如《汉书·李广苏建传》有“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 除此之外,还有邹衍在“大九州”学说中提到的,“九州”是世界的一部分,“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11]2848,每一大州的四周都有大海环绕。 东汉王充也提到“每一州者四海环之,名曰裨海。 九州之外,更有瀛海”[12]474。 “四海”在“大九州”学说的背景下,建立了以世界为整体的天下观。 总之,虽然“四海”的“四方”疆域在不同时期所指不同,但其作为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代表,是当时人们对中国四方疆域的泛指。
其次,“四海”泛指中国周边区域。 《禹贡》有“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1]323,顾颉刚、刘起釪认为这里“表述了《禹贡》作者较踏实的对神州大陆四至的认识,只有东边是海,西边是流沙,南北两地笼统地指出其边境辽远未定,都不说有海”[13]868。 此处的“四海”就是指中国疆域所至之地。 又如《荀子·王制》篇中有提到明确的东海、西海、南海、北海,但却不都指海域。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东海则有紫紶、鱼、盐”,“西海则有皮革、文旄”[14]161。 其中,北海、南海和西海生产的“走马”“羽翮”“皮革”等都是陆地上的物产,说明“四海”并不是按照实际情况划分的四个海域。 正如顾颉刚、童书业指出的:“最古的人实在是把海看做世界的边际的,所以有‘四海’和‘海内’的名称。”[15]120可以确定的是,“四海”作为一种自然地理观,其表达的“四方”疆域范围多是泛指,表现的是人们对世界边际不同时期的认知。
(二)“四海”之“四夷”民族观
“四海”的概念中,还包含有中华民族早期的民族观。 当时,将中国周边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即夷、蛮、戎、狄等地,称为“四方之夷”。 夏、商、周时期,逐步形成的以中原地区华夏族为核心,以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为四方的民族格局。
“四海”所代表的“四方之夷”,多是对周边夷、狄、蛮、戎等少数民族的泛指。 《尔雅·释地》云:“九夷、八蛮、六戎、五狄,谓之四海”。 其中,夷、蛮、戎、狄是对四方民族的泛称或统称,实际又包括着很多不同的部族和族群。 “夷”是中国古代对东方各民族的泛称,《春秋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纣克东夷,而陨其身”[10]4473,商朝晚期与东夷之间的征伐使其国力大损。 西周时期东、南、西三个方向都有夷族;“蛮”指中原地区以南的少数民族部落,但实际上“蛮”并不限于南方地区,《诗 经· 宫》 中 的“至 于 海 邦, 淮 夷 蛮貊”[2]1332,指的便是东方部族,《史记·匈奴列传》也明确记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11]3483;“戎”泛指中国古代西方的少数民族,但在东、南、北方也有戎族,《春秋左传》中有“北戎侵郑”“北戎伐齐”,也有“楚大饥,戎伐其西南”的记载,可见戎族的方位并不固定。 “狄”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但并不限于北方,如《春秋左传》记载白狄与秦同州,居于西方,随后势力范围扩大到北方。 又有“以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缘斯”,指的是东方的长狄。 清代崔述考证“蛮夷乃四方之总称,而戎狄则蛮夷种类部落之号,非以四者分四方也”[16]319。 童书业也认为,四夷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经出现,并没有固定的方位,各部族之间的区分也不明显[15]155。
最早可追溯至尧、舜、禹时期,就有中原地区与四方部族关系的记载。 《墨子·节葬》曰:“尧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东教乎九夷。”[17]181提到尧去北方教化八狄,舜到西方教化七戎,大禹去东方教化九夷。 《孟子·梁惠王上》中又有“莅中国而抚四夷”[8]5809,指出统治中原地区也要安抚四方的少数民族。 战国时期开始将夷、戎、蛮、狄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搭配起来,汉人则沿袭了这种看法。 《毛诗序》有“《蓼萧》泽及四海”,汉代郑玄解释为“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2]898。 《礼记·王制》更是记载了关于中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方之民及其习性、语言、衣服、器用等内容。 “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 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北 方 曰 狄, 衣 羽 毛 穴 居, 有 不 粒 食 者矣。”[5]2896无论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只是对一方民族的统称。 历史文献所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即“四夷”,反映的是当时人们对四方民族区域地理的一种动态认知。
(三)“四海”之“天下”世界观
“四海”还常常被用来指代君王所统治的疆域 范 围, 即“四 海 之 内, 舟 车 所 至, 莫 不 宾服”[18]125。 因《尚书·禹贡》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和“五服”,人们认为在此行政区划之外的边缘地区就是“四海”。 关于“四海”在地理版图中的实际范围,不同文献中的记载也不尽相同。《礼记·王制》又有“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5]2917。 《吕氏春秋·有始览》提到“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19]281。《河图括地象》中有“夏禹所治四海内地,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20]352。 这些文献记载的“四海之内”的面积和边界虽不尽相同,但都明确了“四海之内”的地理版图是上古君王的统治疆域范围,就是“天下”。
葛剑雄指出,天下的四周即是“四海”,“随着统一范围的扩大和地理知识的增加,天下的概念也延伸到所有已知的土地”[21]113。 秦朝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仅实现了对中原地区诸侯国的统一,而且平定四方少数民族,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四海一家”。 贾谊《过秦论》中有“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22]217,即是对秦始皇统一六国政绩的赞扬。 其后,历代多以“四海”作为君王统治的天下之意。 汉代有“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之语[23]1240,唐代有“讫于有隋,四海一统”之言[24]1091,宋代有“陛下神武,四海共知”[25]2834,明朝有“继正统而有天下,四海九州罔不臣服”[26]402,清代有“一统车书四海宁”[27]2852,等等。 可见“四海”已经成为历代君王政治文化上大一统理念的代表,体现了人们对“四海”天下观的历史文化认同。
作为广义的地理概念,“四海之内”既包含东、南、西、北四方海域,又指东、南、西、北四方少数民族,更是上古帝王统治天下疆域的代表。 尽管“四海”所指不一,但都是对中国早期地理疆域的认知,与“九州”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中国”疆域,体现了古人早期的地理观、民族观与天下观。
二、“四海一统”: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
中华民族“四海”大一统的观念,孕育于夏、商、周的国家建构。 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与“四海”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频繁,西周礼乐制度构建的稳定社会秩序,促进了中原“雅乐”与四海“夷乐”的文化交融,形成了礼乐文化的“大一统”。 《公羊传》正式提出“大一统”观念,秦汉以后,随着民族融合的不断加深,中国成为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一)周代礼乐制度与“四海”一统文化的生成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源远流长,起源于上古夏、商时期,至周代礼乐制度逐渐成熟与完备。“雅乐”作为礼乐的重要形态,出自宫廷庙堂,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祖先及朝贺、宴享等典礼所用的正乐,浸润着国家意志、社会秩序。 “夷乐”又被称为“四夷之乐”,是四方部族的乐舞,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 礼乐制度下雅乐对夷乐的规范和影响,夷乐对雅乐的丰富,充分体现了礼乐教化上的“四海”一统。
1.雅乐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作为礼乐范本彰显国家一统的精神,也是天下与四方的礼乐范本
《毛诗序》有“雅者,正也。 言王政之所由废兴”[2]568。 西周时期,以王都地区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周初雅乐以六代乐舞为主体,主要用于周王室的各种大型祭祀典礼。 其中用《云门》祭祀天神、《大咸》祭祀地神、《大韶》祭祀四方、《大夏》祭祀山川、《大濩》祭祀周的始祖姜嫄、《大武》祭祀周的祖先。 六代乐舞经历夏、商,流传至周代,周公用以“制礼作乐”,成为礼乐制度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稳固周王朝“四海”一统的重要文化措施。 《礼记·明堂位》载:“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5]3226。 其采用的就是周代乐舞《象武》《大武》与夏代乐舞《夏籥》。 《诗经》作为周代典礼活动中雅乐的文本,收录了来自王畿与十五诸侯国的音乐。 《诗经》中多次提到了持掌国政,必须维系四方部族的重要性,以及臣子们为国事在四方奔波经营。 《诗经·小雅》有“秉国之均,四方是维”(《节南山》),“旅力方刚,经营四方”(《谷风之什》),“何人不将,经营四方”(《何草不黄》);《诗经·大雅》有“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大明》)、“勉勉我王,纲纪四方”(《棫朴》)、“受天之祜,四方来贺”(《下武》),天赐洪福于勤勉理政的君王,四方诸侯都来祝贺。 随着周代政权的进一步巩固与礼乐制度的不断完善,雅乐的影响也逐渐由中原地区向“四海”部族传播、推广,为周王室的“四海”一统服务。
2.雅乐对于“夷乐”的吸收与改造,推进了“四海”一统观念的形成
早在夏、商时期,中原地区与四方民族“夷乐”之间的交流就较为频繁。 《竹书纪年》载“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 再保庸会于上池, 诸夷入舞”[28]13。 分别记载了夏朝少康与姒发即位时,来自四方的民族部落都来祝贺与献乐舞。 商朝时期,据甲骨文记载:“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29]243。 其即是指教授来自地方的贵族子弟习武与习乐,习武是为了征战,习乐是为了祭祀。 据《周礼》记载,周王室的乐舞机构中, 设置了专门教“夷乐”的官吏,有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属焉”[6]1730。 又有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吹而歌之,燕亦如之”[6]1372。 郑注:“四夷之乐, 东方曰《韎》,南方曰《任》, 西方曰《株离》, 北方曰《禁》。《诗》云‘以《雅》以《南》’是也。 王者必作四夷之乐, 一天下也。 言‘与其声歌’, 则云乐者主於舞。”[6]1731一般认为,“四夷之乐”均为具有该部族民俗特征的原创乐舞,本来不纳入礼乐的范畴。但周王室的乐舞机构中有乐官专门教授国子“夷乐”,说明“夷乐”虽保留本民族的习俗风尚, 但已经部分得到周王朝礼乐加工改造,改造后的部分夷乐纳入礼乐的一部分,用以教授国子,以养成国子对天下一家的认识,树立弘扬礼乐文明的志向。 《白虎通德论》有言“乐所以作四夷之乐何?德广及之也”。 其中引用《乐元语》曰:“受命而六乐。 乐先王之乐,明有法也;与其所自作,明有制;兴四夷之乐,明德广及之也。”[30]18其明确提到四夷之乐的用途,即是为了“明德广”,使得君王的德行遍及天下四方,为“四海”大一统做铺垫。 通过“雅乐”的礼乐教化与对“夷乐”的吸收改造,对四方各部族民族进行了统一的文化熏陶,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四海”大一统观念形成的基础。
(二)历代民族融合与“四海”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确立巩固
中华民族“四海”大一统观念的形成,与历代各民族之间的不断融合也有密切关系。 有文献记载以来,中华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交流就很频繁,少数民族的内迁更是促进了与中原地区汉族的大融合。 《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杞,夏余也,而即东夷”[10]4355,说明杞为夏后姒姓之国,与戎夷杂居。 春秋时期,被认为是“夷狄”的楚、吴、越、秦等国,也在“尊王”“争霸”的过程中逐渐与华夏相通相融。 梁启超曾指出:“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 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31]8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形成了七个比较强大的诸侯国,周天子已经完全失去“一统”的号召力,而原有被认为是“夷狄”的诸侯国,已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西周时期形成的“天下”“四海”“四方”等观念,也逐渐演变为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观念的认识基础,各诸侯国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并因此争霸天下。
虽然经历了不同朝代之间的政权更迭,“四海”大一统的观念一直是历代君主所推崇的。 秦汉大一统王朝建立本身,就是彰显了这一观念。《史记·秦本纪》载“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11]307。 汉代沿袭秦代郡县制,实行郡县制国家治理,郡国并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自分立的政权为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都以“正统”自居。 “统一天下”与“四海宾服”成为各民族政权统治者所标举的内容。 《廿二史劄记》提到“《晋》载记诸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有文学。 刘渊少好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史》《汉》诸子无不综览”[32]173。 可以看出,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受到“大一统”文化精神的影响,主动接纳与吸收儒家思想。 尤其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及实施的一系列汉化政策,促进了鲜卑族以及其他北方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四海”大一统观念,而且为隋唐时期的大一统与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政治上的大统一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和平稳定的环境。 《旧唐书·吐蕃传》载:“唐有天下……彰王者之丕业,被四海之声教。与吐蕃赞普,代为婚姻,固结邻好。”唐朝实施“抚九族以仁”的民族政策,通过设立边疆行政机构、册封各族首领、和亲与会盟等措施,维护了国家团结和边境的基本稳定,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 五代十国和辽宋夏金时期,虽然各民族政权之间冲突不断,但都是处于中国疆域内的多民族政权,客观上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文化交流也更为频繁。 如宋朝实行“以文治国”的方略,对各民族一视同仁。 辽朝和金朝都曾设立汉人科举,选拔汉族官员,提高汉族官员的地位,以加强对汉族的统治。 金朝还积极吸收汉族文化,提倡汉文,并在科举中设立汉学科目。各少数民族政权同时也以“四海”一统作为本民族政权的象征。 如《辽史·萧孝忠传》记载“天子以四海为家”,《金史·熙宗本纪》载“四海之内,皆朕臣子”。历代政权更迭、战争流徙,也从一个侧面推进了中华民族之间的融合。 而无论政局如何变迁,历朝历代均对“四海”所代表的大一统观念高度认同,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四海”大一统的格局。
三、“四海一家”:中华民族“大一统”精神的文化符号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观念中,“四海”不仅是一种地理概念,更是一种天下意识的表达,以及君王权力话语与正统地位的体现。 “四海之内”不仅指君王所统治的天下疆域,“四海一家”更成为大一统的政治文化理想代表。 纵观历代典籍,先秦元典以“四海”构建起天下观,历代的史学传统中也以“四海”作为君王权威与统治的象征。 后世文人也常在文学作品中以“四海”抒情言志,寄寓对天下统一、社会安定的向往。 可以说,“四海”是中国文化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大一统”观念的重要文化符号。
(一)先秦元典的“四海”文化认同符号
“四海”在先秦元典中的记载,以《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略》与《诸子略》提到的典籍为主,主要表现为君王统治的四方疆域,以及对君王的德行与治理天下等功绩的赞扬,同时也寄托了古人对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的期望。 因此,“四海”作为先秦元典的代表性文化符号,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首先,以“四海”言说君王统治的四方疆域,以此指代君王治理的天下。 如尧逝世时,《舜典》称:“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1]272天下百姓悲痛不已,三年之中四方之内都断绝了乐音。 又如商代武丁时期国家的疆域已至上千里,《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2]1344商王朝开拓的疆土已达天下四方,百姓安居乐业,四海邦国之民都来归附。《孟子·尽心上》亦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8]6019,以“四海”指代“天下”之意,即站在天下的中心,安定四海的人民。 同时,“四海”也是臣子负责管辖的领域。 《尚书·周官》提到“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1]500。 冢宰代理天子之权,统领百官,包括四方部族的首领。 《春秋穀梁传·僖公九年》亦有“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即天子的宰官,通达天下。
其次,以“奄有四海”赞扬君王的德行与政绩。《大禹谟》记载帝尧是“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大禹为“敷于四海,祗承于帝”[1]282,尧和禹都是得到了上天的眷顾,才能得以统御四海,成为天下的君主。 《论语·尧曰》又有“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如果君王治理不当,使天下百姓陷于贫困,上天赐予的禄位就会永远终止。 韩非子更是认为君主就是圣人,《韩非子·扬权》载:“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虚而待之,彼自以之。 四海既藏,道阴见阳。”[33]44事情要由四方的臣去做,国家的最高权力要在君主手里,君主已胸怀中包藏四海,就可从静中观察臣子的动态。 《禹贡》提到“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1]323,即天子的德教传播到四海之内。
再次,以“四海”安定象征天下一统与社会秩序的稳定。 《孟子·离娄上》有言“天子不仁,不保四海”[8]5912。 孟子认为君王可以通过“仁政”保障“四海”的安定。 《荀子·儒效》也提到“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14]121,在儒家的仁政德治之下,国家一统,社会和谐,实现真正的“四海”大一统局面。 韩非子则认为只有用法令严明赏罚,才能“独制四海之内,聪智不得用其诈,险躁不得关其佞,奸邪无所依”[33]36。 臣子即使在千里之外,也不敢隐瞒事实,权位处在郎中也不敢隐瞒是非。 《韩非子·奸劫弑臣》亦有“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33]101。 天下诸事皆在君主的耳目之内,即使身处深宫也能管理天下,使得四海一统和社会安定。
最后,以“四海之外”寓意逍遥自在的人生境界。 以《庄子》为例,《逍遥游》与《齐物论》中提到“神人”和“至人”的逍遥境界都是“乘云气”和“游乎四海之外”[34]31,即游历于四海之外更广阔的世界,表达了对自由、无拘无束生活的向往。《在宥》 篇载“其疾俛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34]381,庄子认为人心的活动十分迅捷,片刻之间就能遍及四海之外。 《荀子·尧问》有“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14]646,意为内心忠诚守信,就会表现在外,遍布于四海之内,天下人自会归顺。 总之,无论“四海”是作为君王统治的天下,还是社会稳定与逍遥的人生境界,都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二)史学传统“四海”的文化正统符号
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四海一家”理念在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中国史学传统中一脉相承,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秦汉以前,“四海”是古人对世界边际的想象与认知,或是四方海域,或是四方邦国民族,但都表现了中原地区位居中央的天下观。 周代记载的五史中,有小史掌管王畿内的各诸侯国史,内史负责宣读“四方之事书”,外史掌管四方诸侯国的史记,“掌达书名于四方”(《周礼·春官·大宗伯》)。 可见,中国史学之渊远流长,早在西周就已经开始对四方诸侯国展开管理。 直到秦汉统一全国以后,二十四史中对中国与周边的“四海”地理疆域有了较为明确的记载。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有意识地记载了中国与周边邦国的历史,从此形成了“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世界观念,这个传统延续了两千多年[35]5。 其后《汉书》《后汉书》等历代史书,依然有着不少对于“四海”与周边世界的诠释,体现了当时人对天下的认知。“四海”在二十四史中常作为“天下”之义,寄托人们对“四海一家”的期望。 《史记·夏本纪》与《汉书·地理志》收录了《尚书·禹贡》全文,继承了“四海会同”与“声教讫于四海”思想的同时,也进一步地阐发了“四海”的内涵。
首先,“四海”多次出现在二十四史的帝王本纪部分,成为君王统治天下的“大一统”象征。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了帝舜任用禹、皋陶、契等人以平“四海”的事迹:“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11]50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11]52。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常以“四海”来赞扬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事迹,如“秦并四海”“以养四海”“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囊括四海之意”“威振四海”等,用以肯定了秦统一天下的政绩。 《汉书·高帝纪》也有“四海之内莫不仰德”“大王德施四海”“天子以四海为家”等,皆是以“四海”称赞汉高帝刘邦的建国功绩。 《宋书·武帝本纪》有“四海来王”,《南齐书·高帝本纪》有“永清四海”,《隋书·高祖纪》有“四海归向”,《旧唐书·太宗本纪》有“四海安静”,等等,都将“四海”与帝王的大一统政权与权威结合一起。
其次,以“四海”为周边邦国,展示四方民族对大一统王朝的归附与融合。 《史记·三王世家》有“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贡祭”,《史记·儒林列传》有“圣帝在上,德流天下,诸侯宾服,威振四夷,连四海之外以为席,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等,《史记·大宛列传》有“威德遍于四海”,皆是以“四海”表达君王平定天下、四夷归附之意。 又如《明史·外国列传》中追溯了尧舜时期,“四海来宾”的历史,又表达了君主“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的志向。
最后,将“四海”延伸为国家祭祀的“四海神”,作为君王维持天下一统秩序的构想。 天子祭祀四海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周礼》有“凡将事于四海山川”,提到君王巡守途中将会祭祀四方山川。 《史记·封禅书》中详细介绍了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活动,其中雍州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 诸布、诸严、诸逑之属”[11]1654,总共有一百多座神庙,《汉书·郊祀志》采纳了《史记》的说法。 可见,到西汉时期,祭祀四海神已经是国家祭祀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国家祭祀中四海神属于众多山川神明之一,如《晋书·礼志》“地郊则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之佐……凡四十四神也。”《隋书·礼仪志》“五官之神、先农、五岳、沂山、岳山、白石山、霍山、无闾山、蒋山、四海……皆从祀。”《旧唐书·礼仪志》“神州及五岳、四镇、四渎、四海……并皆从祀”。 《明史·礼志》“星辰二坛;次东,太岁、五岳、四海”等,都是从四海天下观出发的,是国家“大一统”政治格局的象征。 鲁西奇指出:“政治的统一乃是文化统一的前提与基础,而统一的 制 度 则‘造 就’ 或‘形 塑’ 了 统 一 的 文化。”[36]647由此可见,以“四海”为代表的国家海神祭祀活动,在经过历代君主的实践与规范化后,已经逐渐成为文化“大一统”的一部分。
(三)文学、艺术中的“四海”文化符号
“四海”作为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文化符号,经过历史层累模式的建构与强化,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与艺术中已经成为了一种习见的经典意象,寄托了古人对于“四海一家”大一统国家的向往、对天下太平与社会稳定的赞颂。
1.以“四海”来抒情言志,表达对国家大一统的礼赞
《楚辞》有“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云中君》)感叹云中君的光芒遍及九州,踪迹纵横四海。 “名声若日,照四海只。”(《大招》)称颂楚国的政治清明与国势强盛,名声就像辉煌的太阳,照耀四海光焰腾腾。 三国魏曹植有“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赠白马王彪·并序》),东晋陶渊明有“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皆是以“四海”表明诗人的进取之心。 唐代杜甫更是以“四海”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如“阑风长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秋雨叹三首》),诗人以“四海八荒”描述当时雨势,表现灾情的严重与民众的困苦。 其他诗作诸如“四海犹多难,中原忆旧臣”(《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释闷》),“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逃难》),等等,皆是表现了全国四方各地的战争与民不聊生。 在不同的诗人笔下,“四海”也被赋予不同的内涵。 宋代诗人苏轼有“行尽九州四海,笑纷纷、落花飞絮”。 陈师道有“千年昌运此时逢,四海欢声今日沸”。 明代诗人高启有“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等等。 可见,“四海”意象之丰富,寄托了诗人关于天下的情感与情怀。
2.以“四海”作为对君王一统天下、德行天下的赞扬
西汉桓宽《盐铁论》提到“言满天下,德覆四海”(《能言》)、“诚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世务》)。 这里的“四海”等同于“天下”之义,以此来阐释君王的德行与统治覆盖到四海之地。 明代文人李贽在文论中也多次提到“四海”,他认为“岂真有东西南北之海”,“所云四海,即四方也”(《焚书·四海》)。 《富国民臣总论》中也有“所以为国家大业,制四海安边足用之本”。 李贽认为“四海”并没有明确的实指,采纳的仍是经史体系中其所代表的“天下”之意。 《三国演义》中对吕布的刻画,李肃称赞吕布“贤弟有擎天驾海之才,四海孰不钦敬” (第三回),又有“温侯吕布世无比,雄才四海夸英伟”(第五回)。 以“四海”形容吕布的勇武。 《水浒传》中更是多次出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第一回)、“四海之内,名不虚传”(第十七回),等等,以“四海”形容天下一家、人人都为兄弟、应当互爱互助的思想。 元代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中有“平生正直无偏向,止留下四海一空囊”,“四海无家,一身客寄”,“凤飞翩翩兮,四海求凰”等,描述了张生对崔莺莺的痴情。《长生殿》中更是有“四海之富,要他则甚”,塑造了李隆基深情的人物形象。 到了清代有《四海升平》《四海安澜》《四海清宁》等戏剧,皆以“四海”为题作清宫皇帝圣诞的承应剧目。 可见,“四海”作为文化符号,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人们生活中留下的深刻印记。
3.舆地图及多种艺术形式中的“四海”文化符号,推进了天下一统思想的普及
最早有所记载的是《汉书》中西汉江都王刘建曾“具天下之舆地及军陈图”,还有光武帝刘秀“披舆地图”,以及西晋裴秀的《天下大图》,使“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 唐代贾耽绘制的《海内华夷图》按照晋代裴秀六体方法编绘,其表文载“海以委输环外,百蛮绣错”(《旧唐书·贾耽传》)。中原地区有五服九州,四海戎狄环绕,普天之下都是君王的土地。 另撰有《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以补充说明,提到《海内华夷图》是“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旧唐书·贾耽传》),继承了先秦与汉代的“四海”理念,重现中国与周边地区疆域范围的同时,也表现了贾耽的大一统思想以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视。 现存于世的宋代石刻“天下图”有西安碑林的《华夷图》,是以《海内华夷图》为底本,注明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画出了全国的山脉、河流及各州的地理位置,表现了宋人的天下大一统观念。 中国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集《历代地理指掌图》的目的更为明确,就是为了颂扬“王者大一统,四海皆徕臣”[37]162。 明代绘制的《四海华夷总图》标注了“此释典所载,四大海中南赡部洲之图,姑存之以备考”。 该图绘制了围绕着中央大陆的四大海,大海之中散布着标明了名称的国家。 龚缨晏将16 世纪末以前绘制的“天下图”布局特点,总结为“东、南皆海,北缘旷野;四夷环绕,中国独大”[37]144。 直到清代阎咏绘制《大清一统天下全图》、黄千人绘制《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汪日昂绘制《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等,不仅反映了清人对于国家疆域“四海”的认识,更是反映了清朝对于国家大一统的重视,通过绘制天下图的方式宣传国家统一的意识。
除此之外,还有以“四海”为主题的瓷器与屏风等艺术品。 以“四海”为代表的天下一统象征,在清代特别受到了帝王的喜爱,如见于《清史稿·乐志》的“金瓯一统万年清”,乾隆时期养心殿造办处记载:“十一日接得员外郎安泰、金辉押帖一件,内开三月二十六日太监胡世杰交洋漆自行车一件,内装一统万年清陈设一件。 传旨:着如意馆另配做象牙万年清叶,珊瑚子,琥珀苓芝一统万年清陈设一件,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 钦此。 于四月初二日画得一统万年清纸样一张,交太监胡世杰呈览。”[38]176在青瓷器方面,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青花四海来朝纹瓶”,外壁青花绘有波涛、鱼、龟等图纹,象征“四海来朝”的吉祥寓意。 现代国礼景泰蓝赏瓶也被称为“四海升平”,周围以浮雕吉祥水纹环绕,象征“四海”,寓意太平,“瓶”即“平”,整体即四海升平,被用来作为国家的赠礼。还有“四大国宝”之一的翡翠插屏《四海腾欢》,同样表现了“龙腾盛世、四海腾欢”的主题。 可见,作为中华民族“四海一家”的大一统文化符号,在艺术领域的经久不衰。
结 论
在中华民族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四海”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与演化,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下观,体现了历代中国人对“大一统”思想的认同。 作为中国上古疆域概念的“四海”早期内涵丰富,包含“四方”疆域观、“四夷”民族观和“天下”世界观,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大一统”精神逐步形成。 后经中原“雅乐”与四海“夷乐”的文化交融,周代礼乐文化制度实现了“四海”大一统的秩序构建与文化认同,在历代民族的大融合中,逐渐确立了“四海”大一统的历史地位,形成了“四海”一统的文化符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39]“四海”作为中国古代天下观的代表,凝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展现了中华文明“大一统”观念的悠久历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