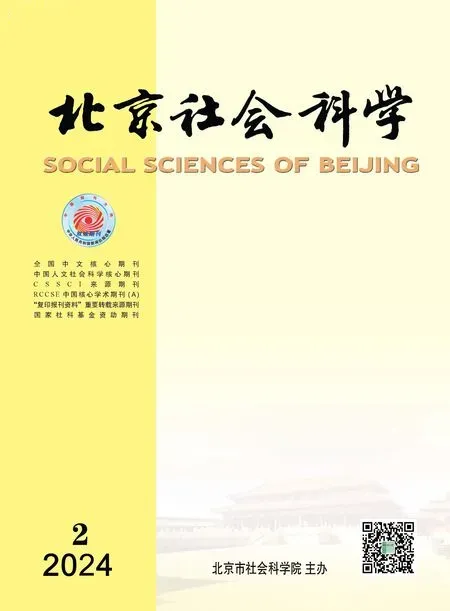单位犯罪教义学的两个问题
时延安
一、引言
目前,刑法教义学体系中并没有单位犯罪的独立位置。在不承认法人犯罪的国家,如德国,其刑法理论体系并无法人犯罪的地位。而我国虽然规定有单位犯罪,在刑法理论体系中并没有强调单位犯罪的特殊性,只是与自然人主体一样在犯罪主体①或者行为主体②中加以讨论。这主要是因为,研究者多数仍然是从自然人的角度理解单位犯罪的行为和罪责问题,认为单位的犯罪行为不可能脱离自然人的行为,单位决策者即自然人的意志就可以理解为单位的意志,相应地,也就为单位确立了罪责的基础。这样简单化的理论体系“处理”,实际上抹杀了单位犯罪及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特殊性,也忽视了规定单位犯罪的刑事政策意义。同时,刑事司法实践中处理的单位刑事案件主要涉及民营企业,而这类企业的经营管理多由企业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做主”,这也就使得对单位的刑事责任追究与对自然人的刑事责任追究结合起来考量。相应地,现行刑事诉讼法也将单位刑事案件的处理与单位中自然人刑事案件的处理“捆绑”起来,在程序设计上对前者的处理从属于后者。
这就产生了一个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在刑法理论体系中应否将单位犯罪作为一个相对于自然人犯罪独立的范畴进行分析和研究?进言之,应否构建相对独立的单位犯罪教义学?显然,无论从刑法学理论体系自我完善的角度,还是从适用刑事实践的角度,乃至从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角度,都有必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并给予确切的回答。
二、对法人进行刑事制裁的正当性
一般情况下,当某一主体应受到刑事制裁时,会被认为其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危害行为,且应当受到谴责。那么,对于法人而言,如果认为其应当受到刑事制裁,也就需要考虑三点:一是法人是否具有人格,即是否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开展活动且自己承担行为后果的资格?二是法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三是法人是否具有独立承担刑事谴责的可能性?只有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才可以认为对法人进行刑事制裁具有正当性。本文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从民法角度思考法人的人格
我国民法理论通说认为,法人和自然人同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即基本上采取“实在说”的立场[1],而在商法学中讨论的大多数法律问题都是围绕着法人展开的。由是可见,在民商法理论中,法人有其特有的人格及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并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相应的民商事活动,且根据法律规定以其财产等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民商法中确定法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并不能当然地推导出法人的刑事责任根据。不过,民商法对法人人格的确立,对法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成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为对法人进行评价和谴责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使其独立承担刑事责任提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当学说上一般认为法人的人格独立于自然人时,也就为法人独立承担刑事责任提供了一个“前置法”上的前提。在民法上承认法人的独立人格,在刑法上自然要接受这个结论,因为刑法并没有确认某一主体人格的功能。因此,在民法上承认法人具有人格,在刑法上也就不能否认法人不具有人格。
(二)从民事行为能力推论法人的刑事责任能力
民商法学中并没有“民事责任能力”这一术语,这可能是因为,对民事责任概念的界定强调的它是一种不利后果,而民事行为能力本身则涵盖了民事主体承担不利后果的能力。比较而言,刑法中所说的刑事责任能力,实际上也是一种行为能力或者犯罪能力。我国刑法通说认为,刑事责任能力,是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的,是行为人具备的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从这一定义中可能看出,刑事责任能力的本质就是一种行为能力或者说是一种犯罪能力。不过,刑法通说中所说的刑事责任能力带有明显的“自然人视角”。如果借用民事行为能力的视角来分析,对行为能力的性质界定,重点在于强调行为主体的自我决定及其法律意义。那么,对刑事责任能力概念的内涵界定,也应当强调行为主体自我决定其行为的能力及在刑法上的意义。从这一内涵界定展开,法人并不具有等同于自然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但却具有自我决定如何行为的能力,而这种自我决定以及由此做出的行为,会在刑法上产生评价乃至给予谴责的意义,因而也就可以认为法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三)对法人实施严重危害行为的谴责问题
刑事制裁本身是一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其内容表现为对犯罪人基本权利的限制和剥夺,而刑事制裁的前提则是对犯罪人人格的否定性评价及谴责。这一前提,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就是刑事责任的范畴。对于刑事责任的实质,高铭暄教授指出,它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司法机关对基于个人自由意志实施违反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的人所做的一种否定性评价。[2]以这一界定为学理根据,对犯罪人的刑事制裁一方面是其实施了一定的危害行为,另一方面则是其应受到否定性评价。由此展开,对犯罪人人格的否定性评价及谴责,是对犯罪人进行刑事制裁的根据。那么,否定性评价及谴责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同样,从上述界定出发,其内容应当是犯罪人人格中表现出反社会的人格倾向,即对现行统治秩序的反对态度。刑事责任范畴的核心功能就是判断犯罪人是否具有这种倾向及程度。如此,也可以大致厘清,行政制裁与刑事制裁的差异所在,即前者并不强调对违法行为人反社会人格倾向的判断。
在承认单位具有人格的前提下,犯罪单位承担刑事责任,也应对其人格进行否定性评价。不过,对于犯罪单位人格的反社会倾向如何理解,却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国刑事责任理论的哲学基础认为,行为人具有相对的意志自由,只有当行为人有选择合法行为的可能却选择违法行为时,才有对其谴责的合理性,而只有当行为人选择犯罪行为时,才有对其人格中的反社会倾向进行否定的合理性。单位作为组织体,并没有等同于自然人的意志自由;单位如何选择行为,是其决策机构中自然人的合意或者代表人的意志所决定的。对于单位而言,决策机构中自然人的意志决定从效果上也就是单位的意思表示,从而看起来好像对单位犯罪的谴责与自然人的谴责不可分离。不过,当我们将单位看成一个独立的存在时,单位意思表示的形成机制更为重要,即多数自然人的合意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什么在单位做出违法乃至犯罪的决定时,该单位内部没有有效的机制进行纠正并促进其合法经营。由是以观,单位人格的反社会倾向在于其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着重大问题,以至于单位不能做出合法的意思表示、实施合法的行为。
总之,单位人格的特殊性实质上决定了对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不是其具有相对的意志自由,而是其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着弊端,因而对犯罪单位的谴责不是聚焦在其内部的自然人,而是聚焦在其内部的治理结构。
三、组织体责任论的内涵应从“单位是规则组织体”来认识
川崎教授提到了三种学说,即企业组织体责任论、单位行为责任说(即等同路径)和组织模式说。企业组织体责任说,是将单位等企业组织的自然人行为视为企业组织体的活动;单位行为责任说,是将单位代表的意思和行为视为单位的意思和行为。这两种理论,实际上都是将特定自然人的行为视为或者等同于单位的行为,进而为单位追究刑事责任提供立论基础。川崎教授将这两种学说称之为个人模式,这与英美刑法有关替代责任(vicarious liability)和同一视原则(identification principle)具有相通之处。组织模式说,则尝试将单位中自然人的刑事责任与单位的刑事责任区分开来,以单位的法律义务为着眼点,认为这类义务的负担才是单位所具有的,当单位违反义务而形成法益侵害时,就为追究其刑事责任奠定了基础,由此也将合规计划及其实施纳入承担刑事责任的考量。在主张组织模式说的同时,他也不否定个人模式,即采取并用的观点。采取并用的观点,确实是一个比较折中但又务实的路径:采取个人模式,可以较好地解决中小规模企业的刑事责任根据问题;采取组织模式,则可以较好地解决大规模企业的刑事责任根据问题。不过,从现实及发展的眼光看,单位犯罪采取组织模式说更为妥当,在我国刑法学语境中对应着组织体责任论。
(一)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及司法实践实质上对组织体责任论的贯彻
我国规定单位犯罪最早可追溯到1987年的《海关法》。将单位规定为犯罪主体,是有很强的集体主义色彩的,因为当自然人为了单位利益且基于单位集体决策的情况下实施犯罪时,让自然人为集体承担刑事责任是不公平的,而单位作为一个集体有其特殊的“人格”,因而可以也应当规定为犯罪的主体。也因为如此,在一些犯罪(如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单位行贿罪)中,对单位中自然人(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定刑要低于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在定罪量刑标准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司法解释对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也确定了不同的数额、数量标准。
在学理上,源自英美的替代责任理论和同一视作为学说被引进,但一般认为,这两种理论无法解释我国刑法有关单位犯罪的规定;如果考虑到单位犯罪立法背景所具有的集体主义考量,那么,我国单位犯罪的立论基础应更接近于组织体模式。对单位犯罪成立要件的判断,强调三个特征:单位名义;单位意志;单位利益。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大量的犯罪单位是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而这类企业通常都是负责人决策(即便其采取公司化的方式),因此,对单位犯罪成立的判断就转变为“单位名义+单位利益”,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一些法院甚至只考虑将“单位是否从犯罪中获益”作为最重要的判断根据。司法实务中之所以有意无意地忽视“单位意志”的判断,笔者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难以区分是单位中自然人的意志还是单位的意志,所谓单位的意志往往是模糊和不确定的。
在合规话题引入中国刑法学视野之前的十年多时间里,对单位犯罪的研究乏善可陈,而恰恰是在合规理论引入之后,中国刑法学界开始重新思考单位犯罪的责任根据问题。例如,黎宏教授系统而深入地论证组织体责任论。[3]与黎老师观点相似,刘艳红教授提出合规责任论[4],王志远教授提出,要超越行为责任,提升单位犯罪采取归咎的刑事责任说[5],两位教授提出观点的基础仍是组织体责任论。学说上确立组织体责任论的地位,相应地也就会在单位犯罪解释论上形成一系列应然的结论,甚至也为刑事诉讼法中设立相对独立的单位刑事案件处理程序提供了实体法上的理论根据。[6]从以上关于法人人格、刑事责任能力和刑事可谴责性的分析,就会得出单位刑事责任应采取组织体责任论,也就是说,无论将民法理论作为论述的前提,还是从对单位进行刑事谴责的必要性及根据来看,都会将单位区别于自然人来看待,并脱离自然人的意志自由来讨论单位的刑事责任根据问题。
对单位类型的理解和观察,对研究者在单位犯罪刑事责任问题上采取何种立场产生了一定影响。以企业为例,我们观察不同规模的企业会有不同的认识,如果将眼光放在中小规模企业,尤其是靠家族创业、经营的企业,会很容易将企业与自然人结合起来,在理论上也会倾向于选择从自然人的角度观察、理解企业的刑事责任问题;反之,如果将眼光聚焦在已经实现现代企业治理要求的企业时,则很容易将企业理解为一个脱离于自然人的独立主体来看待,在理解其刑事责任时会更多地从一个独立的组织体来看待。对待企业犯罪,采取一种向前看的思路更好,就是从现代企业制度来理解企业活动和其承担法律责任的根据。
(二)组织体责任论的“内核”应采取规则组织体的观念
黎宏教授认为:“单位是由人和物复杂结合而成的法律实体,具有自己独特的制度特征、文化气质和环境氛围,这些要素能够对单位中的自然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根据应采纳组织体责任论,根据这一认识,组织体责任论的“内核”包括三个方面,即制度、文化和环境。据此推论,这三方面的共同作用会影响单位中自然人的行为,而“单位的制度、氛围或者说气质,若容许或默认犯罪的发生,或者在防止犯罪方面措施不力,便可将其作为引致该单位成员犯罪的条件或者原因,此种场合下的单位成员个人犯罪可以被视为单位自身的犯罪”[3]。这一带有拟人化的观点,对于理解单位犯罪中自然人行为如何能视为单位行为具有积极意义。不过,诸如文化、气质、环境等在实践中难以判断,例如,如何基于企业文化来判断是企业文化促成了单位中自然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在我看来,包括企业在内的单位可能是一个带有特殊文化或者气质的组织体,但更是按照各种规则构建起来的一个规则组织体。既然如此,我们在理解单位的刑事责任时就要考虑其作为规则组织体的意义。
单位作为一个组织体,实质上是一个依靠规则构建的组织体。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单位的人格是从依法设立时开始的,从《民法典》第58条有关法人的规定即可略见一斑。进言之,单位的成立条件、程序均由法律、行政法规确定,其成立需要得到有权机关的批准。二是,单位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均源自法律,其享有的权利类型和义务类型明显区别于自然人。三是,单位内部人员之间及单位机构的职权等依照法律和其章程确立,其内部是依靠规则运行的;单位对内、对外的意思表示,都是根据这套规则而产生的。实践中常说的“家族企业”,其内部也是依靠规则,只不过这种规则并非法律所认可的规则。认识到单位是一个规则组织体,认识到其是依靠一套规则运转的,那么,在认识其人格、意思表示及行为时就会认识到规则对于单位内部管理、外部行为的意义。当我们对一个实施犯罪的单位进行谴责时,不是因为它是个“坏”单位、没有“良知”的单位,而是支持它内部运转、运营的规则以及由此建立机制是易生成违法行为的、是具有明显的危险性的。所以,对单位刑事责任的理解,不能类比自然人、从人的意志自由来进行分析,而是应当考虑其作为一个由人组成的组织体、一个规则的组织体,从其内部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的违法倾向以及社会危险性来进行理解。
(三)从合规的视角理解单位犯罪
川崎教授在演讲结束部分提到,“不将合规体制的建立视为法人固有的注意义务,而仅将其视为刑事政策视角下作为激励措施的免责事由,这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从这句话来分析,合规体制的建立对法人犯罪是否成立的影响,存在着两条可供选择的路径,即从是否履行注意义务的角度切入和将其作为法人犯罪的责任阻却事由看待。就第二条路径来讲,单位既然是一个规则组织体,当其已经建立合法合规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运营机制即已经建成合规体制的话,该单位也就不再具有应谴责性的可能,因而有效的合规体制可以作为单位的责任阻却事由。这条路径是可行的。不过,在罪责部分讨论合规问题,在单位犯罪成立的判断流程设计上可能过于滞后了,更为妥当的思路还是在构成要件的适格性阶段进行判断。
我国刑法中的单位犯罪(除合同诈骗罪)几乎都是法定犯,其行为构成犯罪的第一个要件就是,单位是否违反了行政法或者民商法所规定的强制性义务,个别情况下也包括合同义务。当单位没有违反义务或者属于行使权利,或者具有民商法上的免责事由时,就不成立犯罪。[7]既然有效合规建设本意首先就包含了守法的意思,当单位已经建立有效合规后,就认为其已经履行了法律义务,这种情形导致危害后果发生的自然人行为,就只可能构成自然人犯罪。例如,涉案企业已经建立有效的环境合规体制,其工作人员违背企业规定擅自非法处理污染物的,就只应追究该自然人的刑事责任。
四、结论
本文仅仅讨论了单位犯罪教义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其一,结合我国单位犯罪理论与司法实践,论证法人刑事制裁的正当性,肯定其在刑法上的独立人格,进而指出单位人格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不是其具有相对的意志自由,而是其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着弊端。其二,对单位刑事责任的归责采取组织体责任论,其“内核”应采取规则组织体的观念,从合规角度理解单位犯罪。对于单位犯罪的完整理论体系构建,还有很多工作要完成,本文期冀能够将以上两个问题解释清楚,为单位犯罪教义学打下最为重要的基础,循此实现单位犯罪的理论与实践完善。
注释:
① 采犯罪构成理论的教材,都是在犯罪主体中予以讨论。例如,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八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102.
② 采犯罪阶层理论的教材,则在构成要件中行为主体部分讨论。例如,张明楷著.刑法学(上)(第五版)[M].法律出版社,2016: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