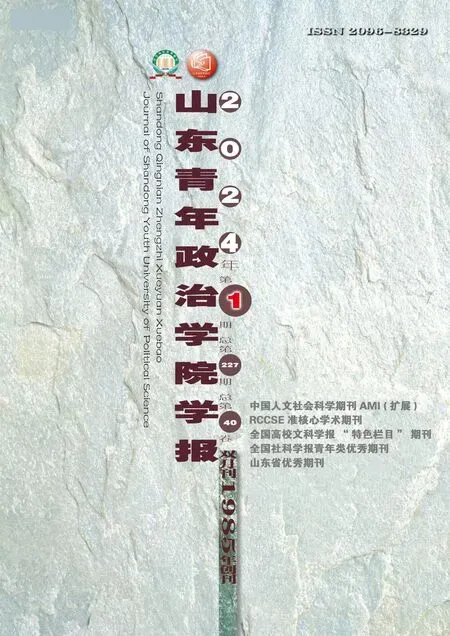以“大人之学”分判朱王之学
魏子钦
(安徽大学 哲学学院,合肥 230039)
作为“初学入德之门”与“孔氏之遗书”的《大学》,(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0,第1页。经过朱子的诠释,曾在宋明之际大放异彩。王阳明早年也曾深究朱子所注之《大学》,并借其“格物”思想而格竹,但七日未见竹理,遂致重疾。直到龙场悟道,阳明乃叹“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2)王守仁:《王阳明集》,中华书局,2016,第1031页。于是,阳明批评朱子“析心与理为二矣。”(3)同上书,第41页。不过,朱子后学也以败坏人心,祸乱朝纲为罪,批判阳明之学是阳儒阴释,荼毒人心。按照梁启超的判定,面对明朝覆灭,清初学者的“王学反动,其第一步则返于程朱。”(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第110页。正如张履祥言:“姚江著书立说,无一语不是骄吝之私所发。”(5)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中华书局,2002,第1173页。有“清朝理学儒臣第一”之称的陆陇其,亦撰《学术辨》《松阳讲义》等著作专批王学。由此,朱王之学纠缠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影响后世对朱子、阳明之学的客观理解。从朱、王注《大学》看,朱子、阳明注《大学》皆由“大学者,大人之学也”起,但二者却存在明显差异。有鉴于此,本文借朱子、阳明对“大人之学”的阐释,以“大人者”(学习主体)、“大学之教”(学习内容)、“大学之道”(学习目标)掀开遮蔽朱子、阳明注《大学》用意之纱。
一、“何为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与“天地万物一体者”
朱子、阳明在诠释《大学》之时,都曾对学习《大学》的主体作出界定。朱子认为“大人之学”的主体是指“大人”,与其相对的是“小子”,即“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6)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691页。阳明在《大学问》中指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7)王守仁:《王阳明集》,中华书局,2016,第823页。尽管阳明认为“大人之学”的主体是“大人”,但阳明对“大人”的理解与朱子对“大人”的理解存在明显不同,这是因为朱子与阳明对“大人”的诠释立场存在差异。
朱子对“大人”的诠释,是站在古代教育阶段设计的角度进行论述的,并对受教育者何时学习“大学”与何时学习“小学”作出进一步说明。
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0,第2页。
“小学”的学习主体是“小子”。“小子”是指到了八岁、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的子弟。这些“小子”进入“小学”之后,开始学习“小学”的具体知识,如洒扫应对等礼仪规范、礼乐书数等知识文化。“大学”的学习主体是指完成“小学”后立志成为“大人”的这批学子。这批学子是指“十有五年”从天子之元子到凡民之俊秀的优秀群体,他们不仅是从“小学”选拔出来的人才精英,也是被社会寄予厚望的一批学子。所以,他们在完成“小学”的学习任务后,进入“大学”所学的主要内容便是蕴含在“小学”之中的深层义理。朱子讲:“古者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定,已自是圣贤坯璞了,但未有圣贤许多知见。及其长也,令入大学,使之格物、致知,长许多知见。”(9)朱熹撰,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2020,第135页。朱子对“大学”与“小学”的学习主体的讨论,首先考虑到受教育者的身心、年龄等发展阶段与社会阶层问题。朱子也告诉立志成为“大人”的“小子”,只有“于小学存养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学,只就上面点化出些精彩。”(10)同上书,第136页。
因此,朱子对“大人”的概念界定,是以“大德”阐释“大人”。他认为“大人”乃是“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1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第267页。换言之,“大人”必是有大德之人,有此大德者须正己为先,不可好逸恶劳、斤斤计较,畏缩在个人的利害得失之间。换言之,大人者须先正己,但亦要向外扩充而正物,不能正物,也非大人。故而,朱子以《周易》阐释“大人”,认为“大人”是以“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谓‘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者。”(12)同上书,第332页。可见,朱子对“大人”的阐释,不仅使“大人”包含德盛大化的道德属性,也包含正己正物的政治属性,使“大人”并不是仅仅停留在个人的修养层面,而是告诉人们真正的“大人”一定要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这也正如朱子所言:“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13)同上书,第272页。故朱子之“大人”,乃是从其大体而论,其德广盛与天,其志通达天下,其业安定万民,大人可断天下之疑,敦厚崇礼,开物成务。
与朱子所理解不同的是,阳明认为的“大人”并非朱子认为的大德之人、正己正物者,而是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而且,阳明认为对“大人”相对应的主体,也不再是朱子认为教育阶段设计中的“小子”,而是不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小人”,即“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14)王守仁:《王阳明集》,中华书局,2016,第823页。阳明以“万物一体”为判定标准对“大人”与“小人”作出区分,认为“小人”在形骸上亦有人我之别,而大人却能与万物皆为一体,能够以“一体之仁”体知到亲亲仁民而爱物,如孩提入井之忧、草折瓦裂之惜。在此基础上,阳明也指出,不是体验到“万物一体”就是“大人”,而是体验到“万物一体”的那一刻才是“大人”。所以,只要“大人”一旦堕落到私欲之界,“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15)同上。
对于“大人”的理解,朱子与阳明不仅在诠释立场出现分歧,也在概念界定存在差异。所以,面对“大人”的诠释内容问题,朱子与阳明也就出现更为明显的分歧。朱子认为学习“大学”需要从“小学”入手。“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16)朱熹撰,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2020,第136页。朱子认为小学与大学的关系,是理之所以然与理之所当然的关系。不过有人问朱子:“大学与小学,不是截然为二。小学是学其事,大学是穷其理,以尽其事否?”(17)同上。这是说,尽管提问者知道大学与小学不是分割的关系,但还是基于两者学习内容而产生疑惑:即虽然知道小学是学事,大学是学事中之理,但是却对大学与小学的如何关联问题产生疑惑。朱子指出,大学与小学的学习内容“只是一个事。小学是学事亲,学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18)朱熹撰,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2020,第136页。也就是说,只有做到了“小学”,在此基础上,进行细致的“大学”学习,才能努力让自己学成“大人”。
面对“大人”如何学习“大人之学”的问题,阳明提出人人皆可学习大人之学,人人皆可成圣的主张,即“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19)王守仁:《王阳明集》,中华书局,2016,第29页。只是,按阳明之义,如果说万物一体就是人我之间便无分别、亦无贵贱的话,那么也就正如徐爱的疑惑那样,就会出现《大学》为什么又说个厚薄的疑问。对此,阳明答复到:
“惟是道理自有厚薄。……及至吾身与至亲,更不得分别彼此厚薄,盖以仁民爱物皆从此出,此处可忍,更无所不忍矣。《大学》所谓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20)同上书,第100页。
依《大学》所言之“薄”与“厚”而论,似与阳明之万物一体发生龃龉。但按照阳明的观点而论,如果非要在两件事物中选择一种,那么此时一定会有厚薄之别、主次之分。他认为,在《大学》中,道理本身确实有厚薄之分。其中的厚薄是指良知上的自然条理,是对道德和伦理的追求和理解。具体来说,在面对自己和亲人时,立志成为大人者不能存在厚薄之分,应该同样地对待自己和亲人,不偏袒地对待每个人。只有当立志成为大人者能够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做到得饶人处且饶人,做到“此处可忍,更无所不忍”。故而面对道理的薄与厚,阳明认为应以“万物一体”为判断依据,即孰厚孰薄需落在“良知”上作出价值选择。
朱子受“庆元党锢”之祸,导致其学在当世备受打击,如他对“大人”的诠释立场、概念界定、诠释内容并未受到当时世人的广泛学习与支持,仅是在《四书章句集注》等著作中明述“大人之学”。直到淳祐元年(1241)以后,宋理宗手诏下令以朱子从祀孔庙,淳祐四年(1244),南宋倡导程朱理学,全尚理学,使得《四书章句集注》备受重视而依此为言道标准,后又为官方读本、科举考试的根本依据。到了明代,直到王阳明的心学出现,朱子学的一统天下地位开始被撼动,同时也撼动朱子对《大学》“大人之学”的理学阐释。
朱子、阳明注解《大学》“大人”的主体判断上存在差异。朱子站在古代教育阶段设计的诠释立场上,认为大人是“有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并对受教育者进入小学、大学的学习条件设置年龄、身份、社会阶层的各种条件,依此揭示出“大人”的诠释内容,挺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阳明以“万物一体”为诠释立场,依此区别大人与小人,认为小人是“形骸而分尔我者”,大人是“天地万物为一体者”,“大人”的诠释内容则是指人人皆可学大人之学,人人皆可成圣。尽管朱子、阳明之学各有特性,但朱子、阳明着力阐发“大人者”的同时,也强调“大人”须真切把握“大人之教”。
二、“大学之教”:“格物穷理”与“致良知”
尽管朱子、阳明对“大人”的理解存在不同,从诠释理路看,朱子、阳明同样是从对学习主体的概念界定,推演出对“大人之学”的学习内容的系统分析。只是,由于两人的诠释立场的不同,导致他们对“大人”的理解难以保持一致,使得两人在“大学之教”即“大人”的学习内容上,呈现不同的安排与主张。
面对“大学之教”的内容安排问题,朱子以为“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学。”(2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0,第1页。对此,朱子分大、小之学,以为欲为“大人者”须学“大人之学”,学“大人之学”必读“大学之书”,效验“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22)同上书,第2页。。对此,朱子指出“大学之书”重在“格物”。朱子指出:“《大学》是圣门最初用功处,格物又是《大学》最初用功处。”(23)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2772页。
朱子特重“格物”,到王阳明这里,尽管阳明一生极少注释儒家经典,但阳明也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说过:“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辑之。”(24)王守仁:《王阳明集》,中华书局,2016,第70页。可见,阳明不满朱子以“格物”补《大学》,他要恢复《大学》古本之义,故而拒斥朱子分经传、重章句、做补传的方法。而且,据《年谱》记载:(阳明)“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其书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以补处。以诚意为主而为致知格物之功。”(25)王守仁:《王阳明集》,中华书局,2016,第1054页。阳明认为《大学》要旨是“诚意”,“诚意”才是践行“格物”实现目的。对此,黄宗羲指出朱子、阳明在“格物”与“诚意”之间的各自侧重。“朱子之解《大学》也,先格致而后授之以诚意;(阳明)先生之解《大学》也,即格致为诚意。”(26)黄宗羲编《明儒学案》,沈芝盈点校,中华书局,1985,第7页。所以,在“格物”与“诚意”之间,阳明以“诚意”为先,朱子则是以“格物”为首,足见两人对“大人之教”内容设置的理解差异。
朱子与阳明之所以对“大学之教”有不同的理解,是因为二人所面临的经典诠释困境不同。朱子认为学习“大学之书”重在“格物穷理”,其原因在于朱子不满汉唐经学家对《大学》一书的注释。东汉郑玄说:“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27)孔颖达疏,郑玄注《礼记正义》,中华书局,第1592页。之所以称为《大学》,是因为大学一书教人广博而治平天下。唐代孔颖达疏解郑玄之说:“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从诚意为始。”(28)同上。孔颖达认为《大学》主旨是为学治国,此以明德为本,诚意工夫为始。朱子不满郑玄注解《礼记·大学》原文顺序有问题,故而重新对《大学》重做修订,将《大学》分为“经一章”与“传十章”两部分。另外,朱子也否定汉唐经学家讲《大学》从“诚意”为先的看法,认为《大学》古本存在阙文,于是取程子之义做补,作《格物致知传》,将“格物”传、“致知”传放在“此谓知本”后,列于“诚意”传之前,强调“格物穷理”而后才是“诚意”,突出“格物穷理”在“大人之教”中的重要。
阳明则不满朱子注释的“格物致知”。“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29)王守仁:《王阳明集》,中华书局,2016,第41页。阳明认为朱子对事事物物上求一定理,易使心放而使之,出现心与理为二、知与行相分离的局面。所以,阳明不认同以“敬”诠释“即物格物”的朱子学。“如新本(指朱子《大学章句》)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有根源。”(30)同上书,第36页。阳明认为须“以诚意为主,而为致知格物之工,故不须添一敬字。”(31)同上书,第1032页。
除以上问题外,朱子与阳明也对“大人之教”的具体主张作出说明。朱子讲“格物穷理”,认为“格物穷理”的涵盖范围是天下事事物物,任何事物皆可被格。朱子言:“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3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0,第5页。尽管“格物穷理”面向一切事物,在培养“大人者”的立场上,朱子强调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3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0,第2页。教欲为“大人”者。这是由“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34)同上书,第267页的身份条件决定的。如果是社会中一般的普通人,他们的“格物穷理”可以停留在“小学”,即洒扫庭除,但大人不仅要修养自身,也要治理天下,既要为学,亦要为政。因此,要想成为“大人”就不能仅限于自我修养,也要正己正人,这就需要学习“穷理、正心、修己、安人”(35)同上书,第2页。之道,“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36)同上书,第8页。
阳明则认为“格物”之“物”并未独立于心之外,所谓“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37)王守仁:《王阳明集》,中华书局,2016,第1070页。也强调“理”也未独立于心之外,所谓“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可见,阳明对“格物”“穷理”的理解,不再如朱子般以“敬”诠释,而是认为“敬”本身就来源于心,无须再外求一个“敬”字,一切如“敬”般之道理皆可收摄于心、皆可落在心上。所以,阳明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为一者也。”(38)王守仁:《王阳明集》,中华书局,2016,第1089页。与朱子不同的是,阳明强调的是“致良知”。“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39)同上书,第826页。阳明认为“致良知”乃原取于《大学》古本之义,非朱子歧出之学。“致良知”既推扩良知使其发展达至极处,又是指操存良知、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致良知”发挥人的内在主体性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40)同上书,第1089页。,使事事物物皆见得天理。阳明认为“致良知”不似朱子“格物穷理”般仅留驻扩充知识之义上。所以,“致良知”同样面向一切事物,但却不再似朱子以知识束人手脚,而是以人人皆有之良心推扩于外物。在培养“大人”的立场上,阳明强调“大人者”乃“天地万物一体者”,高扬“致良知”之学,主张人人皆可学“大人之教”。
另外,阳明也注意到,大人能呈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结果、可以把握“大人之教”,并非是受到外在强加规范的“他律”,而是在于自识“一体之仁”使之流行遍布。阳明说:“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41)同上书,第823页。阳明认为,之所以大人能够成为大人,乃是由大人的内在之仁不断扩充而呈现。具体而言,孟子所谓“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瞬间生发的“怵惕恻隐之心”,这是阳明反复强调的“良知”。扩而充之,如同大人者见草木犹有生意,见草木摧折而必有悯恤,瓦石毁坏必有顾惜,即是吾人之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与草木而为一体。阳明高扬“致良知”,认为要想成为“大人”,“大人之教”就不能是朱子的“穷理、正心、修己、安人”,而应是以“大人者”自识“一体之仁”实现“万物一体”。
关于朱子与阳明对“大人之学”中“大人之教”(学习内容)的理解,后世学者看法各异。唐君毅以为,朱子、阳明论“格物致知之教”各有其美:“阳明之说不同于朱子者,则在朱子之格物穷理,皆由人之知其所不知者,以开出;而阳明之致良知,则由人之知其所已知者,以开出。”(42)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台湾学生书局,1986,第349页。冯友兰先生则指出,朱子、阳明论《大学》皆有缺失:“《格物补传》由‘穷物理’转入‘穷人理’,所以显得两橛。心学专讲‘穷人理’,所以显得直截。”(4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册,人民出版社,2007,第202页。冯达文先生曾指出:
朱子所讲的“知”与阳明所讲的“知”,在内容上即有差别,朱子广泛涉及外在之“物”与“理”,而阳明仅限于“德”;朱子既以外在之“物”与“理”为所知者,则他所面对的问题,为殊相与共相之关系问题,此为知识论的基本问题,阳明所面对的问题,其实为如何成德之“行”的问题,此实为信仰的问题。(44)冯达文:《从朱子与阳明之<大学>疏解看中国的诠释学》,黄俊杰编《东亚儒者的<四书>诠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4页。
唐君毅先生侧重于朱子、阳明论“格物致知”的特色,冯友兰先生则重在解析心学与理学的流弊,冯达文先生是以“知”为标准,分判朱王的知行观。但以“大人之学”而观,朱王之学呈现出学习“大人之学”的两种诠释进路也值得注意。朱子强调“格物穷理”,“大人之学”是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阳明则高扬“致良知”,认为“大人之学”是自识“一体之仁”,认为只有大人者去除人欲之蔽,才能复明其德,揭示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但无论朱王之学如何分庭抗礼,两者皆是十字打开“大人之学”,使“大人”通向“正人正己者”或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即“大人”通过“大人之教”向“大学之道”无限敞开。
三、“大学之道”:“修己治人”与“中国一人”
朱子、阳明对《大学》的经典诠释,最终都落在学习目标即“大学之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涉及朱子、阳明的终极关怀问题。朱子言:“大学一书,如行程相似。自某处到某处几里,自某处到某处几里。识得行程,须便行始得。若只读得空壳子,亦无益也。”(45)朱熹撰,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2020,第267页。读《大学》需沉潜涵泳,逐字咀嚼,契入此书血脉,切不可只读个“空壳子”。这就间接指出,《大学》一书在纲领上看,也确实具备“空壳子”的特征。正如牟宗三先生言:“《大学》只是一个‘空壳子’,其自身不能决定内圣之学之本质。”(46)牟宗三:《心体与性体》,正中书局,1985,第424页。
正是因为《大学》只列出三纲领、八条目的实践纲领,“只说一个当然,而未说出其所以然,在内圣之学之义理方向上为不确定者,究往哪里走,其自身不能决定”,(47)同上书,第18页。故而出现朱子、阳明两种不同的讲法。然而,朱子、阳明对《大学》这“空壳子”的经典诠释,并不局限于书斋,而是促使他们在“空壳子”中以自我价值为文化生命内核向宇宙、世界、人生投射终极关怀与实践思考,即西方诠释学所谓“解释者必须恢复和发现的,不是作者的个性与世界观,而是支配着文本的基本关注点——亦即文本力图回答并不断向它的解释者提出的问题”(48)戴维·E·林格:《编者导言》,载高达美《哲学解释学》,夏镇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12页。。朱子与阳明面对《大学》文本对它作出的经典诠释,无不是关联着他们各自提出的问题,而这一问题,落实在推行“大人之学”上,则表现在“大学之道”的践行问题上。
朱子回顾一生,自谓“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先须通此书,方可读他书。”(49)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2020,第275页。认为“大学之道”可使“国家化民成俗,学者修己治人”。阳明则指出“大学之教”可使“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这是因为,阳明认为“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但又因为出现“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的问题,圣人担忧此局面恶化,于是“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50)王守仁:《王阳明集》,中华书局,2016,第50页。故而,为传续各自心中的古代圣哲之真意,朱子、阳明分别以理学与心学诠释《大学》“大学之道”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朱子以“气质之性”诠释“大学之道”。在《经筵讲义》中,朱子曾指出“气禀”的现实性、“变化气质”的必要性。“臣(朱子)窃谓天道流行,发育万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为一身之主。但其所以为此身者,则又不能无所资乎阴阳五行之气。而气之为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浊,有纯有驳。以生之类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51)朱熹:《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692-695页。朱子从天道论阐释人的生成过程,指明“气禀”的现实束缚一面,朱子强调以“变化气质”实现“明明德”,认为“明徳”乃是“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眛,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5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0,第4页。故而,朱子主张“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53)同上。,以“变化气质”使旧民能够自明其德,成为“新民”。
与朱子不同的是,阳明是以“万物一体”诠释“大学之道”。“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阳明又言:“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54)王守仁:《王阳明集》,中华书局,2016,第51页。阳明从万物一体论阐释人己、物我一体的道理,指明万物一体的重要。进而,又以体用关系之“体”阐释“大学之道”中“明明德”的核心地位。
首先,“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55)同上书,第823页。
阳明认为:“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56)同上书,第23页。其中,“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57)同上书,第824页。所以,“明德”意味着“良知”,当“良知”未发之时,本身未受私欲遮蔽,灵昭不昧,它就只是“至善”,待“至善之发见”时,作为“心之本体”,它就会成为主宰善恶是非的意念。“明明德”是通过去除人欲之私重新回返到“人心一点灵明”,以立根工夫呈现良知本来面貌,目的是为了呈现“明德”还原“良知”。紧接着,若“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58)王守仁:《王阳明集》,中华书局,2016,第824页。谈“明明德”一定要与“亲民”相连。只是在两者之间,亦是如“种树者必培其根”(59)同上书,第30页。一样,须以“明明德”的立根工夫为先。
其次,“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60)同上书,第823页。
阳明以体用关系之“用”阐释“大学之道”中“亲民”的关键作用。其实,阳明对“亲民”的认识是立足对朱子以“新民”阐释“亲民”的观点进行批评、改正的。朱子根据《盘铭》《康诰》《大甲》“新”字,认为“亲民”是“新民”之义,指出“新者,革其旧之谓也。”(6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0,第4页。由于人们受到气质之性的拘束,所以,只有所学之人进行变化气质,才能复其明明德,进而推以及人,便能除去自身旧染之污,成为自新之民。对此,阳明否定朱子“新民”的讲法,通过援引《论》《孟》《尚书》论证“亲民”的合理与合法。在面对“新民”与“亲民”之别,徐爱曾针对此问题请教阳明: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其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62)王守仁:《王阳明集》,中华书局,2016,第2页。
朱子与阳明各自站在理学与心学的立场分别以“新”“亲”阐释“亲民”。其中,朱子是以“气质变化”解释“亲民”之“自新”;阳明则是以“万物一体”解释“亲民”之“一体”。按阳明的观点看,“亲民”的实现源于“致良知”的完成,使“良知”由吾人之心泛出,并在恰当时机向外界流动,即以其“一体之仁”扩充到孝敬父母之“孝”,友爱兄长之“弟”。进而,随着吾人“良知”的自致工夫与达至极致,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良知扩充。可见,“亲民”在阳明的眼中是立根工夫的外化与实践。换言之,人人皆可以实现的“亲民”,是实现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实践门路。
朱子与阳明对“大学之道”中“止于至善”解释的也不同。朱子以为“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6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0,第4页。朱子认为“止于至善”,是说认识并完成事物最高之理,始终如一的践行保持不变。阳明则认为“止于至善”是“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64)王守仁:《王阳明集》,中华书局,2016,第24页。“止于至善”是指通过“致良知”时刻保任吾人之良知,让良知呈现本来面貌,复其本然。
至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朱子、阳明均认为此三者乃“大学”之纲领。但朱子视“三纲八目”为不同节目,如“明德、亲民,便是节目;止于至善,便是规模之大”,从理学进路出发,认为“大学之道”是实现由复其自性的“明明德”,到使之自新的“新民”,再到“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的学习目标。朱子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关系认定为层层递进,形成“次第”工夫体系。阳明则认为“明明德”是“万物一体”之“体”,“亲民”是“万物一体”之“用”,“若知明明德以亲其民,而亲民以明其明德,则明德亲民焉可析而为两乎?”(65)同上书,第825页。阳明以体用关系诠释“明明德”与“亲民”,认为其最终归宿在“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明明德、亲民而不止于至善,亡其本矣。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谓大人之学。”(66)同上书,第824页。王阳明从心学进路出发,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者为一事之体、用、极处,形成“立根”的心学工夫。
朱子、阳明对“大学之道”的诠释,形成“次第”的理学工夫与“立根”的心学工夫。钱穆先生曾指出,阳明重成色轻分两,不能“于成色分两上一并用心”(67)钱穆:《湖上闲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第30页。。因此,“阳明良知学,实在也只是一种小学,即小人之学”,“晦翁的格物穷理之学,始是大学,即大人之学”(68)同上书,第30-31页。。对于造成阳明学沦为“小学”的内在原因,这是在于阳明骨子里沿袭宋明理学讲学大传统,“总是看不起子路子贡冉有公西华,一心只想学颜渊仲弓。他们虽也说即事即心,却不知择术,便尽在眼前日常琐碎上用工。一转便转入渺茫处。”(69)钱穆:《湖上闲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第31页。
尽管钱先生高举朱子学,以朱子学的诠释立场评价阳明学,但如果从“善”与“至善”的递进关系言,阳明对“大学之道”的诠释进路,也是无法实现朱子学般的层层上达。这是由于阳明学的“万物一体”之自身特性所决定。阳明对“大学之道”的追求,是以“立根”工夫追求“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朱子认为“大学之道”应是以“次第”工夫实现“国家化民成俗,学者修己治人”。尽管朱子阳明对“大学之道”的诠释存在各种分歧,但二人的“大人之学”均立足于儒家心性论阐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使“大人之学”在儒家心性之海中全幅展开而一路高扬。
四、结语
朱子、阳明注《大学》皆由“大人之学”而起,从主体、进路、目标的诠释面向看,二人阐释的“大人之学”存在分歧,但在儒家心性之学的映照下,朱子、阳明之学亦有共通之处:朱子、阳明均是顺着“大人”—“大学之教”—“大学之道”而一路发挥之。而且,朱子、阳明的“大人之学”在儒学基本问题上也具有一致看法:即作为一个人,该如何认识自我、如何实践自我、如何实现自我。对此,用牟宗三先生的意思来表达,则是说无论是朱子还是阳明,他们均是借《大学》这一“空壳子”,使道德主体在儒家经典中获得神圣体验与通体光辉,将经典世界与现实世界融为一体,以“道德的理想主义”开出“立千年之人极”。
作为“空壳子”的《大学》,既容纳朱子、阳明以“次第”工夫与“立根”工夫展开的经典诠释,也包含朱子、阳明以“格物穷理”与“致良知”开启的理论图式。朱子、阳明对“大人之学”的阐释,不仅反映两者建构哲学体系的学理思考,也揭示两者重塑精神世界的心性实践。总之,朱子、阳明以此身生命守护、践行、开拓“大人之学”的诠释活动,不仅对儒家经典诠释学的现代建构与发展具有模范作用,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体系建构具有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