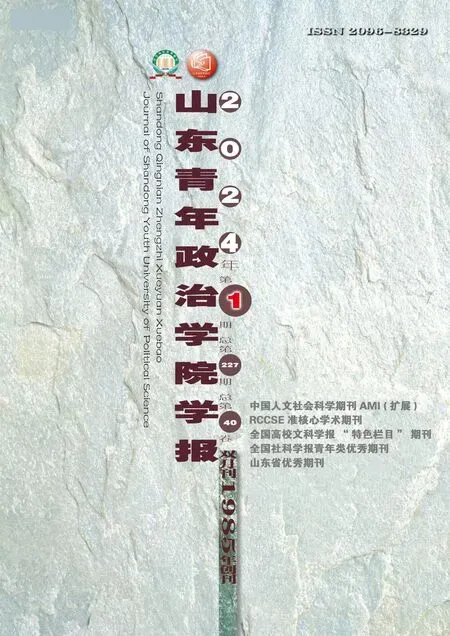微粒社会下青少年手机“软瘾”现象的批判性分析
王 健
(常州工学院 师范学院,江苏 常州 213022)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科技全面渗透到了大众生活之中。为了获得更便捷有效的生活,人们往往愿意借助移动网络手段加工和存储自己的信息,个体的需求进而能以数据的形式被各种算法精准测量,大众也就随之进入了个人生活被精细解析的社会。德国学者库克里克(Christoph Kucklick)提出了微粒社会(the granular society)的概念,微粒社会是高度解析且不再关注平均值的社会。(1)库克里克:《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黄昆、夏木可译,中信出版社,2018,序言第6页。这一概念中的“微粒”一词源于计算机科学术语,用于表示解析程度。数据的发展让精确度进一步提高,微粒社会就是个体和大众生活被数据精细解析后的一种社会类型。
在微粒社会中,“单体”的价值被充分发现和重视,以平均值为判断依据的科学规律被针对每一个“单体”的个性化分析和判断所代替。(2)常生龙:《即将到来的新型社会——读库克里克<微粒社会>一书有感》,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news/215490,访问日期:2023年9月3日。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浏览痕迹、通过APP上传的个人信息被仔细地分析和研究,个体越来越被机器精细掌控。互联网的精准投喂之下,青少年对手机的过度使用现象愈发严重。在没有智能手机等上网设备的时刻,很多青少年会表现出“无所适从”甚至“忧心忡忡”,这些表现已经明显具有了“软瘾”的特征。“软瘾”本质在于满足个体表面的欲望,忽视或阻碍了更深层次的需求。(3)莱特:《软瘾——终结那些窃取你时间、夺走你生活的强迫性习惯》,董黛译,花城出版社,2022,第55页。>手机“软瘾”虽然没有对青少年的正常生活和学习产生实质性的伤害,但却明显干扰了青少年的正常生活节奏、工作进程以及学习效果,家长、教育工作者、工作机构对此问题往往劳心费力却收效甚微。当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青少年网络成瘾、游戏成瘾等这类明显具有心理病理学特征的活动的诊断与干预,缺少从媒体文化批判角度对青少年以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的过度使用为主要特征的“软瘾”现象的分析。因此,如何更好地理解手机“软瘾”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并助力于家庭指导、学校教育以及社会工作等日常实践,就值得从文化和心理两个维度对这一现象进行批判性反思。
一、手机“软瘾”:当代青少年的拟真化生活
拟真(simulation)这一概念是由法国哲学家、后现代理论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提出。这一概念的本质在于强调一种受代码支配而非生产支配的时代与价值结构中的模式,拟真占据了已经死亡的真实的空位,是由数字代码构建的“真实的荒漠”(4)张一兵:《拟像、拟真与内爆的布尔乔亚世界——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在当代青少年的生活场景中,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携电子设备已经成为微粒社会的一种象征物,一种不可缺少的身体构成。这些智能电子设备成为当代青少年规划生活和感知外界的中介和代理,手机屏幕也变成了青少年感知现实的窗口。这种“窗口”虽然让青少年感官得以愉悦,但其对现实的生活世界却进行了简化与稀释。正如当代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所言,以智能手机作为中介的生活方式,限制了个体与现实世界产生物性联系,导致了一种去身体化的、无视线的数字化交流,“现实失去了它的当下在场状态,感知失去了身体,智能手机祛除了世界的现实性”(5)韩炳哲:《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谢晓川译,东方出版中心,2023,第39页。。正是在此意义上,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智能设备为青少年群体构建起了一种拟真化的生活。
借助微粒社会中的数字化技术,个体和群体心理特征通过手机得到了精准解析,可以视为当代青少年个体拟真化生活的底层技术逻辑。与“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这句话的本质一样,个体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各种网络设备上的浏览、滑动、点击等行为,早已被相关网络运营公司精准分析,形成了有关青少年个体生活的海量数据。借助大数据算法,运营主体得到了有关个体喜好和行为习惯的数据画像,可以对相应个体乃至特定群体进行精准“投喂”。于是,当代青少年逐渐受困于“信息茧房”而无法脱身,最终形成了一种数字化生活习惯,即手机“软瘾”。这种习惯通常会导致青少年忽视对现实情境的体验,只想在手机呈现的虚拟网络上通过“点赞”等方式获得愉悦;若达不到想要的目标,就会产生极大的失落感,于是更加热衷于通过手机网络技术“晒”“秀”。(6)迪芬巴赫、乌尔里希:《数字抑郁时代》,张骥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2,第3页。结果导致青少年不再重视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的真实体验,把现实中的一切分享到网络世界才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中心。人们在生活中经常可以观察到,青少年只要有时间就会在网络上记录他/她所认为重要的事件,这种行为也就成为了“软瘾”的主要表现之一。虽然借助网络记录生活这种行为并非完全无意义,但是青少年如果经常且过多“驻足”于网络生活的建构和展示,不仅影响(甚至可能改变)他们对环境的认知和注意调控能力,而且还会助长青少年的虚荣心。把是否被记录、是否得到朋友圈的积极关注,作为评判人生事件的价值标准,这也就导致青少年对手机影像或照片是否“够好”的重视超越了现实体验本身(7)同上书,第42页。。
在此意义上,手机“软瘾”的本质则是“将个人对幸福的决定权让渡给互联网,让其定义自己生活的意义”(8)同上书,第10页。。大众正是因为相信技术对生活大有裨益所以自愿过度使用智能手机。于是,尽管人们在不断调侃网络照片是“照骗”,青少年却仍在“精修”手机图像的道路上乐此不疲。因此,手机“软瘾”的形成具有相应的技术基础。换言之,能够广泛占据当代青少年现实生活的手机“软瘾”现象,背后实际上暗含着社会大众的一种技术价值观。
二、手机“软瘾”的成因:技术霸权与心理需求
造成青少年手机“软瘾”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唯科学主义文化影响下社会大众对信息技术的崇拜;二是个体的心理需求在大数据精准解析的基础上不断被满足。
(一)外部成因:唯科学主义下的技术霸权
在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波兹曼(Neil Postman)看来,大众对技术所隐含的意识形态的意义视而不见。(9)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第103页。唯科学主义就可以视为对这种技术意识形态的反映。根据波兹曼(10)同上书,第162页。的看法,唯科学主义有三个相互联系的观念:一是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二是社会科学生成的原理可以用来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三是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产生不朽的感觉。在此意义上,技术对个体的生活信念具有一定的塑造作用。当代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在晚期现代性大背景下,个人之无意义感——那种认为生活未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正逐渐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11)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8页。于是,在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和个体想要疏解无意义感的影响下,数字信息技术就在一定程度上填充了人们生活中的空白地带,占据了社会的真空,让人们在其间可能产生的无聊之感荡然无存。(12)迪芬巴赫、乌尔里希:《数字抑郁时代》,张骥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2,第48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代社会压力环境给青少年带来的消极感受。
对于波兹曼而言,由于分值、统计数字、分类系统能为人们的境遇或信念赋予技术的真实,所以技术能够清楚显示人的境遇或信念的本性,进而使得唯科学主义成了社会大众的一种绝望中的希望、一种虚幻的信仰。(13)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48页。换言之,唯科学主义让人们相信以标准化的程序为手段的“科学”能够提供一种超人的基础,一种无懈可击并能够回答许多问题的道德权威的源泉。(14)同上书,第180页。在这种技术价值和信念标准下,个体行为是否有用或者有多大产出等功利主义价值观主导了人们的生活,效率成了现代化评价所有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准。(15)艾恺:《持续焦虑——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第15页。功利主义把人和其他物体视为具有一样的性质,都可以通过有用程度和被使用后的成果来加以判断。在此意义上,判断一个人或一个行为也就是判断其成效。这就导致大众社会交往中的诸如亲和、爱、感激等情感变得无关宏旨,工作成就大小才是评判个人存在意义的重中之重,除了实用之外的其他价值变得可有可无。(16)同上书,第21-23页。正是在这种价值导向的压力下,时间绝对不能浪费。换言之,人们在任何时间下都要有相应的价值产出,即便闲暇也要有价值,发呆因此就有了原罪。在这种时间压力下,人们应有的放空自我的时间成了毫无价值的“无所事事”,为了破除这种无聊感,当代青少年的手机“软瘾”便应运而生。
青少年“用工作、行动、娱乐和消遣来填补存在的空洞和空虚,直到再也看不到任何空余的空间”(17)迪芬巴赫、乌尔里希:《数字抑郁时代》,第52页。,为了追寻这种所谓有价值的时间利用,青少年依赖手机创造他们所谓的趣味和意义,却破坏了真实的生活世界。换言之,青少年越是想完全消除无聊时间,越可能会让自己失去源于这种闲暇时间中的体验和创造力。尽管数字化技术为那些能以数字化形式传达的体验创造了优先权,开辟了一片新的空间,为一种新的、永远不受约束的、粗暴的讨论文化提供了场所,比如青少年的网络亚文化,但是真实的交流却遭到了破坏。(18)同上书,第148页。实际上,以无聊为感受特征的闲暇时间会让人们直面存在的问题,而关于“何为生命的真正含义,何为人的定义,科学并不拥有这样的权威去确定诸如此类的标准”(19)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180页。。波兹曼曾举例,如果医生过分依赖医疗器械,医生会失去仔细检查的能力,越来越依靠医疗器械而不是经验和洞见。(20)同上书,第108页。与之类似,当代青少年对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过分使用,同样也会让他们失去最真切的表达,失去对周遭世界的具身(embodiment)体验。在此意义上,手机移动网络把当代青少年“有关自然、生物性、情感或精神的主张置于从属地位”(21)同上书,第122页。。
(二)内部成因:绩效主义规训下的心理需求
作为一种技术性概念,绩效主义主要是指企业中的一种管理方法或模式,这种模式将绩效视为比完成绩效的人更重要,并以绩效来确定人的身份和价值。(22)王建华:《教育优绩主义及其超越》,《高等教育研究》2023年第1期。当代青少年一方面要迎合外在效率标准的要求,比如来自工作环境或者学校、家庭的期盼,又想满足内心本能的放松欲求,于是,表面看似在“忙碌做事”实则“一事无成”的手机“软瘾”就成了最终的行为选择。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放松方式。青少年个体在牺牲必要的休息甚至睡眠时间的情况下,长时间使用手机(比如“刷”短视频)之后,体验到的往往是更多的疲惫与空虚。正因如此,手机“软瘾”既无法真正产生有价值的成绩,也无法达到休闲的目标。那么,青少年为何还会宁愿牺牲本就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也要进行这种毫无价值的活动呢?这就必然会涉及个体心理因素。
技术从来都不是技术,而是一个永远充满激烈情感依赖的世界。(23)西摩:《推特机器——为何我们无法摆脱社交媒体?》,王伯笛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第53页。上瘾是在一种情感关系失败时被塑造出来的另一种情感依赖(24)同上书,第74页。。精神分析的中间学派代表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认为,那些让儿童可以确定无疑地过渡到现实的物称为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在心理发展意义上,青少年虽然会放弃最初的过渡性客体,但是其内在本质特征却并未丢弃,这些特征会赋予其后的其他物体或行为,作为一种过渡现象存在于日常生活领域并展现在青少年的心理图景上,青少年花费大量的时间体验、重新组织以及重新创造其内在和外在世界。(25)郗浩丽:《温尼科特过渡客体理论的发展线索》,《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在此意义上,智能手机等数码产品可以视为最“了解”青少年自我的一种客观存在。正因如此,在韩炳哲看来,人们与智能手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共生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共生关系,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数字移动设备就可以视为当代青少年的一种过渡性客体。借助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当代青少年为自己创造出了游戏的空间——一个放松、安全、没有争吵的栖息地,祛除了对孤独的恐惧。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帮助青少年实现了这种对生命具有重要意义的功能,为使用它的个体传递了一种安全感。就像儿童如果丢失了自己喜爱的过渡性客体就会非常恐慌一样,日常生活中的青少年一旦找不到或者丢失了手机,也会焦躁不安。换言之,青少年和智能手机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26)韩炳哲:《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第43-44页。。
在心理学研究中,个体在早年生命历程中缺失的东西,往往会在后期表现出过度满足的行为或习惯,可以称之为心理上的一种“过度补偿”。在当代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来自家长和教师的严格的教育规训,其自我掌控被弱化。在当前压力重重的社会环境中,相对完整的闲暇时间非常难得,每天的学习空余、工作间隙以及睡前时间就成了青少年唯一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资源。于是,学习或工作一天后的“报复性熬夜”现象也就成了典型(27)艾娟、张博凡、黄文馨等:《青年学生报复性熬夜与手机成瘾、时间管理的关系》,《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青少年在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上的点击和划屏 “成了一种宗教仪式般的姿势”,由此带来的心理满足仿佛成了“睡前甜点”。这不仅极大影响了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同时也强化了自我关联的特性,让世界服从于自身的需求,“世界显现在完全可控的数字化表象中”(28)西摩:《推特机器——为何我们无法摆脱社交媒体?》,第33页。。但是,这种貌似拥有“掌控感”的自动化却让青少年付出了代价。以煮咖啡为例,全自动咖啡机的使用让获得一杯咖啡更为快捷、便利,“一键式”煮咖啡让人只关注结果。从按下按键到喝到咖啡之间的时间就成了毫无意义的等待,人们体会自己的手艺以及充分的参与感则不复存在。(29)迪芬巴赫、乌尔里希:《数字抑郁时代》,第18页。最终,真实的身体经验遭到了破坏。
长期沉浸于由数字移动技术所构筑的虚拟世界,青少年很容易失去对他人的兴趣。现实中的他人暗含着不确定性,附带着不可掌控的风险,而拟真化生活方式则会让青少年形成一种留恋。原因在于,相对于自己在虚拟网络中构建出的或者被“精准推送”的美好形象,现实世界中的人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也就导致真实的人是否在身边变得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网络中大量存在的“更好的”他者。(30)塔登:《自我决定的孤独——难以建立亲密感的社会》,顾牧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第110页。因此,表面上看,当代青少年深陷手机“软瘾”之中,实质上则是他们对让人紧张或恐惧的生活面的一种抵御,是对符合自身理想他者的追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自身的情感体验能力。正如韩炳哲所言,由于人们在智能手机中主要是关注自己,于是个体通过智能手机退缩到自恋场域中的同时也摧毁了共情。(31)韩炳哲:《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第46页。进而,青少年习惯于去身体化的交流、离群索居的生活以及对虚拟生活的偏爱,导致他们在由智能手机所构建的虚拟世界里,让有生命的他者变成了没有身体的存在。(32)同上书,第126页。比如,青少年待在家里也能通过手机屏幕所呈现的虚拟空间了解远方、结识新人,这也导致他们对分离和联系、失去和拥有产生了新的理解。(33)同上书,第106-107页。这就进一步加强了青少年的自恋、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和对虚拟自我的美化。
三、手机“软瘾”的戒断:当代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的重构
根据以上分析,技术文化的渗透与个体心理的满足是导致青少年手机“软瘾”现象的两种重要原因。同时,手机“软瘾”也反映出当代青少年生活方式的“离身”倾向,即技术设备取代人的身体成为人与世界产生关联的主要媒介,真实的身体经验被边缘化,被虚拟的符号认知和技能所取代。因此,破除手机“软瘾”,重构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可以从心理、技术以及具身三个维度着手。
(一)心理维度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曾指出,人是生活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34)孟庆延:《谁的问题——现代社会的非标准答案》,中信出版集团,2023,第238页。然而,在当代青少年通过手机所构建的拟真化生活中,自己和他人却成为一种抽象而非具体的形象。由于这种形象是以满足自身喜好作为出发点,不具有任何现实中的威胁和压力,青少年对拟真化生活的沉迷实质上是一种爱自己或自恋主义的反映。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劝导人们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本身,胜于爱生活的意义。从心理层面而言,首先要帮助青少年明确自己在网络上的行为表现的目的和意义所在,降低从事那些无任何成长意义的事情的频率,避免网络亚文化和网络流行语成为自己思想和语言库的主导。同时,在青少年认识到拟真化生活对自身心理具有消极影响的基础上,家校社三方需要进一步提供各种心理支持,引导青少年走出充满自恋感觉的虚拟网络舒适圈,不以自己感觉安全和舒服作为人际沟通的唯一考虑,不把移动互联网技术视为构建生活方式的最好媒介。在认识到微粒社会中的唯科学主义的弊端后,也需要帮助青少年破除对数字的迷信,不把网络的精确计算当作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评判标准。
(二)技术维度
荷兰学者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在拉图尔(Bruno Latour)和阿特胡斯(Hans Achterhuis)等技术哲学家有关道德物化(materialization of morality)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技术中介论。该理论认为,技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起着中介和调节作用,技术不但影响着人们对外在世界的感知,而且还影响着个体的行为方式。换言之,世界的表象通过技术的中介显现于人,而人的表象也通过技术的中介显现于世界(35)张卫、王前:《道德可以被物化吗?——维贝克“道德物化”思想评介》,《哲学动态》2013年第3期。,可以通过物的布置、使用和流行来践行道德(36)王小伟:《道德物化哲学的当代科技伦理启示》,《道德与文明》2023年第3期。。在此意义上,既然技术具有关联人与社会的作用,那么网络和电子设备的设计就需要重视技术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比如,技术作为情感教育的工具有以下缺陷:频繁的多任务处理会导致抑郁、社交焦虑,以及无法读懂人们的情绪。(37)特克尔:《重拾交谈》,王晋、边若溪、赵岭译,中信出版社,2017,第47页。网络技术人员和设备研发人员,可以将有助于提升道德或情感能力的技术嵌入智能手机这类电子设备中,比如,当前很多游戏厂商为了防止未成年人的游戏成瘾,在游戏中运用了防沉迷技术。如此一来,就可以从技术维度上降低青少年对电子设备的依赖,从而提高这一群体处理与应对现实世界问题的能力。
(三)具身维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认知科学领域越来越强调具身性的观念。具身性观念重视身体在人的认知和心智中的基础性和运作方式(38)冉聃:《赛博空间、离身性与具身性》,《哲学动态》2013年第6期。。然而,在当前青少年的数字化生活中,由于缺少面对面的交流互动,降低了身体接触的频率。研究者认为,当代社会中空间距离的增大、人们对高移动性的追求以及交流方式对技术手段的依赖,共同造成了这种局面。(39)塔登:《自我决定的孤独——难以建立亲密感的社会》,第18页。同时,当代个体主义文化对边界感的重视,导致青少年更倾向于避免身体接触,保持距离,以免被突然的、无法掌控的亲近所伤害或者避免自己去侵犯他人。(40)同上书,第80页。但是,已有研究发现:人类能在没有视觉、听觉甚至嗅觉的情况下生活,但若失去了触觉,就无法正常成长甚至死亡,肌肤接触能够促使身体成长,身体接触能够缓解压力。(41)同上书,第12页。在此意义上,个体只有在拥有“具身的自由”之后,才可以在关系、情感、心智上培养躯体的感官和感觉能力,才能在与他人的相遇和身体的接触中真实地活着。鉴于此,家庭、学校和社会就需要在生活中积极营造可以让青少年亲身参与的活动环境,通过劳动、美育活动,提供更多符合当代青少年兴趣的主题活动。换言之,通过不断让青少年增加真实生活中的具身经验,帮助其戒断手机“软瘾”。
四、结语
当前青少年手机“软瘾”现象的普遍化,可以视为这一群体对社会结构造成的困境的消极抵抗。换言之,手机“软瘾”是青少年缓解日常工作压力、学业焦虑、未来的不确定性等问题的一种消极应对方式。正如学者莱特指出的那样,“软瘾”只是人们安抚自身的一种错误尝试,一种试图缓解劳累、分散注意力、应对强烈情绪或自娱自乐的方法,其中的关键在于这类行为不会丰富个体的生活,反而会耗尽人们本可以用来推动实现梦想的宝贵资源。(42)莱特:《软瘾——终结那些窃取你时间、夺走你生活的强迫性习惯》,第21页。关注青少年手机“软瘾”现象,不能只是考虑从物质层面限制或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问题,还需要重视分析青少年这类行为背后的情感诉求和身心体验。换言之,在以风险、不受掌控、个体化为特征的现代性文化中,以手机依赖为主要特征的“软瘾”现象,本质上指向的是青少年个体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同时,人们也应认识到,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被迫卷入“为自己负责”的文化语境中的时候,他们必然更加看重人际关系的有效性,重视环境与工作对于自身的意义。正因如此,如何指导当代青少年处理好外部环境与心理需求之间的平衡,从而构建起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将是社会、家庭与教育领域持续思考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