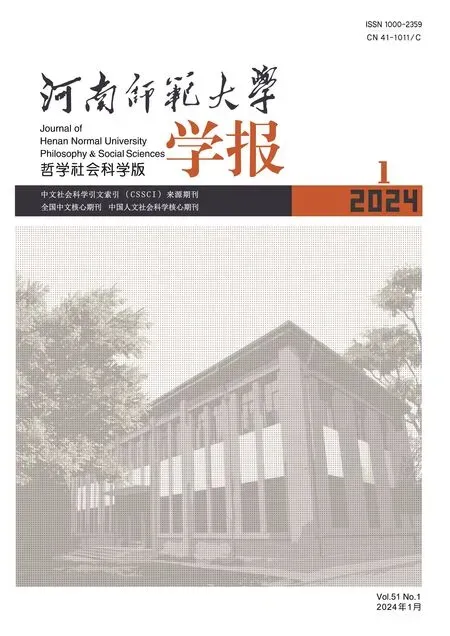法律实证主义的价值论问题
——制度法论的解决方案与反思
郭 栋,陈 旭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8)
近代法律实证主义的崛起有两个前提:一是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的近代科学的兴起;二是发轫于笛卡尔的近代哲学与伦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第二个条件来说,休谟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的“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在法哲学领域掀起一波至今仍未平息的认知浪潮。由此,自然法学派因其从事实推导出价值的认识论桎梏愈发明显,而逐步让位于法律实证主义。对“休谟问题”的回应是法律实证主义演进脉络中的一条内在线索,也是理解法律实证主义理论内核的密钥。制度法论运用“制度事实”的理论创建在规范与事实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尝试着构建一种融合了事实、规范和价值的法律解释与法律分析框架,从而建立了一种新的法律实证主义价值论。制度法论是如何回应“休谟问题”的?这一问题至今仍缺少全面的梳理与分析。因此,在法律实证主义的历史沿革中,全面探讨制度法论如何在价值论意义上探讨事实、规范与价值的关系,是理解制度法论综合性与开放性的全新视角,对当代法律实证主义的研究颇有裨益。
一、价值论领域的“休谟问题”:法律实证主义视域下事实、规范与价值的纠缠
(一)“休谟问题”的产生与发展
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哲学问题:一个是归纳问题或者因果问题,也即认识论问题;一个是“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即价值论问题或道德哲学问题。本文主要研究后一个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应当”语句包含有支持“应当”的理由,此时的“是”与“应当”之间没有完全割裂开。而随着近代以来个人主义的全面胜利,支持命令的理由不断减少,“应当”语句以上的特征才逐步消失。因此,随着“应当”语句目的论背景的瓦解而带来的语义变化是“休谟问题”出现在18世纪的主要原因(1)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32-233页。。笛卡尔哲学体系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外部世界分离,由此,使得基于人类理性的价值判断与外在的事实判断之区分成为可能。
在具备了物质、哲学以及文化上的种种条件之后,揭示价值论领域的“是”与“应当”问题就具备了理论必然性。随后,康德的道德哲学对“休谟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与回应。首先,康德肯定了“是”与“应当”的区分,他以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的区分作为“是”与“应当”之间互相隔离的界限,自然哲学研究“是”,而道德哲学则研究“应当”;其次,康德反对从“是”直接推出“应当”的论断,认为这种越界的推理只会导致本体世界先验的幻象(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版),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7-200页。。
康德之后,摩尔提出的“自然主义谬误”的论断可以看作“休谟问题”在伦理学领域的延伸。摩尔认为关于“善”的定义是伦理学中的最根本问题,而“善”具有非复合性与非自然性,其性质在自然科学所能描述的范围之外。因此,具有规范性的“善”的概念与自然主义描述性的概念之间便存在着一条鸿沟,当自然主义者试图跨越这条鸿沟时,“自然主义谬误”便产生了(3)G.E.Moore, Principia Eth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2, p.41.。摩尔所揭示的“自然主义谬误”,可以被归结为从描述性概念推导出规范性概念的尝试,也即从“是”到“应当”的推论。
20世纪中后期,哲学领域对“休谟问题”的研究仍绵延不绝。约翰·赛尔认为,借助制度的概念,可以通过构成性规则从“是”中推导出“应当”(4)John R. Searle,How to Derive Ought from Is,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1.73, No. 1 (Jan,1964), p.57.。普特南的思路则是淡化“是”与“应当”的区分,他认为事实与价值之间是互相渗透、纠缠与融合的,“每一事实都含有价值,而我们的每一价值又都含有某些事实”(5)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212页。。
(二)传统法律实证主义对“休谟问题”的回应
发端于哲学领域的“休谟问题”经过不断的解释、阐发与转化,逐步渗透到了法学领域。在哲学的视角下,价值论领域的“休谟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一是“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二是从“是”到“应当”的推导问题,从“是”不能推导出“应当”也被称为“休谟法则”(Hume’s Law)(6)John Rawl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p.85.。而在法律规范主义的视角下,需要把叫作“规范”的楔子嵌入价值与事实之间,这个规范就是法律规范(实定法)。由此,法学领域的“休谟问题”变成了包含道德(价值)、规范(法律)与事实三个维度的立体问题。其中包含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即“分离命题”)(7)H.L.A. Hart, 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 in his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pp. 615-621.,以及事实与规范的关系问题(即“规范命题”);其次,法律实证主义在回答从“实然之法”向“应然之法”的过渡时,也会涉及法律的正当性来源问题。
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奥斯丁、凯尔森、哈特和拉兹都曾对“休谟问题”进行回应,以之为线索可以一窥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演进脉络(8)段卫利曾详细研究过奥斯丁、凯尔森和哈特对“休谟问题”的回应策略。参见段卫利:《“是”与“应当”之间:法律实证主义对休谟问题的回应》,《法理学论丛》,2016年第9卷。。
奥斯丁旗帜鲜明地坚持分离命题,“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优缺点是另一回事”(9)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9-230页。。即主张法律与道德的二分,同时主张“应然法”与“实然法”的二分,法理学只研究“实然法”。在事实与规范的关系上,奥斯丁将规范与事实混同,认为法律与事实不可分,进而剔除了法律义务的规范性,用从“是”到“是”的逻辑结构回应了“休谟法则”。在法律规范的正当性来源问题上,奥斯丁以“主权者+服从习惯”的模式保障分离命题的成立(10)陈景辉:《法律的界限:实证主义命题群之展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页。,但这无法为法律的规范性来源提供足够的解释。
在对“是”与“应当”的区分问题上,凯尔森通过创造“基础规范”这个先验性的概念,作为法律有效性的来源,进而以从“应当”到“应当”的逻辑结构回应了“休谟法则”。哈特以非先验预设的“承认规则”代替了凯尔森的“基础规范”。承认规则需要用一种“内在的观点”来解释,可以被还原为人们行动、信念和态度的社会事实。从外部陈述来说,承认规则是事实,从内部陈述来说,承认规则是“法律”。因此,承认规则是法律与事实的统一(11)支振锋:《法律的驯化与内生性规则》,《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承认规则的概念,借助解释学的方法,将社会实践、主观心理以及规则等要素凝结成了一种贯通的逻辑,进而在不违背“休谟法则”的前提下,解释了法律规范性的来源。
对于分离命题,拉兹有着严格的实证主义立场,他用渊源命题解释法律的存在,摒弃道德性评价,坚持了法律与道德的二分(12)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2nd e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9 , p. 53.。但同时,渊源命题将法律归结为社会事实,这便存在混淆事实与规范的可能,背离了规范命题。拉兹把法律解析为事实权威与合法权威的统一,其中,法律的有效性体现在法律是事实权威本身,而法律的规范性则来源于对权威的合法性证成,这种证成最终被归结于服务性的权威观念。所以,从根本上来讲,权威概念只是一个中转站,拉兹实质上仍旧是用从“应当”到“应当”的进路来回应“休谟法则”。
二、制度法论对事实、规范与价值的关系重构
制度法论的理论构建有如下层次:首先,在法律本体论上,将法律事实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并将其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结合规范的成分构造出“制度事实”的基本范畴;其次,面对法律实证主义中规范与价值循环论证的困境,制度法论强调在规范与价值之间建立联系,并将法律原则视为价值与规范的汇合点;最后,制度法论发展了实践哲学在法律推理领域中的运用,法律系统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是一种人的理性在综合性社会背景下的思维过程,这种思维不仅需要在事实中收集信息,而且要从人们的态度中凝结价值。
通过分析制度法论语境下法律系统的开放性,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制度事实”“法律原则”“实践理性”的概念如何形塑并规范着制度主义法理学的哲学构造、法律推理以及社会实践,同时也为解读制度法论对休谟问题的回应创造了条件。
(一)制度事实: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制度主义法理学的主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法是一种制度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
魏因伯格提出:“制度事实——例如法律制度——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出现的复杂事实:它们是有重要意义的规范的构成物,而且与此同时,它们作为社会现实的因素存在。”(13)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9、136页。与麦考密克关于制度理论的解释性事实(interpretative facts)(14)Neil MacCormick, Institutions of Law: An Essay in Leg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6.note10, pp. 16-20.不同,魏因伯格在一种规范与现实的二元结构中勾勒出了制度事实的轮廓。所谓“制度事实”是一种介于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复杂混合物,这种混合物既有主观成分又有客观成分,既是规范的构成物又是社会现实,既有外部可观察的物质特征,又需要一种解释学的方法来理解。
“制度事实”的概念借鉴于约翰·赛尔(John.Searle)。赛尔为了说明语言的规则结构,指出了“构成规则”与“调整规则”之间的区别:“调整规则调整先在的活动,这种活动的存在从逻辑上说是独立于规则之外的。构成规则构成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的存在从逻辑上依赖于规则本身。”(15)J. Searle,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Cambridge,1969) , p.34.也就是说,调整规则调节规则之外的行为,而构成规则则不同,遵守构成规则本身是产生某种行为或活动的前提,如果违反构成规则,这种行为也将不复存在。例如,在国际象棋比赛中,不按某个规则的走棋(如象走直线)是无效的。
麦考密克沿着赛尔“制度事实”的进路,认为制度的概念必须更广泛地运用规则来界定和构成。麦考密克提出了法律制度分析的三种规则体系,这三种规则分别为“创制规则”“结果规则”和“终止规则”。具体而言,法律规定,当发生某种行为或事件时,就会出现有关的制度的具体实例,这种规则称为“创制规则”;一项合同、信托或遗嘱存在时,法律便会有效地以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方式产生一整套的进一步的法律后果,这种规则称为“结果规则”;每项制度都可以把这些关于终止的法律规定视为一种规则,这种规则称为“终止规则”。麦考密克通过制度概念的规则化表达,提供了一种理解法律结构的新视角,无疑是受到了哈特的影响(16)哈特主张法律应该被仔细地区分为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H. L. A. Hart,The Concept of Law(Oxford,1961),esp. Chapters 3-6, pp. 91-95.。麦考密克用制度事实来解释规则是其理论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在哈特的基础上为规避规范主义与极端社会现实主义冲突的一种策略,制度事实的概念在两种话语体系间架起了桥梁。但是,创制规则与结果规则的区分是否必要?因为创制规则的结果正是结果规则的条件,“用合同来举例即‘存在一项有效的合同’,正是这些词语首先作为结果然后作为条件起作用”(17)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2页。,那么为何不将创制规则与结果规则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单一规则呢?麦考密克回应说:律师和法学工作者实际上正是以这种方式来使用制度概念的,法律主题的复杂性是这种规则术语在现实中存在的实际理由。实质上,麦考密克回避了问题的实质,他并未从规则(规范)本身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而是跳到了社会现实的领域,用社会现实以及人们的态度和认识来支撑其理论的逻辑漏洞。
这种从规范到现实的转换也正是整个制度法论的特点,这种特点表现在,“制度事实”概念在哲学意义上的“制度”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的实例”之间来回穿梭,在概念上架起了“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理论联系,并基于这种概念在不同层面上对法律进行解释。
(二)法律原则:价值与规范的汇合
在论证价值与规范的关系时,自然法持一种价值主义的立场,法律实证主义持一种规范主义的立场,而制度法论则在法律实证主义的旗帜下,提出“超越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18)《制度法论》第五章正是以“超越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命名的。的立场。制度法论从理论与实践的路径上扩展其规则体系,以实现价值主义与规范主义的融合。在理论路径上,制度法论强调一种基于分析法学方法论的法律推理理论,通过民主主义下的“商谈(discourse)”模式来消解规范与价值间的隔阂;在实践路径上,制度法论通过对法律原则的运用实现了价值与规范的汇合,弥补了法律规则论在效力范围上的漏洞,回应了法律作为一种实践科学的现实面向。
在理论层面,制度法论所建构的规则体系是对制度概念的形式主义描述,其本质是理解法律的逻辑结构而衍生的思维系统。一个制度的创制规则无论制定得如何细致,都无法保证一个制度的假想实例的完整有效性。法律规则对于制度实例的有效性而言是一种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法律规则无法穷尽制度实例的无限可能。
那么,法律原则为何能够改变法律规则的有效性,亦即法律原则较法律规则高阶的效力来源于什么?答案是法律原则中蕴含着价值。实际上,法律实证主义并没有否认价值与规范的联系,哈特内在的观点隐含着规则是以价值为基础的倾向(19)H. L. A. Hart,The Concept of Law(Oxford,1961),esp. Chapters 9, p. 198.,制度法论也认为法律秩序体现意识形态。那么,如何在主张规范与价值二分的前提下,又将价值的因素映射到规范之上呢?哈特采用了“解释学”的方法,相对地脱离了社会行为人的立场,使法律实证主义与道德哲学并行不悖;而制度法论则借助于法律原则实现了价值与规范的汇合,在保证规范层面价值无涉的前提下,又将价值因素通过法律原则的载体,内嵌于法律运行的过程中,法律原则是客观价值与实体规范之间的连接工具。
同时,法律原则与规则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承担着规则的目的论背景,并且在例外的情况下能够为规则的效力提供解释。法律原则本身就体现着一种规范主义。同时,法律原则承载着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体现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因素给法律补充了必要的灵活性,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法律原则也是价值主义的。所以,法律原则通过价值范畴与规范范畴的衔接,实现了价值主义与规范主义的融合,从而弥补了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单范畴理论的不足。
法律的正当性问题是现代法理学的核心关切之一,而麦考密克则认为相较正当性而言,法律的第一优点是合理性,而合理性又分为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20)Rheinstein/Shils, Max Weber on Law and Society, Cambridge,Mass.,1954,pp.1-3; R. S. Summers,Two Types of Substantive Reasons:The Core of a Theory of Common Law Justification,Cornell Law Rew.63(1978),p.707.。若要实现法律体系的合理性证成,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之间就需要一个连接点,这个连接点就是法律原则。法律原则一方面承载着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能够实现规范框架下个案裁判的效力变更,是实现规范目的的条件保障。因此,法律原则不仅是价值与规范的汇合点,而且是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的统一。
与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者相比,制度法论将规则、法律原则以及判决的必然推论纳入法律的范围中,并且公开地将价值标准与道德因素包容在实在法的范围之内。与自然法独立于人类意志的先验价值标准不同,制度法论中的价值因素是在制度的框架内具体化于人们的态度中的实在物(21)余涛认为,“实在化”是麦考密克对制度化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参见余涛:《法律制度理论的后实证主义面向及其困境》,《法律科学》,2020年第4期。,这便是其所宣称的“超越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的立场。制度法论对法律原则的阐释是理解这一基本立场的重要环节,正是通过法律原则的范畴,规范主义与价值主义达成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和解。同时,法律原则是法律合理性论证中的重要环节,合理性理论提供了一种理解法律权威性或有效性来源的新视角,弥补了实证主义与自然法之间理论上的对立与鸿沟。
(三)实践理性:以事实和价值为背景
制度法论作为法律实证主义新发展的另一特色,在制度化过程中将实践哲学引入法律推理。制度法论通过实践理性(22)实践理性的范畴来源于康德,参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30、43、45页。的概念,将解释学的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进而实现规范主义、价值论法学以及现实主义法学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融合。研究制度法论实践哲学的整个概念,特别是深入分析魏因伯格的行动理论以及实践推理的非唯知性后,我们会越发清晰地认识到,制度法论的实践理性是以事实和价值为背景的。
魏因伯格的实践哲学是与麦考密克的解释学(23)制度法论所借鉴的解释学主要来源于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 Thuth and Method, Second, Revised Edition. Trans. By J. Weinsheimer and D. G. Marshall, Continuum Publishing Group,2004(reprinted 2006).方法论互为对照的。解释学是关于理解的精神科学,这种理解带有人类认识与态度的印记,并且依赖于人类的认识与态度而成为区别于自然科学方法的独特方法体系,通过作为部分的具体现象与作为整体的社会背景的不断循环而实现认识的无限发展。人类的认识与态度,无疑是解释学理论的核心,这种作为架构制度的思想成分,是人们在各种实践性辩论中形成的,由此便需要一种评价性的公正标准,作为实践辩论的指导。因此,关于公正的标准是实践理性的理论起点。与传统正义理论把正义理解为一种客观认知不同,魏因伯格主要考虑的是正义所能给予行动提供的指导,他尤为强调在法律体系中正义标准的相对化。正义的原则不是纯粹抽象的理论,而是要在行动中既指导个人生活,又指导社会关系。魏因伯格将正义分析与目的和规范相互结合起来,从解释学的角度说明正义可以作为人类活动的理由,由此引出了以“形式的—目的论的行动论”为要素的实践哲学的概念。
这种实践哲学对理论的语句与实践的语句作了区分,实践性语句是不能通过任何纯粹认知的方式获得的,而必须引入价值观、目的论等因素,这便是这种实践哲学的非唯知论(24)非唯知论(Non-cognitivism),又称非叙述主义(Non-descriptionism),是西方元伦理学上的概念,其主要观点为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既不能用经验证明,又不能用逻辑论证,具有非认知性质。特点。然而非唯知论并不是反理性的,这种理性就是关于规范结构的合理性证明。“合理性”不等于“正确性”,“正确性”讲的是真,不包括对事物的评价;“合理性”与之相异,侧重点是评价问题。实践理性是一种包容了非唯知论的价值观、目的论以及涉及评价态度的合理性证明的综合性概念。为了更好地理解实践理性的作用,就需要分析实践中的行动理论与非唯知论是如何将事实与价值统一于制度的框架内的。
魏因伯格的行动理论是一种既是形式的又是目的论的行动理论,“目的”相较于“原因”更加贴近行动的本质,同时目的论的关系通过形式制度表现出来。制度法论的行动理论反映了社会现实因素在法律本体论中的独特作用,并通过一种解释学的方法来理解制度的事实面向。行动理论的框架得以解释个人与社会在实际生活中通过“行为”连接的相互关系,人们在行为的交互中形成集体性意向,来认同某些规则所附加的地位和功能,从而将其看作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在这种交互性事实的形成过程中,行动理论构成了实践理性的事实背景。
非唯知论在制度法论中的运用是对凯尔森价值相对主义的一种发展,实践认知或者是纯粹形式的或者是经验性的,均无法为规范的实质正确性辩护。因此,魏因伯格认为要从经验上不言而喻的直觉中,通过表明态度的论点,来作为实践推理的支撑,并将其视为人类学上的事实。人们的态度实际上要在以合理性为参照的个人选择的过程中实现,这种选择要受到包含价值性观念的制度的制约。非唯知论在否定绝对价值的同时又离不开对价值因素的运用,价值对实践理性而言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存在,更贴切地说,是一种作为背景的存在,这构成了实践理性的价值背景。
因此,通过在制度性框架之下的解释学分析路径,实践中的行动理论与实践推理的非唯知性构成了实践理性的事实与价值背景,实践理性的概念正是在事实和价值的背景中得以理解和阐释的。
三、对制度法论法律实证主义价值论的反思
如前文所述,价值论领域的“休谟问题”在法律实证主义的语境下被精细划分成了两个层次的三个问题。首先,在“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上(关系层),包括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分离命题),以及事实与规范的关系问题(规范命题);其次,在“是”到“应当”的推导问题上(推导层),涉及如何从“实然”的法律规范中寻找“应然”的正当性来源问题。本文将分别对照“休谟问题”演绎而成的三个子问题,反思制度法论法律实证主义价值论对“休谟问题”的回应。
(一)制度法论是否坚持了法律与道德的二分
在法律与道德相区分的问题上,麦考密克定义法律实证主义的第一个原则:法律的存在不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任何特定的道德价值。虽然制度法论似乎明确坚持分离命题,但其真实态度有待考察。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根本的理论分歧在于对于法律存在之性质的认识不同。亚里士多德、厄斯金(Erskine)(25)John Erskine, 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Scotland(1st ed.,Edinburgh,1795),esp,I.i.、孟德斯鸠(26)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Is ted,Geneva,1748;tr. and ed.by Thomas Nugent, Sub. nom. The Spirit of the Laws ,New York,1949),Vol. I, p.2.、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27)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1st ed.1765),esp,pp.38-40.等不同时期的政治与法律的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法律的存在必须以某种形式扎根于自然法;近代以来,边沁首先强调法律的“实证性”,否认法律的存在是以道德为前提条件的,这便意味着法律实证主义的第二个原则:法律的存在有赖于它们是根据社会中人们的决定创立的,也即法律的社会来源原则(28)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Oxford,1979), p.152.。哈特是对法律的社会来源原则进行改良的集大成者,他反对奥斯丁和边沁对规则所作的外部的、行为主义的描述,而主张在理解规则的性质时必须采用一种“内在的观点”,在理解法律时要研究人们之间的态度。
然而越是沿着哈特的进路去分析“内在的观点”,便越发现规则在哈特的视角下必然构成或者有助于价值,这便引起了与法律实证主义第一个原则的矛盾,由此引发了疑问:规则是否必然扎根于价值?为了解决这个疑问,麦考密克沿用了哈特解释学的方法,并通过解释认识性因素与意志性因素在内在的观点中的关系,完成了对哈特理论的改进。具体而言:第一,对于作为解释学研究者的法学理论家来说,其力求实现的是用“内在的观点”来理解法律,即使他本人完全否定法律中内在的价值。由此,对规则的构造中所可能包含的价值因素的适用由 “认同”转化为了“理解”,价值可以不作为前提,而是作为可以被理解与诠释的背景而与规则发生联系。第二,作为专门化规则系统的法律与道德有不同的特点,法律由于规则体系的不断完善而制度化,而制度有其以官僚体系为连接的国家强制力的支撑,以至于法律的有效运行并不需要社会公众的一致认同。由此,公民的道德概念与官员们的法律概念成了两种相区分的东西,法律的实际有效性是道德无涉的。这两点共同表明,把法律建设在特定的普适性道德原则之上的任何尝试都将是无法实现的。
在麦考密克的理论构建中,法律并非要优先于道德,而是要在法律秩序与道德秩序相区分的前提下,以价值作为“理解”的背景而与规则发生联系,而法律则在这种专门化的规则系统中表现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形式。因此,制度法论似乎并未违背法律实证主义的两个原则,法律与道德在制度法论的语境下是分离的。但是,仍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法律原则”,法律原则被麦考密克认为是价值和规范的汇合点,进而也就是法律与道德的汇合点。接下来,应如何理解法律原则的性质呢?其实,法律原则的概念更多是作为一种中介物,既承载着价值观念的因素,又能够为具体的规则或法律制度提供一以贯之的目的论背景,进而使得规则体系完成自身的合理化证成,最终结果是冲破了传统法律概念的束缚,赋予了法律体系的开放性。因此,法律原则在制度法论的引用并未触及法律实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而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规则与价值是如何在法律体系的内部实现联系与作用的。
综上,制度法论基本上坚持了分离命题的基本立场,法律与道德虽然在多种意义上彼此联系,但这种联系不足以成为否定实在法有效性的全部证据(29)余涛认为麦考密克在其后期的著作中否定了“分离命题”,但其实是对“分离命题”的概念进行了替换,本文以哈特“弱分离命题”的概念范畴为标准,认为制度法论的主张并未违反“分离命题”。参见余涛:《法律制度理论的后实证主义面向及其困境》,《法律科学》,2020年第4期。。
(二)“制度事实”是否混淆了事实与规范
在事实与规范的关系上(规范命题),制度法论对休谟问题的回应值得我们探究。魏因伯格对规范的描述有诸多路径。他首先将规范理解为“思想”,认为规范是一种客观意义上的思想,是从意识的过程中抽象得来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可以用规范—逻辑的方法加以分析;紧接着,规范又是一种“思想—实体”(thought-object)(30)“思想实体”(thought-object)与“物质实体”(material object)相对应,具体参见M.A.B.温苏埃塔:《新制度主义、法教义学与法社会学》,郭栋译,载《法理——法哲学、法学方法论与人工智能》,第5卷第2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59页。。“作为思想—实体的规范与其他种类的思想客体区分开来的特点,可以通过语言学分析来推敲,也可以通过考虑规范性语句的实用功能,特别是与陈述性语句的实用功能相比较。”(31)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5页。最后,规范又是一种可以从“作为现实的规范”的角度加以考察的现象。“思想”强调规范的非物质性,“思想—实体”强调规范由规范性语句定义下所具有的“决定行为”以及“评价”的实用功能,是规范的实质属性,而“作为现实的规范”也并非将规范与物质现实直接画等号,而是为了对物质现实和理想实体之间的功能关系的理解而进行的概念划分。
在对事实概念的描述上,魏因伯格提到,“一个规范不是一个物质实体,不是借助于观察设备就能直接或间接地观察到的某种东西”(32)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2页。。若将事实理解为“物质实体”,那么制度法论便承认了事实与规范的二分命题。但在制度法论的视角下,事实显然有更宽泛的含义,麦考密克将事实分为“原始事实”与“制度事实”,原始事实与物质世界的有形存在有关,可以用纯描述性的语句加以区分;而制度事实虽然在现实世界也有诸多的物质附属物,但却不仅仅作为物质实体而存在,“世界杯”显然要比其作为一堆金属的物质实体有更重要的意义,对这种意义的解释需要借助规范性的语句并依赖于人的理解。
制度法论对事实与规范相区分的态度是模糊的,这体现在其对规范与事实概念解析的层次性上。规范既可以是“思想—实体”,又可以是“作为现实的规范”;事实中既有“原始事实”,又有“制度事实”。若从第一种含义去理解,那么显然规范与事实是相分离的,但在制度法论的语境中,规范有事实层面的含义,规范可以是“作为现实的规范”,而事实也有“制度事实”的类型,对制度事实的理解是在规范层面上的理解。制度法论把规范与事实在概念上作了一种交互式的延伸,这种延伸无疑是精巧而细致的,企图通过“原始事实”与“制度事实”的二分,以实现事实概念的社会现实性与法律规范性的融合。但这种处理方式是粗糙的。
总而言之,制度法论在应对规范命题时的内在矛盾暴露无遗:它既要遵循规范与事实的分离,又在不断尝试混淆彼此间的界限以增强自身的理论解释力。
(三)制度法论是否违背了“休谟法则”
在“是”与“应当”相区分的层次上,制度法论坚持了法律与道德的二分(即“分离命题”),却混淆了事实与规范的概念(即“规范命题”)。但“是”与“应当”相区分只是“休谟问题”的第一个层次,更重要的是从“是”到“应当”的推导。在法学的语境下,对“休谟法则”的回答也就转换成了应当如何解释法律规范性的来源,如何从“实然”的法律规范中寻找“应然”的正当性来源,法律实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总是面临着种种挑战。它既无法像自然法一样借助于神圣的前提假设,又不愿将法律理解为仅仅是专横权力抑或暴力强制的产物。如此,余下的解释路径或者是以附录式的独立内容来加以修饰,如哈特“最低限度的自然法”,或者是在事实的领域寻求规范的正当性基础,麦考密克和魏因伯格所选择的正是后一种。制度事实的概念最先来源于约翰·赛尔,赛尔认为“许诺”是一种制度事实,一种不借助于规范性语句的纯粹描述性的事实,而许诺是以非规范性的规则加以界定的。因此,通过作为制度事实的“许诺的格局”的运用,以描述性的起点在逻辑上达成了“应当是这样”的结论。
然而,赛尔运用非规范性规则来界定制度事实的尝试无法达到一种逻辑上的自洽,“许诺的格局”必然包含着一种外部的支持作为其前提条件,制度法论作者在这一点上批评了赛尔对其所谓用“构成规则”来描述制度事实的狭隘性,进而主张一种更为宽泛而系统的规则理论来界定制度事实的范围,并且承认了制度事实的规范性特征。当我们仔细审查麦考密克的“创制规则”“结果规则”和“终止规则”时,不难发现,在这三种规则背后,是麦考密克法律制度规范性的立场,“结果规则”中所设定的作为法律后果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其本身就暗含了一种规范性的表达,即法律后果为主体的行为提供了规范性的理由。因此,抛开种种规则体系的修饰,我们不难发现麦考密克构建制度事实的逻辑理路:第一,将制度事实从概念上框定在事实的领域;第二,通过规则体系为其构建规范性的内核,进而实现事实性与规范性的结合。虽然制度法论不止一次强调规范性语句与陈述性语句的区别,“即在体系中不能从纯粹的陈述性前提推演出规范性语句”(33)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页。,然而,通过制度事实的概念将上面两个步骤连接起来,在事实的前提中通过规则体系演绎出规范性的内涵,实质上正是一种从“是”到“应当”。
在理论脉络上,制度法论是对哈特理论的发展,哈特用承认规则推导出法律规范,并用内在的观点联系了法律规范与事实,解释了法律规范性的来源。制度法论则更进一步,创造了一种既是规范又是事实的二元概念——制度事实,但如此仍无法摆脱从“是”到“应当”的逻辑困境,是对“休谟法则”的违背。
结语
抛开繁杂精深的理论阐述与晦涩难懂的哲学证明,制度法论讨论了事实、规范与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坚持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下,隐含着对价值论意义上休谟问题的回应。制度法论重新建构了“事实”概念,通过解释学的方法,试图以“原始事实”与“制度事实”的二分,将法律问题的复杂性限制在自身概念的涵摄范围内。但实质上,基于“制度事实”的本体论主张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制度事实”中的“事实”概念在适用中随意转向,混淆了规范与事实的界限;规则体系的演绎隐晦地认可了从“是”到“应当”的推理,违背了“休谟法则”。总之,制度法论虽然立意新颖,观点独特,但仍然陷入了事实、规范与价值的纠缠。
另外,制度法论企图包罗各流派之所长也未免显得自身方法论杂糅,其结论的脆弱与松散难以有效回应现实问题。因此,制度主义法理学若要在当代继续丰富其理论脉络,就应当将重点由“事实”转向“规范”,以法律的规范性论证作为理论分析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