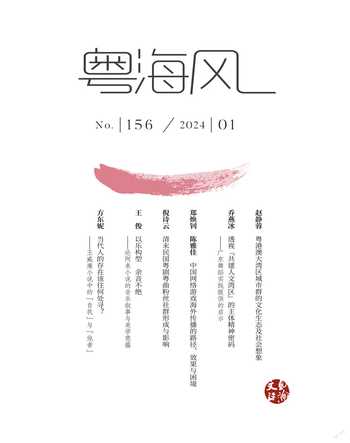以乐构型余音不绝
王俊
摘要:音乐为阿来带来无尽的启发,由是他将音乐内化于心,让其成为创作的底色,借此展示出对历史与生命的深刻思考。他曾多次模仿多声部性复调织体的特色,让作品呈现出交响的曲调模式,最新作品《云中记》更是与莫扎特《安魂曲》形成对位,获得了“乐章式叙述”的评价。乐章既成,旋律渐显,阿来借音乐叙事奏出“命运感”的旋律,其背后蕴藏着浓厚的悲剧美学意蕴,最终指向“净化”之审美意义,给予读者无尽的思考空间。以音乐叙事的角度观照阿来小说创作,可以更为立体地开掘出阿来文字中潜藏的丰富美学意蕴,达成文学涤荡灵魂,振奋心灵的审美意义。
关键词:阿来 小说 音乐叙事 美学意蕴 审美意义
音乐与人的现实生活密切交织,一方面以独特的形式反映着人类生存的精神状态,尤其是情感的历程;另一方面以声音形态反作用于人类的精神世界。阿来承认在爱上文学之前便先爱上了音乐,他曾言:“我们之所以喜欢音乐,就是因为音乐好像很简单就能直接突破我们的那些表征,用一种单纯的声音组合来让我们得到共鸣。”[1] 音乐之于他,像是乌云裂缝中透出的一线微光,充满了天启式的色彩,它早已内化于他的生命之中,成为他创作不可忽略的底色。那些动人的词句正如音乐海洋中四散的音符,最终被他谱写成和谐的乐章,突显出他独特的美学追求。借助音乐化的叙事,他得以表现出饱满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考,有关生命、有关灵魂、有关信仰。
巧妙的曲式与织体[2] 排列,是音乐打动人心的前提。文学作品中的段落与章节,宛如乐曲中的曲式与织体,在作品类别与主题的需要下,为作家有序建构,最终生成动人的篇章。音乐给予阿来无限的启发,他曾在创作时多次模仿多声部性复调织体的形式特征,让作品呈现出交响的曲调模式。在《尘埃落定》后记中,阿来提到,小说的结束就像“一个交响乐队,随着一个统一的休止符,指挥一个有力的收束的手势,戛然而止”[3]。这是阿来首次将小说作品与交响曲作比。作为由管弦乐队演奏的一种大型管弦乐套曲,交响曲可以借助各类音乐形象的对比和发展来呈现社会生活的矛盾冲突和人们的感情体验,以庞大的规模、丰富的音响和强烈的表现力著称。交响曲多声部演奏的特点,需要一种特殊的形式支持,即复调音乐织体,交响曲式小说也是如此。复调这一音乐术语早已被巴赫金创造性地运用于诗学批评之中,他将叙事线索和音乐旋律作比,将叙事声音与音乐声部对应。在复调小说中,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原本局限于一人的视角也被分置于几个完整的同等重要的视野之中。这正如复调音乐中的对位技法[4],即几条线索同时进行。巴赫金将复调音乐的“对位法”化为文学中的“对话性”,这不断启发着后来的小说创作及研究。在《尘埃落定》中,阿来便塑造了各色人物,让他们之间的对话形成复调,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是拥有独立观念的主体,并不完全为叙事者所控,作品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状态,读者得以多元的视角感受去分辨作者笔下那个复杂的世界。《机村史诗》延续了这种交响曲模式,并且仍使用多声部性复调织体,让不同性别、年龄、阶级、民族的人们用不同的叙述声音,演奏出一首宏大的乐章,故有评论总结,此作是“一部混沌的村落交响曲”。批评家认为:“阿来指挥自己演奏了一场音乐会,他努力让每个乐器发出饱满而细密的声音,他制造了一系列让人心领神会的声响,又用随之而来的另一个声响遮蔽了之前所有的余音。于是,人们沉浸在声音的不断更迭中不能自拔。”[5]
一、“乐章式叙述”:
《云中记》与《安魂曲》的对读
阿来对音乐形式的借鉴,在前期的作品中切实存在,但也呈现出较含混的状态。随着对音乐技法的深入领悟和创作的不断推进,他不再局限于对单一音乐形式的借鉴,其最新作品《云中记》便是最好的证明。阿来曾谈到,《云中记》的创作伴随着莫扎特《安魂曲》的演奏。作为莫扎特的名作,《安魂曲》的每一乐章都显露出创作者细腻且卓越的“词语描绘”手法,小到单音、连线、旋律,大到主题、结构,莫扎特用各种各样的音乐手法生动再现了宗教的内涵以及个人对于人性的理解,这或隐或显地影响了阿来的写作。在《云中记》新书发布会上,欧阳江河提到两者的联系,阿来总结:“《云中记》中,阿巴去安抚那些死后的魂灵。他去寻找它们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自我寻找,他想寻找死后的他。这一伏笔跟《安魂曲》有一个对位关系,它化成了小说叙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元素。”[6] 也因此,《云中记》第一次出版的封面有“乐章式叙述”之语,即为此书定位。据此,笔者将《云中记》与《安魂曲》进行对读,以期理解文本的音乐叙事。
《云中记》的故事始于阿巴回村祭祀、告慰亡灵,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在阿巴的独述中得以展现,作者以阿巴为线索,借倒叙、追叙、插叙等方式将每一户村民的经历串联,并使它们紧紧围绕主线,最终文本结构显示出板块分明、脉络明晰的特征。这与《安魂曲》的块状结构类似,具有清晰性、紧密性和规律性的特征。阿巴缓行于回村之路上的场景,如整部乐曲的第一声长叹,好似巴塞管奏出悠长忧郁的音调。接着作者以他对地震的回忆为引,将云中村的一切娓娓道来,正像乐曲中定音鼓及铜管的强调,也伴随着人声四个声部依次由低到高,遞进演唱。阿来用灾难与迁移的痛苦记忆奠定了小说悲壮的底色,侧面突出小说主题——安魂,这种安排使人联想到《安魂曲》安息之主题。而小说的第二章则像是音乐结构类别中的二重赋格曲,作者设置“第二天和第三天”两个部分:第二天阿巴进村向死去的村民宣告自己的归来,同时在对旧事物的观察中展开回忆;第三天阿巴来到水磨坊外告慰妹妹的亡魂,由此他回忆起童年与青年时期度过的那些静谧而温馨的时刻。这些往事的回忆和讲述节奏缓慢,音调低沉,同时饱含温暖,为乐曲的升调作出铺垫。
小说的第三部分作为叙事的高潮,描写了五年前灾难发生时的可怕情景,那日也正如《安魂曲》中的审判之日。莫扎特曾用四声部合唱,以快速齐唱的方式,表现简短但激昂的旋律,同时在乐曲中加入许多与音程不协调的跳跃和半音。他借助语调化的旋律和迅速跳动的音区,突显人们在末日时的恐惧。又以突出的鼓号声和急剧滑动的弦乐声完成强势的伴奏,同时辅以阴沉的颤音,营造出不安定的音乐氛围。阿来则以简洁却铿锵的笔触书写了灾难来临之日大地震动、房屋倒塌的可怕场景,其时哀声四起,仿佛乐章中狂乱的人声声部,使读者感受到长歌当哭的苦楚与深远刻骨的悲戚。在《安魂曲》中,小提琴作为一个重要的线索贯穿全曲,连接不同声部,而阿巴正如乐曲中的小提琴伴奏,用逐户祭祀的历程接连展现了各户村民的身世经历,这些故事宛如整个乐章中的一段多声部合唱,烘托出凄婉的氛围。最后,在阿巴的祭祀结束时,人声终于消失,大地归于沉寂,文字凝聚成庄严肃穆的音响,显示出光辉温暖的格调,表达出人对神明庇护的期望以及对安息的渴求。
祭祀完成后,阿巴来到故居,回忆起自己曾与母亲、妹妹度过的美好岁月,这段仍像是乐章中的过渡段落,为接下来的另一个高潮作出铺垫。它呈倍速行进,在慢板内部制造张力。同时,阿巴与家人的幸福往昔同当下天人两隔的遭际形成对比,更显示出他无根可依的凄惶境遇,让人联想到《安魂曲》中的唱词——“我还向谁去求庇护?”于是他展开了对山神的歌颂与对苦难的悲诉。在五年前定下的祭祀山神的日子,阿巴独自完成了未竟的仪式,他在记忆中还原了往昔的繁荣:那些飘扬的风马、尖利的长箭、五彩的经幡、燃烧的火焰、盛装的男女伴随着雄浑的古歌,共同组合成一首神圣的颂歌。这不禁让人想起《安魂曲》的中段乐章《威严的君王》,此章作为所有乐章中最神圣的乐章,先借乐队营造出一种恢宏的效果,随之引入有力的合唱,表达对君王宽厚仁慈的无上赞颂。后主题又转回与前面所有乐章相同的一种哀戚悲凉的感叹,强烈的对比表现出君王与普通民众的悬殊地位,同时也可能包含了民众希望被君王拯救的一种情绪。小说中,阿巴也在不断向山神进献马匹与弓箭,希望阿吾塔毗如传说一般,带领他的子民走向繁荣,庇佑他们繁衍生息。但雪山与神明的沉默让这场盛大的祭山仪式最终变成一个人的狂欢,神圣的颂歌终化为寂寥的哀叹。
小说的后半部与之前不同,改以“月”为计时方式展开叙述,篇幅从细说一天变为漫谈一月,提速展现了更多内容。小说叙事的重点也从回忆回到现实。从此处开始,文本与《安魂曲》不再处处应和,更多是情感的共鸣。多重因素的影响驱动使作家演奏出了自己独特的曲式。第一月,阿巴回旧居清理家宅,带侄子祭拜母亲,并同他交涉下山的问题;第二月,阿巴回忆了自己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转变为真正的祭师的历程;第三月,阿巴得知移民村村民敲诈游客的事情,同时了解到仁钦对此事的处理方式与事件的良好结局;第四月,阿巴选一吉日去祭奠被遗忘的谢巴家,同时与地质调查队的余博士交流,共享了各自的知识系统;第五月,断了腿的央金在废墟之上舞蹈,将自己的悲伤化为一场博人眼球的表演;第六月,中祥巴在灾区开发热气球项目,试图利用人们的好奇赚取钱财。在六个乐章的平稳过渡后,《云中记》的终章到来,央金放弃了在节目中利用云中村煽情的功利行为,中祥巴也忏悔了自己唯利是图的生意,阿巴在经历了一场大喜大悲后,终觉完成使命,选择随着云中村一起坠落,此时他已获得了灵魂的救赎,这也与开头呼应,小说因此化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恰如《安魂曲》的首尾应和,共同达成了圆满的境界。
二、“命运感”旋律:悲剧美学的体现
乐章既成,旋律渐显。有学者指出:“阿来的小说,回响着一个既复杂又单纯的旋律,在这块古老闭塞、空旷丰饶的土地上,传统的巨大力量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文明与愚昧的碰撞、社会进步与个人命运的错位等悲剧,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不管人的一生和命运做过多么坚忍的斗争,最后都会必然归于毁灭。阿来曾解释说,这就是‘命运感的主要含义,也是小说的基本色调。”[7] 考察阿来小说可以发现,他偏好展现川边藏族村落由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过程,也因此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情感。对于时代前进而人的思想却因循守旧的景象,他表现出批判与反思的态度;对于现代化进程带来社会巨变的同时却冲击破坏原生态社会中纯洁优良成分的现象,他又表现出惋惜与悲悯。这种矛盾的情感使阿来得以奏出饱含“命运感”的旋律,也让其小说呈现出浓郁的悲剧美学意蕴。
悲剧作为人类审美活动中的一种基本审美形态,是人类与自然、宇宙以及社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对立时形成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不是悲哀、悲慘、悲痛、悲观或死亡、不幸的同义语,而是人生中严肃的事情,因此他将悲剧纳入美学范畴,与日常语言中的“悲剧”区分。其后,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哲学家分别就各自立场对悲剧进行了分析。马克思与恩格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深刻揭示了悲剧的社会根源。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在人类历史辩证发展的客观进程中,悲剧冲突不可避免,它作为新社会制度取代旧社会制度的信号,源于新旧两种社会阶级力量和两种历史趋势的矛盾,是新旧力量矛盾冲突的必然产物。据此马克思与恩格斯将悲剧冲突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新事物的悲剧,另一是旧事物的悲剧,旧事物的悲剧发生于当它“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世界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8]。
《尘埃落定》展现的情境,显然符合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悲剧的第二种概括。小说以土司制度的消亡为主线,围绕末代土司部落的内乱外患和繁荣瓦解展开描写。土司们的钩心斗角、男女间的爱恨情仇、财富与灾难并举的罂粟迷乱,先知与愚昧、温情与杀戮、战争与联合、发展与消亡,这些元素在作者的精心营构下奏出一曲悲情的土司王朝挽歌,为读者带来心灵的震荡。而作为掌管部落军事、政治与经济的大权的统领者,土司们的精神生活粗粝贫乏,对世界的认识并未随着历史发展而向前迈进,反而不断退化委顿,这导致在他们领导下的社会,也不可能有所进步。这种历史的停顿造成这个以强悍自称的族群在频繁的征战中人口减少且财富损耗,生产力和精神都日渐枯竭。同时正如马克思所言,旧事物的悲剧也可能产生于旧世界的内部矛盾对抗。部落曾经的合作伙伴国民政府为了充实军饷,扩军混战,不择手段,命黄特派员带来罂粟种子和现代武器,用军火与白银诱使土司们大面积种植罂粟,最后造成此地粮食短缺,饿殍满地,连年混战,尸横遍野。在混沌与动荡中,这片古老的土地被迫接受了贸易、革命、战争,完成了颠覆性的重构,最终被卷入历史长河之中载沉载浮,土司制度也在人类历史辩证发展的客观进程中走向了悲剧性的灭亡。
与《尘埃落定》不同的是,《机村史诗》系列侧重描写文化更迭之际个人的悲剧,在此作中,阿来始终保持着反思的姿态,用一种悲悯的笔调记录了文化的消失和个人的迷狂。在阿来看来,“一种文化——更准确地说是生活与生产方式的消失,对于一些寄身其中的个体生命来说,一定是悲剧性的”“当旧的文化消失,新的时代带着许多他们无从理解的宏大概念迅即到来时,个人的悲剧就产生了。我关注的其实不是文化的消失,而是时代剧变时那些无所适从的人的悲剧性的命运”。[9]《随风飘散》作为系列小说的首篇,基调低沉哀婉,像是乐章的序曲,以少年格拉在传统信仰逐渐崩塌的古老村落被歧视、被侮辱、被误会,最终含冤而死的故事诉说人性冷漠荒诞的异变,神灵远遁的时代不仅让人们失去了心灵的寄托,也让其失去了慈悲的情怀。《天火》调性高昂,正像是乐声逐渐攀升。作者借巫师多吉之声描述了特殊时期机村的一场天火与众人救火的过程,其间穿插展现鼓动的政治与人们迷狂的欲望,以突显其时人心的失序。《达瑟与达戈》韵律平稳舒缓,展示了达瑟与达戈这两个性格迥异,却意外交情深厚的“时代可怜人”的经历,达瑟逃离尘俗,寄居树上与书为伴,达戈则在爱情蒙蔽与人性异变的情况下,背叛原始戒律与现实法律,最终失去性命。《荒芜》可以说是系列小说的第二个高潮,其呈现出激越的曲调。作家以驼子在时代变迁下产生的一系列身份转变与心灵升华过程,串联历史异象,同时借几个年轻人在土地荒芜、泥石流频发的时期寻找传说古国的经历,表现人们在人性混乱时期对纯净家园的不懈追求。《轻雷》又是高潮后的一个过渡,乐声持续和缓,其下却有暗潮汹涌。作品通过拉加泽里这个正直聪颖的少年堕落的过程展示了时代新变前夕人对利益的疯狂追逐以及对自然的破坏,批判了经济时代金钱至上的观念与乱砍滥伐的行为,后借其改过自新的行为,呼唤人性的纯善。《空山》宛如乐章的结尾,表现出低沉渐隐的特征。作者以归乡人的形象叙述了现代化进程中藏边村落的巨变,抒发了自身对民族传统失落、生态情况恶化的痛心,最终彰显出对生态文明重建的展望和对自然回归的期待。
面对悲剧,阿来希望从本民族历史的长河中找寻出路。在《格萨尔王》中,他借说唱艺人晋美之口,讲述了格萨尔王从降生到除魔、从称王至升天的故事,展示了藏族原始部落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格萨尔英雄史诗的重唱,复现民族曾经的辉煌。但英雄悲剧性的命运,让作者再次认识到,那个开阔雄伟的时代终已远去。神子崔巴噶瓦身负扫妖除魔、拓土开疆的使命来到下界,却在幼年就遭到放逐。其后他力挽狂澜,带领民族不断发展,最终平定天下,成为国王,却被人间的琐事牵绊,妃子争宠让他进退失据,血缘的亲疏让他失去公正。同时他可悲地发现,魔永远无法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也不曾停止,就连他努力打下的江山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消逝。因此他感到幻灭与虚无。作为格萨尔史诗的传播者,晋美也与他故事中的主角一样,遭遇着被时代冷落的命运,被误解,被放逐。物质的发达与精神的堕落同时发生,终于,阿来承认“血性刚烈的英雄时代,蛮勇过人的浪漫时代早已结束。像空谷回声一样,渐行渐远”[10]。現代化的推进,就像是马克思1857年在《印度起义》中描述的神车,身载毗湿奴大神,是世界之主意志的象征。神车过往的路旁伏满朝圣男女,神车神圣无比,一往无前,路边虔诚的信众纷纷投身于车下,用肉体的消亡换取灵魂的超度。人类自得于物质的发展,却忘记了对自然的敬畏、文化的守护与人性的净化。吉登斯曾总结道,现代社会的特征为断裂性和两重性,它为人类开辟了生存空间,换来了丰厚的物质生活,也为人们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道德沦丧等问题。现代社会的变革,总是呈现出悲喜交加的后果。于是阿来以人文主义的立场,在作品中回望着传统文明的消亡,并在其中表现出对现代的审视。
三、“净化”:审美的意义
但阿来也澄清,这种回望,“并不是在为旧时代唱一曲挽歌,而是反思。而反思的目的,还是为了面向未来”[11]。他明白文明的转变不可或缺,关键在于如何克服转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实际上,悲剧在作为美学对象时,最终目的并不是让接受者与其共苦。悲剧美学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不仅会引发恐惧和怜悯,悲剧情节还能使观众认识到灾难的必然律,这种认识最终“净化”了观众此前感性混乱的恐惧和怜悯等感情,进而获得了知识,而这便是悲剧所带来的“快感”。在这一点上,悲剧与音乐相仿,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八卷中提到:“有一些人很容易产生狂热的冲动,在演奏神圣庄严的乐曲之际,只要这些乐曲使用了亢奋灵魂的旋律,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如疯似狂,不能自制,仿佛得到了医治和净化。”[12] 由是阿来小说的音乐叙事与悲剧美学内蕴便共同达成了“净化”的审美意义,其小说最终化为一段段婉转空灵的旋律,在读者心灵绵延,促使他们深入思考历史与生命,喧嚣的灵魂也因此平静清明,复归本真。就像阿来曾经谈论音乐时所言:“……现在,音响里传出最后一个音符,然后便是意味深长的寂静。而且,我始终相信,这种寂静之后,是更加美丽和丰富的生命体验与表达的开始。”[13]
另外,悲剧的“净化”还有一层含义,它可以凭借对人类意志的激发,提高人的品格和精神境界,使人产生审美愉悦性。“悲剧给人产生悲哀的感觉,但同时给人产生力量的感觉。这种悲哀与力量的混成感觉,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悲剧精神。”[14] 这种悲剧精神可以使人类在面对不可抗拒力量时感受到个人的力量,人类的主体性只有在“这没有最终胜利的希望但又永不妥协的奋斗中才表现得最充分”[15]。因此阿来始终努力挖掘民族的美好品质,不论是对格拉怀有悲悯之心的额席江奶奶、为村民奉献自我的巫师多吉,还是守候机村森林的崔巴噶瓦、求知若渴的桑吉、坚守学术的王泽周、坚持本心的翁波意西、心灵质朴的晋美,都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希望。阿来意图通过这些美好的人物,让人们在现代化浪潮中沉浮的同时,领悟到高尚人格的可贵,洗净灵魂的迷狂。在《云中记》中,阿来加强了这种“净化”,此作虽然以灾难与死亡为审美对象,却着重表现了人类在面对自然和命运时强大的精神力和生命力,突显了人类的勇气与尊严,赞颂了生命的庄严与崇高。阿来在对逝去生命进行缅怀的同时,理性审视死亡同时昂扬歌颂生命,这让作品自然流露出救赎与温暖的意味,具备了一种超越性的力量,故批评家总结,此作“有着悲剧的美学逻辑”,同时,“悲剧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生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16]。
突如其来的地震覆灭了古老的村落,也让主人公阿巴见证了众多村民的伤亡,在众人精神崩塌的情形下,他勇敢挑起祭师安抚灵魂的重担,记熟了仪轨和祝祷词,学会了用麦面和糌粑制作施给鬼魂的食子。他在废墟前击鼓摇铃,高声祝祷,祭祀山神,安抚鬼魂。他的行为令人感到一种心灵的震颤。这种行为不仅超度了亡灵,更抚慰了幸存者的心灵,让死者安息,也让活人坚强。云中村集体迁往移民村后,他再次担起祭师的职责,选择回到云中村,直面逝去的生命,告慰每一家的亡魂。在阿巴的观念里,生者得以直面离去之后,亡魂也要面对消逝,灵魂若是身怀执念,囿于尘世纠葛,便会长留世间。对于云中村那些遭受无妄之灾的灵魂而言,他们或许无法自己消解这份惊慌与怨怼,进而游荡于生死边界,即将滑落的云中村将会永远困住他们,使其变为永世的恶鬼和游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阿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与云中村以及云中村的亡魂一起坠落消亡,在另一个世界抚慰那些受伤的灵魂。在一家一户行走祭祀的过程中,生者释然,在无尽的坠落之中,亡魂解脱,这样的选择体现出阿巴对于消逝的坦然无惧,某种更加神圣的东西已经超越了生死的限制,让他愿意献出生命,他不仅救赎了自己与幸存的人们,还安抚了一整个民族的灵魂。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要描写比现实中更美好的,同时又是“与我们相似的”人物,再通过他们的毁灭引起观众的悲悯和畏惧,并从积极方面给人以“净化作用”。阿来塑造阿巴这一人物,并让他为信仰献身,符合悲剧美学与其指向的“净化”意义,所以阿巴的结局,并不是结束,也不代表沉重与压抑,而是灵魂升华后的清净与安宁。借助阿巴独特的身份及信仰、思想及行动,那些被遗忘的文化习俗、社会秩序、精神法则也逐渐于乡民心中复归。这些无形之物抚慰心灵、修复人伦、引导灵魂,在新的社会文明建设中有着重要影响。正如阿来自己所言:“巨大的灾难,众多的死亡当然是让人‘语还哭的,但灾难的书写不能仅止于绝望,更要写出‘行且歌的不屈与昂扬。”[17] 面对灾难与死亡,阿来选择让时间沉淀惊惶、恐惧与绝望,努力救赎过往,《云中记》的内核,必然是超越悲情的哲思。
而救赎何来?阿来也着力书写了人民政府救灾的作为和重建的努力。他用仁钦这个人物的经历串联起灾后村落重建的历程。如果说阿来将对死亡的思考寄托于阿巴这一角色,那么仁钦身上则蕴含着阿来对生命的希望。在天灾面前,他无暇顾及自身伤病,主动挑下灾后重建的重担,组织村民抗灾自救,移居搬迁,复原村落,众人的误解与抵制从未撼动他的初心,他始终以坚韧与耐心的姿态应付复杂的局面,同时解决百姓各种需求。当搬迁遇到困难时,他逐家走访,为村民详细科普地理知识,让其明白迁移的必然性与紧迫性。为了在灾后发展村落经济,他努力开发特色旅游,临危不惧,随机应变,于是许多困难迎刃而解。故事的最后,仁钦从村中带回的那株寄魂的鸢尾也终于盛开,在阳光下彰显出蓬勃的生命力,昭示未来的希望与光明。通过高尚人格的塑造,阿来让读者看到一種在至暗与至明中始终蓬勃的生命姿态,于是小说逐渐化为一首救赎生命、安抚灵魂的颂歌,驱散痛苦与彷徨。在不绝的乐声中,道路趋笔直,灵魂得清净。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注释:
[1] [6] 阿来、欧阳江河:《〈云中记〉献给地震死难者的安魂曲》,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9/0702/c405057-31207134.html,2019年7月2日。
[2] 曲式与织体:音乐结构概念有两种,一种是指时间上的结构,专业名词是“曲式”。曲式是音乐作品的总体结构形式,《音乐百科词典》中将其界定为“音乐的逻辑结构;音乐作品赖以写成的形式规范”。音乐的曲式按照传统音乐可以分为两大类,小型曲式和大型曲式。小型的包括一部曲式,二部曲式,三部曲式,复二部曲式,复三部曲式。大型的包括变奏曲式,回旋曲式,奏鸣曲式,套曲曲式,自由曲式。另一种是指音乐在空间上的结构,我们称之为“织体”。音乐织体,是为研究一段音乐在一定时间里同时表现出多少个不同层次的声音,这些声音由旋律还是和弦构成,以及这些声音层次之间的关系,它包括单声部音乐织体、复调音乐织体、主调音乐织体等多种形式。
[3] 阿来:《落不定的尘埃·阿来藏地随笔》,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36页。
[4] 对位:意为“点对点,音对音”,是复调音乐写作的基本技术。指把两个或几个有关但是独立的旋律合成一个单一的和声结构,而每个旋律又保持它自己的线条或横向的旋律特点。
[5] 付艳霞:《指挥一部混沌的村落交响曲——评阿来的〈空山〉》,《当代文坛》,2005年,第5期。
[7] 刘中桥:《“飞来峰”的地质缘由——阿来小说中的“命运感”》,《当代文坛》,2002年,第6期。
[8] [德] 马克思、[德]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9] [11] 阿来:《有关〈空山〉的三个问题》,《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2期。
[10] 同[3],第238页。
[12]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85页。
[13] 阿来:《从诗歌与音乐开始》,《青年文学》,2001年,第6期。
[14] 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上篇)》,《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15]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16] 晓川:《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研讨会实录》,《阿来研究》,2020年,第2期。
[17] 阿来:《关于〈云中记〉,谈谈语言》,《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