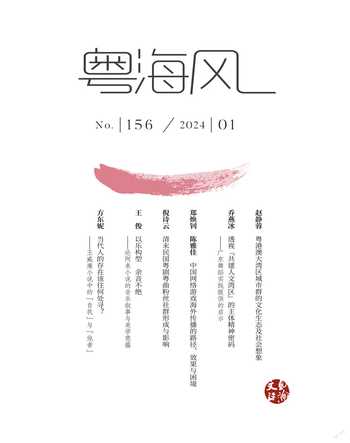普遍文学原理和本土文学经验之融通
陈斐
李笠(1894—1962),字雁晴,浙江瑞安人。1914年瑞安中学毕业后,一边担任塾师,一边刻苦自学。1924年出版《史记订补》,蜚声学界,被聘为温州永嘉省立师范国学教师。同年8月,被聘为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历任中州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等。曾在故里筑藏书楼“横经堂”,发起“知行社”“慎社”“瓯风社”等,与夏承焘等并称“永嘉七子”。学识渊博,兼治语言、文字、目录、校勘、训诂、经学、史学、子学等,能诗文,著有《三订国学用书撰要》《汉书艺文志汇注笺评》《中国目录学纲要》等。[1]
文学理论是李笠教学与研究的重要科目。他除了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国文科编过《文学概论讲义》(下文简称《讲义》)外,还著有《文学概论》(下文简称《概论》)和《中国文学述评》(下文简称《述评》)。《概论》为铅印本,乃“国立广州大学讲义”,卷首“弁言”落款署“民国十三年(1924)九月”,版式粗陋,错讹甚多。《述评》1928年8月由雅宬学社出版,比较精审,卷首《自叙》末云:“甲子之岁(1924),笠承乏广州大学‘文学概论讲席,病坊间无适用课本,辄体斯旨,著篇六编,客秋游梁,重为纂定。自知力不从心,疏舛弘多,商榷至当,盖有待焉。民国十五年冬月,雁晴李笠识于瑞安横经室。”“客秋游梁”指1925年因战事影响,“暑假后,转任中州大学(现河南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2]。《李笠部分著作目录》著录有“《文学概论》中州大学石印”[3]。可见,李笠是应授课之需而编写《概论》讲义的,他先于1924年9月完成初稿,在广州大学印行。1925年秋天后,又在中州大学修订重印。1926年冬天前,再修订为《述评》一书,于1928年8月正式出版。比勘《讲义》和《概论》《述评》三个文本的内容、结构和措辞,可以看出:《讲义》撰写晚于《概论》,早于《述评》,应是截取某一版本《概论》的前面三编删改修订而成的。再考李笠与商务印书馆的学缘:1924—1925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国学用书撰要》《史记订补叙例》《墨辨止义辨》等文;1925年12月出版《定本墨子闲诂校补》。《东方杂志》主编恰好为兼任函授学社国文科主任的钱智修,《讲义》极有可能是1924年9月至1926年冬天前,李笠应钱智修约稿撰著的[4]。其时李笠在廣州大学或中州大学讲授“文学概论”课程,已在学界知名。
在我国,“文学理论”不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一门课程,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其在大学正式开设,较早可以追溯至1920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梅光迪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5]。早先,国人主要通过译介了解这门新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和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影响甚大,而前者也明显受到后者和哈德森《文学研究入门》的影响。这些著作,为国人自撰文学理论著作乃至从事文学研究与评论提供了最基本的观念、方法、框架和问题意识。
李笠的文学理论撰著,即深受西学影响。他在行文中征引了温著,对其观点深表认同。不过,李笠的卓异之处在于,他对时贤易犯的抱残守缺、一味趋新或生搬硬套之病有着高度警惕,力求“旧闻新知”“商榷至当”[6]。其《中国文学述评自叙》云:“前人立论,既有时代观念之谬;而晚近作者,依附西学,土苴固有材料,又非得也。盖文学为情性之产物,义理无误矣,言语、文法恰当矣,其于情趣,不辨中外异撰、远迩殊途也,则秦人之炙,于我何嗜?故评价于一定规律之外,又当审查国情者也。”“总之,以时间言,文学之界义,今胜于昔也;以空间言,文学之情趣,近逾于远也……辄体斯旨,著篇六编。”可见,李笠既接纳外来文学理论之通则,也强调固有文学经验之殊性,希望既能彰明前者,也不抹杀后者。这种将外来理论“中国化”的努力,从温著翻译之时就开始了。译者为了便于国人理解,将书中的例证由西方文学作品替换为中国文学作品,并以“定义则意少而辞多,韵律则不合国情,体别又病其简略”[7] 为由,删去了原著之论诗一章,而以吴宓《诗学总论》替代,附录于卷末。李笠则更进一步,他虽然主要接受了舶来的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但尽量于打通古今中西的视域中辨析其与本土类似或相关观念的异同,以商榷至当,让普遍文学原理和本土文学经验水乳交融、彼此映发;其思理之透辟、脉络之条贯、阐发之到位,令人钦叹!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笠的论著比当时乃至今天的绝大多数文学理论著作都更为“中国化”。大概是自觉到了自己论著的这个特点,在正式出版时,李笠将书名由“文学概论”改为“中国文学述评”。这一改动,也致使今人误将其视为“文学史”著作,因此埋没了它在“文学理论”领域的独特而重要的学术贡献和启示价值[8]。
《概论》包括《正名》《分类》《沿革》《解蔽》《文学与人生》《文学与社会》六编。《述评》略有分合,调整为《何谓文学》《文学之分类》《文学之修养》《文学与个性》《文学与感情》《文学与环境》六编。从整体框架和问题意识看,也颇受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等西学论著之影响。《讲义》因为篇幅限制,只有讨论文学本身问题的《文学观念之嬗变》《文体之孳乳》《文学分类之商榷》三章,应由《概论》前三编删改而成,与《述评》前两编对应。
在第一章,李笠引述了温彻斯特对文学的界定:“书籍非皆文学也。必雄奇瑰伟、善载真道、深契人情,而后始为文学耳。”“其旨在传达思想,而以情为辅助之具,令有完备愉快之领会者,则其书为散体文学,如历史及评论是也;反之,若情感为初旨,思想缘之而入人心者,则其书为美文,如诗与小说是也。”前一句实际上是温氏转引的莫立《文学研究法》中的话。尽管温氏批评莫立此言“乃文学之描写,而非文学之定义……空泛、含混”[9],但因为温氏自己没有对文学下一简洁、明确的定义,只是阐明文学应具备“感情”“想像”“思想”“形式”四大要素,而莫立此言又吻合温氏主张,故被李笠误认,就实质说亦无大碍。李笠赞同温氏看法,《概论》曾明确说:“综论中国文学,其领土所至,当从章说,以文字为准。然不能谓无艺术又无情感者为文学也。换言之,即不合温氏文学条件之一者,去之而已。温氏条件,虽不明言艺术,然云‘善载真道,深契人情,非艺术之至者,孰克能诸。”[10]《述评》中,李笠还对文学下了个定义:“文学者,以美妙的文字、谐调的声音,传达人生之情感、思想、想像、人格者也。”[11] 几乎可以说是代温氏立言。
李笠以此种文学定义为致思基点,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嬗变做了梳理[12]。他指出,先秦时期,孔子、墨子等人,“以文学为语言之经修饰者”。秦汉时期,因文学为儒者所修,人们遂以部分代全体,“以文学为儒术之别名,扩狭义为广义”;又连带称儒者所习之“六艺”或其“一艺”为文学。魏晋时期,文学脱离儒术而独立,文学观念“亦由含混而渐臻明晰”,最大贡献为“文”“笔”之分。梁元帝、萧统等人,对于文学的“情灵”等内美和“翰藻”“宫徵”等外美皆有自觉。不过,其时刘勰、颜之推等人“先打破文、笔之分,而后牵合六艺,以归儒术”。刘、颜等传统派之说,因为“适迎合国人尊经复古之心理”,故“战胜文学独立论者”。此后韩、柳倡古文,宋儒主“文以载道”“文、笔之分遂不为人注意”“文学观念由明晰而陷于紊乱”。清代阮元等重提文、笔之分,欲攻传统派,但因为依附孔子,胶于形迹,难以折对手之心。晚近舶来之温彻斯特等西人的文学观念,与六朝独立派颇多相通之处,故应发扬光大。李笠仔细辨析了二者特别是“纯文学(情的)”“杂文学(知的)”与“文”“笔”的区别和联系,进而总结了我国文学不同于西洋文学的三大特点——“骈散随意,繁寡称心”;句末押韵,句中调声;限制篇幅,提醒研究者和创造新文学者不要轻言放弃。总之,李笠的文学观念主要继承自温彻斯特,既以狭义的“纯文学”为核心,同时也不抛弃含有文学元素的“杂文学”。他由此返观传统,重新发明了六朝独立派,并以之为皈依。李笠对中国文学概貌与原理的述论,即在此视域下展开。
第二章论“文体之孳乳”。李笠首先通观中西文学,指出:“文学演进之迹,无论何国,皆诗先于散文。”因为人类先有语言,后有文字,“诗歌之作,在声音之间”,故为一切文学之源。人类早先的所有著作,“皆不脱诗之形相”。散文则“由诗歌脱胎而出”,为“书契以后之文学”。接着,李笠分别论述了诗、文的流变。他认为我国“诗之流变,就形式言之,则有整齐与参差之别;就精神言之,则有诗乐之分合”,并勾勒了大概轨迹:“《诗》变为骚,别流为赋,骚一变而为五言诗、为乐府,再变而为律诗,三变而为词、为南北曲。”至于文之流变,李笠主要从骈、散着眼考察。他指出,早先文章本互用而不分,至六朝,骈文大盛,唐代韩愈提倡古文,散文“始成专门之业”,从此二派壁垒益明,亦各有流弊。
第三章为“文学分类之商榷”。李笠在评析前人分类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整体而言,他主张按“作用”分类。李笠指出,“古人作文,因宜制体,初无程律”,后人纂集篇翰,“因作用而为名称,因名称而为体制”。对此,《述评》有详细阐释:“从前篇什,只如散钱,后人取其作用同者,納诸一轨,以一公名统之,而后文学作品渐有条贯可寻。此公名者,昔人所谓文章体制也。”[13] 在李笠看来,这才是有意义的文体归纳与衍生途径。然而,历史未能如此理性地展开,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文有名异而作用同者,也有名近而作用异者,还有一名而兼数用者……前人的分类多拘泥于名称,因此治丝益棼。他认为,“文之为用,不外说理、记事、言情三种”,文学分类应“以三者为纲”。他还将“言情”与“情的文学”对应,把“说理”“记事”用“知的文学”统摄。[14] 这在当时,是重新发明传统以嫁接新知的常见作法。
把文学分为“情”“知”或“纯”“杂”两类,源于英国戴昆西“知的文学”(literature of knowledge)与“力的文学”(literature of power)之分。明治三十九年(1906),太田善南在博文馆出版的《文学概论》中将后者译为“情的文学”,分别将“情”“知”与“纯”“杂”文学对应。[15] 从此这个提法被国人辗转接受,在20世纪早期影响甚大。“说理”“记事”“言情”三纲,则既有本土渊源,也受西学影响。自真德秀《文章正宗》以来,已有论者将古文分为“议论”“叙事”两类。至清代,更有人增入“抒情”而成三类。如恽敬《与纫之论文书》分“言理”“言事”“言情”三类谈文辞气象,吴德旋《许叔翘文集序》将文章分为“记事纂言”“言理”“言情”三类。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洋、东洋文学理论、修辞学、作文教学著作,也多从类似理、事、情之维度审视文学或文章的分类或功用[16]。如太田善南《文学概论》将文学分为“纯”“杂”两类。前者“乃诗之别名”“要点在其为情的”“以感动为目的”,可分为“歌的形式(吟式诗)与读的形式(读式诗)”。后者“其要在其为知的”“以教导为目的”“可分为叙述文与评论文两类”。上述固有思想与外来观念嫁接融合,逐渐形成了“说理”“记事”“言情”之三纲说,并随着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姚永朴《文学研究法》、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刘咸炘《文学述林》等著名国文、作文、文学概论教材的流传广为国人接受。[17]
在“说理”“记事”“言情”三纲之下,李笠参考姚鼐《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的类目,辖以“赠序”“书牍”“传状”等文类,类下再分体。李笠强调:“文体与作用,颇不一致。有一体而仅有一种作用者,亦有一体而有二三种作用者,此中消息,不可不为之沟通。”对于诗,他分为“读式诗”“吟式诗”“协律诗”三类,类下辖体。前两个类名亦借自西学[18],但李笠结合中国文学实际作了调整并辨析了两者的差异,他说:“西洋以无韵者为散文诗,有韵者为律文诗;中国则无韵之诗是否成立,尚有问题……西洋诗以情为主,故小说亦入诗类;中国诗以韵为主……中国汉以后之赋、颂……虽有韵而不宜歌……则中国自有其特别之读式诗在也。”总体而言,李笠所谓“读式诗”只能用来诵读,如赋、颂、箴铭;“吟式诗”可曼声长吟,如五七言古、近体诗;“协律诗”则能配乐演唱,如乐府、南北曲。这种分法,大致也是按作用、体制区别的,只不过从音乐角度着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笠指出,文体名称有“正名”“别名”之分。“譬如史传之末所下评语:班固曰赞,荀悦曰论……刘昺曰奏……此亦同体而异名者。若以刘昺之奏,与汉世‘奏以按劾之奏同言,则不侔矣。盖前者为论、赞之别名,后者则为正名;别名亦可谓之嫌名,划之例外可耳。”这对于认识与研究古代文体,具有重要意义。类下所列诸体,李笠广采众说,斟酌至当,务使“名类之不可以假借,而后嫌名皆可依类就范,庶无纠纷之弊焉”。
《讲义》体现的李笠的一些研究理念,颇值得称道。比如,在分析阮元等人“欲攻正统派而仍以六艺为护符”,“不根据六朝文笔之说而扩充光大”之失时,他感慨道:“夫求证之范围宜广,远稽古初可也;辨章学术,则须取明晰时期,以免含混之弊,而收事半功倍之效。”[19] 批评曾国藩“推班固为骈文之祖”,失于附会时,他说:“今论骈、散之体,当以旗帜鲜明者为准……纯单之文,虽始于北周,而自韩氏之倡古文辞,始成专门之业,而与骈文之分界亦益清晰。”阐发“求证”与“辨章”两种治学理路的区别及要点,颇为精辟!再如,他指出,概念使用过程中,有以部分代指全体,进而代指其他部分的现象。汉代以前文学观念的嬗变即是如此。昭明《文选》的命名,也是用“代表之名,概括全部……《文选》之文,当文学之文,非文笔之文也”。这个思路对于我们研究概念史颇有助益。
《讲义》中的个别观点,《述评》有所修正、补充。比如,论文学观念之嬗变,《讲义》分为独立派、传统派、反传统派,误会时期、蒙蔽时期等。《述评》则分为华辞、儒言、文笔、古文、骈文、欧化六大时期。论文体之孳乳,《述评》指出,单、复之变,在文体现为骈、散,在诗体现为奇、偶:“律诗复多于单,绝句单多于复。律诗除首尾四句外,余语必偶;绝句则有‘二句奇二句偶与‘全奇或‘全偶之三体。”[20]《讲义》未论及诗。论韵文整齐与参差之流变,《讲义》认为:“风、雅、变骚,由整齐而至参差也;《离骚》之后,五言与近体承整齐之轨,词与南北曲衍参差之宗;故参差可承整齐之系,整齐不可袭参差之统。”并引朱熹和汪森之言以为佐证。《述评》则认为整齐与参差二派分行,皆由风、雅演变而来,并举律诗和词为二派代表加以说明;分析词时,亦引了朱、汪二人同样的话,但非朱而是汪:“由朱子言之,则词之发生,为自整齐化为参差;由汪之说,则词者自衍参差一派。今案汪说是也。”[21] 论文章之分骈、散,《讲义》认为“为偏颇而不健全,未足与于进化之例”。《述评》则指出,此乃“势积使然,倘亦文学进步之现象欤”!进而阐析道:“骈、散合一,固为文之常体。纯散纯骈,与夫骈多于散、散多于骈者,亦何妨并行而不背乎?文学本为艺术之一,艺术之派别,不厌其多;文章之格式,何惮于繁乎?苟能专攻,各有其美,排诋之心,自然不生。”[22] 当然,《讲义》也保留了一些《述评》没有的有价值的观点,重要者如第二章“文体之孳乳”开头“诗与散文发生之先后”一节、“诗之流变”节论诗乐分合一段等。
(作者单位:《文艺研究》编辑部)
注释:
[1] 李继芬:《李笠传略》,载俞海主编《李笠诗文选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226页;林吕建主编:《浙江民国人物大辞典》,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197页。
[2] 李继芬:《李笠传略》,载俞海主编《李笠诗文选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页。
[3] 俞海主编:《李笠诗文选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
[4] 本文所论李笠《文学概论讲义》,皆据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国文科民国间铅印本。
[5] 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6] 李笠:《文学概论·弁言》,广州:广州大学,1924年铅印本,第5页。
[7] [英] 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译例》,景昌极、钱堃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页。
[8] 任慧編《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作廿七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2册收录了李著,而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傅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生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和贺昌盛《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理论与批评著译辑要(1912—1949)》(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研究近代文学理论学术史的论著皆未提及李著。
[9] 同[7],第19页。
[10] 李笠:《文学概论》,广州:广州大学,1924年铅印本,第7页。
[11] 李笠:《中国文学述评》,雅宬学社,1928年版,第一编第14页。
[12] 李笠之前,杨鸿烈《文心雕龙的研究》(1922年)、《中国文学观念的进化》(1924年)等文已用“纯文学、杂文学及文学进化观念”来“梳理中国文学批评观念”,但不及李笠圆融、贴合国情。杨氏梳理参见张健:《纯文学、杂文学观念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复旦学报》,2018年,第2期。
[13] 同[11],第二编第1页。
[14]《述评》对“记事”略有调整:“纪事则二分其属,主实用者隶于前,富美感者系于后。”(李笠:《中国文学述评》,雅宬学社,1928年版,第二编第17页)。
[15] 参见张健:《纯文学、杂文学观念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复旦学报》,2018年,第2期。
[16]“说理”“记事”“言情”三纲说的本土渊源参见蔡德龙《清代文话研究》第五章《清文话中的文体分类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139页;受东洋修辞学、作文教学著作的影响参见陆胤《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第五章《古文门类的脉延——从国文选本到文学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87—353页。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学观念,三纲说受西方文学理论著作的影响更为直接、巨大,可惜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近乎空白。
[17] 如朱希祖1919年发表的《文学论》云:难者曰,吾国“文学范围,至为广博。鄙人二年以前,亦持此论,今则深知其未谛。盖前所论者,仍以一切学术皆为文学,不过分为说理、记事、言情三大纲耳”(原载《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朱希祖著,周文玖选编:《中国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78页)。刘云孙《文体之分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1919年第3期)主张从“形式”“实质”“功用”三个维度对文章进行分类。从“实质”角度,其把文章分为“纪事”“抒情”“言理”三类。
[18] 太田善男《文学概论》已有此提法(见上文,应源于欧美),后为国人逐渐接受。独应(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云:“夫文章一语,虽总括文、诗,而其间实分两部。一为纯文章,或名之曰诗,而又分之为二:曰吟式诗,中含诗赋、词曲、传奇,韵文也;曰读式诗,为说部之类,散文也。其他书记、论状诸属,自为一别,皆杂文章耳。”(《河南》第4卷,第5号,1908年)朱希祖《文学论》亦曰:“今欧美文学家大氐以通俗之语言为诗歌、戏曲、小说,而读式诗尤重于吟式诗,以尽人能解为贵。”(原载《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载朱希祖著、周文玖选编《中国史学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84页)。
[19] 钱钟书亦认为:“夫物之本质,当于此物发育具足,性德备完时求之。苟赋形未就,秉性不知,本质无由而见。此所以原始不如要终,穷物之几,不如观物之全。”(钱钟书:《钱钟书集·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01页)。
[20] 同[11],第8—9页。
[21] 同[11],第13页。
[22] 同[11],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