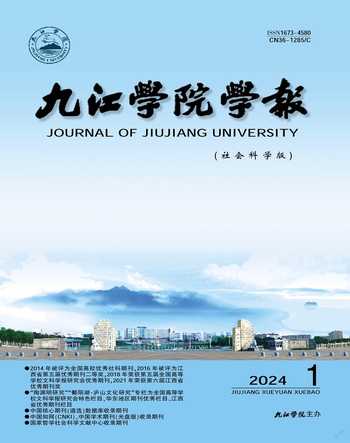后电影:一次“返魅”中的革新
张昊博
摘要:“后电影”是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出现的一种崭新的影像实践。部分学者认为,就总体趋势而论,后电影作为新的媒介技术深刻影响着主体的感知系统。其不再追求稳定的叙事结构,而是将重点置于引人入胜的画面奇观之上,并由此孕育出不同于理性思维的政治潜能。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人指出,后电影是向早期“吸引力电影”的一次“返魅”,二者间存在着若干相似的特质。但“相似”并不意味着“相同”,不能囫囵吞枣地将后电影视为简单意义上的“反者道之动”,其中依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变量需要去探析。
关键词:后电影;吸引力电影;“返魅”;数字媒介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24)01-0109-(08)
DOI:10.19717/j.cnki.jjus.2024.01.019
“后电影”(Post-Cinema)的影像实践经常呈现出时间退场且空间突显的印象,对此,有部分后电影学者指出,后电影是向早期“吸引力电影”(Cinema of Attractions)的一次“返魅”。例如近年来的《阿凡达:水之道》《黑客帝国:矩阵重启》《头号玩家》《失控玩家》等科幻片或动作片皆为此倾向的范例。不仅如此,在研究范式、范畴等方面,这些后电影学者几乎与早期电影理论家如出一辙,皆从电影的感性特质出发,强调电影之于人的感知系统的形塑,以及由此孕育的不同于理性思维的政治潜能。但是,由于技术水平、历史语境、主体构架等多重因素的差异,不能囫囵吞枣地用简化方式将后电影视为对吸引力电影的一次“反者道之动”(也就是麦克卢汉所描述的媒介冷热趋势的逆转),这其中依然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变量需要去探析。
站在辩证历史观的角度上,本文将通过以上所述的三个方面(媒介对主体感知系统的延伸、吸引力的倾向与新的政治潜能)详细讨论吸引力电影与后电影之间的异同,并指出后电影是在“返魅”途中的一次革新。
一、感知系统的延伸:身体意向性与亚感知情动
随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与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媒介不再被简单地视为人类主体与物质客体间的中介工具,还被纳入到人类的感知系统当中,作为人体存在的一部分,深刻影响着主体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换言之,媒介不仅帮助主体改造着客观世界,还以附加物的形式“嵌入”身体器官,重塑着主体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将媒介定义为“人的延伸”:“一切媒介均是感官的延伸。”[1]而唐·伊德在《技术与生活世界》中将人类与技术的关系设定为“具身关系”,并以此聚合体作为人类感知的元模型。在此理路下,回顾1895年12月28号巴黎咖啡馆内发生的事件,作为新媒介,电影必然在人类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那么,尺度之新又新于何处?毕竟与先前占统治地位的文字相比,电影仍然是视觉向的延伸。
匈牙利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认为,印刷术和电影分别塑造了人体器官间不同的协同关系:前者是依托文字的概念文化的表征,它削弱了人体视觉器官的感性强度以及需要诉诸于视觉器官的肢体语言的表达能力,将人类的思想情感通过“转译”浓缩至语言和文字当中,可见的思想由此变为了可读的思想;而后者是依托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等视觉性材料的视觉文化的表征,它以一种“返古”式的潜能恢复了人们对视觉性材料的感性注意,并通过“直译”的具象性来表达人类的思想情感,可读的思想由此变为了可见的思想[3]。在此,巴拉兹实则将电影与印刷术区分为理性与感性的范畴,强调了思维与感官的对立,而这种划分同时也昭示着电影与语言在认知层面上的区别。根据认知科学的原理,作为运动影像的电影(尤其是汤姆·甘宁称之为1906年之前的“吸引力电影”)属于低阶的心理认知层面,观众对于客体的把握具有直接性,不需要复杂的理知系统的介入,在直观中便能把握对象的全部内容;而文字属于高阶的语言认知层面,读者在接触文字时,需要通过符号性意向而非图像性意向与语言符号相对应,进而在从抽象的符号到经验的观念再到直观的形象[4]的熵增过程中把握文字的所指与意义。
由此可见,电影与文字尽管皆为视觉的延伸,但电影所延伸的是视觉的感性强度,是身体对印象的直接把握,用现象学的话语来讲便是“直观”。“直观”是现象学的核心概念之一,“直观”强调的是“悬搁”地把握对象的直接被给予性,是人体知觉器官与对象的直接接触。因此,“直观”便是身体的原初机能,是产生意向性的必要条件,也是建立主体的前提条款,即“我身故我在”。由此回看“一切媒介均是感官的延伸”这一命题,“延伸”便不仅和媒介的特性相关,也与人体器官的感知限度相關,它能够压制或提升某一器官在人类总体统觉中的主导地位,但无法逾越其限阈来创造一种全新的感知方式。正如薇薇安·索布切克所言:“摄影机好比一具机械身体,模仿着我们身体的知觉能力,正是通过这一相似性的转换,观众和电影世界之间才能建立意向性关系。”[5]电影与人体的合谋意味着自电影诞生之后,人类便要求通过与视觉的感知结构相匹配的表征方式去看世界:运动、透视、立体……与现实几乎拥有相同纹理的电影也理所当然成为了人类文化系统的主导样式。“我思”的问题也逐步让位于“可见”的问题,而与“景观”“拟象”等概念相关的探讨在这之后也逐渐浮出水面,并长期占据着理论界的中心范域。
如果说早期电影与人体感知的关系隶属于现象学的范畴,那么后电影所产生的效能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解构。部分后电影理论家对媒介现象学的观点进行了辩证的吸纳,他们同前人一般,同意新技术延伸了感知系统,但却将后电影与所谓“前个人化的身体”“后现象学的客体消解”“亚感知”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力图突破现象学直观意向性的具身感知,在超现象学的非感知层面辨析数字技术所促成的“后感知结构”。后电影所采用的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CGI、动态捕捉、绿幕/蓝幕等技术使其运作过程和处理的素材超出了人体正常的感知阈,尽管我们依然能察觉到影像,但其背后的二进制代码及其运作过程则处于我们的意向阈之外。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马克·汉森指出,数字媒介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不同于自然感知(现象学感知)的“算法感知力”,即一种先于知觉或超出知觉作用于我们的感性强度[6]。
那么,该如何理解这种逾越意向性的“算法感知力”呢?另一位美国学者肖恩·丹森在《疯狂摄影机、不相关影像和后电影情动的后感知中介》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在文中,他首先以尼尔·布罗姆坎普2009年拍摄的《第九区》为例,指出影片中那些无视点或视点混乱的摄影机镜头“偏离了人类具身建立的感知准则——基本物理引擎”[7],使得观众与电影间难以建立意向性的关联。由此,他将这些镜头命名为“不相关影像”,意指那些运作过程推翻了影像作为离散包装单元的本体地位,并将自身投射到我们自己对感知信息的微时间处理中,从而扰乱感知人类主体的相对固定性[8]的一系列后电影影像。紧接着,他指出,这些“不相关影像”在亚感知层面流动,以“分子”的状态对人的亚感知结构产生影响。“分子”是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以及《千高原》等著作中不断提及的一个概念,与“克分子”相对。在德勒兹那里,分子状态描述的是一种前个体化生命的欲望流动,这种欲望之流总是寻求超出任何社会体所能容许的更多的目标、接触和联系,追求“游牧且多音”而且非“隔离且单音的”流动[9],也就是德勒兹所谓的解辖域化的“情动”状态;而“克分子”则是条理分明的“树桩的”制域,其反对松散与无纪律,试图把一切异质化、差异性、边缘化的因素都规范化、系统化、合理化与等级化,以使其最终能够在理解与控制的范域内运行,即对欲望进行制码的辖域化。
后电影之所以具有分子的状态除了难以意向之外,还在于计算机的处理过程总是处于运动之中(如数字影像的渲染),而这与情动的状态相似。情动是被规训化的我思主体难以察觉的,它处于反应和行动之间的间隙,是场域内的力彼此之间不断的运动与互动。在此基础上,丹森用“新陈代谢”来指涉这一过程,强调后电影在非现象学层面通过情动将有机体与环境联系在一起,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的认知模式、行动方式与身体机能。后电影改变了不同场域内力的分配状况,更准确来讲,它强化了情动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进一步激活了有机体原有的机能与欲望。总而言之,后电影的后感知结构是尼采、伯格森、德勒兹、马苏米、拉图尔对新物质主义者式的力、时间、欲望、情动与量子等流动性因素的非意向性感知,尽管我们无法察觉到它们的存在,但它们却在亚感知层面组织了每一个场域。
二、吸引力的倾向:现代性的“震惊”与后现代性的“交互”
新西兰学者列昂·葛瑞威奇在他的论文《互动电影:数字吸引力时代的影像术和“游戏效应”》中对比了罗伯特·保罗1901年拍摄的《乡下人与放映机》和詹姆斯·卡梅隆2009年拍攝的《阿凡达》后认为,就吸引力本身而言,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10],画面而非叙事不仅在早期的吸引力电影,也在当下的数字电影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电影促推的关键手段。就叙事与奇观的对立而言,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构的。不过,这倒不是说二者间可以简单粗暴地画等号,正如葛瑞威奇在文中所强调的那样,数字电影一方面作为吸引力电影的循环发展,一方面又昭示了某些变化的趋势,二者分别表征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维度[11]。因此,不能仅通过画面表象来辨析吸引力电影与数字电影间的“同构”,还需要通过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语境来分辨其间的“异质”。
在甘宁的论述中,“吸引力电影”并非指一些罕见的奇闻异事、怪诞形象或异域风光,而是具有自反性的裸露癖电影。这些电影着眼于突出自身的视觉展示特性,而非建构一个封闭且完整的叙事系统。在此意义上,梅里爱电影中演员直视摄影机向观众致意的镜头便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戏剧幽灵的萦绕,或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而是对自身表现能力有意或无意的指涉,或者说是对摄影机机械性能的“炫耀”。换言之,是机器,而非具体的故事内容主宰着早期电影的创作实践,“早期电影观众去放映场所是去看被展示的机器的,而不是去欣赏影片。在演出海报上做广告的是活动摄影机,比沃格拉夫放映机或维太放映机,而不是《午餐》或《黑宝石快车》。”[12]
电影摄影机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其机械化的工作方式标识着现代性的经验。在一篇易被忽视的文章中,甘宁将吸引力电影的视觉经验称之为现代性的“震惊”体验[13]。震惊是甘宁借用本雅明的一个概念术语,在本雅明那里,震惊不仅是现代性的秘密,同时也是现代性与电影间的纽带。本雅明在对巴黎进行了“漫游式”的观察后发现,现代性所带来的全新的科学技术、交流方式、交通方式与社会空间形成了众多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而与之相比,人的经验系统则具有滞后性与常态化的特质,这种稳定的经验系统让他们无法在自身的经验图式内合理化新现象,而震惊便随之而来。
在此基础上,本雅明将电影视为震惊的典范,“在一部电影里,震惊作为感知的形式已被确立为一种正式的原则。”[14]在本雅明看来,电影不同于以往的艺术,它打破了过去静态沉思式的审美方式,而以不断运动变化的图像来呈现自身,每当观众意欲对电影画面进行思索时,银幕画面就已经变掉了[15]。因此,本雅明的现代性体验与电影体验是同构的,皆为不断的震惊。事实上,电影之所以和现代性同构,在于电影本身就是现代性进程的一部分,电影所创造的一切,无论是运动影像还是机械复制都可以归结为现代性曾经允诺的时空关系与经验。甘宁沿着本雅明的脚步,对震惊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将其与由静到动的形态变化联系在一起:电影最初只是一些静态的投影,“但随着静止的投影开始运动起来,并产生了连续的画面效果,正是这不可思议的活动影像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16]形态上的变迁所带来的震惊感表征着现代性,因为其总是刻意展现自身源头的在场(一架现代性的机械设备),而正是这种不同于以往的经验吸引着早期的电影观众。
如果说在《乡下人与放映机》里,面对火车时手忙脚乱的农夫是现代性震惊反应的典型。那么在《阿凡达》中,聚精会神注视着阿凡达躯体的杰克是否代表着后现代主体面对数字技术的新现象时,所形成的类似的震惊反应呢?也就是说,是否可以将前者的机械复制的运动幻象与后者基于电子计算机生成的去索引性的虚拟影像一同视为对人类内在经验系统的冲击,进而产生类似的震惊体验呢?尽管新媒介会刺激人类旧有的经验系统,但是当人们的感官习惯于新媒介之后,震惊感便会随之褪去。当下的观众很难产生与农夫类似的体验,尽管我们依然会感叹今天数字技术所创造的无与伦比的画面特效,但这已不再是早期观众第一次接触到机械的非人力量时所产生的那种体验。总而言之,今天的后电影依旧具备奇观画面的吸引力,呈现着后现代的视觉想象,但观众与过去相比,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看”,而更渴望于“做”。
我国学者姜宇辉在一次访谈中借用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对后现代概念的定义方式,将“后电影”视为对电影本体性的一次补充。在他看来,交互性或者互动性本来就是电影的本質,电影本质就应该是人们借以表达思想和进行交流的媒介[17],而后电影只不过是在技术的加持下在这个方向上日臻成熟的一种状态,而不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电影之死”的终点。在前数字时代,尽管一部分电影创作者尝试在电影风格等方面进行变革,从而使观众能够与电影形成交互,但受限于技术的瓶颈,电影与观众之间很难形成即时的、实在的交互,观众与电影之间始终伴随着难以跨越的“第四面墙”。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到来,这种物质性的限制逐渐减少,数字技术为电影创作与观众体验带来了新的可能,其不仅赋予观众自主选择或改造电影内容的权力,甚至还帮助观众完成了具身参与电影的夙愿。
后电影总体呈现了“数据库”的后逻辑性。就叙事层面而言,其不再追求在一个线性的封闭时间内,讲述一个有因果律的故事,而是将电影的素材碎片化、空间化为一个无序的项目列表,供观众自行选择与排序。如近年来的科幻电影纷纷建立起各式各样的元宇宙世界,叙事于其中已退居二线,空间则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空间的突显首先意味着观众要对众多的空间自行进行衔接,审美经验与生活经验超越电影创作者的意图,成为电影产生快感与意义的核心要素。其次,一些特效精湛、想象力丰富且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不仅刺激着观众的视听感官,还延伸至他们身体的其它器官,再加上3D、IMAX、杜比音效等技术,予以观众身临其境之感。最后,如果说只符合以上两点的“数据库”逻辑还处于电影的内在层面,那么以《黑镜:潘达斯奈基》为代表的交互式电影则将“数据库”逻辑外在于物质层面。在影片具体的播放过程中,影片被拆解为多个部分,而观众需要根据每个部分结束之后的选项来选择剧情发展的方向,而每一个不同的选择对应着不同的发展脉络,甚至在观众进行选择后,剧中的人物还会对观众的选择进行评价,这一切都给观众带来了即时参与的体验感。
此外,当下很多流媒体平台开放了“弹幕”功能,允许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实时参与到影片的讨论与评价当中,观众由此获得了更多的主动性;而弹幕所形成的第二文本有时甚至凌驾于原初文本之上,改写或颠覆了其原初意义,并成为了观众重点查阅、评价与参与的对象,彻底扭转了先前艺术鉴赏中的等级次序。并且,大多流媒体平台还建基于Web2.0的交互界面与超媒体链接等技术上,这些技术使电影文本实现了开放式结构,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拼贴不同的文本,而不用像前数字电影那样必须在一个封闭的时间结构内被动地跟着剧情发展的轨迹而前进。
后电影的技术赋能使观众进入到了电影的内部,成为了参与者,实现了实在意义上的主客统一。尽管后电影与吸引力电影皆以奇观画面为导向,但“交互”使后电影具备了不同于吸引力电影的内在逻辑,而这也与后现代性下的主体意愿相契合。在经历了接连两次惨无人道的战争创伤后,人们开始审视、质疑,乃至批判以往高高在上的权威,他们不再坐以待毙,而是积极介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新媒体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强调交互性的艺术不断涌现,而电影在经历了漫长的技术革新后也迎来了自己的后现代性曙光。
三、政治潜能:视觉文化的可能性与交互的反思
电影诞生前后,是现代性发展至高潮的一个节点,这一时期“工具理性”在社会各阶层的渗透却并没有像它所应允的那般,让人们获得普遍的启蒙、进步与自由,随之而来的却是无所不在的“异化”(马克思)、“铁笼”(韦伯)与战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沦为了机器运行的零部件,被改造为符合资本利益的标准工具,需要不断地完成既定的工作。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很多理论家开始反思现代性与理性,试图走出资本主义的桎梏。而电影作为全新的媒介,其所带来的全新的感知系统不仅拓展了不同于理性的、趋向感性的视觉文化,还为人们带来了进一步的思考与行动的可能性。
回到上文探讨的巴拉兹,在论述完电影创造的新的文化语境后,他假定了人类彼此拥有通感的话语,并由此断言“电影今天已经只说全世界人民都能了解的通用语言”[18]。在他看来,电影的视觉特性是能够打破语言“巴别塔”隔阂的表意方式,如人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而这种表意方式由于没有经过语言的“转译”环节,因此是人内在情感基于生物性,而非文化性的直接流露,全世界人民都会在此基础上产生类似的理解与情感。由此,巴拉兹认为,电影有助于全世界人民互相团结、互相了解,并因而成为推动人类向大同世界发展的最有作用的先驱者之一[19]。
与巴拉兹不同,克拉考尔与本雅明并没有赋予电影普适语言的宏大使命,而是就新媒介、新感知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寻觅了电影的政治潜能,而在其中,“散心”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散心一词,作为学术性概念出自克拉考尔撰写的《娱乐的狂热》一文,意指一种注意力分散的生理学或心理学的体验状态[20]。在文中,克拉考尔详细考察并分析了柏林大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柏林电影宫的电影放映情况。不同于之后电影院的单一职能,在柏林电影宫进行演出的还有歌剧、杂耍、交响乐等艺术形式。克拉考尔指出,这些类型多样的艺术与电影同台上演,从而使观众很难形成集中的注意力,“电影宫的所有布置只为实现一个目标:把观众的注意力束缚在边缘,以使其不要陷入无尽深渊。感官刺激如此密集地紧随它们,以至于一丁点思考都难以渗入其中。”[21]与本雅明略有不同,克拉考尔认为,电影院而非电影所形成的碎片化的演出风格与现代性社会是同构的,大众在散心式地观看影片的过程中会发现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非理性的一面,了解身处的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以及预见终有一天社会会走向崩溃的边缘。
与克拉考尔的乐观态度不同,本雅明则在震惊的基础上对散心进行了辩证思考。如上文所述,震惊是人们旧有的经验系统无法对外在的新现象合理化时产生的体验。在本雅明看来,人们对现代性经常感到无所适从,因此很容易形成某种内在的保护机制来隔绝外在的刺激。在这样的状况下,大众过往的经验会愈发的贫乏,每个人为了维持生存都变得麻木、疏离与异化。对此,本雅明结合弗洛伊德和伯格森的相关理论,将非意愿性回忆视为解救的途径。具体到电影之中,面对眼前不断出现的震惊画面,观众如何通过非意愿性回忆进行调节呢?本雅明指出,恰当的方式便是散心。电影连续变换的画面让人无法像专注一幅画那般去集中注意力,而只能以散心的方式去接收外部信息。散心和非意愿性回忆都是无意识状态,即习惯性的触觉,它是一种不同于思考的视觉无意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将当下与历史连接在一起,体验生命之本真性,从而让自己跳出历史同质化的流变,获得向“现时”开放的政治行动的能力[22]。与克拉考尔类似,本雅明在此基础上指出,电影所产生的散心效果可以让普罗大众更好地适应现代性所带来的震惊感,完整地把握现代性社会的组织结构,而在集体性的感官升华中,政治行动的种子便埋于其中。
从巴拉兹到克拉考尔与本雅明,这些左翼理论家坚信电影拥有如此重要的政治潜能实则预设了马克思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義发展存在着不可避免与调和的内在矛盾,它在不间断创造利润发展的同时,也创造着毁灭自身的力量。对于巴拉兹、克拉考尔、本雅明来说,电影是资本主义的技术理性下的产物,但它却具备了不同于思考、专注,以及作为它们表征的文字的全新维度,它可以改变人们传统的感知模式,进而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性偏向的文化语境,并借此具备了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力量。
在一些理论话语中,后现代性被描述为与现代性的彻底决裂(利奥塔);而又在一些理论话语中,后现代性则被视为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杰姆逊),但无论如何,后现代社会总归是一个或多或少有异于现代性的阶段:物质的生产让位于信息的生产;福柯式的规训社会被德勒兹式的控制社会所取代;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时间与空间由此前的分裂走向统一。不仅如此,后现代社会还是一个多元的、边界瓦解的社会,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高雅与低俗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异;宏大理论式微,普遍性的真理被差异性的话语所置换。在这样的世界中,真实变得虚无缥缈,景观、拟象表征着世界,它们不再负责再现这个世界,而是生产着这个世界,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或者说成为世界本身。在信息泛滥,而真实隐退的“后真相”时代,我们难以对世界进行清晰的定位;在“我思”退场,主体不再占据中心的时代,我们也无法对自我有一个明确的把握。
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理论家开始重新思考电影与技术、电影与主体、主体与技术间的多重关系,试图在新技术的基础上重新为电影注入政治力量。在这其中,一部分理论家紧跟克拉考尔与本雅明的研究步伐,着重关注媒介、感知系统、文化语境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同时摈弃理性主义二元论的思维架构,试图在后现代的流动且多音的话语中重新寻找真实与主体的脉络。例如,沙维罗指出,后电影时代的电影与音乐视频不仅被动再现社会进程,还积极参与并有助于形成这些进程[23]。沙维罗援引马苏米对“情动”与“情绪”的划分[24],认为情动与杰姆逊的难以表征的跨国资本主义超空间一般难以被捕捉与把握,但又如同杰姆逊主张用一种非认知与非现象学的“认知映射美学”来把握超空间一般,沙维罗也认为充满情动的后电影可以帮助我们以“情动映射美学”的方式来理解新自由主义社会之中难以理解与把握的资金流动与媒体控制。例如,他通过对《登机门》《南方传奇》《公司食人族》《天地逃生》中的情动的流动方式,测绘了当下社会的四幅“地图”,即“全球化经济的疯狂的资金流动”“媒介生态”“控制社会”与“游戏空间”[25]。同样,丹森也强调,后电影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情动的状态,从而让我们在面对网络化的分体性时,可以发展出一种伦理的、激进的后个体敏感性[26],进而在当下多重因素交织的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来把握后现代下流动的、多元的、开放的、相对的主体性与社会状况。
当然,以上所论述的种种观点都具有技术决定论的偏颇性,忽略了人类文化与政治强有力的引导与规范作用。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一稿的最后一章《战争美学》中,本雅明声嘶力竭地呼喊,应用艺术政治化去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艺术化,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电影沦为了希特勒和里芬斯塔尔的合谋工具。并且,尽管电影诞生之初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理性思维的感知模式,但在电影诞生数十年之后,电影很快便被“整合”了,进入了漫长的理性思维统治下的连续性剪辑或经典叙事的时期。有了前车之鉴,后电影是黑格尔-马克思式辩证法的归宿,还是波德维尔笔下的“强化连续性”的一部分,这都需要结合观众具体的观影情境来辨析,或许上文提到的“交互”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发。
在弹幕电影、VR电影、交互电影等电影中,观众获得的不仅是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通过自行的选择来控制剧情的走向、意义的解读与情感的表达。不难发现,这种交互以一种游戏的方式,为观众参与提供了渠道。学者伊恩·博格斯特认为,玩家玩游戏的同时不一定只是默默遵守游戏规则的人,他们还会对游戏的规则产生反思与批判,思考游戏规则是否合理[27],而这种参与性所引发的思考不只会停留在游戏内部,还会进一步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所开放。玩家在反思游戏的规则的同时,也会对社会现实的规则产生进一步思考,考虑其中某些规则的合理性或某些事件的公正性。近年来,“影游融合”逐渐成为电影创作的热门趋势,电影在技术的支持下越来越多地将游戏模式融入其中,赋予了观众/玩家/参与者更多的主动性,他们不仅被这种新式的观影方式所吸引,努力在艺术中自我实现,还可能由此产生反思与批判的意识,以更深入地探索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及自身于其中的位置。
四、结语
当下后电影的发展状况正如其概念的提出者罗伯特·斯塔姆所言,“电影自吹自擂其特性的趋势,如今似乎没入了视听媒体的洪流之中。”[28]数字媒介的崛起将各类媒介融合至自己的领域,“无论是源于印刷媒介的文字传统,还是源于视听媒介的感官传统———都渐渐被统摄于无远弗届的数字逻辑体系之下。”[29]媒介的统一,或者说物质性的合一让曾经的电影学者多少倚赖的“媒介间性”黯然失色。面对这一局面,包括电影在内的一切媒介都亟需面临自身本体论解构的挑战。因此,关键的问题或许已不再是“电影是什么?”这样巴赞本体论式的发问,而是从这样的问题的问题域中提出“‘电影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的时代性问题。
当下,后电影已不再是一个具有媒介特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数字媒介下的种概念。早期吸引力电影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仍保持着影响力,后电影的影像实践也似乎是对吸引力电影的一次“返魅”,但这都需要放置在数字时代的整体背景下来审视。可以说,后电影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整合期后,在数字技术中形成的数字吸引力电影,其保留了源自其根源的部分结构,却更多展现了当今数字时代的“后”特征。因此,后电影是一次“返魅”中的革新。
参考文献:
[1][2]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17-34.
[3][18][19]贝拉.可见的人[A].杨远婴.电影理论读本[C].何力,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5-8.
[4]白旭晨.信息维度:理解冷热媒介的认知转向[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9):26-32.
[5][6]王苑媛.后电影作为一种感知结构——后电影理论述评与反思[J].电影艺术,2018(4):37-44.
[7][8][26]丹森.瘋狂摄影机、不相关影像和后电影情动的后感知中介[A].陈瑜.闪速前进:后电影文论选[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108-133.
[9]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96.
[10][11]葛瑞威奇,孙绍谊.互动电影:数字吸引力时代的影像术和“游戏效应”[J].电影艺术,2011(4):84-92.
[12]冈宁,范倍.吸引力电影:早期电影及其观众与先锋派[J].电影艺术,2009(2):61-65.
[13]甘宁,刘宇清.现代性与电影:一种震惊与循流的文化[J].电影艺术,2010(2):101-108.
[14]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63.
[15]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39.
[16]甘宁,李二仕.一种惊诧美学:早期电影和(不)轻信的观众[J].电影艺术,2012(6):107-115.
[17]黄瑜,姜宇辉.从《奥本海默》看“后电影”技术与情动[EB/OL].(2023-10-10)[2023-11-10].https://mp.weixin.qq.com/s/yzQlcNgS75zOWmlFJDwFEA.
[20][22]张鹏.重释“散心”美学——从本雅明到克拉里[J].文艺理论研究,2020,40(6):96-104.
[21]克拉考尔.大众装饰:魏玛时期文论[M].孙柏,薄一荻,郑家欣,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316.
[23][25]沙维罗.后电影情动[A].陈瑜.闪速前进:后电影文论选[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62-68.
[24]马苏米.虚拟的寓言:运动,情感,感觉[M].严蓓雯,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33-34.
[27]姜宇辉.游戏何以政治?[J].读书,2022(9):3-12.
[28]斯塔姆.电影理论解读[M].陈儒修,郭幼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76.
[29]常江,田浩.间性的消逝:流媒体与数字时代的视听文化生态[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12):137-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