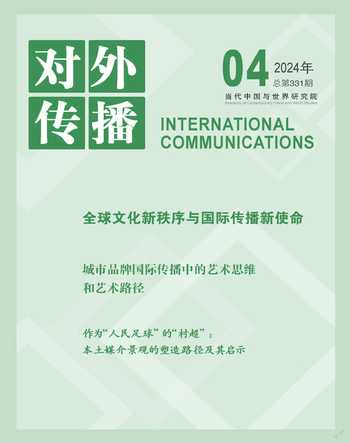Sora冲击波与国际传播新秩序
方兴东 何可 谢永琪


【内容提要】从C h a t G P T到S o r a的爆红,预示着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一次重大变革,机器可能代替人成为信息和内容的主导性生产者。国际传播面临真正的全新范式转变,将再次重构当今社交媒体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经历了大众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1 . 0和网络传播、社交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2 . 0,以C h a t G P T、S o r a为代表的智能传播全面开启智能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3 . 0。国际传播3 . 0以A I技术平台为基础,通过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新要素,将改变整个国际传播的竞争格局和大国博弈态势。中美围绕A I的技术和传播竞争,决战的主战场在全球市场,而不仅仅在中国本国市场。要从智能传播的基本特性出发,制定前瞻性战略,谋求在智能传播技术演进进入到主流化阶段的窗口期,充分发挥中国企业优势,抢占位置;国家层面需要做好系统性布局,提前洞察这场变革的潜在影响,分析未来演进的可能路径,以更好制定前瞻的战略对策与实施路径。
【关键词】SoraChatGPTAIGC 国际传播 智能传播
一、Sora冲击波:智能传播天然就是国际传播
过去的十年,国际传播最大的变局就是社交媒体全面崛起,成为主导性传播平台。从ChatGPT到Sora的爆红,它们所代表的智能传播正以更加迅捷的速度改写国际传播格局,智能传播技术的突破在当今全球格局重塑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每一次人工智能技术(以下简称AI)的迭代都让其进一步突破和超越时空边界,促进世界更加紧密相联与互动。这种重要性,就体现在科技创新力量重塑世界“权力游戏规则”的能力。ChatGPT、Sora的崛起对中国科技产业和国内传播带来极大冲击,但是,最大的挑战还是发生在国际传播层面。
从全球信息流视角看,当今国际传播秩序较之互联网浪潮之前的大众传播时代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技术驱动是全球媒体生态和传播秩序变革的突出特点。当前全球信息传播主要由传统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社交传播和智能传播等四大机制交汇而成。不同机制此消彼长,相互博弈和联动,构成了全球传播格局进程的主旋律。ChatGPT、Sora的爆发,标志着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智能传播正式确立主流地位,也意味着人类信息传播的又一次范式转变,并将引发社会各层面、各领域的基础性变革。Sora展示了文本生成視频的“世界模拟器”的全新可能性,标志着媒介生产自动化与媒体形态一体化的临界点,打通“最后一公里”,开启了人类传播史上又一“谷登堡时刻”。①随着AI算力迈过临界点,并且还在加速迭代。智能传播将很快超越前三种传播机制,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导性信息传播机制。
Sora所采用的扩散模型(去噪扩散概率模型,Denoising diffusion probabilistic model,DDPM)②,使其超越了过往的文生视频模型,功力大增。总的来说,扩散模型在图像生成任务中具有较高的生成质量和稳定的训练过程,并且可以通过引入指导信息来控制生成的类型③,提高了数据的利用效率,拓展了其生成各种高质量视觉内容的能力。实际上,在不断发展的通用人工智能(AGI)领域,Sora代表了一种变革性的方法,使文本到视频的生成更加以人为本。Sora将提示改进与GPT-4相结合,使其能够以类似于人类理解的方式解释用户的指令,提供了一个更加友好和直观的体验。这不仅将彻底改变视频生成的秩序,还将彻底改变一般的内容生成规律,最终将在虚拟现实领域中形成主导影响。技术升维引发的信息传播范式的转型已然开启,随之而来的便是国际传播秩序的变革。
全球化时代对多语言内容信息的需求逐步上升。ChatGPT和Sora等新一轮智能传播技术浪潮消解了文本、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媒体形态的边界,尤其消除了语言这一人类传播固有的最大障碍之一,仅从传播的基础层面考量,就可以预见智能传播对整个国际传播的影响远大于其他传播机制。同时,在注意力稀缺的数字时代,对大型企业、新闻机构和所有内容创作的主体而言,寻求更多的触达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尽管最终呈现的是内容,但驱动方式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过去内容驱动的生产模式已经被数据驱动的生产模式所取代。同时,相比于用户驱动、用户主导的生产模式,数据驱动将更加精准与个性化,以“窄播”的可能性,实现“宽播”的必然性,“弥漫的传播”将真正降临。④人类信息传播的信息量和传播力将实现指数级的增长。
如果说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无论从基础设施、用户群体和信息生产与传播等角度,依然呈现鲜明的地域性和国家性,社交传播开始呈现一定的全球性特征,那么以大模型和算法驱动的智能传播,无论是大模型、语料、数据、传播范围都是全球性的。借助互联网全球一体化的基础设施体系,⑤天然就属于超越地域和国界的国际传播。智能传播对国际传播与国际舆论新秩序的影响与重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国与国之间技术创新能力的比拼。由此,国际传播秩序进入一个快速演进和迭代的大重构阶段。
二、四大传播机制此消彼长与当今国际传播秩序
ChatGPT和Sora等技术发展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智能传播的技术、产品与应用处于爆发的初期,变化之大、种类之多、迭代之快以及新陈代谢的难以预测性,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站在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的角度看,智能传播对于国际传播的颠覆性影响已经呈现基本的发展趋势和内在逻辑。审视当今国际传播的格局与秩序,传统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社交传播和智能传播等四大机制相互叠加,又此消彼长,构成了当今国际传播的基本生态和格局。从媒体发展成熟度角度看,四种传播机制承前启后,分别处于不同的阶段。根据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传统媒体已经进入成熟期后期,网络媒体正处于成熟期,社交媒体处于高点的成长期。而智能传播,随着ChatGPT和Sora的成功,正在快速穿过孕育期,进入用户规模化的初始时期,并且将在可以预见的近期,几无悬念地顺利跨越主流化的鸿沟,真正开始对社交媒体构成直接挑战。
首先,传统大众传播虽然在关注度方面呈逐渐下降态势,但没有完全退出国际传播的历史舞台,仍然在全球舆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报纸的发行量和电视的收视率持续下降,美国成年人表示“主要从智能手机、电脑或平板电脑上获取新闻”的比例从2021年的51%、2022年的49%一路飙升至2023年的86%⑥。但传统媒体因其长期与公众建立的信誉和黏性,使其在假新闻和信息过载日益成为全球性问题的当下,仍然获得一部分稳定的受众。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传播技术,电视、广播和报纸等传统大众媒体纷纷寻找各自的生存方式,在数字时代努力延续自己的影响力。在经历了一系列积极的变革与创新后,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社交媒体之间的区分和边界变得愈加模糊⑦,实现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社交媒体和智能媒体高度的联动与协同。尽管从整体趋势上看,美国代表性传统媒体《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报纸的印刷版订阅量都在下降,但他们的数字版订阅量都出现了大幅增长,依然是美国国际传播系统的重要环节。
其次,网络传播依然是国际传播的活跃组成。尽管社交媒体逐渐跃升为主导性的传播机制,但是,以静态网页为表现方式的Web 1.0模式的网站仍不可或缺。截至2023年2月底,全球共有11.3亿个网站,其中大约有2亿个网站处于活跃状态。网站构成了庞大的分布式内容网络,依然有着巨大的存在感。虽然,网络传播难以形成社交媒体巨头这样的规模和影响力,但静态网络媒体依然是定义当今国际传播格局的重要背景。从世纪之交的门户网站时期,美国就垄断了互联网的域名与地址分配权,而这一现实延续至今,美国网站数量超过1亿。不断在数量上遥遥领先,而且内容丰富多元,几乎覆盖全球所有区域和国家,成为其国际传播巨大的信息网络。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的网站数量为383万个,数量不到美国的2%。而且呈现持续下降趋势,2022年较2021年末减少31万个,比2018年的523万个网站下降30%。而且中国网站以服务国内用户为主,几乎都为中文内容,缺乏足够国际化的网站生态,也缺乏向外延伸和辐射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说,美西方国家的网站没有明显的国内与国外分界,其传播天然就是国际传播。我们目前的这一短板,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通过相关政策引导和激励,及时加以弥补。繁荣Web 1.0内容建设,对于国际传播秩序的影响,依然很有战略价值。
第三,社交媒体是当今主导性的传播机制,但其能力已经开始见顶。截至2024年1月,全球约有50.4亿人次社交媒体用户(存在重复账户),相当于全球总人口的62.3%,相当于网民数量的94.2%。而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交媒体用户新增2.66亿。⑧巅峰时刻的社交媒体初步实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理想,但是很快开始面临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智能媒体的全面侵蚀和威胁。⑨考察社交媒体,主要是两个维度:一个是用户维度,社交媒体就是信息传播的“人民战争”,一个网民就是一个媒体,典型的“人多力量大”。中国遥遥领先的10亿级网民群体应在国际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和作用;第二个维度就是平台维度,全球超级平台主要由中美两国主导。共有15家社交媒体月活跃用户超过4亿人次。脸书(Facebook)每月有30.49亿人次活跃用户,照片墙(Instagram)、WhatsApp每月也有超过20亿人次的活跃用户。当然,除了抖音国际版(以下简称TikTok)等个别网络,中国网络平台主要局限在国内,而缺少真正全球性的平台阵容。我们依然需要大力发展面向全球用戶的超级网络平台。
最后,以ChatGPT和Sora等为代表性应用的智能传播凭借迅猛的发展态势,很快成为国际传播场域新兴的力量。智能传播是人类数字技术发展的结果,本质是数据驱动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变革,中国在这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势。⑩其中,TikTok通过算法驱动、内容分发,是真正步入主流大众、成为最早“杀手级应用”的智能媒体。11数据显示,TikTok在2020年第一季度以3.15亿次的数据创下了全球任意一款APP的单季下载纪录,成为当时下载量最大的应用程序。到2023年底,活跃用户相比2022年增长16%,超过15亿人次,预计2024年将超过18亿人次。12TikTok等智能传播媒体利用全面的数据收集和精准的算法分析,获得大批用户的青睐,在短短两年时间内迅速占领市场,网民覆盖率达18%。此外,TikTok在中国、美国、印度尼西亚和巴西都占有了重要的市场份额,成为脸书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但是,随着以ChatGPT和Sora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应用相继出现,智能传播开启新的时代。ChatGPT是基于大语言模型技术,在用户和AI的交互中实现理解并生成文本的人工智能应用。ChatGPT在用户规模上极速增长,仅用2个月的时间就达成了照片墙两年半、TikTok 9个月才达成的1亿人次用户目标,直接成为当前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消费级应用。2023年9月,开放人工智能公司(OpenAI)证实,ChatGPT在2021年9月的数据基础上将正式开始使用互联网资源,为用户提供最新的新闻和时事。至此,以AI为基础的内容生产模式使社会信息的传播开始面向全球成为一个无限的开放系统。截至2023年9月,GPT-4可以生成25,000个单词,能够理解26种以上的语言,可在全球100余个国家使用。而文本-视频生成扩散模型Sora,能够理解并处理多种类型的视觉数据,生成与文本提示高度匹配的视频或图像。其高度的创造性和适应性标志着智能媒体的又一里程碑。当前,Sora的使用被限定于特定用户群体。然而,随着OpenAI逐步扩大其使用范围,Sora凭借其在智能传播领域的潜在影响力和应用前景将再一次成为一款现象级应用。
从TikTok所代表的数据和算法驱动的传播变革,到ChatGPT和Sora等应用在AIGC领域的探索,智能传播正在快速改写着以大众传播为基础的社交传播和网络传播的规则。显然,随着智能传播走向主流,新的国际传播秩序将完成颠覆性的重构。未来,AIGC将可以产生与真实现实难以区分的内容。这一即将到来的现实将重构国际传播格局,也对民主、新闻、司法的运作以及个人互动关系和社会运行与治理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13一跃成为全球国际传播博弈的最前沿。
三、技术主导:智能传播如何重构国际传播新秩序
四大传播机制构成了机制不同但是相互贯穿的四大舆论场。从信息流视角,构成当今国际传播秩序的相应四大舆论场包括大众传播舆论场、网络传播舆论场、社交传播舆论场和智能传播舆论场。四大舆论场各有侧重,但信息流动使其相互交叉影响,共同塑造了国际舆论场的秩序。新的正崛起,旧的并没有消亡,但是新兴的传播模式将成为主导,智能传播舆论场趋向于获得优势,而旧有舆论场主要通过与新兴舆论场联动和协同,获得新的生命力。目前我们处于智能传播崛起的初期,由于AIGC的技术生产机制还不成熟,使得未来发展走向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变革的方向已经清晰而明确。
推动国际传播秩序变局的力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力量,一类是自下而上的技术力量。而构成当今变革的主旋律,主要是自下而上的技术力量。尤其是互联网发展进入到大数据和大模型阶段,技术越来越成为决定性力量。制度性力量因为全球机制的失灵和低效,暫时很难主导传播秩序的变局。因此,智能传播将是新一轮国际传播变局的决定性力量。
智能传播的崛起首先带来的是内容生产上的变革,它将实现指数般的内容生产速度,海量的信息将快速涌入国际传播的舆论场当中。在国际传播的视域下,ChatGPT在信息检索场景中如同百科全书般无所不知,在内容生产场景中如同马良神笔般无所不能,甚至在情感陪伴场景中能够化身“客观中立”的世界性虚拟伙伴,重塑了跨国传播多元场景与多维交互的交往模式。14Sora可以被视作ChatGPT的可视化应用,其所具有的高级文本解释、高质量视频生成、快速内容创建、复杂机器学习、内容创建多功能性、文化语言的适应性等特征,掀起了智能传播的又一次革命。
其次,以AI为基础的智能传播正在颠覆知识、传播与权力。智能重塑了媒介的延伸,在智能传播机制中,搜索即答案、信息即服务、媒介即认知。15有专家认为,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是获取并维系意义感、价值感、存在感的来源,并以此成为智能传播的认识论的基石。16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内爆”方式带来新的感知和认知模式,创造了新的物质和文化环境,17它改变了知识生产和重构话语生产,使生命体成为自由的个体和行动者,自由地联结、行动、创造意义。18因为它第一次夺走了人类对信息流的主导,使传播指向一个无限的开放系统。
同时,AI正在重塑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智能传播的效果将不再浮于原本的引起注意和激发情感,也不止于行为的改变、行动的集结,而将深入重塑个体的认知。在智能媒体的赋能下,国际传播的效果预期从原本的宣传动员,转向了更深层次的认知改变,这也使得网络空间舆论战向认知战范式转型。19社交机器人、深度伪造技术、计算宣传与计算检查等等舆论工具都是基于智能传播的基础,地缘政治时代将走向技术政治时代,20基于数据驱动的智能传播机制将宰制国际舆论场。
而从体系来看,AI算力基础大模型正成为技术博弈与产业竞争的核心。在智能传播初始形态的发展中,算法驱动的TikTok等半社交半智能的短视频平台竞争中,中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对美国社交媒体第一次构成了全球性的威胁。但是,随着ChatGPT和Sora等横空出世,美国在智能媒体方面依然显示出其独特的竞争优势。以Sora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内容生产的底层逻辑和规则制定与调整的权力仍集中在少数技术寡头和掌握相关技术的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手中。历史上看,电脑、智能手机、电子商务、社交媒体等主流科技应用,都是美国一马当先、引领全球。充分显示了美国在研发投入和创新突破方面全球独一无二的底蕴与优势。这一次智能传播也不例外。虽然ChatGPT和Sora等让不少人对中国科技发展产生了新的悲观情绪,但是,参照历史经验,中国科技企业的优势窗口期,还没有真正到来。因此,对于这一轮智能传播的发展,我们可以保持谨慎的乐观。
四、智能传播的中国对策与路径选择
根据专家预测,未来5年之内,机器生成的内容将占据90%以上,意味着趋于成熟的大众传播、网络传播和社交传播等以人为核心的生产内容三大机制将迅速边缘化。这也意味着国际传播秩序将因为智能传播而出现颠覆性的变局。这既是重大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在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两个领域属于后来者。随着微信和TikTok等社交媒体的崛起而拥有了一定的主导权,开始在国际舆论场中有了一定的显示度,而且发展态势引人注目。而智能传播方面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决定中国在未来新的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地位和能力。
因此,在国家战略层面,核心就是抓住AI浪潮的战略机会,全面发力智能传播,有力推动国际传播秩序转变。目前,智能传播还处于市场导入期,我们与美国差距不小,而且短期之内差距还可能拉大。美国在以企业为核心、市场驱动的技术创新方面依然全球显著领先,因此,这一轮AIGC浪潮中,中美的现有差距是正常的,并不是意外。但是,根据个人计算机(PC)、智能手机、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等科技创新的历史经验,随着市场主流化和成熟期的到来,中国企业依然存在后来居上的重大契机。
因此,我们现在正视差距的同时,更要立足长远,需要从基础层、模型层和应用层等层面全局性布局,除了创业公司等市场化力量,更要调动央企、高校和地方政府,加速以AI算力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智能传播打好更坚实的基础。目前美国主要借助强大的企业创新能力和资本市场支持力度,引领智能传播的发展节奏。但是,智能传播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属性,需要资本密集和人力密集的AI算力、大模型和数据等研发,有着高昂的沉没成本和较低的边际成本。这方面,结合市场与政府力量,用好双管齐下的举国体制,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而企业在应用创新和推广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可以实现更有效的资源组合。
同时,我们依然要在大众媒体、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方面继续发力补课,智能传播并不是独立运行的传播体系。四大机制的联动与协同是当今国际传播秩序的基本运行机制。系统性能力的强大才是一个国家国际传播能力的关键。从ChatGPT到Sora的成功事实上很大程度是借助大众传播、网络传播和社交传播的强大威力,而得以迅速在全球吸引诸多注意力和用户群体。因此,单一机制都难以发挥最佳传播力。中国目前没有形成四大机制都很强大的系统性能力,是我们在国际传播层面始终难以逆转格局的根本原因。发展智能传播,也同时继续发力另外三大机制,相互促进,相互助力,是正确之道。
第三,国际传播秩序不是简单中美两国的博弈,而是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各自网络的博弈,更是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两大体系的整体博弈。因此,中国国际传播能力不仅仅在于自身能力的建设,更需要善于在国际合纵连横的传播格局中发力,形成全球性各国更紧密的联动与合作,这是长期战略的关键。当今国际传播主战场已经全面转向网络,传统大众媒体已经趋于边缘化。而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两大区域,网民数量总和占全球比例只有20%,大致相当于中国网民数量。而且其普及率都超过90%以上,趋于饱和。而另外占据约80%的亚非拉网民,基本上属于发展中国家和欠发展国家,还有大量的新兴网民(见表2)。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南方国家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四,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力量,也是变局的关键。20世纪70年代,“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是广受第三世界欢迎的一个关于全球传播体系改革的目标。这场当时声势浩大、围绕全球信息不平等而展开的运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甚至得到了西方国家很多人的呼应。只是没有能够形成持续推进的能力,而最终功败垂成。今天,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已经今非昔比,智能传播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数字鸿沟,加剧信息传播的不平等现象。在这种态势下,借助联合国缔结《全球数字契约》契机,重新启动新一轮智能时代的信息不平等运动,让追求信息平等重现、掀起成为全球共同的潮流,已经势在必行,也已经水到渠成。
总之,Sora在文字生成视频方面的突破,完成了文本、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各大媒体形成的相互转换,消解了曾经制约内容生产和传播的边界,堪称革命性的突破,标志着智能传播浪潮已经全面开启。美国在智能技术和智能媒体方面目前暂时处于全球领先。但依靠庞大的用户规模、强大的企业和产业基础、丰富独特的人才资源和政府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的全面展开,中国在智能传播层面的全球崛起依然有无与伦比的机会。只需要加大力度,补全短板,夯实基础,等待技术创新迭代速度放缓、智能应用走向成熟,一定会迸发比过去更强大的爆发力。推动国际传播秩序的改变,这一轮智能传播浪潮机不可失。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媒介体制与社会信任研究”(19ZDA325)和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的阶段性成果。
方兴东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乌镇数字文明研究院院长;何可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谢永琪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方兴东、钟祥铭,《谷登堡时刻:Sora背后信息传播的范式转变与变革逻辑》,《现代出版》网络首发,http://www.wz-institute.com/index.php?m=content&c=ind ex&a=show&catid=15&id=436,2024年3月12日。
②Jonathan Ho, Ajay Jain, and Pieter Abbeel. 2020. Denoising diffusion probabilistic models. 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33(2020), 6840–6851.
③Cho J, Puspitasari F D, Zheng S, et al. Sora as an AGI World Model? A Complete Survey on Text-to-Video Generation. arXiv preprint arXiv:2403.05131, 2024.
④杜骏飞:《弥漫的传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⑤方兴东、钟祥铭、李星:《互联网元架构——解析互联网和数字时代范式转变的底层逻辑》,《现代出版》2023年第5期,第25-39页。
⑥Pew Research Center. News Platform Fact Sheet.https://www.pewresearch.org/ journalism/fact-sheet/news-platform-fact-sheet/2023-11-15.
⑦Reid Chassiakos Y L, Radesky J, Christakis D, et al.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digital media. Pediatrics, 2016, 138(5).
⑧GLOBAL SOCIAL MEDIA STATISTICS. https://datareportal.com/socialmedia-users.
⑨方兴东、顾烨烨、钟祥铭:《ChatGPT的传播革命是如何发生的?——解析社交媒体主导权的终结与智能媒体的崛起》,《现代出版》2023年第2期,第33-50页。
⑩方兴东、钟祥铭:《智能媒体和智能传播概念辨析——路径依赖和技术迷思双重困境下的传播学范式转变》,《现代出版》2022年第3期,第42-56页。
11方兴东、钟祥铭、顾烨烨:《从TikTok到ChatGPT:智能传播的演进机理与变革路径》,《传媒观察》2023年第5期,第39-47页。
12Tiktok report 2024:https://www.businessofapps.com/data/tik-tok-statistics/.
13van der Sloot B. Regulating the Synthetic Society: Generative AI, Legal Questions, and Societal Challenges. 2024.
14何天平、蔣贤成:《国际传播视野下的ChatGPT:应用场景、风险隐忧与走向省思》,《对外传播》2023年第3期,第64-67、80页。
15任天知、沈浩:《智能重塑媒介的延伸》,《新媒体与社会》2023年第2期,第130-139页。
16陈卫星:《智能传播的认识论挑战》,《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9期,第6-24页。
17张洪忠、徐鸿晟:《智能传播时代的范式转变:媒介技术研究十大观点(2023)》,《编辑之友》2024年第1期,第38-44页。
18石涎蔚:《技术时代的“内爆”:从麦克卢汉、鲍德里亚到哈拉维》,《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第21-29、36页。
19喻国明、郭婧一:《从“舆论战”到“认知战”:认知争夺的理论定义与实践范式》,《传媒观察》2022年第8期,第23-29页。
20张梦晗、陈泽:《信息迷雾视域下社交机器人对战时宣传的控制及影响》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6期,第86-105、128页。
责编:霍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