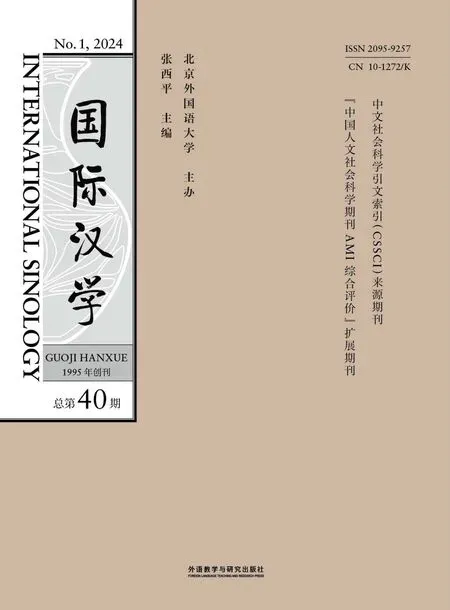中国孝行故事在18 世纪欧洲的传播*
□ 谭 渊 宣 瑾
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末清初,来到东亚传教的耶稣会士很快就注意到了儒家所倡导的孝道在中国和日本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发现,不但中国流传有《孝经》《二十四孝图》等著作,而且受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日本也有大量反映孝道观念的戏剧在上演。因此,耶稣会士在向西方介绍东亚文化的过程中,也将儒家的孝道观念和中国的孝行故事介绍到欧洲,并在欧洲引起关注。
一、中国孝行故事的西传
早在1590 年左右,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高母羡(Juan Cobo,1546—1592)在菲律宾将流传于八连地区的《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其手稿被带回欧洲后于1595 年进献给国王菲利普二世(Filipe II,1527—1598),今藏于马德里国家图书馆。该译本中的“孝行篇”里便辑录有孔子、孟子等人关于孝道的论述和数个小故事。1592年,最早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又将《明心宝鉴》译成拉丁语,其手稿至今保存在罗马伊曼努尔二世国家图书馆,是中国孝道观念传入欧洲的有力见证。①胡文婷、张西平:《蒙学经典〈明心宝鉴〉的拉丁语译本初探》,载《中国翻译》2022 年第4 期,第39—40 页。1594 年,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又在其用中文撰写的《天主实义》一书中对儒家所推崇的“孝”进行了解读。在首篇中,利玛窦援引《孝经·开宗明义》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并写道:“夫父母授我以身体发肤,我固当孝”。②利玛窦著,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注:《天主实义今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103 页。在第七篇中,利玛窦还引述了舜的孝行故事。利玛窦去世之后,《利玛窦中国札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1615)中也有多处谈到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孝道观念,例如:“中国的道德书籍充满了有关子女应尊敬父母及长辈的教诲。”③利玛窦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76 页。1676 年,西班牙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de Navarrete,1610—1689)又将《明心宝鉴》翻译成西班牙文,收录在1676 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与宗教论集》(Tratadoshistoricos,politicos,ethicos,y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中。但在这一时期,传教士对“孝”的理解主要还局限于子女对父母的服从层面。①胡文婷、张西平:《蒙学经典〈明心宝鉴〉的拉丁语译本初探》,载《中国翻译》2022 年第4 期,第43 页。
1711 年,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cois Noël,1651—1729)将《孝经》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小学》等儒家经典的拉丁语译本一起收录于《中国经典六种》(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并在欧洲出版,使欧洲人对中国人的“孝道”有了更多的了解。1735 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在巴黎出版的四卷本巨著《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eographique,chron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进一步将大量体现儒家道德伦理的典故、格言和文学作品收录书中,使孝道观念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传播开来,对作为“道德伦理之乡”的中国形象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此基础上,1779 年,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Pierre Machal Cibot,1727—1780)编纂了《中国古今孝道》(Doctrine ancienne et nouvelle des Chinois sur la piété filiale)一书,收录在耶稣会士文集《中国杂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es,les mœurs,les usages des Chinois)第四卷中。该书以孝道作为主题,不仅收录了《孝经》译本以及从《礼记》等书中摘选的格言、警句,而且强调了“孝治天下”,即孝道与帝国治理之间的密切关系。韩国英在序言中指出,中国古人将国家视为一个大家庭,皇帝是这大家庭中的家长,因此孝是“中国人的国家美德”,与帝国治理密不可分,任何有违孝道之人都会遭到全体国人的唾弃。②Pierre Machal Cibot, “Doctrine ancienne et nouvelle des Chinois sur la piété filiale,”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les artes, les mœurs, les usages des Chinois IV.Paris: De l’Imprimerie de Stoupe, 1779, pp.2-3.作为佐证,韩国英还选译了康熙朝“奏议”以及康熙作序的《御制孝经衍义》和雍正、乾隆作序的《圣祖仁皇帝圣训》,以此证明中国官方对孝道的重视和“天子之孝”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在该书最后,韩国英还特地从“礼仪之争”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孝道的内容是纯净而神圣的,与之相关的祭祀礼仪并不违背天主教教义,而从对孝道的实践来看,中国人的孝道甚至十分接近于《福音书》的精神。③Cibot, op.cit., pp.286-298.作为对此的佐证,韩国英在书中还编译了一组中国古代的孝行故事。
耶稣会士著作中对中国孝道的介绍引起了启蒙运动晚期颇有名气的德国教育家、诗人普费弗 尔(Gottlieb Konrad Pfeffel,1736—1809) 的关注。普费弗尔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地区,早年曾在哈勒大学学习法律,听过启蒙思想家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的课程,后获得瑞士公民身份,深受卢梭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创作了很多具有教育意义的诗歌和寓言。而启蒙时代的欧洲正处在一个伦理观念发生巨大变革的关口。传统的欧洲神学认为,神是一切的尺度。在《创世记》中,人类通过偷吃伊甸园中的知善恶果有了善恶的意识,后来上帝又通过摩西赐下《十诫》,进一步为人类规定了律法的准则,因此是上帝为人类确立了道德观念。而启蒙思想家则从理性至上的角度对道德的来源重新进行了推导,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康德所阐述的“道德律令”(Imperativ),即把道德看作理性为自身所建立的法则。而普费弗尔则受到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的影响,在伦理学方面反对康德的“理性至上”和“道德律令”观念,认为应从人的自然本性(human nature)出发,将幸福感与良心视为人的基本冲动(原动力),即与生俱来的道德感才是人类道德的根本基础。④卫茂平:《君特·艾希与中国:君特·艾希作品与中国精神界关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304—305 页。这与孟子的“四心说”和“性善论”完全一致。因此,在将“孝”视为人之本性的中国故事中,普费弗尔幸运地发现了来自东方的知己,也找到了支持其道德哲学和“道德教化”思想的例证。故而从1779 年开始,普费弗尔从《中华帝国全志》和《中国古今孝道》中取材,创作了一组基于中国孝行典范的叙事诗,分别题为《吉翂》(Kiefuen)、《贺连》(Holien)、《兄弟》(Die Brüder)和《母亲与女儿》(Mutter und Tochter)。这四首诗都源自耶稣会士译介的中国典籍,体现了儒家的孝道思想。
二、《吉翂》《贺连》与孝道感召力
韩国英在《中国古今孝道》中选编的孝道故事如《杨香扼虎救父》多出自《二十四孝》等中国古典典籍,而其中一篇讲述15 岁少年主动要求代父赴死的故事则出自《梁书·孝行》。原文如下:
翂幼有孝性。……天监初,父为吴兴原乡令,为奸吏所诬,逮诣廷尉。翂年十五,号泣衢路,祈请公卿,行人见者,皆为陨涕。其父理虽清白,耻为吏讯,乃虚自引咎,罪当大辟。翂乃挝登闻鼓,乞代父命。高祖异之,敕廷尉……厉色问翂曰:“尔求代父死,敕已相许,便应伏法。然刀锯至剧,审能死不?……”翂对曰:“囚虽蒙弱,岂不知死可畏惮?顾诸弟稚藐,唯囚为长,不忍见父极刑,自延视息。……明诏听代,不异登仙,岂有回贰!”……法度具以奏闻,高祖乃宥其父。①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七》,1739 年,第5—6 页。
故事中的吉翂虽然只有15 岁,但却可以为了拯救父亲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恰恰可以证明“孝”是人之本性。韩国英在将吉翂救父故事作为古代孝行范例编入《中国古今孝道》时,对这一故事又进行了一番文学演绎。他写道:
吉翂的父亲遭到诽谤和诬陷,被判处死刑。吉翂日夜站在监狱门口哭泣、哀号,足以软化最坚硬的心。“我的父亲啊!我的父亲!”他喊道,“谁能让我代替你去死?”皇帝从御史那里得知了此事,暗中让人再次进行了审讯,因为他无法相信一个有德行的儿子的父亲会犯下被指控的那些罪行。案情很快被查清,证明他的父亲是清白的。
为了让整个帝国都知道孩子的孝心,皇帝让人把吉翂带到面前。“年轻的傻瓜,”皇帝用一种可怕的眼神看着他说,“当你要求代替你父亲时,你知道法律的严厉吗?在你主动赴死之前,请慎重考虑;一旦你接受它,就没有回头路了。”“陛下,我太年轻了,”吉翂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些惩罚的严厉性,但我的父亲一直深爱着我,与看到他死亡的痛苦相比,我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皇帝说:“我同意了,把他带到监狱去代替他的父亲。”吉翂带着如释重负的喜悦服从了命令,……但他刚戴上镣铐,就又被皇帝下令取下。不仅父亲重获清白,陛下还宣布对吉翂的孝心给予褒奖和赏赐。②Cibot, op.cit., pp.266-267.
在故事中,儒家所倡导的“孝道”展现了与宗教一样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既为吉翂之父赢得了自由,也打动了贤明的君主。而在普费弗尔改编的诗歌《吉翂》中,主人公同样是一位甘愿代父赴死、以尽孝道而闻名的少年。但在将故事改写为叙事诗时,诗人进一步加强了对语言与行动的描写,并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抨击。他写道:
盗匪四起之际,诸侯们/只管把自己的罪责宽恕,/一名官吏却被判处极刑。/他的儿子吉翂跪倒驾前,/恳求君主免去父亲一死,/“我知道,他罪不容赦,/若定要向法律献上祭品,/就将我处斩,换他自由!”/君主故作严厉开口说道:/“你的愿望已获得恩准,/来人,且将他押赴刑场。”/少年激动吻罢君王之手,起身便走。/皇帝噙着泪光喊道:“站住!/我将父亲送还于你,而你当献于祖国,/来将我拥抱!我的朋友,/赤子忠诚当得勋带加冕。”/儿子拉住皇帝衣袍婉拒:/“不,请勿将这饰品赐我,/恐怕它会让我每天想起/父亲当年曾经身负罪责。”③Gottlieb Konrad Pfeffel, Fabeln, der helvetischen Gesellschaft gewidmet.Basel: Thureysen, 1783, p.194.
普费弗尔改写的诗歌,故事仍发生在中国,但诗人的想象力却并没有真正飞向中国,无论是行吻手礼告别,还是皇帝与人拥抱、大谈祖国并颁发勋带,都是十足的欧洲宫廷做派,与中国氛围毫无关系,显示出作者的思维还被牢牢束缚在欧洲文化中。同时,作品中还含有一股讽刺意味,因为作者在诗歌开头写道:“盗匪四起之际,诸侯们/只管把自己的罪责宽恕。”显然这并非一番天下太平的景象,统治阶层的“诸侯们”不但没有挺身而出主动承担“盗匪四起”的责任,以求弥补过失,反而将所有罪责都推卸到一位官员身上,几乎让他无辜送死。幸而他的儿子挺身而出,开明的皇帝也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对孝道的嘉许,这才化险为夷。在诗歌结尾处,吉翂说:“请勿将这饰品赐我,/恐怕它会让我每天想起,/父亲当年曾经身负罪责。”这般推辞固然是因为品行高尚,同时出于孝心不愿每天去回想父亲落魄的样子,但如果考虑到父亲原本就无辜蒙冤,而真正的罪人——诸侯们还安然无恙,吉翂又何尝不是害怕每天想起诸侯们的险恶嘴脸和朝政的黑暗?不过,从诗歌所呈现的皇帝形象来看,虽然他与中国皇帝的真实形象相去甚远,但无论是他对孝行的赞许与嘉奖,还是对少年的宽宏与热情,都呈现出一位贤明君主的形象,也比较接近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开明君主”的理想形象。
1783 年与《吉翂》一起发表在诗集《献给赫尔维第协会的寓言》(Fabeln,der helvetischen Gesellschaft gewidmet)里的还有《贺连》一诗。1793 年,两首诗还一同被收录在文集《寓言与故事》(Fabeln und Erzählungen)中,并都配上了插图。《吉翂》表现了中国人为父尽孝的思想,而《贺连》则讲述了一个孝敬母亲的故事:有个盗贼晚上潜入贺连家行窃,贺连怕惊扰老母,就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直到盗贼将手伸向他用来为母亲做饭的陶罐时,他才出声恳求盗贼放过,此举打动了盗贼,使之放弃了行窃。诗中写道:
在中国,昏暗的灯光下,/有一个青年躺在草席上……他看到/一个盗贼踏入他房中,/却没有发现自己的存在。/那人只要看上什么东西,/就马上塞进宽大的背包。/而他只在床上一动不动,/仅有双眼还眨动,这时,/盗贼将手伸向一只陶罐,/它空空如也,立在房角。/住手啊,可怜的人,/贺连这时才恳切地喊道:/“请放过我这只罐子,/让我明天能为母亲做饭……”/盗贼震撼了:“放心睡吧……/我不会劫掠这样的儿子。”/他把战利品全都放下,/在喃喃中拭去脸上泪水, /从那一天起,再不偷窃。①Pfeffel, op.cit., pp.97-98.
这个孝行故事的原型同样来自中国,但主人公原名并非贺连,而是赵咨。《后汉书·赵咨传》记载:“咨少孤,有孝行,……盗尝夜往劫之,咨恐母惊惧,乃先至门迎盗,因请为设食,谢曰:老母八十,疾病须养,居贫,朝夕无储,乞少置衣粮。妻子物余,一无所请。盗皆惭叹,跪而辞曰:所犯无状,干暴贤者。言毕奔出,咨追以物与之,不及。”②范晔:《后汉书·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1313 页。这一故事在宋末元初被冠以《迎盗安母》之名,收录于蒙学书籍《二十四孝日记故事》中。内容仅略有变化,其全文如下:“(后汉)赵咨敬养老母,有盗至劫之,咨恐母惊,乃先至门迎盗,拜曰:老母病须养,乞少置衣粮。余无所请。盗相谓曰:此孝子义士也,不可干犯贤者。遂辞谢而去。党称其名。”③《锲便蒙二十四孝日记故事》,四有堂,1614 年,第19—20 页。
这个想法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一来是袋子容易破,二来是如何使氧气长时间保存?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一解决。佟庆富先是选用了一种更加厚的塑料袋,把活鱼装进袋子里,灌进水和氧气再把袋口密封,但是鱼在里面只能存活一天,而一天之隔,原先鼓鼓的塑料袋也会瘪掉许多,因为塑料袋上有很多肉眼无法看到的小孔泄漏了氧气。佟庆富又把目光转移到了更坚固更易于密封的塑料瓶上。佟庆富选用了几个塑料瓶,装进净水和一个注满氧气的鱼筒,最后将塑料瓶密封起来。这样一来,不用担心瓶子会破,也不用担心鱼会缺氧而死。
《二十四孝日记故事》又称《日记故事》,是一部以儿童伦理道德教育为主旨的书籍,明清时期流传很广,梵蒂冈图书馆便藏有1689 年寄到欧洲的一部《日记故事》。给《中华帝国全志》撰稿的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1664—1741)称其为“一本讲给儿童听的故事集”,从中选译了多个故事,其译稿至今仍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值得注意的是,下文要提到的《兄弟》一诗的故事原型《乞命归养》和《母亲与女儿》一诗的故事原型《受杖悲泣》也都被收录在《日记故事》中。④同上,第18—20 页。1735 年,这三个故事的译文一起被杜赫德收录于《中华帝国全志》。其中,《乞命归养》《受杖悲泣》被收录于第二卷“一本讲给儿童听的故事集摘录”部分,即从《日记故事》中节选的孝行故事。⑤参见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著,许明龙译:《请中国作证》(La preuve par la Chine),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192—193 页。《迎盗安母》则出现在第三卷“关于(儒家)伦理的学说、思想、榜样汇编”部分。①蓝莉认为这部分内容译自明朝末年李九功编撰的《文行粹抄》一书,但笔者在核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1678 年版《文行粹抄》后,发现在这部分译文所涉及的220 多个故事中只有少量能在《文行粹抄》中找到对应内容,剩余的故事应另有源头,此处的《乞命归养》(《赵咨传》)故事便是一例。因此《二十四孝日记故事》很可能是真正的源头之一。随着《中华帝国全志》在1747 年至1756 年被译为德文出版,三个故事也由此进入德语世界。巧合的是,这三个分属不同卷册的孝行故事最终又在普费弗尔笔下重新汇聚在一起。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诗人对中国的孝行故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其对“孝道”的把握也相当准确。将普费弗尔的作品与《赵咨传》和《日记故事》中的版本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改编后的叙事诗《贺连》更加突出了“孝”的强大道德感召力:连窃贼也被孝子所感动,不仅放下了到手的财物,而且洗心革面,从此不再做贼。这也凸显了“孝道”在道德教化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三、《乞命归养》与《受杖悲泣》故事的异国改写
普费弗尔的叙事诗《兄弟——一个中国传说》(Die Brüder:Eine chinesische Sage)讲述了兄弟二人的孝行故事。在故事中,兄弟二人曾“手拉着手起誓,无论多么贫穷,都要赡养病弱的老母”。由于发生饥荒,哥哥张孝不得不出门挖树根充饥,但却被强盗抓住。他苦苦哀求对方让他先把好不容易才弄到的一点树根送去给母亲,然后再回来就死。哥哥回家后,弟弟张礼看出了端倪,于是跑去找到强盗,要求对方吃掉自己,以便让哥哥活下去继续赡养老母。但哥哥这时也赶来要救下弟弟,最后强盗被兄弟二人的孝行和深情所打动,于是放走了他们。诗中写道:
在中国有一对兄弟,/他们没有站在祭天(Tien)的神坛前,/而只是手拉着手起誓,无论多么贫穷/都要赡养病弱的老母。/他们愉快地履行誓言,/直到一年后凶年来临,……/哥哥张孝(Hyao)只得走出家门,/去树林中挖掘树根。/有所收获后就忙往家赶,/途中却被三个强盗围住,/要命啊,灾荒已将他们变成吃人魔王,/当刀抵在可怜人的胸口,/他跪倒在地祈求怜悯。/你们想要吃掉我?/请容我先把树根送给家母,/我对天起誓,随后会飞奔赶来,/就像插上雄鹰的翅膀。/强盗们惊叹不已:让他去吧!/他们的首领说,我相信他的诺言。/年轻人带着他微薄的收获,/赶回家去把树根献给母亲,/他佯装受惊,向弟弟发出信号,/就像是想要背弃誓约逃走,/弟弟却已发现哥哥的计划。/他随后回到母亲身边,/将命运恩赐给好人的/最后一点时光,/用来孝敬母亲。/这时,弟弟张礼(Tschang-Li)却在林中,/跪倒在强盗们前面。/他恳求他们:让我/代替哥哥偿还欠债。/看,我比他更嫩更胖,/你们应该吃我的肉。……/他话音未落,/哥哥张孝飞奔而来。/莫要信他对你们所说,/他叫道,我,我愿意去死!/只见强盗们眼睛湿润,/低下了头,满怀敬畏,/他们转过身去,/挥手让兄弟二人离去。②Gottlieb Konrad Pfeffel, Ausgewählte poetische Werke.Leipzig: Reclam, 1876, pp.344-345.
本诗开头处对祭祀“天”的渲染很可能与同时代的中西方“礼仪之争”有关,正是在《中华帝国全志》中,耶稣会士对中国“敬天”思想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力图塑造出中国古代文化与基督教的相容性。③李晓书、谭渊:《马若瑟〈诗经〉译本与“礼仪之争”》,载《国际汉学》2022 年第2 期,第45—52 页。而这一故事的真正源头则是《后汉书·赵孝传》,故事发生在两汉之间王莽篡位、天下大乱的时代,由于天灾人祸,以致发生“人相食”的惨剧。文中写道:“赵孝,字长平,沛国蕲人。王莽时,天下乱,人相食,孝弟礼为饿贼所得,孝闻,即自缚诣贼,曰:‘礼久饿羸瘦,不如孝肥。’饿贼大惊,并放之。”故事主要讲述的是兄弟友爱,赵孝愿为拯救弟弟牺牲自己,结果赵孝的自我牺牲精神打动了强盗,兄弟双双得以生还。此时,这一故事与孝道尚无关联。到了《日记故事》,除原有赞扬兄弟之情(“悌”)的部分外,故事中又加入了兄弟二人赡养母亲(“孝”)的内容。兄弟二人的名字则从《后汉书》中的赵孝、赵礼变成了张孝、张礼。为《中华帝国全志》供稿的殷弘绪据此将其音译为Tchang hiao 和Tchang li,普费弗尔在诗中也沿用了这两个名字。在《日记故事》中,这篇被命名为《乞命归养》的故事紧跟在《迎盗安母》之后,全文如下:
(后汉)张孝张礼遇饥馑,礼养老母,孝拾菜归,途遇贼,欲杀之。孝叩头曰:家中老母,朝未得食,乞命少时,归家供讫,即来就死。礼闻之,走于贼所,谓贼曰:吾兄辛苦羸瘦,礼身肥多肉,愿代兄命。孝曰:孝本遇杀,何得杀弟。贼感二人孝友,乃皆不杀。①《锲便蒙二十四孝日记故事》,第20 页。
在大约创作于18 世纪90 年代的诗歌《母亲与女儿》中,普费弗尔将注意力转向了女儿的孝道。该诗的故事原型《受杖悲泣》同样收录在《日记故事》中。原文为:“韩伯俞至孝,时有过,母杖之,大泣。母曰:往者杖汝常悦受之,今悲泣何也?伯俞曰:往者杖常痛,知母康健,今杖不痛,知母力衰,是以泣也。”②同上,第18 页。这一故事出自汉代刘向的《说苑》,三国时吴国将军朱然的墓中就有讲述该故事的《悲亲图》存世。历史上的韩伯俞本是男性,普费弗尔却将其改为女性,可能是为了笔下的孝行故事更为丰富,避免给人千篇一律之感。不过,在普费弗尔笔下,这个故事则多出了几分戏谑的意味,诗中写道:
在中国,那敬重白发老人/与棍棒教育都司空见惯的国家,/曾有位八十岁的老母责打女儿,/一个六十岁的顽皮孩子。/女儿恸哭失声,悲鸣不已,/母亲问道:“何至这般哀嚎?/我从前打你可是打得更重,/却从未听你哭得如此悲凉。”/“是啊,亲爱的母亲,你说得都对”,/女儿哽咽喊道,“唉,/年岁已使你的胳臂虚弱,/但正是这点,令我心碎。”③Gottlieb Konrad Pfeffel, Fabel und Poetische Erzählungen, Band 2.Stuttgart, Tübingen: Cotta, 1802, S.208.
在作为源头的中国故事中,韩伯俞虽然遭到责打,但他非但对母亲没有任何怨言,只想到母亲老迈,进而悲从心起,甚至比对自己挨打还要更加伤心,从而凸显了孝子对母亲的关爱。普费弗尔在诗中一边赞扬中国子女孝敬老人,一边又批评中国的棍棒教育;一面肯定女儿多年来孝顺母亲,一面又调侃她还是“顽皮孩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启蒙时代的教育家,普费弗尔似乎对带有专制色彩的棍棒教育能否取得成效颇为怀疑,因为不仅女儿到了60 岁还是“教育不良”,而且老母亲的棍棒显然未能令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当棍棒及身时,孝女的思绪早已云游万里。这不由得让人感觉这一幕中的棍棒教育与夸张的恸哭一样,都只是一套徒有其表的程式,多少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
四、结 论
回顾以上中国孝行故事在欧洲的传播历程可以看出,故事中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是其传播的动力之源。它们作为来自中国的孝行榜样,不仅为欧洲读者了解儒家思想、体验中华文化魅力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而且进一步强化了作为“道德伦理之乡”的中国形象。同时,中国孝行故事还为启蒙时代的欧洲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灵感。从普费弗尔在诗歌中改写的四个中国孝行故事来看,他颇为看重孝道的精神感召力和在道德教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不过,其后期创作的《母亲与女儿》一诗却带有一丝戏谑色彩。人们从中隐约可以看出,到启蒙运动后期,德国启蒙思想家已经从一味赞赏儒家伦理中的自然哲学成分转向更为理性的思考。虽然普费弗尔依然肯定孝道,但他对中国孝行故事中过度讲求形式的夸张成分已有渐渐疏远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启蒙运动后期德国思想家们对中国看法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