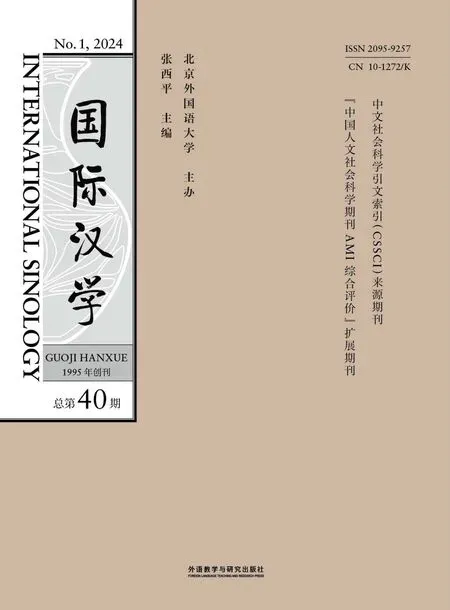塞尔维亚汉学家拉多萨夫·普西奇访谈录
□ 采访人:[塞尔维亚]碧莲娜(Biljana Simić Veličković)
□ 受访人:[塞尔维亚]拉多萨夫·普西奇(Radosav Pušić)
碧莲娜:普西奇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您多年从事汉学方面的工作,对中国哲学和历史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且在相关领域有译著出版。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的?您刚开始着手研究的时候,受到哪些启发?
普西奇:当我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过去的岁月时,就像所有人一样,我会看到跌宕起伏的历程,不过我也看到,尽管时间带来了种种变化,但其中一条线始终存在,它是发现生存意义、理解生活、对爱的追求的点的集合。从这些点出发,我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换句话说,我发现我与古代中国哲学在许多方面有共鸣,它能帮助我找到一些年轻人在面对大千世界时苦苦求索的答案。那时候我只有15 岁,刚上高中。尽管当时我还不清楚我的兴趣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是科学研究还是其他类型的研究,但我知道除塞尔维亚文化遗产外,中国与我最接近。从这个角度来看,动机和启发是多种的。一方面,我希望了解中国的思想、历史、艺术、文学、音乐,另一方面我希望找到一些关于生存意义的答案以及一个人在某个特殊时期想要创作某种有目的的作品。
碧莲娜:1985 年您毕业于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学院哲学系,2001 年获得博士学位。1981 年至1984 年,在上大学期间,您在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选修了汉语。您当时的汉语老师德扬·拉齐奇(Dejan Razić)教授对您选择研究中国文化有哪些启发?
普西奇:每当我想到或说到拉齐奇教授时,除了尊重,我还会感到非常深刻的爱。在我的许多老师中,他比较特殊。他极富天赋,可以向他的学生传达美、真理、信仰和善。我上大学时的专业是哲学,除此之外,我还在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选修汉语课。我记得,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27 个人,而到了三年级,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当然,这不是因为我比其他人更聪明,而是因为我对这门根本不易学习的语言拥有更多的爱、毅力和耐心。有趣的是,那年除了拉齐奇教授之外,我还有两名中国教授,他们是北京语言大学(当时称“北京语言学院”)的张维教授和南京大学的范彬教授。我对中国的态度深受他们的影响。一名学生由三位教授来教是极其难得的。那年,我和拉齐奇教授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有时我们会去斯卡达里加街(Skadarlija)上的餐馆吃晚餐,他会详细地跟我分享他的生活以及如何克服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他的话一直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当时,甚至今天,都是对我最大的启发。此后不久,拉齐奇教授病重。在我去中国学习的几个月前,他邀我去他家,嘱咐我带上书包,别问原因。那天晚上我到了以后,他将我带入他的书房,并指向他的中文书库,然后告诉我可以拿走所有我感兴趣的书。那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但是在他说不再需要那些书之后,我意识到他是在以这种方式向我和代表他一生的书做最后的道别。如果您问是什么促使我继续研究中国,那就是那天晚上以及我握在手里的那份珍贵礼物——中文书籍。当时我还看不懂,因为我的汉语水平还很低。但是那天晚上,我告诉自己:我会努力学习,有一天我一定会把我的教授、老师和朋友给我的书全都读完。就这样,很幸运,我信守了诺言。
碧莲娜:您是第一位把《老子》从古代汉语翻译成塞尔维亚语的学者。1997 年塞尔维亚版《老子》由世界出版社(Svetovi)出版了。请问您的这次翻译跟以往从英文到塞尔维亚文的翻译相比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如果读者不会说中文而且不太了解中国,他们是否能够理解《老子》里的一些概念,比如道、德、抱一、无为而为?当时在研究和翻译这本书时,您遇到了什么困难?如果您现在重新翻译的话,您会对《老子》里的概念有哪些新的理解和感受?
普西奇:《老子》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了我的生活。从我开始学习中文的那刻起,我的愿望就是有一天将这一文本翻译成塞尔维亚语。如果您问我所做的翻译的特点,答案很简单。首先,我是从中文翻译成塞尔维亚文的,这就是它与其他翻译的不同之处。与某人交谈时用对方的语言和通过口译交谈并非一回事。其次,如果说我的生活和我对世界的看法、对哲学的理解与其他学者有所不同,那这些不同或者说特色恰好反映在我的翻译中。《老子》的读者是否能够理解他的哲学基调?我不知道。这是留给读者的问题。我认为这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个人发现甚至获得老子在书中谈到的一些经验或技能,那么他自然就能够理解道、德、抱一、无为而为等。
我在北京大学参加关于中国古代经典作品翻译的国际研讨会(2014 年11 月1—2 日)时,会上谈到了在翻译《老子》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我指出,几千年的距离是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无论是谁,拥有多少知识、技能和能力,他都无法呼吸那时候的空气,不能喝那时候的水,也不会被那时候的阳光温暖。因此,对任何译者和《老子》译本都不应该有太大的期望。当然,这里指的也包括所有其他经典作品。另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古代汉语本身——尽管它有一定的语法规则,但它还有一个特点,即译者不仅需要把文字读出来,更需要感受到这些汉字背后的信息和氛围。这很难,但是我却很喜欢这一点。时至今日,在处理《老子》文本方面仍然存在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老子》最初的形式是歌谣,有自己的节奏。《老子》最早的记录之一是以当时的方言写的。麻烦的是后来的抄写者由于对文本节奏的不理解,对原来的文本进行了改动。所以我提供了两种翻译,试图在我的翻译中指出那些地方,而不去幻想我可以解决任何现有的问题。问题的第三个方面是老子所使用的词语是他独有的“技术术语”。您已经提到了最常见的道、德、抱一、无为,但还有一、二、三、玄门、气等。如何在不干扰文本结构和原始思想的情况下表达其含义是一种极大的折磨。因此,文本的处理方式是一种比较明显的悖论。文本只能由入“道”的人理解,而且他没有特别的意愿告诉其他人。言而不语,接近水和婴儿(更确切地说是胎儿),也就是说,接近道,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在翻译中很难传达这种沉默、柔和、和谐、简单、无声等。我手头有15 种以上的翻译版本,我选择出版的版本不是根据某些专业标准,而是因为当天我觉得那个版本是最有趣的。如果是别的哪一天,我可能会选择其他版本。放到今天,也肯定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给读者一个建议,那就是每个想要与老子交谈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中文,然后亲自加入对话。因为跟爱情一样,这是非常私密的关系,如果想接近“道”的话,是不应该有中介人的。实际上翻译只是译者对原文的个人看法,词语或汉字仅表示而不显示其真正含义。语言只能作为路标。但是,语言要带我们去哪儿呢?它可以直达情感、思想、想象、直觉、心理建设、编造、梦想等地方,一切都是允许的,因为这种关系是个人的。翻译实际上更能反映出译者是谁及其想法,而不能完全反映出老子的想法。这是因为老子根本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老子》这本书本身就藏着这种“狡猾”,它是最美丽的,又是最可怕的。无论其含义是什么,《老子》故事的背后是诗歌、音乐、呼吸以及与原始自然合而为一的艺术。
碧莲娜:在您的书《婴儿与水:中国先秦哲学故事》中,您提及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孔子、庄子、墨子等。您根据历史记载介绍了他们的生活,并对他们思想的关键概念进行了仔细分析和探讨,如孔子所提出的仁、礼、文、行、忠、信,再如墨子所提出的兼爱、爱人、利人、天意。请问塞尔维亚人(包括南斯拉夫人)对中国哲学和文明的了解程度如何?您认为中国古代思想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哪些思想与塞尔维亚人以及斯拉夫人的古代思想完全不同?您觉得通过哲学以及对古代思想的研究和翻译,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塞文化及人文交流吗?
普西奇:是的,我认为通过翻译和研究来诠释中国古代思想,可以促进塞尔维亚和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为了让双方合作,实现真正的沟通,首先必须彼此了解,而翻译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医学、日常生活文化中的文章、书籍和材料,有助于双方拉近距离。塞尔维亚人或南斯拉夫人民对中国哲学和文明的了解程度,体现在他们与中国事务有关的行动上。据我所知,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能说非常深刻,更不用说了解中国哲学了。当我们考虑中国和塞尔维亚文化矩阵的差异,或者中国和斯拉夫世界的文化矩阵的差异时,首先必须考虑到我们自己的差异。我们的文化有什么不同点?如果我们注意到并接受我们自己的差异,那么我们也许已经准备好面对如此遥远而又不同的中国文化矩阵了。
当然,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判断困难的。例如,1985 年我与中国的第一次“会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一直感到自己不是到了另一个国家,而是踏上了一个完全未知的星球。而且,别忘了,我可是坚信自己通过三年的汉语学习和阅读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已经做好了去那里的准备。
今天也许有所不同,也许中国与现代世界“更加接近”,也许它更渴望与其他国家和文化进行对话,但是我不确定肤浅的、快速的、简化的,并且在许多方面扭曲的世界图景,以及我们世界虚拟的和数字的现代性,能够理解和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的深层内涵以及它的每一层内涵。另外,在所有“非文化”的海洋中,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古代斯拉夫文化,这也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对于那些已经完全了解这两种文化的人来说,谈论异同很容易。正如庄子曾经很好地觉悟到“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这种状态只有那些与之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人才能实现,也可以说“命运的”关系,而其感情、思想和梦想是交织在一起的。最后,我们都聚集在意义和爱、愉悦与不满、美丽与丑陋、生与死之间。在中国和塞尔维亚,眼泪都是眼泪,只是它们的缘由不一样,而且氛围也不同。笑也是笑,但幽默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因此欢乐和悲伤带来的其他的一切也都不一样。但是,当我们更仔细地思考时,不仅是中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差异,而且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差异。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身边的人的悲伤或幸福,也许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来自中国的悲伤或幸福。这些基本的假设跟个人的成长、渴望以及对自我修养的热爱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了解自己,那么无论别人来自何方,我们都会了解别人。例如,孔子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仁,爱人也。
碧莲娜:中国哲学是不断发展的,在不断与外部思想的交流中演化,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宋明理学就是对佛教的一个理论回应。同时,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不断与本土思想融合,从而形成中国本土的佛教,如禅宗。您认为中国哲学最重要特点是什么?我们塞尔维亚人能否从中国哲学中汲取智慧?
普西奇:从汉朝到宋明时期,在中国土地上存在的思想、哲学、宗教运动的多样性很难简短地介绍——几乎不可能。公元前4 世纪,佛教传入中国,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它在当时的中原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这并不奇怪。在汉代,它与道教和儒家思想一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使时人对大自然和世界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不同的宗教运动和教义先后得以建立,它们介绍了各自对世界的看法。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为了能够被接受,必须使用一种当时的中国人都能理解的语言。因此,从一开始,它就接触道家、道教、儒教以及巫教。几个世纪之后,它们碰撞的结晶被称为“禅宗”。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中国数千年的哲学传统,三言两语很难介绍中国哲学的特点,特别是中国哲学各个时期在其哲学渊源上有很大的不同。我可以列举一些中国古代哲学的关键术语,例如:仁、乐、道、诗、礼、德、气、义、兼爱等,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们只是空洞的单词,没有特别的,或者重要的内容。原因很简单,我们已经远离了那时候的时代精神,远离了这些词语当时被创造和使用的语境,即有意义的生存环境。当我们远离这类事物时,我们不仅不能感觉到它的“呼吸”,甚至听不到那些时代的回声。我们对这些内容一无所知。当谈到唐、宋、明、清中国历代的哲学思潮时,也很难挑出任何特别之处,因为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各自的一切都是特别的。在谈论某件事时,必须提及周遭环境或导致这种事情发生的时代精神。这就是我们无法用几句话说出中国哲学特点的原因。但是为了回答您的提问,我将提供一个小小的参考,说明答案可能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即在所有时期的中国哲学中,有一条线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理论、思索内容与实践的连接,对身体不寻常的态度以及对自身变化的聆听,更确切地说是聆听我们内心深处的宇宙脉动。这意味着,在中国的世界形象中,我们是社会的、自然的、宇宙的生物。
就塞尔维亚而言,就像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在塞尔维亚可以从中国哲学实践以及任何其他实践中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需要和渴望学习。孔子在教育和学习中看到了人自我塑造这一本性的无穷可能性,人有可能改造世界,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但他必须顺应宇宙的发展规律。他的大多数思想、远见、建议、教训,在当时和今天都是非常适用的,因为它们存在于每个时代中。这里指的不只是老子,还包括墨子、庄子等人的思想。麻烦在于,我们倾向于对世界采取极端简化的态度,我们把所有传统,中国的、希腊的、印度的、斯拉夫的、阿拉伯的等都看成过去的传统,而我们忘记了即使是过去的事情,其中一部分可能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这种永恒的维度,人们不容易看见。而对于那些总是用概括且肤浅想法玩弄世人的人来说,正如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曾 经 说 过 的 那样——当然极具讽刺意味——“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不是因为它确实是最好的,而是因为人们不想了解其他的世界,虽然很少有人会相信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是最好的。任何人都将自己的存在缩小到一个很小的领域,可以被描述为:局限、愚蠢、硬性、无意义等。决定学习和拓展我们的视野,并真正地向他人学习,将是非常好的事情,而中国的哲学是全世界所知道的最有价值和最伟大的宝库之一。
碧莲娜:您写过关于耶稣会士的论文。在您的论文《中国和西方:上帝,爱及其他》(“Kina i Zapad: bog, ljubav i ostalo”)中提道:“尽管今天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活动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肯定对东西方文明的初次交流和对话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之一)”①此文被收录于《当代中国及其传统》(Moderna Kina i njena tradicija)论文集中,第180 页。。基督教的爱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墨子提出的“兼爱”有一些相似。很多基督教包括东正教的核心理念比如说十诫中的句子,与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概念比较相似。塞尔维亚人能不能以基督教和东正教去理解一些中国古代思想的概念?哪些基督教和东正教的概念和思想可以帮助塞尔维亚人理解中国古代思想?
普西奇:说“是”和“不”是最容易的。但是,更难的是解释“是”是什么,而“不是”又是什么。很难说一个人是否可以从一种传统中“跳跃”到另一种中去,并用自己的视野取代另一种视野。最好的例子是耶稣会士,他们试图将中国基督教化。先听听这个故事可能会有所启发,然后对是否可以通过基督教的某些概念和原则理解中国哲学并作出自己的判断。也就是说,当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1506—1552)从印度返回日本时,当他决定把任务扩大到中国,他知道如果没有中国人和汉语知识,那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8—1606)不久后作为东亚所有任务的主管来到中国澳门,他确定了在中国的传教的具体内容和开始时间。1579 年7 月,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抵达中国澳门,并在抵达后立即开始学习中文。面对繁重的任务和众多的困难,他要求上级派遣传教士来帮助他。在罗明坚的坚持下,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82 年来到中国澳门,并且开始学习中文。第二年他去了广州,1583 年9 月10 日,他与罗明坚一起设立一个常驻代表团。这个日期被视为耶稣会士在中国开始传教的日期。罗明坚和利玛窦是所谓的“主要以儒家和基督教作为主要战略方向”的中国传教团的发起人。耶稣会士估计,将儒家对上帝的讨论与基督教对上帝的看法连接起来,对他们的任务大有裨益,其最终目标是将中国的“上帝”彻底转变,让他穿上基督上帝的“礼服”。
由于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描述上帝,耶稣会士被迫在中国古典著作中寻找特定的表达方式,这将使中国人更接近上帝本身。他们最常使用《诗经》《周易》《尚书》,从中采用词语上帝和帝。他们从儒家那里借用了“父孝”一词,将其与统治世界大家庭的“大父”的存在联系起来。他们从“四书”中使用了“上帝”和“天”这些术语。显然,他们被迫使用了大量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基督教里的神,使其更加贴近博学的中国人。因此,当时使用了一系列中国哲学术语来传教也就不足为奇了:上天、皇天、天命、天子、帝、上帝、天主等。如果再加上1627 年12 月至1628 年1 月,11 位耶稣会士就如何更好地将“deus”(上帝)一词翻译成中文进行了辩论,并且如果我们牢记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的建议,将其翻译为大父母的话,那么基督“教育者”所面临的困难就更显而易见了。也有一些人说很难仅凭一个名字来理解上帝,作为论据,他们引用了圣经,其中以不同的名字启示了上帝。他们补充说,这些名字中的每一个都说出了他崇高本性的一部分,这是人类无法理解的。今天在汉语中,比较常用的是“上帝”和“神”。耶稣会士以极大的困难试图说服中国学者,天主教已经存在于中国传统中,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时必须让中国人相信,基督徒的讲道中没有异国情调,这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很难说他们此番解释有多么令人信服,但众所周知,今天中国基督徒仍然遵循这个矩阵。当《圣经》中著名的句子:“太初有词(逻各斯),词与上帝同在,上帝就是词”,翻译成中文时,我们有:“太初有道,上帝与道同在,上帝就是道。”当我们在翻译中引入“道”一词时,我们也随之引入了整个中国文化遗产。那是“逻各斯”吗?很难说。尤其是把“罗格斯”翻译成中文,即“理”,而它的意思是“宇宙原理,法律,起点”。我们可以说,基督教“爱”的观念与中国哲学家墨子提倡的古代中国“兼爱”思想有一些相同之处,但是奇怪的是,耶稣会士为什么没有把它当作两个文明矩阵的交汇点。我猜是因为这表明基督教在耶稣前在中国已经存在。这意味着耶稣会士应该被中国化,而不是将中国人基督教化。这种亲密关系的线索不太合适。
“爱你的邻居如你自己”这个想法也是墨子的想法。我们在基督教中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只是在基督教中,最高的爱不是对人的爱,而是对上帝的爱。
现在回到您的问题,对于那些心里有爱的人,有可能基于基督教和东正教的一些概念和原则来理解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爱”是基督教和东正教中的关键思想,可以帮助塞尔维亚人理解中国古代哲学。如果没有爱,我们就不能理解自己及其他与我们不同的人,但我担心的是,没有爱,我们的世界将会消失。
碧莲娜:您对老子和赫拉克利特(Heraclit,前540—前480)的思想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提到对这两位思想家来说,知识和智慧是对立的,在您的论文《道与罗格斯:老子和赫拉克利特的世界观》(“Dao i Logos: svetovi Lao Cija i Heraklita”)中,您写了“赫拉克利特强调‘很多知识不会教我们怎么成为聪明人(第40 分段)’,而老子的书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能够理解(道)的人不是有很多知识的人,而有很多知识的人不理解(道)’”。①普西奇的这篇文章收录于《珍珠里的米粒》(Biseri sa zrncima pirinča)论文集,第54 页。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应该为获得更多的知识去奋斗,而应该洞悉生活的本质、事物的本质、洞察自己以及对世界的看法?许多老年人,例如我们的祖父母,甚至没有上过学,也很聪明并有智慧。他们知道的许多生活准则,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能也不知道或不了解。老子和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智慧,可以这样理解吗?
普西奇:积累大量的不必要的知识跟受教育不是一回事。孔子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说,一个想要学习而又不想去思考的人是非常危险的。危险是因为鲁莽导致胡说八道:在他的无知范围内是危险的,因为可能已经获得了一些知识,但是由于无知总是无思想;他的自负使他很危险:对自己和他人生命构成危险。这些是老子和赫拉克利特的独到见解。因为他们也意识到这种丰富知识并不能让我们成为聪明人,反而会将我们引向另一个世界。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遵从古代先贤的教导。正如您所提到的那样,对基本要素即道和罗格斯的理解实际上是教育,但是教育作为自我认识和对世界的起点和本质的认识,应该是自我完善、自修,而不是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后却不知道如何使用。在缺乏这种需要的时候,积累各种知识,不仅不会引导我们去认识世界和自己,反而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困惑和无知,最后,困惑成了许多麻烦的根源。
您提到了我们的祖母和祖父,还包括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的祖母和祖父,他们聆听宇宙和自然的节奏,触摸、感受和品尝自己的内心和周围的世界,并具有独到的见解,那不是大量的知识或者空虚的故事带来的。离地球更近意味着离自己更近,因为如果我们把地球当作自己的母亲,她便像所有母亲一样,希望保持平衡,开始训练我们,使我们回到自己的根基,使我们谦虚,提醒我们不要走错路。她的教训一点都不客气,而这种“教育”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当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与大自然一起玩耍时,她会根据人类的能量与我们一起玩耍。地震、火山、洪水、病毒、疾病……难以理解的变化只是她回应的一小部分,这些只显示了我们招惹她跟我们一起玩耍的后果。虚拟世界和现代世界本身不一定坏,但是它揭示了人类一个非常丑陋的特征。一方面,它引起了无知的人对自己的意义和重要性的幻觉,而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些特点;另一方面,它剥夺了人类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使他们受现代技术的支配。轻易地沉溺于表面的、容易实现的、虚构的和想象的世界是危险的,任何没有宇宙和自然循环基础的世界,至少赫拉克利特和老子是这样认为的,都注定会覆灭。让我们记住赫拉克利特明智的见解:这个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任何没有分寸、超出其能量、过度使用自然馈赠的人,都将很快用完他从生活中得到的一切,最终因疲惫而放弃。这就是为什么老子说他所讲的道并不难理解,但是没有人需要这个。没有道的世界就是没有意义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无论您是大学教授、制鞋匠、街头清洁工还是诗人,都没关系,“所具备的知识”不是关键的,关键的是我们是否往意义转向。老子、孔子、赫拉克利特都对人没有幻想,他们知道大多数人不愿意在这条道路上受苦。他们知道人类对待自己、大自然和世界的轻松态度会导致毫无意义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自老子、孔子、赫拉克利特的时代到今天,人类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改变。一个人面临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变,只是氛围和场景有所不同。光芒四射又温暖的太阳依旧照亮并温暖我们,今日像过去一样,雨水还是雨水的味道;不幸的是,鸟类的数量越来越少(成千上万的物种灭绝了)。它们仍然提醒我们,在这个多样的自然世界中汇集了多少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