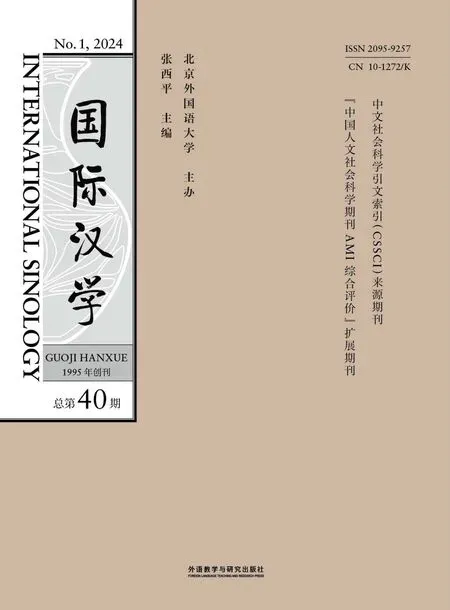“白蛇传”德语译介史述*
□ 段亚男
一、引 言
作为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蛇传”源自口头叙事,在口耳相传与集体共享中累积嬗变,传承不衰。早在唐人笔记小说《博异志·李黄(白蛇记)》中便出现白蛇化身美女,勾引迫害男子的故事;①(唐)谷神子:《博异志·李黄(白蛇记)》,载王汝涛主编《太平广记选(上)》,济南:齐鲁书社,1987 年,第507—511 页。南宋传奇话本《西湖三塔记》也塑造了白蛇精食人的故事,并将故事与西湖风物“三潭映月”相关联,抒写出奚真人作法将白蛇精等三怪镇压三塔之下的传说。②洪楩编:《西湖三塔记》,载洪楩编《清平山堂话本》,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 年,第17—25 页。这些早期有关白蛇精怪的记载勾勒出“白蛇传”故事的基本轮廓。其后,流传于民间的白蛇传说浩如烟海,但鲜以连贯完整的面貌呈现。直至明朝天启四年(1624)冯梦龙通俗话本小说《警世通言》第28卷中《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问世,赋予白蛇以人格化特征,塑造了许宣(许仙)、白娘子和法海等典型人物形象。③(明)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载冯梦龙《警世通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248—265 页。至此,街谈巷议的白蛇传说由文人写定,“白蛇传”故事得以基本定型。此后,“白蛇传”经不同传播媒介的演绎,成为一个兼具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多功能性中国故事,堪称民间故事经典化的代表作。
19 世纪,“白蛇传”首度传入德语世界。在近两百年的传播过程中,“白蛇传”在中德文化碰撞与交流过程中被重新演绎,从早期片段式的文本翻译不断衍化完善,催生出版本各异的译作,译者群体的构成也从汉学家推展到外交官、自由作家、医生等,彰显出中国故事跨越文化时空的感召力与生发力。不同译本的源流衍变,不仅是译者文化选择与文化自觉的思想溯源,也是寓于文化场域下文本审美价值的特定延伸,④徐畔、汪晓彤:《翻译之维度与阐释之限度——基于传统典籍域外传播的译介考察及文化思考》,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23 年第2 期,第91 页。折射出不同时期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认知与接受。
二、“白蛇传”译介之滥觞与底本考辨
“白蛇传”在德语世界的书面记载肇始于19世纪30 年代。1833 年,德国《外国文学杂志》(Magazin für die Literatur des Auslandes)刊 载 译文《药剂师和蛇:奇幻小说〈雷峰塔〉第一章》(“Der Apotheker und die Natter.Erstes Kapitel aus dem fantastischen Romane: Lui-pong-ta”),①Anonym, “Der Apotheker und die Natter.Erstes Kapitel aus dem fantastischen Romane: Lui-pong-ta,” Magazin für die Literatur des Auslandes 149.4 (1833): 593-594.正式拉开“白蛇传”德译序幕。事实上,该译文并非参照中文,而是从法国著名语文学家、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同年发表于《欧洲文学》(L’Europe littéraire)的法译文转译而来。②1833 年,儒莲将玉山主人的《雷锋塔奇传》第一章回翻译成法语,刊载于《欧洲文学》杂志,这是目前有据可考的最早关于“白蛇传”故事在西方外译的情况。参见Stanislas Julien, “Loui- Pong-Ta, oul’Esprit de la Couleuvreblanche, roman fantastique,” L‘Europe littéraire 2 (1833): 214-218。译者在后记中写道:“儒莲教授正在筹备出版整部小说,小说的第一章作为前奏率先在公众面前亮相”。③Anonym, “Der Apotheker und die Natter.Erstes Kapitel aus dem fantastischen Romane: Lui-pong-ta,” S.594.这里整部小说是指1834 年儒莲完成的首个法语全译本《白蛇与青蛇或两蛇仙,一部中国小说》,封面写有“白蛇精记”四个汉字,故该法译本常被学界简称为《白蛇精记》。该著由巴黎查尔斯哥塞林出版社(Librairie de Charles Gosselin)出版发行。该译本不仅是“白蛇传”故事在法国的首个全译本,也是欧洲地区的第一个全译本。Stanislas Julien, Blanche et Bleue, oules deux couleuvresfées, romanchinois.Paris: Librairie de Charles Gosselin, 1834。彼时,儒莲刚继任恩师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的职位,执掌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席,主张以科学的态度,从源头上认识中华民族,充分理解其真正的文化根基、内涵、形式,而不是去凭空想象或把它塑造成人们所希望的模样。④路斯琪、高方:《儒莲法译〈道德经〉的经典生成路径及呈现》,载《中国翻译》2020 年第1 期,第56 页。在他看来,与当时在欧洲闻名的《玉娇梨》和《好逑传》不同,“白蛇传”属于另一类中国小说,它根植于中国底层阶级的民间信仰,为中国下层民众所作,是宗教思想在民间创作中的反映。⑤Stanislas Julien, Blanche et Bleue, oules deux couleuvresfées, S.VIII.而从德语译者的译文后记中可以窥见,他转译这一中国故事的缘由之一在于这部小说能激发欧洲读者对中国仙幻世界这一未知领域的兴趣。⑥Anonym, “Der Apotheker und die Natter.Erstes Kapitel aus dem fantastischen Romane: Lui-pong-ta,” S.594.由此可见,早期西方学者翻译“白蛇传”并非出于“天然的兴趣”,其译介行为隐含着对于西方世界之外的其他文化圈层的陌生化倾向,⑦徐畔、汪晓彤:《翻译之维度与阐释之限度——基于传统典籍域外传播的译介考察及文化思考》,第93 页。意欲借助生发于中国民间的文学作品镜鉴中国状貌。⑧2015 年,该译文作为德国早期认识、了解中国文学的样本,被德国当代汉学家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收录在其编辑的著作《18、19 世纪德译中国小说》(Chinesische Romane in deutscher Sprache im 18. und 19. Jahrhundert)中再度发行。详 见Hartmut Walravens (Hrsg.), Chinesische Romane in deutscher Sprache im 18. und 19. Jahrhundert. Zur frühen Kenntnis chinesischer Literatur in Deutschland.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5, S.173-179。
但儒莲未曾到过中国,“白蛇传”文本如何侨迁至西方,目前学界尚无定论。⑨尽管未有确切资料显示儒莲从何处接触到这一中国故事,但据考证,至少可上溯至1829 年。1829 年(道光九年),包括李若瑟、吕玛窦在内的四名中国基督徒前赴巴黎遣使会总会学习,以备日后接受神职回国传教,但由于法国爆发“七月革命”,政局动荡,他们于1830 年11 月被提前遣返回国。这四人在旅法期间曾与雷慕沙、儒莲等汉学家和学者有所接触。参见李声凤:《道光九年四华人旅法事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12 年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 年,第283—294 页。尽管如此,该译文所参照的中文底本却有据可考。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理性主义和法国社会革命的影响下,“忠实性则成为重要的翻译准则,……尊重原著成为这一阶段翻译的最大特点。”⑩路斯琪、高方:《儒莲法译〈道德经〉的经典生成路径及呈现》,第57 页。而无论是回目还是叙事结构,首篇面世的“白蛇传”译文都与嘉庆十一年(1806)玉山主人校订的章回小说《雷峰塔奇传》极为吻合。儒莲在法译本前言中亦写道:“……作者以‘玉山主人’为名,是一位博学的名士,热衷研究传统古籍。当他在镇江遍访古迹遗址时,一位老者给他讲述了一个关于白蛇和青蛇的传奇故事。”①此处为笔者试译,法语原文如下:“…quiprenait le titreIu-chân-tchu-jîn (l’hôte de la Montagne de Jade), étaitunlettré célèbre qui recherchait avec ardeur toutes les traditions anciennes.Comme il visitait un jour la ville de Tchîn-kiang pour eхaminer les restes de ses antiques monuments, un vieillard lui raconta l’histoire merveilleuse de Blanche et Bleue…”, Stanislas Julien,Blanche et Bleue, oules deux couleuvresfées, p.XI。这恰好贴合《雷峰塔奇传》卷首吴炳文对玉山主人版本创作由来的介绍:“余友玉山主人,博学嗜古之士,新过镇江访故迹,咨询野老传述,网罗放失旧闻,考其行事始终之纪,稽其成败废兴之故,著为雷峰野史一编。”②玉山主人:《雷峰塔奇传·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年。据此推断,从法语转译而来的首个进入德语读者视域的“白蛇传”故事极有可能是玉山主人版本的《雷峰塔奇传》。
三、世纪之交葛禄博对“白蛇传”的译介
如果说儒莲对“白蛇传”西传而言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人物,那么生于俄国的德国汉学家葛禄博(Wilhelm Grube,1855—1908)无疑是推动“白蛇传”在德语文学中传播的先驱。19 世纪、20 世纪之交,葛禄博先后将不同体裁的“白蛇传”故事引介到德语世界。
不同于前几代德国汉学研究者,葛禄博接受过系统的汉学训练。他师从俄国彼得堡科学院院士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1818—1900)和德国著名汉学家甲柏连孜(Hans Conon 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在中国民俗与文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德国东亚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其论述中可以窥见,葛禄博读过法译本《白蛇精记》小说,但他首度译介“白蛇传”则缘起于他的首次中国之旅。1897—1898 年,他曾在柏林民俗博物馆(Königliches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③柏林民俗博物馆成立于1873 年,现为柏林民族博物馆(Ethnologisches Museum Berlin),是世界上关于非欧洲文化和艺术的最大、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也是柏林国立博物馆之一。在甲柏连孜的引荐下,葛禄博于1885 年在柏林民俗博物馆任职,并获得一次东亚之行的机会,先后在北京和厦门等地考察游历,并收获不少珍贵藏品。的资助下,赴北京实地考察并从事民俗研究。其间,他在《北京东方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撰文介绍北京的丧葬风俗:“送葬队伍中常见两位身穿白衣、黑衣的女性侍从,这正是对儒莲翻译的‘白蛇传’故事中白蛇和青蛇的演绎。”④Wilhelm Grube, “Pekinger Todtenbräuche,” Journal 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 IV.Peking: Pei-Tang Press, 1898, p.122.葛禄博译述了故事中白娘子求仙草救许仙的前因后果,以此推论送葬队伍中的白蛇和青蛇承载着人们的美好祈求,渴望逝去的亲人能像许仙一样起死回生。
1901 年,柏林民俗博物馆推出由葛禄博撰著的《北京民俗》(Zur Pekinger Volkskunde),书中不仅记录了北京当地的风俗惯习与民众的娱乐生活,而且对京剧知识及当地戏剧文化加以烛照,为西方戏剧学者提供知识供体。他撮录并翻译了“白蛇传”经典选段《雄黄陈》(“Der Schwefelzauber”)、《金 山 寺》(“Der Tempel Chinshan-sze”)和《断桥》(“Die zerbrochene Brück”)。⑤Wilhelm Grube, Zur Pekinger Volkskunde.Veröffentlichungen aus dem Königlichen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VII.Band, 1-4.Heft, Berlin: W.Spemann, 1901.这些出目为何引起葛禄博的兴趣值得注意。从故事情节来看,葛禄博选译的内容主要关涉“端阳”“求草”“水斗”“断桥”等出目,而这些情节主要围绕白娘子展开,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有勇有谋、至情至性的女性形象,其行动几乎被合理化为对许仙深情,与法海所代表的“佛法无情”和许仙的“怯弱无情”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如此,她依然“被统摄在威严的宗教宿命支配之下”⑥袁韵:《〈雷峰塔〉的儒释道文化阐释》,载《中国文学研究》2012 年第3 期,第83 页。,佛教对人欲的禁锢和人在佛法面前无法主宰自我命运的宿命在这强烈的冲突下尽数呈现。除了蕴含佛教文化精神,这些出目的道教和儒家文化色彩同样浓郁。一方面,无论是白娘子能由蛇身幻化为人形,还是求仙草复活许仙,抑或是与法海斗法,都是对道教法术的展现;另一方面,在这三篇选段中,白娘子的道德品行有着鲜明的儒家价值倾向,可以说儒家对女性的道德伦理规范在白娘子身上得以具象化地呈现,她为获得人伦之乐而进行的努力、抗争以及以失败告终,令故事在佛道宗教的外衣下折射出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①袁韵:《〈雷峰塔〉的儒释道文化阐释》,载《中国文学研究》2012 年第3 期,第85 页。
葛禄博选译该故事自然有其当下关怀。是时,奉行强权的德意志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推行激进的“世界政策”,大举加强对华活动,于是反映中国传统民俗与宗教信仰的文本尤为契合彼时德国社会需求,成为汉学家翻译研究的首选。葛禄博曾坦言,通过认识和解读生发于中国民众的民间文学,不失为了解中国及其百姓的一条有效途径,“中国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由于中国上流阶层对外国人保持封闭的状态,因而小说为读者提供了关于这个国家特性的最具启发性的见解”。②转引自宋莉华主编:《西方早期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珍稀资料选刊》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第247 页。而“白蛇传”戏剧的这三篇选段不仅展现了彼时中国社会儒释道文化的错综复杂,而且反映了神佛强权对人性的压抑,同时映射出百姓对封建制度下“存天理、禁人欲”的不满和渴望个性解放的自由意志,是一部“思想意蕴最为复杂深刻、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精神”③袁韵:《〈雷峰塔〉的儒释道文化阐释》,第85 页。的剧作。
1902 年,葛禄博将法译本《白蛇精记》小说的故事内容部分转述并翻译成德语,收录在其编写的《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中。④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Leipzig: C.F.Amelangs Verlag, 1902, S.438-446.从葛禄博以缩略形式转译的内容来看,故事内在的民族性和宗教性仍是其择译的首要驱动力。显而易见,其译本的目标群体并非限于汉学或文学研究者,而是面向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一般读者,向德国社会展现异于西方世界的中国文化特质。但葛禄博的翻译难以避免西方基督文化和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摄入而表现出单一的意义指向,他大幅度删减故事情节与人物角色,保留的核心人物多半关涉中国民俗文化或民间信仰,如观音、佛祖、西王母等,而带有宗教色彩的词汇,如金钵、寺庙、命运等词汇出现频率颇高,宗教指向明显。而与欧洲文体形式迥异的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叙事结构与文学表达样式则被忽略或“过滤”。
1904 年,葛禄博受邀参与19 册中国影戏剧本《燕影剧》手稿的翻译,⑤1901 年,作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探查队员的汉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从北京戏班那里收集了一批皮影戏道具和19 册影戏唱本的手稿,1904 年这些手稿转交葛禄博进行翻译。其学生夏礼辅对这些中文手稿进行了修订与补充,并将其整理成册,于1915 年在山东省兖州府天主教印书局主持印制了十六开精装本《燕影剧》中文原版,随后在德国莱比锡正式出版。详见Wilhelm Grube,Emil Krebs (Hrsg.), Yen-ying-chi.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1915.《白蛇传,五幕剧》(“Die Weiße Schlange, ein Fünfer-Zyklus”)皮影戏剧本被收录其中。该剧本囊括《借雨伞》(“Der Geliehene Schirm”)、《金山寺》(“Der Tempel des Goldenen Berges”)、《 断 桥》(“Die Zerbrochene Brücke”)、《合钵》(“Die Almosenschale”)和《祭塔》(“Das Opfer an der Pagode”)。遗憾的是,葛禄博并未完成全部手稿的翻译便于1908 年因病去世。他的学生,德国驻华公使夏礼辅(Emil Krebs,1867—1930)在其去世后接手这本文集的翻译,并对已完成部分进行整理润色。⑥《白蛇传,五幕剧》中的《借伞》、《合钵》(第一出)和《祭塔》由葛禄博翻译,《金山寺》、《断桥》、《合钵》(第二出)由夏礼辅翻译。直到1915 年,这部耗时十余年的中国影戏剧本德语译著由巴伐利亚科学与人文学院⑦巴伐利亚科学与人文学院前身为选帝侯科学院,由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约瑟夫(Maхimilian III.Joseph,1727—1777)建立,建立之初主要得益于王公贵族的资助和政治庇护,后来逐渐发展成由学者主导的学术交流和促进机构。详见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编:《美英德日科技社团研究》,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年,第129 页。发行。⑧该德译本编者为汉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他将该作命名为Chinesische Schattenspiele(中国影戏),并为其撰写绪论,介绍中国影戏的起源与发展历史。详见Berthold Laufer (Hrsg.), Chinesische Schattenspiele.München: Verlag der Königlich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15.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夏礼辅在译文注释中补充道:“这则五幕剧以小说为蓝本,……(1834年)儒莲曾将该小说译成法语”。①Berthold Laufer (Hrsg.), Chinesische Schattenspiele.München: Verlag der Königlich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15., p.1.据此可以推断,他认为这则《白蛇传,五幕剧》改编自玉山主人的《雷峰塔奇传》。但实际上玉山主人并未沿用前人版本中“断桥”的说法,而是重新虚构了“叠木桥”这一地名,且该剧目手稿是从北京一个戏班那里获得,属清代北京影戏剧本,因此认为该剧目取自《雷峰塔奇传》的论断并不十分准确。
四、战后两德对“白蛇传”的译介
两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废墟上重建,而且也给德国汉学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大批反对纳粹的汉学家迁移到了国外”。②张西平:《跨文化视阈中的德国汉学》,载张西平、李雪涛、马汉茂、汉雅娜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第15 页。在此局势背景下,“白蛇传”德译一度陷入停滞。直到20 世纪60 年代,德语世界关于“白蛇传”的译介研究又显露出复苏的新迹象,这一中国故事经过时代的淘洗后重新被西方读者熟悉。
1966 年,德国吕滕与勒宁出版社(Rütten &Loening)出版小说集《玉女:十二个中国古代故事》(Die Jadegöttin.Zwölf Geschichten aus dem mittelalterlichen China),摘选的12 个故事均取自明代冯梦龙、凌濛初编著的“三言两拍”话本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Die weiße Schlange”)亦被收录其中,③Liane Bettin, “Die weiße Schlange,” Jaroslav Průšek (Hrsg.), Die Jadegöttin. Zwölf Geschichten aus dem mittelalterlichen China.Berlin: Rütten & Loening, 1966, S.114-170.进行文本择选之人则是20 世纪50 年代著名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 1906—1980)④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曾任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院院长,是20 世纪60 年代布拉格汉学学派的奠基人和领导人,被誉为20 世纪下半叶国际汉学界内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参见马立安·高利克著,阎纯德、吴志良主编,张京媛译:《捷克和斯洛伐克汉学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年,第158—166 页。。普实克对这部小说集给予高度评价,并坦言希望欧洲读者能从正确的历史角度来看待这本集子中的故事:
一方面,这些短篇小说家扎根于人民。他们的作品首先为人民而作——这样大众化的环境使他们的作品具有生动的现实元素;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必须达到足够高的艺术水平,才能在高雅的文学鉴赏家那里得到认可。……毋庸置疑,这一双重目的是驱动其叙事艺术的强大推动力,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最好的中国短篇小说诞生于这一时期。从形式和风格上看,这种叙事传统对中国史诗散文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⑤Průšek (Hrsg.), Die Jadegöttin. Zwölf Geschichten aus dem mittelalterlichen China, S.410.
相较于此前“白蛇传”的德语译文,这篇译文蕴含着真切的人生体验与明确的教化意味,表现出对佛教的推崇,而儒、道相对没落。该作面世后不负众望,引发广泛关注,并在短短二十载由德国三家出版社六次重印发行。
受政治原因及文教政策的影响,⑥民主德国的生存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同苏联的盟国关系,20 世纪60 年代中苏冲突极大冲击了民主德国汉学发展,汉学研究和汉学家培养规模大幅度缩减。在此背景下,民主德国的汉学研究具有周密的计划性,且政治论题占有主导地位。参见坎鹏(Thomas Kampen)著,任仲伟译:《民主德国的中国学研究:科学计划、高校论文及自我描述》,载张西平、李雪涛、马汉茂、汉雅娜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第261—285 页。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当西德如火如荼地掀起对中国的革命狂热和对中国新文学的政治化接受时,东德知识界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和传播者陷入了沉默。”⑦顾文艳:《民主德国(1949—1990)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受》,载《国际汉学》2022 年第2 期,第137 页。民主德国翻译和发表中国文学的机会骤减,基本限制在古典文学,这反而促使一些汉学家回归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和古代通俗小说研究。1966年,德国汉学家梅薏华(Eva Müller)⑧梅薏华:《一辈子献身于中国文学》,载臧健编《两个世界的媒介:德国女汉学家口述实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11—29 页。在捷克布拉格汉学学派奠基人雅罗斯拉夫·普实克的支持与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前“白蛇传”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演变》(“Zur Widerspiegelung der Entwicklung der Legende von der weißen Schlange in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bis zur 1.Hälfte des 20.Jahrhunderts”)。①论文中译名参考自梅薏华自述。另据梅薏华所言,当时德国洪堡大学东亚所没有教授研究中国文学,其导师贝尔靖(Siegfried Behrsing,1903—1994)研究中国历史。但其论文写作得到捷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的支持和指导,“他对我论文的题目很感兴趣。”详见梅薏华:《一辈子献身于中国文学》,第17 页。她着眼于不同历史阶段“白蛇传”故事的精神旨趣与时代价值,探求这一中国故事在中国文学中的百年嬗变历程。②Eva Müller, “Zur Widerspiegelung der Entwicklung der Legende von der weißen Schlange in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bis zur 1.Hälfte des 20.Jahrhunderts,” Dissertation Humboldt Universität, 1966.
与此同时,儒莲法译本对“白蛇传”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影响历久弥坚。1967 年,库尔特·博斯哈默(Kurt Boshamer,1900—1981)夫妇在儒莲法译本基础上,将其翻译成德语,首部“白蛇传”德译单行本问世。③Johanna Boshamer-Koob, Kurt Boshamer, Die wundersame Geschichte der weißen Schlange. (Pai shek’ichuan). Chinesischer Geisterroman.Deutsche Bearbeitung u.Erläuterung nach der Übersetzung von Stanislas Julien.Zürich: Werner Classen Verlag, 1967.译者库尔特·博斯哈默表示,作为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儒莲意图通过“白蛇传”的翻译让法国人有机会从叙事风格、文体结构和表现方式等方面,了解此类中国小说,所以他逐字逐句进行翻译,但也因此损害了文体的流畅性与美感。④Ibid., p.9.概言之,儒莲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尽可能地体现东方思维,还原中国小说的话语方式,但也因此挑战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影响西方读者的阅读体验。基于此,博斯哈默夫妇尝试重新翻译这部小说,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增强小说内容和表达方式上的流畅性。
库尔特·博斯哈默强调“白蛇传”故事之于中国民众的特殊意义,“对于中国百姓而言,……这些妖鬼神仙都是不断变化的自然和世界的一部分”,“只有当人们意识到中国百姓在故事中看到的不是童话而是现实时,才会感受到整个故事的魔力”⑤Ibid.。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译者并非文学家或汉学家,而是联邦德国的两位外科医生。由此亦可窥见,“白蛇传”在西方的传播并未囿于专业学者的小圈子,而是渐渐潜入大众视野,成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重要桥梁。
五、统一后德国对“白蛇传”的译介
“80 年代的中国热冲击了德国社会”,⑥马汉茂著,廖天琪译:《德国的汉学研究:历史、问题与展望》,载张西平、李雪涛、马汉茂、汉雅娜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第26 页。中德文化关系逐渐回暖,德语世界汉学研究迎来新的时潮,玉山主人版本的《雷峰塔奇传》在时隔百余年后迎来首个德语全译本。1991 年,德国汉学家赖纳·施瓦茨(Rainer Schwarz,1940—2020)根据玉山主人的《雷峰塔奇传》原著将其直接翻译成德语,⑦Rainer Schwarz, Die wundersame Geschichte von der Donnergipfel-pagode. Leipzig: Reclam, 1991.并颇具新意地在译文中插入中国连环画“四小名旦”之一的颜梅华和颜志强创作的《白蛇传》连环画,⑧徐飞改编,颜梅华、颜志强绘画:《白蛇传》,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 年。由莱比锡雷克拉姆出版社(Reclam Verlag)出版。与早期译者不同,施瓦茨不仅看重“白蛇传”故事的民俗文化价值,而且颇为关注以其为代表的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在文体风格和叙事技巧层面的文学价值。⑨Rainer Schwarz, Die wundersame Geschichte von der Donnergipfel-pagode.Nachwort, S.161.他赞叹“白蛇传”“值得一读”:“一方面,‘白蛇传’是最受欢迎的中国传说之一,因此值得我们关注;另一方面,就其蕴含的所有想象而言,这部小说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的视角,从而成为人类发展的诗性见证。”⑩Ibid.
迈入21 世纪,“白蛇传”仍然显现出强大的生发力和影响力,且其在德语世界的译介突破了以宗教色彩、民俗信仰为选译首要原则,趋向颂扬白娘子对现世情谊坚贞执着、对现实命运不屈抗争的观念,显扬故事中富有全人类共有的生命精神与人性光辉的品质。2009 年,德国作家赫尔穆特·马特(Helmut Matt)重新编译“白蛇传”故事《白蛇传奇——中国的魔法世界》(Im Zauber der weißen Schlange—Magische Einblicke in ein geheimnisvolles Land),并在其中收录了中国画家任率英创作于20 世纪50 年代的连环画《白蛇传》中的13 幅图画。①任率英绘:《中国近现代名家作品选粹:任率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 年,第10—17 页。事实上,早在20 世纪90 年代,马特便在德国知名汉学杂志《东亚文学》(Hefte für ostasiatische Literatur)上刊文评述汉学家赖纳·施瓦茨翻译的《雷峰塔奇传》。②Helmut Matt, “Rezensionen.Die wundersame Geschichte von der Donnergipfelpagode,” Wolf Baus (Hrsg.), Hefte für ostasiatische Literatur, Nr.14, 1993, S.137f.此后,马特曾多次到访中国,并游览西湖。他盛赞“白蛇传”是一部“关于永恒与时间、爱情与激情、存在与消逝的伟大传奇”。③Helmut Matt, Im Zauber der weißen Schlange — Magische Einblicke in ein geheimnisvolles Land.Bad Schussenried: Gerhard Hess Verlag, 2009, Vorwort.在序言中,马特提及编译这一中国故事的来由:
这个国家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总是和文化价值紧密相连。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西湖堪称中国人眼中最美的地方之一。来自西方的游客们也不禁会被这古老的文化景致所深深吸引。若要感受她的全部魅力与浪漫,应当把风景与当地传说联系起来。④Ibid., p.7.
赫尔穆特·马特以简明扼要的16 个章节标题概括核心故事情节,故事脉络一目了然。整体来看,他保留了“游湖借伞”“端阳显形”“许仙复活”“法海与白素贞斗法”“白蛇生子”等“白蛇传”故事中的经典情节单元,但在叙事内容上做了不少改动,删改了大量细枝末节的情节,简化了人物关系,主要围绕许仙、白素贞、法海、小青四个主要人物展开,削弱了人物的复杂性与戏剧冲突,叙事框架带有明显的指向性和功能性。在他看来,“白蛇传”是一个衍生于西湖风景和百姓生活中的美好爱情故事,因此在他编译的“白蛇传”故事中,白娘子与许仙的爱情是行动主线,顺应人性、追求幸福与自由爱恋的勇气与行为是文本主旋律,所有情节指向也是为了突出这一核心话语。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减少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习俗的陌生感,便于情节展开,赫尔穆特·马特在文中详细解释了异于西方的文化风俗,包括古代中国婚礼习俗、饮茶文化、端午饮雄黄酒、中秋赏月、元宵灯会等中国传统节日、民俗仪式,也囊括了“西湖”“断桥”“雷峰塔”“昆仑山”等风物,以空间、节日、地方性知识为支撑共同推动叙事的发展,引导读者走进其建构的诠释世界。马特敏锐地看到这一故事里中国文化的异质性要素,并通过重新编译“白蛇传”的故事,将异质元素以契合西方读者的方式化为叙事单元,尽可能向德国读者还原景观中的“中国元素”,以帮助德国读者“以更知性、更开放的心态去感受中国的风土人情”,⑤Ibid., p.8.为中西方读者架起沟通的桥梁。
《白蛇传奇——中国的魔法世界》发行后引发不俗反响。德国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迅速作出反应,积极促成该作回译,2009 年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便推出该小说中德对照版本。⑥赫尔穆特·马特著,刘达、邓晓菁译:《白蛇传奇——中国的魔法世界》,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年。随后,该作陆续被翻译成英语(2012)、波兰语(2017)、克罗地亚语(2017)、马其顿语(2018)、阿尔巴尼亚语(2018),并出版发行,其影响力和关注度可见一斑。这无疑为助推“白蛇传”乃至中国故事在世界舞台的传播提供了有效借鉴。
除传统文本外,21 世纪“白蛇传”译介愈发多元。2015 年,德国斯图加特博物馆在德国教科文组织委员会的赞助下展出来自中国的皮影道具,并出版《皮影戏的世界:从亚洲到欧洲》(Die Welt des Schattentheaters.Von Asien bis Europa)一书,“白蛇传”故事作为中国皮影戏代表被收录其中,译者为慕尼黑五大洲博物馆馆长乌塔·韦利希(Uta Werlich)。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介绍世界皮影戏历史的论著择选了中国白娘子形象的皮影用作图书封面。①Uta Werlich, “Die weiße Schlange,” Jasimin Ii Sabai Günther, Inés de Castro (Hrsg.), Die Welt des Schattentheaters. Von Asien bis Europa.München: Hirmer Verlag, 2015, S.58.此外,中德译者合作成为新世纪“白蛇传”德语译介的新模式,一些精练、短小且通俗易懂的“白蛇传”译文拓宽了受众广度。但不少译文也暴露出新时期中国故事外译面临的困境,简短且偏向口语体的译文易于导致“白蛇传”故事文本的文学性大幅流失,丧失中国古典小说的诗意之美,且不少译文极大程度简化人物关系,仅以具有实际叙事功能的情节发展为主,侧重写实而忽略内在精神实质,译介深度有待提升。
六、结 语
纵观“白蛇传”德语传播史脉与接受情况,早期“白蛇传”德译以转译和概译为主,译文散见于中国文学及文化论著中。相较于文学层面的审美评述,此时“白蛇传”更多被西方世界当作了解中国风俗习惯与民众性格特征的媒介,故事的宗教性与民族性成为汉学家关照的重点,西方意识形态和强势文明对源语文本的操纵处于主导地位。尽管如此,这些早期译文为德语世界的中国研究开辟新径,加深他们对中国社会风俗的了解,个中价值不可等闲视之。“二战”以后,德语世界的“白蛇传”全译本迭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论著亦相伴而生,且对“白蛇传”的研究评述不再囿于故事的民俗价值与文化意义,关涉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学性与艺术审美得到一定程度地提高。东西德统一后,“白蛇传”德译依旧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译文趋向通俗化、故事化,偏好彰显故事主人公对生命意志和爱情自由的理想追求,但亦有译文忽略了文本的美学价值。如何兼顾中国故事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又不失其美学价值与文化烙印,成为新世纪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