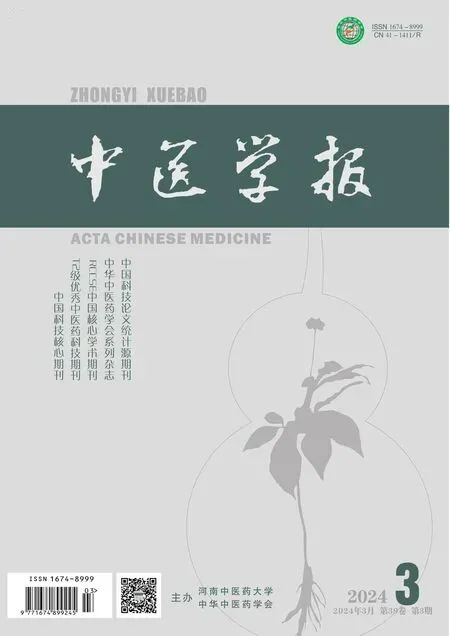蔡圣朝从风邪论治膝痹病*
黄俊,齐春伟,蔡圣朝
1.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8; 2.安徽针灸医院,安徽 合肥 230061
膝痹病,西医称之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本病是常见的一种骨关节炎疾病,其临床特征为关节周围组织的慢性炎症[1]。据调查本病在我国发病率约为18%,膝痹病初期症状较轻,若未及时治疗,随着疾病的发展,会引起关节畸形,甚至残疾,降低患者生存质量,为患者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2]。相较于西医保守治疗,使用药物所带来的不良反应,中医药及针灸则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蔡圣朝教授,主任医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幼承家学,至今已家传四代。蔡老自幼接受中医熏陶,熟读中医典籍,对中医有浓厚的兴趣,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蔡老师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老中医药专家周楣声教授,伺诊20余年,耳濡目染,尽得真传。现将蔡老诊治膝痹病的临床经验介绍如下。
1 病因病机
膝痹病在中医学中有“鹤膝风”“历节风”之称。蔡老结合自身临床经验提出膝痹病当以肝肾亏虚为本,以风、寒、湿、热、痰、瘀为标,二者合而为病,病情日久亦见气血亏虚。《黄帝内经》记载:“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溪[3]。”肾者属水,藏精而主骨生髓,人年四十,则阴气自半,五脏渐衰,天癸渐竭,肾虚髓败,则不能濡养关节。肝主筋,为诸筋之会,束骨而利关节,肝木生于肾水,肾水渐衰则肝木不生,水寒则木枯,生气亏败,故筋力消乏,行动不利。《医门法律》记载:“鹤膝风者,即风寒湿之痹于膝者。”蔡老提出诸标者又以风邪为首,万物以风气而长。风者,百病之长,亦为百病之始也。诸病之始,皆由经脏亏损,卫外失护,外感风邪,风邪开泄,腠理疏松,发而为病。物之润泽,莫过于气,气者熏肤、充身、泽毛、卫外,若雾露之溉。肝肾亏虚,筋骨失养,肾气不足,阳强失密,则风邪更易趁虚而入,流注关节。风邪夹寒,客于肌肤,阳化气,阴成形,阳气本虚,寒闭其表则伤形,形伤于皮肉或可外发为肿,屈伸不利。风邪夹湿,淫泆肌肤,湿气不除,阻遏卫阳,流注于关节,侵伤筋膜。湿蒸为热抑或寒邪束表,表气郁闭,郁而生热,热蒸其里则伤气,气伤则内郁而为痛。痰者水也,其本于肾,肾虚不能制水,水泛为痰,或聚湿而生痰,或热邪炼津而生痰,留注于关节。然而寒、热、痰诸邪,又可生瘀血,或久病则入络,膝痹日久,气血亏虚,血脉运行失畅,化生瘀血,阻滞局部。
2 以“五体理论”为基,以“风邪”为主
“五体理论”属于中医基础理论之一,首载于《黄帝内经》,即筋、脉、肉、皮、骨五体,“五体理论”既突出了各自独立的层次性,又重视五体之间的内在联系[4]。蔡老认为膝痹病的病程演变与“五体理论”相符,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内因以肝肾亏虚为本,外因则以风邪为首。风者,百病之长,易夹杂诸邪气侵犯机体,为主要致病因素。蔡老在临床中注重“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原则[5],以肝肾亏虚为本,以风邪为主,辨证施以解表疏风、温阳散风、通络搜风、燥湿祛风、清热宁风、养血祛风、化痰蠲风及填精逐风等治风之法。
2.1 其在皮者,治风而实皮在中医学“五体理论”之中,皮部是人体第一道防线,与外界直接接触,具有络属脏腑、运行气血及抵御外邪等重要功能[6]。百病始生,先于皮毛,外邪犯表,痹阻于皮部,腠理开泄,久之影响营卫之气运行,局部或出现皮温改变,或有僵硬、麻木不仁之感。此在皮者,当予解表疏风之法,风药在解表的基础之上亦具有疏通腠理、畅卫通经之效[7],常选取防风、独活、秦艽、威灵仙等药物散寒祛湿兼以祛风解表。风药体轻而善行,可胜湿,若其湿邪偏盛,亦可配伍苍术等燥湿之品;其人肾阳不足,推动无力,寒凝气滞,留于皮肤,可配伍桂枝、鹿角胶等温阳散风。现代研究表明,针刺可以有效降低膝关节内炎症因子的表达水平,改善膝关节局部血液循环及肌肉张力平衡,调控中枢神经疼痛传导通路[8]。膝痹病初期在皮,多责之于肺,肺在体合皮,因此本病初期可在局部选穴的基础上选取肺经穴位,如列缺、经渠等穴位,亦可选取与其相表里的大肠经穴合谷穴以及背俞穴调肺御邪。肺气受损,子病及母,亦可取足三里补益脾胃,培土生金。在临床中蔡老针对本病局部取穴常以“髌九针”即梁丘穴、鹤顶穴、犊鼻穴、阳陵泉、血海穴、内膝眼、阴陵泉、阴膝、阳膝等穴为主,辨证加减[9]。此时期为病变在表,针刺多以浅刺为主,刺激皮部,驱邪外出。亦可采取灸法,施灸于局部,灸法具有温经通络,散寒祛湿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提高机体抵抗力,有效改善局部症状[10]。
2.2 其在肉者,治风而荣肉肉部,相较皮部而言,其层次更加深入。肉在现代医学中认为其包含各种肌肉组织、脂肪组织及横膈、网膜等肉质器官组织[11]。中医理论认为肉为墙,分布于全身骨骼及关节周围,其不但是机体的保护屏障,而且还可以为关节提供动力性稳定的作用[12]。此时期可见膝关节僵硬、肿胀疼痛或局部灼热等,休息后缓解,劳作后加重。多因其人脾胃虚弱,或喜食肥甘厚腻之品,湿热内生,损伤脾胃,或风寒湿邪从阳化热,此当施以清热宁风之法为主,可配伍秦艽、苍术、黄柏等品清热祛湿及白豆蔻、石菖蒲等芳香健脾之品。或脾胃虚弱,气血化源不足,肌肉失于濡养,此当予益气养血祛风之法,兼以健脾,可配伍黄芪、桂枝、当归、白芍等。脾喜燥而恶湿,湿邪更易侵犯脾脏,或留滞肌肉,或化湿生痰,可灵活配伍薏苡仁、半夏、陈皮、茯苓等药物祛痰除湿。此时期主要与脾胃相关,针刺取穴可选取脾经及胃经穴位,如足三里、三阴交、中脘等穴位,亦可选取背俞穴,如脾俞、胃俞调理脾胃。有研究表明,足三里具有补益脾胃、活血通络以及显著的抗炎镇痛效果[13]。此期邪已入里,针刺应深刺到达肌层,在局部取穴的基础,若痰湿偏盛,可取阴陵泉、丰隆、脾俞等穴;寒邪偏盛者可局部予温针灸;气血两虚,可取气海、血海、足三里等穴。
2.3 其在脉者,治风而通脉脉即经脉和络脉,藏血而舍神,是人体运行气血的主要通道[14]。《灵枢·本脏》记载:“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15]。”脉以通为要,血脉不通则百病由生。蔡老认为此期虽病在血脉然其病机多与脾肾阳虚及痰瘀息息相关。五脏六腑之阳气,非肾阳不能温煦,肾阳为人身阳气之根本,阳虚则血行不畅,可见膝关节肿胀、疼痛、屈伸不利,或见局部刺痛,或局部络脉怒张等症状,此当辨证施于温阳散风之法,可配伍炮附片、肉桂、吴茱萸、鹿角胶等温肾助阳。或素体气血亏虚,卫外不足,风邪夹杂诸邪气乘虚而入,客于血脉,若气血不畅,加之外邪侵袭,化生瘀血,或膝痹日久,亦多见瘀血阻滞,此当予通络搜风之法,常配伍化瘀药,化瘀通络搜风,如川芎、牛膝、蜈蚣等药物。若湿热之邪侵袭,或寒湿之邪郁而化热,或其人喜食肥甘厚腻、嗜酒,而致湿热内生,湿热之邪留滞经络,阻滞于膝关节,出现关节灼热,疼痛剧烈,可选用威灵仙、知母、虎杖等。此期针刺在局部取穴的基础上,可取心经穴位及其背俞穴,如神门、心俞等穴位。心主血脉,取心经可调节气血运行并调养心神。同时可配伍气海、血海、内关、太冲等穴位以调气行血,疏通经络。血海穴,属脾足太阴之脉,此穴为脾经气血聚集之所,具有较强的补血活血之效,可调节气血运行,通则不痛[16]。内关穴,心包经之络穴,联络三焦,影响气血运行,太冲穴,肝经腧穴,有疏肝理气之效,二穴合用以调理气血,疏通瘀滞[17]。
2.4 其在筋者,治风而柔筋筋者,位于骨骼之外,藏于肌肉之中,纵横交错,具有维持骨骼稳定及关节运动的功能[18]。膝者,筋之府,若肝肾亏虚,肝血不足,则筋失濡养或劳累过度,损伤筋骨,或风寒湿诸邪气侵入,而至筋伤,则可出现膝关节疼痛、灼热、行动不利等症状,此时当以填精逐风之法,补益肝肾,标本兼治,可配伍鹿角胶、菟丝子、黄精等药物。若患者关节疼痛明显,可酌情配伍木瓜、五加皮、杜仲等;若湿邪偏盛,关节肿胀重着者,可配伍威灵仙、薏苡仁、炒苍术等;若膝关节明显屈伸不利,活动受限,可配伍木瓜、白芍、伸筋草、透骨草等药物;若久病血瘀者,可配伍土鳖虫、全蝎、蜈蚣等药物。对于膝痹日久的患者,蔡老在临床中常配伍藤蔓类及虫类药物,此因藤蔓之属,像人之筋,善走经脉,既可活血祛风,又可兼以“通络引经”,虫类药物多为血肉有情之品,善于搜经通络,对于膝痹病痹阻经络,疗效确切[19]。然而虫类药物久用伤阴,临床需加养阴之品予以纠偏[20]。此时期患者多肝肾亏虚明显,可在局部取穴的基础上,取肝俞、肾俞、关元等穴位补益肝肾。肝主筋,在临床中亦可酌情配伍肝经及肾经穴位,如行间、太冲、太溪等穴位。肝经与胆经相表里,胆经之合穴阳陵泉,八会穴之筋会,为机体筋气汇聚之所,膝为筋之府,阳陵泉对筋病具有显著疗效[21]。
2.5 其在骨者,治风而强骨骨,属于五体中最深层的结构,是脑髓和骨髓的外在防御器官,静止时构成人体的支撑框架,运动时表现为关节的屈伸运动[22]。膝痹病侵犯到骨部,多病程日久,迁延不愈,而至肝肾亏虚,筋骨失于濡养。此多以肝肾亏虚为本,复感外邪,或外邪入里,病程迁延。膝痹病进展到此期,其病因复杂,风、寒、湿、热、痰、瘀、虚等多种因素并见,但多以肝肾亏虚为主,此时当施以填精逐风法为主,重视补益肝肾,可配伍鹿角胶、黄精、何首乌、淫羊藿、菟丝子等药物。在重视补益肝肾的同时,兼以祛除其余病理因素,在填精逐风的基础上,灵活配伍化瘀、清热、补血、养阴之品,随证施治。若关节肿胀变形,此多因肝肾亏虚,骨髓失养所致,可配伍威灵仙、炒续断、炒杜仲、骨碎补等。《威灵仙传》阐述:“威灵仙去众风,通十二经脉,朝服暮效。”现代研究表明威灵仙具有抗炎镇痛、保护软骨、保肝等多重作用[23]。此期患者以肝肾亏虚为主,故取穴当以补益肝肾,舒筋止痛为主,可在局部取穴的基础上选取肝经、肾经穴位及背俞穴,如太溪、复溜、太冲、肝俞、肾俞等穴位补益肝肾。若膝痛不可屈伸,可配伍筋缩、大抒、悬钟等穴位;若瘀血阻滞,可配伍气海、膈俞等穴;若患者脾虚失运,可配伍足三里益气健脾;若见膝关节周围有明显络脉暴露,亦可予刺血疗法。现代研究表明刺血疗法是对血液和血管的双重刺激,具有改善局部微循环、调节神经肌肉以及调动人体免疫功能等多重作用[24]。
3 验案举隅
姚某,男,56岁,2022年3月29日初诊。患者诉双侧膝关节疼痛反复发作1年余。患者1年前体力劳动后突然出现双膝关节疼痛,活动后加重,下肢沉重。平素自觉双膝关节寒冷不温,遇风寒和阴雨天气则自觉加重,遇热则疼痛减轻,舌质暗红,苔薄腻,脉双尺沉弱。查体:双侧膝关节局部压痛(+),活动时有弹响,活动尚可。中医诊断:膝痹病,证属肝肾不足,寒邪内侵;西医诊断: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治法:补益肝肾,填精逐风。予以中药口服及针刺治疗。药物组成:酒黄精20 g,制何首乌20 g,淫羊藿20 g,炒白芍10 g,覆盆子15 g,菟丝子20 g,当归 10 g,川芎10 g,桑寄生15 g,桑葚子20 g,木瓜20 g,五加皮10 g,鹿角胶(烊化)10 g。14剂,水煎服,每日1剂,早晚分服。针刺取穴如下:肾俞、命门、关元、梁丘穴、鹤顶穴、犊鼻穴、阳陵泉、血海穴、内膝眼、阴陵泉;刺灸法:诸穴均平补平泻,其中犊鼻穴、内膝眼、鹤顶穴施以温针灸3壮,其余各穴得气后留针30 min,其间行针1次,每日施针1次,每周连续施针6 d,休息1 d。
2022年4月13日二诊:患者诉双膝关节疼痛减轻,但遇寒后仍有加重,舌质暗红,苔黄腻,脉滑。继续当前治疗。药物组成:酒黄精20 g,制何首乌20 g,菟丝子15 g,淫羊藿15 g,肉苁蓉片15 g,桑寄生15 g,川牛膝10 g,木瓜20 g,威灵仙20 g,炒白芍10 g,鹿角胶(烊化)10 g,干地黄15 g,地骨皮10 g,桑葚子20 g,锁阳10 g。14剂,水煎服,每日1剂,早晚分服。针灸取穴同前,刺灸法同前。
2022年4月28日三诊:患者诉膝关节疼痛明显好转,仅在活动及受寒后轻微疼痛,舌质暗红,苔薄,脉弦。中药守上方继服14剂,停针刺,嘱患者回家自行温和灸关元穴。
2022年5月13日四诊:患者现无明显疼痛,嘱其避风寒,避免负重。随访3个月未见复发。
按语:《黄帝内经》有言:“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患者年过半百,肝肾亏虚,正气不足,加之膝部劳损,局部经络失养,外邪趁虚而入,滞气涩血,不通则痛,迁延日久损伤筋骨。法当补益肝肾,填精逐风,兼以散寒除湿。方中酒黄精、制何首乌、淫羊藿、菟丝子、覆盆子温补肝肾,五加皮、桑寄生祛风湿兼以补肝肾,当归、川芎补血而活血,内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意,通则不痛,白芍养血舒筋止痛,木瓜舒筋活络兼以除湿,鹿角胶温补肝肾,滋益精血。蔡老临床中主张“无阴则阳不存,扶阳先扶阴,阴中求阳,则化源不竭”,故辅以桑葚子滋阴而益肾,于阴中求阳,阳得阴助则化源不竭。辅以针灸肝肾同补,筋骨并调,通络散寒止痛。二诊患者服药之后肾阳得复,气血得通,故去当归、川芎,配伍威灵仙以祛风湿,通经络,配伍牛膝补益肝肾,兼以引药下行。患者服用一派温阳之品,渐生热像,故予干地黄、地骨皮滋阴清热。继辅以针刺治疗。三诊患者症状不显,然考虑患者病程较长,故予守方继服,巩固疗效,嘱患者自行温和灸关元穴补肾培元,强身壮体。
4 结语
膝痹病是临床中常见疾病之一,西医目前以保守治疗为主,多予口服非甾体抗炎药等,疗效尚不明确,但会带来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如胃肠道反应、肝脏受损及毒性反应等[25]。中医方法治疗本病具有独特的优势。蔡老认为膝痹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与中医“五体理论”相符,在临床中当以肝肾亏虚为本,基于“五体理论”,以风邪为主,依据临床病情的差异,随证施治,施以中药、针刺、艾灸等多种方法,协同治疗,疗效确切,复发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