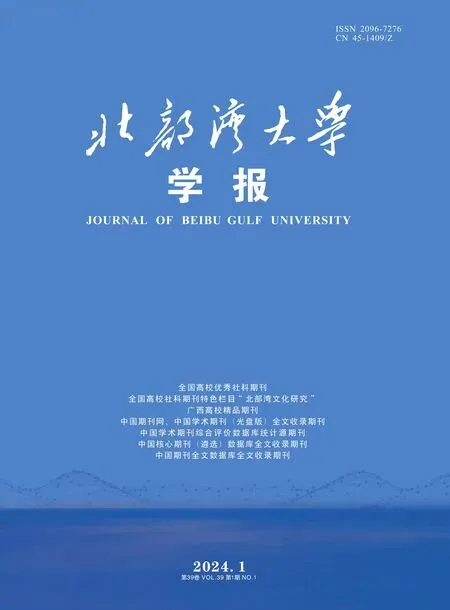常州词派词学“寄托”说的现代价值
——词学“寄托”说之二
景旭锋
(1.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2. 广西师范大学教务处, 广西 桂林 541004)
“寄托”,作为常州派的词学范畴虽然晚出,却是对整个中国古代诗学史“比兴寄托”说的总结。 钱锺书在《谈艺录·随园论诗中理语》中系统地进行了寻源溯流式的研究和评论。 从《诗大序》的“比兴之义”和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的“香草美人”开始,“比兴寄托”之说即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流行开来。 “风气既开,囿人难拔。 香艳之篇什,淆于美刺之史论。 至吾州张氏兄弟《词选》,阐‘意内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傅景物,推求寄托,‘比兴’之说,至是得大归宿。”[1]所谓“大归宿者”,即指以《诗大序》“比兴”说诗为开端的方式,到常州张惠言发端的“寄托”得以完备。 这就充分肯定了“寄托”说作为“比兴”诗学的总结地位。 但钱锺书在这里仍然将“寄托”理解为汉儒式的索引比附,这种理解体现了现代学者对常州词派“寄托”论词的总体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寄托”论词在批评实践过程中的深度阐释模式与美学张力。
一、 “寄托”何以可能成为独立的审美范畴
张惠言并没有直接使用“寄托”这一术语。 在《词选》及其对唐宋词的评介中,张惠言使用的是“比兴”“所兴”“寄意”“寓意”“用意”“所指”等词,这一方面说明张惠言并没有为词学建构“寄托”范畴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也说明古代诗学范畴内涵的丰富性与含混性。 就“寄托”而言,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与“比兴”经常缠绕在一起,殊难分解,以至于有人认为“比兴”就是“寄托”,“寄托”就是“比兴”,很少去作区分。 “所谓‘寄托’与‘比兴’犹如镜之两面,一明一暗,一表一里。”[2]因此,我们的辨析首先从这里开始。
李健在《比兴思维研究》中认为“比兴寄托”是弥漫于古典的艺术思维主潮。 “比兴寄托又简称兴寄,这一概念肇始于汉代。 ……比兴寄托似乎是同义反复的两个词,二者可以相互包容,比兴中有寄托,寄托必用比兴。”[3]112在李健看来,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提出的“香草美人”笔法是“以实证的方法分析屈原《离骚》中的比兴寄托。 比兴寄托在这里已经和盘托出,它是从比兴逐渐演化而来的诗学批评概念”[3]113。 诚然,“寄托”是从“比兴”逐渐发展而来的范畴,作为思维方式的“寄托”和“比兴”在诗词的创作实践中更是有着诸多的一致性,所以“寄托”之中包含“比兴”的传统内容,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据此认定二者就是一回事,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既是后世文人无意开拓“寄托”理论的缘由,也是后世文人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地忽视贬低“寄托”理论价值的原因。 故而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对“比兴”的继承与超越,使得“寄托”这一范畴从“比兴”中独立出来。 李旭的《中国诗学范畴的现代阐释》即从这一角度理解“寄托”,并将其定位为“常州派词学的基本范畴”,“本来‘比兴’‘寄托’就常州派词学来说是同等程度的范畴,意义基本相同,不可拘泥于词语。 但考虑到‘比兴’在诗学中使用时间更长、涉及范围更广,我们选用‘寄托’作为词学范畴,来揭示词体美学的一些独特的内涵,其中很多意义仍然是和‘比兴’相通的”[4]。 “不可拘泥于词语”是指陈匪石在《声执·比兴》中认为“张、周(笔者注:张惠言、周济)二氏之言,即毛诗学者之所谓‘兴’也。 ……名以‘寄托’,犹涉迹象也。”[5]在李旭看来,选用“比兴”还是“寄托”作为常州派词学的基本范畴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区别,仅仅是词语的差异而已,又因为常州派词学揭示了词体美学的一些独特内涵,故选用“寄托”以便于强调与诗学中使用时间较长的“比兴”的差异。 这似乎是说选用“寄托”作为常州派词学的基本范畴仅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并非为了辨别“比兴”和“寄托”的关系。
我们认为,将“比兴”和“寄托”分别限定在诗学和词学范围内,大致是妥当的。 这一限定并非是简单地区分诗与词之间的范围,而是从“比兴”和“寄托”这两个范畴对诗学和词学这两种体裁确实具有不同的意义来着眼的。 特别是对词学而言,以张惠言为开端的常州词派提出“寄托”这一范畴,自有其意义在。 首先,这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开山纲领——“诗言志”在词学中的落实,“诗言志”的触角深入到词学的领地并将其笼罩。 其次,这也是对词体美学地位的确认,是对词体审美特质的体认。 经学思维、诗学背景、政教诉求,这是张惠言词学思想展开的理论基石,正是在此基石之上,张惠言才合乎逻辑地提出“意内言外”,才以“诗之比兴”来规范“词之寄托”。 这一思维理路经过周济的推衍,从而在词学领域开拓出独立的“寄托”范畴[6]。 “寄托”对于“词学”的标志意义即在于此。 早在20 世纪30年代,詹安泰发表《论寄托》一文,名动词坛。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第一次以现代学术的眼光对“寄托”进行了理论上的审视。 尽管前有谭献“以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千古词章之能事尽,岂独填词为然”的高论,但詹安泰的论述仍然将其严格地限制在词学的领域之内,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足以说明“寄托”对于词体的独特意义,也说明“寄托”具有成为独立的审美范畴的可能性。
二、 “寄托”审美范畴从依附到独立
考察“比兴”和“寄托”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助于辨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区别与有机联系。
“比”“兴”这两个术语首次出现在《周礼·春官·大师》中: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7]796
《周礼》并没有对其作出具体的解释。 其后,《诗大序》改“六诗”为“六义”:
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7]
720《诗大序》的这一改动表明汉代经师对《诗经》的关注重点发生了改变:汉儒不再关注《周礼》所强调的音乐性,而是把焦点集中于诗歌内容所展现的政治教化作用上。 孔颖达的疏解便是在这一意义上展开的: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 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者是诗之成形。 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有篇卷也。[7]271
孔颖达的疏解显示出“释义”的努力,完全将“比”“兴”界定为诗歌艺术手法。 这是对郑众“比、兴”之释的继承。 郑众注《周礼·春官·大师》:
比者,比方于物也。 兴者,托事于物也。[7]796
孔颖达的疏解对此同样有阐述:
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 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 取譬引类,起发己心。[7]796
孔颖达阐述“比”重在比拟,阐释“兴”重在发端。 所谓“兴发感动”则源于此。 这种不涉及政教的观点对南北朝诗文评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黄侃因此特别称赞刘勰“辨比兴之分,最为明晰;一曰起情与附理,二曰斥言与环譬,介画了然,妙得先郑之意矣”[8]。
与郑众不同,汉末经学大师郑玄注“比”“兴”,将其与诗歌表达情感的委婉方式联系起来: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 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7]271
这种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显然与《诗大序》“主文而谲谏”的内在思路有着一致性,也启示着后世“寄托”意识的苏醒。 先于郑玄的王逸,“以实证的方法”分析出屈原《离骚》中的“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的特殊用法,更是这一思路典型的表现,《离骚》的“寓托”意识跃然纸上。
两汉之后的六朝,经学衰落,玄学大盛,审美成为时代的主潮。 虽然六朝人仍然分别解释“比”“兴”,但已经开始强调“比兴”的连用了。 此外,讽谏的要求已经匿迹。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之赞语:
诗人比兴,触物园览。 物虽胡越,合则肝胆。 拟容取心,断辞必敢。 攒杂咏歌,如川之涣。[9]
王元化认为刘勰坚持“比兴”必须综合在一起,因此在《比兴》篇的论述中肯定了“讽兼比兴”的《楚辞》而批评了“用比忘兴”的辞赋。 “‘用比忘兴’也就是徒知取象,不知示义,徒知拟容,不知取心的意思了。”[10]总览全文可知,刘勰《比兴》篇强调“比兴”作为艺术手法可以使文章更加生动隐约。 刘勰的贡献,首先是将“比兴”结合在一起使用,其次是使“比兴”从强调讽谏转而强调托物言情言志。 刘勰之后,钟嵘将赋、比、兴名之为“三义”,“寓托”意识更加明显: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 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11]
钟嵘强调“兴”的委婉含蓄,使“文已尽而意有余”,对常州词派周济的“寄托出入”说有直接影响。 钟嵘也是将“比兴”合在一起使用,而且同“赋”合在一起交错运用,这样可以解决表“意”之“深”与“浮”的问题了,作品主旨的合理表达受到关注。 作品主旨的表达方式受到关注之前,首先要审视的就是作品有无主旨。 钟嵘论诗的标准便以“寄托”之有无与“寄托”之深浅为其重点。 在具体的品评中,有如下评语:“托谕清远,良有鉴裁”(评嵇康)、“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评阮籍)、“托咏灵芝,怀寄不浅”(评郦炎)、“其体华艳,心托不奇”(评张华)。 这里开始透露出“比兴”向“寄托”转型的信息。
唐代,以陈子昂为代表的儒家诗学提出“兴寄”的概念,是对汉儒“比兴”诗学言志、讽喻和美刺的一次体认,也是“寄托”观念的一次较大发展。 唐代诗人大多在陈子昂“兴寄”的口号下进行诗歌创作。 白居易也十分强调“比兴”,并在内容上赋予它一种批判现实的规定性。 白居易赞美张籍的乐府诗“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12]5,论自己的诗“率有兴比,淫文艳韵,无一字焉”[12]104,又道:“自拾遗以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谓之讽喻诗”[12]2794,可见他所谓的“比兴”,是和“美刺”“讽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干预性,这既是对六朝诗歌风气的反拨,也是向汉儒解诗的回归。朱自清对白居易“比兴”论诗的意义看得很明白,《诗言志辨》有云:
从唐宋以来,“比兴”一直是最重要的观念之一。 后世所谓“比兴”虽与毛、郑不尽同,可是在论诗的人所重的不是“比”“兴”本身,而是诗的作用。 白居易是这种诗论最重要的代表。 ……后世论诗所说的“比兴”并不是《诗大序》的“比”“兴”了。 可是《大序》的主旨,诗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发乎情,止乎礼义”,却始终牢固地保存着。 这可以说是“诗教”,也可以说是“诗言志”或诗以明道。 代表这意念的便是白氏所举“风雅”“比兴”“美刺”三个名称。 ……白氏以后,“比兴”这一名称用得最多。[13]
在古代诗学批评史上,“比兴”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这里再次得到体现。 不仅如此,“比兴”的观念蔓延到词。 这是“比兴”诗学观念笼罩性影响的结果,也为“寄托”在词中的出现再次注入理论的活力。
宋人已经开始以“比兴”“寄托”论词,但将“寄托”观念真正发扬光大还是在于张惠言等常州词派的揄扬[14]。 张惠言与周济之后,畅论“寄托”者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道:“夫人不能无所感,有感不能无所寄。 寄托不厚,感人不深”[15],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道:“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 如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皆是”[16]546;沈祥龙在《论词随笔》中道:“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斯寄托遥深,非沾粘焉咏一物矣。”[17]“自常州诸词老论词专重意格,鬯言比兴,力崇词体,上媲风骚,以深美闳约为主,以醇厚沉着为归,阐发‘意内言外’之旨。 于是‘寄托’之说,霞蔚云蒸,倚声之士,咸极重视。”[18]张、周二氏之后,以“寄托”论词为词人之习语,“寄托”在千余年的流变中也终于正式成为中国词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以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千古词章之能事尽,岂独填词为然?”在谭献看来,“寄托”不仅仅是“填词”所特有的艺术途径,而且也是一切文学创作所遵循的普遍规律。
三、 “寄托”作为独立范畴的意义
“寄托”作为独立的范畴,对于传统诗学究竟有什么意义?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回到传统诗学的发端处。
中国“诗学”传统是从“学诗”开始的,“不学诗、无以言”乃圣人雅训。 学诗的第一步就是通过对语言文辞的理解从而知晓诗歌的意义与诗人的志向与意图。 《万章》篇记载了孟子和学生咸丘蒙“学诗”时的一次对话:“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从性善论出发,认为人的天性都是一样的,解说诗歌的说诗者是完全有可能理解诗歌创作者之内在动机与创作意图的。 古代的注疏传统常常把焦点集中在“说诗者”的“意”与“作诗者”的“志”能否契合的问题上,因为“诗言志”。 在强大的作者中心论的宰制下,读者常常处于从属的地位,面对作者的绝对权威,读者往往是被动的角色,无法对诗歌文本的意蕴提出独立的见解。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对张惠言最有力的反驳是“知人论世”即考查作者的创作意图与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 张惠言视温庭筠为旗帜而大加赞扬,对此,李冰若在《栩庄漫记》中批评道:“飞卿为人,具详旧史,综观其诗词,亦不过一失意文人而已,宁有悲天悯人之怀抱? 昔朱子谓《离骚》不都是怨君,尝叹为知言。以无行之飞卿,何足以仰企屈子”[19]。 对张惠言批评实践的最大指责是疏于考证、不辨本事。 谢章铤就曾指出:“《尊前》《花外》……必欲深求,殆将穿凿。”“东坡之《乳燕飞》,稼轩之《祝英台近》,皆有本事,见于宋人之纪载。 今竟一概抹杀之,……独创新说。”[20]王国维则声称:“固哉皋文之为词也! 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 皆被皋文深文罗织。”[21]挑战传统总是充满风险的,而这也是张惠言屡屡受到批评的根本原因。 文本的意义不一定就是作者的意图,文本不是一个固定的容器,作者的意图也不是随物赋形的万斛泉源。而阅读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有的理解都是生产性的,理解的目的是添加意义而不是寻找意义,理解总是另有所解。 读者对文本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有效解释,为了使文学发生,读者其实和作者一样重要。 谭献则以周济的“寄托出入”为本,明确提出了“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心何必不然”的时代强音。 事实上,尽管常州词派在建构“寄托”解词的过程中有着极端化的表现,张惠言的“寄托”确实也存在着穿凿附会的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寄托”作为独立范畴,赋予读者参与重建文本意蕴的权利,赋予词学一种几乎全新的阐释模式和批评话语。 而以读者为中心的批评模式,直到接受美学的兴起才逐渐为学界所承认。
“寄托”作为独立范畴,是与“意内言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言能否尽意是哲学持续探讨的问题。 庄子笔下的轮扁对“言能尽意”的嘲讽,始终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心结,“言”“意”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传统文学批评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含蓄”与“寄托”作为两种解决言意间距与矛盾的手段,常常被混为一谈。 叶夑认为:“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妙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 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22]叶夑的论点代表的是当时普遍的看法,但事实上,“‘言外之意’,说诗之常,然有含蓄和寄托之辨。 诗中言之而未尽,欲吐复吞,有待引申,俾能圆足,所谓‘含不足之意见于言外’,此一事也。 诗中所未尝言,别取事物,凑泊以含,所谓‘言在于此,意在于彼也’,又一事也,前者顺诗利导,意即蕴于言中,后者辅诗齐行,必须求之文外。 含蓄比于形之于神,寄托则类形之于影”[23]。 由此可知“含蓄”和“寄托”是两回事。
在解决“言”“意”矛盾的策略上,“含蓄”注重的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美学效果,一唱三叹、余味无穷是它的美学特征。 它要求在有限的语言文字之内表达多重的意蕴,引发读者无限的联想空间,故而“文外之旨”“文外重旨”就成为特别重要的手段。 刘勰《隐秀》篇中强调的“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隐以复义为工”,可以说首次阐明“含蓄”的美学效果在于话语蕴藉的多重性。 在《定势》篇中刘勰将命意浅显直白的作品全部称为“综意浅切者,类乏蕴藉”,可见其对“蕴藉”之美的重视。 刘勰极力倡导“深文隐蔚,余味曲包”之作,影响到皎然的诗歌理论,“两重意之上,皆文外之旨……但见性情,不睹文字”,进一步丰富了“含蓄”的多重蕴藉性。 其后,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将“含蓄”表述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极力突破语言的局限性与有限性,增强文字的修辞性、修饰性与暗示性,给读者一个无限自由的联想空间,使“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味”“韵外之致”充分激发读者在有限的语言文字之外体味无限的意蕴。 “含蓄”是中国诗学与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其哲学基础是言与意之间存在的矛盾关系。 在这个独特的哲学基础之上,言意之间的矛盾张力构成了文学“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殊效果。
“寄托”则不然,张惠言具有深厚的经学背景,是清代易学三大家之一,其言“寄托”,则力主微言大义。 “含蓄”的美学效果是言尽而意未尽,已经知晓的意义在表层文字中表露无遗,期待探究的意义在表层文字之外。 “寄托”则追求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的艺术效果,正所谓“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 作为一种策略,“寄托”则是主体情感有意识地进行自我遮蔽的手段,侧重于诗人情志隐蔽化的表达,属于创作手段。 晚清学者刘熙载的《艺概·词曲概》对此有很好的阐述:“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 如寄深于浅,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16]546词具有抒写文人隐秘情志的独到品质,张惠言在《词选序》中反复致意:“风谣里巷男女哀乐”“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以及“低徊要眇”之情,均可以通过词体来描述,使之获得独立的审美意义。 “寄托”所承载的情志,往往为主体所刻意遮蔽,“以不言言之”。 托物言志或托物寄情是“寄托”最常见的艺术手法,它强调的是对“物”的依赖。 这种依赖,或者延续了寄情于物之际的情感,或者转化为作者刻意表达的意志,是从假借于物开始最终超越假借于物而达到物我交融的结果。 正如钱锺书所言,“寄托”则如形与影,以影写形,以虚显实,是一种对直接表达方式的回避。 而作为艺术手段,“寄托”具体要通过意象与事象的塑造编织来实现,同时,它也要求饱满的情感与意志落实于词体之中。
四、 “寄托”说的当代价值
常州词派词学思想及其“寄托”范畴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处于争议之中,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对政治性的比附上。 进入21 世纪以来,这种看法在逐渐发生变化。 许多学者的分析与论述已经指出这是阐释共同体的差异而已:身处传统之中的张惠言及其常州词派学者极具深厚的历史意识,他们通过重建诗歌与历史的关系来阐发作品的思想意义,具有合理性。 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将“结论”称为“政治批评”,“‘结论:政治批评’并非打算意味着:‘最后,一个政治的替代’;却打算意味着:‘结论是我们已经考察的文学理论是具有政治性的。’”[24]197在伊格尔顿所考察的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有俄国形式主义,有现象学、诠释学与接受理论,有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有后结构主义与精神分析,这些理论大多是强调在文学理论自主性的号召下相继发展而来,但就是这些所谓的“纯”理论,都无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 所以,“文学理论不应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谴责,应该谴责的是它对自己的政治性的掩盖或无知”[24]197,当然,在这种思路之下,就不能将政治简单地理解为僵硬的意识形态。 陶东风在《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一书中曾引阿伦特的话道:“政治乃是人的言谈与行动的实践、施为,以及行动主体随着言行之施为而做的自我的彰显。 任何施为、展现都必须有一展现的领域或空间,或者所谓‘表象的空间’,以及‘人间公共事务’的领域。”[25]作为常州词派的开拓者,张惠言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其为文为词,虽多有在今日看来已经完全过时的阐道翼教之作,但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学人的确是以自己的行动与实践努力进行自我的彰显,极力站在公共的空间发言。 张惠言坚守着儒家以德为本、美善相兼的悠久传统,而其所交,多为贫寒之士,在这种寒士心态的影响下,又经受着乾嘉经学的熏陶,所以往往以诗教复振为己任。 故而可知,常州词派的词学思想,在推求词旨时表现出泛政治化的倾向,其合理性正在于此。
作为在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体,词具有可以抒写文人情怀的独特品质,词学讲“寄托”有着更贴切的文体优势。 “男女哀乐”“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以及“低徊要眇”之情,都能通过词来描述。 正是这一点,使得词体由早期的教坊娱乐演变为士大夫的抒情工具。 而词学在清代争取正统地位的艺术抗争中,使得“寄托”这一范畴从此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以更加具体的含义得以确立,并对词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寄托”其对“比兴”传统的继承与超越,是对中国抒情传统文学的创作经验的总结,为初学词和创作有成的词人提供了进入创作和更上层楼的具体可行的道路,同时也为一般的读者与全力为词的评论家提出了如何欣赏作品的可靠途径。
——兼论梅里词派及浙西词派的形成过程》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