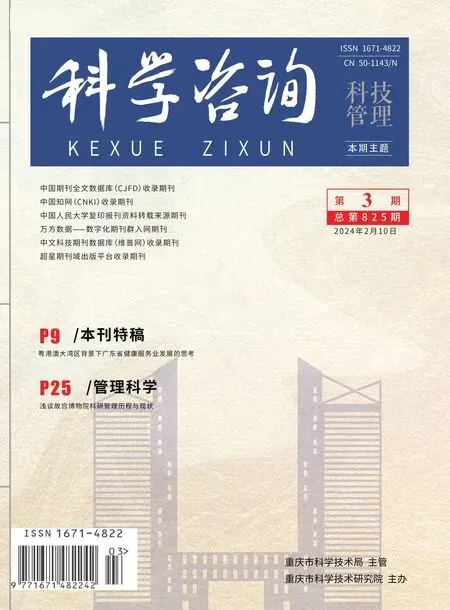从《氓》与《孔雀东南飞》的婚变看中国古代女性意识的觉醒
欧阳瑛,马香梅
(1.广州市从化区第二中学,广东广州 510920;2.广州市从化区从化中学,广东广州 510920)
人类在迈入文明时代之前,曾经历过以女性为主导的母系社会,“民知母而不知有父”。父系时代的起源,史无所据,但社会学者普遍认为,男子凭借其膂力掠夺氏族女子并独自占有,可能标志着母系社会的衰落之始。《易·爻辞》中的“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匪寇婚媾”描述的即是原始时代掠夺婚姻的真实状况。掠夺婚姻的盛行,标志着父系社会已取代母系社会,并逐渐形成了宗法的家族制度。宗法组织的核心是家长的威权,定于一家之尊,而子女则是父母的附属品,女子更是男子的附属品。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妇女的地位被深深嵌入宗法制度之中。“男尊女卑”成为当时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女子的悲惨生活因而拉开了时代的序幕。纵观三千年的妇女生活史,她们早被宗法礼教禁锢在狭小的家庭之内,饱受摧残与蹂躏。然而,历代也有不愿成为男人附属品、不甘居于被奴役地位的女子。她们不顾宗法礼教的制裁,挺身而出,为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婚姻而誓死抗争。例如,《氓》中的女主人公和《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便是敢于冲破宗法礼教藩篱,追求个性独立与婚姻自由的先行者。
《氓》出自《诗经·卫风》,是一首自诉爱情婚姻悲剧的诗歌。该诗中的女主人公以沉重的口吻回忆了恋爱生活的甜蜜以及婚后被丈夫虐待和遗弃的经历,诉说了自己的悔恨心情与决绝态度。这位女主人公的遭遇深刻地反映了古代女子备受宗法礼教的压迫和摧残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女性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自由婚恋的反思。
古时的女子因经济不能独立,唯有依赖家庭与男人而生。因此,女子一生的大事便是出嫁。出嫁之后,“大事毕矣”,可见婚姻对于女子的重要性。《氓》中女主人公的女性独立意识觉醒,是个体潜意识的自我唤醒,源于女性对美满幸福爱情生活的本能渴望。其独立意识的觉醒主要体现在自由恋爱、私定婚期、反省婚姻三个方面。
追求自由恋爱是女主人公独立意识的萌芽。《氓》中女主人公所生活的周朝,是一个婚礼制度并不严格的时代。男女之间的交往相对较自由。《诗经》中说:“明年仲春,若不待礼会之也”。《周礼》记载:“以仲春之月会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这反映了当时男女私下恋爱的真实情况。因此,尽管受宗法制度的约束,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仍然是可能的。女主人公与氓是在“抱布贸丝”的市场中邂逅相识。可能是女主人公的美丽善良触动了氓的心,或是氓的憨厚诚实赢得了女主人公的心,他们开始秘密相会,倾诉衷肠。女主人公内心渴望纯真的爱情,希望选择心仪的伴侣,渴望一生和谐美满。在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下,她私下把自己的心交给了氓。这可以说是她内心向往并付诸行动的大胆尝试,也标志着她独立意识的萌发。正是这种自我独立意识的萌芽,促使她勇敢地迈出追求两情相悦的第一步。因此,在碧水荡漾的淇水之滨,在春光明媚的顿丘之上,她与氓沉浸在浪漫的爱河之中,一同占卜吉凶,憧憬美好的未来。
私定结婚日期是女主人公独立意识的确立。《氓》所处的历史时期,虽然宗法制度不如后世严酷,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习俗依旧盛行。《诗经·南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这表明婚姻依然是由父母决定,由媒妁往来传递婚姻信息。况且,婚礼是传宗接代的大事。《礼记·经解》言:“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这表达的意思是只有经过婚礼的女子,才能成为自己的配偶,对于其他女子,则必须恪守男女之大防。《礼记·郊特牲》认为夫妇是人伦之基,是“万世之始”。所以,即便女主人公与氓私定终身,但要步入婚姻殿堂尚需经历议婚、定亲、亲迎、成婚等婚姻之礼节。否则,男女如果私下“淫奔”,就会受到家庭与社会的耻笑。《孟子·滕文公下》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氓》的女主人公虽然私相爱慕、谈婚论嫁,但氓并未有媒妁之言,而女主人公亦未得父母之命。所以,对于婚期的约定,女主人公的内心应是忐忑矛盾的,一边是挚爱之人,一边是宗法之俗,如何取舍是她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因此,氓每次借“贸丝”幽会,女主人公是知其“贸丝”的用心。其“贸丝”的目的即是“谋我为室家耳”。想必女主人公起初虽与氓约定了婚期,但后来迫于世俗的压力或父母的威慑,她可能爽约而“愆期”了。因此,女主人公在“涉淇”之时面对氓的催促与恼怒,才有“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的劝慰,并承诺“秋以为期”。由此可见,女主人公在选择婚姻之时,曾有过彷徨的焦虑,甚至有过退却的动摇,但她最终还是挣脱了宗法礼教的束缚,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一生幸福托付给了氓。女主人公私定婚期,足以说明女性的独立意识已经在她心中生根发芽。她将自己的婚姻决定权牢牢地攥在手中,不再听命于世俗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跟随自己的内心去选择自己喜欢的爱情与婚姻。对她来说,每一个女子都有选择自己婚姻的权利。正是这种独立意识的觉醒,给予了她挑战宗法制度、自主选择婚期的勇气。因此,即便与氓的婚姻不合宗法礼教,即便是未来的婚姻生活无法预知,她也愿意氓在“秋”期“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来迎娶自己。
反思婚姻失败标志着女主人公独立意识的成熟。在《诗经·氓》中,女主人公尽管未按宗法礼教的传统聘娶仪式结婚,但她与有情人最终成为伴侣,展现了她自主选择婚姻的决心最终得到了肯定。可能是因为对婚后生活有过多美好憧憬,女主人公婚后尽守妇道,勤劳无懈,但现实并未如她所愿般美好。尽管她辛勤地承担家务,全力以赴,却未能得到氓的认可。反而,曾经深爱她的氓变心了。从“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到“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以桑树的变化比喻女主人公的容貌从青春到衰老,同时也暗指氓对女主人公从婚前情意绵绵到婚后色衰爱弛的心理变化。欧阳修说:“‘桑之沃若’,喻男情意盛时可爱;至‘黄而陨’,又喻男意易得衰落尔。”这样的比喻正对应了氓最初的热情到最终的离弃——“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不可否认,在宗法制度下的男尊女卑让女性在婚姻中容易受到歧视和责难,哪怕女子再柔顺贞静、无非无仪,也难以逃脱被摧残的悲惨命运。正因如此,女主人公对自己所选择的婚姻进行了深刻反思。她明白,在宗法礼教制度下,男女对待婚姻的态度本质上是不同的。《大戴礼记》说:“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由于这种观念,女子没有独立的人格,只能依附于男子生活。所谓“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所以,女子既以“已与之齐,终身不改”为出嫁之标准,就必须将自己一生的幸福寄托在男子身上,就必须心甘情愿地承受许多不平等的待遇。男子可以自由抛弃妻子,而女子则须恪守“三从四德”之道德规范。历代的女子往往一朝被弃,总都有一点不忍遽舍的表示。
《诗经·遵大路》云:“遵大路兮,掺执子之袪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这句话表达了一位柔弱女性被遗弃时的悲痛之情。《氓》中的女主人公被抛弃,很可能经历了与其他被遗弃女性相似的痛苦,如怨恨、怅惘与绝望。但她并未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而是“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她对自己选择的爱情与婚姻进行了理性思考与深刻剖析。她意识到,对氓的盲目爱恋不仅使她失去了自我,也忽略了社会上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一语道出了宗法制度下婚姻的真谛,男子才是婚姻的主导者,而女子只不过是男性的附庸。一旦女性陷入宗法婚姻的框架,就难以摆脱其束缚。哪怕是遇到像氓这种“二三其德”“至于暴矣”的不良男子,女子也只能怨叹啜泣,不能轻易请离。而对男子来说,他们的婚姻目的只是需要一个极端柔顺的女子,为其操持家务,伺候舅姑、相夫教子。女子等到年老色衰或家庭不和,就可能被男子以“妇道”之名堂而皇之地驱出家门。此时,女主人公已看穿了氓虚伪的真面目,郁积于心的困惑与迷惘也瞬间醒悟,但她没有选择委曲求全,也没有选择寻死觅活,而是选择了决绝地离开。“亦已焉哉”,一句释怀的叹息,是她断然放弃企图依附男子以获得婚姻幸福的幻想。她知道一个女子要想拥有美满幸福的婚姻,就必须拥有独立的人格,摆脱对男子的依附。
尽管《诗经·氓》中的女主人公没有得到像一些幸运女性那样理想的幸福婚姻,她在爱情和婚姻中的追求与挣扎却显露出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在婚前,她拥有对爱情和婚姻的独立思考,未受传统礼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限制,而是勇敢地追寻自己渴望的爱情和婚姻。在婚后,面临丈夫的冷漠抛弃和暴力对待,她能够理性地反思自己在爱情和婚姻中失败的原因,并决绝选择结束这段不幸的婚姻。她的故事,是用自己对幸福婚姻的不懈追求谱写了一曲女性意识觉醒的悲歌[1]。
如果说《诗经·氓》中的婚变象征着女主人公独立意识的自我觉醒,那么《孔雀东南飞》中的婚变则代表了像刘兰芝这样的被压迫、被伤害女性对封建宗法礼教体制的坚决抗争。
刘兰芝是封建礼教体制下的一名叛逆者。她生活在比《诗经·氓》中女主人公所处时代更为严苛的封建礼教制度之中。《孔雀东南飞》发生在东汉末年,而汉代是封建礼教形成的重要时代。《汉书》记载朝廷诏赐褒奖贞妇之史实,足以说明汉代是封建礼教之滥觞。汉代不但朝廷提倡礼法,而且社会亦盛行以礼法作为裁定女子生活的标准。刘向的《列女传》以女子传记的形式宣扬了女子母仪、贤明、仁智、贞顺与节义之妇德,为当世妇人生活之鉴戒。而班昭的《女诫》则更系统地编纂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夫为妻纲的道理及三从四德等压迫女性的观念,构建了以“夫权”为核心的封建家庭道德伦理观,将之变成束缚女性的枷锁,导致女性地位极度降低。当时,女子虽未有正式的教育,但不成形的教育还是存在。《女诫》言:“但伤诸女,方为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于他们,取耻宗族。”可见,女子受教育之目的,惟在“事夫”。刘兰芝自幼深受封建礼教的教导,这种“明于妇道”的教育无疑严重地钳制了她的独立意识,并使之自觉地遵从并维护妇道之礼。所以,刘兰芝的独立意识的觉醒并不是《氓》中女主人公那种本能的、自发的个性追求,而是在以焦母、刘兄为代表的封建礼教逼迫之下的勇敢抗争。所以,她的抗争本质是一种女性独立意识觉醒与压抑这种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封建礼教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旷日持久斗争中,刘兰芝从主动请归到夫妻殉情,无论是她的意识觉醒还是斗争方式都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进行,从而全景式地反映了封建礼教压制下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抗争历程。
“严妆”辞别是刘兰芝对无端被弃的无声反抗。“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足以说明刘兰芝符合《女诫》所言的必需品质。她幽闲贞静、不道恶语、服饰鲜洁、专心纺织,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淑女与贤妻。所以,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被“遣归”是焦母的故意刁难,但她不能争辩申诉。因为《女诫·曲从》说得很明确,“姑云不尔而是,固宜曲从;姑云尔而非,犹顺命”,意为妻子对丈夫要曲不能争,直不能讼,对舅姑亦要一味顺从,不可违逆。《女诫·敬慎》所云:“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讼争既施,则有忿怒之事矣。”惟其如此,夫妻才不至于滋生“媟黩”。刘兰芝深知申辩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才会主动自言“请归”,以此表达对焦母无端遣归的反抗。辞别时的“严妆”更是借容颜之娇媚、体态之绰约、服饰之华美来明示自己“请归”的从容与坚强。她与焦母道别时,言辞恳切,不卑不亢,看似谦卑,实则字字有怨,不露声色地对焦母骄横的态度进行了有力反击。正如清代学者浦起龙所言:“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
夫妻盟誓是刘兰芝对真挚爱情的执着坚守。刘兰芝主动“请归”应该是她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古代家庭伦常的和顺,是通过礼来实现的。因此,礼法对婚姻的钳制是格外严酷的。《汉书·外戚传》曰:“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可知礼法对婚姻的重视。她知道焦母必然要祭出“礼法”的威权来拆散自己的婚姻。因为焦母作为一家之长,她手中握有左右子女婚姻的礼制大权。《大戴礼记·本命》云:“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以“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为由遣归刘兰芝,实则就是“不顺父母去”。当然,她也清醒地知道焦仲卿的求情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礼记·内则》明确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仲卿替刘兰芝说情,恰恰就坐实了这条“遣归”的理由了。所以,刘兰芝与焦仲卿的婚姻,不是在刘兰芝手中,也不是在焦仲卿手中,而是在一家之主的焦母手中。即便如此,她也没有向焦母妥协退让,而是决然地离开焦家。“鸡鸣天欲曙,新妇起“严妆”。”刘兰芝“欲曙”即起,就是向焦母明示了不愿在焦家继续生活的决心。但她离开焦家的内心是矛盾的,毕竟焦家还有自己铭刻在心、难以割舍的爱人。“严妆”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不经意地泄露了她不忍遽去的心理,离家时不带自己的嫁妆,而是“留待作遗施”,并叮嘱焦仲卿“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流露的是对焦仲卿的一往情深,甚至到了临别的大道口,依然“低头共耳语”,盟誓“不相负”,期盼“君早来”,毫不掩饰地表达她对爱情与婚姻的忠贞与坚守。在封建礼教的重重逼迫之下,一个被遣归的弱女子能够保持这份对爱情与婚姻的坚守,需要很大的勇气。“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这句掷地有声的誓词既是对真挚爱情的表白,更是对宗法礼教的宣战。
相约殉情是刘兰芝对封建礼教的最后抗争。自始至终,刘兰芝对宗法礼教都有着清醒的认知。她与焦母之间的矛盾不仅是家庭婆媳之间的冲突,而且是一个女性叛逆者与封建礼教维护者之间的冲突。女子既须依男子为生,便没有了对等的人格与独立的思想,只能任其奴役摧残,却是不能有轰轰烈烈的反抗。故在秦汉之时,对于出乎礼者,往往入乎于刑,以达“明刑弼教”之目的。所以,她清醒地预感到与封建礼法制度的抗争必定会失败。但她于心不甘,不愿放弃心中美好的追求,故在盟誓时暗示焦仲卿“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遣归”后面对太守、县令的遣媒议婚,刘兰芝以“盟誓”在先断然“拒媒”。她“拒媒”并非为遵从“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汉代朝廷虽用官势褒奖贞节,《女诫》亦用“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的戒条鼓吹贞节,但社会对于贞节终不过分看重。女子再嫁,无人制止,也有人愿娶。她的“拒媒”纯粹是对爱情与婚姻的坚守,是对封建礼教的坚决抗争。“拒媒”之后,刘兰芝再次面对代表家长制的兄长逼婚,假意允婚,口头答应“处分适兄意”,实则是对自己抗争结果的清醒预估与对家长制淫威的蔑视。她深知自己的力量根本就不能与强大的封建礼教抗衡,抗争的最后结局必是自我毁灭。“黄泉下相见”,既回应了当初“不相负”的盟誓,也饱含着殊死抗争的决绝。“举身赴清池”的义无反顾就是对封建家长制拼死反抗的无所畏惧。刘兰芝不愧是反抗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她没有像其他女性一样逆来顺受地屈从,而是选择了悲壮地死去。因为死与屈从,都是反抗封建礼教的必然结果。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她选择了屈从,那么即使她还能嫁入豪门,但她的灵魂与爱情理想将不复存在了。而悲壮地死去,却能表现她为爱情理想而不懈抗争,既符合宗法礼教社会的必然性,也可赢得后人对她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女性追求个性独立、粉碎封建礼教的精神力量[2]。
《诗经·氓》的女主人公和《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均是受封建礼教压迫和伤害的底层女性。她们体现了勤劳善良、质朴孝顺、温柔贤惠等传统美德,同时也展现了女性的独立意识。她们相信,爱情与婚姻是更美好的生活向往。为了追求自由爱情与幸福婚姻而觉醒的独立意识,促使两位卑微的女子开创了反抗封建宗法礼教的先河。她们的悲剧为我们揭示了女性解放的出路,只有摆脱宗法制度的约束,女性才有机会迎来新生。然而,长期的封建礼教压迫,仅凭女性个体的反抗难以彻底改变命运。这两位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以她们生命的微光点燃了女性独立意识的灯塔,指引女性认清封建礼教的本质,并指明了向往新生活的道路。随着独立意识的觉醒和新思想的推动,中国女性开始勇敢地发起解放自我的浪潮。有了意识觉醒和发展的机会,女性就能拥有拒绝压迫的力量和自由,进而实现彻底的解放。而《氓》中的女主人公和《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作为中国历史上反抗宗法礼教的先行者,她们的抗争和牺牲成为时代进步的伟大壮举。
——《原野》中焦母命运倒错的三重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