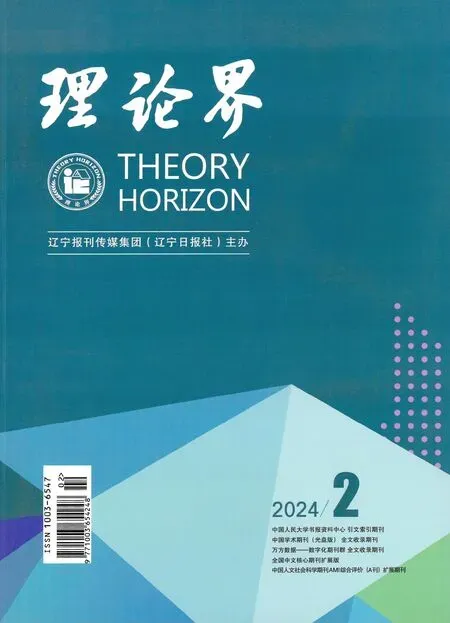作为分享经济模式的农家院的发展路径
——基于情感消费视角
李洪君 赵萤萤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分享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强劲的经济力量。信息网络的加速运转,更加促使其风靡全球。分享经济涉及领域众多,主要包括产品类、空间类、知识技能类、劳务类、资金类、生产能力类、等等。〔1〕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分享经济使得闲置资源得以优化处理,是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和环保意识提升的一种体现,对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激发了学术界的激烈讨论。
农家院分享经济作为房屋住宅及生活空间的一种共享形式,其中包含房屋所有者对其使用权的分享。物质生活的日益富裕促使人们对精神世界有更进一步的追求,高速运转的城市生活充实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农家乐娱乐休闲能够帮助人们实现短暂的空间转换,让人们长久紧绷的神经得以舒缓。农家院经济属于空间类的分享经济,不同于传统的酒店行业,农家院分享经济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加生态和自然的生活场景,以其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不一样的休闲消费体验。农家院是分享经济在农村地区适应性发展的一种体现,也逐步成为农村农民创收的一种重要途径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形式。市场经济的急速转变导致社会情感的压抑和资本化运作,这些宏观力量有意无意之间对农家院分享经济模式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辽宁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农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升农民参与度,才能让农村改革、乡村振兴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家院分享经济的发展拥有强大的政策后盾。政策扶持让农户在开展农家院分享经济模式时更具有信心和动力,对于提高生活质量和改善生活条件具有更加强烈的追求欲望。本文立足于辽宁省农村地区分享经济的发展情况,欲依托情感消费的分析视角,通过文献研究方法和对比分析方法探讨辽宁农家院分享经济在农村空间场域之中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等问题。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视角
所谓分享经济,一般是指借助第三方创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供应者从闲置资源使用权的让渡中获得额外的收益,消费者则以合理的价格满足需求。其中,分享经济所交易的,仅仅是商品本身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它依靠最大化商品的使用价值来创造共赢。随着社交网络逐渐深入渗透人们的生活中,特别是微博、微信等移动社交工具的普及与全方位应用,分享经济正迅速蔓延到各个领域。〔2〕“分享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1978年由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克斯·费尔逊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合作发表的论文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中。〔3〕2008 年金融危机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分享经济呈现一种井喷式发展。按照通常的观点,所谓分享经济,是指资源所有者将自己闲置的资源拿出来,供那些需要的人有偿使用。〔4〕从某种意义上看,分享经济也可以作为广义上的第三次分配,即指的是互联网平台所促成的合作消费。它需要人们加入互联网平台所支撑的某种网络组织,并在其中借助资源再分配的方式,实现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和相互帮助。〔5〕本文所提及的分享经济主要以分享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给出的定义,即分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分享海量的分散化闲置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本文将分享经济作为对闲置资源重新分配的一种手段,依托互联网技术,让农村闲置资源实现有效整合和高效利用。
农家院,亦称农舍,意为农民住的房子。《中华字典》中给出的农家院的定义是农家院已经成为一种旅游业态之一,主要是以经营农家乐为主的个体户形式出现,让城市里的市民们到农村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体验农家生活,感受安详宁静的生活环境。而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实践中,各地方政府依据不同的观察角度赋予了农家院不同的官方称谓和定义,如北京的农家院的官方称谓是“民俗旅游户”,重庆、广西、湖北、陕西、浙江、四川、山东、安徽等地农家院的官方称谓是“农家乐”,江西的农家院官方称谓是“农家旅馆”。〔6〕尽管各地名称不同,但都透露出农家院的本质属性:经营主体的农民性、经营空间的农家性、经营内容的农耕文化性。本文主要以赵新峰和李祗辉对农家院的定义为主,即农家院指的是以农民为经营主体,以民居院落为经营场地,向游客提供餐饮或住宿等服务,以营利为目的的小型旅游餐饮及住宿接待设施。
农家院分享经济模式主要是指,随着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发展,农家院业主或农民将自己的农村住宅、农田、农产品等资源通过共享经济平台或其他形式进行共享,以获取额外的收入或提供服务。这一模式的核心是将闲置的资源和农村地区的特色和优势与需求方进行链接,从而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价值的最大化。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更加促进了情感消费的流行与走红,情感消费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潮流和商业发展趋势。情感是人们思想和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考方式和实践行为。从商品消费的历史来看,情感不仅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消费选择和消费行为,而且自身也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消费品。〔7〕所谓情感消费,指的是人的消费行为呈现鲜明的因情感驱动消费的特征,消费的目的指向的不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而是人的情感需要。〔8〕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消费已然成为一种常态,但是在扩大商品消费空间的内在驱动和商品形式创新的大背景下,情感消费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样态。一方面,它相对于传统商品消费具有特殊性,将情感纳入消费过程,通过情感赋值拓展商品消费的空间;另一方面,它与传统消费又存在统一性,成为一种新的消费形态。〔9〕目前国内关于农家院分享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振兴和生态旅游方面,以情感消费视角探究分享经济一方面可以丰富现有的研究角度,另一方面也可探究分享经济在情感视角下的主要内涵和运作逻辑。
三、农家院经营者:情感氛围营造的分享经济主体
作为情感氛围营造的主体,农家院经营者在农家院分享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拉动者的角色,依托得天独厚的先赋性自然资源,在情感资本化市场中推动着当地农户的就业转型与资源共享,即从最初种地务农的第一产业跃然转变到提供情感营造服务的第三产业。由于主要是以本地化就业为主,因此,其发展农家院分享经济所付出的时空成本较低,属于低成本高收入的经济发展类型。
1.得天独厚的先赋性自然资源优势
辽宁省农家院主要有依托景区和自筹自建两种类型。依托景区型的农家院有沈阳棋盘山汪家大院农家院、本溪老边沟幽闲居农家院、丹东双凤山庄农家院以及鞍山佳祥农家院、等等,自筹自建型主要有丹东于家清水河农家乐园、沈阳山里人家采摘农家乐以及大连庆禄农家院、等等。依托景区型农家院镶嵌于较为原始的自然生态环境,而自筹自建型农家院则通过自我定位主动将自身贴近自然生态系统。无论是依托景区型还是自筹自建型,农家院都离不开对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山明水秀和清新空气是农家院分享经济形成与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农户开办农家院分享经济的原始资本。农户正是借助这些先赋性自然资源的优势,得以顺利开展农家院分享经济活动。
2.基于情感的就业转型
农家院分享经济的开展是宏观市场经济的助推,也是农户情感性自主选择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辽宁省经济结构变革,单位制逐渐瓦解,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让社会成员逐渐呈现一种个体化和原子化趋势。怀旧情感驱动农户选择开办农家院,满足其回味旧时情感的需要,同时也可以为其他有相似情感需要的人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农户从最初“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自主性务农职业者,转变成提供包括情感劳动在内的第三产业从业者,从最初情感的自我满足到为他人提供情感劳动,这一转变使得农户将农家院视为产业与事业,并对其进行规范化、专业化以及商业化运营。在农家院分享经济运营发展过程中,农户就业领域实现了从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转变,这种转变同时也让农户得以将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分享给他人和服务于他人,实现了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共享。
3.低成本的情感空间营造
农家院商业化模式讲究的是一种地道的农家环境和情感氛围。作为农家院分享经济的主体,农户需要付出的原生态场景营造成本较低。在住宿方面,辽宁农村自建房较为普遍,农户将自家闲置房屋作为客房供消费者使用,实现了房屋资源的共享。一般而言,农户自建房的占地面积较大,面积一般为120~360 平方米,房屋建筑风格独特,格局南北通透,独具风格的“炕文化”是吸引消费者体验的一大亮点。在饮食方面,房前屋后的庭院种植和家畜养殖基本能够满足农户与消费者的饮食需求。小鸡炖蘑菇、铁锅炖大鹅、五彩大拉皮、猪肉炖粉条以及锅包肉等东北特色美食是辽宁农家院餐饮文化中的必备选项。在人力资源方面,农户就业转型使得原本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转变为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职业身份发生转变,农户家中剩余劳动力转变为服务人员,完成职业身份转变的同时降低了人力成本。
四、消费者:情感空间的参与者
消费者作为农家院分享经济的受惠者以及情感消费的客观承担者,其情感在农家院分享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乡愁”情绪推动消费者在田间地头寻找故乡的味道,资本对情感消费的营造和符号化运作让消费者卷入资本化旋涡,现代社会的个体化与原子化催动青年向外实现场域转换和探求情感慰藉,这些构成了消费者融入农家院分享经济模式的微观要素,推动着农家院分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乡愁”情绪下的情感驱动
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急速发展,带动了辽宁振兴与产业发展。先富带后富的发展理念让部分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小康,实现了从农房到楼房的转变。这种转换不仅是生活场景的转变,也使得人们的情感和思想观念发生转变。城市化和城镇化背景下高速的生活节奏使得人们感到压抑,回归乡土和感受自然的心情更加迫切。恋旧与怀念过往的情感加速了“乡愁”情绪的酝酿。而乡愁的产生需要实际的物质环境触发,农家院建设正好成为乡愁文化触发、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性要素。以文化挖掘和体验为载体,以呵护乡愁、留住乡愁、活化乡愁为目标,农家院可以帮助消费者寻找乡愁产生的共鸣点,保护乡愁文化,让乡愁看得见摸得着。〔10〕辽宁农家院分享经济中有相当一部分经营模式以“乡愁”为营销主题,不仅顺应了分享经济发展大潮,也迎合了消费者寻求回归乡土,体验农家生活的情感需求。由此来看,辽宁农家院分享经济模式既是大势所趋,亦是民心所向。
2.情感消费的符号化
情感在资本的裹挟下,不再是人本真的、自然的心理状态呈现和表达,而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要么情感本身成为可以用货币衡量的商品,要么情感附加于商品之上,沦为促成商品消费的关键因素。〔11〕一方面,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压得人们难以喘息,迫切需要向外发展,转换活动场域和自身思维。逃离水泥森林,亲近自然,情寄山水成为部分消费者加入农家院分享经济的主要原因。对自然的热爱激发人们走出家门,走入田园,探求大自然的奥秘。辽宁省农家院分享经济商业化建设中有相当一部分农家院设于依山傍水之间,环境清幽,空气清新。另一方面,这种向往大自然的情感被资本化,资本以此进行商业化营销,通过互联网平台将其标签化、符号化,以短视频和文字的形式大量传播,鼓吹消费者“逃离工作”,融入自然。例如,“裸辞”风潮、露营的爆火、特种兵式旅游、等等,凡此种种都含有资本对情感的符号化运作,而消费者在不知不觉间被卷入这场情感消费的旋涡当中。
3.情感社交与认同的原子化
人的社会属性是通过社交得以实现的,而交往活动乃是人获取象征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重要途经,也是满足人情感需求的重要方式。〔12〕在个体化的时代,年轻人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他们已经逐步摆脱阶层、婚姻、家庭、地域等束缚,致力于自我实现和自我塑造,在婚姻、职业等方面的选择上有了更大的自由。〔13〕当年轻人逐渐成为原子化的个人之后,他们最明显的感受是奋斗的孤独,在一二线的大城市里,他们有无穷尽的竞争压力。他们缺乏安全感,面对这种自由,他们不是充满动力而是日益焦虑。〔14〕工作中同事之间由于工作绩效等利益关系,在情感社交方面偏向于“轻社交”的形式,鲜有存在类似“同窗情”“竹马情”等深厚的情谊,青年人在工作和生活场域中缺乏足够的情感社交与情感认同,由此,只能借助各种外部社交活动丰富自身的业余生活和情感需求。辽宁农家院分享经济的商业化模式的受众群体中不乏青年群体,他们正逐渐发展成为推动农家院分享经济的新兴动力。同时,辽宁农家院分享经济模式为消费者提供众多休闲娱乐的活动项目,例如休闲垂钓、生态蔬果采摘、作物种植与收割劳动、自助烧烤、户外野炊、等等,这些活动项目作为分享经济中的具象形式满足了消费者对于转换空间场域,寻求心灵休憩和社交的需要,同时也促使农家院分享经济商业化模式的丰富化和多样化。
4.情感消费的双重属性
在农家院分享经济活动中,消费者是情感运作模式下至关重要的一环,其所进行的情感消费具备双重属性。一方面,消费者作为体验者,感受农家院的乡土氛围和怀旧情感,深深地参与到农家院的经营活动当中,既满足其情感释放的需求,同时又推动农家院分享经济的发展,促进当地的产业进步。另一方面,消费者作为情感空间的营造者,实现了情感消费的再生产。在如今信息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消费者完成一次农家院消费体验后,往往会借助互联网平台,例如微博、微信朋友圈、小红书、抖音、快手等等,分享自己的消费体验和感受,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互联网其他用户也加入农家院消费当中,进而完成情感消费的再生产和情感空间的二次营造。农家院分享经济中情感消费的双重属性是市场化运作和信息网络发展下的产物,不仅满足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同样也实现了分享经济的再生产。
结论
从情感消费的理论视角看,辽宁农家院分享经济模式的微观逻辑体现出作为资源分享主体和情感消费营造者的农家院经营者的拉力作用以及作为资源接收方和情感消费承载者的消费者的推力作用。农家院分享经济的理念是通过共享资源提高整体效益,在农家院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共同作用下,辽宁农家院分享经济模式得以顺利成形。在辽宁农家院分享经济的商业化模式中,一方面,农户将自己的闲置资源分享给消费者,另一方面多样化的商业化模式使得多个农户的资源共同利用,进而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促进就业和当地经济的发展。辽宁农村可以充分把握分享经济的发展机遇,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提升服务品质,推动农村旅游和农业产业链的发展,为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