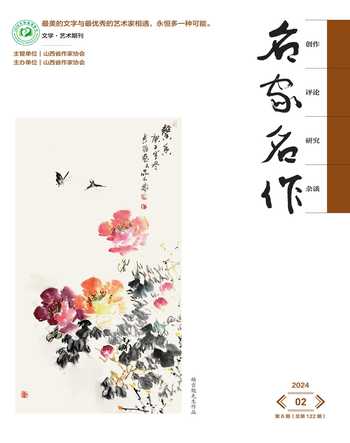庄子和海德格尔的“物性”之思比较研究
[摘要] 在中西美学史上,庄子和海德格尔都曾对“物性”做过论述,虽然两者所处的文化语境有异,但对于物性的理解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二者都认为物的本质在于其无用性,且人无须为无用性担忧,不仅揭示了人类异化的本质问题,还让我们在反形而上学逐渐走向科学哲学的今天对现代化社会作出新的反思、试图从兩者对于“物性”的思考原点出发,探究其在中西文化语境中的沟通和对话。
[关 键 词] “物性”;庄子;海德格尔
对庄子和海德格尔思想的比较研究近年来已然成为东西方学界的热点话题,两位相隔万里、相距千年的哲人有着不同的生存背景、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却能在这条历史长河中实现跨越千年的对话。
海德格尔哲学体系的形成与老庄思想渊源颇深,他曾在1945年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了八章《道德经》①,为了论述真理发生的起源和工具的使用问题,他曾以《庄子》中的两个故事为例,即“濠上观鱼”和“无用之用”。现在东西方的许多学者在单独论及庄子和海德格尔时也会不同程度地将两者挂钩,学界也蜂拥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庄子和海德格尔思想契合点的比较文学,内容涉及“存在论”“本体论”“生死观”以及二者对“诗性”的探讨等。《跨越时空的对话——老庄和海德格尔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郭德君,2003)、《庄子和海德格尔思想的初步比较》(夏绍熙,2006)、《庄子和海德格尔美学思想比较》(戴冠青,2000)等多篇文章从宏观角度对二者思想进行了分析比较,研究内容囊括了庄子和海德格尔哲学或美学的主要思想体系。对庄子和海德格尔“生死观”的探讨,则涉及《〈庄子〉内七篇与海德格尔的“生死观”之比较》(吴福友,吴根友,2011)、《庄子与海德格尔的生死观及其当代意义》(刘晶,2018)、《浅析庄子与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杨鹿鹿,2017)等多篇期刊或学位论文。此外,四川大学钟华的博士学位论文《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与庄子诗学思想比较》、大连理工大学武恒的硕士学位论文《庄子和海德格尔诗化语言观的统同一性研究》以及何芳在1998年发表于《学术交流》上的《追寻诗意的栖居——庄子与海德格尔诗学比较》等文章集中对庄子和海德格尔的诗学研究进行了比较。关于存在论和本体论的探讨主要有《“从本有而来”与“道法自然”——海德格尔与庄子的本体论比较研究庄子之“道”与海德格尔的“本体”之思——从词源学的角度》(徐良,2020)、《海德格尔与庄子关于人与世界关系观点的联系与区别》(王诗语,2020)等文章,而本文着力探讨的二者对于“物性”之思的比较研究则出现次数较少,包括《国外文学》2005年第1期上刘月新发表的《在“物”中寻求诗意的栖居——比较庄子的“物化”与海德格尔的“物性”》、《哲学研究》2002年第3期彭富春的《什么是物的意义?——庄子、海德格尔与我们的对话》等少量篇章。
综上所述,对庄子和海德格尔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从宏观角度整体论述和对比分析庄子和海德格尔思想体系的异同,内容涵盖的范围较广;二是从两者可类比的一般概念出发探究其思想的交汇处、契合点,涉及“存在论”“本体论”“生死观”以及对“诗性”的讨论等,对于认识两者如何在相隔万里、跨越千年的时空语境中实现对话极具启发意义和价值,但是有关其二人“物性”之思的专门性研究还较为单薄或者提及较少,而笔者认为对“物性”的探讨不失为链接庄子和海德格尔的一个重要枢纽。因此,本文试图从二者的“物性”之思入手来理解其同异性,以期在现代化社会为两位中西方影响重大的学者对物性的认知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
受现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史容易被笼统地认作是一部形而上学的历史,但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庄子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反思中不难看出两者思想中的“物性”,仅仅因为其思想没有通过对现实政体制度的批判来解决人生困境问题就将其视为唯心主义和对现实的逃避是不可取的。这实际上混淆了现实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和由人的异化造成的生存困境之间的区别,似乎造成人类异化的原因是某些特定的专制者或某一现实的社会制度,但事实上,马克思看待人的异化问题也是从人类本质出发的。谈论庄子和海德格尔对“物”的看法,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被认为是传统形而上学思想中的一些参透人类本质的看法。
一、庄子的“物化”
《庄子》的“物化”是其哲学的重要思想观念之一,物性论指的是对人的世俗、功利之心的涤荡,消解人的欲念和是非观,以“虚静”之心观物,“与物冥合”,从而回归物自然的本真状态。对物的思考是《庄子》对自然、对世界最本质的追问,庄子本人对文明进程的发展所带来的人类本质异化的问题无不充满深忧,《庄子》中将对物的最本质的认识称为“真知”。“真知”不仅要达到对物的“真”性认识,还要求人的内心保持“本真”,其根本表现是否定式的,庄子认为对事物有用性的思考遮蔽了人的心灵,也遮蔽了对事物原初状态的认识,他指明无论是从物方面还是从人方面都需要“无”。否定就是去蔽,去蔽就是揭示①。
“无”不是对客观事物存在的否定,而是对主客二元论中作为认知对象的物性的否定。也可以说,庄子主张回归物的本性而提出的对于知识的否定并非指向人类赖以存在的一般性实用知识,而是针对那些企图通过将社会人生和整个世界逻辑化以寻求物的有用性的认知结构的否定。庄子曾对对理性的逻辑运作所造成的主客对立提出疑问:“且也相与吾之耳矣,庸讵知吾所谓吾之非吾也。”并在《大宗师》篇里说道:“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详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正是对人类理智所造成的悖论性知识结构进行的严厉批判。“无”是对“道”的超验性指称,从某种程度而言“无”就是“道”,《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故自无以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就诠释了万物与我“合而为一”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参透事物的本质,而用言语(理性)是无法把握事物的,一旦言语出现,主客之间就会形成对立,即呈现为“有”。
庄子将人的本性和天地万物达到绝对自由的最终归属界定为“逍遥”,而“逍遥”这一宗旨的重要实质内容即是向“无”的回归。“无”体现为对物性把握中功利和理性的荡除,在对立之心清除后方能达到“人见于人,物见于物”(《庚桑楚》)的状态。庄子和海德格尔在对于物的意义进行追问时,二者都认为:物的意义就是其无用性,而且人无须对无用性担忧。庄子的物即自然,且合于道,海德格尔的物则来源于其对存在的追问。
二、海德格尔的“物性”
海德格尔在其1927年出版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中首次提出了“存在的意义”这一问题,在此之前,他曾经一直是胡塞尔现象学的狂热追随者,對先验还原理论的不认同驱使他产生了对存在的追问和思考,他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混淆了“存在”和“存在者”的概念,其所追问的存在指的是存在自身,即作为存在的存在,而并非指存在者的存在;存在者指的是一个凝固化的对象,而存在则是一种运动变化着的状态,存在即是一个让存在者得以显现的过程,海德格尔在对物进行追问时并不是关注某一特别的事物,也不关注物的一般抽象形态,而是强调物性本身,亦即存在本身。
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德格尔的整个思想历程中,物的重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早期著述将物的世界结构描述为“在世界之中存在”,物的世界并非是体验的世界,也非意识的世界,而是此在的世界。此在在其论述中被规定为人,作为存在者,能够理解自身的存在,物只有在此一世界中才显现为自身的存在,于是他将现象学“Phenomenology”一词重新建构为“phainomenon”和“logos”的组合,翻译为“显示出来的存在者”和“言说、判断的过程”,即在判断或理解的过程中让存在显示自身,此在是存在的第一性,因为他有意识,能够去追问和领悟到一般存在者即其他事物的存在,而世界中的物又分为此在物(即人这一特殊的存在)、手前之物(自然物)和手上之物(人造物)。将物自身立于历史的角度来考量是海德格尔中期理念的一个显著特点,物的历史就是为存在的历史,也是存在的真理发生的历史,海德格尔认为物的真理发生于大地和世界,真理或物性发生的本原正是来自二者的抗争②。晚期的海德格尔则将世界看作是天地人神的聚集,其存在则是一个四者交互生成的存在。
“物性”作为一个概念经常出现在海德格尔后期哲学中,通过对其进行阐释来反思现代技术及近代主体哲学对“物”的征服和破坏,以此让“物性”得以显现和澄明,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曾经用现象学的解释描述过“物”的物性,他认为“可以上手的东西”才称之为“物”,而物正是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才得以显现自己,并以希腊人对物的使用中将物看成是“纯粹的物”而使得其实用性退居其次来赞扬人与物之间的原始关系。然而,这种原初关系随着现代科学和哲学体系的确立,被撕裂成为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关系, “物”和人日益远离,成为被人算计和测量的客体,随着对象性思维的拓展,“物”成为人类探讨和分析的对象,人有了关于“物”的不同的知识和观点,“物就成了人的各种感觉的集合体”,成了形式与质料的统一,正是在对物的这种解释中,“物”消失不见了,“物”之物性被遮蔽、被遗忘了①。
三、比较庄子与海德格尔的“物性”之思
综上对庄子和海德格尔对于“物”的物性所作出的思考,我们不难发现二者思想的契合点,庄子是以人和物回归自然的本真状态亦即本体论来探讨人对于物性的把握,而海德格尔则是从对存在的追问中来把握人与物的原初关系,其共同的思想主张都指向去除对对象的功利性认识,以纯粹自然之心来感受“物”之物性,都认为物的意义在于其无用性。
二者虽在对于“物性” 看法的结论上殊途同归,但其出发点却是存在差异的,庄子出生于距今两千多年的战国时期,他是出于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反思和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所导致的人的本质异化的忧思中提出的“万物归于无”的思想,其反对的是人的理性进程,使得人作为主体从大道和自然中分离出来而与客观世界形成对立的局面,斥责的是人类对于“物”的占有立场和无止境的掠夺性质,因此庄子的“物化”论是从劝说人们回归到“用心如镜”、返璞归真的角度出发的。海德格尔则生于工业革命繁荣的时期,其反对形而上的革命思想则是出于对科学哲学和工业革命造成的人与“物”原初关系破裂的不满,他认为“逻辑”和“技术”作为手段来认识和处理作为对象的“物”是作为此在的“人”对于“物性”的破坏,人将物的实用性置于首位,将一切除人以外的物体对象化,实际上也是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主客对立化,也是对于“物”之物性的消解。相对应的,人这一特殊存在物,其在世之“在”也被区分为本真和非本真的存在,通过情态、理解和话语显现出来,当此在不能保持原本的自我、被原始的情绪所支配或无法独立地领会世界,就会沦为常人,成为闲谈、好奇和混谈的工具,“此在”并非一个名词,而是一种未完成的动作时态,亦即“to be”,人有决定自己如何“去存在”的权利,可以充分发挥积极的自由选择呈现本真的自我,而不至走向沉沦和异化。
庄子和海德格尔自身的思想及其所否定的思想特征实际上代表了中西思想的一般特征,二者都是在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把握下作出的呼唤,道家学说自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倡导,“藏己于万物”,而“万物归于无”正是这一观念的具体体现,这与海德格尔提出的“此在的澄明”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正是人类生存绵延不绝的首要条件,庄子和海德格尔的“物性”说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人类本质的异化对于人与万物关系所造成的不和谐局面,如此引人深思的洞见自然不能因为其没有对某种社会制度和人类生存体系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就将其认定为是对社会和现实的逃避等。
四、结束语
时至今日,反形而上学已经成为中西方普遍关注的哲学问题,两位曾在中西方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哲人对“物性”做出的思考又引发新的热议,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僵化运用往往导致我们对一些“超验”问题的选择性忽略和一票否决,站在时代和文明发展的角度来反思其合理性才是明智之举。
参考文獻:
[1]杨国荣.庄子哲学及其内在主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1-8.
[2]杨国荣.《庄子》哲学中的个体与自我[J].哲学研究,2005(12):40-46,123.
[3]洪汉鼎.何谓现象学的“事情本身”(Sache selbst)(上):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理解之差异[J].学术月刊,2009,41(6):30-38.
[4]俞吾金.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海德格尔、卢卡奇和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比较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1(2):54-65,205.
[5]俞吾金.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39-45.
[6]王晓升.世界、身体和主体:关于主体性的再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21(12):176-198,203.
[7]彭富春.什么是物的意义?:庄子、海德格尔与我们的对话[J].哲学研究,2002(3):50-57,81.
[8]刘月新.在“物”中寻求诗意的栖居:比较庄子的“物化”与海德格尔的“物性”[J].国外文学,2005(1):10-20.
[9]李向平.“息我以死”与“向死而在”:庄子和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J].社会科学家,1989(1):37-45.
[10]苏菡丽. 后现代视域下庄子与海德格尔人生哲学的对话[D].苏州:苏州大学,2006.
作者简介:
张秋梅,(2000—),女,汉族,云南大理人,西南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美术理论。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美术学院
注释:
①苏菡丽:《后现代视域下庄子与海德格尔人生哲学的对话》,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注释:
①②彭富春:《什么是物的意义?——庄子、海德格尔与我们的对话》,《哲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50-57,81页。
注释:
①刘月新:《在“物”中寻求诗意的栖居——比较庄子的“物化”与海德格尔的“物性”》,《国外文学》2005年第1期,第10-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