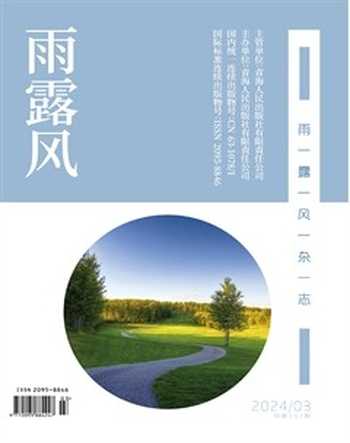命运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

中国当代文坛备受瞩目的史铁生,以自传体散文《我与地坛》在文坛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篇文章被选入中学教科书,许多人接触史铁生便是从《我与地坛》开始。史铁生亲切朴实的写作风格、深邃澄澈的思想和宽厚博大的情怀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文章中关于生死感悟、苦难思索和母爱怀念等内容深深触动着读者内心。这些充满情感和意蕴的文字,对年轻一代走向社会、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挫折和磨难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人生历程
史铁生从清华附中毕业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前往延安参加农村劳动,却在朝气蓬勃的二十一岁双腿瘫痪,三十岁又遭遇新的疾病。如何应对自身的苦楚以及无法回避的命运,成为他最日常也最关切的问题。长期承受疾病痛苦的他最终在2010年12月31日与世长辞。史铁生的写作,就是从自身的问题开始,一点一点、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的。命运摧残身体,却让他通过纸笔立起了精神,开启了思想的大门。他的作品,就是他精神思想历程的叙述。
大多数人的青春可以用迷茫、喧嚣、惶恐这些词来形容,青春很美好,但也浮躁迷茫。《我与地坛》让人发现,原来我所经历的那些迷惘,早就有人经历过,并以一种温良的方式记录下来。突然之间,迷茫的青春就被稳稳地托住了,好似被汩汩泉水温和地包容着。史铁生告诉你如何面对不平的命运:“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如何应对渴望放弃的虚无感:“要善待荒谬,它们将引导你回到最初的视角,迫使你去探索生命中固有的疑难。”甚至他在尝试回答生命的意义这样的终极问题:“生命本无意义,生命在向你要意义。”
二、景物分析
作者在平静的景物描写中讲述了自己双腿残疾的残酷事实,让读者感受到平静的叙述下隐藏着极深的痛苦,这是命运带给他的第一个大磨难。每一处景物的对比描写又是作者对“生命”和“世界”的解读,将生死的哲理思考映照在景物描写之中,不仅让作者感受到了生命的涌动,也与读者共品人生的百味。[1]
“四百多年里的地坛,浮夸的琉璃剥蚀了,门壁上的朱红淡褪了,高墙坍圮了,玉砌雕栏散落了。老朽的园子只有野草荒藤自在坦荡。”这一段中所用的动词“剥蚀”“淡退”“坍圮”“散落”都是为了强调地坛的“凋零”,而“琉璃”“朱红”“玉砌雕栏”则代表了曾经地坛的荣耀。[2]地坛曾经的辉煌与现在的败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这种反差与作者的不幸相对应。所以作者与地坛的见面仿佛宿命。
地坛的自然生态中,作者着重描述了蜂儿、蚂蚁、瓢虫等,它们各自在大自然里拥有自身独特的活动,自成一道风景。园子经历了风雨洗礼,历尽沧桑岁月,然而园中的小生物却以一种独特而透明的方式展现了生命的坚韧。无论是蜜蜂、蚂蚁、瓢虫、蝉蜕或者植物,它们都不会因为自己微不足道的存在而放弃展现自我,并向世人呈现出色彩斑斓的生命之美。而露珠在叶子上的积聚壮大直到最后一刻叶子承受不住其重量轰然倒塌“摔开万道金光”,表现了地坛虽然荒芜但并不衰败的强大生命力。
祭坛石门中被落日平铺照耀的坎坷之路,落寞的时光中高歌的“雨燕”,严寒中孩子们的脚印,无悔站着的古柏,暴雨突临的气味,秋风播撒的味道。作者用客观的视角展现出每一个生命独特的存在方式,它们不因处境的艰难而自艾自怜,而是换一种视角让自己活出光彩。从视觉、听觉、嗅觉着手,让不起眼的角落都显示了生命的激情。生命的長短不过是相对而言,只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节奏活着,仍然能享受人生。
地坛对于史铁生来说,无疑是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精神地标。史铁生在那段极其灰暗的人生岁月里,沉下心来观察和思考这个世界。地坛的方位、环境甚至氛围,都恰如其分地呵护了史铁生渴望独处的心理状况。而史铁生的想象和冥思,也令这座废弃的故园焕发出了精神家园般的光芒。
三、母亲形象
文章用舒缓的语气描写母亲,主要写母亲生前默默对“我”悉心地照顾,但“我”却毫不领情,在“我”最终理解并感受到母亲的默默付出,在人生道路上即将有所成就时,母亲却去世了,再也看不到重拾信心的自己了。这样舒缓的描写像绵绵的细雨,浸润读者的内心。这是命运带给他的第二个大磨难。
当史铁生流连忘返于地坛,努力去猜测生命谜题时,却未曾料到这些行为在无形中为他人,尤其是自己的母亲设下了一道新的生命谜题:“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3]15对爱子心切的母亲来说,她的生命谜题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思史铁生之所思、想史铁生之所想。她不会像铁生那样,总是站在思想的高度去猜测答案,她心中的生命谜题,就是孩子如何活,以及怎样活得更好。这显然是母亲基于生活之上的一种生命意识,在设身处地为孩子思考生命问题的过程中,母亲真正向史铁生诠释了爱的深切含义:它一方面圣洁高尚、无私无畏,另一方面又情意绵长、血浓于水。
母亲担心儿子独处却又怕给孩子带来麻烦时会说道:“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3]17在这段记叙中,史铁生以他细腻的笔触,让读者明白了什么叫作“可怜天下父母心”。因为残疾,母亲害怕会刺激到孩子的敏感心灵,因此只能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儿子的自尊。史铁生想要做什么,母亲便由着他去。可是她内心却又不舍、担忧、紧张与焦虑。明知让儿子在外面终日晃荡不是个办法,但困在家里势必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如此纠结彷徨的矛盾心态,给母亲带来日益加重的惆怅与无奈。所以每逢儿子出门,她都要细心地准备一番,待目送他摇着轮椅走进那不可知的未来时,母亲也在饱受煎熬。她只是希望儿子平安顺利,这是一个母亲最低的祈求与期盼。
后来母亲去世了,史铁生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着。一遍遍回想曾经每天都会在这个园子里等待着他、给他温暖和关怀的母亲。可是现在,母亲永远地离开了他,不再回来。他反复描写“母亲已经不在了”“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3]24用这样反复的叙述方式,使悲伤之感一次又一次地加深。地坛中不单有作者的脚印,车辙的地方也总有母亲的身影。地坛是史铁生的避难所,为他思考人生问题提供了场地,而母亲的爱与无法言说的痛给他埋下了一颗坚强的种子,二者的融合完整地构建了作者的生命观。
人通常在遭受巨大的冲击或痛苦时,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才会反思自我和探索自己存在的价值。当面临无法解决也无法逃避的困境时,史铁生不得不开始思考生死问题。
四、命运苦难
史铁生通过写作,发现了自己为何而活,他不仅在写作中发现了生命的真谛,还深刻领悟到了如何在逆境中寻求力量。尽管残疾限制了他的行动,却也迫使他深思,从而洞察到生命的本质,对人生苦难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这使得他能够在面对生活的种种困境时,保持内心的平静,以积极的态度接纳并包容一切,最终实现了与自身命运的和解。
《我与地坛》里,史铁生还花了很长篇幅描写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情。热爱唱歌的小伙、饮酒的老者、捕鸟的汉子、中年女工程师、有天赋却背运的长跑家,以及那个漂亮而不幸的姑娘。评说他人的不幸也是直面自己的不幸,埋怨上帝或者怨恨命运的不公毫无意义,只有勇敢地接受才能救赎自己。史铁生对于生命的领悟不仅适用于自己,也包括了这个世界上所有不幸和残缺之人。他顺着自己的苦难对命运进行探索,在此过程中发现每个人都必然会遭受属于自己的苦难,生命的痛苦使得他开始思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于是他接受苦难,最终走出困境。面对悲苦的经历,我们似乎无法避免,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像是在一片荆棘密布的灌木丛中行走,一直逃避,不想面对,就会让自己在新生的荆棘中窒息。生命,需要一次彻底地看清苦难的机会。
生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人都可能遇到逆境。从某种意义上说,经历苦难是人生的不幸,但如果你能够正视现实,从苦难中发现积极的意义,充分利用机会磨炼自己,你的人生将会得到不同寻常的升华。智慧的人知道如何从苦难迈向快乐。对史铁生来说,他完成了对苦难的跨越,但快乐不是幸运之果,而是一种英勇的品质。在这种品质的引导下,他用喜悦平衡着困苦,一点一滴重建生活,从而获得了心灵的安妥、生命的自足。在《病隙碎笔》中,他谈道:“不该以为命运欠了你什么。唯当去求一份智慧,以醒贪迷。”[4]从自我宽慰到走向更加通透和旷达的人生,他的豁达是从泥泞里生长出来的,他的诉说没有虚伪,体现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道德。
五、终极关怀
史铁生的天赋源于绝望,他不断内省,以便在注定的困境中得救;他不斷探问,何为人?人将何去何从?正因为陷入如此疯狂的状态,他才开始写作。史铁生初期的写作就是在自身生存困境下,为了个体的精神超越而创作。随着其对困境的体验之深入,由此及彼、推己及人地探寻到整个人类的根本困境,他的创作动机也开始超越个人,扩展到时代社会的精神需求。
《我与地坛》的很多细节无不体现了史铁生的平静与哲思。首先,他对死亡有着明确的阐释:“死是一个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3]11他把死亡称为“节日”,不是忌讳恐惧,而是把它当成庆祝的节日。积极淡然的心态给“死亡”这样可怖的词带来了不同寻常的赞美。在他眼中,死是新生,是另一种生命的回归,所以他对死亡不再惧怕。但“死是一个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既然人类最后的结果是死亡,那就顺应生命的发展,淡然面对。其次,他对于“苦难”和“残疾”的探索也超越了个体,世上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因素构成的。从个人存在角度看,苦难让人难以接受,而从宇宙存在角度看,世界本就是幸运和苦难组成的。正因有了差别,世界才有多样性与丰富性。因此,他听见“园神”对他说:“这是你的罪孽和福祉。”[3]68残缺并非完全是灾难,舞台上的演员与台下的观众都没认识到自己的身份,自身眼界的局限性使得他们无法看到人生的全景。因此,史铁生认为,人生的残缺既是“罪孽”又是“福祉”。他对命运的沉思上升到了人类生命永恒的流转之中。再次,他对于生死答案的探索也超越了个体,他用“孩子”“老人”“恋人”三个形象感性地展示了对死亡的态度:贪恋、平和、留恋,但最终的结局都是理智地走向人生终点。这三种态度是群体的塑造,他们不仅仅停留在书中的这一刻,更会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进行无尽的探索。最后,史铁生在描写拄着拐杖走下山的场景中,不禁乐观写道:“太阳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3]73还塑造了一个向上跑来的孩子形象,在这个类比和隐喻里,作者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去俯瞰古往今来,无论太阳升起或是落下,都会有新的生命在诞生,每一个新生都可能是逝去的旧我,不必因为个体的逝去而难以释怀,因为人类生生不息。
史铁生《我与地坛》所体现出的命运观,即经历了生死抉择和抗争的过程,并在创作中获得了释然和感悟,实现了本我的回归与超越。他的人生告诉我们,人类不仅仅需要理性地对待现实世界,还需要有面对社会现实的勇气。
作者简介:刘圆圆(2000—),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语文)。
注释:
〔1〕刘红丽.《我与地坛》景物描写中的生命哲思[J].语文天地,2014(13):28-29.
〔2〕赵仲春.领悟生死哲理 共鸣达观情绪——《我与地坛》的景物描写[J].语文教学通讯,2010(31):35-36.
〔3〕史铁生.我与地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4〕史铁生.病隙碎笔:史铁生人生笔记[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