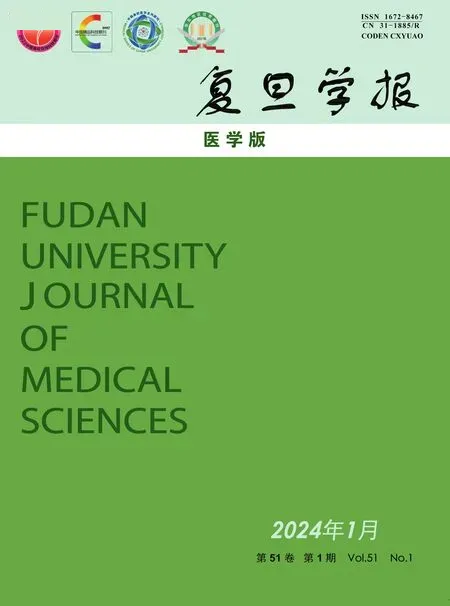基于ERAS 的腹壁下深血管穿支皮瓣乳房重建术麻醉管理进展
楼菲菲 张 军△ 吴 炅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麻醉科, 3乳腺外科 上海 200032; 2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肿瘤学系 上海 200032)
手术后快速康复(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的概念最早由Wilmore 等[1]于2001年提出。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ERAS 策略已在围术期广泛应用,促进了患者术后康复,体现在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住院天数的减少及住院费用的下降[2]。相较于ERAS 策略在其他手术中的广泛应用,其在腹壁下深血管穿支(deep inferior epigastric perforator,DIEP)皮瓣乳房重建术中的开展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目前国内外多个机构所制订的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的ERAS 方案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广及执行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ERAS 策略缺乏相应的指导原则。
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ERAS 策略涉及麻醉科、外科、护理部、放射诊断科等多个学科的多项要素[3]。这些要素若仅仅独立应用,均无法最大化地实现术后快速康复这一目标。因此,我们需要联合多学科进行各要素的整合,充分利用多学科协同优势,共同实现ERAS 的目标而使患者获益。在上述多学科所涉及的ERAS 策略中,麻醉科承担了围术期的要素工作,包括:麻醉方案优化的制订、围术期液体管理及内环境稳态调控、低体温预防、围术期多模式镇痛的完善和术后恶心呕吐的预防等[4]。然而,目前各机构所制订的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ERAS 策略中,对于麻醉部分方案要素所总结的内容过于简单薄弱,与麻醉科在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ERAS 策略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以及承担的大量工作并不匹配。麻醉学科内部也尚未制订全面详细的该类手术ERAS 策略中的麻醉方案,在参与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ERAS 策略相关的临床及科研工作中缺乏指导,与该手术迅速增长的数量之间存在差距。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是国内最早开展DIEP皮瓣乳房重建术的肿瘤中心之一。我院的麻醉科、外科、护理部、放射诊断科等多个学科团队,也较早在国内将ERAS 策略应用于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患者,实现了患者术后快速、顺利康复。目前,我院自体乳房重建术的成功率高于98%,自体游离皮瓣乳房重建术后皮瓣危象的发生率仅约5%,且皮瓣危象解救成功率可达70%,均位居国内领先水平。本文拟总结我院麻醉科在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的ERAS 策略中的麻醉方案,并结合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建立和完善基于ERAS 策略的麻醉管理方案,促进麻醉科在ERAS 多学科团队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并最终使乳腺癌患者获益。
优化麻醉方案
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的常用麻醉方案 DIEP皮瓣乳房重建术的外科操作复杂精细,手术时间长;手术涉及胸部、腹部两个手术区域,创伤大。早期的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主要采用单纯全身麻醉。随着区域麻醉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区域麻醉方法被应用于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并且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5-7]。但胸部、腹部两个手术区域的创伤程度又不尽相同,腹部的供体手术区域的疼痛程度往往较胸部的受体手术区域更为剧烈[8]。鉴于以上特点,此术式对于麻醉方案的制订及实施具有较高的要求。针对胸部、腹部不同的手术区域,我们推荐分别采用全身麻醉联合区域麻醉的方案,并将两者结合,既充分发挥了区域镇痛技术减少术中阿片类药物使用的优点,又显著降低了围术期应激反应和不适[6]。因此,区域麻醉联合全身麻醉已经成为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的ERAS 策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身麻醉联合硬膜外麻醉 目前,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的ERAS 策略中应用的区域麻醉技术存在差异[9]。概括而言,主要包括硬膜外麻醉、腹横肌平面(transversus abdominis plane,TAP)阻滞、椎旁神经阻滞等3 类区域麻醉技术。硬膜外麻醉技术具有出色的镇痛效果,在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中显著改善了患者围术期的急性疼痛[5]。除此之外,硬膜外麻醉还提供其他区域麻醉技术所不具备的肌肉松弛作用。在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的皮瓣获取过程中,术者需要将皮肤和皮下组织从腹直肌前鞘表面分离直至显露穿支血管。首先要识别穿支血管,继而需要追寻每根穿支,进入肌肉间隙,钝性及锐性分离肌束,暴露穿支及其主干,沿着血管主干找到腹壁下深血管。在确定了需要保留的优势穿支血管后,术者需要将其他穿支血管钳夹、离断[10]。以上描述的穿支皮瓣获取的全部过程均需在额戴式放大镜下完成操作。而显微外科操作所使用的高倍值放大镜可提供的手术视野范围狭小,手术视野内的肌肉抽动极易干扰精细的外科手术操作过程[5]。因此该手术操作过程需要严格的制动。硬膜外麻醉联合肌松剂,避免分离穿支血管这一过程时肌肉抽动对外科的精细操作造成不良干扰,为外科医师创造理想、舒适的工作条件[5]。此外,硬膜外麻醉经导管可随时加药从而覆盖手术全程,避免了区域神经阻滞受局麻药作用时间的限制[5]。而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腹横肌平面阻滞,因为其操作区域与腹部手术区域存在交叉重叠,因此TAP 阻滞的镇痛效果仅能为手术后半程提供镇痛,而无法实现手术全程覆盖[6,8]。当然硬膜外麻醉由于存在交感神经阻滞作用,可潜在地导致血压降低,因此硬膜外麻醉是否会影响患者的皮瓣血流灌注存在一定争议[5]。我院对大量接受硬膜外麻醉的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的病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硬膜外联合全身麻醉可以显著改善DIEP 乳房重建术患者的术后疼痛以及恶心呕吐情况,并且对皮瓣转归并未造成不良影响[5]。
全身麻醉联合TAP 阻滞 国际上TAP 阻滞是近年来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较为广泛应用的区域麻醉技术[3,6,8]。在TAP 早期应用于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的过程中,麻醉医师完成定位、穿刺、给药等操作。由于在完全暴露的手术区域,外科医师可根据解剖标志以及触觉反馈,直接进行定位、穿刺、给药的操作从而完成TAP 阻滞,因此随着该技术的开展、完善,外科医师可替代麻醉医师完成超声引导技术在此类术式中的应用[3]。除了TAP 阻滞的发展完善,局麻药物剂型的发展也为该技术在DIEP皮瓣乳房重建术中的应用带来了革新性的变化。布比卡因是TAP 阻滞使用最为广泛的局麻药,但单次给药无法为患者提供长时间镇痛。而在腹部手术区域附近置管,采用连续TAP 阻滞则操作过程复杂,若导管发生移位、脱落等情况均会影响术后镇痛效果。随着脂质体布比卡因的问世,也使TAP 阻滞技术成为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中镇痛的新选择[3,6]。
全身麻醉联合椎旁神经阻滞 除了以上提及的2 项区域麻醉技术外,椎旁神经阻滞在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中也被广泛应用[7]。椎旁神经阻滞的穿刺操作部位与硬膜外麻醉一样,均远离外科手术操作区域。因此,穿刺操作以及置管均不会对外科操作造成干扰。但是,椎旁神经阻滞的药物可扩散进入同侧的上下椎旁间隙,或是侧向扩散进入肋间隙,再或是向内侧扩散进入硬膜外腔。若药物进入硬膜外腔,则其阻滞作用便与硬膜外麻醉相似,且可阻滞交感神经[2]。此外,椎旁阻滞无法提供肌肉松弛作用。
以上3 类区域麻醉技术,均可显著减少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中阿片类药物的使用,降低术后疼痛评分。但是,何种区域麻醉技术在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中具有更佳的安全性和镇痛的有效性目前尚无共识。我们拟开展大样本研究对此进行分析,以期制订更为完善、优化的围术期麻醉方案。
跟人学人样,跟鬼学鬼样。这之后,王祥跟着钱总学起了古钱币生意,不过学的不是识货认价,而是学起钱总一肚子的坏水。日后时机成熟,这两人还要在古玩市场里闹出新花样。这就是后话了。
围术期液体管理及内环境稳态调控
围术期液体管理的重要性及意义 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液体管理的目标是优化皮瓣血流灌注,改善皮瓣微循环[11]。围术期液体管理的优劣与皮瓣转归息息相关。目前,与大量针对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的外科技术相关的研究相比,针对该术式的液体管理的研究数量极少。一项由显微外科及麻醉科共同发起的调查显示,在游离皮瓣重建手术中,患者的液体管理是显微外科医师与麻醉科医师最常讨论的话题之一[12]。术中液体管理是否得当对于游离皮瓣重建术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类术式制订一系列液体管理的标准操作规范,有助于优化术后皮瓣转归,加速患者术后康复。
游离皮瓣乳房重建术理想的液体管理应具备维持合理血容量、防止皮瓣水肿、确保心功能正常以及优化皮瓣血流灌注等特点[11]。Zhong 等[11]对354 例游离皮瓣乳房重建术的回顾性研究表明,手术当日晶体液的输注速度是术后并发症的重要预测因子。Nelson 等[13]对682 例自体乳房重建术的研究显示,术中补液量不足将导致手术后皮瓣血栓的发生率增加。Booi 等[14]开展的一项对104 例游离皮瓣乳房重建术的研究显示,液体输注过量将增加发生皮瓣血栓的风险。研究者认为,从麻醉医师的角度出发,液体治疗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最佳的全身血压。而从乳腺外科医师及整形外科医师的角度出发,液体治疗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游离皮瓣组织的充分灌注。但是这些目标有时可能相互矛盾。因此需在良好的循证医学基础上,优化液体输注方案,同时满足麻醉医师及外科医师的需求[11]。
2015 年Motakef 等[15]发表了基于循证医学证据而制订的游离皮瓣重建术围术期管理的荟萃分析。其中,液体管理推荐:在围术期24 h 内,晶体液的输注速度应维持在3.5~6.0 mL·kg-1·h-1;晶体液的输注速度大于130 mL·kg-1·d-1(5.4 mL·kg-1·h-1)将增加发生并发症的风险;应避免术中晶体液输注量大于7 L。以上荟萃分析有助于指导游离皮瓣重建术的围术期补液管理。然而根据荟萃分析所制订的目标补液速度仍然过于宽泛。并且仅仅就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这一具体术式而言,该荟萃分析并未明确指出在手术操作这段最为关键的时期,麻醉医师应如何调控患者的补液速度。此外,与大面积的游离皮瓣头颈重建术相比较而言,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中的失血量、不显性失水量存在差异[11]。因此,对于接受该类重建术的患者而言,制订更为精准、个体化的补液管理方案至关重要。
目前,虽然有多项研究显示液体输注不当会增加皮瓣危象的发生率及其他不良事件,但其确切的机制仍未明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液体输注不足会导致游离皮瓣灌注不足;而液体输注过量则会引发液体潴留,导致游离皮瓣水肿以及充血性心功能不全[11]。此外,有研究指出,除了液体输注量以及液体输注速度,液体输注的种类同样也会影响游离皮瓣的转归[11,16]。在游离皮瓣重建术中,由于手术时间长和手术范围广,体液转移较大,研究者建议对不显性失水者给予输注晶体液治疗;对于术中失血者,研究者建议给予输注胶体液治疗[15]。
目标导向液体治疗 2015 年一项对于英国全国性的游离皮瓣重建术的调查研究显示,大量被调查者认为,应将尿量作为决定补液决策的依据。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应该将尿量、平均动脉压、中心静脉压等临床监测指标,共同作为决定补液决策的依据[12,15]。目前,目标导向液体治疗(goal-directed fluid therapy,GDFT)尚未成为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中的液体管理的常规策略。但研究显示GDFT策略可显著降低大型手术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及术后死亡率[16-17]。而在显微血管外科手术中采用GDFT 策略,可显著缩短住院时间,并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16,18]。在游离皮瓣重建术中应用GDFT 策略,可显著减少术中补液量,缩短住院时间,降低术后皮瓣并发症的发生率[19]。Polanco 等[20]开展的一项关于在自体皮瓣乳房重建术中应用GDFT 策略的研究结果显示:GDFT 组接受的中位液体总量显著减少;GDFT 组液体输注速度显著降低;GDFT 组的术中平均动脉压中位数显著较低;GDFT 组使用血管加压药的患者比例更高;术后并发症在组间无显著差异;GDFT 组的中位住院时间显著缩短。研究者指出,在显微外科手术中使用血管加压药治疗低血压一直存在争议。既往的多项研究不推荐在该情况下使用血管活性药物。Polanco 等[20]认为,尽管GDFT 组患者液体输注量较少,且血管加压药使用较多,但并未增加该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GDFT 策略的应用应与围术期血流动力学相结合,明确治疗的最优选项,不应脱离对血流动力学等因素的考量而片面使用。因此在接受自体乳房重建术的患者中,应用GDFT策略并谨慎使用血管升压药是安全的,并不会增加患者的术后并发症。
2017 年,Temple-Oberle 等[4]发表了乳房重建术ERAS 路径的围术期管理共识。其中液体管理推荐:避免液体输注过量,或者液体输注不足;应维持水、电解质平衡;GDFT 策略有助于实现以上目标;相较于生理盐水,更推荐使用平衡晶体液;合理使用血管升压药有助于液体管理,且不会影响皮瓣。目前,对于在我院接受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的患者,我们已经将GDFT 策略纳入常规的围术期液体管理中,作为ERAS 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此类术式的患者,我们在术中常规监测心输出量、每搏量变异度(stroke volume variation,SVV)等指标。SVV 预测液体反应性较中心静脉压更敏感,可更加精确地指导液体管理。当SVV>13%时,提示循环容量不足,给予液体治疗;当SVV<13%时,提示循环容量充足,无须进一步液体输注。在采用GDFT策略的同时,我们也时刻注意将GDFT 策略与患者的个体因素相结合,以期为患者制定更为精准的液体管理方案[20]。
预防低体温
低体温对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的影响 研究显示围术期低体温会影响患者伤口愈合,延长患者住院时间,增加伤口感染的概率[4]。长时间的DIEP皮瓣乳房重建术极易导致术中低体温。低体温可导致红细胞缗钱状排列及血小板聚集,进而增加血液黏性;同时低体温还可导致外周血管收缩,继发游离皮瓣血流减少而影响其血流供应[12]。Sumer等[26]在对头颈重建术的研究中发现,术中患者中心体温<35 ℃与围术期并发症密切相关。Hill 等[27]对游离皮瓣重建术的回顾性研究显示,术中患者中心体温最低值<34.5 ℃与术后受区感染密切相关。尽管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心体温过低与患者不良预后密切相关,但早期也曾有研究者持相反的意见。Liu 等[28]的回顾性研究显示,术中保持适度低体温可以降低游离皮瓣栓塞的发生率。低体温对于游离皮瓣的转归所造成的影响在早期并无定论,但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在乳房重建术中维持患者的中心体温在36 ℃以上,以避免发生低体温导致的并发症[15]。
预防低体温的措施与方法 目前,在乳房重建术的相关指南中提倡在术中持续监测体温,并且完善各项保温措施[4]。近年来,在我院接受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的患者,术中鲜有低体温发生,这均得益于手术中严密的中心体温监测,以及联合保温措施的应用。我院手术室内常用的加温方法包括充气加温装置、加温床垫、静脉输注加温液体等。接受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的患者我们常规实施鼓膜/鼻咽处中心体温监测,并且给予充气加温装置/加温床垫与静脉输注加温液体相结合的联合保温措施。
在我院最初开展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的阶段,我们曾经尝试采用单一的加温措施,事实上我们发现任何一种单一的加温措施,在手术进程的前半程虽然可维持患者的中心体温在36 ℃以上,但随着手术时间的延长,大多数患者的中心体温逐渐降低,而在手术结束时往往低于36 ℃。因此我们推荐联合使用不同的加温措施以避免围术期低体温而潜在影响皮瓣转归。
完善围术期镇痛完善的围术期镇痛可缩短接受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的患者术后卧床时间,有利于患者术后早期活动,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减少患者住院费用[9]。我们在术中采用全身麻醉联合区域麻醉方案,但若术后采取区域麻醉这项单一镇痛技术,则仅可为腹部的供体手术区域提供镇痛作用,无法兼顾胸部的受体手术区域。此外,部分患者术后需要接受抗凝治疗以预防血栓等并发症,因此为改善术后镇痛覆盖区域不全,预防硬膜外血肿等并发症,我们对大多数患者给予了静脉自控镇痛。我们推荐合理衔接术后静脉自控镇痛与术中镇痛,以避免由于镇痛作用缺失导致的术后疼痛,进而增加血管张力,影响皮瓣血流供应[29]。
静脉自控镇痛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阿片类药物引起的恶心、呕吐、便秘、瘙痒等不良反应。因此采用多模式的镇痛方法,减少阿片类药物的使用量,是乳房重建术的相关指南对于此类患者术后镇痛的推荐策略[4]。对于接受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的患者,我们在术后静脉自控镇痛的药物配方中,除了阿片类药物,也给予了非甾体类抗炎药。此外,在患者麻醉诱导前,我们给予选择性环氧化酶-2(COX-2)抑制剂以期达到预防性镇痛的目的。
我们对患者术后随访的初步数据显示,接受多模式镇痛策略的患者术后疼痛评分低,严重疼痛的患者比例低,恶心、呕吐、便秘、瘙痒等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因此,我们推荐围术期采用多模式的镇痛方法,减少阿片类药物的使用量,降低阿片类药物的不良反应。
预防术后恶心呕吐术后恶心呕吐可增加术后主观不适体验,影响术后早期活动,延长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30]。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需要切取腹部的皮肤及脂肪组织,移至胸部进行乳房重建。患者腹部的皮肤、脂肪等组织缺失,腹壁薄弱。术后恶心呕吐导致的腹压增加,可引发伤口裂开及出血等并发症。因此预防术后恶心呕吐是加快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患者术后康复的重要内容之一[30]。
乳房手术及整形手术的术后恶心呕吐发生率较高[31]。绝大多数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患者均为术后恶心呕吐的高危人群。研究显示外科手术后恶心呕吐的总体发生率为30%,而高危人群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率可高达70%[30]。Manahan 等[32]对DIEP 乳房重建术的回顾性研究显示,76%的患者发生了术后恶心呕吐,并且66%的患者程度较为严重。因此,在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围术期预防术后恶心呕吐至关重要。
2020 年发布的《术后恶心呕吐管理专家共识(第四版)》推荐联合使用2 种或2 种以上止吐药预防术后恶心呕吐,且研究显示联合用药的预防作用优于单一用药(证据级别A1)[33]。对于在我院接受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的患者,由于采用全身麻醉联合区域麻醉的方案,并且使用多模式镇痛策略,围术期阿片类药物剂量已大大减少。在术中的麻醉维持阶段,我们的前期研究结果和该共识的推荐策略相一致,即:与吸入性麻醉药物相比,丙泊酚可降低接受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的患者恶心呕吐的发生率[30]。在预防性使用止吐药的选择策略方面,我们通常使用联合用药的预防模式,即:麻醉诱导阶段,给予地塞米松5~8 mg;术中应用氟哌利多0.625~2 mg;手术结束阶段则给予5-羟色胺3(5-HT3)受体拮抗剂,可明显降低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率。
结语随着外科技术的不断发展,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的研究重心已经从完善外科手术技术这一单一目标,逐步演变至促进患者术后快速康复这一协同目标。麻醉科和其他多学科团队之间深入的协调、沟通是完善这一目标并使患者最终获益的基础。随着ERAS 策略日益深入人心,作为多学科团队中重要的一员,麻醉科团队的策略细则、工作内容也应及时、相应地调整,在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的ERAS 多学科团队中发挥主导作用,使DIEP 皮瓣乳房重建术更好地应用于乳腺癌患者。
作者贡献声明楼菲菲 研究实施,文献整理,论文撰写和修订。张军 研究设计,论文撰写和修订。吴炅 研究设计,论文修订。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