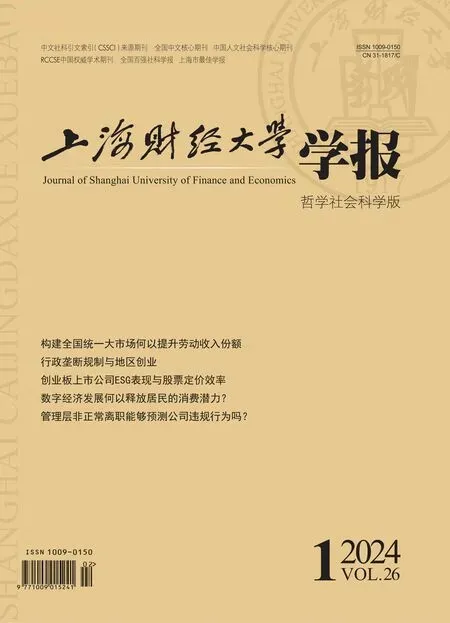双重身份属性下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规制
丁国峰
(安徽大学 法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一、问题的提出
一直以来,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屡禁不止,从2010年奇虎公司与腾讯公司的“三Q大战”到京东诉天猫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再到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尤其是在“双十一”“双十二”等大型促销活动前夕,平台企业之间的“二选一”争斗十分激烈。所谓“二选一”,是指实施限制的平台企业(以下简称“施限平台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强制要求商家选择要么放弃入驻、要么继续使用被限制的平台企业竞争者(以下简称“受限平台企业”)的行为。由于商家对施限平台存在很强的经济依赖性,施限平台的强制行为总能具有较大的约束力,商家群体缺乏力量与之抗衡,由此强制商家进行“二选一”的行为会削弱受限平台的市场力量,同时被强制商家也会深受其害。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实施有赖于其强大的市场优势,商家端的依赖以及受限平台的相对弱势是施限平台开展“二选一”策略的重要前提,因此一般实施“二选一”行为的都是行业内的大型平台企业,而且主要是行业内的首位者。平台企业会充分利用规则制定权、管理权和惩戒权等对商家的选择行为进行激励引导以及惩罚强制,一旦商家不予配合,施限平台企业则会采取下架、限制数量、增加佣金等方式进行惩处,对于在施限平台上进行独家经营的商家则会提供平台资源奖励及优惠。在这一奖一罚之下,平台企业与商家之间的纵向强制关系十分突出,商家对平台的自由选择行为受到扭曲,双边平台市场的竞争机制也发生扭曲,受限平台企业被不适当地削弱了竞争力,最终被挤出市场。例如,为了限制滴滴外卖市场的扩张,美团外卖和饿了么外卖要求商家不得同时加盟滴滴外卖平台,并要求已经在滴滴外卖平台上入驻的商家自行退出,否则就采取限制送餐范围、上涨扣点、关闭店铺等处罚措施。①郭诗卉:《无锡工商局约谈三外卖平台 停止商户“二选一”等行为》,2018年4月12日,http://m.people.cn/n4/2018/0412/c120-10814902.html,2023年8月29日访问。现今,滴滴外卖未能如愿成为外卖行业的新巨头,面临着被迫退出市场的风险。②王炆忌:《滴滴外卖撑不住了,大批人员转岗,或者面临关停的风险》,2019年3月18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8339768179369920&wfr=spider&for=pc,2023年8月29日访问。
事实上,无论是从博弈论出发定量分析社会的总福利,③乔岳、杨锡:《平台独家交易妨碍公平竞争吗?——以互联网外卖平台“二选一”为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还是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视角出发,④苏号朋:《优势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适用》2021年第3期。对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都具有正当性。为避免平台垄断和资本无限扩张、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需要依法及时制止“二选一”等新型网络限制竞争行为,可“二选一”行为具有多样性和隐蔽性,从法律适用的角度解决“二选一”行为会出现理论与实践的难题。一方面,《反垄断法》中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设置的门槛过高,致使支配性地位和限制、排除竞争效果的认定存在困难;另一方面,《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实际适用时也存在若干阻碍,事实上不具有适用的可能性。⑤袁波:《电子商务领域“二选一”行为竞争法规制的困境及出路》,《法学》2020年第8期。为此,相关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或方法模型进一步深化了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规制研究。有学者认为平台“二选一”行为的规制核心在于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我国《反垄断法》应当引入“相对优势地位”的规定,可是“滥用优势地位”的概念存在导致相关法律条款存在滥用的风险。⑥王晓晔:《论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的法律规制》,《现代法学》2020年第3期。也有学者对现行法律体系的冲突与矛盾进行深刻反思,提出以《反垄断法》为规制中心的破题思路,可是对于互联网平台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标准以及合理性抗辩事由的提出还存在诸多商榷之处,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⑦曾晶:《论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法律规制的完善——以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11期。还有学者同样提出了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破局思路,并从有利于监管的视角提出行为豁免、事前控制的方案,但可行性仍有待探讨。⑧许丽:《电商平台“二选一”排他性交易的反垄断规制》,《中国流通经济》2022年第4期。
总而言之,双边平台的独特属性的确给“二选一”行为的竞争效果分析带来了诸多不便,大多数经济学领域的学者都不否认“经济学的旧公式没有为双边平台提供正确的答案”,⑨Evans D S,Schmalensee R.Matchmakers: The new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s,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6,p.15.现行的反垄断执法工具远不足以充分评估双边平台的“二选一”行为的市场竞争效果,其真正影响市场竞争状况也较大背离于其表面所能观察到的市场竞争力,应当受到竞争政策尤其是反垄断规制更多的关注。本文从双边平台的身份属性出发,剖析双边平台能够实施“二选一”行为的核心所在,在此基础上审思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和对策。
二、平台企业的身份属性转变及其管理行为的解构
双边平台成功的关键在于平台与线上交易市场的融合,交易市场的虚拟化形成网上交易市场,①仲春:《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的检视与完善》,《法学评论》2021年第4期。平台凭借其聚集效应成为连通市场各方以及线上交易市场运作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聚集效应和互联网效应、马太效应、锁定效应等诸多效应的综合作用下,平台与线上交易市场不断融合。在此情况下,平台企业和平台的关系以及其与线上交易市场的关系发生了相互的渗透和转化,平台企业的平台管理行为也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变,这些转变使得双边平台的“二选一”行为与传统排他性交易发生了结构上的根本不同,传统理论和规则在适用上如何创新、解释和突破值得深思。
在平台企业实施“二选一”的行为中,平台企业对商家进行强制和惩戒的行为暴露出两者关系上的不对等,而这种不对等并非仅源于商家对平台服务的依赖性,更来源于平台企业对商家所处线上平台市场的运营和管理地位。平台不仅是平台企业为商家参与线上市场竞争提供技术与设施服务,还是商家开展线上商业和线上市场竞争的空间场所和市场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平台控制着关键性基础设施。②Bracha O,Pasquale F.Federal Search Commission-Access,Fairness,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Law of Search,Cornell L.Rev.,2007,93,p.1149.这就意味着平台企业在线上交易市场竞争中同时扮演着服务者和市场管理者的双重角色,平台企业与商家间的关系也同时具备横向与纵向的双重属性。
(一)平台企业的双重身份属性阐释
线上交易存在平台企业、商家和消费者三方主体。商家与消费者为线上交易的实施者,也是线上交易的主要参与方,两者分别对应供给和需求两侧。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而广泛存在的供给与需求匹配低效的问题,借助互联网技术信息高效交换、无形性和空间无限性等特点的双边平台应运而生,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了一个线上供给和需求相互匹配的场所。③陈兵、赵青:《反垄断法下平台企业“自我优待”行为的违法性认定》,《江汉论坛》2023年第7期。平台企业同时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线上市场接入、信息储存、信息交换、线上互动等服务,并促进商家与消费者线上交易的达成。因此,平台企业在线上交易市场的运作中发挥技术服务的中枢功能,平台企业与商家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平台企业为商家提供线上市场并帮助商家接入市场,实际上对商家参与线上市场的竞争起到必不可少的辅助作用,通过线上交易基础设施的构建和完善来服务于商家的线上市场竞争需求。但是,平台企业的功用并不止步于此,平台服务之下市场参与主体及市场资源产生汇聚,并在以平台为界限的领域内进行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由此市场与平台的重合关系引申出平台企业的第二重身份——市场管理者。
在平台经济学的定义中,平台从本质上被认为是一种交易空间或者场所,可以存在于现实世界,也能存在于虚拟的网络空间。④李心灵、祁敬宇:《平台经济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行政管理改革》2023年第6期。该空间引导或者促进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达成,并且通过收取恰当的费用而努力吸引交易各方使用该空间或场所,最终实现收益最大化。⑤徐晋:《平台经济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序。平台空间在聚合商家和用户资源的同时也形成了市场的网络边界,不同平台所形成的网络空间相互独立,平台之间并不互联互通,由此线上交易市场出现了平台化的块状分布特征。但是,线上交易以及市场竞争都发生于平台这一空间和场所,线上交易市场的运作也必须以双边平台为依托才可完成,因此平台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内容的提供者,还构成了商家开展线上交易、参与竞争的市场空间。在此意义上,相互独立的线上交易平台的集合共同构成了线上交易市场整体的运作空间,市场因单个平台的特定性和独立性而具有了虚拟网络中的固定空间范围。
简而言之,平台企业、线上商家和消费者共同形成了线上交易市场,而平台企业通过交易空间和基础设施的提供框定了市场的运作空间,并依靠平台市场所具有的“交叉外部性”锁定线上商家和消费者,①Rochet J C,Tirole J.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6,37(3),pp.645-667.每个平台框定空间的组合就是线上交易市场的整体。在平台与市场发生重合的情况下,平台企业对平台的经营管理行为具有了市场干预的属性,平台企业与商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转化,平台企业的市场地位和市场力量的分析角度和方式也将会受到重大影响。
(二)双重身份属性下平台与商家关系的转变
服务者身份下,平台企业与商家的关系自然是横向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双方的法律地位平等。但在交叉网络效应的作用下,平台价值会随着商家和消费者的增加而不断提升,平台企业的市场地位也随之增强,商家对平台企业的依赖性增大,平台企业对商家的锁定能力也同时增强,其相对优势地位也随之加强。商家与平台企业间的横向关系出现事实上的失衡倾向,平台企业与商家之间的横向服务关系的纵向化也会越来越突出。②Lee R S.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exclusivity in platform and two-sided marke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103(7),p.2960-3000.此外,从平台的线上交易地位来看,平台服务对于商家的线上市场竞争而言必不可少,由此也隐含了平台企业与商家横向关系的微妙状态。
市场身份下,平台与市场重合,平台就是线上交易市场。作为平台的所有者,平台企业拥有运营、管理平台的权力,由此对于线上市场也有管理、干预的现实权力。具体而言,平台企业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制定平台规则,为平台内市场制定除现行法律等规定之外的其他“游戏规则”,以引导或强制商家为或不为一定的市场行为。当然,游戏规则的制定应当建立在法治框架下,否则规则制定行为及规则本身都属违法。同时,平台企业也拥有监督、管理和处罚商家的权力,负责监督和查处商家违反法律规定、平台规则的行为,并根据行为性质及其程度对商家施加处罚,以保障平台内市场的交易和竞争合法有序并维护平台商誉和利益。例如,淘宝设置有警告、扣分、搜索降权、商品下架、店铺关闭等多项处罚机制,③曹阳:《互联网中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成因与危害性的法学思考:兼对我国互联网中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典型案例分析》,《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其中部分处罚还存在时间长短、数量大小等裁量区间。处罚机制是权力行使的保障机制,平台企业的管理行为对商家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强制效力,这也表明平台企业作为管理者对商家具有支配优势。在市场身份下,平台企业与商家的关系为纵向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双方关系并不平等,平台企业具有完全不对等的管理权利和相配套的强制力保障措施。
双重身份下,平台企业与商家同时具有横向服务关系与纵向管理关系,其中横向服务关系的纵向化进一步加剧了双方关系的纵向性。这种纵向管理关系也表明平台企业干预市场、强制商家的相对便利性和有效性,平台企业的市场管理者角色也反映出平台企业的市场干预行为对潜在市场竞争产生了相应影响。
(三)双重身份属性下平台对商家的锁定效应
无论是服务者还是市场管理者的身份,平台企业对商家的优势地位和权利都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市场管理者的身份下商家对于平台企业的管理和强制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但是,商家并非毫无办法,商家对平台企业力量的制衡作用构成了平台企业行为的限制机制,由此双方发生博弈。商家对平台的选择越自由,商家力量的制衡效果也就越强,商家在与平台企业博弈过程中的话语权也就越大。①陈阿兴、相佳秀:《数字经济时代电商平台垄断治理研究》,《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因此,平台企业的权利和相对优势地位的行使不仅要考虑平台自身利益,还需要考虑商家的接受范围和忍耐程度,特别是平台企业在缺乏正当性基础时的滥用行为,商家能否忍耐也决定了平台企业对平台内市场的支配情况,即平台企业对商家的支配力量与商家对平台的依赖应当保持相称。②刘权:《网络平台的公共性及其实现——以电商平台的法律规制为视角》,《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
因技术原因,各平台市场之间并非互联互通,尽管在参与主体上可能存在重合,但每个平台的市场仍是相互独立和特定的。就单个平台市场而言,每个平台市场内商家都会建立专属于该平台市场内店铺的客户资源、销售渠道、店铺信誉等竞争优势,并且为了得到和增强这些竞争优势,商家也会不断地投入时间、精力、金钱等沉淀成本。商家在平台市场内店铺的综合优势和沉淀成本共同构成了商家的转移成本,由此产生了平台企业对商家的锁定能力。从多平台角度分析,商家在某一平台店铺市场的资源积累和沉淀成本投入很难转移到其他平台市场。③曾雄:《平台“二选一”反垄断规制的挑战与应对》,《经济学家》2021年第11期。因此,尽管在多归属的背景下商家可以选择同时入驻多家平台市场,但每个平台市场内经营的店铺实际上类似于商家经营的若干“分店”,而“分店”之间在成本投入、市场地位、资源持有量和利润获取等方面都是相互独立的,均特定于其分别所处的平台市场。所以,在多平台共存和多归属策略之下,商家被入驻的各个平台市场同时锁定了,商家被锁定的强度与平台市场的规模大小相关。在强力锁定下,商家对平台企业的竞争策略只能被动遵从,④焦海涛:《电商平台“二选一”的法律适用与分析方法》,《中国应用法学》2020年第1期。并且容忍一定范围内的不利损害。⑤伍富坤:《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反垄断法〉调整》,《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申言之,就商家而言,分处于各平台的店铺之间不具有可替代性,他们同为商家在线上交易市场的多个经营主体和销售渠道,从多平台到单平台的转变也很难让其回归多平台时的整体盈利状态和竞争能力,因为商家会丧失部分达成交易的机会。⑥王先林、方翔:《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趋势、挑战与应对》,《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因此,平台企业对商家的锁定能力与平台市场的发展规模大小相关,而且各平台能够通过分别锁定店铺的方式锁定商家。⑦孟雁北:《反垄断法规制平台剥削性滥用的争议与抉择》,《中外法学》2022年第2期。
平台市场需要商家的入驻来提升平台市场的整体价值并增加平台主体的盈利(商家交纳的各种费用),而商家则需要平台为其提供线上信息上传、展示和交互等交易所需功能服务进而实现线上产品宣传展示和交易,平台通过提供线上交易所需功能服务来吸引商家并换取商家入驻带来的平台增值和服务费,而商家根据平台服务的质量以及费用的高低进行综合选择,双方在需求的相互满足和博弈中形成市场生态。商家对平台的选择和入驻实际上反映了商家群体构成的市场选择机制对平台的选择,通过对平台整体价值、服务内容和质量以及费用收取等进行综合评判进而决定市场资源的流向,因此商家的选择是对平台的整体价值、服务质量和价格所作出的市场回应。⑧李森彪、邢文杰:《双边市场下商家和电子商务平台的演化博弈分析》,《运筹与管理》2019年第9期。而消费者规模大小是平台创收的根本,当平台未能集聚足够多的消费者时,其无法通过大数据分析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服务形成消费者黏性,继而无法实现收入增长。⑨丁国峰:《大数据运用视角下互联网反垄断规制的完善进路》,《商业经济与管理》2023年第10期。随着线上交易行业日趋成熟,平台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已经激发,平台的资源集聚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平台市场对商家的吸引和锁定能力不断增强,也会逐渐摆脱主动吸引商家的大量资源投入,而将重心转移到消费者体验上,重点扩充用户数量和提升消费者黏性。①张守文:《反垄断法的完善:定位、定向与定则》,《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因此,真正能够对平台产生有效的选择和抗衡效果的是消费者,而非商家,因为商家所受到的锁定效应远不足以使单一平台对他们行使那些特权和优势,他们能够轻易地转移到另一平台市场,②孙宝文、荆文君、何毅:《互联网行业反垄断管制必要性的再判断》,《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7期。平台市场内商品的种类、质量、价格及相关服务等形成的平台综合价值,才是能够锁定他们的要素,而这些主要由平台市场内的商家决定的。一方面,商家的聚集和激烈竞争能够对消费者产生吸引力;③吴太轩、赵致远:《电商平台排他性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另一方面,平台企业对商家有较强的锁定能力,能够支撑其行使地位优势及管理权利。由此可知,商家成为平台企业间进行竞争的主要强制对象,而用户则是平台企业竞争的主要内容,也是平台市场地位的重要衡量标准。
三、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的违法性分析
“双边市场”的概念最先由梯诺尔等人提出,④Rochet J C,Tirole J.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3,1(4),p.990-1029.埃文斯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将“双边市场”理论的聚焦对象从传统的媒体市场、支付卡市场和拍卖市场转向了平台市场。⑤Evans D S.The antitrust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 markets,Yale J.on Reg.,2003,20,p.325.不同于遵循供给需求的函数标准的传统市场,双边平台市场更加依赖于双边需求之间的相互性(又称“间接互联网效应”)。赖特认为双边平台凭借此效应实施的“二选一”行为的市场封锁是非效率的、是反竞争的。⑥Doganoglu T,Wright J.Exclusive dealing with network effec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10,28(2),pp.145-154.而奥康纳呼吁对双边平台多些动态的思考,对一些机构或学者提出的“控制用户数据可以锁定竞争对手”的论断提出质疑。⑦O'Connor D.Understanding online platform competition: Common misunderstandings,Internet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of Online Platforms (May 2016),Competi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2016.
市场管理者身份下,平台企业的“二选一”行为的实施逻辑和竞争效果都发生了变化。线上市场与平台的重合之下,“二选一”对平台的管理和操控直接在平台市场上显现,线上市场所受的损害更加直接且严重。
(一)平台“二选一”行为的逻辑新解
“二选一”行为的实施会强制商家在施限平台和受限平台间作出选择,看似尊重商家的选择自由,但实际是强制商家放弃受限平台并选择施限平台。⑧熊文聪:《电商平台“二选一”的法律问题辨析——以反垄断法为视角》,《中国应用法学》2020年第2期。在强制选择的范围内,施限平台企业具有远超受限平台企业的市场优势,此时相对意义上的优势转化为绝对意义上的优势,市场支配地位在选择范围内成立。因此,“二选一”行为之下,平台企业的支配地位是客观存在的。
以平台整体为“二选一”对象的案件中,施限平台企业通常在市场地位上远远超过受限平台企业,属于行业中的头部平台企业,由此才能确保选择结果有利于施限平台,且其他平台不会搭便车。这里的市场地位并非指平台企业在平台类服务中的优势力量,而是平台企业运营和管理下的平台市场在整个线上交易市场中的地位,因为平台市场是商家竞争和获利的特定场所,其与商家利益高度相关,商家也最为在意。因此,不同平台之间在重叠商家的范围内,商家对平台市场的依赖程度是商家选择的主要依据,即平台企业的锁定能力才是市场地位的准确解释。
此外,同一商家在不同平台市场内的店铺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往往存在差别,而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最强的店铺所处平台市场对商家的锁定效应相对更强,由此具体到单独的商家,每个平台企业都会有更倾向于自己的商家店铺。①苏治、荆文君、孙宝文:《分层式垄断竞争:互联网行业市场结构特征研究——基于互联网平台类企业的分析》,《管理世界》2018年第4期。在此情况下,以个别商家为对象的“二选一”行为应运而生,通过奖励、优惠的诱导和处罚政策的胁迫,施限平台企业驱使特定商家放弃其他平台市场。这种“二选一”行为的针对性更强而且更为隐蔽,实施对象可能表现为平台企业的核心商家,以实现平台市场的长尾经济效应。故而,中大型企业的资源争夺及专项奖惩也成为“二选一”的重要表现类型。例如,为应对天猫的“二选一”压力,京东推出名为“龙腾计划”的重点扶持项目,暗示选择京东的商家能够获得平台费用减免、免费资源支持以及帮助处理商家因“二选一”而产生的滞销库存等优惠和奖励。②杨清清:《天猫、京东持续激战:品牌商面临促销节之痛》,2017年6月8日,http://www.cinic.org.cn/hy/zh/388530.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8月22日。在这种“二选一”行为中,平台企业整体的市场优势可能不太突出,但对于这些核心商家的锁定能力却具有相对的优势,因为商家在施限平台市场内店铺的盈利和竞争状况要优于受限平台市场的店铺。但此时“二选一”行为的分析较为复杂,因为平台企业的实施动机、市场力量及竞争效果可能难以支持《反垄断法》的适用。
(二)“二选一”行为的竞争效果分析
1.双边平台市场层面。平台企业实施“二选一”行为的最终目的是维持和促进平台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使平台市场规模更大、质量更高且稳定性更强,这必然会引发双边平台市场的市场机制扭曲,造成竞争被限制甚至被排除的效果。“二选一”行为的实施逻辑是通过施限平台企业与受限平台企业的市场地位进行简单比较,并以此作为市场资源竞争的唯一依据,即以简单的平台市场大小比较来代替复杂的市场竞争机制。在这种比较式竞争下,竞争的结果是人为控制的,因为施限平台企业一般只有在必胜的情况下(这里主要指攻击性“二选一”案件,防御性“二选一”案件的情况较为复杂)才会选择“二选一”,此时市场竞争机制被人为地扭曲,线上交易市场的市场竞争也被限制甚至排除。
“二选一”行为强制商家对入驻平台作出选择,实际上是要将商家的多归属模式转变为单归属模式,加上平台市场的强大锁定效应的运作,平台市场的封闭性就会逐渐加大,进而封锁了平台市场内的经营商家。③焦海涛:《数字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法律规制》,《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与此同时,受限平台的入驻商家数量也会逐步减少,由此受限平台市场的规模也会逐步缩小,与市场规模高度相关的平台企业的锁定能力、资源汇聚能力和市场优势都同时会降低,受限平台企业会被逐步挤出同行业市场。事实上,受限平台企业往往无法拒绝“二选一”,只能被迫将受限平台市场纳入选择范围,对于选择产生的结果也只能被动接受。在此意义上,受限平台企业非自愿地参与了横向垄断协议。类比刑法中共同犯罪与片面共同犯罪的概念,“二选一”行为在形式和效果上可称之为“片面横向垄断协议行为”。
综合来看,“二选一”行为在双边平台市场产生了市场封锁和市场分割的竞争效果。单归属模式的转化与平台市场的锁定效应共同促进了线上市场商家的固定性。平台市场的封锁趋势也将引发线上交易市场的封锁与平台化分割,继而双边平台市场也被分割。同时,因线上交易市场整体被封锁且商家被固定,双边平台市场就会形成新的进入壁垒,①孙晋、赵泽宇:《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界定的系统性重构——以《反垄断法》第18条的修订为中心》,《科技与法律》2019年第5期。致使潜在竞争者难以拉拢商家并形成自己的平台市场,而且已进入的平台市场具有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等加持,平台间市场的潜在竞争力量就会被严重压制了。比如,自2019年5月28日格兰仕入驻拼多多以来,格兰仕在天猫平台的搜索端陆续出现异常,其曾多次与天猫平台进行交涉但都未有结果,而且导致格兰仕“6·18大促”期间在天猫平台上的六家核心店铺销售额较上年同期均大幅下滑。②人民网:《格兰仕起诉天猫“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获受理》,2019年11月6日,http://it.people.com.cn/n1/2019/1106/c1009-31440201.html,2023年8月28日访问。
2.线上交易市场层面。平台市场及入驻商家是“二选一”行为的直接施限对象,由于平台商家的多归属特征以及线上交易市场的整体性,单一平台企业的强制选择行为具有明显的外溢性,进而对其他平台市场与其入驻商家以及整个线上交易市场的竞争机制都将造成严重影响。为了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选择施限平台市场并放弃受限平台市场,施限平台企业会采取一系列的处罚和奖励措施,由于市场管理者身份的存在,这些措施将直接涉及平台市场资源的人为配置问题,而且在市场封锁与分割之下,不同市场间的商家竞争会被不断削弱,线上交易市场的整体规模和质量也被降低,市场竞争和经济效率必然会受到损害。
具体来说,“二选一”行为的实际强制对象是相对特定的,而特定化的原因并非是市场机制的自发选择,而是商家是否会选择同时入驻多平台以及其在所属行业的竞争中是否处于中上层的地位,③李森彪、邢文杰:《双边市场下商家和电子商务平台的演化博弈分析》,《运筹与管理》2019年第9期。即平台企业的人为选择构成了“二选一”行为的强制对象标准。在被强制的商家同意或拒绝平台企业的选择要求时,平台企业会向商家施加直接的市场打击或资源给予,由此商家在平台市场内的竞争力量会受到相应的损害或提升,平台市场内的竞争机制会被扭曲。在选择施限平台市场的情况下,被强制商家必然要放弃受限平台市场,其在线上交易市场整体的市场竞争力量被迫降低,而且在渠道尤其是大型渠道的放弃之下,商家的业绩下滑、库存增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会直接受到严重损害。同时,受限平台市场内的商家数量减少,受限平台市场也会因此萎缩,继而引发线上交易市场的缩小以及竞争空间的压缩,整体线上交易市场内的竞争有效性和市场活力也会因此降低。如前所述,“二选一”会导致平台市场的相互封锁和线上交易市场的分割,不同平台市场内同行业商家间的竞争被隔离。线上市场与线下市场虽处于不同维度但同属于全国市场,平台企业对线上交易市场的分割同样严重违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类比线下地域市场中政府行政性垄断行为,尽管短期内地方利益得到了维护和提升,但从长远及国家层面的角度来看,地方封锁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割裂必然是得不偿失的。
综合来看,“二选一”行为强化了平台市场的边界和独立性,进而在线上交易市场中同样产生了市场封锁和市场分割的竞争效果。线上交易市场及平台市场内竞争的充分性都受到了打击,市场机制的运作也被平台惩罚和奖励措施所歪曲和取代,在平台企业的强势地位下商家难有足够的力量与之抗衡,平台企业“二选一”行为与行政限制交易行为的相似性也越来越高,对平台企业“二选一”行为的规制强度应当与之相匹配。
四、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困境
“二选一”并非法律术语,通常指向的是排他性交易行为或称限定交易行为。不仅在互联网领域,在传统行业,常见的独家经销、独家采购、独家合作等都属于排他性交易行为。商业实践中,“二选一”并非必然违法,只有在符合相关法律所规定的特定情形下,才可能受到执法机构的查处。
(一)“二选一”行为法律适用体系混乱
反垄断法一直被冠以“经济宪法”之名,①王先林:《竞争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7页。但在我国却未有“经济宪法”之实,其原因主要在于反垄断法内部尚存诸多规制争议或证明壁垒,以至于相关的行政机构或审判机关往往在执法或审理相关反垄断案件中规避《反垄断法》的适用,而选择门槛更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其他法律。在反垄断法中,“二选一”可能构成纵向垄断协议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但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纵向垄断协议时只列举了价格协议,而“二选一”是非价格协议,故规范依据不太明确,法律适用的可能性较低。
《电子商务法》所规定的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制度,能够规制“二选一”行为的第22条,②《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二条:电子商务经营者因其技术优势、用户数量、对相关行业的控制能力以及其他经营者对该电子商务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等因素而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明显与《反垄断法》中限定交易行为规制条款的逻辑一致,离不开相关市场的界定。但是,《电子商务法》的惩罚力度远远不够。③王晓晔:《论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的法律规制》,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3期。相对而言,《反垄断法》的威慑作用更强;并且《电子商务法》自颁布之日起,就因其第35条中关于“不合理条件”的模糊表达而饱受学界诟病。④曾晶:《论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法律规制的完善——以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为视角》,《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11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2021年5月施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中予以细化,将“二选一”列举为违反《电子商务法》第35条规定的具体情形之一。⑤参见2021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尽管第35条是防止平台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侵害平台内中小经营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条款,但相对优势地位与滥用行为的认定标准主观性较强,个案合理分析模式超出基层执法部门的能力范围,甚至可能架空《反垄断法》。⑥吴太轩、赵致远:《〈电子商务法〉规制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的不足与解决》,《竞争政策研究》2021年第1期。
“二选一”行为曾被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甚至被编入浙江省的指导案例中。⑦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浙江2017“红盾网剑”十大案例:金华查处“美团网”不正当竞争案》,2017年8月23日,https://china.zjol.com.cn/201708/t20170823_4857448.shtml,2023年8月20日。不可否认,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在一致性决定了在某些情况下同一行为可能会出现《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能够同时适用的情形。⑧李胜利:《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突然现状与应然选择》,《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3期。但是,在更深层次的行为范式中,两种法律在限制竞争行为的判断标准上存在着差异。反不正当竞争法倾向于竞争权益的侵害,而反垄断法则更偏好消费者福利或竞争秩序的损害。双边平台的“二选一”行为表面上看似乎是对商家的多归属权的侵害,⑨唐要家、杨越:《双边市场平台独占交易协议的反竞争效应》,《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但“二选一”行为往往附有“忠实折扣”的补偿条件。正因如此,“二选一”行为的私人执行多由市场力量较强的商家向法院提起诉讼(平台的补偿不足以弥补这些商家的未来预期利益)。换言之,“二选一”行为多数是平台和商家自愿达成的独家交易,短期来看,这种协议不仅是平台和商家之间的互惠互利,更能减少商家的交易成本,进而将优惠传递到消费者一边。但长期来看,这种互惠依赖逐渐形成平台对商家的锁定效应,商家逐渐处于劣势地位,致使商家最终不得不接受来自平台的不合理的要求,更遑论平台与商家之间的独家交易协议本身必然会限制或排挤平台的竞争对手,甚至会抬高相关市场的进入壁垒,进而对平台市场上的竞争秩序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在行为模式上,双边平台的“二选一”行为本质上是反垄断法上的限制、排除竞争的垄断行为,而非不正当竞争行为,《反垄断法》在规制“二选一”行为时的适用比《反不正当竞争法》更合适。此外,“多元法律规制方案”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二选一”行为规制问题的真正核心,这一建议看似在讨论“二选一”行为的规制选择,实则只是停留在“二选一”行为“是否该规制”的问题上。
(二)平台企业的管理行为存在滥用风险
线上交易市场是互联网与传统商贸行业相结合的产物,它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充分发挥互联网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产生了线上交易市场的新发展生态。①Evans D S.The antitrust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 markets,Yale J.on Reg.,2003,20,p.325.因此,线上平台市场既脱胎于线下地域市场,又因与互联网的结合而具有了新的属性,线下地域市场与线上平台市场的同与不同之处为传统理论的适用、创新和完善提供了事实依据和方向指引。比如在线下地域市场中,地方政府为该地域市场的管理者,与地域市场内的经营者之间为法定的纵向管理关系。地方政府具有规则制定权和管理、监督、处罚权,且权力行使有国家强制力做保障。平台企业处罚措施相比于政府要更加多元且灵活,围绕商家的市场口碑、排名、宣传等市场竞争内容,处罚虽不能像行政罚款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损失,但对商家的市场竞争力量和经营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进而影响商家的盈利能力以及未来发展。换言之,平台企业的处罚设置针对商家的市场竞争力,直接影响商家在平台市场的竞争优势。
就权力属性来看,地方政府的管理权和规则制定权源于法律的授予,根本上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由此权力的行使以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促进为导向。地方政府的权力行使会对市场造成干预,直接影响市场资源的配置,故而干预行为应当具有正当性和适当性,即在市场失灵时实施,且干预时政府部门应保持中立。在立法上,地方政府对地方市场的封锁行为也被严厉禁止,《反垄断法》在总则和第五章作了禁止性规定,政府不得滥用权力以任何形式对市场内、市场间的竞争作出不适当的限制和禁止。平台企业的市场管理权利则源于平台与大量商家、消费者单个服务合同的汇聚而产生,平台企业的市场管理地位及其权利起源于民事契约。而契约具有合意属性,因此平台企业的管理权实际上是私法属性。但是这种管理权的实际运行又会涉及平台市场内的所有参与商家和消费者,直接影响平台市场资源流动与配置,而且商家的多平台入驻和消费者的多平台消费也证成了平台企业的管理行为具有外溢性,市场机制会受到直接且严重的影响。据此,平台企业的管理行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属性,应当要求其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义务,并规制其滥用管理者地位及其管理权的行为,以避免线上交易市场成为法外之地。若从法律干预的角度出发,由于平台企业的管理行为在某些市场条件下已经跳跃出合同自由的范畴,产生了对市场竞争这一更为宏观概念的损害,《反垄断法》必须对管理权进行限制并对滥用行为加以规制。②谭袁:《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制的困境与出路》,载《法治研究》2021年第4期。《反垄断法》对垄断性企业的权利限制和义务增加就是例证,当企业发展到垄断性地位时,该企业就构成了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为不仅代表私权自由,更牵涉公共利益,故应当对其经营自由作出限制,否则社会公共利益将处于严重的侵害风险中。
(三)“二选一”行为正当抗辩适用可能
“二选一”行为是排他性交易行为在互联网行业的典型表现形式,由此适用排他性交易行为的正当理由理应同样适用于“二选一”行为。但是,平台企业不仅是服务者,还是市场的管理者,因此“二选一”行为与传统排他性交易的主体结构、行为逻辑出现差异,正当理由的适用应当对此作出回应。由于“二选一”案件主要涉及“效率抗辩”和“应对竞争抗辩”,下文主要围绕这两项抗辩展开论述。
第一,从“效率抗辩”角度分析。排他性交易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效率或非效率结果均源于市场主体之间的品牌间竞争与品牌内竞争,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产业组织经济学和竞争法律术语解释》,崔书锋、吴汉洪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高经济效率及消费者福利,这种经济效益常常针对“分配效率”或“帕累托最优”而言。②NAAG.Revisions to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torneys General Vertical Restraints Guidelines,Godfrey & Kahn S.C.,Availabe at http://www.gklaw.com/Resources/Documents/249.pdf,Last visit on 2020-01-22.而反垄断法认为,排他性交易可以通过“增加品牌间竞争”“解决套牢问题”“减少搭便车”等方式达到上述经济效益,并将此称为排他性交易促进竞争的效果和正当理由。③曲创、刘龙:《互联网平台排他性协议的竞争效应——来自电商平台的证据》,《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但是,传统排他性交易所涉及的各方主体为同种商品的上下游,而“二选一”行为中平台企业和商家则同时处于完全不同的商品竞争框架下,平台企业的限制行为并不能增强具体商品的品牌内竞争或品牌间竞争,这几项与商品相关的正面效应标准更适用于平台市场内商家的纵向限制行为。而且,互联网经济具有无形性、无地域性和边际成本递减效应的特点,双边平台的固定资本投入很小,接纳入驻商家的成本微乎其微,且一般不产生专属性投资,往往是针对平台整体而言的。即使是平台企业的宣传推广,除店铺购买广告位进行专项推广外,也基本不具有特定性。④焦海涛:《“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法分析》,《财经法学》2018年第5期。因此,“解决套牢问题”“减少搭便车”等也较难成立。此外,“二选一”行为的受益者为平台企业,商家是这场斗争中的受害者,“二选一”行为并不能实现“分配效率”“帕累托最优”,“效率抗辩”很难适用于双边平台的“二选一”行为。
第二,从“应对竞争抗辩”角度分析。在“防御型二选一”案件中,平台企业并非积极主动地实施“二选一”行为,其目的是抵御攻击型竞争策略,由此“应对竞争抗辩”存在一定的空间。但是,“应对竞争抗辩”应当受到严格限制,“应对”一词通常被界定为对已出现问题的解决,而非“削弱”或“打败”竞争对手之意,⑤[美]菲利普·阿瑞达、路易斯·卡普洛:《反垄断法精析:难点与案例》,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975页。其实施目的必须限定在对商业利益的维护,而不能借机加强或滥用市场地位。同时,手段的必要性也应被纳入“应对竞争抗辩”的适用条件中。平台企业具有市场管理者的身份,“二选一”行为会直接损害线上交易市场的竞争秩序,由此“二选一”策略应当属于平台企业的最终防御措施。在其他策略也可维护平台企业商业利益的情况下,平台企业不应直接选择严重损害市场竞争的“二选一”策略。而且,即使“二选一”策略具有必要性,平台企业的强制对象、强制内容以及处罚措施等具体内容是否合理也应加以考虑。⑥许光耀:《互联网产业中双边市场情形下支配地位滥用行为的反垄断法调整——兼评奇虎诉腾讯案》,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此外,“应对竞争抗辩”的法律效果应限定为行为动机的正当性论证,需要进一步分析“二选一”行为的实际竞争效果以确定手段的适当性,这一点在“3Q大战”案中也有印证。在“3Q大战”的上诉审理中,腾讯企业以“应对竞争”为由进行抗辩,最高法院予以认可并认为“被上诉人为排除、限制即时通信服务市场的竞争而采取‘产品不兼容’行为的动机并不明显”。⑦中国裁判文书网:《奇虎公司与腾讯公司垄断纠纷上诉案判决书》,2014年10月16日,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4fe3cab686984f8f91313ec8b921b96c,2023年8月28日访问。
五、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反垄断法规制的进路
(一)冲突化解:明确《反垄断法》优先适用
对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的规制主要有三条路径,即《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就“二选一”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国内学者也是众说纷纭,难以统一。其中,大部分竞争法学者认为反垄断法具有可适用性,只是需要采用更为严谨的反竞争分析方法,以加强反垄断法对双边平台反竞争效果的法律论证。①王先林:《平台经济领域垄断和反垄断问题的法律思考》,《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也有学者赞同《反垄断法》应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协同规制的方案,防止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尴尬局面。②卢均晓:《论类型化的不正当限制交易行为——以“二选一”行为规制为视角》,《价格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8期。至于《电子商务法》的适用选择,其主要理由在于《电子商务法》规范电子商务市场行为的特殊性及其第35条中所谓关于“二选一”行为条款的明确规定。③谢申祥、王晖兰:《互联网平台企业垄断:形式、效应与治理》,《齐鲁学刊》2023年第2期;燕卓:《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的规制路径探索》,《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更加“开放”的多元规制路径,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类学者只是对各“多元”法律路径提出细化或是借鉴“相对优势地位”等理论,却并未就“多元”法律的内在适用秩序抑或法律适用的优先问题给出应有的解决方案。④袁波:《电子商务领域“二选一”行为竞争法规制的困境及出路》,《法学》2020年第8期。本文认为,应明确以《反垄断法》为中心的规制思路,具体理由如下。
一方面,除了已经提及的“二选一”行为本质上更加契合反垄断法所调整的限制、排除竞争行为模式之外,《反垄断法》的基本目标和精神契合是另一个重要的解释。反垄断法的目标,从保护小企业的利益到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从效率唯一到消费者福利的保障,其中具体的反垄断规则和决策依旧所指不明、含混不清。⑤Averitt N W,Lande R H.Using the “consumer choice” approach to antitrust law,Antitrust Law Journal,2007,74(1),pp.75-264.但是,在这个多元价值彼此拉扯的过程中,无论是哈佛学派,还是芝加哥学派,抑或是后芝加哥学派,最为统一的共识是反垄断法是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方式之一,尽管他们对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有着不同的见解。⑥许光耀:《垄断协议的反垄断法调整》,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41页。随着经济学家和反垄断法学者对数字经济市场不断深入地了解,逐渐认识到并不再怀疑“经济干预是例外而不是原则”这一论断,即要对市场抱有一定的信心。这也决定了反垄断法及其相关政策更应该是一种“被动反应机制”,⑦[美]赫伯特·霍温坎普:《反垄断事业——原理与执行》,吴绪亮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即面对市场经济,反垄断法并不是任意干预,而是当市场竞争受到明显排除或限制时,反垄断法才能干预。正如上文双边平台的竞争分析所展现的,双边平台的“二选一”行为既有排除、限制竞争的一面,亦有正当的豁免理由的另一面。反垄断法依法审慎监管的态度更加契合双边平台下“二选一”行为的合理性分析的要求。
另一方面,《反垄断法》的规制模式较《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更科学、准确。事实上,在对双边平台“二选一”行为进行规制的过程中,《反垄断法》被规避的现象是非常常见的。以浙江省海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理的首例利用网络技术手段妨碍竞争法的案件为例,在该案的处罚书中,海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嘉兴市洞洞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采用修改商家配送范围等不当技术手段,强迫其平台商家关闭或停止在“闪电小哥”平台经营的行为,其目的在于维护市场份额,违反了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属不正当竞争行为,而非《反垄断法》中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⑧浙江省海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浙江海盐办结首例利用网络技术手段妨碍竞争案》,2018年9月27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2718588382946653,2023年8月28日访问。但是,《反垄断法》保护竞争而非竞争者,《反垄断法》规制的是垄断行为而非具有垄断势力的大企业。而且,垄断行为也并非垄断势力的充分条件,一些不具有垄断力量但是在行业中具有相当优势地位的企业也可能实施排除甚至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需要强调的是,垄断行为的实施需要一定的市场力量作为基础和支持,且行为的反竞争效果与市场力量的大小存在正向关系,由此市场结构的考察在提高执法效率和加强论证上仍显必要。从域外发达国家执法实践来看,一般都会选择《反垄断法》为核心的控制模式,因为相比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僵硬性,《反垄断法》更为科学、灵活且合理,并且垄断行为而非垄断性市场结构才是损害和威胁竞争的元凶。①张骏、张立森:《网络平台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这并非意味着《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的弃用,而是将《反垄断法》作为主要的规制模式。
(二)机制保障:重塑平台企业外在制衡力量
“二选一”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违法成本与受益的失衡。随着执法压力的加大,平台“二选一”行为变得更为隐蔽,内部协议、行为暗示、平台惯例等都可能成为平台企业对商家实施“二选一”的手段,“二选一”行为的执法查处也变得更加困难。②张一武:《论互联网平台竞争案件中优势传导理论的适用——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例研究为视角》,载《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19年第11期。加之,出于包容审慎的监管态度和促进互联网行业经济发展的考虑,执法机构的查处主要以警告、训诫、通报批评等为主,违法发现的概率与处罚措施的严厉程度均不理想,导致执法力量难以威慑大型双边平台。同时,平台企业作为平台市场的管理者,类似于线下地域市场的政府,商家的抗衡力量明显偏弱,双边平台的“二选一”行为愈加猖獗。因此,须从执法层面和商家层面两个角度重塑平台企业的外在制衡力量,以实现对平台企业“二选一”行为的常态化、稳定性规制。
在市场管理者身份下,平台企业与商家的纵向管理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即使商家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和证据,受制于平台管理权的威慑也难以抵抗,所以须从外界寻求增强商家力量的解决对策。平台对商家的锁定效应形成了平台企业对商家的支配能力,在此理论上平台企业能够在其平台市场内实现竞争的排除和限制,管理行为的外溢效果则会将反竞争影响扩展至整个市场。加之“二选一”行为将平台企业间的竞争简单化为平台市场优势的比较,平台企业的奖惩权代替了线上交易市场的市场机制,“二选一”策略取代了双边平台市场的市场机制,线上交易市场中的竞争被平台企业所扭曲,而结果的确定性加快了平台企业的市场侵蚀速度,因此,行为主义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此外,互联网行业的市场竞争具有高度综合性和复杂性,商业策略的不断迭代使垄断行为的表现形式、内在逻辑和理论基础等都发生变化,传统的类型化垄断行为规定可能难以囊括,③张晨颖、李希梁:《双重路径下排他性交易的反垄断规制》,《知识产权》2021年第4期。由此相关市场的界定以及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也都面临巨大困难,“市场份额推定”的破产、“SSNIP分析方法”的失灵等都是例证。结合政府的执法发现困境,商家的信息和证据优势可以与政府的执法力量相互补充,达到“双赢式”的力量增强。具体而言,执法机构设置专门的举报、投诉机制,接受商家的“二选一”行为举报,并做好信息保密工作,避免双边平台的报复措施对商家举报和投诉的抑制效果。对于查证属实的违法案件应当要求双边平台在停止“二选一”行为的同时恢复受强制商家的应有优势并赔偿损失,以实现商家利益损失的填补,并激励商家积极参与执法查处工作。
(三)违法判断:确立以结果为导向的推定机制
服务交易关系的纵向化与纵向市场管理关系使平台企业拥有相对于商家的天然优势,平台企业可以滥用市场力量强制商家进行选择。“二选一”真实案件表明,实施“二选一”策略的平台企业往往是行业内大型平台市场的拥有者,由此施限平台企业具有足够的锁定能力支撑其对商家的强制。因此,“二选一”行为的选择、实施与施限平台企业的优势市场力量具有较强的逻辑印证关系。一般而言,惩罚性的“二选一”策略意味着更强势的市场力量以及更严重的竞争限制效果,而奖励性的“二选一”策略则可能相对较弱。针对新进入者的“二选一”策略意味着市场封锁和对潜在竞争者的抑制,由此对市场竞争的排除和限制效果相对更为严重。
针对“二选一”行为的发掘,结果推定机制能显著提高发掘效率并降低发现难度。从理性经济人的立场出发,多平台市场同时入驻意味着更多的渠道、更强的市场力量和更高的盈利能力,除非某一平台市场内店铺的经营成本与收入难以平衡且竞争优势不足,否则商家不会选择自我限制和自我削弱并放弃任一平台市场。因此,当某一平台市场发生异常的商家退出情况时,“二选一”行为的外在强制是大概率存在的,而受益平台企业往往是行为的实施者,即平台市场内不正常的商家退出情况能够逻辑地推定出“二选一”行为的客观存在以及实施主体。在具体判断中,应关注商家撤离的规模、数量和时间点等因素,以综合评价撤离是否异常。在此基础上,应当考察商家撤离的原因以及被弃平台市场的经营和管理变化,其中前者直接反映“二选一”行为是否客观存在及具体信息和证据,而后者则可论证被弃平台企业是否存在自身原因。对被弃平台市场的考察应当主要局限在平台企业的经营管理策略以及平台市场的资源聚集能力是否有重大变化,并着重分析该变化与异常的商家撤离情况是否具有紧密的因果关系,其他平台企业及平台市场的变化一般不在考虑之列。
无论是对“二选一”行为的市场支配地位推定还是对“二选一”结果的滥用行为推定都只是暂时性的推定,是出于提高执法效率和加强平台企业自我约束所提的对策,仍应给予涉案平台企业以充分的权力和机会进行反驳和自我辩护。两类推定机制仅系进行执法调查和分析的一种论证方法,本身并不能作为“二选一”行为认定的直接证据,其适用也应当保持审慎,不应滥用或过度推导,对“二选一”行为的查处最终还需落实到具体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证之中。
六、余 论
传统排他性交易的规制理论认为,持续时间构成反垄断干预的重要条件,在持续时间较短的情况下,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恢复市场竞争所受到的损害。但是,平台与市场的重合使得“二选一”行为的作用强度和速度都远超传统的排他性交易行为。平台企业的惩罚和奖励措施对商家而言不仅仅是交易机会和风险的变化,更是市场机制下精准的市场优势打击行为。尽管对于激烈、严重的“二选一”案件,政府会及时干预并平息限制行为,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二选一”行为本身的反竞争性质和潜在竞争威胁。从规制的行为主义和实质主义出发,持续时间的长短也不宜作为阻碍反垄断法规制的重要因素,否则只会掩盖行为本身的严重性质。另外,平台企业的“二选一”行为还具有信号传递效应,即使时间持续不长或间断性较强,也能起到较强的持续性和整体性的引导效果。信号传递效应起初是用于研究和分析政府奖惩行为对社会资源的流动和企业行为产生的引导效果,即市场资源的流动和企业的行为会主动迎合政府的政策要求。①Bergh D D,Connelly B L,Ketchen Jr D J,et al.Signalling theory and equilibrium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An assessment and a research agenda,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4,51(8),pp.1334-1360.平台企业与政府在市场中的地位存在较高的相似性,其惩罚和奖励行为在平台市场内亦具有类似于政府奖惩的信号传递效果,即平台企业向商家传递了“选择有奖,拒绝会罚”的信号,进而引导商家迎合平台企业的要求并进行选择和放弃。最后,持续时间的要求会产生错误的诱导,即时间短则可避免严重惩罚,这实际上为“二选一”策略制造了“避风港”,于执法威慑有害无益。因此,持续时间的形式化特点只会阻碍“二选一”行为的准确分析,不宜将其作为《反垄断法》适用的阻却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