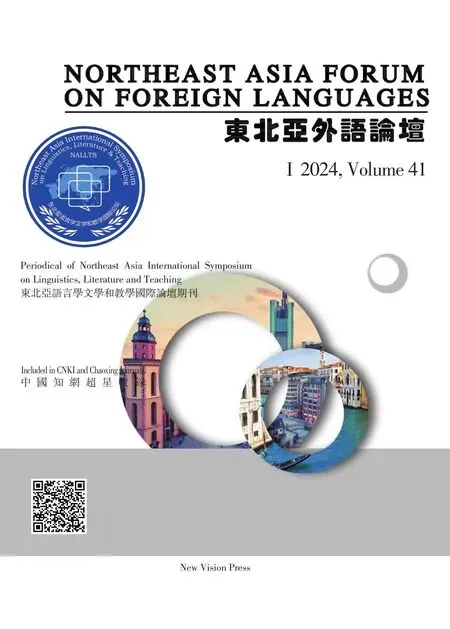论汤亭亭《女勇士》的“后现代”叙事特征
王 楠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大 连 116100 中 国
一、引言
众所周知,美国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群体组成的移民国家,每一个移民族群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渊源。在此背景下,多民族性成为美国文学发展的必然的、显著的特征之一。美国亚裔文学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文坛上逐渐展露锋芒,而华裔文学可以说是亚裔文学中的中流砥柱,发挥着先锋队的重要作用。本文所讨论作品《女勇士》的作者汤亭亭是美国华裔作家中的翘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华裔文学近年来在美国的声誉日隆,与汤亭亭取得的文学成就密不可分。
汤亭亭的父母是中国较早的一批的海外移民,汤父在1925年就跋山涉水地去到美国,其母亲于1939年到达美国与丈夫团聚。对于早期前往美国谋生的华人移民来说,美国社会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绝大部分华人只能依靠美国白人不愿从事的工作求得生存。在此背景下,尽管汤父汤母具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也只能依靠经营一家洗衣店来养家糊口。因此,汤亭亭在童年时期并没有一个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与之相反的是,她的精神生活十分地丰裕。汤亭亭的父亲是一个具有一定学识的传统知识分子,其母亲也总是给孩子们讲述中国各类传统故事,这些都为汤亭亭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美国华裔文学的扛鼎之作《女勇士》的出版不仅使作者汤亭亭饮誉美国文坛同时也使华裔文学在美国文坛大放异彩。《女勇士》全书分为“无名女子”“白虎山学道”“乡村医生”“西宫门外”以及“羌笛野曲”五个章节。作品中充溢着浓厚的女性意识和异乎寻常的中国内容,吸引了大量国内外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除此之外,《女勇士》在叙事方面也同样出彩,该作品跨越不同的文学体裁,整体拼贴式构成,出现了不可靠的人物叙述者,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违规权限,这些叙事上呈现出的独特表征带有浓厚的“后现代”化色彩。
二、文学不同类别和体裁的消解
《女勇士》于1976年一经出版便在美国文坛掀起轩然大波,但随着作品名声和关注度的不断攀升,众多评论家对其体裁判定的争论也水涨船高。这场关于《女勇士》的体裁之争主要分为两大营垒:自传和小说。
自传体裁阵营的支持者认为,《女勇士》着重描述了作者母亲一方的亲眷,作者本人也曾表示其素材来源于其自身的亲身经历和家庭历史,这使得文本内容具备了真实度与可信度。在此基础上,文本又主要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围绕“我”的成长故事展开,读者习惯上就会将作品叙述者“我”等同于作者汤亭亭,从而将《女勇士》划分为自传体裁作品。另外,作品副标题“一个生活在‘鬼’中间的女孩的童年回忆”中的关键词“回忆”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但同时,支持者们也承认,虽然《女勇士》通常被视为自传,但它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生平故事(汤亭亭,1998: 8)。
与此同时,小说体裁阵营则对其自传体裁的判定持强烈否定态度,并提出否定依据。首先,传记区别于其他体裁的根本特征就是其真实性,自传作为传记的形式之一,也就不能脱离这一特点,虽然其中会夹杂主观的一些想法或情绪,但客观上的相关事实应该被翔实地记录与呈现。而在《女勇士》中,作者所使用的汉语词汇、文学典故以及历史表述与事实不符,这违背了传记体裁的根本特点;其次,该部作品中有较大篇幅的虚构部分,并且即便是某些真实故事,其真实度与可信度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多重叙述所消磨。因而不应被判定为自传体裁,更应归于小说体裁。
自传体裁阵营看其“实”,小说体裁阵营抓其“虚”,“虚实结合的独特叙事特征使《女勇士》游离于已知的文学类别与体裁范围之外。汤亭亭的编辑克诺夫曾表示“(《女勇士》)可以被划为任何体裁”(郭海霞,2018: 113),但也从侧面证明了《女勇士》不能被划归为任何体裁。
在此处引入关于汤亭亭《女勇士》的体裁之争,目的不在于对该争论得出什么结论,而是在于借助该争论强调与突出《女勇士》这部作品在体裁方面的跨越性和破碎性。虚实结合的独特叙事特征使得《女勇士》这部作品具有了不确定性和非同一性,消解了不同文学类别与体裁,具有浓厚的后现代意味。
三、文本的拼贴
正如前文引言中所提,《女勇士》全书分为“无名女子”“白虎山学道”“乡村医生”“西宫门外”以及“羌笛野曲”五个章节。开篇的“无名女子”以“我”的姑妈为主人公,讲述了发生在广东20世纪20年代的故事;“白虎山学道”这一章节改写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中国传统故事,该章节的书写具有极大的时空跳跃性;“乡村医生”以母亲勇兰为主人公,讲述了发生在广东抗战时期的故事;“西宫门外”以姨妈月兰为主人公,讲述了其赴美寻夫的悲惨遭遇;最后“羌笛野曲”又围绕童年时期的“我”的成长经历展开。
基于上述,读者与研究者可以发现,从全书的整体构成来看,连贯主人公缺失,章节故事内容独立,章节与章节之间的关联性极弱,而独立性极强。而这打破全书整体性的破碎感与松散感恰恰映照了典型的拼贴手法,《女勇士》全景就是由五个“拼贴画”拼贴而成。从全书的章节布局来看,拼贴这一叙事特征消解了作品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实现了主人公的去中心化,使得整部作品具有了后现代印记。
《女勇士》全书是由五个章节拼贴而成,而其中的“白虎山学道”这一章节则可以说是“拼贴画”中的“拼贴画”。
浓厚的中国气息毫无疑问是使《女勇士》享誉美国文坛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对于“白虎山学道”这一章节,中国读者会产生既陌生又熟悉的全新感受,而这得益于作者汤亭亭对该部分“拼贴”式的创作。该章节的开篇写道,“我”七岁时跟踪着着一只鸟进入群山,在进山过程中,“荆棘撕破了我的鞋子,乱石割破了我的脚和指头,但是我仍然坚持爬山”(汤亭亭,1998:17),在这里读者不难察觉到,汤亭亭实际上复制西方魔幻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中主人公爱丽丝跟着一只兔子进入仙境的情节。接着,“我”进入山中之后遇到一对老夫妇,跟随他们苦练技艺,对于这一部分,作者则参考了唐朝巾帼英雄樊梨花跟随黎山老母习艺的传说故事。习艺的过程中,老夫妇将“我”送至白虎山历练,当“我”在历练过程中面临弹尽粮绝的生死关头时,却碰到兔子自己跳进火堆里,为“我”提供了饱腹之食,这一情节的安排则是汤亭亭对兔子舍身待客的印度神话故事的复制。习艺数载之后,“我”返回家乡,却遇上家人被迫征丁,于是“我”决定替父从军,临行前父母在“我”的背上刺上敌人的罪行、“我”的姓名和住址,在这里,作者则是拼贴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花木兰替父从军和岳母刺字两个中国传统故事。因此,在“白虎山学道”这一章节里,汤亭亭对已有材料进行加工,各种非原创材料不仅拼贴出“我”的独特女将军形象也拼贴出一个令读者既熟悉与陌生的独特文本。对已有材料进行复制与拼贴突破了其意义的确定性,使传统文学中“可读性”文本向后现代“可写性”文本转变。
四、不可靠的人物叙述者的出现
美国文学理论家詹姆斯·费伦曾提出“同故事叙述”概念,用来描述故事叙述者以故事中人物的身份出现进行叙述的文本现象。也就是说,在“同故事叙述”中,人物叙述者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同时也是故事的参与者,“他既承担了讲述故事的叙述功能,又具备了参与角色的人物功能,由于他的多重身份从而兼备了多重功能,使得人物叙述者在可靠与不可靠之间摇摆”(李卉,2019:27)。在《女勇士》的“羌笛野曲”这一章节中,主要讲述了“我”童年时期发生的一些故事。显而易见地,在这段故事中,“我”既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的主人公,“我”的多重身份兼备多重功能,这大大减弱了“我”作为可靠叙述者的可信度。
在这里,需要指明的是,在该章节故事中,虽然故事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但“我”并不是作者汤亭亭。汤亭亭曾经表示“或许在我的人生中,我的很多感受和文中的小女孩的感受是一致的,但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铁定不是这么想的。”因此,我们可以将本章节中的“我”理解为作者笔下的人物。
故事中提到,“我”幼年上学时总是保持沉默,但后来发现有一个女孩比“我”还要沉默,“我”想尽一切办法想让她开口说话,可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在“我”的讲述中,那个比“我”还沉默的女孩最后的结局是“她姐姐当了打字员,没有嫁人。她们和父母住在一起。除了看电影,她不必离开家门”(汤亭亭,1998: 166)。通过“我”的讲述,读者可以接收到“这个女孩因为沉默不肯发声而最终与社会剥离”这一因果逻辑信息。
“在作者笔下的人物叙述者的某些性格特点的原因,他的叙述会带有一定的思想倾向性,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样的人物叙述者是不可靠的”(李卉,2019: 28)。根据“羌笛野曲”这一章节的文本内容,“我”是一个美国华裔女孩。“华裔”“女孩”的双重边缘身份毫无疑问地会给“我”带来痛苦和压抑,这样的压迫激起“我”的反抗意识,“我”要向外界发出“我”的声音,争取“我”的权利。因此,在“我”具有这样思想倾向性的情况下,“我”作为可靠叙述者的身份就会存疑。
首先,比“我”沉默的女孩真的存在吗?这个女孩会不会是“我”借由发声反抗的工具,“我”通过对女孩的斥责从而实现“我”表达意愿的目的;其次,如果“我”叙述故事中的女孩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我”是否如实地讲述了她的经历与结局,她是真的因沉默而无法在社会立足还是“我”为了表达“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反抗决心而改设了她的人生轨迹。
因此,在这一章节故事中,“我”作为一个同故事叙述中的人物叙述者显然不是一个可靠的人物叙述者。
五、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权限违规
当文本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时,传统上或者说习惯上,我们会将叙述者“我”当成是故事的主角,文本叙述围绕“我”而展开,“我”的经历、体验、感受和思考是文本的核心内容。偶尔地,叙述者“我”在故事中扮演旁观者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不是主要人物,但是“我”仍然在文本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无论是上述的一般情况还是偶尔情况,传统文本中的第一人称叙事都是有限视角。而《女勇士》中却对第一人称叙述者进行了多样化设置,下面以《女勇士》中“无名女子”为例,进行分析。
在汤亭亭的《女勇士》第一章节“无名女子”中,以第一人称“我”叙述进行叙述,然而,我们可以注意到,文本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打破了传统的边界,反现实地对未参与、未经历甚至未在场的人与事物进行分析与叙述,将“我”之外的他者主体“无名姑姑”的内心世界展示给读者。
德国学者鲁迪格·海因在其2008年发表的论文《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中对模仿认识论的违背》中,就对这种第一人称叙事出现的新情况进行了集中的探讨。海因借引了认知叙事学家曼弗雷德·雅恩提出的“多叙”概念。雅恩表示“多叙”指的是“一种由于讲得太多而引起的违规:叙述者行使了一种他/她本不该具备的能力;典型的情形是,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或一个历史学家)叙述他人所思,或叙述那些他/她并不在现场的事件(对作者权限的违规行使)”(王源,2020:51)。
在“无名女子”中,母亲平铺直叙地讲述了无名姑姑被指通奸,最终抱着刚出生的婴孩跳井自杀的故事。母亲在讲述的过程中,没有掺杂主观意识也没有细节的表述,“我妈妈已经将该说的说完了。除非的确有必要,她是不会再多说一个字的。这是她的生活原则”(汤亭亭,1998: 4)。“自从我听说过这个故事以来,我从未进一步打听过细节,也没有提过姑姑的名字”(汤亭亭,1998:14)。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是绝没有可能获取更多的关于无名姑姑的信息。然而在文本中,“我”的视界却突破了客观现实的时空界限而回溯到无名姑姑生活的时空,通过违规权限操作将无名姑姑的言谈举止、经历遭遇、思想意识以及心理体验呈现出来,例如,“我的姑姑不可能是独身的浪漫主义者,不顾一切地追求性生活”(汤亭亭,1998:5)。“为了使她保持恋爱时的美貌,她经常对着镜子梳妆打扮”(汤亭亭,1998:7)“我的姑姑对着镜子,把自己的头发梳成别具一格的发髻”(汤亭亭,1998:7)。“‘他们伤我太厉害了。’她想,‘这是心灵的创伤,它会将我折磨死的’”(汤亭亭,1998:12)。在文本中,诸如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在此不一一举证。
读者不难发现,除了开头母亲的讲述部分,“无名姑姑”这一章节文本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在第一人称叙述“我”突破传统的视野限制情况下,依靠第一人称多叙而完成的。
六、结语
汤亭亭的《女勇士》作为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一本书,从出版到如今,不仅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群体还引起了美国多个学术领域的关注与研究。除了其内容上的精彩繁复,文本叙述上也突破了传统,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叙事特征。虚实结合的叙事安排消解了文学不同种类和体裁,拼贴画式的文本构成否定了传统文学文本的连贯性与原创性,不可靠叙述者的出现和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违规权限更是对传统文本飞跃式的革新与冲破。而这些特征使得《女勇士》该部作品在叙述上带有明显的“后现代”化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