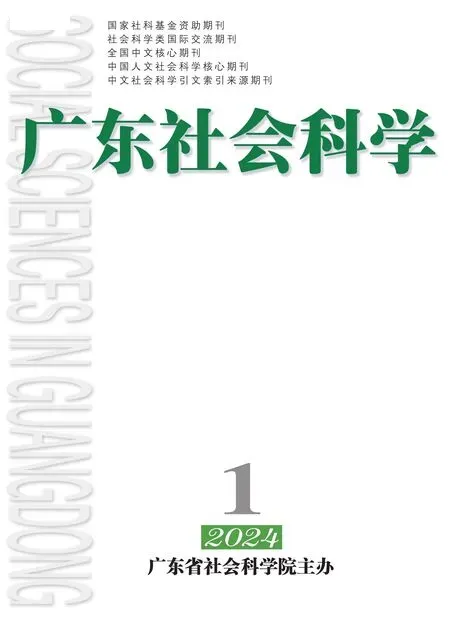1930年代初期中国致公团体内的派别及政治趋向*
石 瑶
致公团体内不同政治势力分野是基于其组织内部独特的党、堂关系而形成的。1925年“致公党一大”决定创建的中国致公党,未能真正实现对致公堂的统领,致公党实际上处于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组织格局。①《中国致公党简史》编辑委员会:《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年,第9页。因此,1931年致公党总理陈炯明试图通过召开“致公党二大”重整政党,解决党堂不分的问题。“致公党二大”召开前夕,陈炯明召集各方致公团体召开了“五洲致公团体恳亲大会”,但是拥护致公党的一方和支持保存致公堂的一方未能达成一致,最终采取折中方案——“致公党、致公堂双方根据组党、存堂原则任听自由结合组织”。这样,支持致公党的一方召开“致公党二大”,在香港重建了“中国致公党”,陈炯明任总理,制定规章,登记党员,欲组成现代意义的政党①陈昌福:《中国致公党建党史上的里程碑——中国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陈昌福认为,在香港的中国致公党通过“二大”实现了由会党向政党的转型,这一观点与目前中国致公党官方书写的党史相一致。然而,对香港的中国致公党作为政党成熟程度的评估,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在香港的致公组织,其“政党”的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或仅为海外致公团体试图在国内登记注册、进而向国内发展的办事机构。笔者认为,无论在香港的致公党性质如何,都是致公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当时的活动展示了致公团体的政治活动与特点。此外,香港的致公党为当时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所关注,也是1947年中国致公党在香港重建组织、实现向新民主主义政党转变时所依托的组织基础,故对其研究是必要的。,在香港及东南亚活动;支持存堂的一方,成立“中国致公堂总干部”作为组党机关,继续谋划组党,负责美东纽约各埠的司徒美堂担任总监督②《中国致公堂总干部报告五洲洪门恳亲大会书》,由王起鹍提供,现存于古巴致公团体档案室。,以纽约为中心在美洲活动。此后,致公组织内的各支主要势力互相联络、互不统属,各自依据不同区域开展活动。
虽然组党、存堂双方因政党名称、组织形式等问题未能就组织中国致公党达成一致,但是陈炯明在双方均有着较强的影响力,他能够召集各方洪门大佬和致公团体共赴香港参加“五洲致公团体恳亲大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另外,主张“存堂”的一方也曾表示只要可以保存致公堂,愿意选陈炯明为总理,并专门列举了保存致公堂对陈炯明的好处,可见其对陈炯明的重视。③同上。因此,1933年陈炯明的逝世,对致公组织内的不同派别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香港的致公党而言,他们失去一位可以实际领导政党的总理;偏隅海外的美洲致公堂则缺乏一位在华侨华人中具有广泛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代理人。
学界现有关于1930年代初期致公团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司徒美堂为代表的美洲洪门致公堂对国内局部抗战的声援,而对致公团体作为政治组织自身的政治活动、政治趋向鲜有关注。④任贵祥:《司徒美堂与抗日战争》,《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陈昌福:《抗日战争与中国致公党》,《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 年第5 期;潮龙起:《从社会冲突看近代美国华侨堂会的兴衰(1848—1949)》,《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0期。对这一问题关注和介入的不足,是现有致公党史研究之薄弱所在,也使对抗日战争后期致公党恢复组织、重组政党的研究缺乏相应的根基,难以厘清致公党在香港成为民主党派的历史脉络,故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十分必要。本文以台湾“国史馆”档案资料为基础,重点关注1930年代初期致公团体内不同派别的政治趋向,以期对民国年间的政党政治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相互借势:美洲致公堂欲举“抗日反蒋”的蔡廷锴为总理
致公团体在海外的活动情况为中国国民党所追踪关注。1935年蒋介石的亲信香港华民署刘伯端在向蒋介石报告致公组织的情况时,做出了如下分析:“海外洪门自致公党与致公堂分家后,致公党举陈竞存为总理,陈死后尚无继者;致公堂向无首领。”⑤《刘伯端等电蒋中正闻蔡廷锴得陈铭枢同意回函海外洪门致公堂愿任该堂总理等文电日报表等二则》(1935年5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451-071。这一陈述一分为二地关照到党、堂之分途,基本符合致公团体实际组织状况。
相较于香港致公党由中央干事会总理党务,美洲洪门致公堂的情况相对更为复杂。1931年中国致公党总部迁至香港后,旧金山五洲洪门致公总堂支持组党的决定,以中国致公党驻旧金山地方总部名义活动,并尊陈炯明为总理。而纽约的堂口势力崛起,逐渐脱离了旧金山五洲洪门致公总堂,自称洪门致公总堂,并在美东地区设立多个分堂。①王起鹍主编:《海外洪门与中国致公党》,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7年,第65页。纽约的洪门致公总堂以司徒美堂为实际领导人,此时的司徒美堂虽然在堂号和华侨华人中颇具影响力,但尚不具备统领所有堂口的能力,加之常年在美国活动,在国内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受到限制。此时的美洲洪门致公堂,寄希望于寻找一位在华侨华人中具有高度认同感,在国内也同样具有声望的政治名人。这样,“福建事变”中“抗日反蒋”,又有洪门背景的广东军人蔡廷锴便进入美洲洪门致公堂的视野。
1935年5月17日,刘伯端向蒋介石汇报道:蔡廷锴在经过檀香山时,致公堂欲举蔡廷锴为总理,蔡廷锴答复回香港考虑后再做决定。后蔡廷锴经陈铭枢同意,函复美洲洪门致公堂允其所请。②《刘伯端等电蒋中正闻蔡廷锴得陈铭枢同意回函海外洪门致公堂愿任该堂总理等文电日报表等二则》(1935年5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451-071。笔者注意到,早在1934年5月16日,具有香港中国致公党身份的陈其尤便向蒋介石报告:“美洲堂号一派萧少等初欲改拥吴子玉(吴佩孚,笔者注),不果,现原拉拢蔡廷锴。”③《陈其尤电蒋中正所谓致公堂阴谋可能系致公党分子罗觉庵暗设机关》(1934年5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435-130。另外,1935年4月26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接到电报说:“香港大众报,经费本甚支绌,向赖陈铭枢等津贴小款,维持现状,闻蔡廷锴回港后,忽拨给四五万元,嘱该报自购置印刷机件,以图发展。查此款乃蔡在美时极力勾结该处洪门党人得其捐助者。故该报近甚为致公堂卖力。”④《李尚铭电杨永泰香港大众报近来受蔡廷锴引介美洲洪门党捐助甚为致公堂卖力》(1935年4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221-076。三天后,刘伯端也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叙述了相同的情况,即蔡廷锴与美洲洪门致公堂联合,继而用所得捐款拨发香港大众报。⑤《刘伯端电蒋中正香港大众报得蔡廷锴拔美洪门捐款故近甚为致公堂效力等文电日报表等二则》(1935年4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450-152。故,虽然并未找到蔡廷锴就任美洲洪门致公堂总理的直接材料,但是美洲洪门致公堂想要支持并拥立蔡廷锴这一推测,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美洲洪门致公堂对蔡廷锴的争取,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美洲洪门致公堂当时的生存境遇与政治态度。蔡廷锴是“抗日反蒋”的代表性人物,由此显示出美洲致公堂及其代表的华侨华人“抗日反蒋”之迫切。华侨华人向来深切关注国内政治,清末即支持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在建立民国及民初反对军阀的斗争中,亦给予广泛的人力物力支持。⑥陈红民:《“新国民党”在海外的活动:1932—1936年》,《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对于在他们支持下建立的中华民国,华侨华人倍感珍惜,并寄希望于祖国国力的发展能为其提供后盾,帮助他们摆脱被歧视与压迫的命运,增强在海外的社会地位。⑦潮龙起:《抗日战争专题研究:美洲华侨与抗日战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28页。华侨华人客居他乡的惨痛经历,使他们更能感受到其在侨居国的社会际遇是祖国命运的一种投射,救国就是救自己。⑧潮龙起:《抗日战争专题研究:美洲华侨与抗日战争》,第230页。因此,“九一八事变”后,抗日迅速成为华侨华人社会中的普遍呼声。
美洲洪门致公堂作为美洲侨社中最有影响力的组织,主张奋起抵抗日本侵略,甚至在共同抗战的决心下结束了延续三十余年的堂斗。美国华侨华人社会男女比例曾长期严重失调,这一失衡的社会结构导致致公堂吸收了大批单身华侨男性,从事烟馆、赌馆、妓院等非法行业。致公堂在从事这些偏业的过程中,形成武装力量,不同堂口间经常因利益纠纷发生暴力冲突,堂斗成为致公堂等华侨堂会当时的主要特征。①潮龙起:《试析早期美国华侨的“堂斗”》,《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指出,“我们各堂的头领好像被人玩弄的蟋蟀,只要小竹丝一挑动,两只蟋蟀就打到你死我活”。②司徒美堂:《旅居美国七十年》,见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司徒美堂》,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23页。“九一八事变”后,美洲各地堂会意识到国难深重,以民族利益为重,停止内斗,致公堂也在一致抗日的共同意志下转变了工作重心。③潮龙起:《移民、秩序与权势:美国华侨堂会史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61页。司徒美堂回忆,“大家团结抗日,枪口一致对外,各堂才平安相处,消灭了被人挑拨起的争执”。④司徒美堂:《旅居美国七十年》,见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司徒美堂》,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26页。据麦礼谦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1933年协胜堂与安良堂发生的堂斗,是美国最后一次堂斗。⑤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第43页。
蔡廷锴在淞沪抗战中的坚决守土、顽强抵抗,使广大华侨一洗“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妥协退让的耻辱,备受鼓舞。1932年1月28日,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蔡廷锴作为十九路军军长带领十九路军奋起抵抗,1月29日蔡廷锴等发表抗日通电:“为卫国守土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国民国军人之人格。”⑥魏宏运:《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4页。司徒美堂迅速予以回应,2月初在安良堂,即纽约洪门致公堂口主持了干事会,做出三项决定:一、以致公党名义呼吁支持坚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二、迅速成立洪门筹饷机构,发动募捐;三、组织华侨青年参加联合救国运动。⑦陈昌福:《抗日战争与中国致公党》,《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1932年夏天,淞沪抗战结束后,司徒美堂曾专程回国,到上海凭吊了战场,并调查致公堂在海外募捐到的钱款在十九路军的使用情况。司徒美堂慨叹“我们捐给十九路军的钱,十之八九被蒋介石吞没了”,对“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态度也表示气愤。⑧司徒美堂:《回忆当年,欢呼今朝》(1954年5月),见中国致公党中央研究室编:《司徒美堂》,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第120页。此外,也有人认为司徒美堂在此期间会见了蔡廷锴并在军部住了几天⑨张兴汉:《司徒美堂先生在抗战中》,见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司徒美堂》,第222页。,但司徒美堂本人并没有相关回忆,笔者也尚未找到相关的档案、报刊资料验证这一说法。
“福建事变”得到美洲洪门致公堂的迅速声援。淞沪抗战结束后,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在福建“剿共”,1933年11月,蔡廷锴作为十九路军将领,同陈铭枢、蒋光鼐联合中国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联合发动“福建事变”,决定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3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由黄琪翔报告了会议理由,后蔡廷锴作为代表之一发表了反对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人民革命政府的演讲。⑩薛谋成、郑全备选编:《“福建事变”资料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8页。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成立后,确定了完备的政府组织大纲,并发表了《政府成立宣言》,宣布以最大诚意完成人民革命政府之使命。①薛谋成、郑全备选编:《“福建事变”资料选编》,第84页。“福建事变”得到美洲洪门致公堂的迅速声援。1933年12月23日,司徒美堂所负责的洪门致公总堂以“中国致公总部”的名义发表通电拥护“福建事变”中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一方面表达对新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英勇抗日的支持,另一方面表达对蒋介石统治的不满,表示“敝团愿竭棉力,效命新邦,并偕海外华侨,悉候驱策,临电无任屏营待命之至。”②《中同致公总部通电拥护人民政府》(1933年12月23日),薛谋成、郑全备选编:《“福建事变”资料选编》,第183页。1934年1月11日,加拿大致公堂也表示,人民革命政府“对内打倒媚日卖国之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对外则贯彻抗日救国,收复失土之初衷”,与致公堂的主张相一致。③《全加致公堂电贺政府》(1933年12月23日),薛谋成、郑全备选编:《“福建事变”资料选编》,第183页。同时,加拿大致公堂通电蒋介石,痛斥其“因阋墙之争,以爱国民众所购之飞机,供一党屠杀不辜之用”。④《致公堂致林汪蒋电,为蒋机炸闽而发》,《工商晚报》1934年1月5日,第2版。
淞沪抗战和“福建事变”使蔡廷锴在华侨华人中名声大噪,亦得到美洲洪门致公堂的特别推崇。一方面,蔡廷锴举起“抗日反蒋”的义旗,特别符合以致公堂为代表的华侨华人对国内政治的主张,双方理念相同、目标契合;另一方面,致公堂对蔡廷锴的赞同也与身份认同相关。从地缘因素看,蔡廷锴是广东人,早年即投身粤军。而广东人在当时的华侨华人中占相当数量,在1914至1927年间,广东的侨汇一直稳定占全国侨汇的80%左右。⑤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1912—1949)》,第380页,台北“国史馆”1997年印行,转引自陈红民:《“新国民党”在海外的活动:1932—1936年》,《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致公堂领导人司徒美堂为广东开平人,堂口成员也多为广东籍。致公堂及华侨华人视蔡廷锴为“广东人的骄傲”。⑥H.Mark Lai,Chi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 Politics,Champaig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0,p.22.此外,蔡廷锴具有洪门背景,“原为洪门三合会之头目”。⑦《讨平闽变纪初稿(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馆藏号:787-1279。有人认为,蔡廷锴在军队中利用帮规之精神带领军队,评价其“如家人父子,如帮中师弟,故能共患难、同生死也”。⑧《讨平闽变纪初稿(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馆藏号:787-1279。蔡的洪门背景使他易于为致公堂中人所认同、信任。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蔡廷锴离港周游世界、行至美国,受到华侨华人的特别欢迎,蔡廷锴本人也将致谢“海外侨胞热烈赞助之盛意”视作出国的重要动机。⑨蔡廷锴著:《海外印象记》,香港:东雅印务有限公司,1935年,第1页。可以说,对于主要在国内从事政治活动的蔡廷锴而言,海外华侨华人是一种特殊而稀缺的资源,除了向淞沪抗战提供过人力物力的支持外,他们还将对蔡廷锴的“抗日反蒋”活动提供宣传价值和其他支持。1934年8月26日,蔡廷锴在纽约登岸时,“侨胞在码头欢迎者达三千余人,各西报访员及各西人男女之到场参观者亦千数百人,汽车三百余辆”。⑩蔡廷锴著:《海外印象记》,第28、30页。后全埠侨众游行欢迎,“所经各处,中西人士鼓掌欢迎”“舞瑞狮助兴,中西音乐,沿途吹奏,响遏行云”。⑪蔡廷锴著:《蔡廷锴自传》,香港:自由旬刊社,1946年,第414页。司徒美堂也回忆到,蔡廷锴是“‘有史以来’中国官员在美国最受华侨欢迎的一人,欢迎场面也是最为壮观的。”①司徒美堂:《旅居美国七十年》(1950年12月),见中国致公党中央研究室编:《司徒美堂》,第61页。在8月30日纽约全体华侨举办的公宴大会上,蔡廷锴回顾十九路军“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之精神,细数南京国民政府“以人民集资购买之飞机轰炸福州、漳州、泉州各地良民”之罪行,将华侨华人本已高涨的“抗日反蒋”情绪进一步调动起来。
美洲洪门致公堂为洪门中人能产生这样一位“民族英雄”而骄傲,积极地为蔡廷锴的走访造势并予以支持。蔡廷锴到达美国前,司徒美堂即接到陈铭枢自香港来电:“蔡欲来美,能否发动侨团保护,免受敌人暗害。”司徒美堂复电表示热烈欢迎,并承诺保证蔡廷锴的安全。②同上。蔡访美期间,致公堂将其全楼均饰有五色国徽、堂徽及美旗,并挂以五色电灯,在楼前悬挂写有“欢迎民族英雄蔡廷锴将军”的白布和“会集洪门俊杰,欢迎民族英雄”的一联金字。③《纽约侨胞欢迎蔡廷锴之热烈》,《世界日报》1934 年8 月31 日,转引自潮龙起:《抗日战争专题研究:美洲华侨与抗日战争》,第139页。司徒美堂陪蔡廷锴遍访了美国十余座城市,为其提供陪同保护,也接洽各地致公堂为蔡的到访、演讲提供场所等支持。④蔡廷锴著:《蔡廷锴自传》,第430页。蔡廷锴行至芝加哥时,当地致公堂借万国酒楼举行欢迎宴,该堂主席陈泽霖赠予蔡廷锴金质徽章,司徒美堂则借此次集会详细宣讲了洪门历史。⑤同上。
蔡廷锴的“抗日救国”活动借助致公堂的力量得以在华侨华人社会中得到更广泛、更声势浩大的宣传与支援,而他本人所具备的声望和影响力也是致公堂实现自身政治目标所特别需求的。“中国致公堂总干部”虽然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政党,但是也已于1931年确定了具有政党性质的宗旨、章程。“中国致公堂总干部”的宗旨明确写道:“永护共和反对党治、安定社会反对共产。”而其章程也明确规定:“重组各派联合政府”。⑥《中国致公堂总干部报告五洲洪门恳亲大会书》,由王起鹍提供,现存于古巴致公团体档案室。上述内容,反应了致公堂总干部当时的政治态度,即既反对中国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又对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持反对的态度。其政治主张深受美国政党制度的影响,将“联合各派,重组联合政府”作为政治目标。虽然此时致公堂总干部所提出的“联合政府”与抗战胜利前夕中共所论述的“联合政府”尚不是一种概念,但其反映出致公堂总干部建立政党从而参与国内政治生活的追求。蔡廷锴等建立的人民革命政府是反蒋势力独立建立政权的成功尝试,这或许使美洲致公堂燃起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希望。而蔡廷锴当选为人民革命政府十一名中央委员之一,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⑦薛谋成、郑全备选编:《“福建事变”资料选编》,第69页。蔡廷锴作为国民党内的地方实力派,所具备的声望和影响力是美洲致公堂领导人自身所不具备的。
总的来说,蔡廷锴与美洲洪门致公堂建立了一种相互借势的关系,蔡廷锴借助华侨华人得到人力物力、宣传等方面援助,致公堂则希望借蔡廷锴这位“代言人”实现其对国内政治的主张。美洲洪门致公堂支持并拥立蔡廷锴为其总理,主要是因为蔡廷锴在“抗日反蒋”上的积极作为,特别符合华侨华人的政治意愿,与美洲洪门致公堂的政治理念一拍即合。而蔡廷锴在国内政治、军事上的影响力和声望又是致公堂所特别看重与缺乏的,他们亟需寻找一位在国内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作为他们参与国内政治的旗帜。另外,蔡廷锴广东省籍与洪门人士的身份因素,使他成为美洲洪门致公堂所特别争取、联络的人选。
二、投石问路:香港中国致公党内的“拥蒋”倾向
香港独特的政治生态,见证了不同政治力量的盘踞、生存与较量,亦是中国致公党活动的重要场域。1925年“致公党一大”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中国致公党,选举陈炯明为总理。1925年12月陈炯明退居香港,谋划制定致公党党纲概要及推进党务,半年间陆续发展登记党员约十万余人,并派员指导粤港澳及东南亚各支部的工作。①陈定炎编:《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下),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第921页。不同于美洲洪门致公堂主要依靠华侨华人推进党务,陈炯明在香港整理致公党党务时,借助的力量主要是他在粤军中的亲信旧部。
因此,1933年陈炯明逝世后,致公党中央主要由陈炯明在广东,特别是东江地区,依靠同乡、同学、同族的关系形成的小团体领导。事实上,1931年“致公党二大”党章曾对总理的权责及产生办法做出过具体规定:总理为全党领袖,有领导全体党员之权责。“总理为全党代表大会及中央干事会之主席”,“总理缺位时,由中央干事会临时主席摄行总理职务,同时于六个月内组织总理选举会,行次任总理之选举。”②《中国致公党全党规章》(1931年11月13日),王起鹍:《海外洪门与中国致公党》,第128页。然而,陈炯明逝世后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并未能够按照党章规定组织筹备总理选举会,致公党相对松散的组织形式也使党员普选总理不具备可行性。中央干事会由此代行总理的职责,领导党务,主持日常工作。③《中国致公党简史》编辑委员会:《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第9页。实质上,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主要仍是由与陈炯明有乡缘、学缘、族缘的亲信成员构成。
马育航为陈炯明的广东海丰同乡,早年加入同盟会,后任粤军总司令部副官长,作为陈炯明的亲信始终追随左右。④海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海丰县志》(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47页。陈炯明逝世后,马育航参与其丧葬事宜。之后,他一方面与国民政府联络,请求国民政府对陈炯明的家属进行抚恤;⑤《陈立夫报告与致公党马育航在沪两次接洽所及大体情形,应如何进行,敬乞示之》(1934 年10 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189-081。另一方面将陈炯明的个人事迹、革命活动送登各报,介绍陈炯明的晚年政治思想,并电告旧金山、吉隆坡等致公党地方党部陈炯明逝世的情况。⑥林忠佳、蔡阳山主编:《陈炯明与粤军研究史料·10·陈炯明言行录》,海丰县历史文化研究会、陈炯明学术研究会2004年内部印行,第460页。马育航通令致公党下设的分支机构,与国民党高层进行接触、互动,均是以致公党的名义进行的。
对于马育航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国致公党,有学者曾提出质疑。笔者认为,陈炯明逝世后,马育航即开始以致公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同陈演生等与地方党部进行联络、开展有关党务的各项活动,实质上参与了致公党的领导工作。此外,中国国民党中统局对致公党进行过详细的秘密调查,亦判定马育航是当时在香港的中国致公党的主要领导成员,局长朱家骅、副局长徐恩曾在向蒋介石报告致公党情况时,屡次提及马育航为“致公党首要”“重要份子计有马育航、陈演生、钟秀南……”。⑦《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公函》(1940年2月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档案号:特8/2.8。可以说,无论是从马育航实际承担工作的性质来看,还是以当时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的观察为据,均可认为马育航是1930年代初期香港致公党的重要领导成员。
香港中国致公党内也出现过举“抗日反蒋”的蔡廷锴为总理的声音,马育航等对此建议予以拒绝反对。1934年5月,蔡廷锴经由香港到达菲律宾,隶属于香港致公党总部的菲律宾支部开会欢迎,并转请香港总部发表通电,表示拥蔡廷锴为该党领袖。此时,致公党处于陈炯明逝世后暂无新领袖产生的阶段,而马育航、钟秀南等拒绝了拥蔡为党的领袖的建议。①《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公函》(1940年2月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档案号:特8/2.8。
不同于美洲洪门致公堂欲借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之势共同反蒋,马育航着眼于试探与中国国民党当局进行政治上联络,甚至结合的可能性。联系国民政府抚恤陈炯明的家属成为马育航与中国国民党当局进行联络的一个由头。以此为“破冰”,他多方设法、辗转托人向蒋介石进言。1934年10月,马育航由香港到上海,先后于10月16日和21日与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立夫进行了两次长谈。马育航表示愿意拥戴蒋介石,在得到蒋介石容纳后,将使致公党成为蒋介石领导下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别动队,秘密接受蒋介石指导,并致力于拥护蒋介石为致公党的领袖。马育航还再三向陈立夫申明,与中国国民党的合作并没有任何不良企图,也不要求附加条件。②《陈立夫报告与致公党马育航在沪两次接洽所及大体情形,应如何进行,敬乞示之》(1934 年10 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189-081。
陈立夫在向蒋介石报告与马育航接洽情形时,对致公党的海外组织及掌握舆论状况做了详细的介绍:在组织上,致公党自陈炯明死后,即由马育航等组织中央干事会领导之中央总部,设于香港,地方总部有旧金山、古巴、秘鲁、巴拿马、伦敦、新西兰、东非洲、吉隆坡等八处,管辖之支部共五十余处,据言登记党员约十余万人;在宣传上,致公党直接有关系之报纸,有旧金山《公论晨报》、古巴《开明公报》、秘鲁《正言报》、南洋《公言报》、东非《永是报》、香港《致公通讯录》等六家,与致公党有关系者,有纽约《国权报》、加拿大《洪钟报》《大汉报》等三处。③《陈立夫电蒋中正关于致公党马育航愿拥戴钧座及与其接洽情形等文电日报表》(1934 年10 月30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442-255。
基于上述情况,陈立夫向蒋介石列举了致公党可以为其所用的政治资源。在国民党容纳致公党后,致公党可以秘密接受蒋介石领导,在华南军事、政治及金融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做各种有利于蒋介石之工作;致公党党报和相关报纸可以逐渐改变态度,做拥护国民政府之宣传,并利用致公党在香港政府工作的党员改变新闻审查态度,利用香港发出有利于蒋介石的新闻,或者在香港创办大规模通讯社、报馆等。除此之外,陈立夫认为致公党对蒋介石及中国国民党最能为其所用的在于海外,因致公党组织多在海外。④同上。
综上,陈立夫判断,马育航之拥护蒋介石,虽其目的不外乎是为致公党谋求出路,“但彼等年来颇觉悟,且对于国事观察,认为唯钧座足以担当国家救亡图存大任,亦一重大原因”。⑤《陈立夫报告与致公党马育航在沪两次接洽所及大体情形,应如何进行,敬乞示之》(1934 年10 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189-081。可以看出,陈立夫已经为马育航展示出的各种“筹码”所动,并且信任马育航等的诚意,比较倾向蒋介石接受致公党的合作请求。
然而,蒋介石对马育航抛出的“橄榄枝”则更加理性、审慎。蒋介石表示,马育航之前曾来函请求国民政府援助陈炯明及其家属,他并没有回复,加之马育航与即将赴香港协助中国国民党当局宣传的陈其尤相互攻讦,他对马育航持保留态度。对于致公党,蒋介石判断其“涣散正极,马所言或者不免夸大”。但同时,蒋介石也不会对致公党能够为其提供的益处视而不见。他看重的是“致公党属历史悠久之华侨团体”,因此提出“实有使之内向收之为国之必要”,让陈立夫与致公党方面商量团体合作的具体办法。①《陈立夫电蒋中正关于致公党马育航愿拥戴钧座及与其接洽情形等文电日报表》(1934 年10 月30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442-255。
1934年11月,马育航又求吴稚晖介绍面见蒋介石。②《陈其尤报马育航拟用致公党名目,求吴稚晖先生介绍面见钧座接洽》(1934年11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190-079。马育航之所以寻求吴稚晖代为联系,一是吴稚晖为中国国民党元老,在党内资历颇深,为蒋介石所尊重;二是陈炯明因“六·一六兵变”与孙中山产生矛盾之时,吴稚晖负责为二人说和,并为陈炯明向孙中山求情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0 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4页。,虽然最终调解并未成功,但吴稚晖、陈炯明二人私交不错。陈炯明逝世时,吴稚晖写挽联“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十年前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表示了对陈炯明个人的肯定。④陈定炎编:《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下),第976页。所以,马育航借陈炯明后事之名,或许是利用陈炯明与吴稚晖的个人关系辗转请求面见蒋介石。1934 年12 月28 日,蒋介石电陈立夫,委以马育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议。⑤《蒋介石电陈立夫委以马育航行营参事》(1934年12月2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70100-00037-035。马育航对这一委任似乎并不满意,1935年他再次去函吴稚晖,提到上个月请其帮忙递信给蒋介石的事情,并解释“该函系为竞存(按“竞存”为陈炯明的字)后事所深恳”,请求吴稚晖在重庆见蒋介石时顺便提及并询问。⑥《马育航刘白致吴稚晖函》(1935年3月24日),《吴稚晖档案》,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典藏号:稚04403。由此可见他对与蒋介石进行联络的迫切。
目前,由于档案资料有限,对马育航“拥蒋”的目的尚没有研究清楚。但不可否认,接受蒋介石领导、与中国国民党联合已成为这一时期致公党内存在的政治倾向之一。譬如,“福建事变”期间,钟秀南曾从事配合国民党中央军、吸收十九路军下级军官的工作。钟秀南1926年曾被陈炯明选为“致公俱乐部”副主任⑦林忠佳、蔡阳山主编:《陈炯明与粤军研究史料·10·陈炯明言行录》,海丰县历史文化研究会、陈炯明学术研究会2004年内部印行,第468页。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港英政府不准华人在香港设立政治性的机构,因此当时在香港的中国致公党以“致公俱乐部”名义登记注册。,“致公党二大”后成为中央干事会人员之一,是国民党中统局认定的致公党“重要份子”之一。⑧《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公函》(1940年2月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档案号:特8/2.8。李汉魂在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也认为钟秀南在致公党“历史深长亦有地位”。⑨《李汉魂电蒋中正称请令中央驻港机关派员与钟秀南联络并分函致公党海外各支部接发指斥陈直中等附汪行径》(1939年10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90200-00023-091。1933年12月,国民政府南京特别党部常委萧吉珊向蒋介石报告福建的情形,提到钟秀南在闽南一带与民团联络甚久,还先行进入漳州,与时任漳厦警备司令兼任厦门市长的黄强进行过接洽,并指出钟秀南“至十九路下级军官彼亦有方法吸收等语”。①《萧吉珊电蒋中正据金章云若闽南开展中央宜派军舰装一师》(1933年12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140-089。
香港的中国致公党与蒋介石进行联络、倾向蒋介石的政治表现,可能与中国致公党组织涣散、党员缺乏对致公党的政治认同相关。一方面,陈炯明逝世后的相当时间内,香港的中国致公党内难以产生一位具备“党统”与“党权”的领袖,正如长期涉足粤省军政的李汉魂所说,“自陈炯明死后该党组织日益散漫,工作大部停顿”。②《李汉魂电蒋中正称请令中央驻港机关派员与钟秀南联络并分函致公党海外各支部接发指斥陈直中等附汪行径》(1939年10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90200-00023-091。而其分支组织由香港辐射至东南亚,美国西海岸等地,分布广泛的独特地域性使其组织更加分散,或需借助于强有力的外部力量整合组织、确保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致公党与国民党的组织纠葛、党员双重身份的前后递变,使马育航等成员对致公党的政治认同并没有那么强烈深刻。孙中山曾促成同盟会与旧金山致公堂的联合③陈昌福:《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政治思潮与洪门致公堂的“改堂为党”——陈炯明、孙中山与中国致公党的建立》,《近代中国》(第十四辑),2004年8月。,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双方人员高度重合,一些人兼具同盟会会员、致公堂成员的双重身份,陈炯明、马育航在1924年与致公堂取得联络并在此后加盟致公党前④1924年2月2日,马育航曾代表陈炯明与致公堂负责人黄三德联络。黄三德述:《洪门革命史》,美国洛杉矶1936年自印本,第48页。,均加入过同盟会及其改组的中国国民党。陈炯明1909年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同年加入同盟会,马育航随后于1910年加入同盟会。⑤陈予欢编著:《民国广东将领志》,广州:广州出版社,1994年,第3页。1912年同盟会改为中国国民党并成立广东支部⑥陈定炎编:《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上),第91页。,陈炯明担任支部长10年之久,直到1922年6月与孙中山决裂前方辞去中国国民党广东支部长之职。⑦陈定炎编:《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上),第503页。
党魁去世后,致公党所赖以生存的政治资源更显不足,马育航等便希图通过“拥蒋”,依靠中国国民党为致公党寻求一条出路;也有可能,马育航等是出于个人权力的向往,想以致公党为政治资本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谋求职位,故与之进行联络。无论如何,“拥蒋”成为1930年代初期在香港的中国致公党的政治趋向,而蒋介石也瞄准致公党联结华侨的功用,谋求收之为国民党所用。
三、私人代表:陈其尤以“驻港宣传指导员”身份在港活动
陈其尤,也是陈炯明的广东海丰同乡,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黄花岗起义和光复惠州战役,辛亥革命后公派赴日本留学,曾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后跟随陈炯明迁至香港。⑧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1365页。关于陈其尤加入致公党的时间,有1925年致公党成立时和1931年“致公党二大”时两种说法。从严格意义上讲,陈其尤在1930年代初期或许还难称为一个独立派别,但蒋介石在对致公党进行关注时,曾将陈其尤作为致公党内与马育航相对的力量进行过评估。⑨《陈立夫报告与致公党马育航在沪两次接洽所及大体情形,应如何进行,敬乞示之》(1934 年10 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189-081。此外,抗战胜利后陈其尤促成中国致公党重建组织并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政党,且长期担任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故本文对陈其尤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也予以关注。
陈炯明逝世三个月后,1933年12月22日,陈其尤致电蒋介石,表示即将去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晋谒①《陈其尤电蒋中正即赴行营晋谒》(1933年12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140-033。,后陈其尤与金章一同抵达南昌行营。②《萧吉珊电蒋中正据金章云若闽南开展中央宜派军舰装一师》(1933年12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140-089。而蒋介石此时身在上海,安排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代为招待陈其尤与金章,并表示可以委任陈其尤、金章为行营参议,每个月发三百元。并特别表示“其尤兄如能在赣暂住待中回赣晤面后再行更好”,准备与陈其尤进行面谈。③《蒋中正电杨永泰告以金章、陈其尤来时请代为招待可委其为行营参议》(1933 年12 月28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141-033。12月30日,蒋介石再次表示希望陈其尤能留在南昌等待他回去后进行面谈,否则可以另行约定日期④《蒋中正电杨永泰据金章、陈其尤称未克面敘甚念闽南诸事迳与杨永泰商洽办理或另约期相晤》(1933年12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141-064。,并委托杨永泰给陈其尤多发川资三千元。⑤《蒋中正电杨永泰请发金章、陈其尤两人人三千元车资》(1933年12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141-065。由蒋介石计划与陈其尤见面,委以行营参议并给予重金可以看出,蒋介石对陈其尤极为重视。虽然没有关于蒋介石与陈其尤洽谈的具体情形,但可以得知陈其尤应该是已经接受了蒋介石请其为行营参议的请求。1934年2月,蒋介石专程发函给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的陈立夫,表示陈其尤即将回港办理宣传及联络等事,希望陈其尤到南京时陈立夫能予以指导,俾利进行。⑥《蒋中正电陈立夫告以陈其尤赴香港办理宣传联络事宜到京時希予指导俾利进行》(1934年2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141-065。从陈、蒋二人的联络过程,可以看出蒋介石对陈其尤的关照与重视。
1934年3月,陈其尤到达香港后“冀图报称助成统一大业”,帮助蒋介石统一各派势力,而其时“此间各派混集情形复杂”,陈其尤号称晤见了各派首领“宣布钧座伟大真意,致力于剿匪建设二端”,使得“空气立为转变”。陈其尤表示如果需要进一步接洽各派,最好先要委以官职,蒋介石拟以通讯社之名作为陈其尤联络各派的机关。⑦《陈其尤电蒋中正香港各派混杂如欲迳來接洽最好先饬职办理》(1934年3月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151-102。此后,陈其尤调查香港通讯社的情况,发现香港已经有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所办的通讯分社,及《东方日报》《天南日报》,陈其尤认为这三个机关彼此不相联合、精神散漫,便以“拟就此整理指导,可费省效大”之由请蒋介石委任他为中国国民党中央驻港宣传指导员,并要让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加以委任并分别电令相关三个机关遵照办理。⑧《陈其尤电蒋中正请电宣委会及该会所办通信分社等委职为中央特派驻港宣传指导员统制整理各通信社事》(1934年3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152-079。
很快,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便致电蒋介石,同意陈其尤赴香港指导宣传之事,蒋介石南昌行营随后电委陈其尤为中央特派驻港宣传指导员⑨《邵元冲电蒋中正驻港指导宣传事令派陈其尤前往负责办理》(1934年3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153-053。,邵元冲亦电令中央分社主任周野蓁、《东方日报》总编辑李伯鸣、《天南日报》社长罗伟疆三人,“今后应与陈其尤密切联络,并接受其指导矣。”①《邵元冲电港地宣传事项已令周野蓁、李伯鸣、罗伟疆今后与陈其尤密切联络并接受指导》(1934年3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154-010。不难看出,蒋介石对待马育航与陈其尤态度的云泥之别。可以说,早在马育航向陈立夫坦陈可以为国民党在华南特别是香港提供各项便利的半年前,蒋介石即已拿定主意,由陈其尤代其在香港进行宣传及联络活动。
对于蒋介石的委任,陈其尤在自传中归因于蒋介石认为二人是“粤军老友”。②陈其尤:《陈其尤自传》,《中国致公》2002年第12期。陈其尤在留学日本期间即结识蒋介石。③林忠佳、蔡阳山主编:《陈炯明与粤军研究史料·10·陈炯明言行录》,海丰县历史文化研究会、陈炯明学术研究会2004年内部印行,第489页。1918年至1919年间,陈其尤曾任粤军援闽总司令部机要处长,同一时期蒋介石也在粤军中供职,二人因都是留日同学比较亲近。④《陈其尤同志小传》(1954年),致公党广东省委会档案室藏。1918年8月蒋介石觉得未被重用辞别粤军时,陈其尤受陈炯明之托专程挽留。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正午搭火车赴汕车中遇陈其尤,总司令特派其来沿途挽留也”。⑤《蒋介石日记》,1918年8月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不再注明)。1921年5月20日,蒋介石受陈炯明电邀赴粤,“上午登岸,往访陈其尤交涉使”。⑥《蒋介石日记》,1921年5月20日。9月9日,蒋介石奔母丧返粤之时,陈其尤已任潮梅海关监督兼汕头交涉员,在潮汕声势显赫,仍前去接应,蒋在日记中专门记录到,“船进汕头港,陈君其尤来接,到其海关监督署谈天。中食于日本旅馆。”⑦《蒋介石日记》,1921年9月9日。可以说,在蒋介石不得志、丁母忧等人生低潮时,陈其尤的关照应该给他留下印象,为二人关系打下基础。
陈其尤也曾为致公党的运转争取过经费,但他本人与致公党较为疏离。陈其尤向蒋介石介绍到,陈炯明之前创办的致公党,计在港党员五六千人,在南洋一带者近万,在美洲更多,并进一步表示他已经提倡致公党“改变方针拥护委座,日来干部会议原则通过”。⑧《陈其尤函蒋中正现在工作为在和平原则下联络各方指导宣传遇事侦查报告及请自本月份起每月暂给致公党港币一千元等文电日报表》(1934 年3 月12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429-169。但是,陈其尤并未提及他与致公党的渊源、在党内的职务,仅将倡议致公党拥护蒋介石的原由归结为“其尤因与競存(按指陈炯明)向有历史关系”。⑨《陈其尤函蒋中正现在工作为在和平原则下联络各方指导宣传遇事侦查报告及请自本月份起每月暂给致公党港币一千元等文电日报表》(1934 年3 月12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429-169。这似乎与陈立夫向蒋介石介绍致公党在香港活动情况时提供的情报相吻合,即“陈其尤与陈竞存虽有关系”,“上次赴赣系全为个人谋事,该党尚未请其代表。”⑩《陈立夫报告与致公党马育航在沪两次接洽所及大体情形,应如何进行,敬乞示之》(1934 年10 月3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典藏号:002-080200-00189-081。
虽然陈其尤日后认识到中国国民党内的贪腐,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在中共地下党员黄鼎臣的争取与帮助下,逐渐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为抗日战争后致公党的重建、“致公党三大”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做了巨大贡献。但是,陈其尤在香港期间的活动多以“中国国民党中央驻香港宣传指导员”的身份进行,主要负责向蒋介石报告中国国民党内各派势力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及香港的舆论情况。这一时期,陈其尤受到当时往来于香港的各界要人,包括港督、港绅①《港督昨宴陈其尤》,《香港华字晚报》1937 年3 月3 日,第7 版;《何东宴陈其尤》,《香港华字日报》1936年11月2日,第8版。的特别重视,这为中国致公党日后恢复组织活动积累了广泛的社会资源。
四、结 语
中国致公党成立于美国旧金山,因“华侨中十之八九皆系洪门成员”②秦宝琦著:《洪门真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8页。,其分支遍布海内外、党员人数众多。若能提高组织的内聚性,其政党组织实力应当不容小觑。然而,组织上的党、堂不分是致公党成立后就困扰着该党的问题,散居于各地的致公党、堂始终未能就组织形式达成一致,缺乏内部组织结构的协调性、严密性,更遑论实际运作的有效性。1931年致公党党魁陈炯明召集各地党、堂,试图整顿党务,解决党堂不分的问题,却未能如愿,致公团体组织结构仍然散漫如故。
创党领袖陈炯明在世时,致公团体内不同力量尚能聚于香港、共商党(堂)务。1933年陈炯明逝世,政党领袖所能发挥的凝聚作用消失,致公团体面临更大的组织离心力,组织内部不同派别明显分途。且不奢望党、堂间有共通的“主义”或纲领,即使在如何对待最高领袖蒋介石、如何处理民族危机这样最基本的政治议题上,组织内的不同派别已经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美洲致公堂及其代表的华侨华人久居海外,将自己在侨居国的社会际遇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对“抗日反蒋”特别迫切。在共同抗日的目标下,各致公堂口停止纷争、结束堂斗,但这仅仅是暂时的、阶段性的、有限度的,内部立场各异仍是其基本面相。香港的中国致公党主要辐射东南亚地区,与大陆较接近,其内部涌现出“拥蒋”的倾向。然而,蒋介石认为致公党“涣散正极”,并未予以致公党所期待的回应。如蒋介石所认识的那样,香港的中国致公党组织涣散,其成员对蒋介石的联络,有时是以“个人”的身份而非“党人”的身份,政党成员缺乏对该党的政治认同,时常疏离于致公党之外。
分散于不同地域的党与堂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这种分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民党内派系纷争的政治生态之影响,也是国内政局动荡和政治斗争的一种典型反映。但无论选择拥护蒋介石,还是选择借势于与蒋分庭抗礼的地方实力派,均体现了致公团体无法“求诸于己”,只能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由此,可以看出致公团体距离组织独立华侨华人政党的差距所在,也有助于理解其内部组织形式及抗战胜利后各方恢复组织、重组政党的努力之艰辛。这或许不单是致公党的特点,也是民国年间各“小党派”的普遍面相。
全面抗战爆发后,致公团体努力弭平内部分歧,捐弃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嫌隙,毅然举起抗日旗帜,客观上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以乾隆末年至咸同年间洪门会簿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