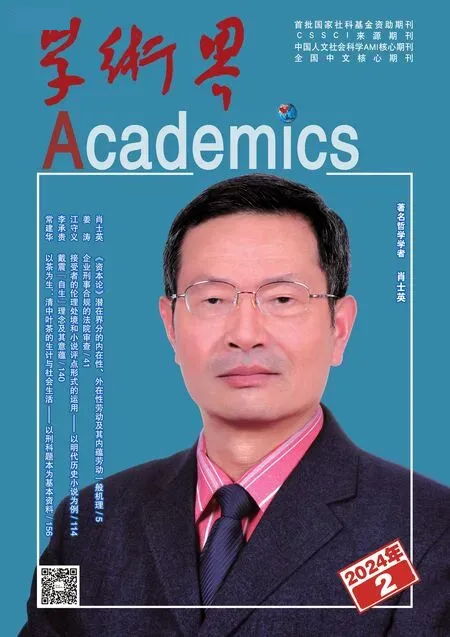戴震对程朱“气质之性”的批判与重释〔*〕
张盈盈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3)
程朱以“理”为最高范畴建构了“理主宰气”的宇宙图式,以此作为道德之善的根源。据此将人性分为:义理之性(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视“性”和“理”一样在人未出生之前就先天存在,性善是先天的、本然的、永恒的;后者一直是宋儒贬低的对象,因“气质之性”被视为人性“恶”的根源。这种二元人性论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强调压抑、遏制情欲而服从道德原则(理),限制了人作为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上的能动性,逐渐形成扭曲人性的伦理观念。因此,戴震极为反对程朱之“气质之性”,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的正文中,“气质之性”出现了28次,所提到之处均是以批判程朱的“气质之性”为主。戴震虽未直接以“气质之性”命名其性论,但是“气禀”“气质”却是其人性论中的核心,故本文以“气质之性”为其人性论的根本。〔1〕阐释戴震从人的经验生活的具体境遇出发探寻人性之善,揭示“气质之性”在“情欲”与“心知”互动的作用中所形成的道德人格,凸显了戴震的人性论具有认识论与伦理学统一的倾向。
一、性与气质的对立
戴震与程朱理学人性论最明显的不同是人性的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区别。所谓一元与二元是从理和气上说。明代中叶以后,“气本论”思想家对宋代以来的“理气关系”完成了整序,“气”向“理”的渗透并逐渐取代“理”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重要依据。理气关系的转变反映在人性论上是儒者们不再以道德形而上学为主要立场,而是转向从经验的层面看待人性的问题。戴震是这一思潮的杰出代表,他批判以程朱为主的宋儒以“气质之性”非性,反对脱离经验言人性,认为人的本然之性是气质之性,提出迥异宋儒的人性学说。
戴震批判程朱理学受老、庄、释之蔽而不自觉,“杂袭”老释之言以解“孔孟之书”,所以导致孔孟之书“失其解”。从人性论看,程朱的“失其解”是将性与气质对立起来,才有贬低“气质之性”的各种论断。“气质之性”最早由张载提出,他主张人之气质美恶“所受定分”,是先天的。“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相比具有不完满处,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实现“变化气质”,以纠正气质的偏差。程颐在“理主宰气”的本体论范式中言人性,其“性即理”说将“性”与人的气质对立起来。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性即理”说,将心、性、情置于“理本体”中以定型化。概而言之,程朱的人性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天命之性(义理之性),这是人的本然之性,至纯至善。二是气质之性,“气”与人的形体相联形成气质,气质的清浊影响人性中善的实现,是人性之“恶”的根源。“理”是程朱理学的最高准则,是人性善的根据;情欲出于“气质”,强调“气”对本然之性的限制义。宋儒把人的嗜欲、不善等“恶”的因素归于形气,本质上是将“气质之性”排除于人性之外,使得本然之性永远孤离于具体的人。因此程颐认为,论性就是指“义理之性”,气质之性根本算不上“性”,这种二元的人性论形成严重的割裂。戴震总结为:“宋儒剖析至此,皆根于理气之分,以善归理,以有恶归形气。”〔2〕他认为,宋儒所说的“理”只不过是主观的“意见”罢了,离开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空谈“理”是“祸天下”的行为。
事实上,程朱对人性的两种划分是对孟子性善说的一种补充。自孟子提出性善说以后,性善说一直是儒家思想的主流,但是“性”并未被视作本体。自宋代以后,程朱以天理纯善无恶,“性善”有了本体论依据。所谓“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3〕“善”与“恶”都是人性的品质,人性之“恶”又从何而来?为此,程颐以“理”“气”对举的方式,解决了恶的来源问题。他认为“性即理”,理是形而上之道,理善则性善;气是形成万物的具体形态,气有善有不善,现实中很多“恶”的现象是受“气”的影响。程颐认为,孟子所讲的“性善”不是具体现实的人性,只是禀理而生的人性,孟子论性善而忽略“才”的不善;告子相反,虽然认识到“才”的不善却不知“性无不善”。程颐说:
性字不可一概论。“生之谓性”,止训所禀受也。“天命之谓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缓,天性刚急,俗言天成,皆生来如此,此训所禀受也。若性之理也,则无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4〕
可见,程颐把“天命之谓性”视为人禀理而生的本然之性。朱熹的“气质之性”说与程颐稍有区别。他说:“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五常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5〕人禀于理而具有仁义礼智之性,禀于气而有形体之躯。人与物未生之时,天理流行所赋予的人性是本体之性,亦是“天命之性”。但是,人在出生以后,禀理之性就坠在形气中,此时的人性便不是“天命之性”或禀理而生的性了,而是由气禀决定的“气质之性”。因为气质的驳杂会使人性受到遮蔽而偏离人的本然之性,人被“气禀所拘”而有诸多限制,故“气质之性”成为影响人之道德理性生成的负面因素。因此,程朱道德修养的目标是倡导人“复其初”,即回到原初的、没有气质之杂的状态方可恢复人性本然。
具体而论,程朱的气质之性与人的情欲相涉。气不停的运动积聚为形质,人禀受气而成形体,这个形体便是血肉之躯,情欲根源于血肉之躯,如果不加以控制,就会成为“恶”。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血气”下了定义:“血气,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阴而气阳也。得,贪得也。随时知戒,以理胜之,则不为血气所使也。”〔6〕人的形体由血气而生,血阴而气阳,要随时控制“血气”,强调以“理”胜之,不能被血气所左右。“气质之性是理坠入人的血气形体之后形成的,这个性已经不是理的本来面目了。”〔7〕与人的“血气”之躯相对,人心亦生于形气,人心本来不是“恶”,但如果人心放任流荡变为人欲即是“恶”。若依于天理合乎规范便是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合乎天理便是合乎官方倡导的伦理规范。换句话说,生命要以人的本然之性化掉感情欲望中的不合理成分。然而,在实际的道德生活中,人们不禁会质疑,为何经过功夫修养却很难达到纯洁无染的天命之性?人欲是否可以完全消除?在天理与人欲极端对立的模式中,人们不可避免的陷入种种悲剧。为此戴震说: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8〕
在戴震所生活的时代程朱理学已被官学化,其直接性的社会影响是产生了许多“以理杀人”的现象。戴震亲见许多惨案,痛斥“以理杀人”,疾呼“理”不能凌驾于人欲之上。事实上,明代中叶以后,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禀于气而有的情欲是人的天性中固有的组成部分。“所有过去认为先天的、义理的、道德的,可以完全放心拿来作为行为依据的说法,此时皆无法稳稳的站住。”〔9〕王夫之认为,如果没有“欲”,那么何谈尽“理”?饮食男女是“人之大共”,即人欲是人的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此时众多思想家无法接受程朱对“气质之性”的负面评价。
可以说,在明清之际反对宋明儒的思潮中,天理与人欲的次序逐渐发生转变,反对宋明儒以“气质之性”为恶是主要的靶向点,重视“气质之性”的儒者不在少数,如陈确、颜元、王船山等,至戴震已形成一种成熟的哲学表达。戴震是否直接地接触过这些人的著作尚且不论,但是从思想的形成来看,他对“气”的崇尚和对“情欲”的肯定确实存在着观念上的延续。戴震认为,天道气化流行变化产生“血气”而有人类繁衍的男女之别形。“耳目百体之所欲,血气资之以养。所谓性之欲也,原于天地之化者也。”〔10〕可见,他认为“欲”是人作为“血气之属”与生俱来的本性,谋求人“遂其生”与“遂其欲”是可以落实的经世原则。戴震批评程朱以告子的“生之谓性”之说附和孔子的“性相近”说,创立名目曰“气质之性”,并视其为人性之恶的根源。“专以性属之理,而谓坏于形气,是不见于理之所由名也。”〔11〕他指责程朱把人的本然之性归于理而空谈心性,人一旦出生成为现实的人后,禀理之性便被破坏了。究其原因是程朱对理与气的截然分明,他们把理视为实有,把气视为粗陋。故戴震以“气”为“天下一本”重释“气质之性”的本质内涵。
二、舍气质无以为性
程朱基于“理本论”的宇宙图式把“性”置于人性的先验结构中,从而将人性的“善”视为不可动摇的形上根据。一边崇尚义理之性,一边大力的贬低气质之性,这种人性学说逐渐脱离现实陷于空洞,陈义过高且不近人情。“理欲关系”变得空前的紧张。戴震从程朱理学内部结构进行解构,以“气一元论”为逻辑起点,提出“气质之性”是人性的根本。
戴震认为人性源于天道,是天道生生不息、气化流行而衍生出来的,具体说是以阴阳五行之气化运行,彼此之间杂糅氤氲变化而生万物。他从动态方面探索“气”的性质与功能,强调“气”的运动不受“理”的制约,重置了程朱的“理气关系”,把自张载以来的“气本论”又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在戴震看来,程朱以“形而上”与“形而下”来形容“理”与“气”:“天地之间,有理由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12〕以“形而上”界定“理”本体,以“形而下”形容“气”。“理”“气”的“形上”“形下”意味着永远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代表宇宙普遍法则的理世界,另一个是代表世间万象的气世界,气的存在和运动是由理来规定。戴震把“道”(理)拉回了现实世界,并突出“道”的物质性。他认为,所谓的“形上”“形下”是对“气”的不同存在形式的划分。“形”即是已成形质,“形而上”是阴阳五行之气没有聚积成形以前,“形而下”是气积聚成形质以后,这样,“形上”与“形下”实为同一个世界,即以气为“一本”的世界。宇宙之间只有一气流行。他说:
气化生人生物以后,各以类滋生久矣;然类之区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气化曰阴阳,曰五行,而阴阳五行之成化也,杂糅万变,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虽一类之中又复不同。〔13〕
人与物的产生是气化过程的自然现象,“气”决定着万物的性质。此外,戴震又将“气”概括为“道”,指出阴阳五行就是道之实体。“气”是“道”之实体,亦是“道”的体现,或者说“道”存在于气之中,“道”与“气”是一回事,只是二者处于不同的状态之中,即一阴一阳氤氲变化运动过程生成了万事万物。万物之间各有各的特点,这在于“禀气”时有厚薄、清浊、昏明、偏全的不同。凡物皆有“生生”之阴阳五行之气自然的周转运行,并不是说在“气”之上还有一个“理”主宰。万物的产生与存在也是“分于道”,即是“分于阴阳五行”,若离开了“气化流行”的过程,意味着存在的终结。
明清之际主张“气质亦性”的思想家不在少数,他们以“义理”即是气质的本然,不是性的另外一个部分,气与性是合一的。在“气”的哲学谱系中,戴震是一“集大成者”,在他之前的哲学家都有相关的理论建树。罗钦顺认为万物的产生是“一气而已”,“气”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中,是世界本原的必要条件。王廷相指出“气者造化之本”,〔14〕从“气”的属性方面进行了界定,“气”虽无形却是“实有之物”,若只知气化而不知气本,没有领会其要旨。王夫之认为理只是“气”之理,“气”外没有虚无之理。王廷相认为气质之性就是本然之性,“气”是“性”产生的基础,如果离开气,性将不复存在。这些思想家都重视“气”,但是,他们对“情欲”却未必如戴震一样持肯定的态度。
戴震提出论性要以“气质之性”为本,舍“气禀气质”无以为性。他说:“舍气类,更无性之名。”〔15〕人是气化的产物,离开气禀气质便不能讨论人性。天道之“气”的“分”与“合”,形成人的“血气之躯”,人的形体来源于阴阳五行之气,包括人的生理特点、感觉器官以及感性功能等。万物由“气禀”而各成其性,包含人与物形成形体的“本受之气”与维持生存与繁衍的“资养之气”,这两种气内外有别,相互作用,都是天地气化运动分化出来的结果。戴震以“气”规定人性的模式与程朱大相径庭,反对把“气质”与“义理”(性)割裂开来。程朱认为人的身与心都属于“气质”的范畴。天命之性(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划分,割裂了“理”与“气”,使得道德主体与道德原则分成两截,为了强调道德行为必然发生,不断地在道德原则(义理)上下功夫,从而忽略了人自身的存在。
戴震以“气质之性”为人的本性旨在阐述“情欲”是人性所固有。他认为“气质之性”的内涵是“血气心知”。戴震将气质又称为“血气”,血气构成与资养人的身体,是人的生理本能,是一种生命力量。他又指出“气化生人生物,而理在气质之中乃名性也”。〔16〕以“气”决定理,“理”是气之理,“性”是气之性。当然,“有的人天生是麦子,有的人天生是稻子,各有其气质之近,不可全部变成‘印板’一般的完人。”〔17〕戴震着重从人之自然材质上凸显人性中的感性内容,例如耳鼻眼口接触外界而形成的感官欲望。同时,人在具体的实践中会产生喜、怒、哀、乐之情,这些都是血气之自然的表现。可见,戴震是以经验为基点把握人性,相对于程朱从形而上的超验世界,更具有现实意义。张岱年先生说:“气质之性,即是本然的,即是纯善的。此种性一元论,发始于明代盛于清世。”〔18〕戴震一直以私淑孟子自称,性善论亦是其根本主张。那么,以自足的、自为主宰的“气”为人性的根源,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便是阐释“气质之性”何以为善,否则便无法缓解程朱理学人性论中“理”与“欲”的紧张关系。
三、“性善”源于“气禀”
程朱以理言性善,戴震则以“气”言之。所谓“人之性善,正要在气质上看”,〔19〕为了说明“气质之性”为善,需要重新架构“气”与“善”之间的关系,以证“气”是人性善的根据。戴震没有像颜元那样主张理气兼善,而是将人性置于经验领域,从人性内在结构包括人欲、人情等基本属性出发,证明“气质之性”中含有道德之善。他从“血气之自然”推出“善之必然”,企图在人性之“自然”与“必然”之间建立内在联系,此“善”乃是过程意义上的善——可能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气质之性”为善的根据在于“气”。“气”不断运动、反复分化自身而产生万千世界,人按照本有的气质而发展,其情欲展现在人伦日用中。气的运行具有“无憾无失”的特征,人与物能继承“天地之善”而“不隔”。“不隔”即是天道之善直接作用于人和物。凡物生即“不隔”于天地之气化,阴阳五行之“气”总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因此,天道之于人之道表现为“无憾无失”。〔20〕王夫之解释“继善成性”时指出“天道惟气之善”,天道有善,人性继承了天道之善。戴震虽然没有像王夫之那样直接以“善”来指涉“天道”,但是他强调《周易·系辞》中的“继之者善”,而后再言“成之者性”,这种先后次序说明人与物对于天地之善是“继承永不隔”的。从天道看,天道之“无憾”即是天德,天道流行不已具有“生生”的特性,就其“生生”而言,讲的是一阴一阳之气的“生生之德”。实际上,天道和天德的区别只是阴阳五行气化之流行中呈现出不同的作用,天道主气之流行,天德负责“生生”。气在运动状态上要符合“条理”,若失条理就不能生生。从这个角度看,天德与“条理”实际是“一也”的关系,如“实言之曰德,虚以会之曰理”。〔21〕戴震认为,“理”不能脱离事物而存在,在事物之中,又为事物之则。天道是有规律有秩序的运行,对“物之质”即事物具体的内在本质把握,是对事物极为微细差别的一种认识,叫分理。血气不受阻是因为循“理”,这个理又是“不易之则”。“气”的运行蕴含“条理”和“不易之则”,具有价值性的含义。
然而,“善”与“性善”是不同的概念。从“善”的角度看,人与物虽各成其性,都能继承天地之善。但是,戴震认为只有人才能禀赋天德而达成“性善”,因为“人之德性”可以上溯“天德”,人之气性通于“天德”。可以看出,他所讲人之性善是指人具有实现善的能力与可能性。程朱所讲的人性善是纯粹的至善,“性即理”,故“性”是形而上的道德本体,其本身蕴含着仁义礼智之德性,所以主张“复其初”而实现性善。为此,他解释“善”的含义为:“一事之善,则一事合于天;成性虽殊而其善也则一。”〔22〕“善”是“大共名”属于“纯美精好”,当其体现在人们的行为活动中,是一种事物发展到一定状态的描述性称谓。“善”的内涵为“仁”“义”“礼”三者组成,此三者为天下之大本。天道之善是天道之生生而有条理;人道之善,是人伦日用无爽失,“善”就在人伦日用之中,具有价值内涵。人性属于“实体实事”领域,是经验世界中的具体存在。然而,现实生活中难免有“不善”的现象,主张“气质之性”纯善,在理论上便要回答“恶何以生”的问题。对此,戴震的答案是:“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23〕“私”与“蔽”是两个范畴,欲之失会流于私而贪生,知流于蔽而不智,偏私与蔽障的结果会致使“恶”产生。或者可以说,恶是善的缺失,所以要“去私”和“去蔽”。这是“性”经过去私去蔽的努力而达到的状态。
为了进一步证明气质之性为善,他将人性阐释为三层结构。他说:“性,其本也。所谓善,无他焉,天地之化,性之事能,可以知善矣。”〔24〕第一层是人与物同有“欲”,都有生理欲望和饥食渴饮,这是“性之事”;第二层是人与物同有“觉”,感觉功能的大小各不相同,这是“性之能”。性之能的延伸便是“情”,情是性之发的状态;第三层是“性之德”,性之事不沉溺,性之能不闭塞,这就是“性之德”。把“性”分为事、能、德进行区别,以证“事”和“能”与自然有关,德与必然有关。“性之德”是“性之事”与“性之能”的统一。
以“气”论性善是从人的材质出发,这个材质具有使人成为善的可能,只是从“可能性”的角度并不能自圆。为此,戴震又从“必然完其自然”的角度,说明人必然能达成性善。人与物的区别在于人可以“性善”,动物之性谈不上善与不善。因人能“明于必然”,所谓必然即是理义,是善。善与必然相联,性与自然相涉。性的自然属性与生俱来,例如人与动物一样都有“怀生畏死”“趋利避害”之本能。在程朱抽象的人性论中,人的需求与欲望被遏制。戴震在程朱“甚未察”之处追根究底,以人之“自然”为起点,这种自然的材质中具有发展为善的潜质,从而达到必然之善。“天地间百物生生”的一切“性”之实体表现不同的自然形质,万物各成其性而遂其自然。戴震眼中的“气质之性”可以称为“天性”。他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25〕“情”“欲”“知”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区别,代表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戴震将“归于必然”与“适完其自然”统一起来,将其称为“自然之极致”,这是从“性之自然”到“善之必然”自然而然的完善过程,使得“自我”进入成长与完善的不断循环,最终达到天地人物之道的完成。
可见,戴震把人性善视为一个生成过程,人作为一个具体的实在,不是说人生下来便都具有“完善”的道德价值,强调人的材质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实现善,这是人的情感欲望、自觉能力和自然本性的有机统一。他说:“成是性斯为是才,人之性善,故才亦美。”〔26〕所谓“才”是指人禀气而言,“禀受之全”则是性,“体质之全”则为“才”。换句话说,性所表现出来的形体气质叫作“才”。戴震主张人性善的同时强调要经过个体的修养与努力才能臻于“性善则才亦美”。“才”是“性”的显现,是外在的,“性”是内在的,“性”与“才”是统一的,依据“才”的表现可以见性。“才”的表现亦受限于“性”中所具备的能力。戴震以此反驳程朱把“不善”归于“才”。从性命的角度来看,人禀阴阳五行之气而生,命、性、才三者“合而言之”是人的“天性”,人性之自然被“命”决定。
戴震亦从“命”的角度找到“命”与“性善”之间的内在联系。什么是命?从道而言,“分于道”谓命,从气而看,“气”的运行不息即是“命”。他说:“凡言命者,受以为限制之称,如命之东则不得而西。故理义以为之限制而不敢踰,谓之命;气数以为之限制而不能踰,亦谓之命。”〔27〕“命”又分为“理义”与“气数”,二者都表示“命”的限制之名。命也是由天道之气化运行而彰显出来,“性”来源于“命”,“命”兼具某种价值性的必然,包含了“性”之自然所发的“欲”。此“命”不同于程朱所说“天命”与“天理”存在“性”中,戴震意指人都有生生之欲,这是人性之自然。戴震对“命”与“善”的解释,是反驳程朱的“天命之性”,意在指出人天生的“性之欲”有“必然不可易之则”,即人的自然的性,可以达致“必然之善”。
四、“心知”达成“性善”
“气”与“善”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说明人之材质使人具有实现善的能力。人是有欲望、有情感、有生命的现实的人。人之材质的内容是“血气”与“心知”,“气质之性”如何能完满地生发出道德(善),实现认识主体与道德主体的统一,其关键一环在于“心知”。“心知”有“知”义理和“悦”理义的能力,可以推动人性为善的实现。这是说“气质之性”蕴含的道德实践能力是人的身(欲)与心知的统一,通过“心知”的实践进而形成德性。
戴震反对佛道“贬血气而扬心知”,从气化运行的角度看,心是“血气”的一部分,“心知”之自然是“实体实事”。关于“心”,戴震解释说:“以人物验之,耳目百体会归于心,心者,合一不测之神也。如耳目鼻口之官,是形可分也;而统摄于心,是神不可分也。”〔28〕对于人来说,“血气”是物质性的,“心”也不例外是身体的一部分,人的认识是以人的生理条件为基础。心是统筹耳目口的器官,是感知外物的窗口,能够感受到外界的声、色、嗅、味等,并把从外界的接触而产生的信息汇集到“心”,形成感性认识。心不仅是感觉的器官,还具有“思之能”的特性。但是,感觉器官与思维器官不能相互替代,二者“能者各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心能思维即有知觉的能力,所谓“知生于心”,这是“心”所固有的属性。“心之所通”称为知,百体皆能觉,因此,比感觉更高一层的是知觉,知觉即是“精气之秀”。
从认识论上看,“心知”的又一特征是人有“天德之知”。首先,“天德之知”是人能够秉其性以应天地之化育,人与禽兽都有知觉,人能知礼义可以发展为德性。其次,“天德之知”还表现在心知之自然皆“悦理义”,因而人对“理义”会自然产生一种欲求,能产生对理义的天然喜爱。这是说,居于主导地位的“心知”欲求高于血气之欲,以保证道德行为的产生。这里,戴震关于“心知”的界定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一。最后,“天德之知”是“心知所同然”与“心之然”的结合,若能与天德相合,便会中正无邪。禽兽没有知天德的能力,所以虽有“血气”却不足以“知善”。戴震认为,知觉虽是人和物共有的感知能力,但与动物的知觉相比,人的知觉在于人的“人伦日用”之中。他说:
人之心知,于人伦日用,随在而知恻隐,知羞恶,知恭敬辞让,知是非,端绪可举,此之谓性善。〔29〕
作为认知主体具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只有感性认识还不够,需要从感性认识发展为理性认识。“心知”一方面将客观世界的表象进行分析把握现象背后的“理义”;另一方面指人具有知觉道德的能力,为道德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那么,心知觉道德的能力从何而来呢?在戴震看来,这亦是人之“气禀”的结果。人禀“气”而生有“血气心知”,有“血气”而有知觉运动。以“气”而论,“心为形君,耳目百体者,气融而灵,心者,气通而神。”〔30〕可见,人心的特点即为“气通而神”。“心知”是建立在“血气”的基础上,遵循“血气”的发展规则而发展。人作为“血气之属”区别于动物之处在于人不但有心之“精爽”,更能由“知觉”而进入“神明”。或者说“心”与“气”通,才可以入神。可见,心之神明的特性是在人“禀气”而生时就形成的。“举理,以见心能区分;举义,以见心能裁断。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31〕在人的本性中,心有裁断、区别、审察的能力,目的是为了明理义,知不易之则。此外,心之精爽又称为“魂魄”。魂与魄都为“气”作用于人或者说人禀于气而生所形成的不同形态,魂是从乎“气之融”而灵,魄是从乎“气之通”而神。无论是“魂魄”还是“神明”都是指人受气禀而有的天赋的认识能力,当然,这种认识能力指认识理义而言。戴震以“火光照物”作比喻:此“物”指“理义”,人之心识“理义”的过程就像火光把存在于事物中的“理义”照出来一样。火光的大小与明暗决定了能否明理与察物,假若心不具备这种能力,那便是“质之昧”。不过,“火光照物”还有一层含义,假若物不在火光之中,那么也不会有心知理义一说,这从侧面说明戴震所讲的“心知”不具有“理义”。
很显然,戴震针对的是宋儒的“理在人心”。陆王心学一派以“心即理”,将“理”与“心”相连接;程朱一派主张“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例如朱子,他认为人心是知觉声色嗅味的,心也是形体赖以存活的关键。把“心”知觉的能力分为两种,一种是知觉理,另一种是知觉欲。“心”又要去认识和判断在于“心”中的“理”或“天理”,从而产生道德法则的“理”,才能“心具众理”。同时,主张“心统性情”,这是把“心”单独提出来,与人的性情相对,从而突出了“心”对性情的主宰,人的道德理性和情感情欲都在“心”之中。因此,朱熹十分强调道德自觉,以道心控制人心,控制和节制情欲。戴震的“心知”意指“心不是理”,同时“理”也不具于心。
从“气禀”看,“心知”认识“理义”是直接性的,也就是说认识是由心所禀受“气”而形成的能力,故戴震又讲理义在事,接我于“心知”。而且,不需要像程朱那样又另外找到一个“理”而具于心中,心知本身所具有的能力是把主体的目的、能力对象化,反过来成就自己。心是去认识和判断事物之条理的器官。“把主体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成果,转化为主体自己的能力、力量。”〔32〕这意味着,“心”不仅可以用“道德原则”即“理义”处理一切事物,还能够与天地化育的规律相符合。“心知”受气禀所限,需要修养与扩充。戴震认为天地之间的大道蕴含在圣人所作的经典之中。他说:
闻见不可不广,而务在能明于心。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33〕
“增广见闻”对于“心知”识事物之理尤为重要。遇到一事求一事之理,使“心知”不停地得到锻炼。当然,事物之理有时又是变动不居的,戴震以“权变”的方式来掌握变动的人事理则,发挥“心知”的力量,形成心知之智。他极为强调“扩充”对于心知的重要性,“扩充”就是通过学问和修德,使自己原本具有的伦理道德本能(善)发挥出来。此外,心知还有制衡“情欲”的能力,情欲是“气质之性”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是如果不加以制衡会走向另一个反面——纵欲现象的发生。所以戴震强调学习可以增益其“不足”,要不断地“扩充”和“去蔽”追求圣贤之学。
五、结 语
戴震力主“气质之性”为善,在“气”与“善”之间找到人性为善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否定了程朱理学超越的本体的善,肯定了人的情欲的合理性及其在经验世界中道德践行的可能;另一方面,强调了人性的善是一个发展过程。“善”在道德践履中不断地以“心悦理义”结合“克去私欲”而实现。在道德实践中,使得感性欲望与理性自觉统一起来,构成了主体自我发展及道德实践的内在动力!
注释:
〔1〕胡适提出戴震所言的性为“气质之性”,但他批判将气质之性与性善联系起来,认为人可以善是因为人的认识能力远远高于动物,是极为平常的科学知识。参见胡适:《戴东原的哲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47页。
〔2〕〔3〕〔8〕〔10〕〔11〕〔12〕〔13〕〔15〕〔16〕〔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3〕〔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8、34、10、64、70、24、25、34-35、116、82、83、44、9、63、40、106、83-84、153、29、154、3、55页。
〔4〕〔宋〕程颐、〔宋〕程颢:《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3页。
〔5〕〔清〕刘源渌:《近思续录》,黄坤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页。
〔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2页。
〔7〕陈来:《近世东亚儒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0页。
〔9〕〔17〕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4、96页。
〔14〕〔明〕王廷相:《王廷相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55页。
〔18〕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22页。
〔19〕〔清〕吴光酉等:《陆陇其年谱》,诸家伟、张文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6页。
〔32〕张立文:《戴震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8页。
——以《程朱阙里志》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