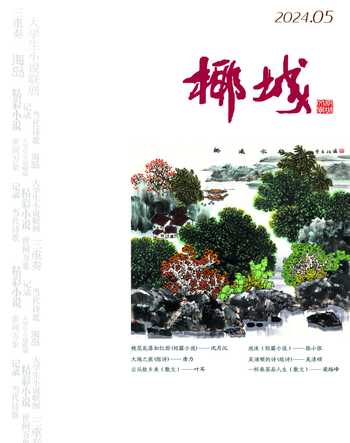谁的青春里没有兵荒马乱(评论)
作者简介:石凌,甘肃灵台人,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作品》杂志特约评刊员。在《文艺报》《北京文学》《作品》《奔流》《飞天》《延河》《收获》《野草》等报刊发表评论。散文集《素蓝如瓦》获第五届黄河文学奖、评论集《一川巨流贯风烟》获甘肃省第三届文艺评论奖,长篇小说《支离歌》获第八届黄河文学奖,二篇评论获“傅雷杯”全国文艺评论征文奖。
昆德拉说过,“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青年人不婚不育,父母亲催婚催嫁正成为一种悄然发生的现实存在。面对这种令父母着急、令社会学家费解的现象,青年人自己如何看待?沈月沉的小说《桃花乱落如红雨》从一对留学归国的大龄男女被父母催婚相亲写起,到他们相亲无疾而终结束,时间限制在相亲的那个下午,以二人闲聊式谈话展开故事,用意识流手法带出那些潜藏在他们心灵深处,影响他们情感价值取向的人和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青年的精神现状。
人是欲望的奴隶。反过来,欲望是催人前行的动力。当人的物质欲望满足以后,人便开始追求精神欲望的满足。当下社会的中产阶层,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青年,已经摆脱了父辈对物质欲望的过度追求,趋向于追求内心的平静与安宁,他们宁可选择精神自由的低欲生活,也不愿意与缺乏精神共鸣的异性走进同一个屋檐下建立家庭,于是,都市剩男剩女成为父母心上挥不去的愁,催婚催嫁屡见不鲜。沈月沉的短篇小说《桃花乱落如红雨》就是一篇表现青年人低欲心态的作品。小说中的四个同龄青年相互交集,又彼此独立,他们都是出身中产家庭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存因物质匮乏对心灵造成伤害。相反,他们身为独生子女,生在中产家庭,父母基本能满足他们上学生活的物质欲望。从他们的交谈中可以看出,造成当代中产青年低婚育的原因既有原生家庭的成因,也是他们追求高质量精神生活的表现。
小说以“我”为线索,串联起同时代同阶层青年的共同记忆,道出他们看似千差万别,实则殊途同归的婚恋价值取向。我三十好几,留学归来,被父母催婚,相亲对象是自己的发小。表面上看,“我”与冯月澄门当户对,二人都出身中产家庭,父母都是体制内公务员,都有留学经历——“我”留学欧洲,冯月澄留学美国,他们漂洋过海历经千帆,却没有找到精神归宿。这种外人眼里门当户对的关系并没有成为他们通往彼此心灵的桥梁。二人一见面,“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冯月澄:“你认识虞诗诗吗?”虞诗诗是“我”的发小,也是“我”的执念——每当父母希望“我”找对象结婚的时候,虞诗诗就会从“我”的记忆里复活。留在记忆里的虞诗诗与“我”是两小无猜的清纯模样,虞诗诗的存在治愈过“我”少年时代的孤独与怯懦,她像贴在“我”胸口的一粒朱砂,平时没机会示人,遇见冯月澄这个共同的少年玩伴,一下子撕开了记忆的密码。“我”与冯月澄之间隔着一个虞诗诗,就像隔着千山万壑,以至于二人想表演出同学相亲者应有的亲近,仍然本能地反抗着第三者对他们内心领地的侵袭。
在“我”不时回忆虞诗诗的同时,冯月澄也在回忆着少年时代的玩伴,她不时提出一个又一个少年玩伴的名字,实则是为了避免两人无话可谈的尴尬。小说通过冯月澄的讲述展示了这代青年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潜流暗涌的青春。在外人看来,冯月澄家庭富裕,有留学经历,归国以后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经常跨国出差……但冯月澄与“我”一见面就谈到她看恐怖片是为了解压。从她不停地喝酒,想要一醉方休的状态可以看出,她的内心其实很压抑很痛苦,那份工作并没有给她带来荣耀与成就感,她的朋友圈充斥着“天花乱坠的电影海报”与“惊心动魄的愤青文字”,这说明冯月澄是一个内心有坚守的女孩,然而,现实迫使她不断地放弃自己的阵地,她总是在发出抒写内心真实情绪的文字后秒删。这种欲对现实规训做出反抗,又不得不屈从现实的心态正是她的内心一片兵荒马乱的体现。这个父母眼里的乖乖女,别人眼里的成功者除了工作,基本沉溺于电影与酒精,她熟知各类欧美电影,却不愿意向外人敞开自己的心扉,她在职场上受到压力只得借酒浇愁,她三十好几还没有恋爱对象……一方面她在经济上活得很独立,另一方面她在精神上活得很孤独。她的孤独源于少女时代的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徐紫依的遭遇。
出现在冯月澄记忆里的徐紫依“桀骜而高雅”,“她有美貌,却因为孤僻乖戾的性格时常被人疏远,她也有才华,可她能背《芙蓉女儿诔》也不能帮她通过计量经济学的考试”,造成她性格孤僻乖戾的原因冯月澄只讲了一半,另一半被徐紫依带走。徐紫依能沉着冷静地致父亲于死地,说明她童年在原生家庭受过很深的伤害,他的神经病父亲对她做过什么令她无法原谅,以至于当她有机会看见父亲心脏病犯了以后毫不犹豫地把所有药藏起来,把电话线掐断,把手机拿掉。“最悲惨的人在价值贬值中总是扮演刽子手的角色,而到了最后审判的号角吹响之日,一个没有了任何价值观的人就会成为自取灭亡的世界的刽子手。”(昆德拉语),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弑父是他悲剧命运的根源,男孩的弑父情结是弗洛依德哲学中的男孩心理发展的必经阶段,女孩通常被喻为父亲上辈子的情人,一个青春期的女孩要不动声色地杀死父亲,必是精神上遭受过无法言说的创痛,外表漂亮的徐紫依正是这样一个心里装着巨大痛苦与秘密的女孩。弑父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父亲在她童年时代造成的伤害,但也把她推入伦理与道德陷阱的边缘。当她把这个不能承受的秘密讲给自己的好朋友冯月澄之后,遭到了冯月澄的疏离。父母无法成为孩子最后的避风港,朋友也无法为自己永远保守秘密。冯月澄的离开成为压垮徐紫依心灵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只能独自奔赴大海——“徐紫依最后驾着车从一号公路冲进了海里。”徐紫依的死反过来又成为冯月澄内心挥之不去的幽灵。冯月澄透过徐紫依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父女可以成为仇人,朋友可以成为路人。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她对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缺乏信心。
经济独立、内心孤独、感情幽闭,这不是冯月澄一个人的状态,这是此时代中产阶层青年的共同状态。与冯月澄一样,“我”在欧洲学习生活多年,依然没有可以倾诉的朋友,多年以后心里装的仍是少年玩伴,出现在“我”意识流里的虞诗诗仍然保留着少年的模样,“我”与虞诗诗见证了彼此天真无邪的少年时光,拥有共同的青葱记忆。守住虞诗诗,就是守住心灵上的那一点微光。所以当父亲询问相亲结果时,“我”毫不犹豫地说出要找虞诗诗那样的对象。
在叙述策略上,留学欧洲的沈月沉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影响,采用“同一空间里不同时间并置”的叙述方式,通过故事套故事的形式,展示了现代都市青年的情感困境。在叙述手法上,沈月沉用诗的意象营造诗的意境。桃花一直是古典文学里的对爱情的比喻,《桃花扇》中候方域题诗桃花扇,赠予李香君,并没有得到圆满的爱情。《红楼梦》中林黛玉面对桃花乱落,想到身如浮萍,情无所寄,不觉悲从中来,写下千古绝唱《葬花吟》……沈月沉的《桃花乱落如红雨》从题目到内容都可以看作是当代中产青年的精神世界的隐喻。小说中以桃花比喻少男少女的青春,以桃花乱落比喻经历了青春期的兵荒马乱以后各自破碎的内心世界,桃花一样美好的虞诗诗因为父母辈的爱恨情仇闪电般消失于“我”的心空,桃花一樣美丽的徐紫依弑父之后无法面对内心的暗黑选择了自杀,桃花一样娴静的冯月澄拥有“美、白、富”,却无法拥有一份完整的爱情……“红雨”既是他们命运的写照,也是他们内心世界的投影。桃花乱落既是虞诗诗留在“我”心灵深处的一幅唯美图景,也是青年人命运的隐喻,“我”、冯月澄、虞诗诗、徐紫依……哪个年轻人的青春不是兵荒马乱,哪个年轻人又能找到尘世里的“现世安稳”?小说的最后,“我”与冯月澄平淡分手,徐紫依消失在时间尽头,虞诗诗仍然是一个遥不可企的梦。他们只能在茫茫人海中继续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
《桃花乱落如红雨》是沈月沉的处女作,叙述策略与技巧比较成熟,故事套故事,多线交织,一气呵成,小说提出的问题也会引起读者的思考。但小说中的“我”作为唯一的男性,形象很单薄。小说对徐紫依弑父一事流于叙述表面,缺乏合理的解释,徐紫依对冯月澄的影响也没有进行深入剖析,致使故事与故事之间的联系性不够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