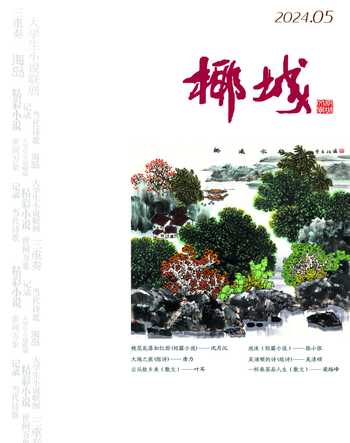叩拜黎山(散文)
作者简介:杨威胜,爱好文学,擅长摄影。先后在报社等多个文化部门工作任职,研究馆员职称。有摄影作品国家、省(市)地比赛中获奖,偶有文学作品发表。1997年被评为“首届海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 2003年被评为“海南省德艺双馨优秀艺术家”、2013年被三亚市政府授予“三亚市优秀专家”称号。
一
弯转曲折的南圣河流过五指山南麓,生我养我的畅好农场就在南圣河畔。我七岁时在农场职工子弟小学读书,班里有许多黎族同学,都是在黎山长大的孩子。班里有位年长我两岁的黎族同学,同学们都叫他“老权”。
农忙季节,学校组织我们到黎村收割水稻。一次,我的手被镰刀划伤,血流不止 ,老权跑到田边扯下一把飞机草,将嫩叶塞进嘴里边嚼边跑回来,从嘴里吐出粘稠的绿色浆液,敷在我的伤口上,几分钟后流血止住了。
我问老权怎么知道飞机草能止血,他给我说:“我们生长在深山,长大还要在山里讨生活,难免遇到各种意外,长辈们就教我们就地取材的自救常识,只要采到对症的草药,都能化险为夷。”
我问:“你们为什么喜欢在深山雨林里安营扎寨?”
老权说:“深山雨林能供给我们吃穿衣食。”
茂密苍茫的原始森林里有无数的河流涧溪、有繁茂的山坡野地、有水草丰美的平滩。树林间有野兽、溪水里有鱼虾、山坡上有植物。树上结的、藤上牵的、土下埋的、溪里游的……都是黎人的食物来源。
深山雨林还有森林树木和竹子藤蔓,都是黎人搭建船形屋、制作桌椅板凳和劳动工具的材料。
黎人依山筑造村庄,傍水搭建峒寨,垦荒山耕田地。他们定居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周边有一道道天然屏障抵御外族入侵,减少台风影响。山水相宜,水草肥美,空气清新,宛若仙境。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念中学时,一个暑期的日子,我们组成五人的“雨林探险队”,由老权当队长,对深山雨林进行探秘。临行前,老权要求我们不穿鞋不戴帽,穿短衣短裤,携带砍刀带上竹篓或挎包。集合时发给每人一条系有绳子的小木棍,绳头末端吊着小纱包,纱包里是盐巴。老权的额头上扎着红布条,藤篓里别着山刀,颇有黎族头领的风范。
“那座山叫‘白雾山,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老权指着远处一座山给我们说,“家有家法,山有山规,进入深山就得按我们黎人的规矩行事。”说话间,走到一棵大榕树下。榕树根部有块很大的黄蜡石,油光铮亮。巨石上有尊土地公神像,鼎里放满了敬香的香炉,三个摆放整齐的酒杯,能看出常有人来此膜拜。
老权神情虔诚,双手合十,对土地神鞠了三个躬,嘴里用黎话念叨了几句。
我们也跟着他鞠躬。
“进入深山雨林会惊动山神,山上的植物动物都有灵性,我们祈祷土地神保佑我们。”老权给我们说。
现在回想起来,庄重的“自然崇拜”仪式,反映出黎族同胞千百年來热爱深山雨林,与其相伴共存、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念。
一条小河呈现在眼前,老权嘱咐大家先把小盐包放在河水里浸泡一会儿。山路越来越窄,茂密的草木遮蔽了路面。老权奋勇当先挥刀砍断挡路的藤木,为我们开路。
“哎呀,山蚂蟥爬到我脚上了。”我的胞弟惊叫起来。
深山雨林的山蚂蟥有“吸血鬼”之称。它们闻到人或动物的气味,就会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攀附到动物身体上吸血。被山蚂蝗叮咬过的伤口流血不止,奇痒难耐。
“别怕,把小盐包往蚂蟥身上拍打几下,它就会掉下去。”老权说。
随着在雨林中的深入,山蚂蟥几乎侵袭了所有人,但都被我们携带的小盐包击退了。
进入深山,不时看到人类活动的痕迹。老权告诉我们,黎族人进山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凡是打上草结、划过刀痕、做了记号的东西都不能随便搬动,更不能拿走。因为,那些东西已有所属。
“注意!”老权喊叫一声,我们立即停住脚步。老权指着一条横在我们头顶的弯竹子说:“看,竹子上缠着一条青竹蛇,它会伤人。”
老权叫大家退后,他跑到竹丛的根部,砍断那根竹子,趁着竹子尚未倒地,老权将带蛇的竹子直接扔下山沟。
我终于明白,老权叮嘱大伙别穿鞋戴帽上山,是黎族同胞长年在深山雨林生活的经验之道。
遮天蔽日的深山雨林是热带动植物生长的天堂,山里珍藏着长臂猿、坡鹿、猕猴、飞蜥、睑虎等野生动物,森林里有根抱石、高板根、古藤缠树、老茎生花、空中花园、树木绞杀等雨林奇观。
我们这些探险队员气喘吁吁,口干舌燥。我提议休息一会儿。老权跑到附近砍下一段手腕粗、丈余长的山藤,把山藤截成五节分给大家。
“这是‘鸡血藤,里面有淡红色的汁液,用嘴对着刀口吸吮,解渴润喉。我们黎人进山,渴了就把这个当水喝。”
老权谈性更浓:“眼前的这棵是大板根树,左边那棵是铁梨木,右边那棵叫陆均松,后面那棵叫香椿木,山藤也很多种类,过江龙、鸡血藤、无根藤,还有红藤、白藤……我背的篓就是用红藤编织的。”
突然,两只山鸟从涧溪水潭中飞出。老权放慢脚步,带我们走近鸟儿飞出的水潭。
清澈的溪水里游动着好多条黑鱼、塘鲺鱼,还有一只山龟,它们正在吞食一种果实的浆液残渣。老权说这种梨形果实是水潭边一种大叶树根茎部结的果实,可以吃,叫“木乃果”。
老权安排我堵截入水口。他和另外两人把水潭的出水口拓宽挖深,加快排流速度。半个小时后,水潭变成浅水坑。我们跳进浅水坑,大鱼都被我们捉进篓子里。
老权说:“中午了,那边山上有瀑布,还有竹林,我们到那里吃午饭。”
同学说:“没碗没锅,怎么吃午饭啊?”
老权走到一个沙滩中间,说:“我们就在这儿做午饭吧。山林防火人人有责,在沙滩上烤鱼,烧竹筒饭,比较安全,但还是要特别小心。”
老权负责生火,他把我们捡来的干竹干柴堆在一起,燃起火堆。火堆四周,用刚砍的生树枝搭起支架。黎族同学用砍刀削掉竹节外的两头,在其一端穿了孔洞,竹筒内灌进山泉水。然后,用一片竹叶卷成漏斗状,将山兰米灌入竹筒中,再将一卷竹叶塞住洞口。
老权将灌好米的5根竹筒放在火堆架上烧烤,用竹签穿过鱼腹,放在木架上方。老权和黎族同学掌握火候,转动鱼串和竹筒。
老权把烤熟的竹筒饭和鱼摆在芭蕉叶片上,给鱼上撒了盐巴。大家开始享用黎家特色的山兰竹筒饭和烤鱼,还有“木乃果”。
“想不想采点野果带回家?现在是橄榄果的成熟季节。”老权用食指竖在嘴唇上,示意大家别出声。从地上捡起一根胳膊粗的木棍,轻手蹑脚地走到一棵大樹下,突然抡起木棍,向大树杆横扫过去,木棍打在树腰间,整棵树剧烈摇晃。顿时,果子噼里啪啦坠落下来,地上堆满青黄色的橄榄果。我也拿起木棍,使出力气敲打树身,却不见有果子掉落下来。
老权说:“我敲打橄榄树的时候它正在睡觉,所以才有那么多果子掉下来。你再敲打它就不掉果子,因为它已经醒了。”原来,第一次敲打落下的全是熟透的橄榄果。第二次敲打,树上挂着的都是生果子,怎么会掉落呢?
谜底揭开,大家会心地笑了。
日已偏西,我们走出深山雨林,告别丛林峡谷溪流。那一次的深山雨林的探险,成为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二
我家所在的生产队旁,南圣河从山坡下流过。河的对岸是黎族居住的毛曼村,有百十号人,整个村子在大榕树和椰子树的浓荫之下,几十间船型茅草屋依山而建。农场职工和黎族同胞隔河相望,共饮一河水。隔河相望的异族兄弟,是深山雨林里唯一邻居,语言不通但和睦相处,见面点头微笑打招呼。
深山的野兽也很多,我亲眼看见山猪闯进我家伙房边的栅栏,用嘴拱出土里的地瓜吃;眼镜蛇溜进鸡笼中吞食小鸡和鸡蛋;山外的野公鸡和我家的大公鸡“决斗”;两群猴子在榕树上打架,打得你死我活,发出凄厉的惨叫。
傍晚,森林里传来各种飞禽、野兽的尖叫声。每到夜晚我都不敢闭眼睡觉,更不敢靠近门窗,生怕有山猪和野猴闯进屋里。我奶奶为了让我不再害怕,特意从工友家要来两只小黄狗,不管什么时候,一有动静狗就会叫,野猪野猴再不敢到我家来了。
农闲时节,我看见许多黎族村民,拿着渔网、鱼篓、鱼笼、鱼叉、还有木棒,声势浩大地沿河直下,在水里横站成一排,前面的人一边高声喊叫,一边用木棒击打水面,驱赶河里的鱼群,整条河人声鼎沸河水浑浊,鱼儿被惊吓得东游西窜,跳出水面。村民们则用手中的捕鱼器具,捕捞鱼儿。
我很小就看到黎族猎人扛着火药枪,身背弓箭,牵着猎狗进山打猎。回来时,抬着山鹿或黄猄,拎着山鸡或狐狸,枪管上挂着布谷鸟或毛鸡。猎狗跑前跑后嗷嗷直叫,向人们炫耀战果。
我家的大黄狗是我家的忠实朋友,天天陪着奶奶和我进进出出,野兽再也不敢来骚扰惹事了,我晚上也能安稳入眠。大黄狗通人性,我父亲到场部开会,晚上沿着山路步行回家,大黄狗隔着两公里都能嗅到父亲的气味,兴奋地用前爪和叫声,报告父亲回来的消息,然后跑去迎接父亲。
有一天黄昏,一队黎族猎人带着捕获的猎物从我家门口路过。我家的两条大黄狗猛然发起冲锋,一个猛扑把猎狗撞翻在地,双方撕咬起来。我家的大黄狗身高体壮,丝毫不输那些瘦小的猎狗。奶奶急忙从伙房跑出来,大声训斥大黄狗。在黎族猎手和我奶奶的阻止下,它们才被拉开,一场狗斗得以平息。一位长者模样的黎族老猎人跟我奶奶搭话,奶奶听不懂黎话。老猎人取下一只布谷鸟递到我奶奶手里,打着手势指着我说了许多,意思是让奶奶将它煮了给我吃。
两年后,我家那条母狗产下四条小狗。小狗毛色金黄,肚皮泛白,耳朵直竖,眼睛晶亮,毛茸茸的憨态可掬,很是讨人喜爱。
一天晌午,那位黎族老猎人路过,看见我家的几只小狗,就爱不释手地抚摸小狗。他抱起小狗对着狗嘴吐口唾沫,看小狗是否舔食唾液。黎族猎人挑选猎狗非常挑剔,不但要看狗的外形是否威猛,还要看它是否具有超常的嗅觉。之后,老猎人找到我奶奶边说边比划着。恰好一位邻居能听懂,告知我奶奶,他想抱养一条小狗。
我奶奶爽快地答应了。但黎族老猎人没有当即抱走小狗,只是给其中一条雄性小狗做了记号。翌日一早,老猎人抱着一只大阉鸡和一袋山兰米,放在我奶奶面前,然后抱起那条做了记号的小狗离去。
我早有耳闻黎族同胞会以物易物交换东西,这次,亲眼见证了全过程。
如今,深山雨林已被划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许多动植物列入国家保护物种。黎族同胞告别了下河渔猎上山狩猎的生产方式,维护青山绿水。毛曼村黎族同胞的船型茅草屋,如今也改造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农舍或民宿。
三
这天,老权打来电话,说他下个月农历初十搬新楼,请我过去喝酒。放下电话,老权的形象又在我脑海里闪现。
1973年,老权父亲因病去世,他高中毕业就回到黎村务农,与本村一位姑娘结了婚。我高中毕业在农场参加工作,后来调到三亚学医。
四年后,我回农场探望父母,想起老权,徒步到黎村找他。老权家没上锁,但屋内空无一人。老权家的屋子是落地船型屋,屋顶的茅草流泻而下,几乎挨着地面。屋门用木板框和竹片制作,泥巴墙边堆放着不少格木桁条。
老权出现在我眼前,皮肤黝黑,头戴草帽,上身套布褂子,敞开胸膛,卷着裤腿,挑着一担箩筐,腰间别着竹篓,篓里还插一把山刀,一身典型的山里农民打扮。
我要和老权握手,他说:“我们就不握手了,你看我这手又黑又脏”。
我一把握住老权的手:“你说什么呢,我还能嫌老同学的手脏?”
看着他布满老茧的手,脸上的皱纹,我感觉到老权生活的艰辛和不易。
一名孕妇和两个小孩走到跟前,老权介绍说:“这是我老婆,这两个是我的孩子。”
我说:“才几年工夫,你居然弄出那么大的动静?”。
老权说:“农村夜里没事做,就搞生孩子运动。”
走进屋,室内黑漆漆,摆设十分简单,正室有一口大水缸,两个水桶和一条扁担;旁边有三块石头垒的锅灶,一口大铁锅架在石头上;灶台、墙壁和竹架上挂着自制的葫芦瓢、椰子殼汤勺及陶瓮;炉膛中还有火星,几根手臂粗的长木柴冒着丝丝青烟;铁锅盖是用葵叶和竹片绑夹做成。锅里有大半锅熬熟的猪食。屋内飘着烟熏、潲水、汗臭混杂的味道。
老权媳妇把铁锅里的猪食往桶里舀,挑出去喂猪,临出门时老权在她耳边嘀咕了几句。
老权搬来小木凳让我坐,砍了一根甘蔗递给我:“我们口渴就喝缸里的水,怕你喝不惯,吃甘蔗解渴吧。”
老权忙着刷锅煮水,从箩筐里拿出雷公笋、芋头竿、地瓜叶,还有小螃蟹、小泥鳅和田螺等,一边忙活一边说:“你能来我家是看得起我,中午没什么好招待,就尝尝黎家的野菜。”说话间,老权老婆提着一只老母鸡进屋,说:“这只母鸡正在下蛋,你真舍得杀它?”
老权瞪了老婆一眼,说:“老同学那么远来咱家,杀只鸡招待不应该吗?”
我十分过意不去,劝老权刀下留情,留着老母鸡下蛋给老婆孩子补补身子。
老权二话不说一刀下去,眼看母鸡挣扎几下就不动了,接着鸡被放进锅里的热水中。
鸡煮熟了后,老权取下墙上的簸箕,垫上一块木板,拿起菜刀就剁鸡。他老婆到外面割回几片芭蕉叶,铺垫在簸箕上,把剁好的鸡肉和煮熟的野菜,放在芭蕉叶上,搬出盛山兰酒的陶瓮,取出两根竹制吸管。
我看着坐在一边的孕妇和孩子,实在不忍心吃那些鸡肉,吃了几口野菜就放下筷子。
去年的农历三月初十,我驱车开进老权村寨口,一个黎族大力神图案装饰的门楼映入眼帘,上书“梦里黎乡欢迎您!”
我把车开到老权的果园,老权出来迎接:“我刚接到村里人的电话,猜想就是你,快进来。”
我从后车厢搬出电饭锅交给老权,老权乐呵呵地说:“这些电器我们都有了,请你来参加我的入住新楼仪式,补偿当年你在我家吃的那顿饭。”
“当年你把家里生蛋的老母鸡都杀了慰劳我,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哩。”
老权说:“当年我家的条件你都看到了,全家连个砧板、饭桌都没有,根本就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招待客人。当时我就想,等条件好了一定好好招待你。”
老权的新居是一幢三层半高的楼房,外墙抹米黄色的涂料,显得崭新靓丽。人字形的门楣造型,屋檐用绿色琉璃瓦装饰,还有四扇不锈钢金属大门。走进大厅,长短沙发、茶几、供台一应俱全,客厅上方悬挂一串吊灯,背景墙是50寸平板彩电,厨房和洗浴间都配置全新的厨具和卫浴洁具。
老权和老伴住在一楼。他陪同我逐层上楼参观,两个儿子分别住二、三楼。老权说:“老威你看,黎村如今都建成水泥结构的平房或楼房!”
“开饭啦,漱酒啰!”没过一会儿,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彻山谷。楼下搭的帐篷,摆放十几张大围桌,桌面摆满大菜:红烧猪肉、尖椒牛肉、梅菜扣肉、清蒸鱼、白切鸡、烤乳猪、五指山野菜等,共十二菜一汤。白酒、啤酒、山兰酒样样齐备。
老权的大儿子是当兵出身,也是现任村长,端着酒杯说:“今天是我家乔迁新楼的大喜日子,我代表我父亲和家人,谢谢各位的光临。感谢改革开放,让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