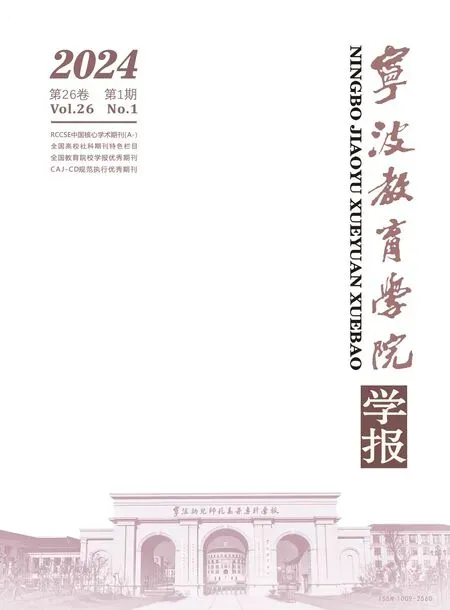陶行知儿童教育价值取向的三重意蕴阐释
陶志琼,黄 鑫
(1.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2.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陶润幼儿园,浙江 宁波 315211)
陶行知作为现代中国儿童教育实践的开拓者之一,汲古开今、兼容东西,积极推进儿童教育的现代化、科学化与中国化的发展道路。对陶行知儿童教育的已有研究揭示了他在办学实践中呈现的人本化价值倾向[1-2],全人生儿童观是从实用主义教育到生活教育的跨越[3-4]。陶行知的儿童教育实践离不开价值引领和价值取向。所谓儿童教育价值取向,是指儿童教育主体以自身的儿童教育观念为指引,为满足自身对儿童教育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儿童教育实践层面的行动偏好。儿童教育价值取向一方面是主体所持有的儿童教育观念与需要,另一方面是在观念与需要的驱动下的行动方向。正是基于价值取向的引领,陶行知从实践生发出的儿童教育理论仍为时人所认可与化用。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对陶行知儿童教育价值取向予以阐释。
一、儿童本位的价值取向:创造儿童的世界
自人类诞生以来,儿童便客观存在着,这种存在不仅是肉身式的存在,更是精神式的存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成人对于儿童的认识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人都不曾完全地认可儿童的存在价值,往往将儿童视作小大人或成人的附庸,使得儿童的生命价值受到不同程度的遮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迎来儿童的“发现”,带来儿童本位的价值思潮,推动教育的现代化转向[5]。陶行知是持儿童本位价值取向的代表之一,他在以儿童为本的观念指引下,希望通过教学做合一的方式培养创造性的儿童。他汲取了杜威“儿童是中心”的思想,并适当地加以改造。陶行知强调如其所是地了解儿童,在洞察的基础上开展教育。这种教育以儿童的生活为本源,在教育的过程中充分解放儿童的主体性,最终由儿童自己动手创造属于他们的世界。
(一)以儿童为本的价值观念
在陶行知看来,儿童是鲜活的生命体,他们天生爱玩爱闹爱问,有着独特的自然天性,不可简单地与成人画上等号。儿童的本真样态值得尊重、值得了解,应还原式地看待他们。“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6]545,“儿童应该是快乐的”[7]464,他们身上所携带的童性是可贵的,不应盲目地让其学做小大人,致使其在充斥着“谣言、恐怖、享福、书呆、残酷和奴隶”的地狱中挣扎[6]546,在痛苦中成长,沦为可悲的小老翁。儿童并非成人,但本质上也是人,只是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而已。由此可知,我们须从根本上化除对儿童的轻视乃至漠视,平等地对待儿童。陶行知所谓的儿童从来都是儿童大众,“我们应承认儿童的人权”[7]464,亦即承认儿童大众的独立人格与主体地位。
陶行知将儿童比作人生幼苗,并强调“六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8]70,由于各个方面居于萌发的状态,若“培养得宜,方能发荣滋长”[8]115。因此,儿童能否顺利地由幼苗生长为大树,关键在于此阶段的生活是否得到了良好的关注与启蒙。换言之,教育必须认可儿童期在人生序列中的黄金属性,把握其蕴含的特殊且丰富的教育性价值,植根于儿童真实的生活,了解儿童真实的需要,据此提供合宜的爱与培育。儿童身上携揣着伟大的能量,但这种潜能有待成人的激活才能充分释放。激活意味着成人放弃对儿童的圈禁,允许解除儿童身上的各式桎梏,真情实意地为他们营造一个能够舒展想象与发挥创造的空间,“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7]3,这是成人与儿童的携手相长。成人如能复归童心,孩子般地加入儿童的队伍,那是再好不过的。唯有儿童的双手与大脑获得解放,在双手与大脑的协同运用中才能调度自身的能动性,继而真正迎来崭新的儿童世界。
(二)以培养“创造”的儿童为价值需要
陶行知认为,“社会因循而民气不张,政府因循而国魂不振”。他主张发展创造的教育,培养创造的儿童,以此改变旧习。首先,陶行知认为儿童身上蕴藏着创造的潜能,“儿童不但有力量,而且有创造力”[8]367。儿童虽小,但是创造的潜力却不小,有待激发与转化。教育在于根据儿童的实际生活,通过激活与解放儿童的创造力,让儿童全身心地发挥创造的力量从事创造性的工作。陶行知认为既然儿童拥有创造力,下一步便需要将儿童的创造力予以解放:一是解放头脑,使其有漫想的自由;二是解放双手,使其有动手操作的权利和条件;三是解放嘴巴,使其有表达的自由;四是解放空间,使其突破学校的束囿,延展至自然的世界;五是解放时间,使其拥有闲暇与嬉乐。陶行知对于培育“创造”儿童的需要,体现了他对创造性精神、创造性能力的尊重,这是时代发展的价值诉求。培养“创造”的儿童便是将儿童从封建迷信的桎梏中解救出来,让儿童在手脑并用中实现劳力与劳心的结合。培育“创造”的儿童的价值需要不仅体现了陶行知对于创造力的价值肯认,也体现了其对儿童主体性发展的倡导。
(三)以教学做合一为价值行动方向
陶行知通过“教学做合一”的方法与路径,真正落实培养创造的儿童的需要,并在教学做合一中始终贯彻以儿童为本的价值观念。陶行知吸收、内化与改造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从做中学”,提出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为准则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认为教育应该与生活相融合,或者教育应回归到生活的世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便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教育不应与真实的生活脱轨。眼及之处均是生活,生活与教育是融通的关系,生活本就是教育。教育如生活般遍及各处,不必将教育拘泥在狭隘的校园之内。教育应使儿童通过“教学做合一”达致“劳力上劳心”,这是陶行知对试验精神的坚守,注重实践与动手的价值,在知与行的关系中,强调行动胜于知识。人的实践本质就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是彰显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的过程。教学做合一既是教育的方法,亦是生活的方法。教学做合一强调“教的方法应该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应根据做的方法,事情怎么做就怎么学,怎么学就怎么教”[8]87。先生是在做上教,学生是在做上学,无论先生还是学生,都强调“做”。“做”指的是“劳力上劳心”,是身心的充分结合。唯有动手又动脑,儿童才能逐渐获得自身的生活力,运用生活力创造自己的生活,逐步蜕变为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与艺术的趣味”的真善美齐全的“活”人。
二、科学本位的价值取向:以科学之方,新教育之事
“科学是人类认识并改造世界的最有力的手段和最伟大的工具,是人类业已形成的、特有的生存发展方式,科学本身就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标志,其发展本身就意味着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9]309中华民族正是在炮火的洗礼中醒觉发展科学技术、弘扬科学精神的重要性。陶行知认为我国教育发展在形式上确有改观,但“教育进化之根本方法”与“智识进化之根本方法”却鲜有问津与钻研[8]209。这就使教育切断了对真理的追逐与探寻。因此,教育的土壤上亟须播撒科学的种子,以科学精神作为价值导引,造就科学的儿童。陶行知秉持科学本位的价值取向,致力于实现儿童教育的科学化,在教育现代化为主导的价值观念指引下,为满足造就科学之孩子、科学之中国的价值需要,走上了一条立足于儿童大众的科学“下嫁”之路。
(一)以教育现代化为主导的价值观念
在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陶行知无疑作出了特殊贡献,他对现代化不仅有前瞻性的价值认知,认为现代化是“大众的出路”,是“民族与人类整个的出路”[10]492,与此同时还通过现代化的教育推动中国的现代化。1916 年,陶行知在英文著述中首用“现代”一词形容教育,他提出“现代教育者”与“现代教育学”[11]。1934 年,陶行知首次就“中国现代化”的命题展开了系统阐释,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全方位、全人和全过程的现代化,构成三位一体的关系:一是“整个民族现代化”,二是“整个生活现代化”,三是“整个寿命现代化”[12]518。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改造有赖于教育。“我们是现代的人,要过现代的生活,就要受现代的教育。”[10]403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行的研究会上曾倡导“以科学之方新教育之事”[8]231,极力主张通过科学试验的途径改造中国的传统教育。陶行知认为真正现代化的教育应处在与时俱进的动态变化发展之中,既要生长在本民族文化土壤之上,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植根于儿童生活的本真面貌,还要融会贯通外来思想和本土传统,与世界的整体趋势相接轨。在教育顺应现代化的道路上,科学化势必是教育价值追求的应有之义。
(二)以造就科学之孩子与科学之中国为价值需要
五四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与民主成为两大基本价值追求,“科学”一度成为现代文明与人类进步的风向标。陶行知的教育实践始终关注着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他清醒地认识到科学对于国家与民族的重要性:“科学是工业文明的母亲,要想创造合理的工业文明,必须注重有驾驭自然的力量的科学”[10]269。中国若想成功地由农业社会转型过渡至工业社会,需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科学技术要取得进步,就要提升国民的科学素养,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将科学变得如同阳光、空气一般普遍”,使得大众能不断提升实践与创新的能力,树立求真务实的新风新貌。陶行知认为儿童的培育关乎民族与国家的未来,“有了科学的儿童,自然会产生科学的中国和科学的中华民族”[6]627。“科学教育应从儿童时代下手”[13]。“科学要从小抓起,我们要造就一个科学的民族,必须在民族的嫩芽——儿童上去下功夫培植”[14]253。陶行知尤为关注儿童的科学教育,他认为儿童教育的目标在于培育科学的儿童,进而造就科学的中国。唯有对儿童施予科学的教育,激发其对科学的兴趣,才能在中国培育出如爱迪生这般的杰出科学人才。“科学的训练应该从幼稚园便开始”[10]577,较之成人,儿童在科学方面的兴趣更强,更具备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将儿童视作科学教育的重要对象,造就科学的孩子与科学的中国,体现了陶行知价值需要的人本性与民族性。
(三)以科学“下嫁”为价值行动方向
20 世纪30 年代,陶行知发起了科学“下嫁”运动,他将科学教育的重心聚焦在儿童身上,将儿童看作科学救国的重要起点。陶行知陆续发表了《科学的孩子》《培养科学儿童以利创造科学中国之始基》等文章,逐步构建起科学教育的理论体系。在他看来,中国科学教育之匮乏主要受制于传统教育的诸多弊病,培养出的是不动脑不动手的书呆子。因此,他于1931 年便积极投身于科学普及教育。
首先,创办科学园。陶行知在《科学的生活》中指出:“儿童理应过上科学的生活,应亲近生活、亲近自然,在亲近之中发展好奇、开展探索,发扬科学之精神。”他在《科学的孩子》中提出“现在是科学的世界,科学的世界应该要有科学的中国”[10]411。科学的世界、科学的中国应该由科学的儿童去创造。其次,主编《儿童科学丛书》。这些书的内容广泛,包括生物、地理、天文、生理卫生等内容,引导儿童在阅读中养成科学的习惯、焕发科学的精神。陶行知认为仅有科学知识不可行,还应将其付诸在亲身行动之中,整合动手、动脑与动心。再次,成立儿童科学通讯学校。陶行知携手陈鹤琴等人于1932 年正式成立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该校宗旨是“造就科学的儿童,造就科学的民众,使中华民族成为科学的民族,适应科学的世界”[10]437。该校主张科学训练应从小抓起,向广大的儿童普及儿童科学知识。
三、民族本位的价值取向:小朋友是民族的未来
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引发了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使命。作为教育人的陶行知给出了教育与社会改造相结合的方案,走上了通过教育复兴民族的道路。儿童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民族的未来由其谱写,陶行知希望通过培育科学的、创造的儿童,造就新一代国民,进而发挥教育反哺社会的济世之用。“民族从本质而言是一种文化认同意义上的想象共同体”[15],民族独立的根本是文化独立,而教育是文化保存与延续的重要机制。面对儿童教育界病急乱投医的乱象,陶行知认为盲目效仿的教育遗失了民族根基性,主张儿童教育做中国化的改造,秉持民族本位的价值取向。
(一)以教育救国为主导的价值观念
陶行知从救亡图存的高度提出发展教育的重要性,是其时内外交困的中国之必须。如果说人是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的中心,那么儿童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群体。陶行知将儿童的主体性建构与民族、国家的塑造结合起来,认为儿童教育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之一。陶行知自幼便表现出爱国、报国的志向,15 岁那年他在学校宿舍的墙壁写下:“我是中国人,要为中国做贡献。”[16]他在《共和精义》中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8]189陶行知曾向友人坦言:“余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17]1918 年,陶行知演说道:“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8]218在陶行知看来,“教育是一种武器,是民族、人类解放的武器。”[7]303若想求得民族与人类的解放,势必要扛起教育大旗,发挥教育的力量。
陶行知认为,中国社会发展滞后的根源在乡村,尤以乡村教育之不振为关键所在,若想改造广大的乡村地带,教育无疑是最有效、最彻底的方式。“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8]85乡村教育“离农”取向过甚。那么,“什么样的教育更适合乡村生活的实际”,而不是“如何通过教育将儿童抽离乡村”[18]。在乡村教育的改造中,“小学教育是建国之根本,幼稚教育尤其是根本之根本”,他认为“向儿童瞄准”是当务之急。若“不用全副目光、精神向着小学或幼稚园瞄准”,那么日后的教育势必举步维艰。陶行知教育救国的价值观念确立了一种乡村的维度,将乡村教育的改造提高到救亡图存的高度,并遵循着自下而上的价值逻辑路线。陶行知强调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具有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动性与创造力。
(二)以普及儿童教育为价值需要
陶行知认为儿童教育应“使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6]95,将儿童教育的普及作为价值需要。儿童教育理当顺应工业生产之需要,解放广大妇女群众的生产力,使其有机会走向工作岗位。当时本就贫乏的教育资源集中于城市,为贵族阶层所独享。陶行知疾呼广设幼稚园,切实地办学,切实地惠及儿童、惠及儿童的家庭。以1927 年《乡教丛讯》创刊为标志,陶行知正式投身乡村教育的推广,“为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1930年以前,陶行知以传统视角看待教育的普及。1930 年以后,陶行知转换视角,认为教育的普及应着眼于“整个民族的现代化,整个生活的现代化,整个寿命的现代”[6]33。由此可见,陶行知所主张的普及教育是一种现代化的普及,普及的是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教育。1934 年,陶行知在《普及教育运动小史》中指出,普及教育的立足点应该在农村,通过教育获得科学知识的补足,进而实现国民的现代化[6]95。1931 年至1935 年,陶行知发起了普及教育运动,其儿童教育思想获得了丰富与发展。一方面,陶行知首创“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看见儿童的潜能,发扬儿童的力量,将儿童与普及教育、民众教育有机联系起来。另一方面,陶行知在上海成立了“山海工学团”[14]302。普及教育不仅是纵向上历时性的全人生教育,更是横向上共时性的全面教育,是一种纵横交错立体化的普及。
(三)以中国化、平民化和省钱化为价值行动方向
我国的儿童教育尤其是低龄段的幼稚教育,自清末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附有较为浓厚的洋化气息。面对此象,陶行知主张及时止损并加以修正。挣脱洋化的枷锁,但是对于“真知识”的输入表示“竭诚的欢迎”[7]303。陶行知认为,别国先进的办学模式和教学经验,有其生长的文化土壤与经济基础,不能照搬照收。由此,陶行知致力于探索立足于中国国情、贴合中国广大儿童生活实际的教育。陶行知指出国内幼稚园的三种弊病,即“外国病、花钱病和富贵病”[8]71。陶行知立足弊病有的放矢地提出了破解之道,以中国化治疗外国病,以平民化治疗富贵病,以省钱化治疗花钱病。
陶行知认为,儿童教育在观念层面上,一是应提升对于儿童的价值认知。儿童作为个体生命的初始阶段,无论是生活还是教育都是十分重要的,均需获得细致的关爱与良好的引导。二是破除阶级偏见,讲求受教育权的平等,将教育献给全社会的儿童。教育事业是公共属性的,理应惠及所有人。教育应向所有孩子敞开,承担起“运用好孩子化坏孩子”的教化之用[8]115。在实践层面上,一是创办中国的、省钱和平民的儿童学校。工厂与农村是最为薄弱的环节,幼稚园要推广进厂运动与下乡运动[8]93。陶行知发出“征集一百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呼唤[8]86,正式确立通过乡村学校来改造乡村社会的观点。陶行知携手陈鹤琴、张宗麟组织中国幼稚教育研究会。1927 年陶行知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乡村幼稚园,即南京燕子矶试验乡村幼稚园。陶行知认为乡村幼稚园的目的在于“谋幼稚儿童之幸福,并补助家庭教育之不足”[12]242。二是转变师资培育的模式。教育普及倚赖师资力量的保障,可以灵活采用两条途径培育师资:大力创办幼稚师范学校,“造就能与乡村儿童妇女共甘苦,以谋求乡村儿童妇女幸福之增进的幼稚园教师”[10]324。通过“艺友制”,即“先行先知者在做上教,后行后知者在做上学,”实现师友间的“共教、共学、工做”[10]476。
四、结语
当前,我国儿童教育的发展正朝着科学化、人本化与普惠化的高质量方向迈进,向着“更好”前进。向好的过程中势必交织着多样化的价值诉求,甚至可能陷入价值抉择的迷惘。陶行知所处的时代虽已离我们远去,但关于价值本源、教育本质的理想认识却存有相似性与联系性。“思考过去的事就意味着在世界上深耕、扎根,并因此而安身于世。”[19]陶行知的儿童教育价值取向对我国当前的儿童教育发展依然有着启迪的意义:学习与继承并举,最好的办法是在继承中发展。通过注入新鲜血液,让教育获得更新与巩固,在新的时代生存、生长。无论是儿童教育理论工作者还是儿童教育实践工作者都应及时更新儿童教育价值观念,合理化、规范化儿童教育价值需要,立足于儿童教育的育人本性并兼顾时代的现实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