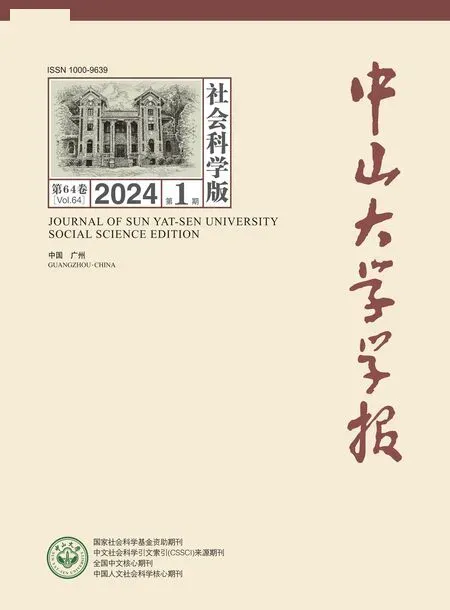谢林与黑格尔艺术哲学中的“象征”之争 *
先刚
在我们进行相关论述之前,有必要首先澄清“象征”概念的基本含义。根据《哲学历史词典》的考据②Vgl.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Unter Mitwirkung von mehr als tausend Fachgelehrten herausgegeben von Joachim Ritter und Karlfried Gründer, Basel: 1984. Bd.10, S.710 ff.,这个词语起源于希腊语的“symballein”一词,意为“嵌合”或“配合”,其核心意义在于两个东西的“合体”或“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一方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某种意义上的在场,而我们因此能够通过一方而认识到另一方。比如柏拉图用来描述爱情的那句名言,“每个人都经常在寻求自己的另一半”③[古希腊]柏拉图著,王太庆译:《会饮》191d,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2页。,其中谈到的“另一半”(symbolon),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象征”一词。但恰恰在这里,“合体”或“一致”又分为两种情况,因为它既可能指不同事物之间的一种本质性的、必然的结合,也可能指一种人为制定或约定的、部分的、偶然的结合,而在后面这种情况下,“象征”又引申出“比喻”“暗号”“标志”“记号”“符号”等日常通用的含义①比如在汉语学界的卡西尔研究和胡塞尔研究中,本文所说的“Symbol”经常也被翻译为“符号”,但严格说来,真正与后者相对应的原文概念是“Zeichen”。在我们看来,“符号”的译法强调的是不同事物的人为制定的、偶然的结合,它和“象征”的译法本身没有对错之分,至于两种译法之间的取舍,应当取决于哪一种译法更符合哲学家本人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想要表达的思想。最近山东大学卡西尔专家梁乐睿教授在和我深入讨论之后,已经决定在他的卡西尔译著中把“symbolische Formen”这个核心概念译为更符合哲学家原意的“象征形式”,而不是译为“符号形式”。。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谢林与黑格尔对于“Symbol”的理解大体上就是分属上面所说的两种情况,尽管如此,在黑格尔那里,“Symbol”绝不是一种像符号那样简单粗陋和偶然随意的东西,而是精神的一种必然的、哪怕不完满的呈现方式,因此它仍然是“象征”,而不是“符号”。
一、象征在哲学尤其是艺术哲学中的基本意义
正如前面指出的,“象征”的关键在于两个东西——尤其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东西——的结合或一致。在哲学的层面上,这个概念立即与“思维与存在是如何一致的”“思维与感性如何结合”之类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里就遭遇到了这个困难。也就是说,当他通过先验演绎证明了范畴或纯粹知性概念是全部经验性直观(甚至一般的感性直观)的必要条件之后,仍然面临一个问题,即范畴与直观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前者仅仅属于思维的领域,绝不可能出现在后者之中,既然如此,怎样才能够把前者应用于后者,或者说让二者真正结合起来呢?比如,虽然我们知道“因果性”范畴是指“原因”和“结果”的必然结合,但这些全都是抽象的概念,只能被思考,而我们在直观中并不能看到因果性本身(就像休谟已经指出的那样);因此,只有借助于一个第三者,即所谓的“范型”(Schema),抽象的概念才能够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②Kants Werke, Akademische Textausgabe, Band III, Berlin: 1968, S. 134, S. 469.。比如我们只有借助于因果性范畴的范型(“不同事物按照一个规则在时间上先后存在”),才直观到一个事物是原因,另一个事物是结果。简言之,康德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感性事物(直观)—范型—概念”的模型,范型在其中扮演着枢纽和联系者的角色,它把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总是能够一方面从感性事物还原到概念,另一方面从概念过渡到感性事物。在《纯粹理性批判》前面的“原理分析论”里,康德一开始只是用形而上演绎的方式“找到”了各种范型,而在该书后面的“先验方法论”里,他才指出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建构”(Konstruktion),即“先天地呈现出一种与概念相吻合的直观”③Kants Werke, Akademische Textausgabe, Band III, Berlin: 1968, S. 134, S. 469.。这种吻合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一体化”,而当康德把范型称作“想象力”的产物时,就已经揭示出这个概念术语的深刻意蕴,因为德语的“想象”(Einbildung)在字面上恰恰是“一体化塑造”的意思,因此它不是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意指胡思乱想,而是特指不同性质的东西的结合或一致,相应地,“想象力”也就是指一种能够突破鸿沟和界限,把性质迥然不同的事物结合在一起的能力。
但需要指出的是,康德在这样做的时候,给出了一个限制。因为在康德那里,“概念”本身又分为经验概念、纯粹知性概念(范畴)、理性概念(理念)三个层面,而在他看来,只有前两者才能够与感性事物或直观结合,反之理念仅仅是一种只能予以思考,却不能真正加以直观和认识的东西。一方面,在《判断力批判》第59 节,康德明确指出:“要展示我们的概念的实在性,永远需要直观。如果是对应于经验概念,那么直观叫做实例(Beispiel)。如果是对应于纯粹知性概念,那么直观叫做范型(Schema)。如果人们甚至要求理性概念亦即理念……也展示出客观实在性,这就是追求某种不可能的东西,因为根本不可能有对应于理念的直观。”④Kants Werke, Akademische Textausgabe, Band V, Berlin: 1968, S. 351.但另一方面,康德并不否认,或者说甚至完全承认,从理性自身的本性来看,人们永远摆脱不了这个追求,即企图直观理念,展示出理念的客观实在性。因此康德又指出:“一切生动呈现作为感性化都是双重的:要么是范型式,即先天地给出知性概念的直观,要么是象征式,即为理性只能思考却没有对应的感性直观的概念提供这样一个直观,通过这个直观,判断力的处理方式与其在范型化里观察到的东西仅仅是类比关系,亦即仅仅就这个处理方式的规则而言,不是就直观本身而言,随之仅仅就反思的形式而言,不是就内容而言与之相一致。”①Kants Werke, Akademische Textausgabe, Band V, S. 352.在这里,康德第一次提出“象征”的概念,并且把它与“范型”对立起来:二者都是为了让先天概念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但范型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的呈现,而象征却仅仅是一种借助于类比的、间接的呈现,它严格说来只是效仿一个规则(Regel),即“概念可以应用于一个感性直观的对象”这一规则,但并没有真正让理性概念(理念)成为这样一个对象。也就是说,康德的结论是:理念不可能呈现于直观——除非它只是以间接的方式(通过类比),仿佛呈现于直观。
以上的铺垫叙述是希望表明,康德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尝试以深刻思辨的方式打通概念与直观之间的联系,并且探讨其各种联系方式,而不是像之前的哲学家一样要么武断地主张、要么武断地否认这种联系。但囿于康德哲学本身的框架,这种联系是不彻底的,尤其是最高理念与直观的联系,仅仅被看作一种虚拟的、仿佛如此的联系。谢林和黑格尔作为康德的后继者,正是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完成思维与存在的真正的同一性和一致性。两位哲学家的相关努力不仅体现在他们的形而上学、认识论、自然哲学和法哲学的领域,同样也体现于他们的艺术哲学。因为从最一般的层面来看,谢林和黑格尔不但打破了康德在“概念”和“理念”之间划出的鸿沟,把全部概念都看作理念,而且专门用艺术哲学去讨论感性事物和概念之间的独特的嵌合或一致,而从具体的层面来看,艺术哲学讨论的就是:艺术如何以客观的、感性的方式呈现出理念。
关于这一点,两位哲学家对“美”的界定给出了最明确的答案。在谢林那里,思维与直观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也被刻画为在无限者—有限者、观念东西—实在东西、普遍者—特殊东西、理念—事物等名目下相互对立的东西,而艺术并不是像哲学那样通过认识活动而把后者完全消融在前者之内,而是通过一种生产活动来保持二者的共存,但不是一种对立式或分裂式的共存,而是一种交互融贯的和谐共存,即二者的“一体化塑造”(Ineinsbildung),而这就是“美”。正如谢林指出的:“当概念本身作为无限者进入有限者,并且以具体的方式被直观到,那里就设定了美。”②[德]谢林著,先刚译:《艺术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3,44页。在另一处文本,谢林又说道:“美是实在东西和观念东西的一体化塑造,并且在一个映像中呈现出来。”③[德]谢林著,先刚译:《艺术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43,44页。在这些文本中,美都是立足于一个被直观到的感性事物或实在东西,而概念已经融入到这个东西之内。就此而言,从宽泛的意义上来看,谢林所说的“美”就是一种象征,因为它代表着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的结合或一致。
在黑格尔那里同样也是如此。黑格尔在把概念等同于理念时,专门加了一个说明:“只有当下出现在它的实在性里,并且与这个实在性结成统一体的概念才是理念。”④[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第135页。实际上,黑格尔无论是在讨论概念还是在讨论理念的时候,都始终强调它是一个统一体(以区别于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抽象空洞的“概念”),而这个统一体的定在(Dasein)⑤朱光潜把“定在”一律翻译为“客观存在”,虽然这个译法在美学的语境里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但严格说来,“定在”作为黑格尔的一个核心概念不应当被这样消解掉,而且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完全不同于“客观存在”。就是理念的客观方面或实在方面,是可以以感性的方式被直观的。因此从宽泛的意义上来看,黑格尔哲学同样是立足于一种象征的关系,即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的结合或一致,而他对于“美”的界定尤其明确地表现出这一点:“当真相在它的这种外在定在中直接呈现于意识,而且它的概念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时,理念就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因此美可以被规定为理念的感性映现(sinnliches Scheinen)。”①[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 卷,第142 页。朱光潜把这里的“映现”翻译为“显现”,不甚确切。因为黑格尔在其逻辑学里明确区分了这两个概念,即“映现”(Scheinen)强调的是内外两个因素的勾连关系(这才符合黑格尔对“美”的定义),反之“显现”(Erscheinen)主要强调的仅仅是外在因素这个方面。
简言之,经过康德的奠基工作,象征所指代的那种关系在谢林和黑格尔那里不但是一般哲学的基础,更是他们的整个艺术哲学的立身之本,并且体现出他们的艺术哲学在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我们接下来就会发现,两位哲学家对于象征的具体理解和评价很快就分道扬镳了。
在境外流通的中国古代货币不止一种,每一种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通常都是那个朝代最出色的货币。比如汉“五铢”钱,钱文为“五铢”,篆书横读,光背,直径26毫米左右,穿径约10毫米,重如其文,重量以3~4克者居多,少数的超过 4克,大小轻重适中,形制美观,合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便于携带,特别是外郭的采用可以保护钱文,不容易磨损,因而在汉武帝以后的西汉、东汉、蜀、魏、晋、南齐、梁、陈、北魏、隋等朝代均有铸造,使用时间长达739年。“五铢”钱成为我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铸造流通使用时间最长、最为成功的长寿货币。
二、象征在谢林艺术哲学中的意义
刚才已经提到,康德在谈到先天概念与直观的贯通方式时,把范型看作概念的直接呈现方式,把象征看作概念的间接呈现方式。但如果我们跳出纯粹的哲学考察的范围,就会注意到另一种间接地呈现概念或思想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尤其在艺术领域里有着广泛的运用。这就是“寓托”(Allegorie)的方式。这个起源于希腊文的词语从字面意思来看即“另一种言说”或“说的是另外的事情”,后来引申出“隐晦的言说”等意思,总之同样也是把两个不同的东西嵌合在一起,从而属于宽泛意义上的象征,同时又侧重于用一个东西去掩饰或揭示另一个东西,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比喻”。与此相对立的则是“直白”(Tautegorie),即“所说的就是这个东西本身而非别的东西”②[德]谢林著,先刚译:《神话哲学之历史批判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29页。。或许是因为寓托经常是随意地把两个东西(不管它们究竟是不是属于同样性质)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严格地限定于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概念和直观)的结合,所以康德才没有把寓托拿来与范型和象征相提并论,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谢林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康德的全新理解。
谢林的哲学体系,尤其是同一性哲学时期的体系,具有很强的斯宾诺莎主义色彩,即其阐述的是唯一的、普遍的绝对者与它的无穷多的特殊规定之间的关系——普遍者与特殊东西在本质上是无差别的,它们的结合在斯宾诺莎那里被称作“样式”(modi)或“分殊”(affectiones),而在谢林那里则是被称作“理念”。在谢林看来,哲学和艺术的区别恰恰在于,哲学是在普遍者(思想)里通过那种无差别去呈现出绝对者,而艺术则是在特殊东西(客观事物)里通过那种无差别去呈现出绝对者。关键在于,谢林不是笼统地把一切普遍者和特殊东西的结合都叫做“象征”,而是仅仅把特殊东西之内的这种结合叫做“象征”,而这是艺术的专利。与此同时,谢林在这种广义的“象征”下面又区分出三种结合方式。也就是说,在普遍者与特殊东西的结合里:
其一,如果普遍者意味着特殊东西,或者说特殊东西通过普遍者而被直观到,这就是范型方式;
其二,如果特殊东西意味着普遍者,或者说普遍者通过特殊东西而被直观到,这就是寓托方式;
其三,如果既非普遍者意味着特殊东西,也非特殊东西意味着普遍者,毋宁说二者绝对地合为一体,这就是象征方式③[德]谢林著,先刚译:《艺术哲学》,第72—73,224页。。
在另一处文本,谢林也明确说道:“要么让特殊东西意味着普遍者,要么让特殊东西在意味着普遍的同时就是普遍者本身。前一种呈现是寓托式的,后一种是象征式的。”④[德]谢林著,先刚译:《艺术哲学》,第72—73,224页。
正如我们看到的,无论是范型式还是寓托式,其呈现方式都是让一个东西A“意味着”(bedeuten)另一个东西B,即从A过渡到B:我们首先看到的是A,但最终直观到的却是B。在范型式那里,是从普遍者过渡到特殊东西,比如一位技师(工艺品制作者)就是按照一个既定的规则制造出一个特定对象。通常文艺创作中所谓的“概念先行”,也属于这种情况,即作家在讲故事和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事先已经具有一些想要传达的思想和观念,然后再制造出各种与之相对应的事件和人物。这种方式几乎总是带有机械的特征和浓厚的人为痕迹。与此相反,在寓托式那里,是从特殊东西过渡到普遍者,因为普遍者(艺术家想要传达的思想)并不是现成已有的,而是隐藏在特殊东西后面,所以这个过渡充满了不确定性,于是整个作品也可以经受各种解释,仿佛包含着无穷的意蕴,具有无限的意义。因此一般而言,寓托式呈现是比范型式呈现更为高级的方式,尽管前者本身内部又有高低之分,比如在谢林看来,但丁、阿里奥斯托、塔索的寓托手法是极为卓越的,反之伏尔泰的寓托手法却是十分显白和粗陋的①[德]谢林著,先刚译:《艺术哲学》,第76,53,64—65,77,278,244页。。
但是,象征式不同于范型式和寓托式的地方在于,当我们说A 是B 的象征时,并非A“意味着”B,或者哪怕我们也可以说A“意味着”B,但实际上A就是B。就此而言,A不是“意味着”B,而是“代表着”B,A作为一个特殊东西,就是普遍者B 的当下在场。因此这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最完满的结合方式或贯通方式,或者说是“最高潜能阶次的”呈现方式。由此可见,谢林区别于康德的地方在于,他认为理念能够以各种方式在艺术作品里客观地呈现出来并被直观到。与此同时,谢林区别于同时代的另一些推崇象征的人(比如歌德)的地方在于,他并不像歌德那样认为象征是理念的“直接”呈现,寓托(以及范型)是理念的“间接”呈现(因为对谢林而言,艺术里的一切呈现都是直接的),毋宁说,象征是理念的“完满”呈现,而寓托和范型却做不到这一点。在谢林看来,希腊神话里的诸神就是象征的最好实例,因为绝对者和特殊规定相结合的同一个统一体,作为观念的东西来看,是理念,而作为实在的东西来看,则是诸神。因此从一个角度来看,每一个理念都是“特殊形式下的上帝”“特殊的上帝”或“受限状态下的神”等②[德]谢林著,先刚译:《艺术哲学》,第76,53,64—65,77,278,244页。,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诸神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理念,并非意味着理念,毋宁就是理念,比如不和女神厄里斯(Eris)就并非意味着“不和”,毋宁就是“不和”本身。正如谢林所说:“哲学建构起来的理念王国所包含的全部可能性实际上在希腊神话里已经完全穷尽了。”③[德]谢林著,先刚译:《艺术哲学》,第76,53,64—65,77,278,244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高度理性和开明的希腊人同时又对诸神深信不疑,因为在神话那里,希腊人只不过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艺术或诗)呈现出他们在哲学那里已经认识到的同样一些真理。
更重要的是,谢林把“范型—寓托—象征”的三分法应用到了所有方面。比如他认为,物体是自然界的寓托,光是自然界的范型,而有机体是自然界的象征;又比如,他认为思维是范型式的东西,行动是寓托式的东西,而艺术是象征式的东西,甚至认为算术是寓托式的,几何学是范型式的,哲学是象征式的④[德]谢林著,先刚译:《艺术哲学》,第76,53,64—65,77,278,244页。。当然,谢林主要还是在艺术的领域内部使用这种三分法,比如在言语艺术里面,抒情诗是寓托式的,叙事诗是范型式的,戏剧诗是象征式的,而在造型艺术里面,音乐是范型式艺术(从节奏、和声、旋律等普遍规则出发走向具体的音素),绘画是寓托式艺术(从特殊的平面形象和色调出发走向无限的意蕴),而雕塑则是真正的象征式艺术,因为雕塑(尤其是其中最高等级的以人为题材的雕像)优于绘画之处在于,它将空间包揽在自身之内,而不是像绘画那样依赖于空间,而且雕塑作品作为立体的东西,取消了全部视角的限制,从而提升为全方位独立的东西,能够代表其想要传达的理念,而平面的绘画作品缺乏这种独立性⑤[德]谢林著,先刚译:《艺术哲学》,第76,53,64—65,77,278,244页。。在这些阐述中,谢林也表达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观点,比如他在讨论作为寓托式艺术的绘画时,又认为存在着象征式绘画:“如果一幅画的对象不是仅仅暗示着理念,而是理念本身,那么它就是象征式的。”⑥[德]谢林著,先刚译:《艺术哲学》,第230页,亦参阅第243页。为此他甚至提出了象征式绘画的标准,即只要“存在和行动在对象里合为一体”⑦[德]谢林著,先刚译:《艺术哲学》,第76,53,64—65,77,278,244页。,传达出充足理念,那么这个绘画作品就是象征式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当我们鉴赏各类伟大艺术家的作品时,就会发现不仅有象征式绘画,也有象征式音乐、象征式叙事诗等。又比如,谢林虽然一般地总是把象征置于寓托之上,但有些时候又认为象征之上还有寓托,以至于“当自然界的象征性因素仅仅被当作一个更高的理念的寓托,就产生出更高类型的寓托”①[德]谢林著,先刚译:《艺术哲学》,第243页。。除此之外,谢林始终没有澄清,我们究竟如何在现实中区别“象征”和“寓托”,因为二者都是聚焦于特殊东西或具体的个别东西,但我们如何判定这个东西究竟是仅仅“意味着”理念,抑或同时就“是”理念呢?对于这个问题,谢林从未给出明确的答案。
总的说来,谢林关于象征的言论虽然包含着自相矛盾和含糊之处,但其对于性质不同的东西的各种结合方式的细致而深入的辨析在艺术哲学内部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最重要的是,谢林不仅以艺术作为伟大的例证推翻了康德关于理念不可能呈现于直观的限制,而且通过对于象征的极端推崇而把艺术抬高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至少可以与哲学分庭抗礼的地位(因为哲学无论是从特殊东西走向普遍者还是反其道而行之,都只能以寓托或范型的方式呈现出绝对者,而艺术却能够以象征的方式用每一个特殊东西呈现出绝对者),但这一点恰恰是黑格尔所不认可的,因此黑格尔提出了另一个评价艺术类型的标准,从而给予象征另一个定位。
三、黑格尔艺术哲学中的象征型艺术和古典型艺术
黑格尔的美学(艺术哲学)思想直接传承自谢林的艺术哲学,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②比如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和美学史家鲍桑葵就指出:“可以说,黑格尔的《美学》中的论点很少没有受到在谢林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的那些见解和理论的启发。”此外他还指出:“黑格尔也受到谢林对于艺术和审美哲学的看法的莫大影响……虽然我们取黑格尔而舍谢林,这也一部分是因为谢林的思想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反映的缘故。”[英]鲍桑葵著,张今译:《美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11、430页。。因此黑格尔和谢林一样,专注于理念在特殊东西那里的感性映现,即理念和感性事物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东西的结合。但不同于谢林在“建构”或“一体化塑造”的名义下把全部艺术划分为三种单纯就呈现方式而言彼此不同的类型,即范型式艺术、寓托式艺术和象征式艺术,黑格尔是依据另一个标准亦即“内容和形式”的对比关系把全部艺术划分为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
简言之,在黑格尔那里,关键不是在于一件艺术作品身上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如何呈现出来,而是在于内在的东西如何外化出来。因此,在黑格尔评价艺术的标准里,“内”和“外”的对比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不能按照通常的理解,把内在的“内容”和外在的“形式”看作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尤其把内容看作某种独立于形式的东西,仿佛二者只是在不同的程度上拼凑起来。这里我们必须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论部分关于“映现”(scheinen)这个概念的规定,即只有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一方面返回到自身之内,成为内化的存在或内容,另一方面必然同时投射出外化的存在或形式,并形成“内”和“外”的对比关系③参阅[德]黑格尔著,先刚译:《逻辑学 II》,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4页。。也就是说,一切内容都是自带形式的,尽管后者看上去是外在的,与内容分开的。关键在于,内容和形式之间是绝对联动的关系,因此并非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同一个完满的内容可以具有许多完善程度不同的形式,毋宁说,不完满的内容就只能具有不完满的形式,反之完满的内容必定有完满的形式,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的:“严格意义上的内容只有在包含着成熟的形式时才是内容……‘无形式’的意思是指‘乱七八糟’,因此不是指根本没有形式,而是指没有正确的形式。但这个正确的形式并非与内容漠不相关,毋宁是内容本身。”④[德]黑格尔著,先刚译:《哲学科学百科全书 I 逻辑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26页。
因此,如果说在谢林的艺术哲学里,理念从一开始就已经是现成的、完满的,那么在黑格尔的艺术哲学里,理念本身作为内容还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而它的形式相应地也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对黑格尔来说,这个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象征性艺术。在这个阶段,理念本身仍然处于模糊不清的或糟糕的、非真实的规定性中,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被当作内容。因此象征型艺术与其说是一种真正呈现的能力,不如说仅仅是对于形象化的一种“尝试”(Suchen),而理念尚未在自身之内找到形式,始终只是围绕着形式的“挣扎”(Ringen)和“追求”(Streben)①[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第95,94页。。鉴于内容和形式的这种共同的低级状态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消极关系,黑格尔一方面把象征型艺术看作全部艺术的开端,另一方面,按照他一贯贬低开端的抽象空洞性的做法,他仅仅把象征型艺术看作一种“前艺术”(Vorkunst)②[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9页。亦参阅第22页。,也就是说,甚至不情愿让它进入真正的艺术的行列。在这个地方,黑格尔也给出了“象征”的一个定义:“一般而言,象征是一个直接摆在直观面前的或给定的外在实存,但这个实存作为直接摆在面前的东西不是被当作它本身来看待,而是应当在一个更开阔和更普遍的意义上被理解。”③[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2卷,第10,13,33,157页。按照这个定义,象征那里必须区分出两个东西,即“意义”(Bedeutung)和“表现”(Ausdruck),二者相互之间起初的不匹配使得象征在本质上是模棱两可的,而如果随后取消了模棱两可,明确地指出意义和表现之间的关联,象征就变成了“比喻”(Vergleichung)或“明喻”(Gleichnis)④[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2卷,第10,13,33,157页。。顺着这个线索,黑格尔又把整个象征型艺术区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无意识的(不自觉的)象征系统:波斯、印度、埃及,将自然事物精神化,将精神性东西感性化;
第二,崇高的象征系统:肯定的方面是带有泛神论色彩的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神秘学,否定的方面是强调崇高性的犹太教诗歌;
第三,有意识的(自觉的)象征系统,以“比喻”为总特征:1. 寓言、格言、宣教故事;2. 寓托、隐喻、明喻;3. 宣教诗、描绘诗、箴铭⑤[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2卷,第10,13,33,157页。。
撇开黑格尔关于象征型艺术的具体阐述不论,也暂不管黑格尔在此和在他的历史哲学里一样,充满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偏见和歧视,我们在这里注意到一个明显的问题,即黑格尔所理解的“象征”和谢林、歌德等人所理解的“象征”并不是同一回事,确切地说,黑格尔那里的“象征”其实更类似于谢林那里的“寓托”,因为它们都是从一个眼前的东西过渡到另一个或隐或现的东西,区别仅仅在于,谢林所说的寓托是从特殊东西过渡到普遍者,反之黑格尔所说的象征完全是混乱地从一个东西过渡到另一个东西。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黑格尔不懂得,或者说不承认谢林意义上的“象征”呢?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发现,当黑格尔提出象征型艺术之后的古典型艺术的特征时,其想要表达的就是谢林所说的“象征”的意思。比如黑格尔说:“在古典型艺术里,内容的独特性在于,内容本身就是具体的理念,而作为这样的理念,它就是具体的精神性东西。”⑥[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第95,94页。在另一处文本,他也明确地说道:“古典美把自由的、独立的意义当作它的内核,也就是说,这不是意味着某东西,而是意味着它自己(das sich selbst Bedeutende),随之指向着它自己(das sich selber Deutende)。”⑦[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2卷,第10,13,33,157页。这些表述都清楚地表明,黑格尔心目中的古典型艺术就是谢林所说的象征式艺术,而且,正如谢林把雕塑看作象征式艺术的最高表现,黑格尔也把雕塑看作他心目中的古典型艺术的核心,而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推断。
也就是说,黑格尔所说的“古典型”,按照其基本意义和代表性艺术形式来看,就是谢林所说的“象征式”,但前者的范围相比之下狭隘得多,仅限于希腊罗马的雕塑艺术,反之后者在原则上可以出现在一切艺术形式里。而且从谢林的角度来看,黑格尔所说的“象征”根本不配叫做“象征”,毋宁属于各种低级的“范型”或“寓托”,即用一个不完善的特殊东西去意味着一个普遍者—特殊东西的不完善的统一体,而这种全方位的不完善甚至导致黑格尔宁愿将象征型艺术称作“前艺术”。
更重要的是,虽然“象征式”和“古典型”在谢林和黑格尔那里分别代表着艺术的顶峰,但谢林的目标是让艺术止步于象征,而黑格尔却要让艺术超越古典。也就是说,对谢林而言,象征既然代表着艺术的最高呈现方式和完满形式,那么它就是一切艺术的永恒模板和目标。但对黑格尔而言,完满的古典型艺术即便在艺术的层面内部,也仅仅是一个过渡环节,是浪漫型艺术的一个铺垫。按照谢林区分的各种特殊艺术形式,在造型艺术(音乐、绘画、雕塑)和言语艺术(抒情诗、叙事诗、戏剧诗)内部,虽然第三个环节亦即象征的环节是完满的环节,但前面的两个环节通过调节普遍者和特殊东西这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同样可以在自身之内达到某种意义上的象征。但按照黑格尔区分的特殊艺术形式,从象征型艺术(建筑)到古典型艺术(雕塑),再到浪漫型艺术(绘画、音乐、诗),却是遵循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即随着感性因素愈来愈退隐,精神性因素愈来愈展现出自己的无限性,最终从诗过渡到散文,从表象过渡到思维,超越了艺术。所以黑格尔说:“如果说古典型艺术形式本身还有什么缺陷,那就仅仅是艺术本身和艺术层面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在于,一般而言,艺术把一个按照其概念而言无限具体的普遍者(精神)在感性的具体形式中当作对象,并且在古典型艺术里把精神性东西和感性东西的定在的完满的一体化塑造确立为二者的吻合。但在这个交融中,精神实际上并不是按照它的真实概念而达到呈现。”①[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第99页。一言以蔽之,对黑格尔而言,精神按照其真实概念的呈现只会出现在哲学里面。
四、“象征”与“古典”:不仅是语词之争
或许人们会认为,既然两位哲学家对于艺术的顶峰有着同样的刻画和评价,甚至为其划定了同样的范围(即希腊罗马的雕塑艺术),这就已经表明,黑格尔完全理解并且认同谢林关于“象征”的思想本身。至于究竟是像谢林那样把这个顶峰称作“象征式”,还是像黑格尔那样将其称作“古典型”,这难道不是一个不涉及问题实质的单纯的语词之争吗?
事实显然不是如此简单。因为黑格尔肯定知道“象征”这个词语的原本含义,即两个东西的“合体”或“一致”。但正如本文开篇指出的,这个词语最初仅仅是一个笼统的称呼,既可以指两个东西在本质上必然的结合,也可以指两个东西的偶然随意的结合。诚然,康德把这个问题真正尖锐化了,聚焦于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东西的必然的结合,而谢林和黑格尔进一步把“象征”拓展到了艺术哲学的领域,强调理念的感性映现,并且认为这种映现在艺术的某一个类型或某一段时期达到了顶峰。但黑格尔和谢林的最大区别在于,黑格尔并不像谢林那样认为艺术达到的这个顶峰足以让艺术独当一面,与哲学分庭抗礼。正因如此,黑格尔没有对谢林亦步亦趋,没有用“象征”概念去指代艺术的巅峰表现,反而是故意摘取了这个概念的较为低级的含义,用它去指代艺术的不成熟的萌芽阶段,并且通过这个方式与谢林的艺术哲学划清界限。但另一方面,黑格尔毕竟也不能否认谢林意义上的“象征”在希腊罗马的雕塑艺术里达到了巅峰这一事实,而他之所以选取了一个具有时间性意义的词语亦即“古典”去指代这个阶段,正是因为他希望借此表明,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能停留于艺术的层面,毋宁说,精神一旦达到完满的古典型艺术,必定会溢出自身,过渡到愈来愈不依赖于外在形式的浪漫型艺术,最终超越艺术本身而走向宗教和哲学。
由此看来,谢林和黑格尔对于“象征”的不同定位首先是体现出两位哲学家的不同的艺术观。因为从根本上看,谢林的“范型式—寓托式—象征式”三分法是基于精神的一个静态的、永恒的结构,把艺术本身当作一个永恒自足的世界,而黑格尔的“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分法是基于精神的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把艺术看作宗教和哲学的铺垫环节,以至于尽管他对艺术有着无数的赞美之词,但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艺术终究只是一种不完满的“前哲学”。这个比较似乎意味着,谢林的艺术哲学缺失了黑格尔的那种动态的、历史的维度。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谢林那里同样有“古代精神”与“近代精神”的区分和对立,随之有“古代艺术”和“近代艺术”的区分和对立,而且谢林同样看到了黑格尔所说的浪漫型因素或寓托因素在近代艺术里面的支配地位,只不过谢林坚持认为,这些区分和对立并不能动摇艺术的永恒本质,而是最终必定会在艺术的内部被扬弃①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阐述,可参阅先刚:《试析谢林艺术哲学的体系及其双重架构》,《学术月刊》2020年第12期。。就此而言,谢林的艺术哲学是一个比黑格尔的艺术哲学更为丰富的整体。
而从更深的层次来看,谢林和黑格尔关于“象征”之争也体现出他们各自的哲学体系的延伸范围的差异。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单向度的,总体说来是遵循着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模式,尤其在讨论伦理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的历史发展和历史本身的时候更是如此;与此同时,他的哲学体系也是西方中心式的,把希腊文明当作真正的起点和标准,正因如此,对于时间上更早的和空间上位于异域的民族和文化,他一律将其贬低为蒙昧不成熟的低级环节。虽然黑格尔自诩是以“理性”或“合理性”的呈现程度为评价历史的标准②参阅[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第8 页;[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82页。,但究竟什么是“理性”,黑格尔的界定(比如“理性是对于自由的意识”)并不是唯一的、绝对的标准,更何况即便以此为标准,他的成见和偏见也蒙蔽了他对于非西方民族和远古文化的判断。相比之下,谢林的哲学体系是多维度的,也就是说,他一方面也像黑格尔那样承认精神从希腊到当今时代的前进发展,但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从希腊回溯到远古文明,在其中揭示出理性早已达到的辉煌高度,而这些是黑格尔不愿意、也不能够看到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举出谢林的神话哲学作为例子就足够了。即便是以本文所说的“象征”为例,虽然谢林绝不可能赞同黑格尔对于“象征”的理解及其在这个名义下贬低非西方文化的做法,但换个角度来看,假若是在谢林自己所理解的“象征”的意义上去审查非西方民族的文化(尤其是他们的艺术),那么谢林或许也会接受这个界定,并在他自己的艺术哲学的框架之下揭示出其中达到的辉煌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