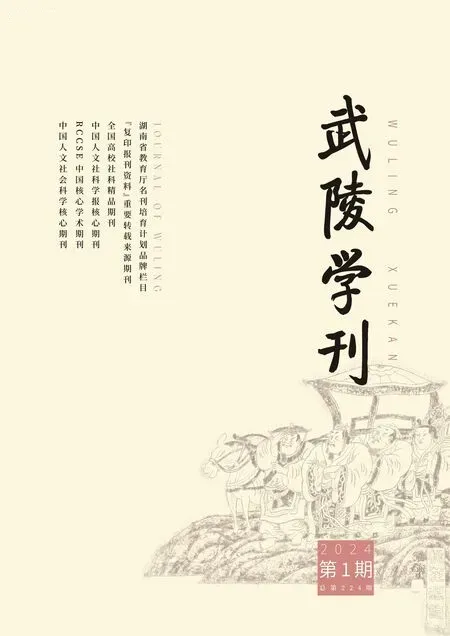中华传统勇德思想探源
——基于儒道释三家勇论的分析
李保玉
(曲靖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纵观中西,自古以降,勇德作为一种向善与为善的道德科目,因其德性内涵而备受各家推崇,在中国被列为“三达德”,在西方被列“四主德”。然而,在当下,人们往往对勇德持有误解、抱有成见,习惯性地将它泛化为勇或简化为勇敢,看作破坏、暴力、流血的特有符号,因而没有将其视为“主德”来推崇,甚至视其为“下德”而远离之,从而导致了诸如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等深层次的道德问题。事实上,作为一个德目,勇德是介于德与勇之间的,是德对勇的规限与勇向德的升华。从本源上看,勇德是人之不惧且积极的生命力量,是一种“向善”的精神与“为善”的力量,是一种推动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的实践力量。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勇德思想,儒家、道家、释家、法家、墨家、兵家等对勇德均有论及,这为新时代弘扬勇德精神、开展国民道德建设提供了充实而丰厚的思想养分。本文就儒道释三家的勇德思想进行溯源分析,澄明勇德内涵,剖析弘扬之道,为新时代践行勇德提供学理支撑。
一、儒家的“道义之勇”
儒家关于勇德的论述始于孔子,发展于孟子与荀子,成熟于儒家后世众学者。儒家论勇遵循着整体意识和系统观念,将“勇”放置在整个道德科目中加以审视,强调勇的道义内涵与伦理属性。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在这一表述中,“勇”与“知”“仁”并存,它们同处在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由“知、仁、勇”三达德构成的道德体系中,并且把勇德上升为主德,开启了儒家勇论的思想先河。孔子从勇的原始涵义中提炼出德性内涵,赋予勇以道德德性,将其限定在知与仁的道德阈限内,认为勇德只有发乎仁、合乎知,才能祛其劣性、扬其德性,从而成为君子的理想人格[1]。这一思想被儒家后世学者充分继承与发扬,他们关于勇德的论述均是建立在勇与知、仁以及礼、义、耻等其他德目的相互关系之上的。归纳起来,儒家关于勇德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勇德要以“知”为基础。在古语中,“知”通“智”,即智慧、知识之意。儒家所倡导的勇是对善的遵循、追求与坚守,为此要有明辨是非、区分善恶的知识和智慧。在儒家看来,知是勇合乎道义、彰显德性的基础与前提,如若丧失理智或缺乏理性约束,勇就会堕落成一种恶的情感,沦为“作恶”工具,成为荀子所言“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唯利饮食之见”的“狗彘之勇”、“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见”的“贾盗之勇”和“轻死而暴”的“小人之勇”(《荀子·荣辱》)。勇作为道德之勇,必须具有理性判断和审慎分析的智慧和能力,凡事要思考再三、谨慎而行,而感情用事、鲁莽无谋则不为勇德所推崇,即孔子所说的“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论语·述而》)。君子之勇只有内含“知”的德性因子,以“知”为基础,满足“知”的要求,在面临危险或困境时冷静判断与清醒分析,才能真正做到“可逝”而“不可陷”,“可欺”而“不可罔”(《雍也》)。儒家不仅阐释了勇的认知基础,而且还指明了“知”之勇的弘扬方向。孔子曰:“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阳货》)孔子认为,人非生而知之,知是后天学习的结果,只有通过不懈学习,才能获得知识,增长智慧,从而逐渐养成并不断完善道德之勇。“学”是获得“知”的重要方式,是成就“勇”的基本前提。在儒家看来,为了更好地成就道德之勇,“学”的内容要丰富多样,既应包括以四书五经六艺为载体的思想知识和道德规范,也应包括认识事物与分析问题的实际能力。
其次,勇德要以“仁”为旨归。“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儒家的最高道德规范。儒家各学派关于道德的学说及其德目均发端于“仁”。在孔子看来,“仁”既是君子人格的最高理想,也是为人处世的最高道德标准。所谓“仁”,最初的含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善关系,即“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这种亲善关系是建立在严格的自我要求与自我规定之上的:一方面,要做到尊重他人,体谅他人,承认他人,不要将自己不喜欢的事物强加给他人,即“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另一方面,还要具有恭、宽、信、敏、惠五种道德品性,在为人处世时做到恭敬庄重、宽厚待人、诚实守信、勤奋敏捷与慈善恩惠,即“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阳货》)。儒家认为,“仁”与“勇”紧密相连,如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勇既是“仁”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仁”的重要途径。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意思是说,仁爱之人一定是个勇敢的人,因为一个真正的仁者一定具有敢于向不仁之事或不仁之行作斗争的决心和勇气;表面上看起来胆大威猛的人如若缺失了“仁”,就不是真正的勇者,也不值得称颂。因此,道德之勇必然内含着“仁”的意蕴,以“仁”为旨归。个人只有把“成仁”当作人格理想与奋斗目标,心怀仁爱之心,“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才能达至“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的人生境界,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勇者。关于如何培育与弘扬“仁”之勇?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同上)他告诉我们“仁”之勇出于人心,而非外在之物,是否具有合乎“仁”的勇德,完全取决于自己,反诸己身才能得到合“仁”之勇。
再次,勇德要以“义”为导向。在古语中,“义”通“宜”,即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在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中,“义”与“仁”联系最为紧密,是“仁”延伸出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概念,被作为判断道德行为是否适宜或合宜的标准。儒家非常重视“义”对勇的规制与引导作用,认为勇如若摆脱了“义”的束缚,不以“义”为导向,就会作乱、为盗,即孔子所说的“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荀子也认为,君子之勇应以“义”为限度,合乎道义,固守正义,不为权与利所动,即“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可见,在儒家看来,勇就其行为结果而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可能是应该的、正义的、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应该的、不正义的、不合理的,具体结果如何由“义”来引导。只有以“义”为导向,遵循“义”的基本规定,勇才可能成为道德之勇。关于“义”之勇如何培育与弘扬,儒家认为,“义”作为“仁”的衍生物,源自人的本性(本心),抑或“义”由心生,即“义”是人性的规定,是善性或善心的显现,比如,孟子本着性善论的原则,将“义”规定为“羞恶之心”(《孟子·公孙丑》),即一种防范错误的情感意识。因此,“义”之勇的弘扬问题就转化成了善性或善心的培育或发现问题。关于善性的弘扬或发现的方式,儒家认为大体有二:一是强调后天学习或实践在善性培育中的重要作用,如“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二是通过克己复礼、自我修炼、修身养性来发现善性,即“存心养性”(《孟子·尽心上》)。
最后,勇德要以“礼”为规范。“礼”是从原始宗教仪式及风俗习惯中逐渐演绎出来的概念。一贯主张维护周礼、恢复周礼的孔子将“礼”纳入“仁”的范畴,作为“仁”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礼”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基本制度与道德规范,它既是社会存续发展的纽带,也是社会稳定运行的调节器,整个社会的一切事情与行为都要遵从“礼”的规制与引导,勇也无法例外。在儒家看来,勇作为一种不惧的精神气概,既可以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也可以破坏封建礼制,因此必须接受“礼”的规制,融入“礼”的意涵,才能实现德性定位。勇只有符合“礼”的规定,满足“礼”的要求,才能为君子所接受,成为道德之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孔子在回答子贡的“君子亦有恶乎”这一问题时,才说“有恶。……恶勇而无礼者”(《阳货》)。显然,在孔子看来,那种一味崇尚蛮勇、不遵循礼制规范抑或超越甚至破坏礼制规范的行为,是君子所不齿的。关于如何培育与弘扬“礼”之勇,儒家认为,合“礼”之勇的实现,关键在于“知”,即须深化对“仁”“义”“礼”的认知,着力于培养人们自觉遵守宗法伦理与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愿。
二、道家的“无为无待之勇”
道家的勇德思想是道家伦理道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散见在老子、庄子的论著中。道家论勇立足于事物的自然本性,着眼于摒弃私念、克制人欲,在“无为”“无待”中实现对自然本性的遵循。与儒家的社会道德观不同,道家的道德观强调人的自然性,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然道德观,正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这里的自然,并非形下意义的自然界,而是形上层面出于本性的自然而然、自然如此、不加造作,所有人都不应运用自身理性来改变自然界的和谐与平衡。在老子看来,一切道德行为都是一种顺应本性的、无意识、无目的的行为,而社会道德规范是人为的东西,是社会风尚衰颓的表现,应当抛弃。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第二章》)意思是,天下原本没有固定的道德规范与绝对的善恶标准,一旦人为地制定了规范与标准,人们就有了善恶美丑之念以及对这种观念的刻意追求和曲意逢迎,从而陷入贬褒毁誉、诽谤责难之争,甚至以伪善的方式博得善的浮名,而崇尚自然的道德观念自然导向追求个性自由与人格独立的价值观。道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与理想人格是摆脱社会伦理道德与功名利禄的束缚和奴役,追求自由超越,融通宇宙自然,成为消除物我两分的“至人”或“真人”,即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真人”知天亦知人,知道亦知德,知物亦知我,是精神自由与生命通达之人。故此,庄子曰:“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大宗师》)这种理想人格是超越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既要求由人达天、由德至道而不断超越,也强调由天及人、由道化德而返回现实,正所谓“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乎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踯躅而屈伸,反要而语极”(《秋水》)。
正是基于对这种理想人格与人生境界的追求,道家赋予勇德一种顺应自然、遵循本性、无为无待的自然德性,呈现出谦退、敛藏、中和、知足、超然、淡泊、节俭、坚韧等行为特征。从内涵上来看,道家的勇德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勇于“无为”。“无为”是道家道德哲学的最高理念,也是其自然道德观的基本原则。老庄的“无为”思想最早并不是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而是对君主的政治要求与道德告诫,是指君主不与民争、顺应民意、不妄为的意思。在后世道家诸学者的丰富与发展下,“无为”逐渐泛化为一种普遍的道德理念和自然精神,意指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本性,保持事物本质,不人为造作等。道家认为,面对功名利禄、富贵荣华、酒色美食等,能够克制私欲、摒弃杂念而不为所动、皈依自然,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唯有勇者能之,故而“无为”是属于勇者的品质。在道家看来,儒家所强调的积极进取、刚健作为、自强不息等勇德品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得于道、成其为德的天性,这是自然而然的东西。因此,真正的勇不是一种为了得到一些诸如赞扬、名誉、权力、利益等身外之物而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并作出忍耐让步或自我牺牲的道德品性,而是回避一切纷争,顺应自然本性,保持纯真自我与独立个性的无欲无求无惧之勇,故而老子曰:“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道德经·第七十三章》)因此道家之勇是一种“不敢、不争、不应、不召”的出世之勇。
二是勇于“无待”。“无待”是庄子的道德理念和生活态度,是他对老子“无为”思想的丰富与充实。“无待”是指顺应自然运动变化规律而实现精神上的完全独立与彻底自由。这就是庄子所说的:“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逍遥游》)在庄子看来,世界万事万物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束缚的关系,人作为宇宙万物中的一员,自然也难摆脱被他人他物束缚、制约、奴役的命运,这就是“有待”,即人类固有的“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局限性。同时,庄子还认为,真正的勇者绝不会满足于此,他们会竭尽全力地超越人类自身的局限性及现实困境,寻求一种精神层面的“无待”境界,在精神上实现自由与解脱。庄子的“无待”之勇实现了精神对形体的超越,在本质是一种向往自由、追求独立、不断超越的道德品质。
在道家看来,“无为”之勇与“无待”之勇的弘扬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以慈促勇。老子曰:“慈故能勇。”(《道德经·第六十七章》)而法家的韩非子将之解释为:“圣人之于万事也,尽如慈母之为弱子虑也,故见必行之道,见必行之道则明,其从事亦不疑,不疑之谓勇。不疑生于慈,故曰:‘慈故能勇’。”(《韩非子·解老》)可见,只要拥有慈爱之心,对分内之事就不会疑虑,就会获得尽心尽力做事的决心与毅力,从而产生勇。与儒家注重以“知”促勇不同,“慈”属于情感的范畴,道家看到了情感对意志的促进作用,强调以情促勇。其二,以柔塑勇。作为一种情感,“慈”并非刚性情感,而是一种柔性情感,是柔的表现。所以,道德之勇还要符合柔的要求,满足柔的塑造,成为“天下之至柔”。在老子看来,柔具有海纳百川、包容万物的特性,这正是道德的基本精神。天下至柔,莫过于水,故老子以水为喻:“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第八章》)老子鼓励人们学习水的柔顺、谦让和包容精神,并认为这种不争之勇才是合乎道德的最高层次的勇。同时,老子还指出儒家所提倡的顽强、刚劲之勇并非真正的勇,而恰恰是老、死的表现或征兆。他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七十六章》)“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第五十五章》)。其三,以心强勇。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道德经·第三十三章》)在道家看来,勇或强的关键不在于身强体壮、力大无穷而战胜他人,而在于心性强大、意志坚定而战胜自己。真正的勇者或强者是能认知自己且能克制自己、战胜自己的人,即自制者。自制者的取胜之道不在于力,而在于心,它是一种强大的心性灵力与精神意识。进一步看,这种心力之勇则依赖于静修养性与体道悟道,正如庄子所说,精神上的“无待”境界只能通过“坐忘”“心斋”的方式来实现。总的来看,慈、柔与心是道家实现德性之勇的三大途径,但具体的实现方式均须遵循“无为”的基本精神,只有顺应自然、合乎本心、不人为造作,才能达到“无不为”的最高境界。
三、释家的“放下之勇”
释家关于勇的论述非常丰富,在《金刚经》《心地观经》《地藏经》等诸多佛经中均有体现,所涉内容非常广泛,如执念(我执和法执)、四圣谛苦集灭道、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无常、无我、誓愿等。在诸多的经文表意中,“放下”之义始终贯穿其中,放下“我”“法”及一切以度己、度人,即谓勇。释家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因其丰富完整的伦理观念与价值体系而受到了部分国人的认可与青睐,并在与我国本土文化历经千年的碰撞与融合后,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学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释家的伦理观念与道德思想集中体现在大乘佛教的“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佛法中。在释家看来,天地万物并无固定不变的本质,随生随灭,变幻无常,现实社会及其伦理关系均是假象,世界的本质是空的、虚幻的、“无我”的。世界充满了灾祸、劫难、烦恼与痛苦,人在现实社会中只能感受到不幸与困苦,而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与快乐,所以,只有放下“执念”(主要有我执和法执两种迷妄之见),皈依佛门,才能回头是岸,脱离无边苦海。因此,帮人脱离苦海,助人解脱,就成了释家的最终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释家提倡一种大无畏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牺牲精神,这与儒家的“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之勇不谋而合。然而,相比儒家,释家的牺牲精神更加纯粹、无畏,正如“一切菩萨复有四愿成熟有情住持三宝,经大劫海终不退转。云何为四,一者誓度一切众生,二者誓断一切烦恼,三者誓学一切法门,四者誓证一切佛果”(《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这里的誓愿就是一种勇气,不仅誓度一切众生、誓学一切法门、誓证一切佛果是一种勇,誓断一切烦恼更是一种勇。所谓能断方能勇,勇往往与金刚、坚硬、断等概念相关联。
显然,释家所要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出世精神,遵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规律,促使人们始终恪守怜悯众生、关怀世人、教诲劝诫、行善积福与牺牲自我的道德原则。“故学佛者,识五蕴之皆空,澄六根之清净。……为法忘躯,则如割皮刺血书经,断臂投身参请,而不怯不疑;为物忘己,则如忍苦割肉喂鹰,舍命将身饲虎,而不怖不畏。钱财珍宝,国城妻子,弃之如敝屣;支节手足,头目髓脑,舍之如遗脱……”[2]其中,“识五蕴之皆空”,就是要消除色、受、想、行与识五种欲念;“不怯不疑”,即不胆怯、不犹豫;“不怖不畏”,即不恐惧、不畏惧。只有消除“五蕴”,才能真正领悟“四圣谛苦集灭道”的精髓,得到“众生皆苦”的真相,追究苦的根源,超越生老病死到达涅槃的彼岸。可见,在释家道德观念中,有德之人或修佛之人就要勇于了达诸法实相,抛弃我、法两执,做到摒弃一切私心、杂念与私欲,消灭一切妄见与烦恼,对外积德行善、普度众生,对内清心静修、一心向佛。显然,这已经超越了儒家“大勇”的境界。
正是在这种道德观念的支配下,释家对勇德的解释是:“谓如前说,堪能忍受,发勤精进所生众苦,诸淋漏苦,界不平苦,他粗恶言损恼等事所生众苦;非此因缘,退舍修习正断加行。故名为勇。”[3]总的来看,释家所说的勇,就是主动放下红尘俗念和一切迷妄之见,破除“我执”和“法执”,自觉向佛,积极行善,始终以宽容与劝善之心待人,不放弃任何一次普度世人的机会,给所有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就此释义来看,释家的勇德具有以下内涵:
第一,勇德是一种坚韧的道德品质。释家认为,勇德的关键在于“堪能忍受”,即能够忍受众生之苦,这些苦既包括因他人的粗言、恶语、暴行、损伤带给自己的困苦,也包括因自己的贪欲、杂念、强势所引致的烦恼,正如《金刚经》中提到的“佛被歌利王割截身体时心不生嗔恨”的片段,此等忍辱之勇无疑是众勇中之大勇。勇德就是要把这些外在困苦与内在烦恼看成自己的因缘,是佛对自己的考验,是成佛必经的磨难,要依靠自己的决心和毅力对这些苦恼进行否定、克服与超越,从而破除“我执”,使内心趋于平静。
第二,勇德是一种劝善的道德品质。释家认为,能否忍受众生之苦,取决于心中是否有善。释家的道德观建立在慈悲之上。所谓慈,即予众生欢乐;所谓悲,即拔众生之苦。慈悲源自心中的善念,乐从善生,苦随善散,人们只有心中有善,才能脱离众生的困苦与烦恼,获得真正的幸福与快乐。劝善既是慈悲的基本表现,也是实现慈悲的重要方式。所谓劝善,即劝诫人们存善心、施善行。释家认为,众生平等,众生均有善根,众生皆能成佛。而勇者正是心存善念、常施善行的大慈大悲之人,如“菩萨”一词在藏语中又被译作“勇识”,释义为五浊恶世度化众生须有一颗坚强勇敢的心。勇者的使命在于帮助他人找到善根,劝人向善,成就佛果。
第三,勇德是一种静修的道德品质。与道家将静修看作实现勇德的途径不同,释家不仅将静修看成实现勇德的途径,还将其纳入勇德的内涵。静修的目的在于放下“执念”与“挂碍”,这是勇德生成的基础和前提。释家所说的“挂碍”就是相,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只有做到了无所挂碍、无我无相才能慧行坚勇、究畅无极,也才能舍身伺虎、舍身求法。在释家看来,破除“我执”与“法执”,摒弃贪嗔痴念,抵制红尘俗世的一切诱惑,“退舍修习”(《瑜伽师地论·第九十八卷》),走出无明,了达诸相,当为一种勇德的高尚品质。静修往往与寂寞、孤独、清贫相伴随,唯有信念坚定、意志坚强且具有巨大决心和勇气之人,才能做到。
释家道德观不仅强调勇德的内涵与价值,还注重勇德的培育与弘扬。总的来看,释家培育与弘扬勇的方式是一种自修或禅修的方式,即自我修行、自我觉悟,如静坐、观想、诵经、念佛、拜佛、参禅等。在释家看来,红尘俗世是人的外在束缚,私心贪欲是人的内在束缚,它们是人们变得胆小懦弱、勇气不足的现实原因。人们只有摆脱红尘俗世、私心贪欲的内外束缚和诸法实有之妄见,才能破除“我执”与“法执”,心无贪恋,从而无牵无挂、无私无欲,进而产生勇的力量。自修或禅修恰恰是人们摆脱内外束缚的重要方式。禅修不仅可以使人们化解自身一切不健康的或恶的念头和情欲,增强禅定的能力(俗称定力),还可以使人们在参禅与拜佛中得到佛的力量,获得“存在的勇气”[4]。进一步来看,禅修的方法有六,即“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般若,它是通往彼岸世界,达到涅槃境界的六大法门,非大勇之人莫能为之。
在“六度”的指引下,释家培育或实现勇的具体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正觉,就是对众生、生活及道德有一个正确的或公正的认识和把握。只有认识到一切皆空,一切皆苦,世俗生活充满生老病死、生离死别等束缚与困苦,才能产生寻求解脱、摆脱束缚,通往极乐世界的动力和勇气。二是等觉或遍觉,此处的“等”,即平等;“遍”,即普遍。意思是说,正觉要有平等性或普遍性。真正的勇者不仅要自己觉悟,即觉己,还要让他人觉悟,即觉他,用释家的话说就是自觉觉他,也被引申为自渡渡人。释家认为,众生平等,因果循环,善恶终报,个人只有将自己融入众生,与其一道克服局限、共进共生,才能最终离苦得乐,达至彻底的觉悟、解脱、清净与圆满。三是圆觉,所谓圆,即圆满、无缺。这是禅修者所向往的一种觉的最高境界,即成为一个彻底的、透彻的觉悟者,即成佛。在释家看来,佛是高于菩萨、罗汉的最高果位,是修行最高、觉悟最深的圆满者。佛具有一切道德品性,是功德圆满、大慈大悲、大智大勇之人。所以,成佛即成勇,心中有佛,心中亦有勇。
综上可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道释三家均内含着丰富深厚的勇德思想。就勇德的培育途径与弘扬方式而言,三家虽各有侧重,但亦有共通之处。总的来看,儒家遵循的是由内而外的发现逻辑,而道家与释家遵循的是由外而内的生成逻辑。儒家强调人性本善,勇德作为一种善德,是根植于人性的一种为善的力量,勇德精神的培育与弘扬离不开对人性中“为善之力”的不断发现与持续彰显,是一种“为学日益”的过程;而道家与释家注重静坐禅修与无欲无私,认为外界的牵绊与束缚、内在的贪恋与不舍使人充满疑虑与怯懦,勇德精神的培育与弘扬就是要丢掉一切杂念、私心与贪欲,无欲无私从而才能无惧,这是一种“为道日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