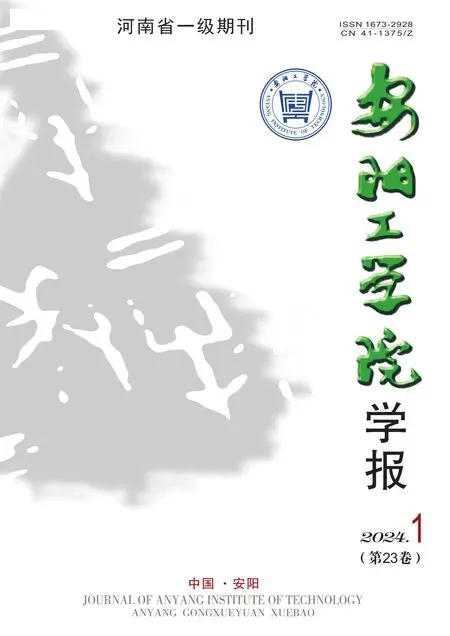论刑事案件事实的规范建构
殷哲浩,朱德安
(1.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天津 300170;2.天津商业大学 法律事务室,天津 300134)
1 从客观事实到案件事实
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并非是同等概念。客观事实是脱离人主观的纯粹存在,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使用的“客观存在”的范畴。恰似罗素认为的,“我所说的‘事实’的意义就是某件存在的事物,不管有没有人认为它存在还是不存在……大多数的事实的存在都不依靠我们的意愿……部分物理事实的存在不仅不依靠我们的意愿,而且也不依靠我们的存在”[1]。张心向将二者作了如下区分:“客观事实是指实际发生过的‘原汁原味’的案件事实,是曾经存在过的事实真相;而法律事实则是指法院在审判程序中认定的案件事实。”[2]131他进一步解释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客观事实是法律事实的基础,法律事实应该是客观事实的再现或者反映,法律事实并非都能准确地反映客观事实,法律事实始终以客观事实为追求目标”[2]142。
从上面表述可以看出,所谓的客观事实在性质上是一种前法律规范的概念,属于“未发现的事实”,甚至属于一种“不可能真正发现的事实”。所以,从作用上看,虽然未被发现的纯粹客观的事实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类事实与法律规范相距甚远,只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并没有太大的社会或者规范意义。进一步说,未被发现的客观纯粹真实在法律规范上根本就并不存在,它只在法律之外,并不在法律之中。真正具有社会以及规范意义的是案件事实,或者说是法律事实。案件事实,是经过主观发现后才逐步成型的事实。案件事实的形成同客观事实不同,前者是经过证据的证明、法律规范的界定和法律思维的加工后才筛选出的事实,即法律事实是法律人主观发现的事实。这种经过规范和思维的重构、再经二次描述以后所产生的事实,实际上已经成为“认识的事实”或者“思维的事实”。因此,“从规范的视角看,案件事实是被规范建构的事实。刑法运作过程中的案件事实,并不是原汁原味的案件原始事实,而是被规范裁剪过的法律事实”[3]。
客观真实不应该作为法律事实的追求目标,这是法学界的共识。因为,法律事实是主观的真实,是规范的真实,其先天就有别于客观真实。无论是我国现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还是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辩诉交易制度,都摆脱了对客观真实的执迷,进而越来越重视法律的效益。“审判程序的改革不能一味地去追求公正,公正也不是刑事审判的唯一价值目标。其实,能否对效率进行充分的关注以及能否在公正与效益之间保持适当平衡也是衡量程序公正的一项重要标准。”[4]笔者认为,案件事实具有主观性,它的目标应当是规范性。案件事实并不要求和客观事实相一致,只要是在刑事诉讼法和刑事实体法的规范之下所能触及到的真实,便具有了足够的法律意义。
同时,法律的事实又有别于日常的生活事实。日常事实是一种“直觉的事实”,它更多是凭借生活的经验所加工出的事实。和法律事实相比,日常事实并没有或者极少受到法律规范的影响和法律思维的解构。因此,对非法律人而言,对客观事实的认知更多是依靠生活直觉、道德规范和伦理规范等;相反,对法律人而言,更多依靠的却是法律规范和法律思维。当然,当我们谈及法律的时候也并不能脱离生活,只是法律思维终究极大程度地受到法律规范的引导,具有强烈的规范性,这一点在刑事法律上显得尤为突出。
由上述可以看出,所有被发现后的刑事案件事实都必须经过主观的价值判断。虽然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会有所不同,但无论是日常生活影响下所产生的“经验”,还是经过法律专业训练后所产生的“法律思维”,都将客观存在推向了主观评价。因此,刑事案件从来都不可能被真正客观地描述。可见,法律事实寻求的是一种经过主观评价的相对真理,具有多重性;而客观事实寻求的是一种绝对真理,具有唯一性。那么,我们在承认二者差别的基础上,就不必讳言案件事实本身所具有的“主观性”。正如上文所言,纯粹客观存在的事实由于未被发现,对人类社会而言并没有太大的价值,而真正具有意义和价值的,就只有那些被发现后的事实。如此一来,我们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案件事实是如何被发现或者形成的。
2 法律前见是法律人认识刑事案件的出发点
犯罪的过程是由因生果的,即先有原因后产生结果,但是刑事案件的认识过程以及刑法上的论证过程却是反向思维的,是由果及因的。有学者在论述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排列顺序时说道:“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的排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的,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5]这种从客体出发,再进一步到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的思考过程,表明了认识过程和事实本身的倒置性。这种与客观事实相反,由果生因的现象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之中,“前见”在不自觉地对案件事实进行加工和判断。
前见,又称为前理解,原属于解释学上的一个概念。但是,在还原并对具体的刑事案件作出评判时,前见会通过影响每个人的感知从而形成模糊的预判。“针对案件事实而言,前见可谓对案件处理结论的预判……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预判,他就不知道应当将事实与哪一个刑法条文规定的构成要件进行对应,不会去判断该事实可能符合什么犯罪的构成要件,因而不可能形成任何解释结论或者刑法适用结论。”[6]于是,基于每个人先天生物属性与后天成长环境的不同,每个人对案件事实所形成的前见就不会完全相同。以著名的许某恶意取款案为例。银行的工作人员偏向认为许某取走存款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注重许某取走存款这个事实,而一般人把焦点放在银行的存取款机的程序出现了问题上,即既然银行本身错误在先,而人性本身又难以抵挡住巨额金钱的诱惑,那么许某的行为就不能认定为盗窃。这正是由于人们所处的立场和角度不同产生的认知差异。
同样,具体到法律人而言,在新发现的案件事实面前,会形成相应的法律前见。法律前见,指的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在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面前,内心先行具有的见解或看法。有学者曾作出如下解释:“法官刚接触到判决案件时,就会自动加工获得的不充分信息,作出直觉的判断,进而得出初始的假定结论。这种假定结论会非常顽固地嵌入法官思维中,成为法官进行推理的隐形前提,而且法官会为证明假定结论的正确而寻找各种证据,虽然法官不会公开承认这一司法心理过程。”[7]
3 法律思维对刑事案件的整合
在前见或者说是预判的基础上,法律人便开始对案件的事实进行解构和重构,通过事实的进一步发现,不断地在前见的基础上重新反复归纳案件,其结果或者是进一步巩固前见,或者是彻底推翻前见。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思维开始发挥作用,引导法律人逐步对案件事实进行整合与再整合。就刑事法而言,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刑事法律思维游走在案件事实、刑事法规以及犯罪构成理论之间。也正是在这一过程当中,刑事案件事实的主观性和规范性愈发明显,逐渐演变为具有法律价值的事实。
在这一过程中,演绎推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基于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推崇,演绎推理一直被奉为刑事司法的主导裁判方法,它被期望在帮助法官推导刑事判决的同时,又能限制法官恣意。”[8]于是,法律思维一开始就被严格地限定在了三段论所划定的逻辑范围之内,即通过大前提和小前提的匹配,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在这一逻辑推理的要求下,大前提被置于首位,其次是小前提,最后得出结论。然而,在案件事实刚被发现之时,法官实际上是在接触小前提之后,才从小前提出发去寻找大前提的。如若大前提得以与小前提匹配,那么自然得出结论;如若大前提与小前提不匹配,则法官就不得不重新寻找大前提或者重新发现小前提。后一过程,就是案件事实被法律思维不断寻找和发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案件在法律思维的引导下,得到了动态的建构。法官遵循着三段论的经典思维导向,对应规范的要求去匹配具体的案件事实,从而对先前所勾勒的案件面貌产生进一步的理解。正是在这个思维过程当中,抽象的案件演化成了具体的案件,先前未被发现的事实得以发现、被轻视的细节得到了重视,进而,案件的全貌经由逻辑的引导得以立体化,案件的各个要素得到了重新的增删和排列。
首先,法律思维增删案件细节。在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案件中,以杀人这一基本事实为核心,案件事实将会重新铺开。比如,杀人的原因究竟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还是单纯地出于往日的恩怨;行为人是否受到了他人的指示;行为人的手段如何,是否残忍;如果残忍,哪些细节体现出其残忍等。因此,法律思维将会根据法律规范的需要,增删案件事实,使需要的内容被突出,不需要的内容被忽略。
其次,法律思维排列事实情节。除了增删细节以外,法律思维也会引导法律人排列案件的事实情节。如,在杀人取财的刑事案件中,到底是先杀人还是先取财,这样的情节排列会影响案件的定性。此外,取财的动机到底产生于杀人之前还是杀人之后,也会影响对行为人行为性质的判断。所以,法律思维要求案件的事实情节必须按照相应的逻辑顺序进行排列,不同逻辑顺序下所排列出来的法律事实,会成为性质不同的案件事实。
上述对细节的甄选和对情节的排列之所以需要一系列逻辑的过程,就是因为法律思维要求法律人在构建法律事实之时,必须依照法律规范,即遵循大前提的需要去增删和排列小前提的内容。如果不经过法律思维的引导,那么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就将具有高度的随意性,事实和结论也将南辕北辙,毫无章法。因此,法律事实不仅是主观的事实,还是逻辑的事实,具有规范性、严谨性。
4 刑事法律规范作为刑事案件的归宿
脱离了法律规范的事实超出了法律所能调控的范围,该事实就不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因此,刑事法律规范不仅是法律思维所该遵循的原则,还是案件事实的最终归宿。案件事实的终点必须与法律规范相吻合。
首先,规范中抽象的用语将重构具体的案件事实。马克思·韦伯曾言:“每一个具体案件的判决都是抽象的法律规则在具体事实中的‘适用’。”[9]既然规范是抽象的,而案件事实是具体的,那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抽象的规范和具体的事实如何完成对接以及每一个具体案件的判决是如何选定最终的案件事实的。“具体事案可视为是一个平面——呈各种主客观因素绞缠一体的事实状态,而法律文本则表现为另一种平面——在一种威权发令的平台上向社会传递着统一的规制信息,表征各种行为在法律上之类型化意义……事实的平面对应于规范的平面进而经正当程序获得刑法评价意义。”[10]正是在这个对接过程之中,具体事实和抽象规范不停地互动,具体事实按照抽象规范的要求不断地格式化、模板化。“案件事实成为被证据并依据一定的证据规则证明确立的与犯罪构成要件相关的事实。案件事实被依据构成要件的类型要求加以相应的格式化,以使之能够满足构成要件归类或涵盖的框架要求。”[11]最终,就案件事实而言,它便不得不依照规范的需要,例如将具体的毒杀、砍杀或者枪杀等变成为抽象的“杀人”,将具体的隐瞒、夸大或者沉默等变成为抽象的“诈骗”,具体的事实就这样在规范的指引下逐步抽象化。
进一步而言,法律规范本身虽然抽象,但并不是毫无生趣的,而是包含着价值取向和态度情感。法律事实不仅仅是规范所选择后的事实,也同时是规范评价后的事实。因此,规范的价值取向也将重构法律事实。
刑法法规的文本,乃至其他实体法的文本并非是空洞无味的,而是蕴含着强烈的好恶爱憎。一方面,语言和文字本身天然地带有立法者的价值态度。词汇是人类所创造的,既然如此,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当词汇生成以后,又能再为人类所循环反复地使用,并且共同地、基本没有歧义地运用,就是因为该词汇本身所高度概括的、相同的、相似的情境得到了人类社会的普遍知悉和认可。这表明,语词中所包含着的概念意义、价值倾向、情绪情感等都已经得到了一个成熟理性人的共同理解。比如,当我们单独使用“杀人”“抢劫”一词时,我们情感中会天然地带有“恶”的价值评判,但是,如果我们结合具体的情境进行描述时,这种情感又会转变,如杀害的是正在欺凌弱小的恶霸。在这样的情境之中,先前“恶”的价值情感就会被弱化。这是因为,当我们在做所谓客观的描述时,语言本身都已经带入了感情色彩和价值评判。所以,即使是规范的语言描述,也难以避免对案件事实进行主观情感的处理。譬如,若是符合了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那么杀人行为就将被规范评价为救人行为。此时,案件事实依旧是同样的案件事实,但是,法律人的立场和态度却都将发生转变。因此,在案件事实的评价过程中,抽象的规范必将涉入,使得案件事实得到规范的价值评价。
因此,法律事实不仅在法律规范中得以抽象化,还在抽象化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价值评价,从而法律的事实也不再仅仅是逻辑中的事实,还是规范化、价值化后的事实。这种规范事实和纯粹的客观事实相比,才是法律事实最终的归宿和目标,因为只有这样的事实,才具有法律规范上的意义。
5 结语
纯粹的客观事实是没有规范上的意义的,真正具有意义的是法律事实。法律事实具有主观性,它是前见、法律思维和法律规范相互影响下的结果,具有多个维度和侧面。具体而言,这种主观的事实先由前见大致描绘,再由法律思维和法律规范构建,具有逻辑性和规范性。因此,笔者认为,当我们在把握案件事实的时候,应当注意描绘和评价该案件事实时所处的视角和阶段,不同视角下的案件事实所展现给我们的面貌不同,意义也就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