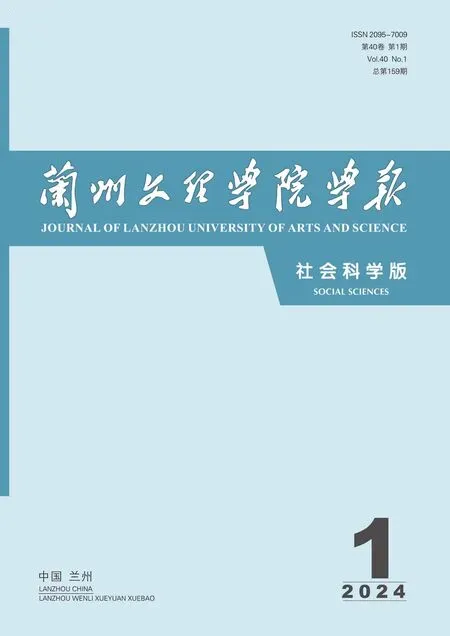边缘人的文化融合与身份建构
杨 艺 村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2400)
雷祖威是美籍华裔作家中的佼佼者。其作品量少而精,仅有一部长篇《野蛮人来了》,一本短篇小说集《爱的痛苦》收录了11篇短篇小说。他的作品描绘了华裔,尤其是华裔二代,在美国的生存现状:华裔青年作为接受了强势美国文化的年轻一代,与坚守中国文化的父辈之间始终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年轻一代在美国生活,距离他们相隔太平洋的祖先越来越远,慢慢接受了自己作为美国人的身份。
雷祖威曾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创作旨趣和基本主题:“我的作品是通过写作的行为,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而具有政治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要求分享某种权利。我认为一些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重新定义了美国华裔男性的形象,他们扩大了华裔或亚裔美国作家所表达的题材和主题。我的作品清晰地表达了第一代和第二代华裔美国人的挣扎。”[1]在对美国社会现实的系统性分析中,雷祖威揭示了华裔二代与原生家庭的矛盾,在婚恋关系中的挫折,以及在更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受到的压抑,在叙述中多角度、多维度建构了华裔青年的双重身份。他们始终处于夹缝之中,同时受到两种文化的冲击,因此具有了独特的生命体验。
一、母国文化身份的继承与疏离
第一代移民完整地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思维与观念,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他们仍旧抱团取暖,坚持以固有的方式生活。他们把中国的人生哲学带到了美国,在新的环境中重新定义了生活的认识和理念。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中,华裔二代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规训,他们虽然在学校里接受了美国式的教育,但在早期中国家庭中的经历也持续影响着他们的人生态度和人生选择,他们自以为是美国人,却在无意识中建构起了属于中国的身份印记。小说集同名小说《爱的痛苦》描述了华裔青年与母亲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以及两代人的冲突与和解。
第一代华裔始终坚守着中国文化的阵地,无论在美国待了多久,他们仍然持有中国传统的观念和态度。庞太太在美国生活了四十多年,但是“她一定出于某种极大的意志力量,居然坚持不学英语”[2],由于完全不懂英语,庞太太对美国文化近乎是无知的。她住在唐人街,“遇到朋友们聊起广东话来就没完没了”[2]2。而她的儿子阿伟,中文程度“充其量才不过是个早熟的五岁小孩那样”[2]4。一直处在自己的文化堡垒中,庞太太自我建构起了与孩子们交流的屏障,语言的隔阂导致了他们完全无法交流的痛苦。对庞太太而言,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一种文化和身份标识,她对英语的拒斥,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上的。在她看来,使用英语生活是对中国文化的背离,会引起强烈的身份焦虑。她跟随丈夫来到异国他乡,丈夫死后,也唯有语言,能时时刻刻提醒她的“根”在何处。
庞太太热切地希望儿子娶一个中国姑娘,她尝试说服阿伟的弟弟,也就是她的三儿子比利娶一个中国女孩,并说,“她会记得我的坟墓,带上食品和纸钱来悼念我的。要是光靠你,我死后也要挨饿了”[2]13,这其中渗透着中国浓厚的鬼神观和祭祖传统。但是这种思想和意识是永远无法被华裔青年所理解的,尽管他们在原生家庭中接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但是由于缺少真实的文化环境与生活土壤,他们对于故土的礼仪与文化,无法拥有直观的感受,因此他们也完全不能理解父母的思维方式。甚至于凭借他们的汉语水平,都不能理解父母想要表达什么,因此也更不可能同情和关照父母的感受。
庞太太的儿子,阿伟,从主观上竭力追求美国主流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他作为“本星球上具有责任心的公民”[2]2,时时刻刻关心着政治、环境等一系列世界问题,并常常对母亲的只顾吃穿的小农意识加以批判。然而,早期在中国家庭中的生活经验,让他无意识中受到了中国文化的规训,接纳了异质的意识形态体系影响。父亲去世后,他又情愿和母亲住在一起,践行起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准则,他的女友要求他搬出去住,并称呼他为“妈妈的孩子”,他也无动于衷。当新女友与母亲发生冲突时,他没有尝试调和矛盾,而是觉得“和她们两人都说不清”[2]10。但女友开始不尊重母亲时,他又开始不自觉地维护母亲,暗想道,“正如渔民常说的,你反正也不是个长久厮守的人”[2]10。阿伟性格中矛盾的一面,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他在思维方式上与美国文化高度融合,践行着美国的社会规则与道德伦理,摒弃甚至贬斥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社会观念,俨然以“美国人”自居。但是,在潜意识深处,他仍然被童年时期父母言传身教的中国式的行为准则所影响和塑造,孝道伦理被深深植入了他的心里,在婚恋的选择上,他向母亲的观念妥协了。
由此,雷祖威绘制出了华裔二代在美国的真实面相。他们渴望融入白人社会,在主观上认可并坚守美国主流价值观,以本地人自居,拒斥与父母在观念和思维上的捆绑,不认可自己的中国身份。但是在客观上,童年的生活环境和生存体验又浸染了他们的生命底色,在他们成长的岁月里持续地施加影响,使得他们避无所避,华裔青年在美国社会中,受到中国身份的牵绊,在思想和行为上同时被两种文化犁下了痕迹,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之中。
二、婚恋的男性气质与身份焦虑
由于渴望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华裔青年往往将白人女性视作理想的伴侣。通过与白人女性的结合寻得一种归属感,缓解身份认同的危机,这可以看作是华裔青年完全西化的一种途径。正如雷祖威在访谈中说,“如果你和白人女性约会,就会有某种授权的意味,尤其是对亚裔美国人来说。人们总是在谈论‘阉割’。”[1]207得到白人女子的青睐,是华裔青年证明自身魅力和男性气概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们成功融入主流社会的标志。但在雷祖威的笔下,华裔男子和白人女性的恋爱、婚姻,无不是以悲剧告终。在短篇小说《生日》中,华裔青年华莱士与离异的白人女性西尔维娅的爱情以西尔维娅回到前夫弗兰克身边而结束。
华莱士的父母一直希望他能够找一个中国姑娘,但是华莱士对白人女性有一种痴迷。在开车来父母家的路上,他从收音机听到了加利福尼亚兀鹫濒临灭绝的讯息,于是他就想到:
我便想象自己是一只处在进化尽头的兀鹫。我感到血管里汩汩地流淌着原生浆液,眼盯着同类中最后一批雌鹰,我的整个身体颤抖着。我知道该去寻偶交配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干。对啦,我该先挑个对象。但哪一个好呢?我把她们逐个打量了一番,仅存三只了。她必须有优秀的基因才行。最后,经过仔细地考虑,我选中了——她,一只长着金黄色尾羽的雌鹰。然后,我听到了父亲的声音:“不,不是这个,是那个。”[2]47
金黄色尾羽,隐喻白人女性金黄色的头发,毫无疑问,华莱士认为在黑、黄、白三个人种中,白人是更高等的人种,拥有更优秀的基因。而作为华裔,处于“进化尽头”,暗示着华莱士对华裔血统的轻视。华裔的血脉已经无法再继续“进化”,因此就需要一个白人女性来改良基因。这不仅仅是华莱士的看法,也是雷祖威笔下,近乎所有华裔青年男性所秉持的观念。
华莱士希望能寻得一个白人女子作为伴侣,即便是像西尔维娅这样离异又带着一个孩子,也在所不惜。他在与西尔维娅的相处中,时刻扮演着一个讨好者的角色。西尔维娅要试探他对于自己的感情,叫他去偷她的前夫弗兰克的收音机,华莱士看到“收音机随着一个身材结实得像重量级拳击手的男子进了一家健身俱乐部”[2]46。冒着“重重挨揍”的风险,华莱士偷到了收音机,当他提醒西尔维娅“那个男人的拳头比我的脑袋还要大”时,西尔维娅却刻薄地笑着说,“弗兰克不会伤害他没娶的人”[2]46。此时,任何人都能看出,西尔维娅其实是在戏耍华莱士,但华莱士却认为,“她那时还在从婚姻失败中慢慢恢复,因此不相信别人所说的一切,尤其是事关爱情”,直到西尔维娅出走,华莱士还在一直等待着她,他坚信“一旦她心口的创伤愈合后,她会回家的”[2]45。直到华莱士在弗兰克家的窗户上看到西尔维娅回到了这里,回到了她前夫的家,他才真正死心。
美国的男性气质往往充满侵略性和力量感,“暴力与成功的联系在美国根深蒂固”[3]。美国崇尚的是强壮的、有征服力和侵略性的男性气概,男性的财富、地位和身体形象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华裔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只能做诸如开洗衣房之类的工作,因此他们大多不可能拥有财富和地位,只能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同时,华裔二代虽然在美国长大,接受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教育,但早期在中国式家庭中受到的训诫却持续地把他们推向中国式的性格特点,他们往往更加内敛、胆小和怯懦。如张敬钰所言,“在美国持久的地缘文化背景下,雷祖威小说中的主人公总是发现自己缺乏霸权的男子气概。”[3]67华裔男性发现自己不符合美国意识形态所崇尚的男子形象,是中国文化对男性的不同期待所造成的。张敬钰在评论中反复强调中国“文”和“仁”的价值判断,含蓄委婉、温和理性,是中国传统哲学和伦理体系对理想人格的期许。由此塑造的华裔男性,会经常性地发现自己无法胜任美国化的“男人”角色,他们会表现得更“女性化”,甚至于在美国,很多女性都比他们更加刚强和富有人格魅力。正如赵建秀(Frank Chin)所说,“亚美历史上,黄种男人常常被再现为女性化的异类,他们缺乏男子气概,女性化,柔弱,没有胆识与创新,不够积极,缺乏自信与活力。”[4]当华莱士和西尔维娅抱怨弗兰克的拳头比他的脑袋还大时,弗兰克高大、自信的身影完全笼罩了他瘦小文弱的身躯,华莱士的男性气质受到了阉割,而这也不可能是西尔维娅所需要的真心。西尔维娅情愿回到一个曾经家暴她的男人那里,也不肯和华莱士这样的男人一起生活,足见得美国价值观中对男性力量和个性的追求。
在《爱的痛苦》中,阿伟作为华裔男性,同样有着男子气概的焦虑。他的第一任女友,曼迪,与他的母亲庞太太相处融洽,她学习了汉语,又对中国传统习俗有深入的了解,穿着也大方得体。庞太太对阿伟说,“如果你娶一个不是中国人的姑娘,她倒是正合适。”[2]6曼迪和阿伟分手后,又在和一个日本人交往,阿伟想到,“我不知道自从她离开我以后她是怎么度日的。当她需要那点玩意儿时,她也和伊藤玩同样的把戏?……京岛说过现在是该改变了,光激发男子气的麝香已经不行了。”[2]7他对来自于同一文化圈的日本男子表达了担忧,他们在与白人女性相处的过程中,往往很难拥有自信和活力,总是在白人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下瑟瑟发抖。
男性气质的性别想象是由美国白人霸权形象构成的,他们是白人、异性恋、肌肉发达、有财产[5],所以《野蛮人来了》的主人公斯特林不得不仰视那些拥有男子气概的模型,而留给他的只有自我厌弃。他认为标准是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他不止一次地站在浴室的镜子前,把这位演员的照片举到他的脸上,衡量他的自我缺陷程度[6]。他完全把美国白人男性的优越感内化了,在俱乐部,他的工作场所,他盯着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的复制品,仔细观察每一寸,将自己和大卫比一比。然后他困惑了,“但如果他是理想中的男性美,那我该怎么办呢?”[6]因此,路易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率直但暗淡的画面,即在斯特林的世界里,没有一个与他相似的男性气质模型[5]82。男性的形象是由白人塑造的,作为一个华裔,在这样的世界中始终是一个异类,他无法定义自己,也无法定位自己。他与白人男性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因此他也陷入了彻底的身份焦虑。除了知道自己来自于遥远的大洋彼岸,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无法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丝了解,因此被白人女性贬低和调笑时,他感受到无能为力的痛苦。这也导致他放弃了父母为他寻觅的完美妻子Yuk,极力追求白人女子布莉斯,最后飞蛾扑火。
华裔二代虽然在美国生活,也习惯了美国的处事方式,但他们处于边缘地带,在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中,永远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他们找不到榜样,也得不到力量。并且,在性格和行事准则上,他们被原生家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中国传统对男性的期许植根于他们的生命中,故而当他们试图和白人女性交往时,会惊讶地发现自己无法遮盖的缺陷。他们急于和父母,和中国的传统划清界限,好一步迈入美国主流文化的大门中去,但是当他们真正和白人互动时,却总是能感受到严重的身份危机,仿佛突然之间就成为了他们曾经轻视的中国传统的一部分。
三、生存危机与新身份的建构
作为华裔,如何能真正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是雷祖威一直思考的问题。他从小在白人社区长大,他认为“这样的一段经历使他在看待作为华裔美国人的自己、父母以及兄弟时有了一个新的视角”[1]198。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自己和旁人的不同,这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创作。雷祖威持续关注着二代华裔的生存危机,他们如何在文化夹缝中构建自己的身份,是他着力表现的问题。作品《遗产》蕴含着雷祖威对华裔身份的思考,他描述了一个华裔女性艾德娜在美国的生活,她乐于作一个激进人士,却也为她的行动付出了代价。最后在吴太太的小屋内,她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基因”,认同了自己的中国根。中国身份不再是牵掣华裔在美国生活的羁绊,反而成为了最大的助力。
艾德娜是一个完全美国化了的女性。她受教育程度很高,着装新潮,经常参与政治活动。一天夜里,他们居住地的妇女健康联合会遭到轰炸,第二天清晨,她和一行人奔赴现场抗议轰炸。艾德娜接受了电视采访,晚上就在电视节目里侃侃而谈。她毫不顾忌地谈论,说“轰炸是恐怖主义之举,受总统怂恿,又被司法部长包庇”[2]188。她自认为做得“令人称道”,一些朋友们也为她的“政治勇气”和“严正的道德感”而祝贺,但同时也有一些匿名电话说要烧掉她的家,并割掉她的子宫[2]188。她的父亲艾德塞尔和她说,“当中国人不在电视上表演烹调时,我们知道有麻烦了。”[2]189艾德娜的教育经历告诉她言论自由,但是她显然没有把握好所拥有的自由边界。紧接着,她所工作的学校打来电话,说教务会将在下次会议上讨论她的事情,在此以前她将不能在校区教书。艾德娜从前是一个“消极活动者,一个鼓掌者,一个爱凑热闹的普通老百姓”[2]189,只参加政治活动,不喊口号。而她第一次转为“积极活动者”时,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自己战斗的成果,政治就已经显露出尖利的獠牙。很显然,此时此刻在美国,这并不是华裔应当插手的事务,当人们发现一个华裔在公共场合侃侃而谈,说一些富有争议的言论时,他们会感到错愕和愤怒。从幕后走向台前,同时也预示着极大的风险。
时隔几天之后,艾德娜在路上又迎面碰见了记者。记者阴魂不散地追逐着她,请求她说一些妇女们支持的话,而她已经不能再冒上电视的风险了。艾德娜于是冲进了隔壁吴太太的房子。中国式的小屋给予了她庇护,隔绝了“自由、民主”的外在空间带来的危险。她在那里看到了满屋的箱子,想到了她的母亲从曾经延绵不绝的飞灾横祸中培养出的“藏东西的本能”,同时也因为节约而得以给女儿留下了上千块钱的遗产。在吴太太家的照片让她回忆起了自己家里的照片,照片上祖母巨大而粗糙的手。这双手又和母亲的手重叠了,她联想到母亲的手,那双粗笨的手曾经对她施以教训。想到母亲的严厉苛责的同时,她也意识到了母亲所经受的苦难,儿子女儿孙子都死了,她一直在痛苦中坚强地活着。“如果她没有失去儿子,或者如果我是她的第二个儿子,她的这双手可能永远不会这么粗大、这么难看。”[2]205当艾德娜终于重获自由时,她再一次朝院子里看去:
这一次,我看到的不再是最微小的东西,我的视线越过了难以逾越的距离:薄雾笼罩的灰色山脉、笼中的小鸟、稻田里分开腿劳作的女人。好一副中国南部的景色……这是缠绕在我的DNA中的谜,是我基因的最初颜色,它就是我的遗产[2]208。
阅读中,我们一直认为遗产是指母亲给艾德娜留下的钱物,而直到最后一刻,我们才了解到,遗产指的是中国的基因。在吴太太的小屋内,艾德娜联想到了自己母亲的境遇,之前的困惑都迎刃而解,她从这时才真正理解了中国文化的内核,发现了,反思了中国女性所具有的坚韧、勤劳的品格,和中国人在各种极端情形下艰难求生的韧性。她认可了她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身份,由此也承认了她身上所具有的中国基因。
雷祖威并没有停留在华裔对中国身份的认可,在《野蛮人来了》的最后,他以隐喻的形式提出了华裔真正进入美国社会的可能性策略。在殡仪馆的厨房里,斯特林试图为儿子摩西找一份合适的零食。他把手头的每样东西递给摩西,但摩西接连拒绝了。突然,斯特林想起了父亲放学回家时给他做的零食。这一段故事沉浸在食物的比喻中,斯特林由此完成了从试图融入美国意识形态到归乡的旅程[5]81。斯特林通过制作并食用父亲的炖饼干,建立了与摩西的联系。有趣的是,这道食物既不是中国菜,也不是法国菜,而是他父亲从一个生活贫困的移民单身汉那里学到的。在这部小说中,斯特林既没有通过正宗的中国菜获得中国人的身份,也没有抛弃自己的根,成为一个流浪者。因此,种族认同应当被认为是一个特定群体基于个人和家族的历史以及实践来建构的[5]81。正如路易所言,“我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这些关于转变的想法也是让自己成为华裔美国人的一种方式,就像弗兰克·陈(Frank Chin)最初提出的观点,即我们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1]210美籍华人的概念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自然存在的,所以中国人不需要用这个概念来框定自己。他们必须理解自己是拥有多种族遗产的角色,不应被中国或美国的文化传统所束缚,而应该创造自己新的、自主的文化,融合中西文明,成为美国社会的新部分。雷祖威对这样一种文化形态的思考仍旧是模糊的,因此他只能通过隐喻的方式表征自己的态度,即完全追求西化或回归中国传统都是不可取的。华裔应当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这种身份是不同文化碰撞、融合、变化的结果,是由多种传统组成的,因此也更具有包容性。
亚美历史学者高木在《他岸来的外邦人》一书的结语中写道,“今天,亚裔美国人所处的美国和早期移民进来的美国截然不同。他们不再是反异族通婚法的目标……尽管如此,他们在许多方面,仍旧痛苦地发现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仍旧被视为‘他岸来的外邦人。’”[7]第一代移民在中国时就受到了严峻的生存考验,旧时代的封建政权培养了他们任劳任怨的品格,因此,即便美国有诸多不公,他们也甘于忍耐。而新一代的华裔青年在美国出生,自小接受了自由平等的教育,因此当理想和现实发生巨大碰撞时,他们往往不知该何去何从。美国与中国的巨大差异让他们时时刻刻感受到撕裂,他们积极追求着美国身份,却又被中国身份牵制。在这种双重身份的重压下,雷祖威通过《遗产》和《野蛮人来了》,给予了一种解决策略。基于肤色和文化,华裔青年需要对自己的中国身份有真正的了解和承认,同时也不被中国的传统和观念所束缚和捆绑。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华裔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不单单是盲目追求完全的西化。追求完全西化只能永远活在白人的阴影之下,而将自己封闭在中国传统的囚笼中又阻断了沟通和交流。只有在中西之间找到平衡,才能够形成华裔自身的身份认同,以此在美国立足。正如西华盛顿大学俞宁教授所说:“接受自己与生俱来的本色而不再追求所谓‘真正的美国人’的感觉,才能与造成历史不公的形形色色因素作斗争,才能为自己现在所在国的社会健康发展做贡献。而这也毋宁说是要重新定义美国文化中的真正主流;理清它,保护它,使它不受充满歧视与偏见的假主流的污染与篡位。”[8]雷祖威对未来的美国华裔充满希望,在他看来,种族将不再是中国人和美国社会之间的裂痕,而是他们得以立足美国主流社会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