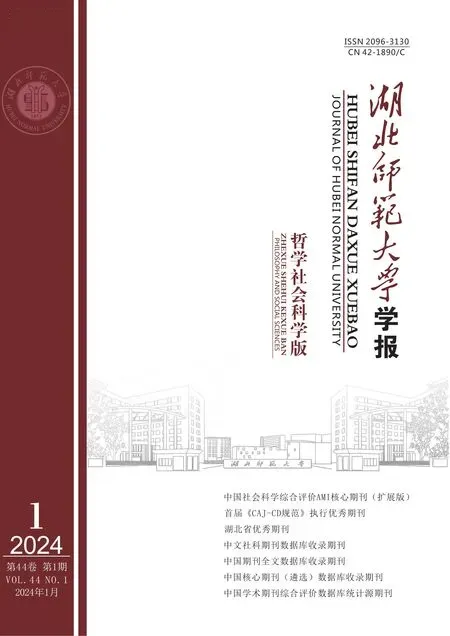蔡文甫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认同
孙晓东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7)
中华文化是凝聚民族向心力和维系两岸价值认同的重要文化根基。然而,近年来随着“文化台独”势力在台湾的抬头,中华文化在台湾本土不断受到排挤,中华民族在文化根源上面临被分化的危险,不少台湾民众,尤其是当代台湾青年人在中华文化认同上产生了疏离感,对作为国家民族认同的有效根基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产生偏移。有论者曾对在大陆高校就读的台湾大学生群体的中华文化认同感进行过调查,发现他们在中华文化的了解程度、自豪感以及学习主动性上还存在一定问题,缺乏中国人应有的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1]。因此,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21世纪,进一步强化中华文化认同感,增强两岸人民的心灵契合和文化自信力,夯实海峡两岸未来发展的基石和反对文化“台独”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正是基于此,对中国文化的精神产品生产者的台港暨海外华文作家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认同问题开展研究,进一步探寻中华传统文化的域外传承和发展也便具有了显在的文化意义和现实价值。
蔡文甫(1926-2020)是“台湾文坛上资历较深的小说家”[2]。他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不俗的成绩,自20世纪50年代登上台湾文坛以来,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雨夜的月亮》《爱的泉源》,短篇小说集《解冻的时刻》《女生宿舍》《飘走的瓣式球》《磁石女神》《玲玲的画像》《移爱记》《船夫和猴子》《小饭店的故事》,散文集《闪亮的生命》等十多部,获中山文艺奖、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奖章暨荣誉文艺奖章、大韩民国文学奖等诸多文学奖项,而且他还长期担任《中华日报》副刊主编,创办台湾纯文学出版机构中著名的“五小”出版社之一的九歌出版社,在编辑出版等文学活动中竭力扶持文坛新人,提携后进,为台湾文学经典积累资料,尤其是其主导出版的两套《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更是堪称1970-2003年“台湾文学最佳断代史”[3]。蔡文甫创作文类以小说为主,兼及剧本、广播剧、散文。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他始终坚守民族传统的善、忍、宽容的本性和道德主题,在台湾文坛西风劲吹、中国文学传统面临背离的情势下,以其丰沛的创作“具体而微的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萃”[4],“写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人性困境、人性的挣扎、人性的异化及情感的冲突”[5]及其对中国民族传统精神回归和中华文化认同的思考与诉求。
一、在平民人生的悲悯与关怀中承续儒家文化
1926年,蔡文甫出生于江苏中北部的盐城建阳镇。这里人文荟萃,文化底蕴丰厚,陈琳、晏殊、施耐庵、罗贯中、孔尚任、李汝珍等历代文人都曾留下传诵千古的诗文著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曾在此倡修“范公堤”,为世代颂扬。蔡文甫家诗教传统浓厚,长兄是个读书人,家里办有私塾,因此他自小便在长兄严格督促下,在家办的私塾里诵读《孟子》《左传》等经史古籍、背诵诗词以及课余翻看家中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封神榜》《金瓶梅》等,接受最初的旧学训练和文学启蒙。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明里暗里地在心里立下了根,塑造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决定了他的文化态度与创造性人格。儒家中“泛爱众”等超越阶级、蕴含人道主义、救世主义情怀的民本传统思想不仅涵养了他传统文人的民本情愫、人格风范和古典情怀[6],而且也给了他一种“积极入世”的忧患意识,尤其是他年未弱冠就开始管理家里磨坊,抗战中进过流亡失学青年扬州招致所,流落江南后在宜兴镇公所担任过户籍干事,最终又投身军营,因而对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和人生困境感同身受,于是在创作中他并没有试图去驾驭宏大的历史与时代主题,而是从自己的生存体验出发,将创作视角对准来自生活底层的平民百姓,描摹普通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人性的寂寞,同情甚至嘲讽处于社会变动中人生的众生态,表达对广大民众现实人生困境与苦难的深切忧虑和关怀。《绿衣使者的独白》中的邹平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维持一家生计,可是命运总是像和他开玩笑:因信件误拆而被局里处分;信件签收时无端被主人家黄狗撕咬伤;送执照被主人薛课长戏弄投诉;工作原因常被同事嘲笑,等。他工作得很憋屈,想辞职以换回人格的尊严,可面对妻子的不解和孩子的天真,他只好打消念头,强作欢颜。作者通过邹平日常工作画面的串接,使人们看到一个处在底层的小职员生活的无奈以及生存的艰难。《新闻一则》虽是作者看到报纸上一则短新闻凭想象写成的,但透过故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底层普通市民生活所面临的生活困苦和人性挣扎。吴老头中风偏瘫在床半年,幸亏女儿兰英悉心照料而最后康复。康复后的他奇怪地发现一向乖巧懂事的女儿行为反常,于是有一天他尾随女儿,发现女儿在风月场所做之事,他生病的医药费、房租、日常生活的开销皆是女儿牺牲自己人格换来的,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自责中,“吴老头的精力向被提尽,一步一步地挪往阴暗的墙角,盘膝坐着耐性等候。他双手摸着冻僵的脚踝,一种冷冰冰的感觉使他心酥,但他觉得脸上有两股热流蠕动着,他抓了一把,满手都是泪水,他无声地哭了。”同时,在《小桃子》《寂寞的世界》《老与小》等短篇小说中,蔡文甫还把他人性关怀的触角延展到更为弱势的未成年人和老人,对他们面临的困境与情感冲突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小桃子》中十五岁的擦鞋童小桃子,母亲离家出走,父亲整天无所事事,全部生活的重担都落在他稚嫩的肩上,但即便这样,他依然得不到父亲的赞许,同时还要忍受同行老七的欺负和羞辱,欲哭无泪,欲逃无门。
儒家思想在给予中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同时,也给予他们一种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蔡文甫自然也承袭了这个文化的血脉,因而他小说中不少人物无论是遇到什么恶劣环境或艰难处境,似乎都有一种超升的希望与勇气。《天堂与地狱》中妓女余四巧在饱受凌辱甚至自我作践之后并没有沦落为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而是怀着新生的希望,跟着先前从良的阿兰,亦步亦趋地踏进教堂的大门去寻求人生的救赎与真义,因而“她的脖头也挺得很硬,膝盖也伸得很直”。《放鸟记》中的大弟、《圆舞曲》中的小李、《山高水深》中的单身汉、《距离》中的胡元坦等,他们都曾徘徊在堕落、沉沦或犯罪的边缘,但最后终能因一念之转而悬崖勒马。他主编出版的畅销数十万本的散文经典作品集《闪亮的生命》亦是选取了十位残而不废、不向命运屈服的人,叙写了他们如何突破生命的极限,最终赢得千千万万人的敬佩与赞誉的故事,让广大读者藉此认识生命的真谛,获得无比的信心与勇气。
二、在传统道德伦理的探寻与思考中反思传统理学
以朱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理学是融儒、释、道为一体的中华文化新形态,是继儒学之后中华文化在哲学层面、道德层面、价值观层面的一次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7]。它建立起为普通大众所接受的有序伦理生活,更加注重伦理和道德教化,“把维系家族血缘和群体感情的孝悌观念确定为最具普遍性的伦理模式和最高的道德价值;以忠孝为核心,配合家族本位形成了三纲五常;任何个人的言论或行为都严格受到道德价值和伦理的制约与牵制。”[8]“仁义”“忠孝”等传统道德观成为人们普遍遵循的道德法则。作为一个从传统中走来的小说家,蔡文甫身上不可避免地背负着很强的传统道德伦理感。在蔡文甫的创作中,他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将其对家庭伦理、婚姻、爱情、生命等的思考融入到他小说的主题中,在传统道德伦理的探寻与反思中体悟传统理学,表达了他对以血缘、家本位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文化体脉的思考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理解。
家庭伦理是家庭中人与人相互关系处理的一种道德约束。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理想的家庭应该是一种父慈子孝、兄弟和睦、成员和谐的伦理环境,然而在新旧变动的时代,伦理“相对于道德的义务、‘应当’,它又呈现出某种自在的形态”[9],所以我们在蔡文甫笔下的家庭描写中,既可以看到对充满爱意的家庭礼赞,也能见到他对现代社会家庭伦理沦丧的忧虑。《成长的故事》通过一个重组家庭的孩子洪耀中对后母由误解到醒悟的情感转变,说明他并没有被家庭抛弃,后母没有把他当作“额外人员”,对他是真正关心和爱的。《爱的力量》写的是陆太太亲生儿子小平被车撞死,就在她心里责骂非亲生儿子小马没有看护好弟弟、伤心欲绝而准备服药自杀之时,肇事者叶强的母亲找到她家祈求宽恕,在得知她也是继母时,感到十分震惊,“仿佛一个火花在她的心底突地亮了起来”,她不想因为自己的偏执而再去伤害一个家庭的和美,最后她选择宽恕了叶强,自己也在肇事者叶强后母的感化下重振生活信心,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因为她明白“爱虽是人类的弱点,但确是一切力量的泉源!”然而,同这些人身上充满亲情和爱意相比,更让蔡文甫忧虑的是人伦亲情的淡漠。《不戴斗笠的农夫》就写了胡民高、胡民智兄弟俩反目成仇的事。兄弟俩在母亲刚去世三个月就闹着找舅舅来给他们分家;后又因秧田放水争执,兄弟俩在雨地里打得不可开交,哥哥差点掐死了弟弟,尽管哥哥最后时刻松了手,但是兄弟亲情的丧失还是令人唏嘘的。《三代》中的金老爹老婆去世早,他又当爹又当妈,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成了家,有了孙女,本该享受天伦之乐,却想不到被好吃懒做的媳妇嫌弃,儿子也是娶了媳妇忘了爹,对离家出走的媳妇念念不忘,人伦亲情的缺失让金老爹倍感凄凉。
婚姻是家庭的纽带。在中国传统的婚姻观里,完美的婚姻应该是夫妻间彼此忠诚、相敬如宾,但上个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台湾正处于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在欧风美雨的吹淋下,台湾的社会风气、婚姻观念、家庭结构等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外遇、离婚等事件层出不穷,“更多爱悦多年的夫妻反目离异;更多‘爱人结婚,新郎或新娘不是我’的爱别离伤感事件演出;许多单亲家庭与二度单身者面临困境;在主客观因素限制下受到创伤的非贵族之单身族类增多;外遇泛滥相当程度地威胁着现代妇女……一时之间,触目所及,尽是在轨道外流离失所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10]这样一种风气恶化、传统丧失的隐忧,自然也激发了蔡文甫对爱情婚姻的思考和探索。与当时许多着力表现台湾社会转型期旧式婚姻家庭破裂真相的爱情婚姻小说不同,蔡文甫没有过多地去铺陈旧式婚姻传统的束缚,而是立足于台湾城市中男女的感情纠葛,从婚姻爱情实践中去开掘其丰富而深邃的社会内涵,表达他对中华婚姻道德传统的认知和文化的认同,《释》《背向着电钟》《解冻的时候》《前妻的震荡》等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无论是有“婚外情”,还是有偶然的外遇,最后都无一例外地以极强的道德感阻止了自己情感或身体的出轨。《背向着电钟》中的女主人公恋上了一个既可称为叔叔、又可称老师的男人。这个男人想在拥有现实的幸福婚姻之外,再有一份情感的慰藉。但女主人公和他在一起却背负着很强的负罪感,同他约会时常想到他的太太、女儿小兰和儿子小马,因为他的太太对她很好,去他家总会包饺子给她吃。她不愿再同他保持这种不明不暗的感情,不愿伤害他的家人,于是她在他们经常约会的地方同他说了“再见”,及时地从这张深陷的情网中抽身,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释》写了一个大学二年级女生娟娟与一个已婚的科长黄书友的情感纠葛。娟娟在大二学期暑假去公司打工时认识了当时的科长黄书友,一下子被他英俊的外表迷住了,被他微笑的眼神融化了,“当她把一切贡献给他时,才慢慢发现他是结过婚的人”。虽然她为了应付母亲和她并不爱的袁井宏订了婚,但她还是希望黄书友早日娶她。可是黄书友总是搪塞她,说等她学业完成后再说,实际是希望娟娟毕业后自己主动不要跟他。她最后看清黄书友拖延的目的,也对这个婚外情感到厌倦,在袁井宏跟踪她来黄书友家里时,她当场宣布解除与袁井宏的婚约,同时也平静地同眼前并不可靠的黄书友结束了这个不正常的关系。娟娟以她的理性和平和换回了她一个少女的自尊。《前妻的震荡》则写了男主人公程学安偶遇前妻周萍而引起的一段情感与理智的冲突。十五年前,周萍嫌程学安不懂生活而同他离婚。十五年后,她后来的丈夫去世了,儿子也长大成人了,一天她与程学安在路上相遇,主动关心他现在的生活,甚至有“破镜重圆”的想法。程学安虽然对现在的妻子不关心人、不浪漫很失望,想和周萍重续前好,但又怕对孩子造成伤害,最后选择了隐忍,因为“只要你不负起丈夫或是父亲的责任,他们就要遭受苦难”。
三、在文学传统的承袭与创化中承传中华文化
中国文学是中华文化的外在表征之一,也是体现作家对于中华文化的追寻与认同的重要方面。蔡文甫深谙中国文学叙事传统,明白“在中国叙事传统的发展中,叙事与抒情的杂陈,韵文与散文的交织,讲唱不分,写实与写意的融合,始终是一个重要特色。”[11]因此,他虽曾因其写作形式的不断探索与创新而被台湾有些评论家列入“现代小说”作家之林[12],但纵观他的小说创作,无论是其描写爱情婚姻的《相亲宴》《牺牲》《芒果树下》《三部曲》《化装舞会》《成长的代价》《爱的回旋》等,还是抒发乡土情怀的短篇小说《乡情》,我们都不难看到其深受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及其小说中渗透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运用的传统古典小说的叙述和春秋笔法以及对说书体、笔记体等文体的承传与转换的因子。如短篇小说《三部曲》写的是发生在婚礼现场的一场悲情剧。故事本身并不复杂,小说主人公于乐天始乱终弃,即将和局长女儿桂芳举办婚礼,而这时前女友芳的到场,让这场本是喜庆的事变成了一个闹剧,新娘当众宣布取消婚礼,因为她从新郎前女友给她的信中知道于乐天爱的是金钱而不是她。蔡文甫虽然力图突破传统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叙事格局,采用类似戏剧分场的方式,为故事的发生设置了场内、场外、闭幕三个场景,间或通过人物对话的交互穿插,“打断故事的自然进程,逼使读者随着小说人物感受品味对方人物思绪的飘荡和脉搏的跳动”,但是从整个小说的架构看依然是一个中国传统的男欢女爱的爱情故事框架,而“不是以小说人物思绪为叙事结构的中心”[13]。小说的微言大义隐于开篇之时,显在收束之处,开头喜庆场面的渲染和结尾新娘带给宾客的震惊,有“空谷传声”之神妙,也与脂砚斋批《石头记》所说的“双峰对峙”效果有着某种承袭。故事的叙述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现、有阳有阴,三个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回环往复,这样的结构手法与中国古典小说在情节设置上峰回路转的结构艺术如出一辙。外场中的通篇对话描写则把读者邀入故事,像中国传统“说书体”文学中说书人角色一样走近故事,感知故事紧锣密鼓推进的节奏,跌宕起伏的情节描写被作者意化到男女主人公你一言我一语的对白之中,让大家看到在一片喜庆的氛围里两个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物在那里算着陈年旧账,上演着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而且作者语言老道,用笔又极为俭省,对人物内心深处的刻画细致入微、言简意赅,三言两语就凸显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颇有中国文学传统的“春秋笔法”之风。因而蔡文甫在现代小说技巧实验外表的背后,流淌的其实是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他曾直言他的创作受“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影响,同时也对鲁迅、巴金、茅盾等“五四”作家的作品“印象深刻”[14]。实际上是他“借了现代小说的结构与技巧元素,编织的依然是带有中国传统与古典情怀的文学空间。”[15 ]
然而,蔡文甫毕竟是在台湾现代主义思潮大行天下的情势下登上文坛的,西方现代主义理论与创作技巧等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的小说观,诱发他的审美情趣的变化。但他温文尔雅的文人情怀和深埋在骨子里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又“使得作家在面对西方文学时,不是一味地采取横向的移植,也没有进行简单的模仿,而是能够融贯中西,回到民族文化文学自身,发掘传统文学中的现代特色,形成其小说独特的风格和艺术韵味。”[16]因此,蔡文甫对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技巧地汲取很“节制”,更多地来自于传统的创化,“在借鉴中自觉融入思维的传统方式及审美意识和艺术技巧的传统观念,穿行于现代与传统之间,使得民族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思想、艺术方法和艺术技巧相得益彰,达到一种有机的交融。”[8]他对意识流手法的吸取就很好地体现了他对传统的创化。意识流作为西方现代主义创作的重要标识,它要标示的是存在于基本意识外的记忆思想和情感,因而它们对联想、想象、内心独白、梦境、象征、暗喻等表现手法格外倚重,并将之视为进入内心世界、展示曾经难以忘却的记忆和情感的一种手段,但随之带来的晦涩、难懂以及意识流动的无序,有时也会让普通人望文生“畏”,云里雾里,影响着文本情节的传达与情感的表达。蔡文甫在其小说创作中没有一味地照搬,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积习的基础上用心体悟而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如在《成长的故事》中,蔡文甫就将西方意识流手法和中国传统“意象”描写结合起来,通过小主人公洪耀中对屋外那棵象征母爱的凤梨树的依恋,展现一个重组家庭里男童对真正母爱的渴望。作者把洪耀中对生母的爱和对后母的怨恨以及对家庭的冷漠通过剧烈的心理活动串联起来,用想象去追忆曾经的母爱。而眼前寄托生母爱的凤梨树死了,生母的爱也将远去,洪耀中也在暴风雨之夜一下子长大了。中国传统的象征手法与想象、联想、象征、回忆等在这里得到有机融合,具体而传神地传达了一个儿童成长的心路历程。《鸽子与田鸡》则用“鸽子”和“田鸡”这两个意象象征着两种不同的人生,通过女主人公左宜贞对“鸽子”和“田鸡”情感的偏嗜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具象化为一幅幅生活画面,让读者在意象与画面的组接中慢慢地品读、体会和思考,一步步走进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寻求一种内在的故事情节发展的必然性联系,探寻女主人公复杂而又矛盾的情感价值观。左宜贞在虚荣、贪图享乐的错误人生观的导引下抛弃了深爱她的吴道之,而与有着金钱、权力、地位的有妇之夫汪经理走在了一起,但人生和地位差异的鸿沟使她最终难逃被抛弃的命运。
四、结语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之魂。对于许多新中国建立前去台作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已融入他们的生命底色,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基因性存在。背井离乡的境遇也使他们对故土、亲人的思念与眷恋更加强烈,对中华文化的孺慕之情由此变得日益浓烈。因而,在与异质文化的交流与交锋中,他们不仅能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的精神底蕴与价值旨归,而且还由于中华文化本身的博大精深,进一步发展为其内在的文化立场和关注的文化视域,使中华文化因子或显或隐地表现于不同历史时期创作的思想主题、意象意境以及叙事传统之中[17]。蔡文甫与生俱有的“中国情结”使其作品必然承袭中华文化传统而对中华文化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与认同,他文学创作的精神内核始终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保持着深刻而紧密的联系,“以一种不露声色的‘道德说教’来演绎民族传统中人性的善、恶、美、丑的主题”,而“没有刻意去突显西方文化中的个性与自我”[8]。扎根于心底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情结也使他在台湾文坛上无论是面对“西风”的劲吹,还是面对“乡土”的声名鹊起,都能保持自己的创作定力,坚持中国文化自身的表达,进而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精神文化家园,也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并延续了中国文学传统的精髓。他融传统于现代的创作追求、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以及对时代、社会及人生的思考于一体,也最终使他成为台湾文坛上一个风格独具的重要作家。他对中华文化的弘扬与发展所作出的个人化探索与“现代”式补充,也为两岸人民的心灵契合和中华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很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