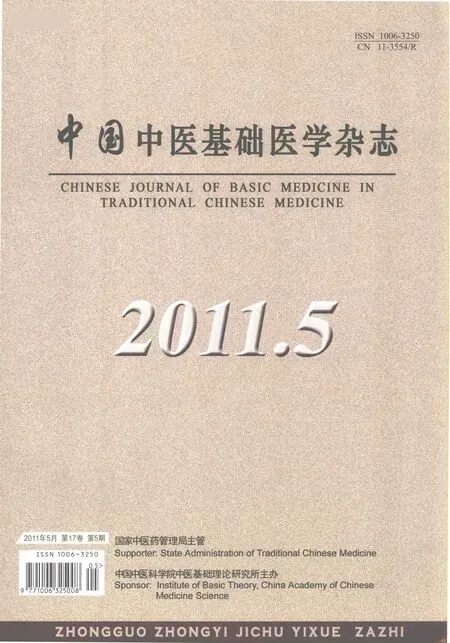李东垣黄连用量规律探讨*
宋 佳,傅延龄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李东垣虽为补土派创始人,喜用健脾益气升阳之品,然而他亦善用苦寒清热之品,遣药制方灵动活泼而不失精当严谨。笔者拟以黄连为例,就《脾胃论》、《兰室秘藏》及《内外伤辨惑论》3书中的方剂对李东垣黄连的用量规律进行探讨。
1 用量统计
据统计,《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3书所载方剂,除却重复者共324首[1]。笔者统计,其中运用黄连的方剂共有86首约占26.5%,包括内服方72个,外用方14个。在72个内服方中需煎汤服用者共44个,作丸服用者27个(包括制丸如梧桐子大者12方,如绿豆大或绿豆1倍大者7方,如弹子大者1方,捣如米粒大者1方,如鸡头大者1方,如黍米大者5方),调膏服用者1个(清空膏)。
在72个内服方中,除益黄散无明确黄连剂量记载外,余者71方皆有明确的剂量记载,需煎汤服用的44方可以明确计算出1服黄连的用量,因李东垣书中绝大多数方子仅有每服药量,并未注明日服次数与连续服量,给折合黄连日服量与连续服量造成一定困难。考虑到宋金元时代的方书体例类似,笔者参照当时影响较大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论饵服法》中的服药方法,无论制丸进服还是煎汤进服者,凡未注明日几服者皆为每日1服,因需要多次进服者有注明,如熟干地黄丸方后“日进二服”与朱砂凉膈丸方后“日进三服”,这样可以计算出李东垣方中的每日服量。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中考证的宋代权衡量值1两相当于现今41.3g[3]折算,则44首内服煎方中黄连的每服最大用量为4.1g(防风饮子),最小用量为0.1g(生津甘露饮子)。其中每服黄连用量小于0.5g的方子共12首约占27.3%,在0.5g~1g之间的方子共6首约占13.6%,在1g~1.5g之间的方子共10首占22.7%,在1.5g~2g之间的方子共4首约占9.1%,在2g~2.5g之间的方子共7首约占15.9%,在2.5g~3g之间的方子共1首约占2.3%,在3g~4g之间的方子共3首约占6.8%,超过4g的方子共1首。由这些统计数据可知,李东垣每服黄连量集中分布在2.5g以下的区间,每服黄连量小于2.5g的方子共40首占到90.9%。因这44首内服煎方多没有注明1日几服,皆按每日1服计算,这样得到的每服黄连量亦即每日黄连量。
2 用量规律
2.1 火热壅盛、病势急重者以较大用量清泻之
据统计,每服黄连用量最大者为防风饮子,其次为救苦汤,二者皆是治疗目疾,前者主治倒睫拳毛(现代医学称之为“睑内翻”,临床上常为椒疮与睑弦赤烂的并发症),后者主治“赤眼暴发肿赤,睑高苦疼不任者”。李东垣在《兰室秘藏·眼耳鼻门》中云:“目者,心之使也,心者,神之舍也……脾胃虚弱,心火大盛,则百脉沸腾,血脉逆行,邪害空窍,天明则日月不明矣。[4]”李东垣认为,多种目疾是由脾胃失运、心火亢盛所致。而黄连功擅泻心火及胃肠之火,为治目疾要药。救苦汤中羌活、升麻、柴胡、防风、藁本、黄连各1钱,仅次于方中川芎药量,其疏风散热、泻火解毒之义不言自明;防风饮子方中炙甘草、黄连、人参三药用量等同且最大,皆为1钱,可见炙甘草、人参皆味甘性温、补中益气。黄连苦寒泻热,清心胃之火,正合李东垣篇中所论“脾胃虚弱,心火大盛”之病机。因倒睫拳毛继续发展可引起角膜溃疡甚至产生云翳,因此需投药足量,阻止病势发展。
用量次之的和血益气汤,李东垣在方中“酒黄连”后注曰“治舌上赤脉也”,舌为心之苗,心主血脉,舌上赤脉正是心火亢盛之象,故以黄连清泻心火。用量又次之的“羌活汤”,主治风热壅盛上攻,故该方中防风、酒黄芩、酒黄连、羌活用量等同且最大,盖因风热上攻,故以防风、羌活祛散风热之邪,以黄芩、黄连酒制,偏清上部之热。
2.2 虚实夹杂,病势绵久者以较少用量佐使之
统计结果表明,中满分消丸、朱砂安神丸、益智和中丸、生津甘露饮子、除风湿羌活汤、升阳益胃汤等方中每日黄连用量极小,均不足0.3g。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①此类方剂所治症状皆为虚实夹杂,而虚证较多,如生津甘露饮子治“时有腹胀,或泻黄如糜,四肢痿弱,前阴如冰”,升阳益胃汤治“饮食无味,大便不调,小便频数,不欲食,食不消”,麻黄白术汤治“四肢痿软,不能举动,喘促,唾清水,吐哕”等症,相比前文所列黄连量较大之方,证见虚多实少,故李东垣仅以少量黄连相佐,去邪而不伤正;②因这些方剂所治病证病情较为复杂,即见实邪,亦不若前段所述救苦汤、羌活汤、清胃散类邪热较为单纯,故可重用黄连,药少力专。统观此类病证复杂的组方,均是药味较多,兼顾各方,即使邪热存在,亦非黄连一药所能胜,举例说明之,如治疗消渴病的生津甘露饮子,全方清热之药共有6种,黄连、黄柏、知母、石膏、山栀、连翘,此6种药各擅其用,非黄连1味加大量所能当;③这些方剂常以补中益气、健脾除湿之药为主,如甘草、黄芪、人参、白术、草豆蔻、炒神曲、茯苓等药,仅以少量黄连反佐,使补中有泻、升降相合,既补益脾胃又清泻土中伏火;④很多主治病证病势缠绵,迁延日久,用药非1d能去,治宜轻剂缓图。笔者统计,在每服黄连量小于0.5g的20方中制丸服用约占到一半,李东垣曾云“丸者,缓也”,对病势缠绵日久者当投以轻剂,缓去其疾,使祛邪而不伤正。
3 影响黄连用量的因素
影响黄连用量之最重要的因素是病证,此外,与天时相应也是李东垣考虑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如在“清胃散”一方中,“黄连拣净,六分”后李东垣注曰“如夏月倍之”。又如在《脾胃论·随时加减用药法》云:“如心下痞,呕逆者,加黄连、生姜、橘皮。如冬月,不加黄连,少入丁香、藿香叶”,“如食不下,乃胸中胃上有寒……如冬月,加益智仁、草豆蔻仁。如夏月,少用,更加黄连”。可见,李东垣于夏月常酌加黄连以应天之湿热之气,于冬月慎用黄连以应天之凛寒之气。笔者认为李东垣此意正体现了天人相感之哲学观,值得后人借鉴。
4 小结
黄连为古今医家常用之药,李东垣对黄连一药的运用灵动活泼,并不拘泥于传统之泻心胃之火,对风热、阴虚所致内热等证皆可配伍相用。与现代临床用量对比,李东垣黄连用量以小量为主,从上文统计数据可得知,每日黄连用量在2.5g以下者占到44个内服煎方的90%,可见李东垣用黄连量之小,笔者考虑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与李东垣顾护脾胃之思想有关,另则与宋金时期散、丸剂盛行使得用药剂量普遍偏小有关。
[1]严善余.东垣制方用药法度[J].中医药研究,1999,15(3):2-3.
[2]卢嘉锡主编,丘光明,邱隆,杨平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