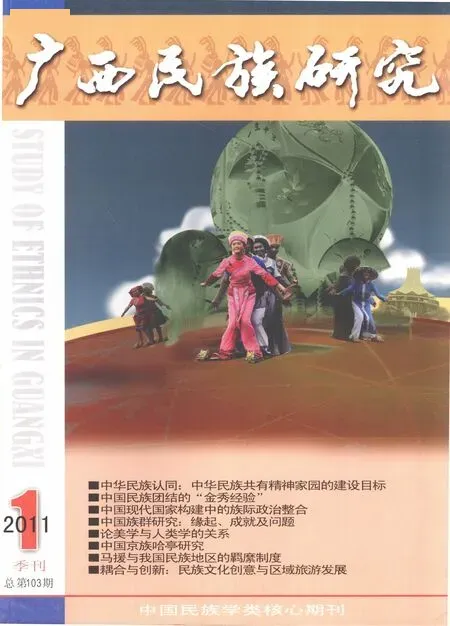走向民族区域自治
——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变迁历史新探
王怀强
走向民族区域自治
——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变迁历史新探
王怀强
对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变迁历史的全面考察是客观认识与评价当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之现实合理性与未来发展可能性的知识基础。作为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总纲领的一部分,中共的民族政策始终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逻辑而不断被重新定义,期间经历了一个逐步成熟、从初期的机械模仿苏联到逐渐立足国情,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最终提出和确立民族区域自治的漫长历史过程。
民族政策;民族自决;民族区域自治
Abstract: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is the precondition to understand the actuality and think the future.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changing history to the policy towards nationalities of CPC between1921 to 1949 is the knowledge base to understand and value the regional autonomy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objectively.As a part of the general guiding principle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the policy towards nationalities of CPC was redefined continually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al logic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own.And it had went through a long historic process from immature to mature,from imitated the Soviet Union earlier to base on the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 later,combined the national theories of Marxism-Leninism with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proposed and established the regional autonomy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finally.
Key words:policy towards nationalities;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the regional autonomy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从建党初期民族政策的萌芽到1949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最终确立,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历史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知识,还在于种种社会制度的连续性把现在、未来与过去连续在了一起。”[1]从这一意义上讲,理解1921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变迁过程对于我们客观认识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合理性、正确审视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与现实功能、并有效预测其未来的发展态势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国内学界关于1921至1949年中共民族政策变迁历史的基本描述有两种:一种是以政治模式类型来分期,认为根据中共民族政策的重心,可将这一过程分为“民族自决”时期与“民族区域自治时期”,这一看法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①。另一种叙述方式是以顺序年表的形式来对这一历史时期中共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进行全景展现,如陈云生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采用了这种方法②。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各有优劣,第一种观点高度概括,简洁直观,为我们认识复杂的历史现实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但同时,这种高度简化的方式也容易误导人们对这一过程的认识。同样,第二种观点虽然有利于展现一种“全景式的、系统的”认识,但也难以完成研究工作“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理论任务,不利于人们从整体上把握这一历史过程。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始终是与党自身对革命中心问题的定义联系在一起的,并随着党对革命中心问题定义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理解1921至1949年中共民族政策变迁历史的基本逻辑。党对革命中心问题的认识以革命斗争发展的客观形势以及由此导致的党自身的生存处境为依据,根据革命形势与党的生存处境,党史学界一般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分为五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党对革命的中心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本文也以这种划分为依据,在此基础上对中共民族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做一简要考察。
一、模仿苏联:1921-1923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民族政策
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处于其初创阶段,期间召开了党的一大和二大,其中,二大明确提出了党对中国和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2]因此,中共关于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的主张基本上照搬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关于民族问题及其政策的基本模式,在理论上具有明显的教条主义特征。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四部分提出:“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③这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文件中对民族问题的第一次阐述,其中已明显表达了一种民族平等的观点。但同时也可看出,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尚未处在中共一大的议题之内。
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念出发,对中国本身和世界上的民族问题首次提出了比较详细和系统的阐述。对国际民族问题,认为其本质在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由此导致的对落后地区人民和民族的压迫与剥削,揭示了资产阶级民族理论的虚伪性,以及资产阶级在落后地区和民族中散布其民族自决、民族独立等政治观念的险恶目的,“帝国主义者还口口声声唱什么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人类平等等好听的名词,想把资产阶级掠夺无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强国压迫弱小民族的行为,轻轻隐瞒过去。”并认为:“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3]
对中国的民族问题,中共二大首次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做出了分析与判断,认为蒙古、西藏、新疆等民族地方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中国本部各省完全不同,因此,在政治上不能运用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的方式来统一中国,而主张用联邦制来实现不同民族之间的联合统一认识。“中国人民应当反对割据式的联省自治和大一统的武力统一,首先推翻一切军阀,由人民统一中国本部,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同时依经济不同的原则,一方面免除军阀势力膨胀,一方面又因新生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对此,《二大宣言》规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包括:“统一的中国本部 (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4]。可见,此时中共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分析具有较为浓重的教条主义和“经济决定论”色彩,但这对一个刚成立不久的政党来说是难以避免的。而且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共提出的这个民族政策基本纲领对当时中国面临的国内外政治冲突和民族问题解决方式的建议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二、妥协与斗争:1923—1927年国民革命时期党的民族政策
1923年6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始,三大《宣言》承认:“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5]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纲领表现出了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与思想的基本原则,主张民族自决权基础上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第二,既与国民党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同时,也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原则与国民党对民族同化政策和大汉族主义思想做坚决的斗争。
为了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不得不做一些调整,以使与国民党的民族政策相适应,这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就可以明显看出。相较于《二大宣言》对民族问题的阐述,《三大宣言》的阐述却相当少,仅限于模糊而一般化地提出:“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6]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只用了“中国民族”这一具有强烈“国族”意义的字眼,而没有具体分开地论述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与政治地位问题。因此,如日本学者松本真澄所言:“就像国民革命实行的方针和步骤不能一致一样,《三全大会宣言》是一个没有言及旧藩部和联邦制的国家形态的构想的不透明的宣言。”[7]
但是,与国民党的合作并不意味着中共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政策的基本主张,而是在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仍然对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自决权的政策主张做了明确表述:“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的关系由各该民族自决。”[8]从这种表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基本理论与国民党的民族政策存在的本质差别。
国民党的民族政策源于孙中山。孙中山的民族思想肇始于反对满清统治,其本身具有极强的种族主义特征,如他定义民族概念的各因素中,占第一位的便是“血统”[9]。虽然随着满清统治的被推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孙中山又提出了“五族共和论”,但这一理论仍有明显的民族同化色彩[5]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特征。虽然此后孙中山接受了苏联帮助改组国民党,同意接受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党内合作”,并在此基础上接受了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自决权的思想,最后还将其写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但本质上,国民党所认识的民族及民族自决与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理解仍有很大的分歧。对于国民党来说,满、蒙、藏等民族与汉族本身就具有“共通的血缘”[10],民族自决权源于国家的赋予而非民族自身的属性,民族自决只是在统一国家前提下的一种地方自治类型,而非苏联式的民族共和国。
国共在民族政策上的分歧自然成为这一时期两党斗争的一个中心内容。国民党站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谴责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苏联式民族自决理论破坏国家统一,促使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分离于中国领土。对此,共产党领导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如陈独秀在《我们的回答》中,强烈批判了国民党民族政策的民族同化本质,并对自身的民族政策进行了有力的辩护:“蒙古人愿意脱离中国与否,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自决权。用不着鼓动,我们也不曾鼓动过这个,我们中反对一班人否认蒙古人民的自决权,硬说蒙古是中国的藩属,主张军阀政府出兵收蒙;因此,我们主张蒙古人根据民族自决权,有独立反抗的权利。”[11]
三、民族政策的激进化:1927—1937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民族政策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爆发结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的白色恐怖和对共产党员的大肆杀戮,给共产党组织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灾难,大批共产党员被屠杀,上海、武汉等主要城市的共产党组织遭到巨大破坏。共产党为了争取国内各族民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支持,表明自己反抗军阀统治和大汉族主义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地表明了自己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纲领,公开倡导和支持被压迫民族人民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实行民族自决权利,甚至到承认民族分立。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最为激进的时期,集中表现为民族分立被纳入民族自决权的选择范围。
这一时期,首次明确将民族分立主张纳入民族自决权实现形式范围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中,“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宣言承认内蒙古民族有自决的权利,一直到分立国家,并且要极力赞助内蒙国民革命党力争自决的斗争。”[12]可见,承认内蒙古民族自决的权利“一直到分立国家”,这与中共二大上提出蒙古、西藏、回疆成立民主自治邦,并用自由联邦制,与中国本部成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相比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时的“民族自决权”的内容,已经与前有了极大不同,包含了支持被压迫民族自由分立国家的权利。
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与严酷镇压下,中共的革命活动不得不退出国民党占优势的中心城市地区而向西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转移,这使中共深刻认识到民族政策对于自身作为一个革命党生存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在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这是中共民族政策走向激进化的根源。关于这些,在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文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六大正式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1928年7月29日)中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 (北部之蒙古、回族、满州之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意义,特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大会之前,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大会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13]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发现此时中共不仅关注蒙、藏、回等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同时,也开始关注国内其他人口较少的民族,如“苗”、“黎”等,并认识到民族问题对中国革命有“重大意义”。这种认识在1929年1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军党部“共产党宣言”》里得到进一步证明: “统一中国,承认满、蒙、回、藏、苗、瑶各民族的自决权。”[14]而在1926年12月通过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解放苗瑶决议案》中虽然承认“苗瑶”的民族地位,但并没有承认其有民族自决权,而只是用了“解放苗瑶”[15]的提法。显然,表述上的这种变化是中共民族政策较为激进的一种明显标志。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对中共此时民族政策做了最为系统的阐述:“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地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16]这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上做的最为全面、成熟的一次阐述,特别是这一分析明确说明了中共对于民族自决理念最深刻的理解。如中共再次重申了其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即主张民族平等及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我决定权利,即民族自决权;同时,中共也对实现这一民族原则的政治形式提出了自己主张:一是被压迫民族可以选择分立并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是最彻底的一种选择,后来一般被称为“民族自决”;二是少数民族在民族平等、民族自主的基础上,成立自治邦,与其他民族成立自由联邦共和国;三是“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进行区域自治,自然,这也必须是各民族在民族平等与自主的基础上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被强加其上的。
此外,虽然这一时期中共民族政策出现激进化,将民族分立纳入民族自决的范围之内,但不能由此就认为中共民族政策主张国家分立,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分立在中共民族政策谱系中所处之位置。本质上,它只是一种与国民党统治进行斗争的策略性考虑,这从中共对其民族政策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使用的“一直承认到,”则明显表达了少数民族“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自己的国家,”只是中共民族政策中一较为极端的选择,是民族自决的底线。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共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其本意并非主张民族分裂,而是国家统一与民族平等并重的基本选择。这与中共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1928年7月9日)和《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号—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1928年9月17日)中“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17]的阐述是一致的。
同时,这一时期,特别是在长征过程中,中共在其经过的少数民族地方,为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建立了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如红四方面军在藏族聚居区支持成立的格勒得沙共和国、波巴人民共和国等。红一方面军支持成立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等。这些实践使中共的民族政策真正从文件变为现实,为中共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民族问题,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与民族原则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创造了现实条件,也为中共以后民族政策的正确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民族政策的转变: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民族政策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造成了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剧变,在中华民族“亡国灭种”之祸的严酷现实面前,国共两党不得不停止内战,从昔日的死敌转而联手共拒外敌。民族自决权原则作为中国共产党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日本侵略、争取国内各少数民族群众拥护的有力武器,现在不得不再次做出必要调整。同时,抗日战争的爆发,也为中共重新认识中国民族问题的本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提供了新的条件,并最终导致中共民族政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这种调整首先表现在中共运用民族自决权理论动员少数民族时,去掉了“反蒋”的内容,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抗日”。其次,这种调整表现在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运用上。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15日)一文中,分别用了“我们民族”、“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18]等词语,而全文没有提及蒙、藏、回等国内民族问题。“中华民族,是本世纪初出现的称谓。开始用来指汉族,辛亥革命以后,越来越普遍地用来作中国各民族的总称。”[19]可以看出,大量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而不再分别提及国内各民族,用意明显是为了强调国内各民族在中华民族范围内的整体性和利益上的一致性。
此外,这时中共在民族自决观念的使用上具有越来越明显的策略性特征。如虽然中共认识到民族自决概念与抗日统一战线之间存在的潜在矛盾,主要对民族自决话语的运用做出适当限制。但日本为了将中国分化瓦解,更快地占领中国,却大肆运用民族自决来迷惑满州、内蒙的少数民族人民,煽动他们从中国分立出来,以便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的宣传使满蒙不明真相的许多民族群众受到了欺骗,尤其是在一些旧的上层满蒙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而投靠日本后,更多的满蒙少数民族群众陷入了思想混乱之中,这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由此,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重新审视并强调民族自决权原则的运用,如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1937年10月16日)一文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反用赞助各少数民族的独立自治去欺骗,这是很危险的”,“只有承认少数民族有独立自治之权—才能取得各少数民族诚意的与中国联合起来抗日。不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就不能有平等的联合。”[20]这段话凸现了民族自决权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工具理性特征与中共对其运用的策略性思考。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断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从抗战开始的策略调整进入到实质性转变,这一转变发生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一文第四节中,第一次讲到:“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在该文第五节讲到关于“抗战建国”时,在回答“建立一个什么国”时,运用和发展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认为首先“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在这一前提下,“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21]这是中共首次在重要文献中将国内各民族置于“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和“建立统一的政府”的大前提之下,与上文提及的刘少奇的讲话(《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中“各少数民族诚意的与中国联合起来抗日”一语相比,有了根本不同。这种政治话语的转变其内含的逻辑是有关民族与国家的相对位置关系发生了转换,即从完全的民族本位转变为民族与国家的二元本位。所谓民族本位指一切以民族利益本身为出发点,为了保障民族利益抽象地主张任何民族 (包括国内各民族)都有自主权利选择自己的政治归属,甚至重新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民族与国家的二元本位则不仅承认各民族具有平等的存在权利,同时也承认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现实,民族与国家并重,将这种民族平等置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之下。明显,这种政治逻辑的转变是根本性的。
对“中华民族”概念的使用为这种转变提供了理论条件。毛泽东在同一个讲话中用了“中华各族”一词,很明显,“各族”不可能是仅指汉族。而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年11月6日)中,对此更有明确的表述: “团结中华各民族 (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22]这里明确将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族都归入中华民族的范畴之内了。由此,中国的民族问题完全转变了其性质。如果用现代政治学的话语来表达,这一转变之前,中国民族问题的本质包含着与Nation同一层面的两种关系,即国内的Nation(满、蒙、藏、回、汉等各民族)与Nation(满、蒙、藏、回、汉等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国内的Nation(满、蒙、藏、回、汉等各民族)与国外的Nation(如日本)之间的关系。而Nation在西方既指“民族”,也指“国家”,其思想源头是主张每个民族都应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民族主义古典理论。政治话语的变化标志阗中国民族问题本质的根本转变,国内各民族不再具有Nation的属性,而是变成了用现在的流行学术话语称之为Ethnic④(或称族群)的东西了,由Nation到Ethnic,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消除了国内各民族寻求独立建国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各民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成为最基本的要求。而只有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仍然是Nation(代表国内各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与Nation(如日本)层面的关系了。
随着对中国民族问题性质理解的转变,中共用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政治形式选择也转向了民族区域自治,排除了以前曾主张过的民主联邦制和民族分立。民族区域自治最初是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中提出的:“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23]。此后,虽然在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仍有“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提法,但在各民族联合建立自由统一国家已经成为中共民族政策基本方向的大背景下,这一提法更多只是承担了一种中共民族政策历史衔接与过渡的功能,而不具有实质性的制度建设意义。《施政纲领》关于民族政策的思想和主张,为中共民族工作的进一步实践提供了基本的政治方向。1941年后,许多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指导纲领的地方民族自治政府,在抗日与反抗国内反动势力统治的斗争中正式成立,这些全新的民族工作实践,为中共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不断完善和最终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经验基础。
五、走向民族区域自治:1946-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民族政策
抗日战争的结束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从抗日反帝转向了反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内反动派统治的全国解放斗争事业中,随着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作为其一部分的中共民族政策其中心内容自然也随之发生变化。但从民族政策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这两个时期仍然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这一时期中共民族政策变迁的实质,是用民族区域自治将各民族解放、民族平等与多民族国家统一三者有机结合的过程,促进和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在理论上的成熟和实践上的全面发展。这一转变最终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式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结束。
抗日战争结束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全国人民的独裁统治和对国内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大汉族主义压迫和同化政策,民族政策再次成为中共鼓励全国各族人民起来反抗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的重要政策工具和理论武器。由于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已经对其民族政策纲领形成了由全国各民族自由联合组成统一国家的基本主张。这时,中共对民族权利的主张已根本不同于民族联邦制和民族分立等主张,而是在要求建立统一国家的基本前提下,鼓励被压迫民族人民起来反抗国民党统治。如在《中共中央关于和国民党目前时局的通知》(1945年10月1日)中描述新疆少数民族的反抗时,用了“新疆少数民族起义”[24]一语,“起义”一词既赋予新疆少数民族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又确认新疆少数民族现有的国民身份。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国内任何政治的、民族的纠纷,均应以政治方法寻求解决。”[25]从以上引述可以看出,承认现有国民身份已成为中共看待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前提。同时,中共极力强调民族平等和少数民族自治权,在《评马歇尔离华声明》中,周恩来认为中共与国民党的民族纲领最基本的区别是:“政协主张保障少数民族自治权,蒋宪则取消少数民族自治权。”[26]这一原则性的阐述,既默认了建立统一国家是中共与国民党的共同政治追求,同时,也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我党在少数民族自治权问题上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
1947年4月27日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在中共民族政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在一个较大的地域范围内,以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为指导,由一个民族建立自己的自治政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1947年4月27日),不仅代表了中共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对自治政府的政治目标、性质、指导原则,以及与国家的关系等,都做了十分明确与详细的规定。这是第一次以一个自治区为对象,对中共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基本内容做了如此全面而详细的阐发。此外,《施政纲领》还对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必将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都做了全面的规定和补充,如自治区内的公民权利保障、权力组织、民族武装、教育、宗教信仰、干部培养、经济生产等等。这些都为民族区域自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此后,中共的民族政策在理论上更趋系统和成熟,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一文对中国的民族问题及其与国家建设的关系作了重要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文中还明确提及民族自决权。他说: “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27]在“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的同时,又承认“每个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里是否存在矛盾呢?其实不然,这里有必要对民族自决权的本质作一说明。民族自决权最早是资产阶级为反抗中世纪的分封割据,建立适应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统一民族市场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在当时,是具有反抗封建帝国统治的积极历史意义的。但资产阶级的民族自决权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天赋权利论,认为民族自决权是“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美国独立宣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就此批判了资产阶级民族自决权的唯心主义本质。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权利都具有历史属性,因此,必须放到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它的合理性,民族自决权亦然。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民族自决权,是在资本主义进行全球殖民掠夺的背景下,为了支持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从而为无产阶级联合创造条件而提出的一种历史权利,如列宁所说,“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独立权,即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其本质“只是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彻底表现。”[28]“我们应当使民族自决的要求完全服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利益。”[29]。因此,当存在民族压迫时,民族自决就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当民族压迫被消除,民族联合与民族团结已成为现实的历史条件下,再强调民族自决权就与它的本质不相符了。
同样,对中国共产党民族自决权原则的运用,也必须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视角之下。中共的民族政策本身就诞生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和封建军阀对国内少数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的历史背景下,因此,在民族压迫与民族剥削最终被消灭,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实现民族大联合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之前,中共强调民族自决权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因此,从中共二大提出民族自决的基本原则,经过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民族自决权始终是中共民族政策的理念基础。即使是被称为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政府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其成立的基础仍然体现了明确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第一条指出:“内蒙古自治政府系本内蒙古民族全体人民的公意与要求”而成立的,“本内蒙古民族全体人民的公意与要求”如不理解为民族自决,那做何解?因此,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中对民族自决权原则的明确态度,一方面表达了中共民族政策的一贯性,那就是对民族平等的追求和对民族压迫的反抗;另一方面,新中国尚未成立,这种表述也明确坚持了中共对新中国民族关系的一种确认,即并不因新中国的成立而否定国内的民族差异与各民族平等的权利。新中国成立之后,民族自决权的表述逐渐从中共民族政策话语中淡出,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中共主张“不再强调这一口号”[30],而用民族自治权取而代之,这种转变体现了中共民族政策中的民族与国家二元本位的最终形成。
伴随着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快速到来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中共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也终于从一党之政策主张而成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具有“临时宪法”功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再次进行了明确的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地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31]《共同纲领》的颁布,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地位的正式确立,成为中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与共同繁荣的基本政治制度形式。
注释:
①代表著作如何龙群的《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宁骚的《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兰州大学许彬的博士学位论文《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民族基本政策的历史转型》;张文淼的《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7期;盖世金的《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载《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宠效松的《中共民族问题纲领的演变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3期等。
②陈云生认为顺序年表的方式比较以政治形式分期的方式有以下优点:一是这种表述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政权关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政治形式的探索有一个全景式的、系统的了解;二是避免了以政治形式类别表述形式通常都不可避免的重复;三是可以恰当地对这段探索的历程作出客观的判断,避免了作者出于个人对政治形式的偏好而可能引起的对读者的误导。(见陈云生《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③此文译自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俄文稿,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展件中,“不分国籍”译为“不分民族”。参见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④国内学界关于“族群”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本文作者无意介入这一争论,只是借用这一词更强调文化属性的特征,来表明中国共产党用中华民族来代表国内各民族之总和所产生的在政治上的重大意义。
[1]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前言).格致出版社,2008.
[2]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35.
[3][4][6][8][11][14][15][16][17][20][21][22][23][24][25][26][27]金炳镐.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12-16,18-19,29,31,34,71,61,89-90,65-69,208,223-225,227,285,333,335,343,409.
[5]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4.
[7][10]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62,81.
[9]曹锦清.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C].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4.
[1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第三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491.
[1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第四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388.
[18]周恩来选集[C](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8.
[19]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111.
[28]列宁选集[C](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8-719.
[29]刘锷,何润.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纲要[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103.
[3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4.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开国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286.
〔责任编辑:刘建平〕
The Road Leading to the Regional Autonomy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a new study to the changing history of CPC’s national policy between1921 to 1949
Wang Huaiqiang
D633.2
A
1004-454X(2011)01-0033-008
【作 者】王怀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