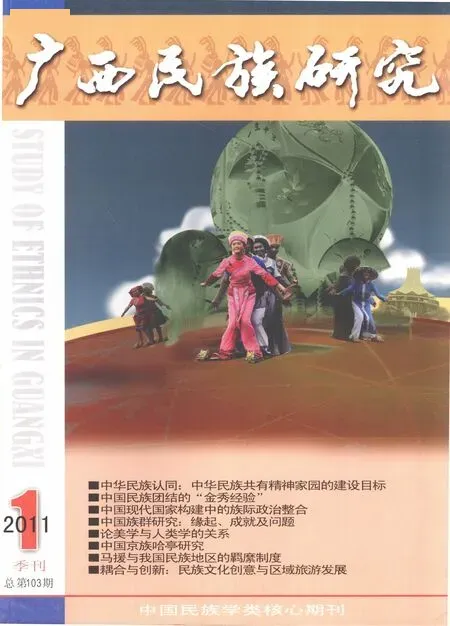“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田野考察的求真之路*
张婷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田野考察的求真之路*
张婷
田野考察是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式之一。做好田野考察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通过互相调查、摆正“自我”与“他者”的立场定位、抛却文化等级主义思想、减少“观察者效应”等方法进入田野。田野考察的最终目的是弄清事实真相、摸清规律,通过走出“他者”、反观“自我”,实现科学性与价值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重视理论的价值,走出田野,促进人类学向着日臻成熟的方向发展。
田野考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Abstract:The field work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approaches in the Anthropology.To do well in the field work,we must dig deep into it’s essence,and observe it beyond its boundaries.Som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for us to dig deep into it’s essence,such as arrange an investigation between the investigator and the native informant,put“Me”and“Other”in appropriate position,discard ideology and cultureclassism,reduce the“Observer Effect”.Besides,we should reflect on our own through“Others”perspective;realize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scientificalness and value,generality and individuality;raise the experiential practice to the level of theory in hopes of pushing the progre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study of Anthropology.
Key words:field work;dig into the essence;observe the field work beyond the boundaries
“田野考察”是“field work”,“field study”或“field research”的中文译法,也称田野调查、田野研究,它是研究人文现象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广义而言,所有的实地研究工作都可称为“田野研究”,包括社会调查访问、各种问卷测验的施行、考古学实地发掘、民族学调查考察等都属之,但是狭义而言,田野工作却特指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考古发掘与民族调查,其中尤以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最为引人入胜。[1]田野考察研究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实地”,即研究者一定要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环境,且要在其中生活相当长一段时间,靠观察、询问、感受和领悟,去理解所研究的现象。[2]然而,田野考察并不等同于实地调查,如王铭铭先生所提到的“心离身不离”式的书斋研究同样也属于田野考察的范畴。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现象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渗入实地调查的工作方法后,现代人类学家在选择田野工作点时,往往聚焦于偏远、边缘的社区与文化现象,其实田野工作地点的选择并不一定拘泥于野外或基本未被开发的地方,只要能够鉴别出某种文化形态的特质,能体现出“他者”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一所学校或一间教室都可以作为田野的现场。本文是针对绝大多数进入他文化中的田野考察所展开的论述,属于田野较狭义的范畴。
研究者通过参与观察、深入访谈等方法收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不是所有的第一手资料都是真实、可靠的,它们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有赖于田野考察的深入度及科学性。做好田野考察,要做到两点:一是“入乎其内”,二是“出乎其外”。费孝通先生也曾在《社会调查自白》中明确提出做研究要“进得去,出得来”[3]。以上两种说法是相通的。这两个要求,看似简单,实则内涵极深。它们是田野考察成败的最关键因素。
一、田野:如何“入乎其内”?
研究者进入异文化的场域中做田野,需要克服与研究对象之间语言、文化上的沟通障碍。即使克服了这些障碍,真正进入田野依然任重道远。如今很多民族学、人类学等研究生为了田野而田野,在考察点待上一两个星期,更有甚者待在当地宾馆中看仪式录像,获取些表面的直观感受就认为是做了田野了,这远远不够。如果仅是停留在表面,搜罗一些无关紧要的数据、材料,而无法进入当地人的心中,无法采集当地人真正的所思所想,依然是没有跨进田野考查的门槛。具体说来,要进入田野,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互相调查
研究者最初进入田野,十有八九是被田野当地人 (研究对象)所排斥的。因为研究者具备一个“外人”的符号。田野之内的人会出现一段时期的敌对情绪。他们不明白研究者的意图,恐惧这些“入侵者”是否会给他们带来灾难。世界各地,很多社区都严禁外人进入自己的社区。即使勉强进入了,有时也会遭到很强的抗拒。例如人类学家乔健在美国拿瓦侯印第安人社区做调查时,当地人曾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的研究对你有好处,对我们却没有好处。”还有人说:“你是从那麻烦最多的地区来的,我们怎能信任你呢?!”[4]在面对突然闯入的陌生人时,研究对象自然会有很重的防备心理,尤其是官方委托派去的研究者,则研究对象的防备心理更重。
所以,研究者首先要被研究对象调查清楚,待他们明确研究者调查目的之后,才可能与之进行合作。大部分研究对象并不需要了解研究的全部内容和过程,他们最关心的是:“研究者是什么人?他/她到底要干什么?我能够从这个研究中得到什么?”[5]要想调查“研究对象”,首先要让“研究对象”调查“研究者”。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这就是一个“互相调查”[6]的过程。
有研究表明,中国人由内向相对的外人传达的信息含量之递减与趋向模糊的大体顺序为:在成年人生活中,表现为,家庭>朋友>同事>上级官员;……乡村生活中,表现为,家庭>宗族>村人>乡镇人>外人。[7]研究者作为相对于研究对象的外人,如何真正进入田野现场,尽可能充分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就要在互相调查的基础上怀着一颗真诚、平等的心与研究对象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
(二)“悬置”自我,走进“他者”
在经过了最初“互相调查”阶段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研究者如何获取研究对象最真实的信息,而不是针对外人的表面的、无关痛痒的或是不属于研究对象真实想法和感受的歪曲事实。走进“他者”,并被“他者”所接受,要注意如下三点:
第一,摆正“自我”与“他者”的立场定位
“他者”是一个哲学概念,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一种符号,一种不同于本我文化的概念。研究者在进入“他者”的文化中时,暂时将自我的文化“悬置”,“忘掉”自己的文化,将自己想象成为“他者”文化中的一份子,充分浸润在异文化中,尽可能的按照“他者”的方式所思、所想,达到“身离心离”甚至“身不离心离”的境界。由马林诺夫斯基所开创的“移情”式主位研究似乎成了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不言而喻的最高原则,[8]这也是我们在人类学中所提倡的文化主位的考察、理解。主位的观点是这样一种研究态度:人类学家从研究对象的观点出发来理解他们的文化,拒绝用我们自己的范畴将他文化切割成零星碎片。如果仅以客位的、局外人角度进行客观主义的研究,对于考察充满价值问题的人文世界来说,甚至会得出违背现实的结果。
然而,对于他文化研究者而言,要达到按照“局内人”的逻辑而思维,在较短的时间内是不易的。每一个研究者都有其所代表的群体和长期积淀下来的思维方式。马林诺夫斯基曾说“不论在哪种情况下,人类学家都应该不带任何偏见地评价现实情况”。[9]可是,研究者是带着灵感与先见进入田野的,要其完全客观不带任何偏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上述所说“悬置”自我,忘掉自我,是一种预期和愿景,这也体现出了主位研究的局限性。在田野工作中,作为研究者是很难仅仅作为一名主位参与者存在的,而是要努力的克服偏见,悬置自我,尽最大可能向“局内人”靠拢,设身处地,研究者忘掉自我,不只想像自己是“他者”,而是要成为“他者”,进而反省主位文化与客位文化异同。为此,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提出了“远经验”(experiencefar)与“近经验”(experience-near)理论。前者用学术语言或研究者自己的概念语言来描述所研究的异文化,后者用当事人的概念语言来贴切地描述出该当事人的文化建构,[10]其目的就在于调和主位与客位研究之间的关系。
研究者在田野现场并非只有严格的主位和客位两种立场,也不能简单的认为研究者是主体,而研究对象为客体。这需要超越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达到一种“文化互为主体性”的状态。研究者需学会换位思考,进入现场要学会一个“融”字,努力成为“他”。要重新确立一种“研究者立场”,它既非“主位立场”,也非“客位立场”,而是一种为了弄清事实真相,理解“他者”为何以此种方式思维、行动而采取的立场。田野考察的目的就是为了求真,为了探究他文化之人、之事的来龙去脉,摸清规律,还原他文化的真相。
第二,抛却文化等级主义思想
文化等级主义是西方“进化论”思想与殖民主义经验结合的背景下产生的。现代田野考查的研究方法多是以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群岛土人中的实地研究做范本的,这是人类学界具有开创意义的考察,也是人类学走出书斋走进田野的典范。但在西方殖民主义大背景下,马林诺夫斯基也曾认为他是“文明人”的代表,他的研究对象是“野蛮人”。在西方严重的种族矛盾背景下,“文明人”才是人,而“野蛮人”不是人,是动物。①我们不否认马林诺夫斯基作为现代人类学奠基人的历史地位,但应看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令人欣慰的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也是日后成为“英国人类学之父”的雷蒙德·弗思 (Raymond Firth,1902-2002)开始意识到,“原始的”、“野蛮的”、“土著的”这几个词不但已陈旧而且还令人感到屈辱,……不论一个民族有多么小也应当受到尊重。[11]他认为文化等级主义的观点是落后的。美国犹太人博厄斯 (Franz Boas,1858-1942)也致力于宣传种族平等、文化平等的理论。然而即使现在世界上持文化等级主义的人类学家仍不在少数,依然存在着的门户之见阻碍了他们发现美的脚步,他们缺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胸襟,因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对其来说也是一种奢望。“文化等级主义”给研究者的双眼蒙上了一层纱,在这种偏见的蒙蔽下,他们就不会从被他们所认为的“野蛮人”和“低等文化”中发现研究对象的灿烂文化。所以王铭铭先生才会说“一个人类学家若不能相对地看待他人的文化,就很难理解这个文化;他若不能理解实践这个文化的人也是人,就很难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12]在田野考察中,特别是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进行考察时,务必避免文化等级主义观念,避免将他文化中的人当物看待;秉承真诚、平等理念,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也不应是盛气凌人的姿态,而是入乡随俗,尊重当地人的禁忌和社交礼仪,真正做到一个“文化价值观的相对主义者”,也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的对话,才是有价值的。
第三,减少“观察者效应”
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初期交往中,常常会出现因研究者在场而造成的研究对象非常态或表演性表现。如某民族地区的村民常会接待研究者的田野考察任务,因不同研究者的问题大同小异,村民早已形成机械回答的习惯,甚至是以研究者所希望得到的答案而并非真实情况来作答。另外,进入田野现场的研究者,有时为了增加自己的可信度,带着单位的介绍信或是批文,无形中又给研究对象的心理带来巨大压力,让他们认为这也许是官方或上级机关来检查的。例如笔者在西双版纳州调查一所学校的教育状况,最初很多教师不配合,认为这是上级教育局派来进行暗中评比而拒绝合作,后期做了大量工作才得以顺利调查。
在受“观察者效应”影响较深的考察中,虽然研究者确实得到了大量一手材料,但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和价值性却是打了极大折扣的,严重的甚至还会给研究者造成误导。这仍然要求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有较长的时间保持密切、持久的接触,使研究者详尽的了解该文化浸润着的群体的传统和价值观,打消研究对象的顾虑,必要时给研究对象以经济或精神上的补偿。研究者需要反思田野考察对于研究对象的价值,目光不可限于狭隘的经济利益,更应从深入的文化价值进行挖掘。研究者创造条件减少“观察者效应”,是研究者获取有价值的一手材料的必要保证。
二、田野:如何“出乎其外”?
田野考察的“入”与“出”并非单纯空间意义上的概念,即:不是说在田野现场就不能“出”,也不是说在本我文化中就不能“入”。有的研究者即使身在田野,但如果只是以客观主义的态度进行考察,也谈不上“入”;同理,即使研究者离开田野现场,回到本我文化中,若受“他者”文化影响太深,无法从他文化中抽离出来,更谈不上“出”。人类学初学者离开他文化回到本文化时会有较长时间的转换期,甚至会在两种文化的漩涡中迷茫。这其实是人类学家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是一种学术上的磨炼。人类学家不能只是“坐在摇椅上玄想人类历史”的人,所以我们重视田野考察;同时人类学家也不能不从田野中“出乎其外”,回到“书斋”,所以还要回归理论研究,从多元中提取共性,从实践上升到理论,这是田野考察体现其学术价值的阶段,也是实现人类学学科成熟的阶段。
(一)走出“他者”,反观“自我”
融入“他者”的文化,是为了能够深入理解他文化中人的行为方式、信仰、价值观。但如果沉溺于他文化中而不能“出乎其外”,则会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弊端。对于他文化如果不能从场外的角度审视就发现不了其精华与糟粕,也不能对自我文化产生有价值的影响。如Bernard所说,“参与观察包括将你自己融入当地人的文化中去,同时又要学会每天将自己从这种文化中抽离出来,这样你才能科学地判断你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事情,才能比较科学地记录和分析这些材料。”[13]参与观察是田野考察方式的一种方法,其特点对田野考察仍然适用。所以,人类学家需要走出“他者”,对于他文化中的问题,首先要理解它,承认它是特定环境下的特殊表现;但同时理解它并不等于认同它,还要思考它的局限性及其出路。列维·斯特劳斯曾说,我们的学科让西方人开始理解到,只要在地球表面上还有一个种族或一个人群将被他作为研究对象来看待,他就不可能理解他自己的时候,它达到了成熟。[14]人类学家通过研究“他者”来反观自身,通过认识“他者”来反省自我。通过此种方式,人类才能更加清楚的认识自己,实现“自觉”。
(二)实现科学性与价值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
唯科学主义导向下的学术研究走向是寻求普适性、抽象化的普遍原理,追求一元化。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因主体的多样性、特殊化、多元化,若忽视地域性、民族性差异,单纯追求共性的“一元化”,在充满价值问题的田野考察中是有局限的。若说田野考察倾向于个案、非主流研究,其研究成果满足了主流文化下的猎奇心理,不具普适性,不能推广到所研究文化之外的群体之中去,这是极片面的。
追求多元,并没有否定其科学性,而是体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在跨文化的田野考察中,寻找差异不是目的,而是在“和而不同”的理念指导下,寻找差异背后不同文化得以沟通的结合点。从多元的个性中提炼出共性,在尊重价值性基础上体现科学性,最终达到科学性与价值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
(三)重视理论的价值
大学里,人类学家的成丁礼要经过“学院——田野——学院”[15]的程序。即进入田野之前和走出田野之后都要注重理论的价值。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田野考察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行万里路”还是要以“读万卷书”来做前提的,“读万卷书”使研究者有基本的考察理论、学术素养以及发现问题的眼睛,舍此,即使“行万里路”也只能是事倍功半。保证实践成功的实践智慧,不只有科学理论构成,其中还有价值理性的成分和情景性知识。但是缺少科学理论的“实践智慧”永远只能是低水平的、经验层次的、残缺不全的智慧。[16]
“出乎其外”还要求研究者从一堆堆驳杂的数据、调查资料中跳脱出来,没有围绕概念或观点,整天埋头于整理经验事实性的材料,造成的结果将会是研究者被海量、看似没有联系的事实所淹没。这就是要以形成理论为目标。理论的魅力就在于将研究者对经验的思考组织起来,形成能够用较少的说明性原则来解释相对广泛的观察现象。当然,我们承认要形成理论是极其困难的,它需要以大量的事实做例证,并且还需要有简约性、可证伪性以及足够的启发性来不断的产生新的知识的特点;并且很多理论的真理性可能只存在于理论层面,而非实践层面,也许短时间内无法被世人接受。形成理论之路是困难崎岖的,但“无限风光在险峰”,正是理论的魅力引导着研究者的个人成长和学科的不断成熟。提取理论框架,寻求更宽广的理论解释力,是田野工作最终的理论使命。[17]
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写到“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18]其道理用于田野考察—— “入得,出得”——田野考察的求真之路不正印证了王国维的辩证之法吗?
注释:
①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第1版:第311-312页。
[1]李亦园.田野图像[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50.
[2]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39.
[3][6]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13,8.
[4]乔健.漂泊中的永恒——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增订版)[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159.
[5]郑欣.田野调查与现场进入——当代中国研究实证方法探讨[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3).
[7]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501.
[8]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330.
[9][11][英]雷蒙德·弗思著.费孝通译.人文类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68,7-8.
[10]刘海涛.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矛盾与困境[J].贵州民族研究,2008,(4).
[12][14][15]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8,18,192.
[13]Bernard,Russell.Research Methods in Anthropology: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M].Maryland: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2.324.
[16]孙振东.教育研究方法论探索[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312.
[17]刘谦.田野工作方法新境界:实证主义与人文精神的融合[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18]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5.
〔责任编辑:罗柳宁〕
Dig Deep into Its Essence,and Observe It Beyond Its Boundaries:the Due Requirement of the Field Work
Zhang Ting
C912.4
A
1004-454X(2011)01-0082-005
重庆市重点文科基地重点项目“西南民族教育研究中民族性与地域性关系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0502003)成果之一。
【作 者】张婷,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2008级硕士研究生。重庆,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