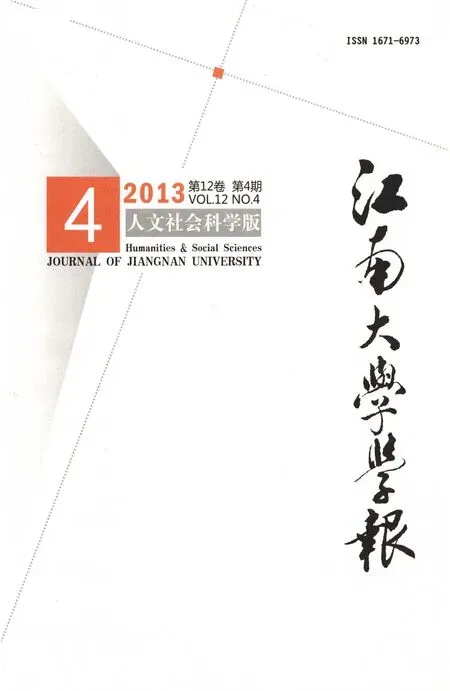明清江南战略地位与地缘结构的变化——兼论文化江南的空间范围
余同元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215123)
地缘是由地理位置联系而形成的系列关系。地缘关系是指以地理位置为纽带而形成的、一定地理范围内共同生活、活动、交往而产生的区域社会关系。地缘结构是建立在地缘关系要素之上的,既具有时代共性又具有地域个性的多维区域空间的功能有机体。区域地缘学重点研究各地区或各集团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相互关系与格局,包涵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地缘文化等基本要素。根据区域地缘学研究在内涵和外延两个维度上的发展,地缘战略包括地缘政治战略、地缘经济战略和地缘文化战略三大部分,每个部分都具有全球的、周边的和地区的等级层次上的空间结构特征。下面试分析明清时期地缘政治江南、地缘经济江南和地缘文化江南的战略地位和地缘结构变化情况。
一、江南历史自然地理结构
明代学者李乐《见闻杂记》卷一曰:
嘉靖九年,更定南北郊礼。南郊皇天、上帝南向;太祖西向;东一坛大明,西一坛夜明,东二坛二十八宿,西二坛云师、雨师、风师、雷师。北郊皇地只北向;太祖西向;东一坛,中岳、东岳、南岳、西岳、北岳、基运山、翊圣山、神烈山,西向;西一坛,中镇、东镇、南镇、西镇、北镇、天寿山、纯德山,东向;东二坛,东海、西海、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坛,大江、大淮、大河、大汉,东向。
相比全国其他区域自然条件,江南最大的特征是因水而成,其自然地理结构首先体现为长江下游河湖密布的水网体系。江南自古号“有三江五湖之利”。“五湖”所指,或认为泛指太湖及其周边众多湖泊,或指太湖流域几大进出水系。“三江”所指,《国语·越上》“三江环之”,贾逵注以吴江、钱塘江、浦阳江为三江;《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出三江之口”,赵晔注“吴江”作“松江”;晋郭璞以岷江、松江、浙江为三江;《吴地记》以松江、娄江、东江为三江;《汉书·地理志》上“三江既入”注“以北江、中江、南江”为三江,等等,说法众多,莫衷一是。独班固《汉书·地理志》“三江”注经《水经注》等书补充完善,最接近历史事实。
《汉书·地理志》毗陵县下曰“北江在北东入海”(即今扬子江);丹阳郡芜湖县下曰“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即今“芜申运河”,最早为“胥溪运河”);会稽郡吴县下曰“南江在南东入海”(即今新安江与钱塘江)。由此可见,古代三江特指古北江、古中江、古南江,简称“汉志三江”。“汉志三江说”源自《尚书》和《周礼》两部经典。《尚书·禹贡》曰:“淮海惟扬州,彭蠡既豬,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厎定。”《周礼·职方》曰:“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籔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汉志三江”流域即明清江南区域,皆因水而构成皖南、苏南、浙江水网体系,使长江下游水系成为一个流动着的循环系统,可谓皖江悠悠,越水滔滔,吴波漾漾,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自然的整体性和文化的统一性日益凸显,形成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同质区域。[1]

图1 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孔安国三江图》Fig.1 Cheng Dachang's Yugong Geographic Chart of Mountains·Kong Anguo's Three River Chart

图2 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班固三江图》Fig.2 Cheng Dachang's Yugong Geographic Chart of Mountains·Ban Gu's Three River Chart
关于古北江,自彭蠡向东北至今镇江、扬州一带入海,实为长江下游干流,今称扬子江者是也。大约在6000年前,长江在扬州、镇江之间形成一个喇叭形河口入海,长江向北向东的出海口均遭海水阻挡,长江下游沿岸相继形成了太湖、巢湖、彭蠡泽等大型湖泊。到汉代,在广陵南郊江中形成沙洲,长江至此分为两道,沙洲之南为大江主航道,之北为支流,这个支流即为曲江。东汉王充《论衡·书虚篇》有“广陵曲江有涛”之说。晋代山谦之《南徐州记》(王谟《汉唐地理书抄》辑本)曰:“京口,《禹贡》北江也。春秋兮朔辄,有大涛至。”
关于古中江,《禹贡导·导江》说“东为中江入海”。《汉书·地理志》丹阳郡芜湖县下注云:“在丹阳芜湖县南,东至会稽阳羡县(今江苏宜兴)入于海。……禹贡所谓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2]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中江”标注于芜湖至太湖之间,由青弋江、水阳江、固城湖、荆溪等天然水道和胥溪等水道组成。大约距今5000年前,海面下降,海水后退,长江口向前伸展,中江发育形成,连接长江和太湖。中江上游的青弋、水阳两江及长江安徽段汛期水位在8-12米之间,相对于太湖流域3米左右的水位,有5-9米的高低落差。青弋江流域与太湖流域之间并无高山相隔,两流域之间的分水岭处有一沟通太湖和古丹阳湖的胥溪运河(据说由伍子胥修建,参见图3:古中江及今芜申运河图),其关键河段在江苏高淳东坝和下坝之间的分水岭上,长约5公里。从高淳流向溧阳的胥溪河,自春秋吴至唐一直全程通航,并筑有坝和堰埭控制水位。唐末由于社会动荡,水利工程失修,造成胥溪航运不畅。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于洪武二十五年重开胥溪河,建造石闸启闭,用来节制水流。嘉靖三十五年倭寇入侵,商旅皆由东坝经过,又自坝东十里的下游原分水堰处增筑一坝,名曰下坝,东坝则称上坝。从此胥溪被截为三段,东坝以西称上河,下坝以东称下河,两坝之间称中河。因上下坝将胥溪河分成梯级,坝与坝之间必须分节通航。

图3 古中江及今芜申运河图Fig.3 Ancient Zhongjiang and today's Wushen canal
关于古南江,郦道元《水经注》承接《汉书·地理志》说法作了进一步说明:“沔水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蠡泽,至石城县分为二。其一过毗陵县北为北江,其一为南江,东至会稽余姚县东入于海。”《水经注·沔水》曰:“南江又东,径宣城之临城县南,又东合泾水,南江又东与桐水合,又东径安吴县,号曰安吴溪。又东,旋溪水注之。水出陵阳山下,径陵阳县西,为旋溪水。分江水自石城(今贵池)东出后,经过临城县南(今青阳县),就到达安吴县,又东径安吴县,号安吴溪(现泾县安吴镇)”。对于《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所言分江水和南江,《大清一统志》认为:“言之凿凿,必非无据,今其道虽湮,未可轻訾。”[3]
支持班固“汉志三江”说者,有朱鹤龄《禹贡三江辨》、钱塘《三江辨》、许宗彦《禹贡三江说》、张澍《三江考》、张海珊《三江考》、萧穆《禹贡三江说》、汪士铎《三江说》、胡薇元《三江说》、黄家辰《三江既入解》、邹汉勋《三江彭蠡东陵考》,等等。顾炎武《日知录·三江》、王鸣盛《尚书后案》、阮元《浙江图考》亦持类似观点。晚清朴学家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认为:“三江之说,以《汉志》最为近古可信。”(参见图4《汉志三江江南图》)。

图4 汉志三江江南图Fig.4 Three River Jiangnan in Han
明清对“江南”一词的运用较随意,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以“江东”为江南范围,[4]但清初设立江南省(即后来的江苏、安徽两省),不仅包括江南地区,还包括了大片江淮地区。而在关于“江南”的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中,学者们采用的范围更是五花八门,大者包括明代南直隶、浙江布政使司、江西布政使司和清代的两江、两浙江地区,小者仅以太湖流域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为叙事范围。[5]
已故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地理学家陈怀荃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分别在《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杂志发表《<汉志>分江水考释》、《<禹贡>江水辨析》、等著名论文,认为“《禹贡》三江实际包括的地理范围,从九江以下,除今皖南沿江平原和太湖流域之外,还有皖南山区和浙江流域。江水的名称,也就由此扩展到钱塘、会稽一带,并逐步成为东南诸川的通称。”[6]“汉志三江”、“魏晋江东”、“唐宋江左”与“明清江南”区域皆“因水而兴”,自然含有现代的皖南、苏南和浙东北三片地域,其中水系相通,源头皆系于皖南(详见图3《汉志三江江南图》)。有人统计,太湖流域行政区划分属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三省一市,其中江苏19399平方公里,占52.6%;浙江12093平方公里,占32.8%;上海5178平方公里,占14%;安徽225平方公里,占0.6%。[7]由此看出,皖南与浙江有新安江钱塘江一脉相连自不用说,皖南与苏南地区不仅自然地理上属“三江”流域这一整体区域,而且行政区划上也很晚才有分治。两地在明代同属南直隶,清初同属江南行省,同属古代“三江”和近代“江南”区域,康熙年间江苏、安徽分省后才有“皖南”与“苏南”之称。“皖南”即清代皖南道所属地。皖南道原名安徽道,雍正十一年(1733)置,驻安庆府(安庆市),领安庆府、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广德州;十二年移驻芜湖县;咸丰五年(1855)移驻宁国府;十年(1860)移驻祁门县;同治四年(1865)移驻芜湖县;光绪三十四年(1908)更名皖南道。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认为宋代江南五大水系并列——即中江水系与天目山水系、吴淞江水系、钱塘江水系和杭州湾南岸北流的一组水系互动。其实这五个水系就是历史上的汉志三江江南水系。其书曰:“据说长江曾在芜湖附近分为两条支流,向南分流的是中江,东流的江水一旦注入太湖,这一太湖水又通过吴淞江的导引而注入海。”[8]中国学者姚汉源在《中国水利发展史》中也认为:“相传自太湖向西,大约经今芜湖附近,还有一条胥溪运河。《汉书·地理志》的中江似即这一水道。”[9]
二、明清江南战略地位变化
1.西北中国到东南中国区位变局下的“战略江南”
顺治皇帝说“万里江山一局棋”,与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所说“大棋局”相近。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说明中国自古有着东南沿海区域和西北内地区域的地缘差别。宋元以前,西北中国是前庭,东南中国是后院。明代中后期“边禁”、“银禁”与“海禁”开放以后,东南中国由“后院”变成“前庭”,中国地缘战略开始发生近代转型。[10]
中国版图兼有南农北牧两大区域,历代长城内外的对峙,农牧民族的分合,正是人类历史上农牧世界二元一体化的历史缩影。自秦汉至宋元,中国的边防主要在北边。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大庭院,宋元以前这个院子的大门朝北开,因为影响中国农业民族的主要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历代封建王朝所谓的“边防”主要指万里长城沿线的防御情况,其内容包括北部的边患和战略、边防的部署和长城的修筑与驻兵守御等,形成了著名的长城文化带。[11]但至明初,开始构筑海防体系,永乐至宣德年间进一步完善海防设施。海上的防线由水军担任,陆上防线由各卫所的陆军和巡检司担任。各卫所负责防守一定的海区和地域,并互相呼应。这样,在沿海构成了基本完整的,有一定纵深和层次的防御体系。中国东南海防地位日益重要,迅速上升并超过西北边防。
现代地理学家以黑龙江漠河到云南腾冲为两端,在中国地图上划一斜线,称“胡焕庸线”(见图5《胡焕庸线》),斜线以西以北为西北中国,拥有占中国领土面积60%左右的土地和占总人数5%的人口,大体上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斜线以东以南为东南中国,拥有占领土面积40%左右的土地和占总人口数95%的人口,基本上是历史上农耕民族(汉族)的主要活动区。

图5 胡焕庸线① 引自谢高地《中国生态资源承载力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Fig.5 Hu Huangyong Line

图6 秦代及明代万历长城图② 引自安介生:《走进中国名关》,长春出版社,2007年。Fig.6 Great Wall in Qin and Ming Dynasties
之所以长期出现东南中国与西北中国这种二元区域双轨发展的局面,是因为中国是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打开世界地图,由东起东北亚的大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格罗斯山、高加索山,向西直至欧洲境内的喀尔巴阡山划一横线,将亚欧大陆区划为两部分:横线以南多为湿润的平原森林地带,宜于农耕,其中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东亚的黄河、长江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等都是人类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农耕中心。横线以北多为干燥的高原荒漠地区,与农耕地带平行,东起西伯尼亚经中国东北、蒙古高原、中亚、咸海、里海以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带,其核心地区是蒙古高原至中亚一带。农牧分界线划分的方法略有不同,台湾三民书局1982年版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国》以亚洲东北部的堪察加半岛尖端与阿拉伯半岛西端相连接划一直线。台湾中央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札奇斯钦《蒙古文化概说》云:“自东北亚洲大陆的嫩江、松花江流域,沿长城线,经西藏高原,伸向阿拉伯半岛划一条线。”这条线正好横穿中国,将中国分为西北中国和东南中国两部分。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之间的分界线时有迁移,与历代长城位置的移动基本同步,反映了自然的农牧过度带与人文的长城文化带的变迁特点。[12]明代长城文化带进一步南移,农牧民族二元一体化进程加速,到隆庆五年“俺答封贡”,边禁开放,长城文化带由“内边疆”形态变成了民族贸易带。[13]
《汉书·天文志》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近代中国社会的开放性源头来自沿海的东南中国。明清社会的开放,最先是在东南沿海登陆,其后在全国引发政治、经济、文化大变动。15世纪中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封建主和寺院大地主为扩充实力,弥补内战损失,怂恿﹑支持海盗活动,因而倭寇逐渐猖獗。嘉靖年间,明廷内政日趋腐败,倭寇乘机与少数奸商相勾结,窜犯今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占据岛屿,攻城掠地,深入久踞。倭寇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给沿海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成为明朝的严重祸患。沿海民众不甘倭寇侵略,奋起抗击。戚继光指挥军民与倭寇水陆交战12次,倭寇大部被歼。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开始,明政府全面整治海防。编绘了《筹海图编》的郑若曾又编绘《长江防御图》与《太湖防御图》。他写出《江南经略》,包括46幅《江防图》和29幅《湖防图》,这些地图是明代江南江河湖泊战备图的代表。其中所绘《江防图》的范围主要为长江下游,西起今江西瑞昌县,沿江而下,东到长江口的金山卫,这个范围也是倭寇进犯可能到达的地方。图上重点描述江防设施、哨所驻地、各营防区范围及其界线、倭寇出没路线等。图上注记文字较多,除了地名、山名、港名、寺名之外,还标注了防区的起止地点,不同巡司间的距离,巡逻水军的兵员多少、舰只数量、巡逻周期等。太湖是倭寇从水路容易进犯的地区,《江南经略》中绘制的《湖防图》,有1幅大的《太湖全图》和28幅16小的《太湖沿边设备之图》,分别描绘了太湖的全景和沿太湖周边的港渎及其防备情况,共有港渎等约250处。嘉靖中期至万历中期,在海防发展的基础上还出现了很多海防理论著作,如《筹海图编》、《筹海重编》、《虔台倭纂》、《皇明海防纂要》等。自海防地位日益提升,中国地缘战略发生整体转型,过去作为后院的东南沿海地区,现在变成了中国的前庭门户。16世纪初,欧洲殖民势力东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相继来到中国。1522年葡萄牙人米儿丁·甫思多灭儿带兵到广东沿海,企图用武力打开通商大门。1549年明军在浙江巡抚朱纨、副使柯乔、都司卢镗等人率领下围攻侵占福建诏安马溪的葡萄牙海盗,使之受到重创。1549年荷兰殖民者侵略澎湖失败。1553年,葡萄牙占据澳门,其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势力相继来华。1622年,荷印总督率军犯澳门被击败,北上一度占据澎湖,1624年被明军击退,后荷军占领台湾。19世纪中后期,清朝东南海疆、西北边疆同时危机,引发了清廷内部半年之久的出海防与塞防轻重缓急之争。

图7 明代郑若增海防图①《万里海防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与现代中国海防图② 《现代中国海防图》,引自中华兵器大全网站,cnweapon.comFig.7 Coast Defense Figures in the Ming Dynastyand Modern China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曰:
以东南之形势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江南而已。春秋时勾吴实雄长於东南,以兵威破楚、臣越、败齐,又阙深沟於商鲁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黃池。当是时,微越之故,吴且霸天下。……或者曰:明太祖以江南而奄有中原,为千古创见之局。此实不然,从来建事功者,得失虽殊,成亏或异,而其能法非以有为则一也。楚南公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故西北与东南恒有互为屈伸之理。[14]
综观明清西北边防与东南海防关系史,发生了多重的变化。
一是前庭与后院的关系:明清时期东南沿海由后院变为前庭和门户。
二是陆权与海权的关系:郑和下西洋、皇明筹海、海权时代开启。
三是守成与开拓的关系:洋防与岸防,战略防守与战略出击。
四是守内与御外的关系:明代防入与清代防出。
五是重中之急与急中之重的关系:晚清塞防与海防之争。
2.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下的“财富江南”
中国之一统,多指南、北方之统一。统一国家大多定都于北方之北京,而以南方之南京为陪都,形成一个南北向的政治、经济、文化轴心带,这是经济中心南移导致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带变换之大势。唐宋元以降,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了,政治中心却不能随之南迁,统一王朝由西向东,由长安而洛阳而开封而北京逐渐移动,可以出现以北京为主、南京为辅的两京制度,而却难以出现以北京为辅、南京为主的两京局面。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历代统一王朝时期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现象。
北宋末,赵构重建宋室社稷,李纲建议:“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 《李纲辅政》)
后来,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汪若海对张浚说:“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张波经略关陕》)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局面中,有两次是以关中为基础完成统一的。秦汉和隋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
“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秦中自古为帝王州,周、秦、西汉递都之;苻秦、姚秦、西魏、后周,相问割据;隋文帝迁都于龙首山下,距故城仅二十余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统。唐因之,至开元、天宝而长安之盛极矣。盛极必衰,理固然也。是时地气将自西北趋东,此正地气自西趋东北之真消息,特以气虽东北趋而尚未尽结,故仅有幽、蓟,而不能统一中原。而气之东北趋者,则有洛阳、汴粱为之迤通潜引,如堪舆家所谓过峡者。至一二百年而东北之气积而益固,于是金元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扩西北塞外数万里,皆控制于东北,此王气全集于东北之明证也。而抑知转移关键,乃在开元、天宝时哉?”(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0,《长安地气》)
但至明清时期,不仅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皆移至江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海上侵略势力到来和东南海防的日益重要,国家战略重心也向东南转移。对此,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篇提出了著名的“建都之问”,认为明清时期战略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首都应该建于南京而不是北京,这样才能使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统一起来。
或问: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
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
……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围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黄宗羲的观点是否正确?揆诸明清史实,“门庭”与“仓库”已然转型换位,建都的战略反思尤为必要。
第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还是统一?或者问为什么分离?
第二、政治中心是否随经济中心迁移?或者人臣能否替代天子守边?
第三、所谓“时不同”有哪些主要表现?“明清江南”地域特征何在?
第四、金陵能否重新成为首都之佳选?或者江南能否成为真正的政治中心?
第五、如何避免再度“贫极江南、富夸塞北”?如何处理中国前庭与后院之关系?
元代以江南地区为主要经济掠夺对象,导致《草木子·克谨篇》所说的“贫极江南,富夸塞北”,或“贫极江南,足实塞北,富极腹里”的极端不均现象。13世纪后半叶,进入汉地和南部中国的蒙古人口,最多不会超过70到80万,而当时居住在宋、金旧土的汉族人口大约有7000多万(不包括云南和吐蕃之地的人口数)。京都“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史·食货志》),在中书省和九个行省中,江南三省(江浙、江西、湖广)每年所征税粮近六百五十万石,占全国总数的二分之一强,而江浙一省就征近四百五十万石,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元末农民义军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作为宣传口号,表达了南人对于民族掠夺的愤恨之情。至元二十年,大小起义二百余处,至元二十六年就增加到四百多处,几乎南方各地都有起义发生。
黄宗羲《建都篇》又曰:
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
或曰:古之言形胜者,以关中为上,金陵不与焉,何也?
曰:时不同也。
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
今夫千金之子,其仓库匮箧必身亲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仆妾以仓库匮箧。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
历史时期建立于东南的政权,有春秋时期的吴、越、三国时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宁、齐、梁、陈、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吴越、南宋、元末明初的周(张士诚)和清太平天国等。但皆是祚长命短,更加说明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长期性。明代学者李乐、张萱均有论说。“国朝定鼎金陵,本兴王之地,然江南形势终不能控制西北。”[15]“南京之形势跨江南北,以为甸服。岷峨以西,五岭以北,川流以万数,皆会于江绕钟山而之海;岍岐之南,太华恒岳之间,川流亦以万数,皆会于河,入于淮,朝宗畿甸而之海。无事则坐享扬越之粟而无转输之劳,有事则席卷全吴之甲而为张皇之本,故正统间有建议南迁者。殊不知以天下大势观之,终不若燕京之胜,而今日都之诚是也。”[16]

图8 朱熹假想地轴图① 参见王子林《紫禁城风水》,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页。Fig.8 Zhu Xi's imaginary Earth's axis
3.闭关到国际开放中的“枢纽江南”
邹逸麟先生《谈历史上“江南”地域概念的政治含义》一文指出,江南地区历代政治地位变迁,分“中原王朝心目中的异域地区”、“南北对峙:江南为另一政治中心”、“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江南”三大阶段。[17]这里重点讨论明清时期“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江南”的国际枢纽地位的形成。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了世界“地理中心(枢纽)”概念,也就是“世界岛”理论。即:谁统治了东欧平原,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全世界。如果将明清中国比作一个“孤岛”,那这个岛内的“心脏”无疑就是地缘江南,即上文所谓的“中国的心房”,它的空间形态虽在南方,但它的政治、经济、文化要素早已开始国际化和全球化,并通过空间的层级的互动与北方的宫廷联为一体。整个明清时期,由于“海禁”政策时作时息,使江南的国际化进程受到较大影响。但自明中期“银禁”、“海禁”、“边禁”等“三禁开放”后,江南毕竟不同于以往,开始正式步入全球化与国际市场化轨道。
明初海禁(洪武到永乐)从洪武十四年(1381)开始,朱元璋正式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明成祖较大程度上放松了海禁,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盛况,但未能明令废除海禁。明中期(洪熙到嘉靖)历经九朝,海禁态度略有不同,洪熙朝到弘治朝海禁政策再次强化;正德年间实行抽分制表明海禁逐步废弛;嘉靖年间海禁政策高度强化后产生“嘉靖倭患”。明后期(隆庆到崇祯),隆庆帝继位不久即下令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此即“隆庆开放”。
清代“海禁”断断续续,总体上朝开放的方向发展,就时间而言包括两个时期。第一个阶段为1655年至1684年,顺治十二年六月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次年六月发布申严海禁敕谕,直到1684年康熙平定台湾后才下令重开海禁。第二阶段为1716年康熙帝颁布“南洋禁海令”至1727年雍正帝废除“南洋禁海令”为止。[18]
1930年代冀朝鼎先生在《中国历史上基本的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书中指出,由于海禁开放和世界贸易,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受到西方工业主义的影响而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铁路修建、工商业发展,起到列强经济与政治行动基地作用的东南商埠,就成了强有力的经济与政治重心,甚至每一港口都控制着一个主要区域。新区域地理轮廓上与老区域一致,主要是以地形条件为标志,但经济基础、区划涵义以及区域范围则与老区域大不相同同。我们认为,这一“不同”的变化早自明代中期已露端倪。
随着商品流通的不断扩大,明清江南白银需求迅速增加,外国白银输入主要来自日本、美洲和墨西哥。西方商人需要中国价廉物美的丝绸、陶瓷、棉布、各种手工业品和茶叶——这些商品主要来自江南,于是他们将美洲白银航运到亚洲,通过马尼拉等东南亚贸易中心和澳门、广州等中国东南沿海港口交换中国江南货物,使白银于大量流入江南地区。江南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因此空前加强,形成了以江南为中心的东亚市场圈。所以,龙登高教授因此把江南视为“中国的心房”和“东亚的心房”。[19]
江南对外贸易港口众多,凡港口开放处便设置市舶机构加以管理。宋代江南便设有江阴军(今江阴)、平江府(今苏州)、上海镇、青龙镇(今青浦)、华亭县(今嘉兴)、澉浦(今海盐)、宁波等多处市舶。元代太仓刘家港码头可容万斛之舟,番商云集,号称:“六国码头”,至正二年在太仓设庆元市舶司,太仓港称“天下第一码头”(《太仓州震阳县志》)。张寅《太仓州志》曰:“凡海船之贸易往来者,必经刘家河泊州之张泾关,待潮而发,经昆山抵郡城之娄门。”明洪武元年,太仓黄渡市舶司设立。郑和下西洋出海之港,“九夷百番进贡方物,道途相属,方舟大船,次第来泊,太仓复旧之宏观”。利玛窦说:“一年到头,苏州商人同国内其他贸易中心的商人进行大宗贸易,这样交换的结果,人们在这里几乎没有买不到的东西。”明代八大码头,苏州居其二,“今天下大码头,若荆州、樟树、芜湖、上新河、枫桥、南濠、湖州、瓜州、正阳等处,最为商货辏集之所。”康熙二十三年驰海禁,江苏设江海关,苏州有浏河口、七丫口、白茆口、福山、徐六泾五处,康熙五十五年苏州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20]
周文英《水利书》曰:“元至元十四年间,海舟巨舰,每自吴淞江青龙江取道,直抵平江城东葑门湾泊。商贩海运船户黄千户等于葑门墅里泾置立修造海船场坞,往来无阻。”洪武元年在太仓黄渡设置市舶机构,后改设至浙江定海。江南丝织品对外贸易主要以日、俄、朝、南洋等地为大宗,“清光绪间,运俄绸缎岁有巨额,以海参威为无税口岸,运商皆由此进口。”日本市场方面,清朝末年尚有苏缎商“自往设庄营业,关税值百抽五”。“苏、浙、闽商往长崎贸迁借居者络绎不尽。”朝鲜市场更是当时江南丝绸的主要出口地,“向为中国大宗贸易,每岁产额几千万元,工商之赖以生活者几千万人,其对外贸易较大者向有二种,一行销高丽、安东等处者,名高丽纱缎,一行销南洋群岛各处者,各曰阔货。”[21]
三、明清江南地缘结构及地域范围
第一,江南地缘经济结构及区域范围
明清江南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包括苏南、皖南、两浙在内的大长三角地区,这正是《汉书·地理志》所说“三江”江南流域。地缘经济(Geo-Economics),或称“区域经济”、“地区经济”,反映不同地区内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内涵与外延的相互关系,是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李伯重界定的八府一州及其周边地区,可以作为地缘经济上的核心江南范围。不能完全包括江南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要素及其分布密切结合的整个区域实体。长江下游“三江”水系是一个流动着的循环系统,形成整体三江江南区域,唯其因水而成,号有三江五湖之利。“明清江南”就是这个广义的长江下游三江流域的历史地理范围。自明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进程已已经启动。这个转型的社会经济基础在江南核心区域最先形成,表现为明清江南社会经济结构率先松动与缓慢转型之上。[10]在此基础上,江南工商业进一步发展,率先步入早期工业化社会。[22]
第二,江南地缘政治结构及区域范围
所谓政治就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地缘政治是一种探讨个人、组织或团体,因为空间分布等地理因素和经营政治的方法及手段。要求从整体空间背景上来观察一国政治格局及各地区各民族各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地理因素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军事、政治等方面进行分析。作为地缘政治江南的地理范围,比地缘经济江南要大得多。
《读史方舆纪要》曰:“南京亦曰南直隶,府十四,曰应天、凤阳、安庆、庐州、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州四,曰:广德、和州、滁州、徐州。属府州十三,属县九十六,而淮安为漕运通渠,凤阳为陵寝重地,安庆为陪京上游,苏松为边海襟要,皆特设重臣,申严封守。”[23]
《抚吴疏草》曰:“皖郡于江北孤城,西连蕲黄,北接庐凤,南滨大江,为陪京第一门戸,长江第一锁钥也。……安庆扼吴楚之咽喉,司金陵之门戸,故皖郡安则江南俱安,皖郡危则江南俱危。”[24]
《甲申纪事》曰:“徽宁在万山之中,在江南形势,如人之有背脊也。”[25]
《江南经略》曰:南畿胜势在长江,留都守御,舟师为急。……扬有咸台,富商走集,民颇丰洽,俗亦浮靡。濒湖农田,涂垫为患。安庆当长江委流,东约全楚,为江表门户。徽州山多田少,民逐末利,风俗用偷。池在山麓,江浒寇盗窜伏。镇江凿山通漕,江潮下上,谷土岁易,利归豪右。苏、松、常三郡,市浮于农,文胜于质,加之田赋不均,税徭日困。沿海兵戍,本以备倭。而滨海滨江之民,擅鱼盐之利,间作弗靖,出没江湖,肆行剽劫。[26]
可见地缘政治江南包括整个长江下游三江流域,沿三江水道设置系列军事重镇,扼守军事要点,构成国家东南战略枢纽。如果以南京为江南之首脑,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湖州、杭州、严州八府则是江南之“腹心”,安庆、池州、徽州、太平、宁国、广德等皖南府州为江南之“脊背”,浙东绍、宁、温、台、处、金瞿七府则为江南之“尻脊外蔽”。所以乾隆《江南通志》曰:
“江南于天文占斗、牛、女、奎、娄、房、心,分野在星纪降娄、大火之次。其地广轮数千里,左临大海,旁界五省。……江之南首重金陵,而安池太平峙其上游,镇常苏松广其辅翼。西北则平原旷邈,以群山为几案,东南则百川汇流,以沧海为池沼。漕河自南讫北,蜿蜒其中,转输飞挽,樯颿相望,东南形胜于兹为最矣。[27]
第三,江南地缘文化结构及文化江南的地理范围
还有地缘文化江南,是指地理空间尺度上楚文化、吴文化与越文化相互融合,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构成的江南区域文化总体。地缘文化是指局部地理环境引起的社会、文化差异与因缘关系。文化与经济的扩展遵循地缘政治扩张的路径,它们是支持一个国家影响力的根本力量。这些文化和经济力量首先在国内聚集,然后向外发展。
首先,江南文化是古代吴文化、楚文化和越文化的重叠与融合。地缘文化学探讨区域文化内涵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江南区域文化整体中包涵着古代吴、楚、越三大分支文化内涵。三楚、三吴与吴越文化彼此重叠,相互融合成一体,形成楚辞越韵唱吴歌的历史旋律。
其次,文化地理学从地理角度研究文化,着重研究文化是怎样影响人们生活空间的。由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感受与理解不同,加上环境、物质要素、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等方面的区域差异,文化要素必然会表现出种种不同阶层不同区域的类型和个性,这就是文化多样性与统一性特征。表现在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方面,出现江南大区域内不同区域间文化彼此竞争与融合,形成流派纷呈的局面。如明清时期三江江南范围内,新安理学、吴中实学、浙东史学、桐城文学、皖吴经学,以及泰州学派、太谷学派,等等,无不争奇斗艳于江南大地,成为江南区域文化的要素标志。

图9 吴方言区范围图① 吴方言区范围图,引自清籁方言学网站www.sinolect.otg。Fig.9 Wu dialect area
再次,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核心要素,那么吴方言就可以是文化江南的核心标志,以此划定标准和方法来确定文化江南的地理范围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学术认同。若以吴语区作为文化江南的范围,又有狭义吴语区和广义吴语区之别。狭义的吴语区通常以苏州话为代表,因为苏州话因声音委婉动听,有“吴侬软语”的美称,主要通行于吴中地区。广义的吴语区主要指中国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大部分地区、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和福建西北角,以及这些地区迁出的吴语移民区。
文化江南的立论前提虽是地缘文化结构的抽象空间,但其空间结构及其区域文化内在规律和模型则有具体点、线、面可以支撑。区域空间结构理论不是寻求单个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的最佳区位,而是揭示多个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它将区域内的各事物看成是具有一定功能的有机体,并且从时间变化上来加以考察,故可视为动态的总体区位理论。五代宋元时期,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就渐成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地缘特点的区域整体。所谓江南胜景,鱼米之乡,佳丽之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遍地绮罗,盈耳丝竹,千百年来使人神驰梦想;粉墙黛瓦、砖雕门楼、幽深小巷、亭廊楼台、小桥、流水、人家,驳斑的墙院、墨绿色的青苔,烟雨缠绵,风情难解,无不深深镌刻成永恒;天道与人文在这里奇迹般交汇成明媚灵秀的山水长卷,构成地缘江南的人文基础。

图10 吴方言区与明清江南范围对比图① 根据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编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和余同元《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研究》插图拼接。Fig.10 Contrast between Wu dialect area and Jiangnan are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随着时代的变迁,划定江南的标准也发生变化。明清江南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下“士商相杂”的异质区域,其区域范围在八府一州之外,至少还应该包括徽州、扬州和浙东的宁绍地区。正如张建雄在《商帮的江南》一文中指出,“是江南的地域环境为商帮搭建了平台,而商帮更造就了繁华的江南。”与此同时,“文化人的介入终于使传统的本末观出现危机,并造就了晚明以降士商相杂的社会现象。”说明广义的大江南可称为“文化江南”,由三个部分组成,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各有一部分,皖江悠悠、越水滔滔、吴波漾漾,大运河联系了这三个水系,而整体是以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泛长三角地区。[28]
明代《联苏松常镇并浙之嘉湖杭严八府属一督抚以保江南腹心议》一文说:
“今西北尽戎马之场矣,识者谓江南丰芑,必当巩固以备巡幸。且财赋所自岀也,然其腹心则在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以形势言之,北则长江天堑,南则钱塘襟带,东则大海汪洋,西则万山屏蔽,真山川天险以卫。此神皋乃以地本一区,属分直省,臂指不应,吭腹不通,莫若合七府属一督抚,驻札镇江,巡历苏杭。改吴淞副将为大将,改海盐参将为副将,设镇江京口一副将,如常山之蛇,以镇江为首,苏州为腹,杭州为尾,湖州带山,松江负海为左右翼,常、嘉为喉、脘、肠、胃诸经络,严州虽稍穷远,然地连杭界高山巅,抗蔽钱塘,不可它属,以之为足,然后可以扼险守要。……故以八府合属一抚以统三镇,而杭嘉四府亦宜设处兵饷,以佐协守,则地势既传,地利亦尽,此保江南之急着也。其浙抚则移居浙东绍兴,以保障宁、绍、温台处金瞿七府,以为江南尻脊外蔽可耳。”[29]
由此可见,“明清江南”与“禹贡扬州”、“汉志三江”、“魏晋江东”、“唐宋江左”一脉相承,皆“因水而兴”,后渐形成皖南、苏南、浙江水网体系。所以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其著作中讨论的江南范围时,提出“长江下游大区域”说法,其范围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两省的南半部与浙江全省,还包含了长江北岸通州、扬州部分地区。这样的江南地缘结构与范围,具备整个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历史地理关联性和区域文化整体性特征。
明清江南地缘结构及文化江南的空间范围划分,不仅反映了三江江南区域率先开启社会经济近代转型的共同特征,而且也反映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以来,由于政治重心与经济、文化重心的分离,其帝国基石地位和分权制约的枢纽作用日益提高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地理因素是影响区域发展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因素,最大的区域发展战略实质上是地缘政治的协调。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边防塞防的根本问题是确保陆权,海防的根本问题是发展海权,一旦边防危机与海防危机同时爆发,国家战略资源的有限性使其不能二者兼顾,必须正确处理确保陆权与发展海权的关系。无论是从中国的《孙子兵法》还是西方的陆权海权理论看,地缘政治关系始终是战略地理学中至关重要的核心因素。明清江南地缘结构与范围的变化反映了当时地缘政治变化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机遇。
[1]余同元.楚水漫漫、吴波漾漾——从汉志三江沿革看皖南与长三角的历史地理相关性[J].池州学院学报,2011,(2).
[2]毛晃.《禹贡指南》卷1《三江》,第14页,《四库全书》第5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乾隆.《大清一统志》卷82《池州府》,《四库全书》第480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31.
[4]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1《江南》[M].上海:上海书店,1983:245.
[5]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1.
[6]陈怀荃.黄牛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144—145.
[7]曾祥华.关于太湖流域管理立法的思考——借鉴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法的经验[M]//江苏法学研究,2008年,第1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M].方健,何忠礼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90.
[9]姚汉源.中国水利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9.
[10]余同元.明清社会近代转型及转型障碍[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
[11]余同元.中国长城文化带的演变[M].台北:老古出版社,2002年版《崇祯十七年》第477-484页.
[12]余同元.明代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与演变[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
[13]余同元.中国历史时期农牧民族二元一体化发展[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
[1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5]李乐.见闻杂记: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39.
[16]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六十二《兵部十一》[M].民国哈佛燕京学社印本.
[17]邹逸麟.谈历史上“江南”地域概念的政治含义[J].浙江学刊,2010,(2).
[18]叶萍.明清禁海立法之比较[J].法制与社会,2008,(11).
[19]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03.
[20]黄锡之.历史上的苏州海外贸易[J].海交史研究,1996,(1).
[21]苏州市档案局.苏州丝绸档案汇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921.
[22]余同元.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J].史学月刊,2007,(11).
[2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55:423.
[24]张国维.抚吴疏草[M]//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25]冯梦龙.甲申纪事:卷十一[M].台北正中书局,1981.
[26]郑若曾.江南经略:卷一下·南畿总论[M]//四库全书:第7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7]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卷一《舆地志》[M]//四库全书:第5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8]余同元.明清宫廷与江南历史文化互动[M].2011年11月10日提交北京故宫学学术研讨会,收入大会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9]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一册《浙江上》,第3—5页[M]//四部丛刊三编.上海:上海书店,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