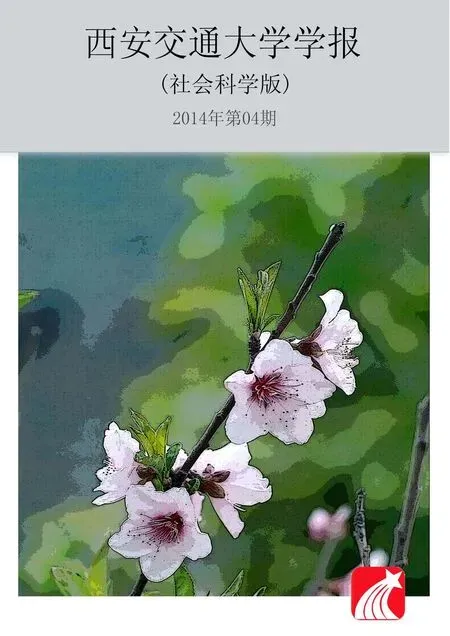“文化公共性”的实践与现代个体优良心灵秩序的养成
袁祖社,董 辉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710062)
我们所生存和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是一个“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的时代”,是一个真正需要凸显文化建设的实践品格与伦理性追求的时代。慑于坚固依然的现代性理念与资本逻辑的强大淫威,藉由势头强劲的全球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那个曾经给予我们理想和高远人生信念的“文化”,逐渐放弃在引领社会公共精神气质方面的应有的角色,逐渐丧失其在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所养成的公共性特质和生存信念,不愿意再有坚定的“匡扶时弊,救治人心”的使命和担当。
此一事实是我们时代文化研究者不容回避的。本论题有关“文化公共性”实践背景下现代个体优良心性秩序生成问题之思,关涉着对文化、人生、人格境界与心性修为复杂关系理论澄明的吁求,伴随着对“我们为什么有文化”、“文化是如何可能的”以及“文化以何种方式可以助益我们‘按照人的方式’成为我们自己”的问题的三重追问。其目的,则是尝试着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做一个现代“文化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二是,我们学会了“以文化的方式”优雅、体面、得体、尊贵式地生存了吗?三是,我们是否对一直以来融入我们血脉,在某种意义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左右、支配我们所思所想的诸多“文化”(价值观念是灵魂)进行过某种形式、某种程度的反思和观照?
一、文化建设中的“公共性价值自觉”关涉民众的精神生活品质和价值理性信仰
我们之于文化以及文化之于我们,事实上以及本质上都已经严重的不堪负累。文化为我们所累,我们同样为文化所累。文化自身在演进的过程中,自我滋生或被人为地赋予了很多原本不是、原本不属于文化本身应有的东西。相应地,我们也不得不被动地、不情愿地接受文化强加给我们的东西。
(一)我们为什么有文化
“我们为什么有文化”作为本论题的第一重追问,同时关联着的,是这样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我们实际拥有的,究竟是什么性质、什么类型的文化?关于“文化”,我们究竟何所知?所知若何?《我们为什么有文化?》是当代英国著名文化学者麦克尔·卡里瑟斯所撰写的一本小书。作者在该书一开始就做了如此这般的发问:“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过一个至今引起反响的问题: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一问题引起人们对于我们自己作为个人深刻而又具有变革性的思考。人类学家们提出一个与其相关的问题:我们如何生活在一起?这似乎引发出一连串的问题:不是‘我是谁?’而是‘我们是谁?’不是‘我该怎么办?’而是‘我们该怎么交往?’不是‘应该做些什么?’而是‘已经做了什么?’”[1]
这些提问是发人深省的。通过文化,我们的确生活并感受了一切文明的氛围,文化成了连接我们的最重要的纽带;但另外一个方面,也正是因为不同的文化,我们之间产生了隔阂和严重的冲突,并因文化而变为异乡人。如果我们从一种文化对生存和生活与此种文化传统背景中的个体的精神生活与人性品质的塑造角度而言,那么就不难发现,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通常会有两种情形发生:一种情形是,这种文化距离人性的优良品质的形成愈来愈近;而另外一种情形则完全相反,那就是,这种文化不断地违背人性的品质,距离优良的精神生活境界的形成渐行渐远。
当代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指出:“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是生产,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解释文化,而是为了实践地改造和建设文化。”“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不着边际的能指,而是具体的、实在的、与我们的日常感觉紧紧联系的政治现实问题。”[2]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著名文化学者詹姆逊有关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揭示了文化之当代实践中一个更为深层的严峻课题。他在发表于1984年的《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曾明确地指出:在所谓“后现代社会里”,“由于作为全自律空间或范围的文化黯然失色,文化本身落入了尘世。不过,其结果倒并不是文化的全然消失,恰恰相反的是其惊人扩散。”[3]在此种情形下,使得无论是作为“知识的文化”,抑或作为“行为方式的”文化其无边无际泛滥扩散的程度,导致“文化与总的社会生活享有共同边界”。“如今,各个社会层面成了‘文化移入’,在这个充满奇观、形象或海市蜃楼的社会里,一切都终于成了文化的——上至上层建筑的各个平面,下至经济基础的各种机制。……‘文化’本体的制品已成了日常生活随意偶然的经验本身。”[3]
(二)为什么要有文化自觉
1.文化建设中的“价值自觉”关涉民众的精神生活品质和价值理性信仰。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体现在民众的信仰和健全的心性秩序的养成上。这是文化的建设必须秉持的一以贯之的明确目标。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众有无价值自觉,价值自觉的程度如何,可以看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的目标之所在。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判断一种文化和价值观好坏与否的的标准,就在于看这种价值体系能否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民族的的心性秩序,纯良化一个时代的人心和心性。从而在此基础上,逐渐优化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质量,提升该民族的整体性的人格修为与境界。
因此,价值自觉关涉文化建设的成效,而文化建设其成效如何,关键就要看对于塑造一个公序良俗社会的精神生活风貌和风范大国民之高雅、尊贵的精神气质等方面的作用。本文所谓“心性秩序”也称“心灵秩序”,其本质的含义是指一种民众的一种优良的内在精神生活秩序。具体说来,现代社会中生活的公民个体,必须具有对既定社会秩序的批判性的反思认同意识,科学的合理的人生信仰,明确的道德责任担当,以及现代公民所具有的家国天下情怀等。
2.文化自觉,自觉什么?[4]自觉的是文化的主体,须以家国天下兴亡情怀,秉持“助人成人”、“成人成己”之信念,努力挽回渐行渐远之文化之心、文化之魂。在市场化社会之浅薄无常的“感性欲望的解放”和作为其显著表征的浅薄异常的“视觉刺激”的俗文化盛宴中,当下的文化已萎靡不振,不知自己是谁,在滚滚红尘中自甘平庸,终至落入丧魂落魄的不堪境地。
文化自觉就是要认识到文化的存在本身以及文化在塑造我们这儿社会的存在秩序时,出现了问题。文化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已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从而圆融自己的本质。
文化建设的价值自觉在于认识到,文化建设的核心、主题以及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是社会真价值的确认,是一种优良价值秩序的重构。而这同时意味着,文化建设必须担负其为我们这个时代寻求、甄别一种社会“真价值”,舍此,则优良价值秩序的重构就是一句空话。
当然,文化自觉不是也绝对不只是学者以及知识分子的责任,而在于通过知识层面的呼吁,造成一种全社会范围内有关文化危机的集体性的全民性的反思批判和建构意识和行动。
3.文化自觉是通过学者们的努力,实际地造成学者们有关文化的研究所本应发挥和具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响。长期以来,学者一直本分而天真地认为,文化和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由于不同的领域限制和逻辑,存在着较大的鸿沟,很难以沟通。于是甘愿放弃了文化影响政治的努力,于是作为一种不作为的结果,客观使政治变得轻狂和任性,完全不顾也根本不理会或者听不进文化的自以为高明的救世或者治世方略。政治放逐了文化,文化疏离了政治。社会如果足够健康,制度如果足够理性,这种状态的存在亦未尝不可。但问题是,学者们所梦寐以求的这种状态,实在是太难以遭遇到了。
任何一种文化都希望生存在一种开明、清明的政治环境之中,任何一种优良的政治也都希望一种优秀文化的理念支撑和价值引领。文化和政治之间的这种理想状态的关系的达成,一定是政治和文化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哪一个方面对对方的轻忽,其后果都必将是非常严重的。
(三)一种“文化公共性价值自觉”为什么是必须的
文化自觉就是要认识到,文化不仅可以成为国家、民族与社会共同体的软实力,更是一种能力、独特魅力的体现,一种文化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正是由此生发。何谓“文化公共性的价值自觉”?文化公共性价值信念的确立,是基于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普遍意义上的“人性与价值公设”。照此理解,一方面,一切文化形态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合理的动机和理由,就在于创设一种“公共性”的话语情景,进入一种文化,就意味着要以此种文化之公共性规范,对该文化个体的行为做一种反思批判和观照;另一方面,面对“世俗”、“功利”,面对“相对”和“虚无”,面对技术所造成的现代个体的“符合化”、“拟像化”之新异化现实,被正确理解了的“公共性”,直接构成普遍的文化迷茫时代,理性个体走进并体验“高尚”的前提。如此,所谓“公共价值自觉”完全可以理解为公共性文化语境中的价值新理解,或者称之为“价值的公共性自觉”[5]。
因此,我们可以由此而知,文化价值的最高本质在于公共性。深言之,一切文化价值在归根结缔的意义上,都是发现、体现、承载并旨在促使社会“公共价值”的生成与实现。人类对文化价值的追求、创造、积累、使用和拥有,实际上是基于一种更为深刻的“公共性”(共有性)生存本质、公共性人格境界的追求。
二、文化建设中价值自觉的目标必须首先是民众优良的心性秩序的达成
学者徐贲指出,文明人类演进真正需要深化、推动的,是文化对国民的心灵教育。事实上,早在2 000多年前,希腊人的教育目标就已经是培养“有文化”的,也就是完整的人了。“希腊文化注重人的心灵和公民精神。例如,希腊人的‘文法教育’不是今天语文课上教的语法、句法,而是诗、音乐和体操。这三项都是心灵教育,不是单纯的技能或知识——这种教育的目的不是积累可以用来换取金钱的知识,而是帮助形成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和人格品德。”希腊人认为,诗人是伟大的老师。希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斯特拉伯(Strabo)说:“古代人相信,诗是一种初级哲学,能从小打动我们,带领我们走进生活,培育我们的品格、感情、行为,并从中得到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希腊用诗来开始年轻人的教育,不只是打动他们,而且是训练他们。”[6]
(一)为什么是“文化”和“心性秩序”
在文明人类进化的意义上,作为一种非自然选择的结果,我们被锻造为一种“文化的存在”。那么,所谓文化性存在对于我们每个个体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文化性存在意蕴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种文化性存在?优良文化体系建设必须遵守社会公共价值的逻辑。判断一种共同体的文化、制度和价值实践优劣的标志,就看其是否提供了一种成就自我的方式,是否能够促进健康、健全而优雅的自我的产生。在这个意义上,核心价值体系只有落实到民众的精神信仰,才可以期望一个有科学信仰、有理想信念、有社会公共责任担当,有家国、天下情怀境界的现代公民社会所需要的理性公民的诞生。
令现代人经常困惑不已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文化究竟如何才是可能的?在滚滚红尘面前,在世俗的无限的物欲面前,在永无止境的的利益追逐面前,文化何以才能葆有自己的一份纯粹?文化是否一定要无奈地不断放下自己高贵的身段,在向被世俗功利绑架的现实情景中将自己降格,在财富面前放下高尚和自尊,只为的是使自己脑满肠肥、雍容华贵?文化难道非得要如此这般,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能耐和堪比甚或超越“经济行为”的本事?假使这种场面一旦真得出现,所有自视清高(我们时代,即使有这种意识的人也已经难能可贵了)文化人一定不愿意承认这是自己所希望的结果。
“文化”与“心”日益严重梳理,当今中国的文化出现了诸多“负心”、“背心”、“伤心”等痛心的行为。历史上,一种文化理念、一种文化主张、一种文化的实践等,一定是指向某种确定优良心性秩序,为着与某种“心性秩序承诺”,致力于以某种该文化所认可的理念和相应的实践典范整殇自己的文化形态,从而明确并承担其文化自身的使命与责任的。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养心、护心、润心已经丧失清魂、安魂的功能,我们已经羞于做一个“文化人”。因为民众不知道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甚或起码的文化人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如此,我们首先必须警惕的是与社会过程“合理化”相伴而生的文化的合理化,因为这意味着文化对社会的反思与独立判断能力的丧失。就文化所代表和体现的理论品质和价值理想而言,它要获得人们的尊敬和向往,一定必须有自己的明确的边界和担当。江泽民在担任国家主席时就明确提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更是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而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关于文化建设的思路更是明晰:中国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建设美丽中国。所有这些文化建设的理念,强调了文化建设的核心,以及文化建设本应坚持和必须实现的公共性、公益性效能和价值目标。
(二)塑造心魂的文化是如何可能的
1958年元旦,以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四人名义联名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其中第六部分——中国心性之学的意义,从根本上指明了中国文化建设所必须努力的方向,以及一代中国人价值自觉的实质。
论及“心性之学”,“五八宣言”如此论述:“我们从中国人对于道之宗教性信仰,便可转到论中国之心性之学。此心性之学,是中国古所谓义理之学之又一方面,即论人之当然的义理之本源所在者。此心性之学,是为世之研究中国之学术文化者所忽略所误解的。而实则此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亦是中国思想中之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说之真正理由所在。”[7]“中国心性之学,乃至宋明而后大盛。宋明思想,亦实系先秦以后,中国思想第二最高阶段之发展。但在先秦之儒家道家思想中,实已早以其对心性之认识为其思想之核心。”[7]“古文尚书所谓尧舜禹十六字相传之心法,固是晚出的,但后人之所以要伪造此说,宋明儒之所以深信此为中国道统之传之来源所在,这正因为他们相信中国之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源。然而现今之中国与世界之学者,皆不能了解此心性之学为中国之学术文化之核心所在。”[7]中国儒家文化关注的是个人内在的生命与心性,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形而上学的概念体系。当代新儒学,可以概括地称为生命儒学或心性儒学,这是因为当代新儒学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生命与心性,用哲学上的术语来说,就是个人的存在、形上的本体和以生命心性为归依的抽象的历史文化。这从唐均迈先生的代表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牟宗三先生的代表作《心体与性体》、《政道与治道》等新儒学的经典著作中都可以看到。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都必然有其“心”,有其“魂”。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地发挥其重要影响,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心魂的存在。问题是,文化的这种心魂,一定是某种文化在其长期的实践中不断修炼的结果。因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文化的失魂落魄情形,其实并不鲜见。如此,以下的追问或许正成为问题的焦点性,那就是:立足市场化社会之强大的功利导向与资本崇拜逻辑,以一种我们所期待的“文化的方式”去生存是何以可能的?
我们这个社会,文化没有按照自己应该有的方式,教会文化个体明其本分和职分,“安分守己”的过自己的生活。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感性欲望的叙事”,除非这个社会是“宗教禁欲”的社会。问题是,谁能保证这种感性化能量的扩张不会超过或者取代社会正常积存下来的理性化能量。谁都无法预知,一旦真的出现了这种文化动能和势能的全面逆转,社会生活会变成什么样的存在态势。“快乐女声”“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舞林争霸”……面对满目的感性文化样态,面对多样的“文化”之令人眼花缭乱的赤裸裸的肆无忌惮的表演,我们感受到了那个长久被压抑了的憋屈的身体“被解放”后的快感。或许我们得承认,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掌握文化成为自己的方式。所有有关文化的努力,因不断地有“非文化”、“伪文化”因素的介入、干扰,根本无法保持自己的纯粹,都变得那么无助。
如果文化人都热衷于名利,如果文化人都忘掉了自己的本分而不愿意安贫乐道(其实现代文化人已不愿意花费多少心思去经历和题为这种使文化人真正成为文化人的必经的心路历程了),这个社会还要文化做什么?这个社会还有什么理由可以称为文化社会?文化人之于社会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每日所能看到的,是被装扮的珠光宝气、艳丽无比的文化,这样的文化还能有什么立场去教化世人?世人又凭什么对这样的文化保持尊敬?“文革”时,为了革面洗心,曾经主张人们要“灵魂深处闹革命”。什么是“灵魂深处”?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文化什么时候,为着何种目的,真正地进入了个体的“灵魂深处”,产生了“动人心魄”、“摄人魂魄”的力量?我们的确有过这样的时代。在文化已经变得不知道是谁的文化,为谁的文化了。主流文化之声音,表面上看似强、大,但实际上是缺乏足够的底气的。所谓引领,只能是流于表面,根本无法触及到民众的灵魂深处。
文化必须秉持自己应有的立场,是文化的一定首先不是经济的,是文化的、属文化的同样一定不是政治的,甚至不是日常生活的。最近,笔者忙里偷闲看央视“世界名画”栏目,感到非常震惊。从梵髙、米勒、高更到梵卜仑……画风变幻之诡异,艺术思想之高深,艺术真理精神追求之坚定、自信和执着,尤其是艺术家那种将艺术与生命融为一体,为艺术痴狂、现身的境界,令人扼腕!其实古往今来,不仅仅是艺术,人类精神生活领域尤其是人文艺术各个行业的从业者中,不乏这样的典范和先例。
三、通过文化建设实现民众优良心性秩序的当务之急:基本价值观基因质素的甄别和优选
当下中国有关“价值”和心灵秩序的理论叙事和话语方式为什么一定要是“文化”的?文化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或者说具备了对诸多异质性“价值”和心灵秩序现实进行反思和评判的资质和能力?这样的文化生成了吗?
文化以何种方式可以助益我们“按照人的方式”成为我们自己?在这样一个论题下,我们理应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文化在何种意义上关乎世道人心,关乎优良人性;二是文化在何种意义上关乎我们每个现实的个体心性(灵)秩序的养成?在文明人类进化的意义上,作为一种非自然选择的结果,我们被锻造为一种“文化的存在”“。那么,所谓文化性存在对于我们每个个体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文化性存在的真蕴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种或者表现得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搞清楚。不仅如此,我们能否说,有一种表明上看似自觉的、自为的文化现象和有目的(为着某种目的)文化实践行为,我们就必然是一种或者会成为”文化性存在“”吗?
严肃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存在,其最为正当性的关切,一定是伦理性的。对于文化本质和文化实践的伦理性关切意味着,这种关切一定是一种基于现代公共生活中现实个体之生存本位意义上的舒适、体面、优雅而后尊严的“伦理性”生活品格、人格修为和境界的努力。优良的文化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一定是关涉此一个体的心性秩序。现代社会对个体的关切有多种方式:利益最大化的关切,身体解放的关切,感性欲望解放的关切,身份、地位的关切,所有这些关切,其实都指向一钟外在性的关切。这是无选择、无未来,并不断膨胀的关切。俗语有云:“心病还得心病医”。我们面对民众业已严重且深度迷误的心灵,一定要审慎地选择和不遗余力、花大气力,精心培育先进文化。先进文化一定是优秀的文化,与文明人类的制度价值逻辑和人性的诉求相一致的。(1)先进文化可以明心、养心;(2)先进文化可以润心、护心;(3)先进文化可以洗心、清心。
文化在更深刻、更根本的意义上关涉人性,其最高成果,是现代公民个体之“人文素养”。文化要走出卑琐和平庸,有助于世道人心的提升。一个民族的生机来自精神价值——慈爱、善心、良知、诚信、正义、人道、崇高、廉耻;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养成的以优雅、尊严、体面、高贵、舒适、从容为基本内容的属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生存心态。当然,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也意味着这不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不完全依靠个人的自我调整,而是需要作出社会组织和制度上的种种安排。文化质性的过去态、当下现实态以及未来可能态的确立,意味着对一种“伪现代性”辩证法意义之社会文化功能的价值自觉反思和检视。文化曾经是一种依托优良制度伦理规范,对特定历史时代和共同体中应然的“助人成人”的理念、方式等所做的最恰当、最合理方式的追问、理解和探究,是一种人性自我证成、自我澄明、自我成就和自我实现的方式;这种努力最终获得的是一种有别于自然秩序、社会秩序的独特的精神生活秩序——人文秩序的求证与获得方式,这是人成为人、制度成为制度的方式,属人的以及人属的根本性价值,就生成在这一过程之中。
但是,人类在文明进程之中,文化的这种以“正能量态”存在和发展的形式逐渐改变了。经济利益的追逐、政治生活中人们对变质了的“权力”的盲目崇拜,思想文化生活中个人失去约制的姿意妄为为的放任化了的自由意志本能,成了新的“文化”功能,取代了甚或渗透到文化之中。当然,我们不能说社会生活场域中完全没有代表正能量场域的文化,但这种文化的影响力正在减弱,根本不足以抵抗与它处于对抗和抗衡状态中的其他也以“文化”面目和“文化”名目而出现和存在着的所谓“文化”。文化还是那个令我们肃然起敬的高尚事物吗?文化如不高尚,还能凭藉什么成为“独特性”存在的理由?还凭什么成为人们敬重的对象?文化商品化、文化世俗话、乃至文化大众化以后,导致的将是文化自身的质变!文化成为谋取个人功名利禄的工具。
真正的文化主体并没有形成,现有的文化主体所严重缺少的,是对一种坚定的道德价值主见的坚持意识。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文化、道德、价值理论一直向现实让步,总是反思理论自身的逻辑非圆融问题,而没有意识到,现实有自己的当然的逻辑和稳定秩序,现实已然变得非常“疯狂”,根本不屑于理睬文化与价值理论。或问:那个与个体优良心性秩序相关的文化,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一定是依托于制度共同体之诸多要素,合力作为的结果。这种性质的文化,首先一定吁求一种风清气正的制度行实践氛围。是优良制度“良治”的产物。
我们必须对文化质性的过去态、当下现实态以及未来可能态——一种“现代性”辩证法意义上的反思和检视。文化曾经是一种依托优良制度伦理规范,对特定历史时代和共同体中应然的“助人成人”的理念、方式等所做的最恰当、最合理方式的追问、理解和探究,是一种人性自我证成、自我澄明、自我成就和自我实现的方式;这种努力最终获得的是一种有别于自然秩序、社会秩序的独特的精神生活秩序——人文秩序的求证与获得方式。这是人成为人、制度成为制度的方式,而属人的以及人属的根本性价值,就生成在这一过程之中。但是,文化的这种以“正能量态”存在和发展的形式在文明进程之中,逐渐改变了。经济利益的追逐、政治生活中人们对变质了的“权力”的盲目崇拜,思想文化生活中个人失去约制的姿意妄为为的放任化了的自由意志本能,成了新的“文化”功能,取代甚或渗透到文化之中。
我们对文化的期望在于这样一种表达语式:希望“我”能帮助“你”,就像帮助“我们自己”。我们有是谁?我们自己的文化自觉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以至于我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向那个我们很不满意的文化提出自己的“过分”要求,希望在不改变自己的情况下,寄希望于贤者和圣者向我们贡献一种新的文化主张,然后我们去现成地接受就万事大吉了。这样一种幻想和天真之见其实并非始自今日,也并非今人才有的一种不切文化实践现实的想法。文化必须具有的神圣的宗教情怀。在一个人们普遍认为是浊世的氛围中,文化首先要做的是净身。文化要形成自己的心灵和心魂,必须向宗教致敬,从宗教中汲取无限的资源以改良和纯净化自身。一种缺少宗教关怀的文化,绝对不是一种世俗意义上的“良善的文化”。文化在成就自己、成为自己的过程中,只有具备一种宗教般的大爱之心、大善之心,才可堪称找到了人性完美化的稳固起点。
着眼于“天下一家”、“人类一体”的世界公民情怀与胸襟,面向未来,为着一种“幸福性生存”与“诗意化栖居”,我们真的需要一种高标超拔的精神文化生态的期许。文化建设与价值自觉的最后的落脚点,一定是基于并为了某种美好的伦理文化生态,以及由此规约所开显出的生存与生活样态。其实质,是一种圆融和完满形态的类精神生态的达成,表现的是人类对待自然所呈现出来的道德态度和价值理念。如著名生态文化学者罗尔斯所言:“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角度看,生态系统的美丽、完整和稳定都是判断人的行为是否正确的重要因素。”[8]307不仅如此,现代人文化与价值高度觉醒标志,就是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一句诗:“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所谓“诗意地栖居”,用中国哲学的语言将,就是在先进文化的引导下,进入一种“心性澄明之境”。文化大儒梁启超有言:“文化是人类所开创的有价值的共业。”如此,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高远目标在于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的文化有助于人类在地球上的诗意的栖居,这种文化是智人这种智慧物种的文化。存在着许多各有千秋的起居方式。诗意地栖居是精神的产物,它要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它将把人类带向希望之乡。”[8]484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幸福意识和观念的获得,是人之为人之真正的文化与价值主体意识觉醒的标志(这种存在状态就是现代人的“生态公民”意识)。只有当人以生态文化的方式理解自然万物的存在本性的时候,属人的文化以及依托于此所获得和享有的心性本位的幸福才是完整的、真实可欲的境界。
[1] 麦克尔·卡里瑟斯.我们为什么有文化[M].陈丰,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
[2] 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J].北京:国外文学,1995(2):3-5.
[3]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381.
[4]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北京大学学报1997(3):15-22.
[5] 袁祖社.“公共性”的价值信念及其文化理想[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7-11.
[6] 徐贲.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教育力量[J].思想理论教育,2012(18):10-14.
[7] 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J].台北:哲学与文化,1958(1):1-17.
[8] 霍尔姆斯·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