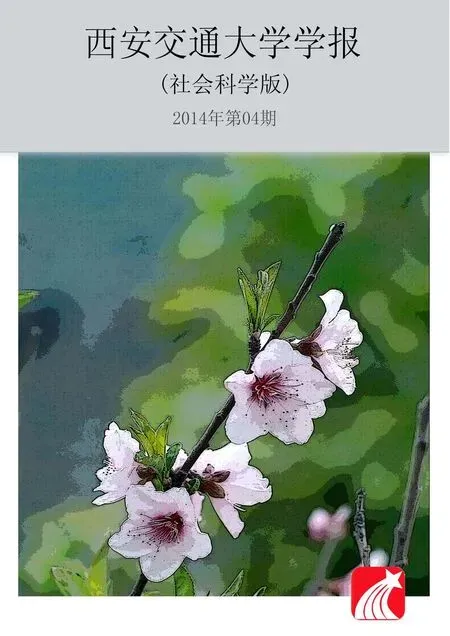《论语》为何多讲“信”而少言“诚”
——兼论“诚”的形上学意蕴
黄 萌,刘学智
(1.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2.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论语》为何多讲“信”而少言“诚”
——兼论“诚”的形上学意蕴
黄 萌1,刘学智2
(1.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2.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却多言“信”而少言“诚”。《论语》为何多讲“信”而少言“诚”?此绝非一般的言多言少的问题,其不仅涉及“信”与“诚”的意义差别,更涉及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其间从孔子到思孟学派的思想深化,特别是“诚”的形上学内涵与其作为道德心性论范畴的思想特质,是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
信;忠信;诚;论语;儒家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以“诚”、“信”为核心,对君子乃至于圣贤提出了修己成仁的标准和要求。《论语》中多言“信”,有“人无信不立”,“言而有信”,“言必信,行必果”等说法,这些说法琅琅上口,并在民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论语》却极少言“诚”,且没有将“诚”“信”二字连在一起并用。而后出的思孟学派所著的经典皆提到“诚”。《论语》为何多言“信”而少言“诚”?这一现象当作何解释?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加以辩明。
一、《论语》多讲“信”,思孟学派多言“诚”
(一)《论语》多言“信”
《论语》中“信”字共计出现三十八次之多,可见“信”在孔子思想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意义,以下将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忠信。“忠信”二字屡见于《论语》。朱熹《论语集注》曰:“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1]55据此,信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就语言上说,发言之实则为信;二就事上说,做事之实亦为信。“信”与“忠”相连,是己忠于人,人信于己之意;或反过来,人忠于己,己信于人。“故人之交相忠者,又贵其能交相信。人不信我,亦不足以竭我之忠;信者,自人而言之也。”[2]忠、信系人与己互相之理,欲忠于人,必须人先信己,若人不信己,则忠不能达。李泽厚先生曾说:“‘忠’、‘信’又是两个重要范畴,既关系乎情感,又塑造乎人格。但其位置仍次于‘仁’、‘孝’”。[3]36由此可知忠信在《论语》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孔子以“信”作为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1]112
孔子从文献、行为、忠厚、信任这四个方面指导学生学习,也就是从书本知识、社会实践和道德修养三个方面教导学生。这是从施教的顺序来说,但是如果从学习的顺序来说则恰恰相反。《学而》篇中有所论及: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56
最后,往高一层说,“信”也是实行政治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条件。
《学而》篇中曾提及施政治国,必重信用: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56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1]153
以上语句说明全国上下都有信用的诚信政治才是稳定、和谐的治国之道。如此,将信任加诸于政治之上,更体现出“信”的重要地位。又有: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1]216
意思是说,对于君子来说,只有获得上至国君下到人民的信任才可以在政治工作中立于不败之地。李泽厚先生曾说:“信任乃由缺乏明确秩序的人类群体组建规范以至成立国家的基本原则和必要条件。”[3]328
孔子伦理学的核心思想为“仁”,而“信”是道德伦理规范之一,与“仁”的联系甚为紧密,是孔子人学与仁学中不可或缺的道德理论与实践之一。《论语正义》曰:“人有五常,仁、义、礼、智,皆须信以成之。若人而无信,其余四德,终无可行。”[4]
相形之下,《论语》中“诚”却仅仅出现两次,一处为《颜渊》篇引用《诗·小雅·我行其野》之辞“诚不以富,亦祗以异”。“诚”作“成”,此句本意为:负心人另有新欢,的确不是因为对方富有,只是喜新厌旧罢了。[5]“诚”之意为“的确”[6]19,而将这句话引在此处,很难解释。宋程颐曾说此处是“错简”,而钱穆亦说:“当时错简,应在十六篇‘齐景公有马千驷’章,因下章亦有齐景公字而误。”[7]据张丰乾所作《〈诗经〉与先秦哲学》一书说:“孔子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是直接回答辨惑,……在孔子看来,爱和恨也是‘过犹不及’,要摆脱疑惑,就要‘主忠信’,从实际情况出发,向正义靠拢,自然不会被偏执的爱或恨所迷惑。”[8]而《论语》中“诚”出现的另一处为《子路》篇“诚哉是言也!”说明此句话很对,别无它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说孔子少言诚,并非说他从未涉及诚的思想。如他所说的“天何言哉”与“诚”就有一些细微的联系。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1]204朱注:四时行,百物生,莫非天理发见流行之实,不待言而可见。圣人一动一静,莫非妙道精义之发,亦天而已,岂待言而显哉?[1]205由此可知,《论语》这里所说的“天何言哉”隐隐含有“诚”之意。孔子认为,以言语教导弟子,不如以自身的实践行为,以身作则来教导更加直接与贴切。天道不言,所以毫无欺骗和保留,人道也同样如此,仅仅言传而无身教,容易使弟子重视了解言论,而忽略了身体力行的工夫。朱熹解释“诚”为真实无妄,与孔子眼中自然之天的天德相近。
故而,可以说《论语》中亦传达出某些关于自然之天的思想。但是,这种自然思想还未达到形而上的高度,仅仅略加提及而已。《论语》更加关注人及人在社会中的行为等以“仁”“礼”为核心的形而下的人生哲学。
(二)思孟学派多言“诚”
孔子少言“诚”,但是思孟学派却多言“诚”。相传由子思所作的《中庸》就从三个层面对“诚”进行阐释。首先,以天人相分揭示出诚的意义。“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1]35诚出自天道,是天道的属性,天道真实无妄地忠实于自身的职责。只有圣人可以做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而达到“诚”的境界,普通人必须要“择善而固执之者也”,通过不断的自身修养,经历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一系列艰苦的过程才可以达到“诚之”。其次,以诚、明合说天道与人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1]37,此句将“诚”作为圣人之天性,明言贤人须经过学习才能到达由明至诚的境界,“诚则明矣,明则诚矣”[1]37指出人道可至于天道,合天人而一之也。最后,将“诚”作为宇宙论的最高本体。“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也”[1]37,“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1]38,“诚”将万物与人相联系,使物从自在之物成为与人密切相关之物。人与万物的浸润感通,人与天的密切相关都通过“诚”这样一个道德本体表达出来。所以,“诚”不仅仅是一种人性的终极存在状态,而且是沟通人与万物,人与天的一切道德行为的超越根据。天生万物真实不欺,是天道之“诚”的自然展现过程。
在思孟学派的其他著作中,也有很多关于“诚”的语句。《孟子》有云“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胡广《四书大全》:“云峰胡氏曰:此所谓‘思诚’即《中庸》所谓‘诚之’其工夫,皆兼知行而言,思诚者修身之本,是修身以知行为先,明善又为思诚之本,是知行之中又当以知为先也。”[9]其后,又有“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认为“诚”是人的真实与诚实的表达,万事万物之理已由天赋予人,只要内求于己,诚实无欺,则能体天下万物之情,获得最大的快乐,进一步表达出对于“诚”以心之思进行修身的工夫。《大学》中亦有“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等等。
由上可知,“诚”作为思孟学派的核心思想,使人和天在大化流行过程中一致起来,而“信”仅仅是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要一环,其思想内涵与诚不可同日而语。
二、“诚”作为道德形上学的思想特质
据考证,中华文字的起源甲骨文中只有“成”与“信”的写(画)法,以“成”为“诚”的通假或解释,而无“诚”。[10]较为晚出的金文、篆体等陆续开始有了“诚”字的写法。
较《论语》早出或同时的典籍对“诚”也少有提及。如,《易经》中以“孚”代表诚信,而“诚”字在《易传》中也仅仅出现两次,《文言》对《乾》卦九二爻辞的解释有“闲邪存其诚”,以及对九三爻辞的解释亦有“修辞立其诚”。《诗经》中也仅有一处提及“诚”,多以“信”来表达诚信之意,或以“成”通“诚”,见《诗经词典》对“成”与“诚”的注释。[6]19-20与其相似的是,《尚书》中仅有一次提及“诚”:“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见《尚书·商书·太甲下》)。
由此可知,《论语》之前的典籍,对“诚”的应用远少于“信”,而其后的思孟学派将“诚”提高到天道的高度,表现出其深厚的形上学意蕴。
(一)“诚”较“信”而言更富有形上学的色彩
虽然,从字面上看,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诚,信也。从言成声”。《尔雅·释诂第一》:“允、孚、亶、展、谌、诚、亮、询,信也。展、谌、允、慎、亶,诚也…《墨子·经上》:‘信,言合于意也。’”[11]晋郭璞《尔雅注疏》曰:“[疏]‘允孚’至‘信也’。释曰:皆谓诚实不欺也。”[12]诚实不欺,也就是信,故“诚”亦有信意,两字可以互释,这只是在一般的字义上说。但是,从字形上看,与“信”为人言不同,“诚”通“成”,具有成己成物之意。
《论语》的“信”,仅仅作为伦理道德规范之一,并未达到与天道、“诚”相齐平的高度。孙以楷在《道家与中国哲学》中指出:“孔子只把‘诚’作为一个次要的规范,更未提到天道高度”。[13]364此言极是。对于信,朱熹《论语集注》谓:“信者,言之有实也。”[1]68孟子译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孟子·尽心下》)。自身实实在在的拥有了可以称为善的德行也就是信,也可以理解为信实,其中实在之意明显。(按:杨伯峻将“信”译为实在)[14]。而朱子在《中庸章句》将“诚”解释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1]36此句意为,“诚”就是真实无妄,是无人为造作的天理的自然本性,并体现出宇宙的创生性,是万物生成和道德价值的最终根源。“诚之”,是天赋予人的自然之性,亦为自然无伪的真实无妄,人如果为气禀物欲所累,则不能达到真实无妄的本性。
首先,诚如牟宗三先生所说,此形而上之诚体是一个抽象体。“自实体言,为诚体流行;自轨迹言,为终始成果;自成果言,则为事事物物”。[15]“诚”是道德伦理超越的根据,并非具体而真实之真诚,通过天道之“诚”对人的下贯以达到天人相互感通的最终目的。类似地,杜维明曾将“诚”看作儒家的道德形上学[16]。在本体论的层面,“诚”首先是本体意义上的天道,即宇宙生成发展过程的一种本质属性或发展趋势;在生成论的层面上,“至诚无息,不诚无物”,“诚”真实无妄,生生不息地创生出宇宙万物而为万物之源。牟宗三先生认为,成就个人道德创造的本心仁体总是连带着宇宙生化而为一的。“诚”则确实充当了这个道德本心仁体的本然天性,且连带着宇宙生化而为一。思孟学派的著述通过对“诚”的诠释,将天道拉进人心,使之内在化,并转化为形而上的实体,达到主客融会天人合一。在宋明理学家看来,“诚”是理,是天理本然的状态;“诚”又是“成”,具有生成的意义,成己、成人、成物。所以,天道诚体,“诚”是天的属性,具有形而上的创生内涵;人之道以诚为工夫,通过反身求己以复归于诚,体现天道,“信”即为人之道,是形而下的为人之方。
其次,“诚”的形而上意义使得《中庸》全篇具有了儒道综合的性质。萧萐父先生认为:“《易》、《庸》学作为儒家的形上学,其主要的理论贡献是:善于有选择地吸收了道家思想,新建构了儒家的天道观和人道观。”[17]这里,吸收道家思想表现为选择了一个与“道”相似的本体“诚”,将人之道德抽象为天道之“诚”。此外,又把“诚”视为一个无形无相的道体,即形而上的实体。由此看来,“诚”作为思孟学派的核心内容,贯通天道与人道,综合了儒道两家的思想特征,既将儒家心性思想提升到了形而上的天道境界,又融合汇通了道家思想中之大“道”的宇宙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开创了儒家心性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二)“诚”作为道德心性论的范畴而得以充分地发挥
“诚”与思、意相关联,且与“性”亦密切相关,可知“诚”涉及心性之学,并作为道德心性论的范畴而得到充分地发挥。据陈淳说:“天道流行,赋于人,而人受以为性,此天命之本然也者,即诚也”。[18]又《中庸》谓:“天命之谓性”。性是与生俱来的,是天赋予给人的,而性的本然状态即诚,成为人性的理想状态,“诚”由天道内化为人的道德修养,具有“成己”之意,外显为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是我之体人以成人,我之体物以成物,使外在的天地、人、物都能与己感通浸润为一体,即成人成物。“诚”是天道对人的敞开,天示人以“诚”,但“诚”不是天道本身,天道无所谓诚与不诚,而“诚之”则是对人心性的要求,最终达到真实无妄,不为物欲所累的圣人之性。所以,“诚”成为人与天地相参的根本条件,也由此沟通天人,使天道之“诚”的外在本体落实到人心,内化为心性本体,成为道德心性论的最终根据。孟子“思诚”亦是从心性上讲如何反身而诚,返归到人的自然本性。又《中庸》关于“诚明”之论,也是对圣人之性与凡人之性的区别。自诚明,是圣人之德,具有天所赋予的自然之性,自明诚,是普通人为学的过程。孔子所说的仁、义、礼、智、信五德都是人修养身心所要达到的道德水平,是为人处事的基础,但却还未涉及到具体的心性理论。所以,较信而言,“诚”更具有内在性,与人的心性紧密相关,是人自然天性的根本来源。孙以楷曾说:“孟子为了给儒家的外在的道德规范以内在心性的根据,并进而为人的心性构建一个形而上的宇宙本体,从而为儒家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取得合理的存在依据。”[13]366陈淳《北溪字义》说:“诚字与忠信极相近,须有分别。诚是就自然之理上形容出一字,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说”。[19]由此,“诚”是天理的自然流行,落实到人的本然天赋,是天所赋予人的根本气质属性,也就是“天命之谓性”的性,用宋儒的话说是“天地之性”,而“忠信”是人后天的道德信条,人的道德行为修养,亦可以表征为“气质之性”。
一般认为是思孟学派所著的竹简《五行》篇中,也有天道和人道的提法。竹简《五行》篇在第二章提出“善,人道也;德,天道也。”[20]陈来先生对后一句有如下论述:“德合于天道,而不是德得自天道…把人道与天道相分,表现出作者既注重从‘形于内’的内在性理解‘德’,也同时从‘天道’来强调‘德’的普遍性、超越性的意义。…只是,在竹简《五行》这里,内在性还未达到《孟子》‘性善’的观念,超越性也还未达到《中庸》‘天命’的观念,但《五行》的作者对‘德’的超越性的面向已经有了明确的肯定,为《中庸》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基础。”[21]由此看来,《五行》篇中虽已有“人道”与“天道”之分,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虽然还未提及“诚”,但是已经看到伦理道德不仅存在于人道,其超越性在于天道,为之后《中庸》、《孟子》“诚”思想的生成发展提供了基础。
朱熹弟子杨时曾对《论语》少言诚有所困惑,他认为:“《论语》只教人,凡言忠信恭敬,所以求仁而进德之事,莫非诚也。《论语》示人以入之之方,《中庸》言其志也……”[22]而“诚”为孔子所罕言,孟子所常言,也是为了更真切、透彻地传承夫子学说,以天道明人道,进一步阐发了内圣外王之道不仅要成己,更要成人、成物,到达天人合一的境界。综上所述,无论《五行》篇之“天道”,或者《中庸》、《孟子》之“诚”,都是将《论语》“仁”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超越人伦道德的天道思想,于内在心性的层面将天人相互联系,从人伦到天道,从形而下之人伦社会到形而上之宇宙论的高度,并且将这种人伦道德引向天道之“诚”。这是儒家学者对道德根源更高更深层的一种追问,而这个道德的终极根源就是天,最终升华到“天人合一”。
三、“诚”对后世儒家思想的影响
“诚”的道德形而上的深刻涵义为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寻觅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根据,那就是天道,所以“诚”对后世儒家思想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唐代,面对着佛道两家对儒家的挑战,唐宋儒者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找出能够明快地彰显儒家思想体系的文献,唐代学者韩愈和李翱注意到《大学》、《中庸》中所阐发的以“诚”为核心的心性理论可以与佛道相抗衡,并且可以从其中梳理出儒家理论体系,所以开始推崇二书。在韩、李的影响下,构建儒家的心性学说和修身理论成为宋儒孜孜以求的目标。
宋儒一派,无论周敦颐、朱熹、二程直至张载,都非常重视诚的学说,以存诚作为心性存养的首推之方法。诚,在理学看来是一种实理,“诚者实理也。专意何足以尽之?”(《二程粹言》卷一论道篇)“诚只是实,诚只是理”(《朱子语类》卷六),阳明也说:“诚是实理”(《传习录下》)。所以,理学家认为做任何事,都应该按照宇宙的实理去做,尊德性而道问学,这样才是真实无妄,否则就是伪。朱熹所著《四书章句集注》对儒家的心性理论做出了系统性的整理和归纳,使得思孟学派的思想得以传承,并被发扬光大。宋卫湜所撰《中庸集说》更是将周、张、程、朱、陆五家之言汇集,对《中庸》思想进行梳理,将“诚”的深刻内涵与性论相结合,阐发儒家修身思想。
总之,无论“诚”或“信”都是儒家道德伦理的核心思想。“信”虽不是孔子的主要思想,但从侧面反映出其为人、处事、治学、论政的思想特征。通过“信”在《论语》中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出《论语》对人的身心修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思孟学派在传承《论语》思想的同时,又将“诚”纳入到儒家心性论的核心思想之中,并赋予其超越的道德内涵,对后世儒家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1] 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
[2]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
[3] 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三联书店.2008.
[4] 刘宝楠.论语正义[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5] 裴溥言.先民的歌唱:诗经[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
[6] 杨合鸣.诗经词典[M].北京:崇文书局,2012.
[7] 钱穆.钱穆先生全集:论语新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8] 张丰乾.《诗经》与先秦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9] 邓球柏.孟子通说[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10] 姜修尚编.甲骨文书法常用字汇编[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11] 胡奇光,方环海.尔雅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2] 郭璞注,邢昺疏.十三经注疏 之十二 黄侃经文句读 尔雅注疏 附校勘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3] 孙以楷,陆建华,刘慕方.道家与中国哲学:先秦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5]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6] 杜维明.中庸洞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7] 萧萐父.《易》《庸》之学片论[J].复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
[18] 陈赟.中庸的思想[M]. 北京:三联书店,2007.
[19] 陈淳.北溪字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0] 刘钊.郭店楚简校释[M].福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21] 陈来.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5.
[22] 卫湜撰,杨少函 校理.中庸集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司国安)
WhyDotheAnalectsofConfuciusSpeakMoreof"Xin"butLessof"Cheng"? ——a discussion on the metaphysical implication of "Cheng"
HUANG Meng1, LIU Xuezhi2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lleg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s a Confucian classic bibliography,have more words on "xin" (faithfulness) but fewer words on "cheng" (honesty). Why? This is absolutely not a problem saying more or less. It not only involve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eaning between "cheng" and "xin", but also concerns some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them, the thought deepening from Confucius to the Si-meng School, especially the metaphysical connotation of "cheng", and its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 as the category of moral mind theory,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is phenomenon.
faithfulness; loyalty and faithfulness; honesty; Analects of Confucius; Confucian thought
2013-05-06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08JA720022)
黄 萌(1976- ),女,江苏淮安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学智(1947- ),男,陕西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B222
A
1008-245X(2014)04-008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