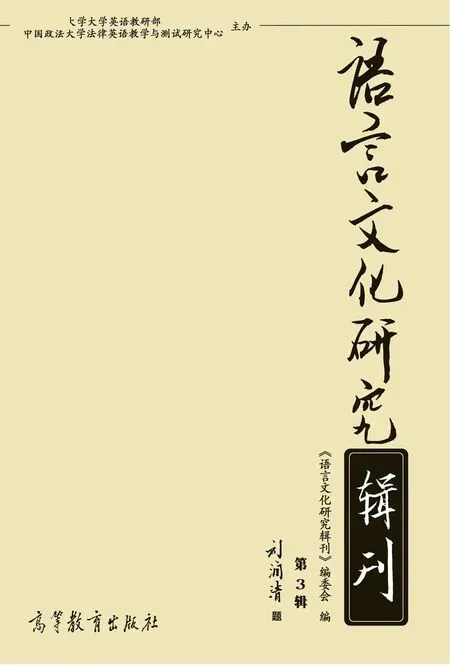爱琴海边的凯尔特薄暮
——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对古希腊悲剧的重写
尹晟(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北京100048)
爱琴海边的凯尔特薄暮
——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对古希腊悲剧的重写
尹晟
(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北京100048)
[提 要]爱尔兰文学向来浸淫欧洲古典传统,向古希腊、罗马文学借鉴甚多。20世纪的爱尔兰戏剧不断重写古希腊悲剧,力求解决爱尔兰的当下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叶芝、辛格、奥凯西三位杰出剧作家重写古希腊悲剧的艺术实践,展现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的艺术景观,探讨爱尔兰民族身份和文学特性的构建。
爱尔兰文艺复兴 重写古希腊悲剧 叶芝 辛格 奥凯西
一 引言
1893年,爱尔兰诗人叶芝整理斯莱戈(Sligo)和高威(Galway)两地的民间传说和神话,创作出脍炙人口的散文诗集《凯尔特的薄暮》(The Celtic Twilight,又译作《凯尔特的曙光》),吹响了爱尔兰文艺复兴(Irish Literary Revival)的号角。早在1860年,爱尔兰著名剧作家迪翁·布希高勒(Dion Boucicault,1820-1890)就在其剧作《金发少女》(The Colleen Bawn)纽约首演海报中如是写道:“爱尔兰,风物万千,温煦浪漫,剧作家们却过宝山而空回。迄今,爱尔兰不过是些浮夸的闹剧,描摹低俗的生活,刻画奴役下的呻吟。这些,并不是爱尔兰社会的真实写照。”(Walsh,1915:74)1897年,“爱尔兰文学剧场宣言”(Manifesto for the Irish Literary Theatre)如是写道:“我们将向世人展示,爱尔兰文学并非其设想那般充斥着插科打诨和陈情滥调,而是古老理想主义的家园。我们坚信会得到所有爱尔兰同胞的支持,他们早已厌倦遭到误解。”(Gregory,1972:20)是年,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马丁(Edward Martyn,1859-1923)、格雷戈里夫人(Lady Gregory, 1852-1932)三位立志改变爱尔兰戏剧面貌的剧作家在高威海滨一所别墅里会晤,揭开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运动的序幕。“从此,一个以民族主义为动力、以理想主义为指导、以艺术完美为奋斗目标的新戏剧运动便发展起来。”(陈恕,2011:155)
“20世纪上半叶爱尔兰戏剧最突出的特点有二:一是矛盾的独立观念;二是英国本土文化和爱尔兰文化的冲突。这些特点促生了爱尔兰文学的三条发展道路,即英国道路、爱尔兰本土道路和欧洲道路。”(罗朗,2008:105)爱尔兰受古希腊传统熏染日久,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曾是很多爱尔兰人的必修科目。当代爱尔兰著名剧作家布赖恩·弗里尔(Brian Friel,1929-)的名作《翻译》(Translations,1984)生动刻画了爱尔兰人对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熟稔与英国殖民者的无知。爱尔兰人对古希腊经典极尽推崇,对英国经典则不加理会。村民学校校长休(Hugh)对英国军官如是回应:“华兹华斯……不。恐怕我并不熟悉你们的文学,中尉。我们更亲近温暖的地中海。你们那个岛嘛,我们总瞅不见。”(Friel,1984:417)爱尔兰剧作家青睐古希腊神话和悲剧,从中取材,以此消解英国殖民者和英国文化的侵袭,争取民族独立和文化自觉。遥远的古希腊悲剧与现实应和,恰好为他们提供一个绝妙平台,争论、求索、角力和反思。他们重写古希腊神话和悲剧,正是经由欧洲道路观照英国道路和爱尔兰本土道路,复兴和繁荣民族文学,澄清和重塑民族面貌,熔铸和展望民族命运。
二 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景观
1800年,爱尔兰王国和大不列颠王国统一,爱尔兰由伦敦的英国议会控制。1846-1849年,爱尔兰因马铃薯减产爆发饥荒,人口剧减,民不聊生,英政府袖手旁观,以爱尔兰共和兄弟会(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为核心的芬尼运动(Fenian Movement)改头换面,卷土重来,再掀独立浪潮。虽然爱尔兰议会党(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领袖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奈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1846-1891)因私生活曝光而身败名裂,未能领导爱尔兰人民实现地方自治(Home Rule),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已锐不可当。爱尔兰运动协会(Gaelic Athletic Association)、盖尔语联盟(Gaelic League)相继成立,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揭开序幕。
1900年,“爱尔兰民族主义意识和鲜明的身份认同,在南方已经多现端倪。”(Ferriter2004:29)地方自治的前景刺激了爱尔兰统一人士(Irish Unionists),备受其阻挠,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Irish Nationalists)坚决要求实现爱尔兰的自治与独立。双方针锋相对,秘密组建的准军事部队——北爱尔兰志愿军和爱尔兰志愿军,冲突不断。“尽管议会政治似乎准备实现地方自治,塑造爱尔兰未来的政治力量倒是积聚于议会之外。”(Ferriter,2004:114)
1916年复活节周期间,爱尔兰志愿军在教师兼律师帕特里克·皮尔斯(Patrick Henry Pearse,1879-1916)和爱尔兰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1868-1916)的领导下,占据都柏林的关键据点,宣布爱尔兰共和国独立。起义六天后遭到镇压,起义领袖送交军事法庭并判处死刑。至此,爱尔兰武力共和派与爱尔兰议会党为代表的非暴力民族主义派彻底分道扬镳。后者领袖约翰·雷德蒙德(John Redmond,1856-1918)虽通过议会政治赢得了爱尔兰在联合王国内的自治,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推迟。到了战争末期,受复活节起义的影响和感染,本不支持暴力运动的大部分民族主义者逐步转向以新芬党①Sinn Fein,爱尔兰语,中文意为“我们”。为代表的武力共和派。1919年,当选英国议会议员的新芬党人在都柏林组成爱尔兰国民议会,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组建爱尔兰共和军。英国政府拒绝承认,培植殖民政权予以对抗,反英独立战争爆发。1921年,新芬党代表亚瑟·格里菲斯(Arthur Griffith,1872-1922)与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签订英爱条约,明确地排除爱尔兰成立共和国的可能,将爱尔兰定位成英联邦下的自治领。条约虽说许可了全爱尔兰32个郡的独立自治,却附加条款容许北爱尔兰六郡退出自由邦,保留在更名后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之中,为贯穿20世纪下半叶的北爱冲突埋下了祸根。因条约被批准,埃蒙·德·瓦莱拉(Eamon de Valera,1882-1975)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带领反条约的新芬党派别离开国会,而共和军中反对条约的也不在少数。1922-1923年间,反条约共和派与条约支持者发生冲突,爱尔兰内战蔓延开来,给爱尔兰社会带来严重创伤,至今仍对爱尔兰政治产生影响。
叶芝(W. B. Yeats,1865-1939)、辛格(J. M. Synge,1871-1909)、奥凯西(Sean O’Casey, 1880-1964)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最重要的三位剧作家。三人的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19世纪后10年及20世纪头30年爱尔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折射时代巨变过程中爱尔兰人民的思想和精神状态,透析爱尔兰如何挣脱“僵化”(乔伊斯语)的殖民枷锁,在血与火中赢得独立和新生。直到19世纪末,世界文学图景中的爱尔兰都由英国人把持和操纵,爱尔兰人不过是些“粗鄙的庄稼汉,迷信,贫穷,暴力,时常喝得醉醺醺。”(Watson,1994:17)在英国人眼中,爱尔兰是一片奇幻之地,却无文明绅士予以教化,到处充斥着野蛮与愚昧。英国人将爱尔兰设想成尚待开垦的后花园和实现抱负的乌托邦,幻想着对其施以改造,彻底完成盎格鲁化(Anglicization——英国化)。“爱尔兰人知道难与英国人抗衡,毕竟后者全面占优势……持续压迫使他们意志消沉,被迫屈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为这些国家提供妓女、劳工、皮条客、小偷、骗子、乞丐和其他乌合之众。”(Mansergh,1965:88-89)19世纪兴起的人种论学说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偏见,一度成为英国殖民者奴役爱尔兰的帮凶。法国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曾经如此持论:“如果允许我们给国家编排性别(就像对个人那样),我们须得毫不迟疑地说,凯尔特民族本质上是女性。”(Renan,2010:81)“历史上,将爱尔兰比拟为女性达成了两个判然有别的意识形态目的:爱尔兰男性借之羁缚爱尔兰女性,将其约束在纯洁性和被动性之中;英国文化帝国主义者借以囚禁整个爱尔兰民族,塑造其孱弱不堪的形象。”①“Thinking of Her ... as ... Ireland: Yeats,Pearse,and Heaney”,see Textual Practice,4.1,1990, p.1.有趣的是,叶芝、辛格和奥凯西三位剧作家在对古希腊悲剧的重写中,都不乏经典的女性形象,算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对英国殖民者和英国文化优越感的最好回击。
三 叶芝对古希腊悲剧的重写
“如果奥凯西算是后世的欧里庇得斯,我们能否将叶芝比作埃斯库罗斯(爱尔兰戏剧之父),而将辛格比作索福克勒斯(在叶芝看来,辛格自己成了一个索福克勒斯式的孤身英雄)?”(Macintosh,1994:xix)作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领袖,叶芝以诗歌与剧作闻名于世,其诗吸纳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数度变革,熔铸出独特风格和多彩景观。叶芝亲历爱尔兰现代历史中最为跌宕起伏的一段,参与民族主义政治运动,曾应邀出任自由邦参议员,同时又长期领导阿贝剧院(Abbey Theatre),呼吁创作爱尔兰人自己的戏剧,复兴爱尔兰文化。叶芝一生创作了近30部剧本,“通过剧场艺术呼唤和建构爱尔兰民族精神,对抗英帝国主义的戏剧文化,提倡回到民族主义的浪漫艺术。”(孙柏,2007:162)
叶芝对戏剧的投入不在诗歌之下,其戏剧创作生涯较漫长,大致可分四个阶段:1898年之前是民族戏剧创作的酝酿期,以处女作《凯瑟琳伯爵小姐》(The Countess of Cathleen,1892)和《心愿之乡》(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1894)为代表,表现他对爱尔兰民间信仰、民间故事、神话的痴迷和眷恋;1898-1908年是民族戏剧创作的鼎盛期,以《胡里痕的凯瑟琳》(Cathleen Ni Houlihan,1902)、《在贝尔海滩》(On Baile's Strand,1904)、《国王的门槛》(The King's Threshold,1904)、《绿色的头盔》(Green Helmet,1910)等为代表,展现他对爱尔兰民族精神的渴求与日臻成熟的诗剧技法;1908年之后,叶芝渐渐远离民族戏剧的创作道路,放弃剧院对群众的集体感召,通过埃兹拉·庞德接触到日本能剧,终于找到对抗现实主义传统的理想道路,即综合面具、舞蹈等多种舞台表现元素,达至间隔之诗意美感,以诗剧《鹰井畔》(At the Hawk's Well,1917)为代表,这一转向与他本人的哲学体系建构密切相关,影响了他中后期的戏剧和诗歌创作①有关该期叶芝的戏剧,傅浩(1999a:59)如是说:他的剧作所表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某种存在的模式;不是传统叙事型戏剧对现实世界的再现,而是一种抽象理想模式的象征。;20世纪30年代,叶芝进入艺术创作尾声,技巧逐渐炉火纯青,代表作有《炼狱》(Purgatory,1939)和《库胡林之死》(The Death of Cuchulain,1939),前者剧情凝练,象征意味浓厚,后者对作者毕生钟情的爱尔兰民族英雄形象加以提炼和归结。
叶芝一生坚持戏剧创作,其作品多变而隐晦。除民族精神、日本能乐、神秘主义等因素外,古希腊悲剧也对其影响甚深。19世纪后半叶,英国和爱尔兰都看重古典教育,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成为知识分子阶层的必修课。叶芝之前,家里三代人都求学于都柏林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叶芝先后就读于英国汉默史密斯的郭德尔芬小学(Godolphin School in Hammersmith)和都柏林的埃拉斯姆斯中学(Erasmus Smith)。其间,尽管叶芝的古典语文成绩并不理想,家庭熏染还是让他对古希腊罗马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说叶芝拒绝上三一学院让父亲失望,可他对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狂热终生不减。此外,叶芝周遭的友人大多具备古典学养,也对其影响很大。曾在三一学院修医科的诗人戈加蒂(Oliver St. John Gogarty,1878-1957)、辛格、马丁等人都熟稔古希腊罗马文学。据牛津大学著名古典学者多兹(E. R. Dodds,1893-1979)回忆,叶芝1914年后与之交往,经常请教古代哲学和宗教问题。不计家庭学校教育和友人影响,叶芝阅读大量古典作品,观赏意大利和西西里博物馆中的古希腊罗马艺术品,研究拜占庭艺术。可见,古希腊罗马文化在叶芝的创作生涯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叶芝喜爱荷马和索福克勒斯,“1908-1910年间可能就读过荷马史诗译本”,(Arkins,1990:18)一直将荷马视作讴歌英雄和生命的顶尖诗人。叶芝阅读了古典学者杰布(S. R. C. Jebb,1841-1905)的索氏现存七部悲剧散文体译本,对《俄狄浦斯王》和《俄狄浦斯在克罗诺斯》尤为着迷,终于在1926和1927年相继改编完成《俄狄浦斯王》和《俄狄浦斯在克罗诺斯》。1907年,叶芝本打算在阿贝剧院首演格雷戈里夫人之子罗伯特的剧本《安提戈涅》,最终却选择了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1907)。辛格认为爱尔兰戏剧运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创造全新的戏剧文学,聚焦新作品的珍奇和感染力,”而非“对公认经典作品愈发完美的诠释”。①see Anthony Roche,“Oedipus at the Abbey”, Classics Ireland, 2001,vol. 8, http://www.ucd.ie/cai/classicsireland/2001/roche.html,2014-09-19.叶芝提出,除乡间剧(peasant plays)外,阿贝剧院还应“择选外国精品演出”以求“拓展表现容度,迎合不同品味,培养新秀作家”。(同上)有趣的是,辛格却未将《俄狄浦斯王》列入“外国精品禁令”单,反倒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诠释了这一经典。叶芝曾尝试改编《安提戈涅》,最终只翻译了781-800行,收入《盘旋的楼梯》(The Winding Stair,1929),题为《来自安提戈涅》(From Antigone)。叶芝借用和改编古希腊悲剧有其政治目的。“一方面,他参与和重构古典戏剧以求将爱尔兰欧洲化;另一方面,他想通过神话、诗歌和戏剧将自身爱尔兰化,摆脱自己英裔爱尔兰人身份带来的困境。”(Younger,2001:7)
从艺术追求和哲学构建上讲,叶芝对古希腊悲剧的青睐也理所当然。他认为戏剧不应该仅仅反映现实生活的片段,他反对自然主义,始终与易卜生和萧伯纳保持距离,力求创建一种高度仪式化的象征主义戏剧。“我发明了一种戏剧形式,高雅、间接、象征,无需暴民或新闻界买账 —— 一种贵族形式。”(傅浩,1999b:122)对叶芝来说,这种戏剧形式在西方传统中的对应物恰是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悲剧。古希腊悲剧几乎围绕神秘题材展开,主人公要么是英雄,要么是神,且演员均为男性,穿着考究,脸戴面具。戏剧冲突靠话语和行动展开,布景极简。此外,叶芝常年阅读哲学典籍(包括柏拉图及新柏拉图学派代表普罗提诺),对灵魂转世和超验学说都有研究。中晚年的叶芝,哲学思想体系越发完善,“塑造的人物典型及其行为、动机、后果等不外乎是对宇宙内部机制的图解、诠释和象征。”(傅浩,1999b:194)“叶芝相信,任何个人秉性和人类历史时期都具有其根本性质,即必属于主观(阴性、创造、情感)和客观(阳性、行动、理智)这两大基本类型之一;而占主导地位的根本性质与其对立面处于此消彼长、你来我往的不断冲突和妥协的运动状态。”(傅浩,2000:18)叶芝青睐主观或者对立(antithetical),憎恶客观或者根本(primary),前者包括古希腊时代、悲剧、浪漫爱尔兰、贝克莱派唯心主义(the idealism of Berkeley),后者包括基督教时代、喜剧、现代爱尔兰和洛克的经验主义。叶芝念兹在兹的是“主人公要么处于必须在相互对立的本性和欲望之间抉择,以确认自我的关键时刻;要么已完善其人格,处于生命的尽头,等待转生到对立的存在状态。”(傅浩,1999b:195)
叶芝对《俄狄浦斯王》和《俄狄浦斯在克罗诺斯》念念不忘,正是由于索氏这两部剧作中体现出的“二元对立”(duality)。在《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展现出人类面临可怕灾祸时的勇气、坚韧和智性”;(Arkins,2011:444)在《俄狄浦斯在克罗诺斯》中,俄狄浦斯“经历超自然死亡,化身英雄,要求得到适当的尊崇”。(同上)对笃信贵族统治和古希腊智性的叶芝来说,俄狄浦斯是一个再完美不过的理想人物了:既拯救,又祸患;既是国王,又是乞丐;既知晓,又懵懂;既是侦探,又是罪犯;既为人民拥戴,又为人民驱逐。此时的叶芝,哲学观和创作观日臻成熟,在对索氏悲剧改编过程中深深刻上英雄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烙印。叶芝保留了《俄狄浦斯王》的核心情节,将1369-1415行俄狄浦斯的独白删去大半,大大弱化主人公自怨自艾的形象,增添其英雄主义气概。1927年9月12日,《俄狄浦斯在克罗诺斯》在阿贝剧院上演。相较《俄狄浦斯王》,叶芝对此剧的改动更为明显:“我想少些直译,多些现代气息,多用些俗语。”(Arkins,2011:445)对叶芝来说,剧中的场景更像是在爱尔兰,而非古希腊,而剧中垂垂老矣、苦觅归宿的俄狄浦斯正是在盎格鲁-爱尔兰族群夹缝中困顿和求索的自己。“准备将《俄狄浦斯在克罗诺斯》搬上阿贝剧院舞台之时,我发觉开场中复仇女神栖居的树林可以是爱尔兰任何一片神圣的树林;俄狄浦斯踏足其间,会感到一阵心悸,就像任何一个爱尔兰农民在高威(Galway)或者斯莱戈(Sligo)某片神秘的树林中那样”。(同上)叶芝删去剧尾安提戈涅对父亲之死的哀恸之辞,大力渲染俄狄浦斯之死的神秘气息和象征意义。“俄狄浦斯最终沟通了叶芝哲学体系中核心的对立面——圣人和战士,”(同上)完美实现了自身的艺术追求。叶芝对俄狄浦斯悲剧中的弑父主题也有挖掘和表现。《炼狱》中,破屋里过夜的父子对话,提起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父亲给儿子讲述自己的弑父经历,还宣称见到了父母的鬼魂。儿子起初不信,后来也看到了,恐惧至极。最终,父亲用同一把刀将自己的亲生逆子杀死。这部剧作象征意味浓厚,蕴含了作者晚年的性情和才思。叶芝一生致力于重写民族神话,恢复爱尔兰传统,以抵抗英国文学和文化。“叶芝坚持爱尔兰性与其他古代文学的特性是一致的,特别是古希腊传统,”(沈家乐,2013:60)要求爱尔兰从不列颠传统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转向欧洲和民间。《炼狱》剧中弑父又杀子的老人沉迷于改变历史进程的幻想之中,试图在舞台上谱写“种族净化的神话”,实现“另置和延宕”,“介入现实世界,诗意的旅行”。这一形象的内涵大大超出索氏剧中的俄狄浦斯,折射出叶芝在爱尔兰民族独立和文化自觉过程中对“理想”文化范式的界定和追求。
四 辛格对古希腊悲剧的重写
辛格是爱尔兰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过世前与叶芝、格雷戈里夫人共同经营阿贝剧院。如果说格雷戈里夫人是杰出的组织者,叶芝是激情的领路人,那么辛格就是坚定的实践者。辛格出生于都柏林郊区的拉什法恩海姆(Rathfarnham),两岁丧父,随母亲(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在严格的新教氛围中长大,幼年多病,酷爱大自然,14岁就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1889年,他考上都柏林三一学院学习语言和历史,因希伯来语和盖尔语成绩优秀得奖。1892年,他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爱尔兰皇家音乐学院,随后四年漫游欧洲,在意大利和法国学习音乐,在巴黎大学修习古爱尔兰语等课程,对凯尔特文明产生了浓厚兴趣。1896年,辛格在巴黎结识了叶芝和莫德·冈,后来参加了民族主义组织——爱尔兰联盟。叶芝劝辛格离开巴黎,重返爱尔兰,投身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辛格听从前者的建议,返回爱尔兰,走访西部的阿兰群岛(Aran Islands),观察当地居民的生活,于1901年完成旅行纪实《阿兰群岛》(The Aran Islands),描述自然风光和岛居生活,为后来的戏剧创作积攒了大量素材。1902年是辛格的“奇迹年”,他创作了《骑马下海人》(Riders to the Sea)、《峡谷的阴影》(The Shadow of the Glen)以及《补锅匠的婚礼》(The Tinker's Wedding)。“他在这些剧作中发现了自己的天赋,划定了自己的耕耘之地。”(Benson,1982:10)1904年,辛格成为阿贝剧院导演。1907年,辛格创作最具代表性的三幕喜剧《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由阿贝剧院上演,引起观众骚乱,遭到民族主义分子的强烈谴责。1909年,辛格在都柏林逝世,当时正在创作改编自爱尔兰古代爱情神话的《黛尔德的悲哀》(Deirdre of the Sorrows)。
作为盎格鲁-爱尔兰族群中的一员,辛格与叶芝一样,面临个人与社会认同的难题以及与生俱来的身份困境。作为新兴特权阶层作家(Ascendancy Writer),辛格一方面想要融入社会之中,另一方面又不想丢掉个人的价值观。“辛格向我们提出一个悖论,或者一个似是而非的悖论:虽孑然一身,却在剧作和纪实中始终关注社群和社群生活的意象。”(Watson,1994:35)辛格虽出生于统一主义者家庭,却因阅读广泛而突破宗教束缚,转向无神论,排斥不列颠传统,背离新教少数派(Protestant minority)。“逃离上帝王国后不久,我开始对爱尔兰王国产生兴趣。我的政治立场由满腔忠诚转向温和民族主义。爱尔兰的一切都变得神圣。”(Murray,1997:66)不过,辛格却不想为狭隘民族主义所约束,很快退出爱尔兰联盟,独立探寻自己的艺术之路。“我希望以自己的方式为爱尔兰的事业服务。要是混迹于革命和准军事运动之间,永远都无法做到这点。”(Murray,1997:67)辛格自己的方式就是扎根爱尔兰乡间,真实反映爱尔兰农民的生活状况,充分挖掘爱尔兰方言的独特魅力。与叶芝不同,辛格塑造了很多爱尔兰平民形象,其中有迷信粗暴的农民、道貌岸然的神父、无拘无束的流浪汉、无知谦卑的青年、敢爱敢恨的女性。辛格作品的剧情笑中带泪,发人深省,语言节奏感强,自然清新,甚至稍显粗野,将20世纪初的爱尔兰戏剧带至全新境界。
辛格向来对古典文学着迷,“就读三一学院第一年间(1888-1889),就喜欢阅读古希腊悲剧,对荷马也很感兴趣。”(Carpenter,1974:66)正是在学习古希腊语和古希腊文学的基础上,他开始研究爱尔兰语,挖掘爱尔兰神话和史诗。“希腊神话和凯尔特神话的对比研究增强了辛格对希腊和爱尔兰亲密关系的认识。”(Lloyd,2011:52)求学巴黎期间,辛格选修著名凯尔特学者儒本维尔(H. d’Arbois de Jubainville,1827-1910)的课程,研读其名著《爱尔兰神话记和凯尔特神话》(The Irish Mythological Cycle and Celtic Mythology),“确证了爱尔兰英雄文学在欧洲语境中的重要性。”(同上)辛格以阿兰群岛所见所闻为背景,融合爱尔兰神话和古希腊悲剧,刻画自然与社会中的个体命运,拓展爱尔兰戏剧题材,深入挖掘个人的生存境况和理想抉择。辛格自小孤僻、敏感,长年恶疾令其感悟生命的脆弱和死亡的迫近,也激发其“在超绝的野性的现实中产生欢快”。(陈恕,2011:173)辛格笔下的人物,无不面对死亡与欢快的夹击,无论接受还是反抗,都踏上从现实世界迈向理想世界的必经之路。“富有激情却不滥情,他总是用荒诞和粗野渲染悲怆,宁愿激赏全身心的悲痛,也不任由自己沉溺于造作的同情。”(Skelton,1971:171-172)辛格笔下最动人的角色要么踽踽独行,要么见斥社会,正是在孤立或者疏离之中,个性得以彰显,命运和抉择得以升华。“这不单是自觉的审美选择,特以反讽达至超脱,暧昧的语调也在不经意间透出辛格与整个文化语境的关系。”(Watson,1994:84-85)辛格与叶芝一样,本打算调和爱尔兰传统和不列颠传统,创造出“令人信服的社群意象”,最终却成全了“流浪汉艺术家”,完成了对爱尔兰生活的“误传”。
辛格并未直接改编古希腊悲剧,而是将其主题和情节融入自身创作之中。《黛尔德的悲哀》从《安提戈涅》和《特洛伊妇女》中获取灵感,描写年轻美貌的黛尔德勇敢追求爱情与幸福,不惜与代表威权和传统的康诺巴王决裂,最终在爱人墓前殉情。黛尔德与康诺巴王的对立,象征着自然天性和社会习俗的对立。在《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与克瑞翁针锋相对,誓死捍卫自然法(神律),不惜与城邦法为敌,也要安葬自己的兄长。两相比较,不难看出辛格对原剧主题的化用。黛尔德殉情的悲怆,与《特洛伊妇女》中女性的无尽哀思,都蕴含着剧作家对生命的哲学思考,对悲剧庄严、静穆之美的敬畏以及对人性尊严的呼告。《峡谷的阴影》反转欧里庇得斯名作《阿尔刻提斯》,塑造一个敢于跳出没有爱情的山谷,寻找自由天地的女性形象诺拉。辛格取材阿兰群岛当地故事,参考古罗马讽刺作家佩特洛尼乌斯(Titus Petronius Niger,c.27-66 AD)的喜剧故事 “以弗所的寡妇”(The Widow of Ephesus),向古希腊悲剧致敬。“尽管没有采用史诗手法,却炮制出古希腊悲剧也适用的苦涩困境。辛格利用所谓的喜剧,向我们表明:以弗所的寡妇也可以是一个值得同情甚至悲剧性的角色,充斥在古希腊悲剧间不可抗拒的命运同样可以笼罩威克洛郡的婚姻监牢。”(Skelton,1971:62-63)
《骑马下海人》一度为评论界视为辛格对古希腊悲剧最为成功的化用。该剧描写阿兰群岛上老妇玛丽,苦劝幼子巴特利别冒着暴风雨去大陆集市卖马,最终却只能承受再度丧子的悲惨命运。剧中刻意烘托神秘气氛,强调超自然因素,大量运用象征意象,将基督教信仰和前基督时期民俗熔于一炉,生动描绘出爱尔兰村庄的蔽塞、迷信与爱尔兰普通农妇的谦卑和坚韧。面对咄咄逼人的死亡和自然,老妇玛丽绝望地四处求助,却无济于事,最后只能默默地屈服,在儿子的葬礼洒上一掬痛心泪。玛丽的形象与《特洛伊妇女》中的特洛伊王后赫枯巴极其相似,都忍受着切肤之痛,眼看着亲人一个个死去。不同的是,辛格笔下的老妇“却无绝望之语,既非接受,也非顺从,而是默许甚至自我安慰”。(Benson,1982:62)在玛丽看来,活着就得倍受煎熬,死去倒是一种解脱。“我们还奢求什么?没人能够永生,我们真得满足了。”(Synge,1982:27)如果说俄狄浦斯是因为过失(harmartia)而遭逢不幸,玛丽及两个儿子则纯粹是莫测命运的牺牲品,是“替罪羊而非主角”。《骑马下海人》以爱尔兰为背景,表现爱尔兰农民之困厄,同时运用象征主义手法,提炼“死亡”作为主题,置换古希腊悲剧中人与神、命运之间的冲突,体现出形而上的虚无主义,为后世剧作家奥凯西、贝克特等留下丰厚的遗产。
《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历来众说纷纭,为评论家和研究者所重视。不堪忍受父亲威权,与其发生冲突并失手杀人的青年克里斯蒂·马洪逃至西海岸梅奥郡一个小村落,却意外成了当地人心中的英雄,得到酒店老板女儿佩格恩的青睐。孰料只受轻伤的父亲追来,戳穿儿子的谎言,最终两人扭打着离去。该剧具备古希腊悲剧的某些特点:单一地点、台上角色转述台下事件、剧情不超过24小时(间隔一晚)。第三幕中,辛格以人群代替歌队。该剧与《俄狄浦斯王》虽都包含弑父主题,却是对前者的反转:俄狄浦斯因弑父行为暴露身败名裂,马洪却因讲述弑父行为倍受膜拜。辛格在对古希腊悲剧的戏谑化处理中展现出独特的艺术构思,抽离索氏对命运和智识的探讨,代之以对长期受约束、压制人群潜意识中弑父情结的挖掘。两部剧作虽包含弑父主题,“却都发生在过去,只有通过语言重现;都以戏剧手法重现往事,继而打乱自然时序。”(Roche,2001:103-104)
当然,《俄狄浦斯王》中对往事的发掘通过侦探式调查完成,而马洪弑父的真相却由其父亲自揭开,极具讽刺效果,也增添了喜剧元素。此外,主角与周遭环境的关系也可资比较。“两部剧作都聚焦闯入的陌生人,因曾给荒芜土地带来全新生机的一次作为而被奉为救世主,最终却在真相公布后不容于世,无奈独自离去。”(Sullivan,1969:243)俄狄浦斯曾解开斯芬克斯谜题,拯救忒拜,终因弑父娶母给城邦带来瘟疫和灾祸,盲眼自逐;马洪宣称弑父,给长期蔽塞、沉闷的村民提供恣意想象和本性舒展的绝佳平台,却因被父亲戳穿谎言而遭耻笑和摈弃。《俄狄浦斯王》贯穿侦探式的双线结构,让主角在逼近事实的过程中经历情感和道德的双重煎熬。《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虽没有明显的剧情分支,却以马洪两度弑父为节点,描摹村民态度的转变,揭示深藏在行动和语言之下的两大主题:镜像与神话。马洪逃匿,其实是“害怕自己的影子,趋避阴暗、被抑制的自我”,(Kiberd,1995:185)无意间却成了村民们“建构神话”的素材和集体想象的“他者”。等到马洪为挽回尊严意欲再度弑父之时,村民们决然“消解神话”,“超我崛起,使自我重返文明”,(韦清琦,1997:83)硬要严惩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马洪历经破折,最终觉醒,“从被动状态中脱身而出,主动自我映射”,(Kiberd,1995:185)借用村民们虚拟出来的镜像实现自我认证。村民们将自我镜像投射到马洪身上,沉溺于对他者的操纵和对反自我(anti-self)的驱策,不愿或者不敢实现他者缺席(absence of the Other)和自我映射,终究囿于传统观念和集体意识,无法实现自我身份的澄清。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期间,民族独立的呼声日渐高涨,暴力手段大行其道,狭隘民族主义将爱尔兰的一切理想化,将英国镜像化为残忍和愚昧的他者,从而在对他者的贬斥和压制中实现民族身份的认同。辛格惯居爱尔兰,对爱尔兰普通民众了解甚深,欣赏其美德的同时也不讳言其缺点。他敏锐地察觉,“复兴主义者对往昔的膜拜实则基于可疑的动机,即予以控制和殖民”,(Kiberd,1995:187)希望看到 “爱尔兰人最终超越社会和文化的误导和限制,成为一群有思想,有见地的人”。(汪艳,2012:271)辛格借用弑父这一“试金石”,“让主流文化重回大地,与边缘文化进行一次面对面、平等的对话”,(陶郭虎,1997:101)以此还原真实的爱尔兰,“形成对自身的观念,而非作为他人的观念存在”。(Kiberd,1995:184)
五 奥凯西对古希腊悲剧的重写
与叶芝和辛格不同,奥凯西出生于劳工家庭,自幼因家贫和丧父而颠沛流离,生活拮据不堪。奥凯西因患眼疾,几乎未接受系统教育,一度目不识丁。13岁时,奥凯西才具备读写能力,14岁时开始四处工作谋生,当过演员、助教、铁路工人。1906年,奥凯西加入旨在恢复爱尔兰语言和文化的盖尔语联盟,学习爱尔兰语并将名字John Casey改为爱尔兰语的Sean O’Cathasaigh。1910年,奥凯西加入激进组织——爱尔兰共和兄弟会。1913年,奥凯西参加都柏林大罢工,翌年担任爱尔兰公民军(Irish Citizen Army)秘书,因对爱尔兰公民军军事化并与爱尔兰志愿军结盟不满而很快退出,也没有参加1916年复活节起义。1923年,阿贝剧院在四次拒绝奥凯西后,终于上演其新作《枪手的影子》(The Shadow of a Gunman),拉开双方合作的序幕。自从辛格去世后,阿贝剧院一直缺乏高质量的作品,惨淡经营,终借奥凯西的剧作复兴,其后相继上演《朱诺与孔雀》(Juno and the Paycock, 1924)、《犁与星》(The Plough and the Stars, 1926),并称奥凯西的“都柏林三部曲”。1928年,叶芝拒绝接收奥凯西交给阿贝剧院的第四部作品《银杯》(The Silver Tassie),批评后者将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胡乱糅合。奥凯西逐条加以反驳,与阿贝剧院分道扬镳,旅居英国。奥凯西中后期的作品熔铸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象征色彩浓厚,关注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和人性。二战之后,奥凯西重新将目光投向爱尔兰,“以讽刺、离奇和娱乐的方式来揭露当时爱尔兰社会的黑暗和保守势力对人类善良本性的压抑”,(陈恕,2011:193)目标直指商界和教会。奥凯西将悲剧和喜剧融为一体,运用多种戏剧技巧,力求如实展现民族苦难,深刻剖析民族劣根性,呼吁爱尔兰民众准确认识自身和民族生存状态,鼓励他们探寻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正确道路,堪称辛格之后爱尔兰最伟大的剧作家。
奥凯西酷爱阅读,涉猎广泛,尤喜《圣经》、莎士比亚、布希高勒、拉斯金、狄更斯和萧伯纳。贫民窟居住的亲身经历为其创作提供素材,新教信仰与天主教环境的冲突为其创作拓展视野,相依为命的慈母为其创作带来灵感。“激情和幻灭接踵而至,塑造其漫长的一生。”(Simmons,1983:3)奥凯西早年对宗教极富激情,曾在唱诗班中服务,还为教区长辩护,后来关心民族解放运动,投身民族主义的怀抱。“如果说民族主义驱逐了宗教,那么他当工人和组织工会之时,社会主义就驱逐了民族主义。”(Simmons,1983:6)奥凯西经历独立战争和内战,深悉战争的残暴和恐怖,这才写出以都柏林为背景、反映复活节起义、独立战争和内战的“都柏林三部曲”。奥凯西身处平民阶层且备尝艰辛,从不回避现实,以“近乎呆板的率直”审视都柏林贫民窟中的命运和人性,对爱尔兰性和爱尔兰民族身份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对都柏林市内酷似人间炼狱的贫民窟来说,“历史非关英雄命运或者神秘剧情,只见混乱不堪和漫无意义。”(Deane,1986:162)民族主义的光鲜外衣下,包裹着怯懦、自私、虚荣和投机,不再有为民族牺牲自己的凯瑟琳伯爵小姐,甚至没有相信自己是“一切战斗的胜利者”的马洪,只有“我早知道只要叩墙声一响,就会出事”的希尔兹。奥凯西往往对剧作中的男性大加讽刺和奚落,对女性却满是宽容和同情,通过人物性格的对比,揭示政治、战争的残酷及对人性的扼杀。“都柏林的男人们争相走上战场,捍卫名为胡里痕的凯瑟琳的抽象观念,却连自己家人和邻居都照顾不好。奥凯西对其男性幻想大加鞭笞,显露出摒弃所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的态度。”(Deane,1986:163)
《枪手的影子》描写诗人达沃林平素高谈阔论,吹嘘自己是共和军的枪手,却因在自己屋内发现一颗炸弹而惊慌失措,眼睁睁看着深爱自己的少女明尼用生命掩护自己。同屋希尔兹原是公民军积极分子,却也自私、懦弱,生怕明尼供出自己。奥凯西通过塑造两个硬充英雄的胆小鬼和一位敢于担当的少女形象,反衬某些民族解放运动参与者的浮夸和懦弱。达沃林生活潦倒,敏感软弱,却因怪异的生活习惯被当作共和军枪手。第一幕中其他角色对达沃林的迥异态度,反映出都柏林普通民众对民族主义者既膜拜又避忌的矛盾心理。同样,对他人的误会,达沃林的立场也极为暧昧:“艺术家式的精英观念与贫民窟居民强加的枪手形象彼此冲突。”(Murray,1997:100)虚荣心和投机欲使达沃林不愿说出真相,而其自命不凡的艺术家气质又不足以支撑和维系为众人所称道的英雄气概。奥凯西借达沃林之口多处摘引雪莱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借用这一经典古希腊神话形象,完成剧作中的互文指涉,增强讽刺效果,在爱尔兰贫民窟的闲言碎语和争闹不休中加重悲剧意味。“诗人将自己视作绝望处境中的高贵之士,捆缚于贫穷的岩石上无计可施。他对艺术和学识之爱可能是盗自天神的火种。”(Simmons,1983:45)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挑战宙斯强权,常被塑造成反抗暴政的义士。达沃林大谈诗歌,迷醉于充当英雄的幻想,到头来却只能靠明尼舍命相救,噤若寒蝉地藏身屋内,默默祈祷度过劫难。“剧情达到高潮,他成了失败者;作者以反英雄甚至直接譬喻的方式推动剧情,访客们成了定期折磨普罗米修斯/达沃林的复仇女神。”(Simmons,1983:47)与之相反,素来被邻里当作轻佻女子的明尼,却在最紧要关头牺牲自己,成了不折不扣的英雄。希尔兹戏称“公寓里住进了一个特洛伊的海伦”,警告达沃林别轻信明尼,显然断定她会“招来灾祸”,孰料最终却要靠这红颜祸水免去灾劫。如果说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让人击节赞叹,那么奥凯西笔下的达沃林就只能如影子般消逝在幻想的光环之中。
《犁与星》描述1916年复活节起义如何席卷各个阶层的爱尔兰人民,以此折射民族主义信念与爱尔兰平民生活的错位(dislocation)和疏离(estrangement)。起义军激战之时,伯吉斯与戈根太太却趁乱抢劫;诺拉因失去亲人而精神恍惚,男人们却兀自玩着牌戏;起义领导人慷慨激昂,号召人民为国家而战,岂料妓女路茜却嘟囔着抱怨战争令其生意冷清。奥凯西用对照手法,讽刺民族解放斗争的神圣意义,指出激进民族主义者罔顾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命运,只将抽象的政治教条和口号奉为金科玉律,普通民众则对所谓民族解放事业并不理解,最多当作争吵和打闹的由头。另一方面,诺拉和丈夫杰克的关系又为整部剧作增添了“希腊式”的悲剧意味。诺拉极力劝阻丈夫参加市民军战斗,迫使丈夫在战友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丈夫将爱尔兰放在妻子之前。这是真正的悲剧:宁死不生。面临选择时,这个爱尔兰男人接受了死亡(Thanatos),而非爱(Eros),至此生命之目的不复存在。”(Costello,1977:170)奥凯西虽然没有直接挪用古希腊悲剧主题和情节,却在两难的选择中“找希腊人帮忙”。
《朱诺与孔雀》以爱尔兰自由邦内战为背景,描绘城市劳工阶层在战争期间的混乱生活和矛盾心态。朱诺典出古希腊神话,本是女神赫拉的罗马名字,出行时每以孔雀驾车。该剧中的孔雀是女主角朱诺给丈夫博伊尔起的绰号,讽刺他自命不凡、游手好闲。一日,博伊尔听说自己有望继承一大笔遗产,便大肆挥霍起来。不料好梦落空,家里债台高筑,残疾儿子因出卖同志而被打死,朱诺带着遭人始乱终弃的女儿离家谋生,只留下酗酒发癫的博伊尔面对萧然四壁怨天尤人。该剧在刻画人物上极其成功,尤以被戏称为孔雀的博伊尔最佳。博伊尔逃避现实,吹牛酗酒,却在妻子面前唯唯诺诺,装腔作势。与阿伽门农相比,博伊尔同样狂妄自大,却少了一份威严,多了几许滑稽。阿伽门农的悲剧命运早由卡珊德拉预示,带有古希腊悲剧式的命定色彩,博伊尔却始终游戏人生,插科打诨,在不经意间“冲淡了悲剧气氛,使我们暂时忘却了痛苦和悲哀”。(孙敏,1997:144)“可怕与绝望于大笑中得到了宣泄,以这种奇特的方式,我们获得了严肃悲剧的净化和升华。”(同上) 奥凯西在都柏林三部曲中,巧妙化用古希腊悲剧主题和技法,结合爱尔兰民族语言和喜剧传统,坚持在艺术创新的道路上探索,为后世剧作家留下了宝贵遗产。贝克特曾经如是评论《朱诺与孔雀》:“这是奥凯西最好的作品,因为它充分展现出这种戏剧式的开裂(dehiscence),思想和世界分崩离析,再难拼合。”(Luckhurst,2008:130)都柏林三部曲中,“政治药方总显得比社会疾患更糟糕”。(Richards,2004:138)奥凯西关注都柏林的城市生活,探讨历史、政治、宗教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解构叶芝和辛格各自创建起来的“爱尔兰乡间神话”(Irish folklore)和民族主义,“令爱尔兰观众震惊,逼迫他们质疑渗透在公众生活各个层面中的政治遗产、宗教信仰以及对国家顶礼膜拜的民族主义态度。”(Luckhurst,2008:125)
六 结语
三位杰出的剧作家,再加上意识流大师詹姆斯·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1882-1941),构成了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文学图景。研究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观照现实与历史如何相互荡击,艺术与理想如何相互砥砺,可以在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和流派中一窥爱尔兰民族身份和爱尔兰文学特性如何构建起来。“一些密切相关的次主题复现:对农民和爱尔兰落后状况的态度,对充满活力却能毁灭一切的民族主义的态度,对英雄和英雄主义理想的态度,对爱尔兰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理解,还有作者与社会认同之渴望与边际孤立感之间张力的时常涌现”。(Watson,1994:13)
叶芝重写俄狄浦斯神话,浸透着贵族艺术的孤傲和理想主义的萧索。辛格翻转俄狄浦斯神话,剖析爱尔兰民众的深层心理和集体意识,在认同与决裂之间聆听“野性的呼唤”。奥凯西直面残酷现实,剥离古希腊神话和悲剧的生存意义,将其荒诞和虚无质性推向极致。三位剧作家置身爱尔兰文艺复兴浪潮,面对相似的境况和抉择:爱尔兰文化遗产消失殆尽,如何构建当下的爱尔兰性(Irishness)?构建爱尔兰神话以对抗英国殖民者固然是条捷径,却无助于国家独立和政治热潮消退后的文化自觉,也无益于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借鉴和改装欧洲大陆传统,又受制于英国戏剧的熏染和约束。既然凯尔特神话与古希腊神话同样悠久,爱尔兰古典教育的传统醇厚绵长,重写古希腊悲剧,搭建异质空间,吸引更多的民众反思和对话,无疑是最佳选择。叶芝、辛格、奥凯西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古希腊,打磨和淬炼各自的戏剧艺术,探索和衍生爱尔兰新时期的文学特性,终于结出丰硕成果,为整个20世纪爱尔兰戏剧的繁荣揭开了序幕。
[1] Arkins,Brian. 1990. Builders of My Soul: Greek and Roman Themes in Yeats.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Books.
[2] Arkins,Brian. 2011. The Duality of Oedipus in Yea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vol. 18.
[3] Benson, Eugene. 1982. Macmillan Modern Dramatists: J. M. Synge.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4] Carpenter, A. 1974. My Uncle John: Edward Stephens's Life of J. M. Syn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Costello, Peter.1977.The Heart Grown Brutal: The Irish Revolution in Literature from Parnell to the Death of Yeats 1871-1939. Dublin: Gill and Macmillan.
[6] Deane, Seamus. 1986. A Short History of Irish Literature. London: Century Hutchinson Publishing Group.
[7] Ferriter, Diarmaid. 2004. The Transformation of Ireland: 1900-2000. London: Profile Books Limited.
[8] Friel, Brian. 1984. Translation, in Selected Plays of Brian Friel. London: Faber & Faber.
[9] Gregory,Lady. 1972. Our Irish Theatre. Gerrards Cross: Colin Smythe.
[10] Kiberd, Declan. 1995. Inventing Irel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Modern N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1] Lloyd,Michael. 2011. Playboy of the ancient world? Synge and the classics,Classics Ireland, vol. 18.
[12] Luckhurst, Mary. 2008. A Companion to Modern British and Irish Drama: 1880-2005. Malden: Wiley-Blackwell.
[13] Macintosh, Fiona. 1994. Dying Acts: Death in Ancient Greek and Modern Irish Tragic Drama. Cork: Cork University Press.
[14] Mansergh, Nicholas. 1965. The Irish Question: 1840-1921.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5] Murray, Christopher. 1997. Twentieth-Century Irish Drama: Mirror up to Nation.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6] Renan, Ernest. 2010. The Poetry of the Celtic Races and Other Studies, Translated by William G. Hutchison, Whitefish. MT: Kessinger Publishing.
[17] Richards, Shaun. 2004.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wentieth Century Irish Dra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 Roche,Anthony. 2001. “Oedipus at the Abbey”, Classics Ireland, vol. 8.
[19] Simmons, James. 1983. Macmillan Modern Dramatists: Sean O'Casey.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20] Skelton, Robin. 1971. The Writing of J. M. Synge.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21] Sullivan,M. R. 1969. Synge, Sophocles, and the Unmaking of Myth, Modern Drama, vol.12.
[22] Synge, J. M. 1982. Collected Works: Plays Book 1, Ann Saddlemyer (ed.). Washington, D. 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3] Walsh, Townsend. 1915. The Career of Dion Boucicault. New York: Dunlap Society.
[24] Watson, G. J. 1994. Irish Identity and the Literary Revival: Synge, Yeats, Joyce and O'Casey. Washington, D. 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5] Younger, Kelly. 2001. Irish Adaptations of Greek Tragedies: Dionysus in Ireland. Lewiston: Edwin Mellen Press.
[26] 陈恕:《爱尔兰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7] 傅浩:《叶芝的戏剧实验》,《外国文学》1999年第3期。
[28] 傅浩:《叶芝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9] 傅浩:《叶芝的神秘哲学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30] 罗朗:《三条道路:论爱尔兰的戏剧复兴运动》,《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31] 沈家乐:《面具、中间境遇与世界图景——叶芝戏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3年。
[32] 孙柏:《叶芝的戏剧理念:去殖民化的诗学》,《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33] 孙敏:《试析奥凯西的悲喜剧手法》,《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34] 陶郭虎:《从内容到形式的一次文化对话——重读“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
[35] 汪艳:《民族的自我认识历程——从镜像理论的视角重读“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论坛集萃》2012年第8期。
[36] 韦清琦:《本我的暴动,超我的觉醒——新评约翰·辛格“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
Celtic Twilight Beside the Aegean Sea:
Irish Appropriation of Greek Tragedy During Irish Literary Revival
Yin Sheng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Irish literature has been borrowing from Greek and Roman literature for ages and Irish drama has been in the course of appropriation of Greek Tragedy all through the 20th century to grapple with contemporary Irish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literary landscape of Irish drama during Irish Literary Revival and explore into the Irish national identity and literary features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practices of W. B. Yeats, J. M. Synge and Sean O’Casey in appropriation of Greek Tragedy.
Irish Literary Revival; appropriation of Greek Tragedy; Yeats; J. M. Synge;Sean O’Casey
尹晟(1982—),男,汉族,四川成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教师。研究方向: 翻译研究、古希腊文学研究、英语教学法等。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05号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100048)。Email:tomsword@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