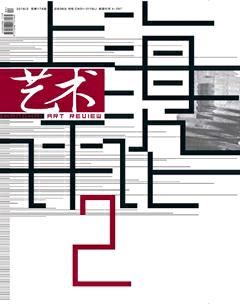渐行渐远的亚洲当代戏剧
孙晓星
本文在亚洲一衣带水的文化语境中、以富有“拼贴”般图像意味的视角将中国和日本戏剧进行对比,并将之置身于上世纪6 0年代以来全球的政治、社会变革的大浪潮中,观察中日戏剧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与思考,并落脚于中国当代戏剧发展的问题剖析。
在东京的剧场里,总想寻找某些与中国戏剧相似的东西,也会思考日本和中国究竟哪一个更接近“亚洲”。2015年10月,铃木忠志以古北水镇长城为背景演出《酒神》,是一幅别具意味的图像,这样的拼贴恰如日本戏剧与中国异样的相遇;同一月,日本东京国际剧场艺术节(2015)开幕,一批“后铃木忠志”时代的戏剧作品接连发表,呈现出并非日中共享着的“当代”。如果说现代日本戏剧与中国戏剧尚处在相似的起点,到了21世纪,前者仿佛已经演化或变异成全新的物种,而实际上,当代日本戏剧与中国戏剧正在渐行渐远。
舞踏vs样板戏
首先,我们要选取一个节点将上世纪60年代作为“当代”的开始,原因是在这个节点上,悉数国家同步卷入了左翼运动的浪潮:从美国的反战与嬉皮士、法国的情境主义国际与五月风暴,到日本的安保斗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其行动主体大多是年轻人,同一时期伴随着政治运动出现的还有新文化的涌现:比如美国摇滚乐、法国新浪潮电影、日本前卫剧场、中国样板戏,它们都不是“纯艺术”,而是带有鲜明的、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反叛”是共同的关键词,但其对象、媒介与策略各不相同。
从这个时间节点上开始讨论当代日本戏剧与中国戏剧,借由“反叛”可以寻找到一个相互比较的交叉点。日本的反安保是反对每隔十年签订一次的《日美安保条约》(以下简称安保条约),该条约也是日本处于美国附属地位的象征;随后,日本国内掀起了战后最大的社会运动即安保斗争。如果说日本的安保斗争所排斥的对象更多是外敌的话,那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为内斗——反资产阶级,即反右派斗争。在上述背景中,该时期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舞台表演艺术——日本的舞踏与中国的样板戏,其“反叛”也具有差异。
日本舞踏在诞生初期被称作“暗黑舞踏”,得名于土方巽的《禁色》以一段黑暗中演员追逐的脚步声结束,作品包含杀活鸡、同性禁忌等场面,也几乎见不到“舞蹈”的成分,于是《禁色》在全日本舞蹈协会新人舞蹈竞赛上发表后,土方巽便遭到了日本舞蹈界的除名。但被边缘化的土方巽却收获了一批追随者,与几乎同步进行舞踏创作的大野一雄开启了日本舞踏的纪元,改变日本舞蹈的未来,甚至横向影响了同时代的日本前卫剧场,比如寺山修司等人。
舞踏“反叛”的对象首先是西方芭蕾的身体造型,从古典芭蕾到鲁道夫·范·拉邦奠基的现代舞,其动力领域是人类如高塔一般地直立,以人的四肢延展和滞空跳跃为美感系数。而舞踏几乎采取了相反的造型,从外观上看,舞踏演员的躯体佝偻扭曲,重心下沉,站姿怪异夸张,面部狰狞,服装有时也十分浮夸艳俗,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实在毫无美感可言,不过一旦将它们放回土方巽等人开创舞踏这种特殊表演的语境中,便可以获得熟悉的辨识,它们是东北寒冷的气候下,农民在田地里的站姿、传统歌舞伎表演中的“隈取”(kumadori,脸谱化妆)、见世物小屋和落语剧场等,抽空意义挪用或转化为舞踏表演里的身体内缩、蟹形脚(重量悬在双脚的外侧)、恶见型(beshimi,被压抑的情感经过活的“隈取”的凝结)、嘉年华式的狂欢祭祀游行等。
以上这些都是回溯日本前现代的剧场和社会图景,“反叛”对由西方刺激明治维新以来所产生的现代剧场,它们包括西方的芭蕾和现代舞、被上层化和高雅化的现代歌舞伎,甚或被压抑的“日本性”,而这些倾向同样反映到日本前卫剧场运动中。这种“反叛”酝酿于60年代到来之前的整个氛围,而借由安保斗争步入高潮,彻底清算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逐渐影响日本的西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全球化。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都会知道,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主要社会矛盾已经转移为国内的阶级矛盾,这从1949年之后的大陆十七年戏剧中就可以观察到,它们描写“工农兵”题材,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而在这三种类型之外的人物就成了被直接或间接批判、贬损、轻视的对象。这一内容到了60年代达到高潮,并且找到了更匹配的形式,它是从时装新戏到国剧这一20世纪开始受西方表演艺术刺激并试图弥合东西方风格的探索的结果,即一种“完美”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就是样板戏。
与日本舞踏不同,它是一场自上而下发动的革命艺术运动,与土方巽被舞蹈界除名的命运相反,样板戏通过江青由权力阶层向全国范围推广,进而成为了所有舞台表演艺术的专断权威,即由官方强行植入民间的文化意识形态。国内主要矛盾的不同,又使样板戏对西方话剧、芭蕾等表演艺术形式不采取排斥的态度,而是吸收融入,成就了一种特殊的美学符号间的杂糅。
“翻身”是样板戏中一个重要的身体动机,即来自于“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典故,因此它并不反对被日本舞踏弃绝的直立的身体造型,反而可能会“嫌”直立得还不够,因此像作为芭蕾舞剧的《红色娘子军》,其中女红军们的脚尖功夫使身体得以高高挺立,而手上紧握拳头与天斗与地斗的上半身塑形消除了既往《天鹅湖》里天鹅柔弱项颈的印象。这种“握拳”再加上挺身和瞪眼就是在《红灯记》里面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三个代表共产党老、中、青典型人物的武生亮相,塑造成一具具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代言的雕像。因此可见,无论是一场艺术运动的发源,还是“反叛”的对象,日本舞踏和中国样板戏都具有极大的差异,其背景是国内面临主要矛盾的差异,进而涉及两种舞台表演艺术的态度立场和形式的差异,前者是站在反西方现代性的角度汲取前现代剧场中具有颠覆性的元素和力量,后者则采取一种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化激进策略,一个是回溯,一个是企图超越。
剧本创作口语化vs即兴发挥口语化
进入80年代,这一时期的主题是“告别革命”。在经历过60、70年代的革命浪潮之后,悉数国家的左翼运动都以“失败”告终,苏联濒临解体,社会主义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西方国家所有激进艺术样式几乎都不可避免地变成文化消费的一部分,丧失了其革命的初衷,比如摇滚乐,比如剧场。中国相对迟钝,因市场化尚未成熟和彻底,在经历了“文革”后的创伤文学与第二次社会问题剧阶段,中国戏剧开始了一条与实验、探索相关的道路,林兆华导演、高行健和刘会远编剧的《绝对信号》作为标志事件,开启了中国小剧场运动,这比日本晚了二十年。在这个时期,日本第一代前卫剧场运动的主将们已经悉数获得了国际声誉,其中最成功的就是铃木忠志,而中国尚未向世界提供一台有分量的当代戏剧作品。
也是在中国小剧场运动开始以后,加上逐步恢复的社会空间,戏剧创作者开始分为官方与民间两个阵营,前者依旧承担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定制功能,后者以牟森和张献等人为代表,努力开拓实验戏剧创作与演出的疆域。此时,中国戏剧尚未面临商业化的危机,顶多是在国家剧场的挤压下寻求更多新的空间。进入经济泡沫时期的日本戏剧则不同,为夺人眼球的橱窗式戏剧比比皆是,抵御消费剧场的侵蚀便成为创作无法回避的任务,其中一个代表就是日本的第三代戏剧导演平田织佐。
平田织佐从80年代至90年代相继提出了“安静戏剧”和现代口语化理论,前者恢复了戏剧舞台上的日常生活,借此反拨商业舞台上那种表面喧闹、虚假的戏剧性场面,因此他的作品会出现长时间的静默、低声细语、同步多组的对话和背台演员等,而他也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第一代戏剧导演铃木忠志在剧场中寻找“日本人”的使命和出发点,认为西方现代戏剧污染了日本戏剧,使演员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交流方式,进一步就是他基于日本人的语言习惯提出的现代口语化理论。
在同一时期,中国戏剧舞台上有两种语言,一种是官方剧场为继续宏大的革命叙事所采取的胸腔共鸣式的发声方法,一般是某个被浪漫化、神格化的英雄人物在高潮段落于台口附近的位置,发出慷慨激昂的演讲或独白,将个人献祭于某个脱离了当下情境的集体历史使命;另一种是实验戏剧逐渐回归日常生活的个人叙事的口语,由台词转变为说话,譬如牟森导演的《零档案》中,担当演员的吴文光站在一台声音装置前追述自己的父亲,该剧也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当代中国戏剧作品在90年代享誉国际。
牟森的《零档案》回应了一个世界戏剧的现况,即回归在地性的个体经验,而它的载体就是口语,平田织佐也是,然而两者还是稍有差别,因为平田织佐的口语化建立在先期创作的剧本上,牟森的口语化则是演员口述的即兴发挥。这种语言问题可以追述到20世纪初的中国白话文运动,相对于书面的文言文,它是一次口语化革命,口语化无论是在现在和未来都会成为中国所有跟语言文字相关的艺术创作无法绕开的问题。
自我边缘化vs中国少年梦
还有一个问题,延伸自80年代开始的“告别革命”的主题,即戏剧的去意识形态化与意识形态化的角力。牟森等人的实验戏剧明显都是在以某种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去回应意识形态问题,这也成为了解构宏大叙事和敏感现实题材的共识性方案。“告别革命”其实是告别一种简单的对抗关系,避免被裹挟进革命对象的逻辑,张献曾明确地提出“成为自己”就是最好的“对抗”,日本的第一代戏剧导演也大多放弃了业已失效的先前“反叛”的姿态。但另一方面,这种去意识形态化或去政治化的方案在21世纪同中国日趋成熟的消费社会合谋,成为一个被新左派批评的理由,以及欧洲前卫戏剧的左翼传统回潮又使得“够不够政治”成为评判好坏的标准,当这股潮流刮入中国戏剧界就是一种再意识形态化或再政治化戏剧的复苏,张广天复活战时活报剧形式的《切·格瓦拉》与近几年流行起来的纪录剧场就是它的实例。
冈田利规是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日本最重要的戏剧导演之一,他有一部作品《三月的五天间》曾获岸田国士戏曲奖,故事发生在美军向伊拉克发动战争的2003年,“三月”一对演唱会上认识的青年男女在情人旅店住下,一起度过了“五天”,战争和抗议的游行只是无关痛痒的背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临时情侣五天后连名字都没有问就分别了。这似乎是日本当下年轻人状态的一个横切面,即不关心政治,只关注个人的愉悦,连交谈都是吞吞吐吐、断断续续,某种“嫌麻烦”的交往困难,在发生肉体关系后连彼此名字都不想知道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其实是把自己彻底疏离于社会关系之外。冈田利规的剧团叫chelfitsch,是一个自造词,包含自私的意思,按照他的说法反映了日本当下年轻人的状态,虽然冈田利规采取悬置批判性的立场,但这种把社会关在窗外的现象正趋于普遍的现实却不可否认。
类似的作品还有三浦大辅的《梦之城堡》,将深度宅的青年男女以及他们生活现场的“堕落部屋”(源于某偶像团体对女生宿舍“壮观”场面的形容,“堕落”有深陷在自己的欲望与兴趣的意思)当做现成品放进剧场,演员挤在同一屋檐下,躺在地板上堆积的衣服中打滚,吃超市的便当,打电动游戏,做爱,以及发生口角,一副十足的当代河边乞食者(kawara mono)形象,自我边缘化的极端就是彻底从社会场景中消失的自我流放。
然而,当代中国戏剧几乎还不具备处理青年亚文化的能力,顶多是在一种长辈训诫式的口吻下,解决一系列伪成长困境,其水平尚停留在社会问题剧的阶段,最终主流意识形态导向一系列中国少年梦,没有看见或遮蔽他们与当下社会范式之间的根本矛盾。
同时,某种理想化的身体造型迷思仍然萦绕在大部分中国戏剧创作者的脑海,其表现为对“训练”的痴迷,譬如铃木忠志方法、梅耶荷德方法等,这些20世纪大师的训练方法和视频资料流传于戏剧从业者之间,并成为炙手可热的讯息,它们都是要将演员的身体训练成彻底反日常的理想模型,其背后是一种身体力行的修炼,实为践行理想生活的苦行。其最大的问题,是对“好”的作品有同质化且排异的品味,并自恃戏剧有能改变现实的功效。
而当代日本戏剧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现状,戏剧的概念也极为开放,与诸多其他媒介艺术家的合作,使得戏剧在整个当代艺术领域获得了尊重并不断地发生演化和变异,观众就像对待街头上的奇装异服者一样,早就见怪不怪,甚至年轻人之间穿得与别人相似才是一件令人羞惭的事情。也是这种寻求差异性而非相似性的出发点,使当代日本戏剧如块茎一般生长,而当代中国戏剧却依然在一条非此即彼的道路上。
20世纪初,李叔同等人在日本成立了春柳社,进而影响中国现代戏剧的进程,但历史的隔膜又使彼此失去了对对方的了解,几乎同步引进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两个国家,现在却处于完全不同的“当代”。21世纪,有必要重新进入日本戏剧发生的现场,从而返回当代亚洲戏剧共同的进程中。